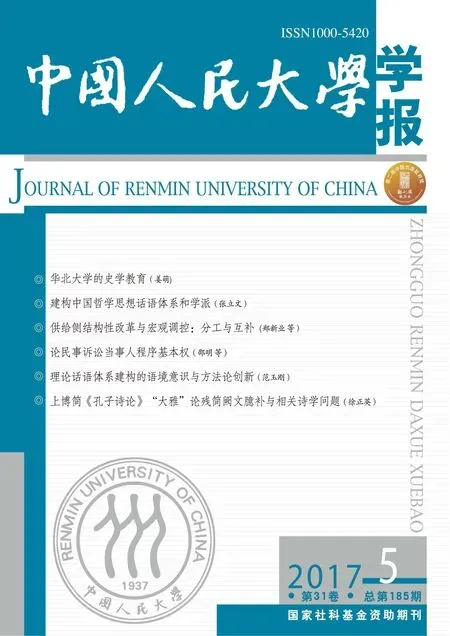论法律解释的实事求是法
韩立余
论法律解释的实事求是法
韩立余
法律解释是争端解决过程中对相关法律规则范围和内容的澄清。在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实践中,专家组特别是上诉机构在遵循一般解释原则的基础上,为实现争端的满意解决,基于争议的特定事实对法律规则进行“实事求是”的解释,建立抽象规则与鲜活事实之间的关联性和参照性。作为一种应用性解释,实事求是解释法以传统的文本解释方法为基础,对传统的文本解释方法予以补充,促进争端的积极和满意解决。国内争端解决实践中实际上也存在这种实事求是解释法,即基于个案事实来寻求三段论推论中的大前提。
世贸争端;法律解释;个案事实;实事求是法
法律解释是争端解决过程中对相关法律规则范围和内容的澄清,对于认定争议措施是否违反法律要求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法律规则的概括性和抽象性以及语言表达的局限性及歧义性,决定了个案争端解决中对法律进行解释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国内外的法律从业人员已就法律解释应遵循的一般原则达成了某种共识,总结出了多种解释方法,这些原则和方法为以解决争端为目的的法律解释提供了指导和工具。但这些原则和方法,主要集中于以文本为基础的文本解释,较少关注个案争端解决中的具体事实,这与法律解释不应脱离案件事实的认知相矛盾,应当肯定个案事实对法律解释的不可替代作用。
本文以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实践为基础,探讨审理案件的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争端解决中的法律解释。①《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第9条规定了部长级会议和总理事会对世贸规则的解释。这种解释相当于立法解释,与争端解决中的解释不同。这种解释的目的是在争端解决过程中处理争端,性质上属于国内学者所指的“与司法裁判过程中的法律适用相联系的活动”[1](P49)。通过对专家组和上诉机构适用一般解释原则实践的考察可以发现,专家组特别是上诉机构在解释规则时,除遵循文本解释的诸方法外,还纳入了争议案件的事实性要素,基于争议案件的特定事实澄清相关规则。本文称其为“实事求是法”。以此为启示,本文对国内争端解决中的法律解释进行考察发现,在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框架下存在的法律解释的实事求是法,并不独存于这一国际争端解决机制本身,国内争端解决法律解释中也存在这样的方法。
一、世贸规则的实事求是解释法
(一)世贸规则解释的一般原则与实践
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谅解》(以下简称《谅解》)建立的争端解决机制,用于保护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享有的权利、监督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的义务履行,为世界贸易组织这一多边贸易体制提供了可靠性和可预期性。《谅解》设立的争端解决机构负责实施争端解决规则和程序,设立专家组并通过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报告,监督裁决和建议的执行,授权中止适用减让或其他义务。争端解决机构基于反向共识方式(即一票通过式或准自动通过式)通过的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报告中的建议和裁决,构成了争端解决机构的建议和裁决。世界贸易组织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对法律规则的解释,因之成为该争端解决机制下争端解决机构对规则的解释。鉴于上诉机构承担的对专家组做出的法律结论和法律解释进行审查的职责,因此,上诉机构对规则的法律解释构成对规则的实质意义上的权威解释。
《谅解》要求依照国际公法的习惯解释原则澄清世界贸易组织的现有规则。《谅解》同时要求争端解决机构提出的建议和裁决,应依照相关权利义务,实现争端的满意解决;不能增加或减少世界贸易组织适用协定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争端的所有解决办法,应与相关协定相一致,不得使任何成员依据这些协定享有的利益丧失或受损,也不得妨碍这些目标的实现。*参见《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谅解》第2条和第3条。这些要求是专家组和上诉机构解释规则应遵循的原则。《谅解》要求依据国际公法的习惯解释原则澄清现有协定,但它没有说国际公法的习惯解释原则是什么。上诉机构在其审理的第一个案件美国汽油案中指出,《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第1款获得了国际公法的习惯解释原则的地位,该规定是条约解释基本原则最权威、最明确的表述。[2](P17)在随后的案件中,上诉机构进一步将这一原则扩大到《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整个第31条(解释通则)、32条(补充材料)和第33条(多种文字)的规定。*参见Japan-Alcoholic Beverages II, WT/DS8/AB/R, p.10; US-Soft Lumber, WT/DS257/AB/R, para.59, p.22.
在争端解决实践中,最常用的是《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规定的解释通则,其中第31条第1款最为重要:“条约应依其用语按其上下文并参照目的及宗旨所具有之通常含义,善意解释之。”*第31条第2款和第3款是有关上下文的进一步界定。“上下文”是《维也纳条约法公约》中文文本对context的中译。国内著作中多使用“语境”一词。该款列出了规则解释应考察的要素,包括用语、通常含义、上下文、条约目标与宗旨。上诉机构在美国虾案中指出了这些要素之间的关系:“条约解释者必须首先从需要解释的特定条款开始,并集中于这一条款。正是在构成该条款的、基于上下文来理解的用语中,来寻求条约缔约方的目标和宗旨。当条文本身赋予的含义有歧义或不确定时,或者需要确认条文本身理解的正确性时,可以从条约的整个目标和宗旨来寻求有用的指导。”[3](P42)就文本解释和目的解释而言,由于世界贸易组织规则谈判和减让谈判的一揽子承诺特点,相对于目的解释,上诉机构主要采取文本解释,探求条文文本表达出的缔约方的共同意图。在具体方法上,上诉机构提出并适用了有效解释、体系解释、协调解释、统一解释、演变解释等方法。*参见US-Gasoline, WT/DS2/AB/R, p.23; EU-Large Civil Aircraft, WT/DS316/AB/R, para.845, p.362; Argentina-Safeguard, WT/DS121/AB/R, para.81, p.27; China-Publication, WT/DS363/AB/R, para.348, p.145; US-Shrimp, WT/DS58/AB/R, para.130, p.48.
从争端解决机制角度看,个案解释是世界贸易组织规则解释的一大特点。换言之,专家组和上诉机构不能“法官造法”。*也有国内学者发文认为争端解决机构可以造法。参见齐飞:《WTO争端解决机构的造法》,载《中国社会科学》,2012(2)。根据《谅解》,如专家组或上诉机构认定某一成员的措施违反了某一适用协定,应建议该成员使其措施符合相关协定的要求;该裁决或建议不能增加或减少适用协定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参见《谅解》第3条第2款,第19条第1款和第2款。上诉机构针对1947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框架下通过的专家组报告指出,“已通过的专家组报告,除了解决争端方的特定争端外,没有约束力。专家组报告的性质和法律地位并没有因为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的生效而变化。”[4](P13)对于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上诉报告,也是如此。*参见US-Shrimp, Recourse to Article 21.5, WT/DS58/AB/RW, paras.108-109; US-Stainless Steel from Mexico, WT/DS344/AB/R, para.158, p.66.这意味着,在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中,尽管存在着二审机制,存在着上诉机构对专家组报告的审查,但法律上并不存在英美法系中的“遵循先例制度”,只是从促进争端的“积极”而“满意”解决这一目的而言*参见《谅解》第3条第4款和第7款。,从设立上诉机构审查专家组报告的法律解释或结论的角度来说,专家组不能“自由无视争端解决机构在此之前通过的上诉机构报告所含的法律解释和判决理由”[5](P66)。“上诉机构的存在就是为了澄清适用协定的含义”[6](P121)。上诉机构的上诉审地位导致了专家组对上诉机构法律解释的事实上的而非法律义务上的尊重(同案同判),但没有改变上诉机构不能造法的底线(个案解释)。
专家组在审理案件中,既要认定事实又要适用法律,事实与法律兼顾,而个案解释决定了上诉机构在每一案件中都需要结合争议措施对相关条款进行重新解释,从而为上诉机构采取实事求是解释法奠定基础。
(二)实事求是解释法的确立
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指出:“解释,按《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谅解》第3条第2款的预期,就是根据国际公法的习惯解释规则阐明相关条款的范围和含义。”[7](P67)范围和含义的释明,只有基于案件具体事实才可以逐步认清法律规则的基本轮廓。“面对无穷的、不断变化的、真实世界真实案件中的真实事实,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并非那么僵硬或无灵活性,而不给充满理据的判决留出空间。”[8](P31)真实世界、真实案件和真实事实,是争端解决者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解释规则所必须考量的因素。
《谅解》第11条规定了专家组协助争端解决机构履行职责。具体而言,专家组应对其审议的事项进行客观评估,协助争端解决机构提出建议或做出裁决。所谓客观评估,包括对案件事实的客观评估、对相关协定适用性的客观评估,以及对争议措施与相关协定一致性的客观评估。换个表述,专家组负责事实认定、法律解释和法律应用。对相关协定适用性的评估,是对某一协定对案件争议事实是否适用的评估。这首先需要根据案件争议事实,建立相关协定与案件争议事实之间的关联性。面对个案的鲜活事实,争端解决过程中的法律解释,不再是抽象的解释,而是针对案件事实的解释。在这一解释过程中,既含有法律的成分,又含有事实的成分。这就是实事求是法。这种方法将前述事实认定、法律解释、法律适用密切地结合起来,而非三个相互脱离的、机械性的过程。在完成法律解释、确定相关协定的适用性后,再进一步评估确定争议措施是否违反了适用协定的要求。由于适用协定的含义,包括适用条件、构成要素等,已经先期解决,因此,对是否违法的评估认定要相对简单一些。
上诉机构只审查法律问题,不审查事实问题。这似乎表明上诉机构的法律解释与事实无关。但上诉机构指出:“某一具体事实或一组事实与具体条约条款要求的一致性或不符,是法律定性问题,是一个法律问题。”[9](P51)这样就将事实认定与法律解释联系起来。同专家组一样,上诉机构在解释法律时,也需要用事实这一“照明灯”来探照法律规则的“真面目”。
实事求是,借用毛泽东的定义,是从“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去研究“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10](P801)。在此,可以理解为从面对的争议事实中找出适用法律的含义。这需要在解释法律时左顾右盼、相互参照法律和事实,以案件事实这一“有色眼镜”去看法律、找含义,大有“弱水三千只取瓢饮”的态势。这是一个基于案件事实探寻和识别法律可能性含义的过程。“‘解释’某一文字系指:在诸多说明可能性中,基于多种考量,认为其中之一于此恰恰是‘适当的’,因此决定选择此种。”[11](P85)案件事实就是此处所说的考量因素。实事求是解释法的功能,是在众多的通常含义中找到与案件有关的具体含义,使抽象概念落实到具体对象,从而确定相关规则规范是否涵盖特定争议案件的争议措施(包括事实和诉求)。案件事实就像是一块基石,奠定了审理案件的法官所做解释的基础,同时案件事实又像是一张天网,罩住了解释者所做解释的边界。基于案件事实解释法律,避免了解释者漫无边际的奇思怪想和不着边际的想入非非,将解释者约束在争端解决者的位置和职责上。
举例来说,一广场立有“禁止车辆入内”的标志。此处的“车辆”包括哪些类型的车辆?如果抽象来解释,可能会罗列多种车辆,但未必有确定的答案。但如果面临的问题是自行车能否进入广场,结果则大不相同。此时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第一,自行车是否此处所说的“车辆”?第二,此处的“车辆”是否包括自行车?在这一解释过程中,“车辆”与“自行车”建立了联系。火车显然不在此处的考虑范围之内,但如果广场内有一铁轨,这一事实会立即使解释者联想到火车。这种联想和相互参照就是法律解释实事求是法的体现。
上述实事求是解释法在世界贸易组织欧共体鸡块案上诉机构报告中得到了最明确的表述:“条约用语的通常含义,必须根据每一案件的特定事实来确定。重要的是,条约用语的通常含义必须‘基于存在的相关情形以当事人所使用的用语表达的’当事人的意图来考察。”[12](P69)在该案中,专家组在解释“salted”这一用语的通常含义时,先审查了这一用语的通常含义,又以“考虑通常含义的事实语境/上下文”为题,审查了另外三项因素,即欧盟减让表包括的产品、产品的物理特征及“腌渍”。专家组在审查后得出结论:就实质而言,在事实语境下考察的“腌渍”这一用语的通常含义表明,产品的特征因为加盐而改变。在构成通常含义的一系列含义中,没有任何东西表明欧共体减让表未包括加过盐的鸡块。在上诉中,欧共体对专家组所采取的这种在事实语境下对条约用语通常含义的分析方法提出了质疑,认为依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对通常含义的分析不涉及对条约用语的事实语境的分析,专家组所表明的事实语境对确定“腌渍”这一用语的通常含义无关,专家组在确定条约用语的通常含义时考虑了不应考量的因素。上诉机构认为专家组的解释方法(interpretive approach)没有错误。上诉机构在此提及了“事实性的上下文”(factual context),虽然承认《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并没有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分析步骤,但同时认为专家组在解释相关术语时考虑的相关事实因素即便不应基于“通常含义”予以考虑,确实也可以基于“上下文”来考虑。[13](P69)有国外学者认为,上诉机构在解释世界贸易组织的条约用语时适用了更宽泛的上下文主义(contextualism)的概念,将上下文主义概念作为“事实性上下文”予以明确承认和界定,事实性上下文的概念和在解释世界贸易组织涵盖协议中的价值,可能源于麦克奈尔勋爵对用语的绝对和相对含义的区分。[14](P269)麦克奈尔勋爵在其著作《条约法》中指出,虽然某一用语在“绝对意义上”具有通常含义,但审理条约用语含义的机构要确定的是“相对意义上”的用语含义,即相对于条约制定的情形以及使用该用语的情形,确定其含义。用语的相对性,即是相对于使用用语的人和使用用语的情形的含义。[15](P367)这种绝对和相对意义上的含义区分,正体现了案件事实的价值所在。
(三)实事求是解释法的应用
事实上,在上诉机构明确基于事实解释法律之前,已经有争端方在适用这一方法。而在上诉机构做出上述明确表态后,专家组也据此明确适用了这一方法。在欧共体计算机设备分类案上诉程序中,美国作为原申诉方和被上诉方主张,确定减让表所用用语的通常含义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进行谈判的成员如何对待争议产品。专家组实际考虑的合法预期的“事实性迹象”,也可以被视为减让表中所做减让的事实性上下文,或作为《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2条允许的补充方法。[16](P16)在美国虾龟案中*美国虾龟案是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审理的早期案件。虾和龟是共生动物,捉虾时易伤害到海龟。在该案中,美国以马来西亚捕虾时未按美国要求保护海龟为由,禁止进口马来西亚虾产品。禁止进口措施本身违反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11条规定的禁止数量限制义务,美国援引该协定第20条进行抗辩。,在分析《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20条句首所含的“专断的或不正当的”歧视的含义时,上诉机构指出:“解释和适用第20条句首的任务是很微妙的,实质是界定和标出成员抗辩权和实体权利之间的平衡线。句首所表示的这一平衡线的位置,不是固定的、不变的;这一线条随争议措施的类型和结构而变化,随构成特定案件的事实不同而移动。”[17](P62)审理该案执行措施争议的专家组在引用前述上诉机构的观点后指出:“换言之,这条线的位置本身,依赖于争议措施的类型和本案中的特定情形……为了确定这一条线的位置,不仅需要指明构成这一具体案件的事实,即事实性上下文,还要考虑在保存海龟的事实性上下文中影响‘不正当歧视’这一概念的解释的法律框架。”[18](P77)“海龟是迁移性极高的物种,其保护引起迁移区域国家的关注,无论是世界贸易组织还是其他国际协定都认为通过国际合作最能实现这一保护,这一事实极大地移动了上述平衡线。”[19](P79)专家组的上述分析表明,“不正当歧视”的准确含义因争议事实而彰显。在上诉中,该案当事人对专家组的这一方法和结论均没有提出异议。
在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案件中,大量案件中的规则解释体现了实事求是解释法的应用。越是事实复杂的案件,实事求是法体现得越明显,其价值和作用就越大。在美国虾龟案中,美国援引《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20条保存“可用尽自然资源”这一规定进行抗辩。对于“可用尽自然资源”(exhaustible natural resources)这一概念,上诉机构通过概念演变法这一解释技巧,根据许多物种濒危灭绝这一事实,将“可用尽自然资源”这一法律概念解释为包括海龟:有生命的物种,虽然原则上是能够再生的,在某些情形下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确实容易灭绝、用尽、枯竭;有生命的资源,与石油、铁矿或其他无生命资源一样是“有限的”。[20](P47)在中国汽车零部件案中,中国对进口零部件“征税”,由中国海关在关境依海关法和相关政策实施。美国政府根据《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提出了违反关税义务之诉和违反国民待遇之诉。中国政府的抗辩集中于中国措施不违反国民待遇义务。事实上,美国政府提出的这两项申诉具有排斥关系,前者涉及第2条的关税义务,后者涉及第3条的国内税费义务,关税措施和国内税费措施是两种性质不同、适用范围不同的措施,违反关税义务则排斥违反国民待遇义务,反之亦然。在国际法上,“一当事国不得援引其国内法规定为理由而不履行条约”*参见《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7条。。具体到争端解决中,国内法对争议措施的定性不等于争端处理机构对争议措施的定性。中国汽车零部件案专家组基于中国措施是对组装成整车后的汽车零部件“收费”这一事实,将分析的重点落在了纳税人“纳税义务的产生时间”上,从而将争议措施定性为国内税措施。[21](P182-183、188-189)如果没有本案的争议事实,很难想象对《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3条中的internal taxes or charges(国内税费)和第2条中的charges imposed on importation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e importation(对进口征收的或与进口相关的收费)这样的文本表述会解释出一个时间要素来。
一些相对性用语,如“立即”,更需要结合案件事实来解释。《保障措施协定》第12条第1款要求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在发起保障措施后应“立即”通知保障措施委员会。专家组将“立即”解释为“不当迟延”,美国则解释为“不迟延”(不干预成员通过保障措施委员会对措施审查的能力,或不使成员无时间决定是否要求磋商)。上诉机构同意专家组的解释意见,“立即”意味着“一定的紧急性”。上诉机构进一步指出,紧急性或立即性的程度,依赖于个案评估,要考虑到准备通知涉及的行政困难,还要考虑提供信息的性质。这方面的相关因素可包括通知的复杂性及翻译成世贸组织官方语言的需求。但准备通知所需要的时间显然在所有情况下都应最低。立即通知是允许保障措施委员会和成员具有最充分的可能时间对保障措施进行考虑和反应。上诉机构不同意美国的下述解释意见:只要委员会和成员有足够的时间审查该通知就满足了立即通知的要求。在上诉机构看来,成员是否立即通知,不依赖于委员会和成员事实上如何使用该通知的证据,也不依赖于对个别成员因通知期限不充分而所受实际损害的事后评估。[22](P35-36)解释的结果因事实而澄清。上诉机构在解释“同类性”这一用语时使用手风琴借喻:“‘同类性’这一概念是一个相对性概念,引发了对手风琴键盘的联想。随着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不同条款的适用,(手指)在不同的地方腾挪、按压‘同类性’手风琴。在任一地方的宽度,必须由‘同类性’一词所在的特定条款以及该条款在特定案件中存在的情形来确定。”[23](P21)
(四)实事求是解释法与其他解释规则、方法的关系
实事求是解释法在法律解释中纳入了事实考虑,与《维也纳条约法公约》规定的习惯解释原则,以及上诉机构实施的有效解释、演变解释、协调解释、统一解释并不矛盾。《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第1款处理的是条文实际用语、上下文、目标及宗旨诸因素的关系。条约解释的出发点是条文用语,条文用语的含义首先从字面或文义着手。上下文、目标和宗旨都是在抽象意义上帮助认定条文用语的真正含义,而实事求是法则提供了一个事实的视角。就具体解释方法而言,有效解释解决实际用语的存在价值问题,演变解释解决实际用语含义随时间而变化的问题,协调解释解决不同规定之间的关系问题,统一解释解决特定规则与整个规则体系之间的关系问题,而实事求是解释则重在解决法律规则与事实之间的关系问题。可以说,实事求是法是上述诸种原则、方法在具体案件中的应用体现,它突出案件解决中法律解释的事实性。
但是,实事求是解释法不同于《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2条所述补充方法对缔约情形的考虑。第32条规定:为了证实适用第31条所得之意见,或者依第31条所做解释依然意义不清或难解,或所获结果显属荒谬或不合理时,为了“确认”其意义起见,可以使用解释之补充资料,包括缔约的准备工作及缔约情况。此处的“缔约情况”指缔约的历史背景。[24](P32)可以看出,实事求是解释法与第32条的补充方法至少存在下述区别:(1)实事求是法关注的是特定案件中的事实情形,面对的是当下问题。而第32条关注的是需要解释的条约的谈判情形,面对的是历史问题。(2)对缔约情况的考察,只是一定条件下(解释结果不清或不合理等)的补充方法,并非争端解决法律解释所必需*上诉机构曾经指出,诉诸第32条的补充方法并非绝对必要。参见US-Carbon Steel.WT/DS213/AB/R, para.89, p.33.,其目的在于确认之前得出的解释结果。而实事求是解释法对案件事实的考察为每一争端解决案件所必需,其目的是确立适用协定与争议案件的关联性,指明适用协定相关用语的内涵与外延。(3)缔约情况只是第32条允许考虑的补充方法之一,可能还有其他需要考虑的补充方法。[25](P110)而实事求是解释法仅考虑特定案件的争议措施,与案件无关的其他事实不在考虑之列。第32条的缔约情形仍然属于文本意义上的方法,而实事求是法则是事实意义上的方法。
实事求是解释法也不同于《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所述之适用条约的嗣后惯例(subsequent practice)。(1)嗣后惯例属于与上下文一起考虑的部分,是确定各当事国对条约解释所达成的协定的条约适用惯例。*参见《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条第3款(b)项。嗣后惯例是条约缔约方的“一致的、共同的、连贯的”系列性行为,足以确立一种可识别的“模式”[26](P13),是一种“共相”。实事求是解释法所考虑的是案件解决所涉及的具体事实,是一种“殊相”。(2)嗣后惯例要考虑非争端当事人的其他缔约方的做法,争端当事人的做法本身不足以构成嗣后惯例[27](P101)。而实事求是法考虑的事实恰恰是争端当事人的做法,对被诉当事人的措施做出认定。(3)嗣后做法构成了缔约方理解条约含义的“客观证据”[28](P221)。而争端解决中的争议措施恰恰处于“主观”争议之中。(4)基于嗣后惯例对条约做出的解释约束所有缔约方,包括没有实际参与形成该惯例的缔约方[29](P107)。而实事求是法基于个案解释的结果仅对案件争端方有约束力。
二、国内争端解决中的实事求是解释法
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处理160多个世界贸易组织成员相互间的贸易争端,涉及传统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保护、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等争端,争议措施的范围涵盖边境措施和国内措施、立法措施和法律适用措施。世贸争端解决不孤立于各成员的法律制度而存在,国际争端与国内做法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中采取的基于案件事实解释法律的做法,无疑会对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产生重要影响。这种影响首先表现在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对世贸争端的处理应对上,采用相关方法捍卫成员自身的利益;同时,也给我们启示,实事求是这一法律解释方法在国内争端解决中是否也存在呢?
经过考察我们发现,事实上实事求是解释法在国内争端解决中也是存在的。只不过学者至少在中国法律学者对法律解释的研究中较少明确肯定基于案件事实解释法律这一做法:他们在一般意义上承认个案解释,但没有深入挖掘个案解释的内在含义;在一般意义上承认法律解释的实践特征,强调在个案中寻找大前提解释大前提,但却没有指出个案事实对解释大前提的重要性;在一般意义上讨论“涵摄”,但较少聚焦于基于事实解释法律这一侧面。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中适用的实事求是解释法,有助于我们厘清对国内争端解决中法律解释方法的认识,加强实事求是解释法在国内争端解决中的应用。
(一)“布兰代斯论据”和先例制度
基于事实来解释法律的最好一例是“布兰代斯论据”(Brandeis brief)。在美国最高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30],布兰代斯作为代理律师,除引用法律外,还利用社会和经济研究成果影响了美国最高法院对法条的解释和判决结果。布兰代斯后来成为美国最高法院法官,这一做法和论据也因其而得名。[31](P149)正是布兰代斯提出的“法官被推定知道法律,但并不推定了解事实”,使得美国最高法院在这一案件中第一次认可了在确定社会性立法的合理与否时需要有关事实作为支撑。[32](P466-468)这一做法和论据的存在以及命名也说明:“一项规则的适用范围及其含义,在确定何种事实系与该项法则所由诞生的事实具备相似性之前,是我们无由加以判断的。”[33](P4)
在普通法系存在着判例法/先例制度。判例法制度意味着法官造法,而法官基于案件事实造法。脱离事实去解释法律,最多也只能是随便说说的、可能也有启发意义的“附带意见”,而不可能构成对争端的裁决理由:“根据基本事实,或在基本事实框架下,对案件做出裁决的法律表达。”[34](P269)在判断一个案件的判决理由时,案件事实是首要一步。“确定某一判例的判决理据的关键问题通常是,我们可以多宽泛地阐述该判例确定的法律规则。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将案件事实进行多大程度地抽象……每一案件的判决理据应将该判例特定的案件事实考虑进去,并将有关案件事实尽可能按照符合判词和实践需要的方式进行归纳。”[35](P445)先例制度适用的要求和结果,即同案同判,都离不开事实这一基本要素。法律和事实不可分、不能分、分不开。“一般认为,普通法判决与大陆法系判决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本质区别在于,普通法法庭对案件事实有着近乎着迷般的关注。事实与法律已经进入无法分开的状态。普通法法官的判词根植于、来源于案件事实。”[36](P489)即便普通法制度中存在的法律和事实的二分法,也类似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中的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分工,依然要求根据事实来解释法律。
(二)大陆法系中的三段论推理
在大陆法系,实事求是解释法也是存在的。德国学者卡尔·恩吉施在《法律思维导论》中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来说明论证和解释问题。法律规定:“如果行为人侵入一个封闭的空间偷盗,他应被处以3个月至10年的自由刑。”需要解决的问题是:A从载人汽车中偷盗,是否应被处以3个月至10年的自由刑?恩吉施认为整个推论应包括7个步骤:(1)如果行为人侵入一个封闭的空间偷盗,他应被处以3个月至10年的自由刑;(2)行为人侵入一个空间偷盗,这个空间被认为是人会进入的,由人造修建物所包围,抵御无权者进入,这个行为人就侵入了封闭的空间;(3)行为人侵入一个空间,而该空间是封闭的,则行为人应被处以3个月至10年的自由刑;(4)行为人侵入载人汽车偷盗,他侵入了一个空间,且该空间是封闭的;(5)行为人侵入一辆载人汽车偷盗,应被处以3个月至10年的自由刑;(6)A是一个侵入一辆汽车中偷盗的行为人;(7)A应被处以3个月至10年的自由刑。恩吉施指出,在这个推论链中,前提(2)和前提(4)指两个特别的命题,其作用是将从制定法中得出的一般大前提接近待决的具体案件。解释明显发生在特别的小前提(2)和(4)中。小前提(2)对封闭空间是什么做了回答,这个回答是一个典型的解释。小前提(4)将这个解释延伸到了载人汽车。[37](P78-79)
恩吉施的上述例证,实质上是结合案件事实解释法律的一个例证。恩吉施针对上述例子进一步指出:“解释的任务是法律者把法律概念的内容和范围想象为具体。对内容的说明在此是通过定义,即通过概念特征的列举(封闭的究竟是一个……空间)而发生。对范围的说明是通过对案件群和单个案件的阐明而展开,这些案件应归属法律概念及从法律概念中推论出。”[38](P79)恩吉施在其他地方使用了“接近”、“等置”等概念来说明具体事实与法律概念的关系:“通过解释直接从制定法抽出的具有抽象概念特征的大前提,将‘接近’待决的具体案件。”“具体的事实行为被归纳在由法律概念标明的共同的类别中……建立在把新的案件与已经确立了类别归属的案件进行等置的基础之上。”[39](P78、62)
实事求是解释法建立了三段论推论中小前提与大前提的联系。“我们所说的解释主要是寻求纠纷解决的大前提的适用法律活动。”[40](P23)在恩吉施所举例子中,要建立“封闭空间”与“载人汽车”之间的联系。“通过解释在直接从制定法抽出的法律大前提与案件的判决之间,不仅有小前提,还有其他的使推论容易被做出的东西被插入。”[41](P78)这就需要对“封闭空间”进行解释,需要基于载人汽车这一事实进行有方向性的解释。生活中我们通常举的三段论例子过于简单,忽略或掩盖了基于事实解释大前提的这一过程。以下述三段论为例:人都是要死的;张三是人;所以张三是要死的。实际上,我们在得出“张三是人”这一小前提之前,需要对大前提中的“人”进行解释,需要建立“张三”与“人”的对应、等置或接近。由于现实中我们认为张三是人理所当然,从而直接略过了对大前提“人”的解释过程,忽略了“张三”与“人”的对应过程。实际需要解决的争端案件并非如此简单、直接。例如,载人汽车是封闭空间吗?海龟是易枯竭的自然资源吗?这些都需要基于案件中的特定事实来解释法律概念的“内容和范围”。恩吉施使用的“插入”这一带有力量色彩的用语,顿使小前提与大前提之间的联系生动、鲜活了,具有了生命力。
(三)“涵摄”与实事求是解释法
上述大陆法系的三段论推理也适用于中国。实事求是法,符合中国法律制度文化中所表达和要求的“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一根本原则。国内学界使用的“涵摄”或“归摄”(subsumption)概念或方法,已经隐含着实事求是解释法的影子。根据国内学者的解释,“涵摄,即把经分解的个案事实归入(或涵摄)到法律的事实构成中去……具体说来,涵摄要经历对法律的事实构成进行分解、对个案事实进行分解、将个案事实归入法律的事实构成三步。”[42](P58-59)根据这一描述,涵摄是一个“推论过程”或“推论模式”。但它没有说明确定法律事实构成的方法。这一任务被放到了解释者身上,通过所谓的“诠释循环”与“等置”,经由生活事实和法律规范的相互的诠释循环,推导出法律构成。这也被认为是将生活事实归入法律事实的方法。[43](P87-89)这类似于恩吉施所说的“在大前提与生活事实间之眼光的往返流转”或朔伊尔德所说的“在确认事实的行为与对之作法律评断的行为间的相互穿透”。[44](P162)上述的“涵摄”、“循环”、“往返流转”或“相互穿透”,都包含了一个双向的过程,即由事实到法律、由法律到事实的过程,中间暗含着基于事实对法律进行诠释的要求,但却没有将这一方向和过程明确地、充分地突出、独立出来,没有将其与法律解释联系起来,没有作为一种法律解释方法而予以分析。事实上,上述对双向过程的表述,重点放在了案件事实形成的框架下或者小前提的构建过程,而非大前提本身。*参见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160-16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郑永流:《法律方法阶梯》,86页以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大前提也需要用事实来“照亮”。有学者指出,对法律文本的解释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进路,即文本解释和事实剪裁。文本解释就是直接对所适用的法律文本或条文解释,将解释结果与个案事实相连接,属于解释者用法律涵摄事实。剪裁事实是不直接就所适用的法律文本或条文做出解释,而是就有关的个案事实进行区分、剪裁,然后将事实与法律文本或条文相连接,属于解释者将事实归摄于法律。在实际的法律解释过程中,文本解释和事实剪裁往往会同时并用。[45](P21)这里,在与文本解释并列的语境下提到了“剪裁事实”,似乎意在基于事实进行法律解释,但上述对剪裁事实的表述本身又说不直接对法律文本做出解释,这就为读者的理解留下了困惑,很遗憾地没有在基于事实解释法律这一方向上再进一步。
国内学者概括了多种法律解释方法。例如,张志铭教授概括了四大类法律解释方法形态,包括语义方法、系统方法、目的—评价方法和跨类型意图方法。这四大类方法又进一步表现为11种具体方法:普通含义论、专门含义论、上下文和谐论、判例论、类比论、逻辑—概念论、一般法律原则论、历史论、目的论、实体理由论和意图论。[46]王利明教授将狭义的法律解释分为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当然解释、反面解释、目的解释、限缩解释和扩张解释、历史解释、合宪性解释以及社会学解释9种解释方法。[47]仔细了解这些方法就会发现,这些方法虽各有特长侧重,但共同点是关注法律文本本身(包括立法资料),不涉及案件事实。即便是合宪性解释和社会学解释,也只是适用于法律文本出现复数解释的情况下,而非案件事实。[48](P276、283)
国内亦有学者认为,法律解释的对象既包括成文法律也包括对法律事实的解释。这一观点建立在对法律解释和解释法律的区分之上:解释法律,其对象是明确的,是各种法律,而法律解释的对象则包括成文法律和法律事实。此处的法律事实,“是由法律规范所框定的,而又经过法律职业群体(法官起着最终决定性作用)证明的‘客观’事实”;“法律事实的解释是指法官等把生活事实认定为法律事实后,关于法律事实所释放出来的法律意义”。法律事实的解释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对法律中规定的法律事实意义的重新阐释;第二,法官等对法律事实的解释是一种对生活事实的提炼和说明。*陈金钊:《法律解释的哲理》,54页、57页、287页、299-300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另有学者对这样的观点不予认同,认为事实的认定是解释的前提,解释的仍是法律文本;法律解释是赋予事实以法律意义,而事实的认定属于证据学的范畴,不是法律解释,但该观点同时认为法律解释的对象是否涉及事实可以探讨。*刘平:《法律解释——良法善治的新机制》,49-5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上述两种观点哪种观点更有道理,说的是否一回事,我们暂不去评判,但两种观点都承认且突显了争端解决中法律解释与案件事实之间的密切关系。那么,法律与事实间的这种“密切关系”是什么呢?他们都没有做进一步分析。本文认为,事实认定与事实定性是需要区分的两个不同问题。事实认定更倾向于自然中发生了什么,而事实定性则更倾向于在法律上是什么。同一事实可能引起国内合同法的违约与侵权竞合,说明事实认定和事实定性的不同。事实定性必须结合法律规定来分析。国际私法中的识别亦是对事实定性。前文分析的中国汽车零部件措施属于国内税措施亦是事实定性。事实定性是法律问题,必然涉及对法律的解释。前述两种观点或类似观点的某种分歧,可能在于没有准确区分事实认定和事实定性这两个问题。
法律与事实间的关系,不能抽象地用“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往返回转”来表示、来解决。在法律与事实之间存在着一个双向关系,这是“往返回转”试图表达的含义,就整个法律适用过程而言也确实如此。但在每一单向关系中,从法律到事实,或者从事实到法律,又是什么样的情况呢?现有研究文献没有给予充分的关注和阐释。本文提出的实事求是法,旨在解决基于事实解释法律的问题,相当于由事实到法律这一方向;将经由解释已经明晰的法律“适用到”争端的具体事实上,相当于由法律到事实这一方向。国内学者所说的通过解释文本用法律涵摄事实,或者通过事实裁剪用事实归摄法律,似乎没有具体说明事实是否以及如何在法律解释中发挥作用的问题。*张志铭:《法律解释学》,2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刘平:《法律解释——良法善治的新机制》,5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国内学者强调寻找裁判依据的不断反复过程,强调要通过事实和法律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寻找大前提*王利明:《法律解释学》,6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但也似乎没有明确说明寻找大前提过程中事实对法律的作用。
三、余论:法律解释与法律适用
或许有人会说,此处所说的实事求是解释不是法律解释,而是法律适用,基于案件事实解释法律这种做法混淆了法律解释和法律适用。这种说法的产生,实际上也涉及对法律解释和法律适用的解释。
“我们所说的解释主要是寻求纠纷解决的大前提的适用法律活动”,“这种法律解释活动是以裁判权为中心的法律适用活动,是法律解释学研究的重点”[49](P23)。因此,法律解释本身是法律适用的组成部分。这是广义上的法律适用。将通过法律解释获得的法律文本的含义应用到需要解决的案件之中,这是法律应用,或狭义上的法律适用。无论采取哪种意义上的法律适用,基于案件事实进行的“实事求是”解释既具有必要性,也具有独立性。
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谅解》规定的专家组的三项职责,即事实认定、法律适用性评估和措施相符性评估,更好地说明了法律解释与法律应用问题。只有在明了相关法律规则的含义之后,才有可能将这一法律要求应用到争议措施之上,以便最终认定争议措施是否违反了相关法律规则的要求。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所有争端解决问题都是解释问题。这一点在国际争端解决中成立,在国内争端解决中也成立。
基于个案事实来澄清相关法律规则的范围和内容,以明确争议措施是否违反相关法律规则的要求,是解决特定争端的必然要求,也是解决争端的方法要求。争端解决中使用的实事求是解释法,是一种具有一定导向性、便利性、实用性的应用性解释方法,也是一种涵盖其他解释方法的综合性解释方法, 是争端解决中法律解释实践的反映和发展。它既符合《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解释原则及解释要素要求,又符合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及国内争端解决的实际做法。使用实事求是解释法,更符合也更能实现法律解释的目的,实现争端解决的目的和法治要求。抛开案件具体事实谈法律解释与适用是不全面的。基于案件事实的法律解释方法及其目的,决定了它不仅存在于世界贸易组织实践中,也存在于或应当存在于国内争端解决中,法律解释的实事求是法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因此,在国内争端解决中,应进一步肯定、强化个案事实对法律解释的“照明”作用。
[1][45] 张志铭:《法律解释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2] US-Gasoline, WT/DS2/AB/R.
[3][17][20] US-Shrimp, WT/DS58AB/R.
[4][8][23][26] Japan-Alcoholic Beverage, WT/DS8/AB/R.
[5] US-Stainless Steel from Mexico, WT/DS344/AB/R.
[6] US-Zeroing, WT/DS350/AB/R.
[7] US-Steel from Mexico, WT/DS344/AB/R.
[9] EC-Hormones, WT/DS26/AB/R.
[10]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1][44] 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12][13][25][27][29] EC-Chicken Cuts, WT/DS269/AB/R, WT/DS286/AB/R.
[14] Isabelle Van Damme.TreatyInterpretationbytheWTOAppellateBod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15] Lord McNAIR.TheLawofTreati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16][24] EC-Computer Equipment, WT/DS62/AB/R, WT/DS67/AB/R, WT/DS68/AB/R.
[18][19] US-Shrimp, WT/DS58/RW.
[21] China-Auto Parts, WT/DS339/R, WT/DS340/R, WT/DS342/R.
[22] US-Wheat Gluten, WT/DS166/AB/R.
[28] Draft Articles on the Law of Treaties with Commentaries, 1966, Yearbook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 1966, Vol.II.
[30] Muller v.Oregon, 208 U.S.412,28S.Ct.324(1908).
[31] Bryan A.Garner (ed.).Black’sLawDictionary,Abridged. 7th edition,St.Paul: West Group, 2000.
[32][35][36] 迈克尔·赞德:《英国法》,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
[33] 艾德华·H·列维:《法律推理引论》,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34] Michael Zander.TheMaw-makingProcess. 6th edi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37][38][39][41] 卡尔·恩吉施:《法律思维导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40][47][48][49] 王利明:《法律解释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42][43] 郑永流:《法律方法阶梯》,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46] 张志铭:《〈法律解释学〉的内容框架与写作场景》,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6(1)。
Abstract: The aim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is to clarify the scope and content of relevant legal rules in dispute settlement process. The WTO panels or Appellate Body clarify the existing provision of agreements in accordance with customary rules of interpretation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and ascertain the ordinary meaning of treaty terms based on the particular circumstances of each case. This kind of seek-truth-from-facts approach, which is in compliance with and complementary to textual approach, establishes the nexus between relevant provisions of law and particular circumstances of a case. This approach actually exists in domestic dispute settlement process, which is used to determine the premise of syllogistic reasoning based on the specific facts.
Keywords: WTO dispute settlement; legal interpretation; particular circumstance; seek-truth-from-facts approach
(责任编辑李理)
TheSeek-truth-from-factsApproachtoLegalInterpretation
HAN Li-yu
(School of Law,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韩立余: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 10087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引领国际经贸规则研究”(16AFX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