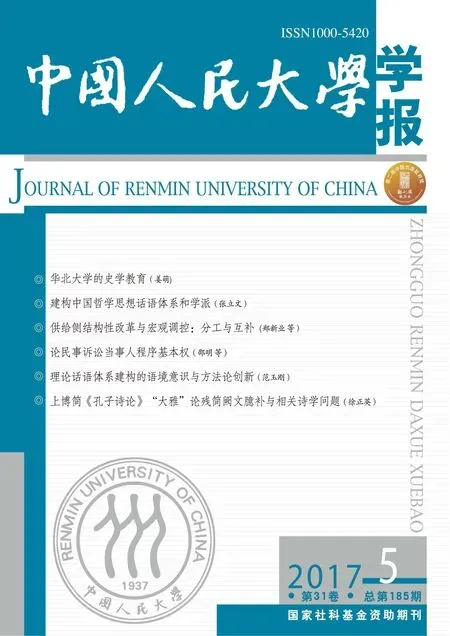华北大学的史学教育*
——从一份新发现的“史地系小组漫谈”记录说起
姜 萌
华北大学的史学教育*
——从一份新发现的“史地系小组漫谈”记录说起
姜 萌
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仍有薄弱之处。研究主题上,史学教育比较薄弱;时段上,20世纪40年代迄改革开放还有很多留白。2015年,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搬迁时,意外发现了一份珍贵手稿——《史地系小组漫谈对课目的意见(共两组)》。这份产生于1949年年初的材料,内容不仅涉及稀见的革命根据地史学教育开展情况,还直观地反映了1949年前后中国史学正在发生的变动。这份文献表明,华北大学的史学教育源自华北联合大学和北方大学,继承了华北联合大学的课程设置思路和北方大学的师资力量。通过对华北大学史学课程设置及授课情况的梳理,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华北大学的史学教育既是“战时教育”、“战时史学”的具体体现,同时也深刻影响了史学教育模式在20世纪50年代的快速改移,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影响深远。革命大学教育者坦诚积极的精神,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宝贵财富,也是当今大学教育者应当继承发扬的优秀遗产。
华北大学;史学教育;马克思主义史学;战时教育;战时史学
一、引言
自20世纪40年代周予同、顾颉刚、齐思和、邓嗣禹等学人将“中国近现代史学”作为研究对象以来,这一领域的研究已取得长足进步。特别是最近二十余年,在“学术史热”、“国学热”和“民国热”潮流的带动下,研究成果数量惊人。尽管笔者已罗列近二十万字的篇目汇编,仍担心有重大遗漏,粗略检视已有研究成果,笔者初步得出这样的认识:
从研究主题来说,史学发展历程、著名史家或史学机构、重要史学成果或史学现象等,在过去数十年是研究重点,成果之多不胜枚举;史学观念、历史书写等问题,近些年来已成为新的关注点,各种成果正在涌现。就薄弱环节而言,史学教育应该是较突出的一个。史学教育研究的薄弱,主要体现在研究成果数量少,仅数十篇而已[1],且尚无引起普遍关注的论著。在这一研究主题中,针对历史教科书的研究成果多一些①大陆学界对历史教科书的研究,周朝民、俞旦初、藏嵘等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所尝试。纪奚在1992年提出“应研究‘历史教科书史’”,参见纪奚:《应研究“历史教科书史”》,载《史学史研究》,1992(4)。纪奚之后,对教科书的研究逐渐增多,二十余年来,周清华、徐松巍、储著武、舒习龙、李孝迁、刘超、张越、李帆等皆有成果面世。,但很多研究是从编纂思想、体例、书写等角度展开的,而非史学教育角度。制约史学教育研究开展的因素,最大的可能是资料局限问题。史家、史著、史学现象等都有可依赖的文本资料,而史学教育往往难以留下较多文字记录,教学过程因声音的消失而无痕,未出版的讲义亦多堙没,接受教育者对教学效果也鲜有记录。没有可依凭的史料,即使意识到问题所在,也难以展开研究。
从研究时段来说,中国现代文史之学的第一阶段——从甲午惨败至20世纪40年代,研究成果最多、研究水平最高,近年正从表面的现象研究向更深层次的问题研究递进;第二阶段——从20世纪40年代迄改革开放,已有一些成果,但是显然还非常不足,无论是表面的现象梳理还是深层次问题的探索,都与这几十年的风云激变不相称;至于第三阶段——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尚未拉开时间距离,现有成果只能说是观察或评论,还谈不上是深入的史学史研究。就整体感觉而言,中国现代文史之学的第二阶段,或将是中国学术史研究的新热点。[2](P122)这一判断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一是这一时期政治社会文化情形异常复杂,史学的分化融合路径梳理得还不清楚*对这一时期史学分化融合轨迹梳理最多的学者是王学典教授,参见王学典:《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载《历史研究》,2004(1),等。此外还有蒋海升:《“西方话语”与“中国历史”之间的张力:以“五朵金花”为重心的探讨》,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总体看,这一阶段还有不少留白。;二是此前一些研究多受意识形态影响制约,很多问题还需要在较为纯粹的学术层面进行清理;三是这一阶段距今已有较长的时间间隔,研究者已初步具备理性分析的客观条件。
笔者在梳理中国近现代史学史发展情况时,并未想到会获得一个幸运机会,寻找到能将上述两个薄弱领域汇合为一的题目——1949年前后的史学教育问题。2015年夏天,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搬迁,刘文远老师从尚钺先生赠书中发现了一份珍贵的史料。这是一页残存的手写体纸张,经过辨认,应当是华北大学史地系教学情况座谈记录。*本文的“华北大学”,特指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时期创办的革命大学,非蔡元培等人在北平创办的“华北大学”。这份新发现的材料引起了笔者对解放战争时期党办大学史学教育问题的兴趣。一年多来,虽然因种种原因尚未能阅读到华北大学的档案,但也陆续获得了一些有价值的史料。本文尝试根据这些史料,从机构变迁、教学组织等角度来透视“华北大学的史学教育”这一问题,以增强我们对解放战争时期党办大学及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了解。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尽管对“党办大学”*此处的“党办大学”特指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之前主办的高等教育学校。如:“中华艺术大学……是由沈端先(夏衍)、冯乃超主持与指导的一所新兴的、进步的党办大学”,参见许幸之:《关于“中华艺大”校址和“左联”成立大会会址》,载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会址纪念馆、上海鲁迅纪念馆编:《“左联”纪念集1930—1990》,147页,上海,百家出版社,1990。、“华北大学”[3]、解放战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4]以及“党办大学的史学教育”[5]都已有一些研究,但还比较薄弱。本文希冀在材料、视角和内容等方面深化这一领域的研究。此外,2017年是中国人民大学建校80周年,本文更具一些特殊意义。
二、 一份新发现的华北大学“史地系小组漫谈”记录
2015年8至9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搬迁。刘文远老师在整理尚钺先生赠书时,在一册书中发现一张略有残破的泛黄竹纸,上面写满字迹。经过识读,几位同事认为是华北大学史地系同学关于课程的座谈会记录,由负责此次座谈会的老师记录、整理,然后送给时任系主任尚钺。尚钺夹在书中,遂幸运地保存下来。内容如下:
史地系小组漫谈对课目的意见(共两组)
A.共同必修科
1、国文
柳捷:国文不太需要,学半年国文不能有甚大进步。
子一:国文学习若只是选文、作文,而不是学修辞学,可不必定为必修科。*原文有下划线,仅此一句。后来国文不再是“共同必修科”,可能与此有关。
温晋:为了将来自己编讲义,国文是必要的。
郭浴生、王烈东:为了练习总结,国文是必须的。
王烈东:最好一个钟头哲学,一个钟头社会科学。
史地系必修科:
第一组 全组通过请求后面增加两点钟的唯物史观。
第二组 同学都同意适当地添一门唯物史观或历史研究法或历史哲学这样的课程。*第一组、第二组前有残缺。残缺处可能有“1、”的标号。
2、郭浴生:史料选读、教材研究,不论中外,最好都偏重于近代史。
3、郭浴生:美国侵华史最好搞明确些。
4、温晋:美国侵华史学完,再学世界史恐怕学不完,是否每周可以增加一个钟头(三钟头)。
樊宁、柳捷:世界史不必增加钟头,因为行政已有很好的计划
5、地理:
温晋:地理是次要的,用以辅助历史,学习地理时,中外地理应同时并进
王烈东、丁蔚:史地应并列并重,地理时间太少
樊宁:地理时间足够,可以不必增加
杨振奎:过去大家对地理重视不够,希望学校尽量充实教员及教材。
以上是两个学员小组“对科目的意见”的正文。另外,还有四行字:在纸张右上角,有两竖排蓝色字迹:“交尚主任”;蓝色字迹左边又有黑色竖排字迹:“辰班已解答”;中间右侧有黑色竖排字迹:“前几天我去的”。除此之外,纸张再无他字。从这些话语可知,记录者和“尚主任”非常熟识,“座谈”也是比较常规的事务。
这份《史地系小组漫谈对课目的意见(共两组)》(下文简称“漫谈”),字数虽然不多,却相当珍贵。无论是对革命史研究、还是对马克思主义史学教育研究,都是一份比较稀见的史料,值得我们深入细致地层层分析:“漫谈”是何时产生的?为什么会有这个“漫谈”的产生?如何在华北大学乃至解放战争大的历史场景中解读这份“漫谈”?为了能深入解读这份材料,必须先确定它的产生时间。
要确定这份文献的产生时间,须逐一分析其中的一些核心信息。第一是“史地系”。早在抗战时期,基于革命需要,华北联合大学就创立了史地系。《孙敬之传》称孙敬之是北平师范大学地理系毕业生,与尚钺“共同创办了联大的史地系”:
偌大的一个史地系最初创立时只有孙敬之、尚钺两个人,一个包教地理,一个包教历史。用尚钺的话说就是:“两个人把史地系办得热火朝天,那种艰苦环境中的热情是难以想象的。”[6](P41-42)
这一说法显然有误。根据尚钺自述可知,抗战时期,他主要在云南大学任教,并不在太行山抗日根据地。抗战胜利后从云南赴上海,后短暂任教于山东解放区的山东大学,并于1948年赴北方大学,后并入华北大学。[7](P20-22)谢韬回忆,尚钺与他在1948年“同时调到正定华北大学二部”,两人关系密切,“比邻而居,朝夕相见,时有过从”[8](P32)。尚钺到华北大学后,担任了史地系系主任。本文件中的“尚主任”,当是指尚钺。因此,此处的“史地系”,应是华北大学的史地系。这也同时说明了,这一文件产生于尚钺到达华北大学之后。
另外,可帮助证明此处“史地系”不是华北联合大学史地系的,是“漫谈”中提到的“美国侵华史”课程。华北联大史地系创办于抗战时期,当时美国正是抗战盟友,党办大学不可能公然教授这一课程。解放战争爆发以后,政治形势激变,中共对美国不满,公开揭露“美国侵华”,已是政治斗争需要。胡华编撰的《日本投降以来美帝国主义侵华史略》于1947年6月由冀中新华书店出版。此书甚薄,只有23页,内容也主要是“日本投降以来”,或许不是“漫谈”中“美国侵华史”课程的教材。“漫谈”所指,更可能是刘大年的《美国侵华史》。刘大年1947年春在北方大学开始研究美国侵华史,1948年8月华北大学成立后,《美国侵华简史》初稿被送到华北局审查[9](P92-96),1949年8月由华北大学以《美国侵华史》为题出版。
华北大学的存在时间是1948年8月至1950年2月。这个漫谈记录产生的时间能否更为具体一些?为了进一步确认时间,我们需要分析漫谈记录上第三个重要因素——学员。
漫谈记录中的郭浴生,出现了三次,显示出他是一位发言比较积极的同学。有材料显示,他在1949年4月时,可能在张家口中学担任地理教员。察哈尔教育厅相关人员到张家口中学视察听课,在总结中特别指出:
在教员中,不管是老区的也好,新区的也好,新出学校参加工作的也好,有不少是努力的热心的,有较好的教学方法的,如化学教员赵士侠、国文教员贾宝昆、地理教员郭浴生,都是较好的教育工作者。[10](P15)
华北大学“史地系”的重要职能就是培养中学历史、地理教员,且是六个月速成培训,第一批学员毕业于1949年2月。[11](P82)因此史地系的郭浴生,与张家口中学的郭浴生似有两条信息是符合的——“新出学校参加工作”与“地理教员”。另外还能找到丁蔚的一些信息。她是青岛女中第一届学生自治会的常务理事,1948年1月离开青岛女中,“转道北平经中共北平城工部介绍,奔向久已向往的晋察冀解放区”[12](P604-606)。她先入华北联合大学政治学院11班,后改编为华北大学一部一班。[13](P144)一部大部分学员分配工作,小部分学员会“转入本校其他各部继续学习或从事研究工作”[14](P241)。丁蔚可能就转入了史地系学习,后来进入北京外国语学院工作。
基于以上分析论证,我们大约可判断这一“漫谈”很可能是华北大学史地系第一期学员的产物,且是第一期中后期的产物。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漫谈”表现了学员们对专业课的各种意见,显示出他们已经开始较深入地学习专业课了。笔者最近还找到了另一份比较珍贵的文献——《华北大学第二部教育工作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1949年3月由华北大学教务处印制。其中一条内容是对第二部(史地系为第二部下设的一个系)整个学习安排的规定,内容如下:
前二三个月主要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以初步树立革命人生观,并对人民政府各项政策求得基本认识;后三四个月主要进行业务教育,以获得有关业务之立场、观点、方法与基本的业务知识。[15](P1-2)
这条材料显示,华北大学业务学习的内容是安排在两三个月之后,而从学员们的“漫谈”中可清晰地感受到,他们对专业课已经有了比较深刻的认知。因此,断定这份“漫谈”产生于华北大学史地系第一期后期,也即1949年年初这段时间。
这份文献的产生时间基本确定之后,我们可以去追问第二个问题——为什么会有这个漫谈记录的产生?解答这一问题,需要我们对华北大学史学教育的源流进行必要的追溯。
三、华北大学史学教育溯源
华北大学的史学学科,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华北联合大学的史地系,一是北方大学的史学部分。兹先论华北联大的史地系,次论北方大学的史学部分。
时至今日,华北联大史地系任课教师的情况以及课程讲授情况已较为模糊。不过从相关回忆录等文献中,可以勾勒出“中国近代革命史”的授课情况。彭明曾回忆说:
这既是教育学院的共同课,也是我们史地系的专业课。这门主课的主讲教师是胡华同志,有一段时间胡华同志生病,所以由浩川同志代课。[22](P53)
据《胡华自传》可知,胡华于1940年4月就开始在华北联大社会科学部和工运部担任“中国近代革命史”教员,授课依据的资料主要是成仿吾编写的《中国苏维埃运动史提纲》(曾在延安中央党校和陕北公学讲授),以及何干之借给他的二三十本中国近代史和中国革命问题的书籍。但是他在1945年12月到张家口市总工会工作,暂时离开了华北联大,直到1946年10月华北联大撤出张家口,才返回设在束鹿县(现为河北省辛集市)的联大,担任教育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和史地系副主任,并重新教授“中国近代革命史”。[23](P285-286)
在胡华离开华北联大的这段时间,担任“中国近代革命史”教员的应该是智建中。智建中1937年7月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曾在1941年2月兼任“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历史教员,讲授“中国史”,后担任延安大学教务科科长,负责日常的教学行政工作。1945年10月随八路军东进纵队离开延安,同年12月到达张家口的华北联大。在联大期间,讲授“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史”,兼任教学组长。1946年6月继续随纵队东进。[24](P106-115)
智建中赴东北之后,联大的“中国近代革命史”课程或曾中断过。1945年12月进入华北联大史地系就读的彭明不仅提到了智建中“任‘中国近代史’课”[25](P52),还提到了联大转移到束鹿之后,史学课程比较缺乏:
作为史地系学生的我们,总在想着,能够有一位讲中国近代历史的老师来给我们讲课就更好了。忽然有一天,村里出现了一位新人……这就是学校给我们派来的胡华老师,时任史地系的副主任。[26](P25)
彭明还回忆道,胡华讲授的课程正是“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史”,“热情洋溢,语言生动,史料感人,头一堂课就给大家带来很好的印象”,而当时条件虽然非常简陋,学生们“席地而坐,膝盖就是书桌”,但学习热情很高,“不停地在记笔记”。[27](P25)
由此可知,虽然解放战争时期华北联大主客观条件都非常有限,但仍力图安排好教学。从史地系的课程设置看,分为共同必修科和史地系必修科两大类,共同必修科课程有中国近代革命史、社会发展史、国文等,史地系必修科有中国通史、近代世界史、中国地理、历史研究法及教学法等。[28](P129-132)从教学重点看,重视中国近现代史,及史地系学生要学习国文、地理,是比较清晰的。而这些信息,在“漫谈”中都有体现。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华北大学史地系课程是在华北联大史地系课程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MRI检查是目前临床上普遍应用的医学影像学检查技术[1],但MRI检查中存在一些潜在的风险[2],其中重要风险之一是患者体内有铁磁性内植物。体内有铁磁性内植物不但使图像出现伪影、图像质量下降,影响了病变的诊断,而且有可能导致患者发生损伤。此外,另一重要风险因素是患者体内有植入性心脏节律设备[植入性心脏起搏器、植入性心律转复除颤器(LCD)、植入性心血管监测仪(ICM)和植入性循环记录仪(ILR)]以及人工电子耳蜗、胰岛素泵等,当患者体内有这些植入性或携带这些设备进入MRI检查室,有可能造成设备功能丧失和损坏。
1946年1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在邢台成立了北方大学,由历史学家范文澜担任校长。学校陆续设立文教、财经、工、农、医等七个学院和经济、历史两个研究室。与史学有关的机构是文教学院和历史研究室,范文澜、刘大年等人是其中的骨干。北方大学文教学院的情况已经有些模糊,最值得关注的是历史研究室,当时学生的回忆也重点突出了历史研究室:
历史研究室建于1946年初,历史教员3人,根据教学需要,成立历史小组。1946年7月,历史教员增为5人,在范校长指导下成立历史研究小组,主要任务是编辑教材。1947年初,中共中央宣传部打来电报,要范校长聚集人才,把历史研究工作继续搞好。1947年暑假,以原历史研究小组为基础成立了历史研究室,范校长兼主任。开始有研究员8人、研究生1人,后增为研究员11人,研究生2人。他们是:尹达、刘大年、王可风、王南、尚钺、丁易、刘桂五、荣孟源、纪志翘、牟安世、杜千秋、靳鲁雨等。该室主要任务是在范校长的领导下,修订《中国近代史》和《中国通史简编》。研究室的成员在从事研究工作的同时,还给文教学院、财经学院、工学院、医学院授课。[29](P23-24)
北方大学历史研究室的力量之强,从以上名单中就可窥见。范文澜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五老”之一,尹达、刘大年是1949年之后中国史学界长期的实际领导者,尚钺和荣孟源是1949年后曾被大规模批判的史学家。《华北大学第二部教育工作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附有一张课程安排表,其中显示史地系课程主讲人为:尚钺(“中国近代史”)、尹达(“中国通史”)、刘桂五(“近代世界史”)、王南(“史学方法研究”)、孙敬之(“自然地理”、“中外地理”)。前四位,都是来自北方大学。
北方大学开设的史学课程及其授课效果,只能从一些回忆材料中再现一二。文教学院的史学课程有“社会发展史”、“中国近代史”、党史等。[30](P64)范文澜处理行政事务之余,会亲自给学生讲授“社会发展史”、“中国通史”及《联共(布)党史》。[31](P51-52)除了固定的课程,还有演讲会。刘大年指出,范文澜曾经在1946年夏天暑期讲演会上讲过《研究中国三千年历史的钥匙》。[32](P184-185)也有当时的学生回忆党史的学习情况:
在北大(按:北方大学)系统学习了中国共产党史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等一系列的有关党的斗争史。对许多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记得历史研究室的孙超同志讲共产党的成立,五次反围剿和省港大罢工等课,给我的印象都很深。[33](P83)
讲课效果,可能因人而异,也有材料反映有学生对某著名教授的讲课效果提出批评意见:
有一次,一位著名的历史教授拿着学生提意见的纸条当众宣读,其中一条意见写道:“老师讲课不生动,我原来对历史很有兴趣,听你这么一讲,我学历史的趣味都没有了”。念了之后,引起哄堂大笑。[34](P27-28)
在这篇文章中,引起笔者特别注意的事情,除了讲课效果外,还有一个是指出当时北方大学的主政者和教师主动积极地听取学生的意见:
学习中,提倡民主作风,互相学习,互相帮助,既耐心帮助别人,也善于听取别人的正确意见。特别是教师,能够经常虚心听取学生的意见。有的意见虽然提得很尖锐,甚至很刻薄,但教师也能虚怀若谷,从善如流。[35](P27)
也就是说,在北方大学,教师或相关人员虚心听取学员意见,是经常性的,而且也能认真对待学员的意见,正如前述著名教授对学生批评其讲课效果不好而诚挚道歉一样。联系到“漫谈”,大约可以感觉到,这种相关管理人员或教师通过“漫谈”等方式,认真听取学生对学习、生活等方面的意见,是党办大学的一种惯例。明乎此,就能更好地理解为何会有这份“漫谈”的产生。
综合以上分析,大致可以作出以下判断:华北大学的史学教育是在整合了华北联大和北方大学两个机构相关资源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大体上说来,课程设置可能主要继承了华北联合大学,而师资上,则以北方大学为中坚。
四、华北大学的史学课程及授课情况
作为“华北解放区之最高学府”、“革命力量的一大源泉”[36](P31),华北大学共设四个部:第一部为短期(六个月)政治训练班性质,任务是对新入学学员进行思想政治改造,初步奠定革命的人生观,了解中共的纲领和政策,体会革命工作者应有的工作作风,主任为钱俊瑞;第二部的任务是培养解放区中等学校师资,分设教育、外文、史地、哲学等系,主任为何干之;第三部为文艺学院,主任为沙可夫;第四部为研究部,任务是储备各科研究人才,设中国历史、哲学、中国语文等8个研究室,主任为范文澜。[37](P241-244)从机构设置的情况来看,华北大学已经是一个任务多、机构较复杂的高等教育机构。因此要梳理华北大学的史学课程,应该分从两个角度考察,一个是史地系的专业课程,一个是其他院系的史学课程。
史地系的课程如何设置,除了“漫谈”透露的信息以外,“方案”对第二部的任务、课程设置、授课计划等,皆有详细记载。“方案”指出:
第二部是华北大学的教育学院,为适应当前恢复、改造与发展解放区中等教育及一般教育工作的需要,暂时采取短期训练办法,培养、提高与改造中等学校师资及一般教育工作干部,使具有为人民教育事业服务的正确观点,必要的业务知识及切合实际的教学技能。[38](P1)
由于这一独特定位,第二部根据需要,共设置了五个系和一个训练班。这六个分支机构的任务各不相同:教育系是“培养师范教育师资及一般教育行政干部”;社会科学系是“培养中等学校的政治教员”;国文系是“培养中等学校的国文教员”;史地系是“培养中等学校的史地教员”;外语系是“培养中等学校的外语师资及中级翻译人才”;教员训练班是“为中等学校其他各科教员进行政治教育”。
第二部的课程分为公共必修课和业务课两类。公共必修课有“社会科学概论”、“哲学”、“教育概论”三门,分别由何干之、谢韬、丁浩川担任讲授人。史地系的业务课为“中国近代史”、“中国通史”、“近代世界史”、“史学方法研究”、“中外地理”、“自然地理”。各业务课讲授重点如下:“中国近代史”重点讲授“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英法联军、甲午战争、戊戌政变与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抗日战争”;“中国通史”重点讲授“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以封建社会为主)”;“近代世界史”重点讲授“法国大革命、德国农民战争、俄国十月革命”;“自然地理”重点讲授“绪论(评资产阶级地理学说)、大气环流、宇宙光、星的例算、星的形成、界限、四季与一天”;“史学方法研究”、“中外地理”未列讲授重点。[39](P1-4)
以上作为华北大学教务处印制的文件,本应是最可信的,但是将“方案”和“漫谈”对照,不免让人疑惑不已。因为上述这些课程,无论是二部的公共课,还是史地系的专业课,其中多条信息都和“漫谈”对应不上。
在公共必修课方面,漫谈中有“国文”课,“方案”中没有。在专业课方面,值得分析的差异之处更多:第一,“漫谈”中“美国侵华史”是重点讨论课程,而“方案”中没有此课;第二,“漫谈”中有“第二组同学都同意适当地添一门唯物史观或历史研究法或历史哲学这样的课程”;“方案”中列有“史学方法研究”课;第三,“漫谈”中有“史料选读”、“教材研究”课,而“方案”中没有;第四,“漫谈”显示中国地理和外国地理进度不太协调,“方案”中显示有“中外地理”。
需要说明的是,《华北大学成立典礼特刊》中刊登的《华北大学介绍》与“漫谈”的课程信息比较一致:
共同必修课程有三门,即国文、社会科学概论及教育概论……史地系有中国通史、史料选读、世界革命运动史、美国侵华史及中外史地等。[40](P28)
如何理解“漫谈”、《华北大学介绍》与“方案”关于课程设置的歧义抵牾?一种可能的推测是,“漫谈”显示的是一个过渡的史学教育体系,“方案”则是在吸收了“漫谈”等反馈意见后,形成的一个较为正式的教育方案,显示了华北大学的教育体系正在走向成熟。由于缺少授课情况的详细资料,很难做进一步判断。但是有一个旁证可证明这一推测或许比较接近历史真实。华东大学1949年中期的记录显示,华东大学教务管理人员曾到华北大学考察学习,并得出这样的认识:
教学实行集体讨论分别讲授办法,同时注重学生意见之反映,做到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值得吾人重视参考。[41](P3)
此条材料不仅可以用来说明“方案”是在吸取了学生意见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也说明了为何山东大学图书馆会收藏这份“方案”。
可以肯定的是,不管是“漫谈”还是“方案”,皆反映出华北大学史地系的教育比较符合“战时教育”的特点。“战时教育”的观念缘起于抗战爆发,是为了适应战争需要对常态教育的必要调整,以适应斗争需要。抗战结束以后,内战很快开始,“战时教育”在解放区延续。陕甘宁边区政府在1946年12月10日就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战时教育方案》,要求:
各级学校及一切社教组织亦应立即动员起来,发挥教育上的有生力量,直接或间接地为自卫战争服务。一切教育工作者都应成为保卫边区的宣传员与组织者。目前教育工作的中心任务是配合军事、政治、经济、群运等工作,争取人民自卫战争的胜利。[42](P30)
虽然华北大学成立后的形势与1946年已有所不同,但是教育要为战争服务,并力求帮助中共取得斗争胜利,仍然是第一任务。正如吴玉章校长在开学典礼讲话时开宗明义指出的那样,“华北大学是一个革命的大学”,它要“为完成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43](P7)
以上借助相关原始文献,对华北大学史地系的课程设置及授课情况进行了梳理,并对不同文献的歧义抵牾之处进行了解析。但这只是华北大学史学教育的一个面向,我们还需对其他院系的史学类课程有所梳理。
由于未能见到比较完整的华北大学全校课程表,对这一问题的梳理,主要借助于其他一些文献。《华北大学介绍》对华北大学各机构的课程设置有相对完整的记录,其中指出:一部的史学类课程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史”,二部教育系有“中国近代教育史”,社会科学系有“中国社会发展史”[44](P28)。此外,据学员回忆,三部有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史等课程[45](P63);农学院学生入学后,也要进行三个月的思想政治教育,“学习《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党史》”[46](P86)。1948年年底的一份介绍华北大学生活的资料指出,第一部的政治班是“华大之重心”,学习期限是六个月,“学习的课程有社会发展史、中国近代史、解放区建设,中共介绍及新民主主义等”[47](P31)。在“方案”中,特别指出以上课程为“政治思想课”,且标注“一部转来学生免修”[48](P3)。根据这些材料,我们似乎可以将这些课程理解为华北大学学生的必修课。此外,还有一些演讲也是史学的内容。
仅从课程设置上看,华北大学各科系史学课程已不少,如考虑到学员们大多只有六个月的学习时间,史学在教育体系中的重要性当是进一步增加了。华北大学重视史学教学,除了传统和形势的需要外,可能和吴玉章校长个人也有一些关系。1952年9月进入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班学习的韩大成回忆说:“我们历史课也是共同课,因为吴老是搞过历史的,他认为中国人都得懂中国的历史。”[49](P405)
另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些课程中的“中共介绍”,基本上也可以理解为中共党史课。华北联大和北方大学合并为华北大学之际,党中央就决定在华北大学开设“中共党史”课,胡华担任了中共党史教学组组长,并负责编写教材。这部教材就是1950年3月出版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50](P286-287)据彭明的回忆,“中共党史”,实际上就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但是范围有所扩展:
为了贯彻毛泽东的“古今中外”法,也有必要把“五四”以前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史”加叙一段,以说明党史的来龙去脉。于是,胡华当时把我调去起草自鸦片战争以来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史,主要依据是范老的《中国近代史》。[51](P26)
也就是说,早在华北大学成立之初的1948年8月,“中共党史”就已经独立于“中国近现代史”课,成为华北大学学生的重要课程。关于这一点,还可以从吴玉章在华北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得到印证。吴玉章指出,要学好“毛泽东思想”,必须借助革命的史学教育。因为,“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之一就是中国历史:
它是从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长期革命斗争中,在中国伟大的四次革命战争——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现在的人民解放战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它是站在全体人民利益的立场上,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方法,概括中国历史、社会及全部革命斗争经验而创造出来,用以解放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理论与政策。[52](P7)
梳理至此,我们对华北大学史学教育的课程设置、教学效果及其原因已有了一定的了解,在史学教育的诸多方面,还有一个方面需要有所交代——教学方式。
华北大学的教学方式和常规大学不太一样,尤其是第一部,除了教师讲大课外,主要方式是漫谈、座谈和辩论:学习以小组讨论为主,先是漫谈,发现问题,然后是座谈,“把漫谈所归结的问题,继续讨论,最后总结为一两个原则性问题”,最后是辩论,“将原则性问题经过彻底的辩论,得出一个圆满的解答”。[53](P20)这种学习方式,在“漫谈”中也有体现,这一意见就是两个小组漫谈的产物。辩论可能还不仅仅存在于学员之间,教师之间也会对一些问题进行公开讨论。比如当时李何林准备给学生讲授“近三十年中国新文学运动大纲”,范文澜、钱俊瑞、何干之等对其“关于中国新文学的性质和五四时代新文学的领导思想”等问题提出了不同看法,往返讨论多次,学校还将讨论信件油印,供广大师生讨论使用。[54](P181)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华北大学的史学教育还继承了自陕北公学时期就形成的良好传统——理论联系实际。[55](P39-40)除了讲授、辩论等学习形式外,华北大学还采取了课外实践教学的方式。有学员回忆说:
为了配合党史、中国近代史学习和革命斗争的需要,学校还组织我们参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参观冀中正定县三邱村地道战遗址。[56](P153)
这种课外教学的方式,在华北联大的教学中也有体现。联大史地系的同学,就曾经参加过三次土地改革工作。[57](P16-17)
五、余论
本文借助《史地系小组漫谈对课目的意见(共两组)》这份新发现的材料,粗略梳理解析了华北大学史学教育的一些情况。笔者以为,只有将这份文献放置到中国近现代史学史,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以及革命史的大脉络中,才能将这一文献透露的信息解读清楚,并更好地认识到这一文献的价值:华北大学的史学教育,既是“战时教育”的具体体现,也是“战时史学”的具体体现。正是由于华北大学的实践,1949年之后中国大学的史学教育才能在短时间内,从民国时期培养专精的史学研究者模式向“为革命服务”的新模式转变。
这一论断主要基于两点认识。第一,华北大学的史学教育是“革命史观”在教学中的全面实践,为1949年之后的教学积累了必要的经验。这种教育的性质是“战时教育”,其内容则是“战时史学”。关于“战时史学”,王学典教授曾经指出:
所谓“战时史学”是在战争中产生的、以“战时历史观念”为灵魂的、从属于救亡与战争的史学规范,它由“战时历史框架”、“战时学术导向”、“战时文化心理”和“战时历史观念”等几重内容构成。[58](P4-5)
“战时历史框架”和“战时学术导向”在华北大学史学教育中的最显著体现,就是“革命史观”在教学中全面实践,“中国近代史”、“近代世界史”、“美国侵华史”、“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史”等课程,都是以“革命”为重点,这一点在 “漫谈”、《华北大学的学习和生活》、吴玉章《在华北大学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及“方案”等文献中皆有体现。而“战时文化心理”和“战时历史观念”等,在上述文献及《陕甘宁边区战时教育方案》等文件中亦有体现。比如“方案”特别指出:“教学是政治任务,是革命宣传,所以应有慎重负责的态度。”[59](P7)可以说,无论教学是“革命宣传”的精神导向,还是“革命史观”为导向的教学重点,都对1949年以后的史学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点认识是,以“革命史观”为指导的历史类教材在华北大学时期初具规模,影响深远。当时的华北大学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主要聚集地,这些史学工作者聚集在一起,主要任务就是编写相关教材。
一、中国历史研究室,由范文澜同志兼主任,刘大年同志为副主任。现集中力量研究并编写中国近代史。二、哲学研究室,由艾思奇同志兼主任。现集中力量研究并编写中国近代哲学史。[60](P29)后来在实际运作中,第四部的任务有所扩大,曾任第四部研究员的赵俪生回忆到:
第四部的研究课题当时是有限的,几个青年人帮范老修订与续写《中国通史简编》,这是一个课题。由范老带头、由支部书记刘大年实际领导的《中国近代史》,又是一个课题。由艾思奇担任组长、由我担任副组长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龚自珍、魏源、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思想的,又是一个课题。[61](P195)
毋庸置疑,《中国通史简编》(范文澜)、《中国近代史》(范文澜)、《社会发展史》(艾思奇)、《美国侵华史》(刘大年)、《中国历史教程绪论》(吴玉章)、《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胡华)及《中国新文学史研究》(李何林)等教材或著作,对1949年之后中国大陆文史学术的发展,产生了全局性的影响。这些教材与著作和华北大学皆有着直接的关系,有的是在此时定稿、出版,有的是在此时孕育写作。
最后,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华北大学的史学教育虽然存在不足,但是坦诚积极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不足。“漫谈”显示了华大学员对教育质量有更高的要求,希望课程设置更合理,讲解更清晰,能够提供优质的教材等,体现出革命青年认真学习的进取意识。而教学管理组织者也能够积极倾听学员的意见,并及时解释、改进,体现出革命大学教育工作者努力工作的负责风气。字里行间,渗透出一种坦诚积极的精神,这种精神,不应该是仅仅在革命年代才有,这种精神,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宝贵财富,也是大学教育者应当继承发扬的优秀遗产。总之,作为解放战争时期党办大学的代表,华北大学虽然短暂,但是在各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值得我们继续深入研究。
[1] 郑之书:《清末民初的历史教育(1902—1917)》,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学位论文,1991;严志梁:《我国的历史教育和历史教科书》,载《课程、教材、教法》,1995(10);桑兵:《教学需求与学风转变——近代大学史学教育的社会科学化》,载《中国社会科学》,2001(4);刘中猛:《晚清新学堂与中学堂历史教育研究》,南京,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3;史雅雯:《论建国初期的中小学历史教育改造(1949—1956)》,扬州,扬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
[2] 姜萌:《“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20世纪20年代中国现代文史之学的形成历程》,载《史学月刊》,2017(1)。
[3] 中国人民大学校史研究丛书编委会编:《中国人民大学纪事(1937—2007)》,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王晋:《华北大学的历史与业绩及其深远影响》,载王晋、汪洋主编:《华实录——华北大学回忆文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4] 朱仲玉:《一九一九至一九四九年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载《史学史研究》,1982(2);刘茂林、叶桂生:《四十年代后期的中国史学倾向》,载《史林》,1987(3);蒋大椿:《八十年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一)》,载《历史教学》,2000(6);张剑平:《华北革命根据地的马克思主义史家与史学》,载姜锡东编:《华北区域历史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2。
[5] 杨东、郝平蕾:《陕北公学的史学教育与社会实践》,载《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6(2)。
[6] 王从军:《孙敬之传》,北京,新华出版社,1993。
[7] 尚钺:《经历自述》,载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编:《尚钺先生》,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8] 谢韬:《纪念尚钺同志诞辰九十周年》,载《群言》,1992(7)。
[9] 周秋光:《刘大年传》,长沙,岳麓书社,2009。
[10] 刘文哲、赵鸣九、张奇:《张家口中学各科教学视察总结》,载《察哈尔教育》,1949,1(2)。
[11][16][20] 中国人民大学校史研究丛书编委会:《中国人民大学纪事(1937—2007)》,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12] 丁蔚:《忆青岛女中第一届学生自治会》,载中共青岛市委党史资料征委会办公室编:《青岛党史资料》,第四辑,青岛,青岛市出版社,1989。
[13][45][46][56] 王晋、汪洋主编:《华实录——华北大学回忆文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14][37] 成仿吾:《战火中的大学——从陕北公学到人民大学的回顾》,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15][38][39][48][59] 华北大学教务处:《华北大学第二部教育工作实施方案》,华北大学教务处印制, 1949。
[17][28][55] 中国人民大学校史研究丛书编委会:《造就革命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大学校史》,第1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18][21][57] 《人民的大学:华北联大介绍》,哈尔滨,东北书店,1948。
[19] 教育阵地社编:《抗战时期边区教育建设》(上),张家口,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1946。
[22][25] 彭明:《忆浩川师》,载《留取丹心:丁浩川纪念集》,出版信息不详(内部资料),1992。
[23][50] 胡华:《胡华自传》,载《晋阳学刊》编辑部编:《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1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
[24] 智长春:《智建中》,载中共长春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长春党史人物传》,第4卷,长春,长春出版社,1994。
[26][27][51] 彭明:《科学研究的艰苦岁月——忆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编写》,载《彭明文存》,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
[29][30][33][34][35] 韩幸茹主编:《回忆北方大学》,长治,北方大学校友会/长治市地方志办公室,1991。
[31] 一丁:《范文澜与北方大学》,载《文史月刊》,2004(2)。
[32] 刘大年:《北方大学记》,载《近代史研究》,1991(3)。
[36][47] 以空:《华北大学的学习和生活(待续)》,载《群众》(香港),1948,2(50)。
[40][43][44][52][60] 华北大学成立典礼筹备委员会编:《华北大学成立典礼特刊》,正定,华北大学,1948。
[41] 《教师联谊会第二组四五六七月学习总结》,载山东大学档案馆藏:《华东大学档案》49-1-7。
[42] 《陕甘宁边区战时教育方案》,载《红色档案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编委会编:《红色档案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汇编》,第12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
[49] 中国人民大学校史研究丛书编委会:《求是园名家自述》,第1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53] 以空:《华北大学的学习和生活(续完)》,载《群众》(香港),1949,3(2)。
[54] 余飘:《记华北大学一次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性质与领导思想的讨论》,载《新文学史料》,1991(2 )。
[58] 王学典:《五朵金花:意识形态语境中的学术论战》,载《文史知识》,2002(1)。
[61] 赵俪生:《赵俪生学术自传》,载《赵俪生文集》,第5卷,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
Abstract: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has achieved great progress,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weaknesses.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research, the education of history is relatively weak. In terms of time, from 1940s to the period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re are still a lot of blank space. In 2015, a valuable manuscript “A Ramble on History and Geography Department about the Opinions of the Subjects(two groups)” was accidentally discovered when the information room of the History Department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was relocated. The material, produced in early 1949 in North China University, not only involv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istory education in the revolutionary base which is rare and precious, but also can reflect the changes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around 1949.Through this literature, we realized that the history education of North China University was originated from North China United University and North College. It inherits the curriculum of North China United University and the main teaching staff of North College. Through the arrangement of the history courses and the teaching situation i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hina, we can co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history education of North China University is not only a concrete manifestation of “wartime education” and “wartime historiography”, but also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rapid change of the history education model in 1950s. All these have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Marx’s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Keywords: North China University; history education; Marxist historiography; wartime education; wartime historiography
(责任编辑张静)
HistoryEducationinNorthChinaUniversity——TheAnalysisofaRecordof“ARambleonHistoryandGeographyDepartment”
JIANG Meng
(School of Histor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
姜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872)
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青年明德学者项目”(13XNJ021)
* 特别感谢刘文远老师允许使用他发现的这份《史地系小组漫谈对课目的意见(共两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