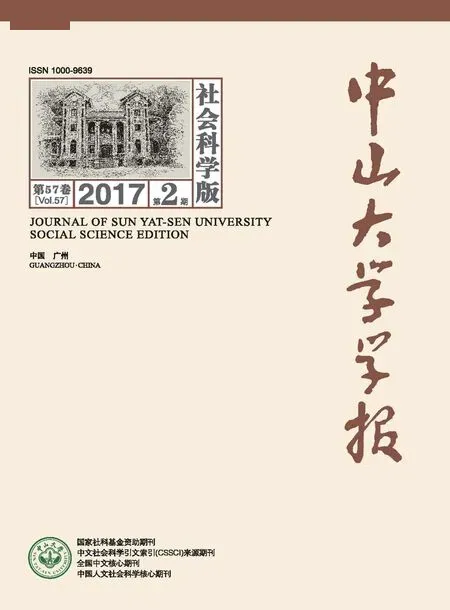新教传教士与19世纪汉语圣经诠释的开端*
曹 坚
新教传教士与19世纪汉语圣经诠释的开端*
曹 坚
西方新教传教士来华后,很快顺应19世纪科学时代背景下的基督教神学发展和中国汉语语境的要求,将圣经作为西学的基本的和有机的成分呈现给中国的读书人,融入西学东渐的潮流;同时,他们还与中国同工一道探索和更新,连续不断地将圣经翻译成深浅不同的文言甚至官话,以求达到最佳的可读性效果。在这些新教传教士所主导的最初的汉语圣经诠释活动中,来自旧约的素材原本属于希伯来文化,在基督教文化和儒家文化的限定和想象之下,在时局面临挑战的情况下,被诠释出的效果显示了一种类似全球化时代的对话关系。这种建立在差异基础上的对话关系产生的作用和反作用,尤其反映在对于古代以色列历史和民族“他者”形象的再造和叙述中。这一“他者”的再造和叙述与19世纪末甚至20世纪中国人的历史和自我意识遥相呼应。
新教传教士; 西学东渐; 圣经翻译; 旧约
前 言
“圣经在中国”不是陌生的研究领域,特别是在基督教和新约圣经方面;但旧约和与之密不可分的希伯来文化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是我们对其获得完整、恰当之理解所不可忽略的。旧约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开始成为启迪中国读者的一个源泉,无疑取决于旧约在汉语语境中开始译介和传播,取决于它不仅作为西方宗教,而且作为西方历史和文学经典的开始被认可。这当中不免有被重新建构和想象的古代以色列历史、旧约乃至犹太人形象,也蕴含不同文化在观念上的融合、冲突和启迪。本文拟从旧约的汉译和它在西学东渐中被当作西学的有机部分两个方面,展现汉语旧约诠释的开端。文章将描述西方新教传教士在向19世纪的中国读者介绍旧约时遵行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策略,回顾最初在汉语语境中诠释和转化旧约观念和人物形象的、由西方传教士与华人同工一道参与的、将旧约翻译为汉语的诸多努力。
一、19世纪西学东渐中的旧约
在与中国政府和社会的接触中,汉人的华夷思维给传教士留下了深刻印象*John King Fairbank, Introduction: The Many Faces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John King Fairbank, ed., 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 15.。19世纪上半叶,来华的西方新教传教士“主要是靠印刷品”进行传教*John King Fairbank, Introduction: The Place of Protestant Writings in China’s Cultural History,Suzanne Wilson Barnett and John King Fairbank, eds., Christianity in China: Early Protestant Missionary Writing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 6.。他们先以印发宗教小册子为主,但很快就发现它们无力应对这里的民族中心主义环境。这些福音小册子在宗教内容上十分保守,难以引起中国读书人的兴趣,遑论得到他们的认同。传教士需要表明:西方具有与中国一样高度发达的文明;西方文明中的基督宗教传统值得尊敬和接纳;西方传教士类似中国传统里的学者兼导师*Jane Kate Leonard, W.H. Medhurst: Rewriting the Missionary Message,Barnett and Fairbank, eds., Christianity in China, pp. 50-51 and 53; Fairbank, Introduction: The Place, p. 13.。因此,早期新教传教士对小册子的内容加以调整,重视世俗学问,同时把宗教观点融入更广阔的历史和文化类印刷品中,以供非教会场合使用和传播*Leonard, W.H. Medhurst, pp. 47-48.。19世纪下半叶的情况更是如此。第二次鸦片战争及相关条约签署后,越来越多的商埠和都市对传教事工进行了解禁开放,促进了中国人与西方的读书人,特别是与传教士的交流。这种交流首先和更多地发生于对圣经的介绍和解读,并且这种介绍和解读不可避免地带有传教士所属差会、时代甚至国籍的强烈印记。
在西方,19世纪以其对自然世界认识的快速提升而被称为科学时代。由于意识到人类同样受自然世界的法则和变化过程的制约,关于宇宙的整个观念都发生了改变。观察、演绎、归纳和实验的科学方法不仅应用于纯科学学科,还应用于人类思想和活动的几乎所有领域*William Damper, A History of Science, New York: MacMillan, 1949, 4th rev. ed., p. 200.。此时,西方的世界观主要由牛顿关于宇宙和达尔文关于人类的理论构成*D.W.Y. Kwok, Scientism in Chinese Thought 1900-195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5, p. 28.。牛顿提供了一幅人与世界的唯物主义图景,却没有否认上帝创造宇宙:自然是自行运转的力学系统,是人类认识上帝这位设计者的意志的主要来源*Fairbank, Introduction: The Many Faces,pp. 8-9.。也在此时,关于自然世界的知识和对于宇宙的认识主要由新教传教士译介到国门渐开的中国。美国监理会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1836—1907)曾说:没有传教士的翻译作品,中国人可能对西学一无所知*William Damper, A History of Science, New York: MacMillan, 1949, 4th rev. ed., p. 200.。尽管忽略了中国译者的作用,他的话基本上还是对的。为了应对科学时代的挑战,19世纪的基督新教建立了所谓的自然神学。新教传教士们相信,传播科学的同时也传播了基督教的自然神学。
为了消除达尔文主义对基督教的威胁并调和两者,传教士极力在基督教和进化论之间寻找契合点,以图建立进化的有神论。在现代科学发现阐述了地球的进化之后, 英国伦敦会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1829—1890)将这一进程归因于上帝的智慧,并将上帝比作一位园艺设计师*韦廉臣:《稽之地球可知上帝之主宰》,《万国公报》1881年5月7日,第339a页。。美国公理会孺里(John Gulick,1832—1923)指出,与其他科学理论相比,进化论有助于表明人类的肉体和精神活动能很好地与自然界相适应,无论何地的生物,适应环境才能生存,因为上帝与此环境同在。因此,进化的证据说明,有理性的人类需要在宗教上信仰上帝*John Gulick, ‘The Theory of Evolution in Some of its Relations to Christian Theology’,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以下简称CR), Vol. 16 (1885), pp. 295-297.。
通过将世俗知识与神圣信仰相结合,自然神学同时使世俗文明和基督教合理化,而且强调两者间的内在关系。
首先,传教士高度赞扬宗教在现代科学发展中的作用,宣称不论在理论还是实践层面,现代基督教文明在根本上与科学进步密切相关;科学发韧于基督教,因而绝不可能将两者分离*Calvin W. Mateer, What is the Best Course of Study for a Mission School in China, Records of the Second Triennial Meeting of the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6-9, 1896,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6, p. 52.。英国浸礼会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写道:
西方文明的改革是美妙和巨大的;但相对而言,这些只不过是枝节而已。基督教才是取得成就的最重要来源,因为它在人类生活的物质、思想、政治、社会、道德和精神等方面,都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真正的基督教是永不枯竭的,圣灵导向全部真理,使我们在爱中完善。*Timothy Richard, ‘The Historical Evidences of Christianity——Present Benefits’, CR, Vol. 22 (November 1891), p. 498. 本文所引传教士言论皆为笔者自译,斜体为作者强调。
其次,传教士认识到,科学和宗教是互利和互补的。科学为关于摩西的记录提供科学支持,而上帝的启示为科学提供道德生命力。他们相信,世俗知识与基督信仰相结合才使世界完美无缺*佚名:《祥证天道启》,《万国公报》1882年9月16日,第50a页。。他们意识到,用自然神学的论证可使基督教最有效地引起高度理性的中国人的兴趣*胡卫清:《近代来华传教士的科学观》,章开沅、马敏编:《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丛刊》第3辑,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48页。。
至于旧约,因其在世界历史、基督教和西方文明中的重要性而被视为西学的一部分。用美国浸礼会耶士摩(William Ashmore,1824—1909)的话来说,人们应该学习旧约:
因为旧约是使人了解人类历史和探寻万国起源的钥匙,是开展任何人类研究的起点……因为历史根基对于一个教义信仰具有超越性的重要意义……因为对于理解荣耀的完整性,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就是透彻理解有关神在火焰中颁布律法的整个境况。虽然我们把它们称为犹太的和地区性的,但他们却为所有正义的法律制度奠定了基础;这样,人就能在神的荣耀来临之前认识正义。*William Ashmore, ‘Why We Should Study the Old Testament’, CR, Vol. 23 (June 1892), pp. 249-255.
这段话涉及古代以色列历史记忆中神拯救他们脱离法老的奴役并为之立法的故事*参《旧约·出埃及记》三至二十三章。。耶士摩明确将人类历史和社会发展中正义的终极标准与神的公正怜悯的本质属性以及神的拯救大能和信实联系起来。在儒家传统中存在这样一个悖谬:正义之念源自人伦道义,而正义之举却又往往只能捐弃人伦,政治正确实际上是一整套国家话语,而各为其主的忠诚又难以排除在国家话语之外,这当中几乎没有个人选择的余地*李庆西:《魏延之叛》,《读书》2016年第4期,第122页。。像耶士摩这样的传教士,其悖谬恰好凸显旧约里包含神拯救事件的“历史根基对于一个教义信仰具有超越性的重要意义”,只有这种超越性才能使神的律法为“所有正义的法律制度奠定了基础”。
旧约与西学的关系也反映在旧约研究中所运用的新视角和新方法以及把旧约研究当作学术或科学研究门类的趋势上。这包括:将考古或地质发现以及索引、历法、地图和图表制作等科学辅助手段用于圣经地理研究*相关例子可参George Owen, ‘The Mosaic Account of the Creation Geologically Considered’, CR, Vol.13 (January-February 1882), pp. 1-17; Jasper S. McIlvaine, The Garden of Eden, CR, Vol.6 (September-October 1875), pp. 344-362; 无名氏《犹太地理择要》英文书评, CR, Vol.14 (March-April 1883), pp. 152-162。;用生物学研究法考察圣经中的动植物*这类专题研究可参R.H. Graves的一系列文章:CR, Vol.10 (March-April 1879), pp. 124-128; Vol.14 (November-December 1883), pp. 479-485; Vol.22 (April 1891), pp. 157-161; Vol.22 (June 1891), pp. 253-255; and Vol.23 (April 1892), pp. 158-162。;研究旧约历史*参《圣史记》的英文书评,‘Our Book Table’, CR, Vol.18 (July 1887), p. 287; 花之安(Ernest Faber)对《玩索圣史》的英文书评,‘Our Book Table’, CR, Vol.24 (February 1893), pp. 90-91。,同时将它与世界古代史研究相联系*参Canon T. McClatchie, ‘The Jewish Nation’, CR, Vol.9 (March-April 1878), pp. 81-85。;努力消解现代科学和旧约之间的矛盾*参法国国立图书馆考古学家Francois Lenormant所撰The Beginnings of History According to the Bible and the Traditions of Oriental Peoples from the Creation of Man to the Deluge一书的英文书评,CR, Vol.14 (March-April 1883), pp. 152-162; The Scriptures in the Light of Modern Discovery and Knowledge一书的英文书评,‘Notices of Recent Publications’, CR, Vol.13 (March-April 1882), pp. 158-160; The Harmony of the Bible with Science一书的英文书评, CR, Vol.14 (May-June 1883), p. 245。;用比较神话学方法研究创世记*参佚名:‘Noah-Nüwa (女娲), Are They Identical?’ CR, Vol. 36 (June 1905), p. 297。;对圣经文本进行高等批判(Higher Criticism)研究等*参佚名:《圣书旧约疑证——摘录圣学指要》,《万国公报》卷12,1880年1月24日, 第210b—211b页。。
对于达尔文主义和科学勃兴带来的人和人类世界的新观念,神学的回应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神学决定了传教士传教的对象和策略,也决定了最可能接触到自由主义神学并受其影响的阶层和读者。信奉自由主义神学的传教士自认为是现代派,相信使宗教适应当代文化的发展不仅是大势所趋,而且是正当的*Fairbank, Introduction: The Many Faces,pp. 8-9.。来华新教传教士传教的主要对象集中于尊奉儒家经典,对历史和文学推崇备至且相信文以载道的中国读书人。对于传教士而言,圣经理所当然才是真理的来源和检验真理的试金石。在美国公理会裨治文 (Elijah C. Bridgman,1801—1861) 看来,挪亚的儿子来到中国时带来了宗教的真理,但后来的摩尼教大纷争使各种邪恶势力横行,千百年来侵蚀中国,导致宗教真理在这里丧失殆尽。他解释道,只有将中国经典文献中蕴藏的古代宗教真理与现代圣经的真理有机相连,中国的异教信仰才有可能得到根除*Fred W. Drake, Protestant Geography in China: E.C. Bridgman's Portrayal of the West, Barnett and Fairbank, eds., Christianity in China, p. 93.。许多传教士采取比较的方法,以求中国读者认识这种联系和西方文明的存在*参J.S. McIlvaine, ‘Cushite Ethnology’, CR, Vol. 6 (September-October 1875), pp. 344-362; ‘Noah in China’, CR, Vol. 11 (July-August 1880), pp. 251-259; and T.P. Crawford, ‘The Ancient Dynasties of Berosus and China Compared with Those of Genesis’, CR, Vol. 11 (November-December 1880), pp. 411-429。在这些文章中,作者试图证明旧约记载和现存中国文献记载的一致性。。
英国伦敦会麦都思(Walter H. Medhurst,1796—1857)和德国路德会郭实腊(Karl Friedrich A. Gützlaff,1803—1851)主编的传教士杂志《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充分意识到了中国人对历史的尊重。该杂志在1833年7月到1834年6月的每一期中辟出好几页的篇幅,说明古代西方与古代中国有同等悠久的历史;并将中国和西方历史纪年进行比较:中国历史从盘古到宋朝,西方历史则从亚当到罗马帝国,最后到大英帝国*麦都思:《东西史记和合》,《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3 年7月至1834年6月各卷。。同样,旧约故事被用以解释中国的起源,而古代汉语也与巴别塔以及语言变乱的创世记故事相连*《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卷1,1837年,第4a—b页。纪年比较的方法也为同时期和后来的不少中国作者采纳。。对于郭实腊,西方文明的意义应从整体上把握;换言之,历史是上帝意志的运作和道德指导的一种方式,伦理与政治交织其中,知识和神学都是基督教的使女*Gützlaff, ‘Remarks on the History of China’, Chinese Repository, Vol. 2 (July 1833), pp. 119 and 127; Gützlaff, Literary Notice,ibid., Vol. 2 (August 1833), pp. 186-187.。所谓的“自然法”乃出于上帝对自然的设计*参郭实腊:《贸易》,《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卷1,1838年,第8—11页。。这家杂志使用文言文,大部分文章极力模仿汉语文体的形式和风格,这或许得益于郭实腊雇用的多位中国助手,他们当中不仅有皈依基督教的,也有教外的,甚至包括佛教徒*参郭实腊1828年7月14日的信件,收于Jacob Tomlin, Missionary Journals and Letters: Written During Eleven Years’ Residence and Travels Amongst the Chinese, Siamese, Javanese, Khassias, and other Eastern Nations, London: James Nisbet and Co., 1844, pp. 149-150, 188-189, 218-219, and 329。。
在文学方面,郭实腊早在1830年代就编写和出版了以色列先祖和摩西的传记文章,即《摩西言行全传》和《圣书列祖全传》。前者是关于摩西作为伟大立法者的传略,开篇为摩西的谱系和出生,接着详细列举了他一生中与其直接或间接有关的重大事件、十诫和法律制度;后者是关于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历史*爱汉者 (郭实腊笔名):《摩西言行全传》,新加坡:坚夏书院,1836年;郭实腊:《圣书列祖全传》,新加坡:坚夏书院,1838年。关于此后传教士对旧约叙事的关注的例子,可参无名氏对于The Representative Men of the Bible一书的英文书评,‘Our Book Table’,CR, Vol. 37 (September 1906), pp. 513-514。。郭实腊自然是基于上帝的主权来重述这些旧约人物的生平故事的。以摩西为例,他是上帝设立的圣人,被上帝赋予了勇气、能力和智慧。然而,郭实腊笔下的以色列先祖和摩西的形象塑造显然受到儒家圣人概念的影响。摩西与上帝的特殊关系使他具备儒家成圣所需的所有道德品质,因而同时成为本民族的领袖和导师。由于领受了天命,摩西得以通过律法在天下传扬大道*爱汉者:《摩西言行全传》卷1,第1、8页;卷5,第48—49页;卷7,第63页。。来自德国的郭实腊身处19世纪的中国,通过对古代以色列和后来的记录,包括以这些或详或略的记录为依据形成的第二手著述进行考察、梳理、分析和想象,写出以旧约人物为历史题材的传记,是必须在写作过程中密切结合叙事技巧和对历史的兴趣的。
这样,旧约在塑造人物和讲述故事方面的叙事艺术自然而然地受到关注。旧约叙事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在圣经里,上帝既没有向我们提供每一事实……也没有揭示所发生的一切。在圣经中,我们寻找到的,只是圣经提供给我们的有关上帝意图的最基本的东西。”*W.H. Collins, ‘On Some Early Scriptural Traditions’, CR, Vol. 9 (March-April 1878), p. 101.对于为何我们应该从文学角度学习旧约,耶士摩的解释是:
因为旧约的(文学)类型和象征意义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代的变迁,它们得到更为深入和广泛的应用……因为旧约包含了新约中神学词汇的具体描绘和实际定义……因为旧约通过细微有力的人性刻画使人性在人生不同的道德层面丰富而真实地呈现出来,一切都毫无瑕疵地得到准确的体现。(在旧约中)人物的这些刻画和描绘成百上千,因此若想了解人性,旧约的价值强过一百部莎士比亚(的作品)……因为在旧约中,我们清楚看到神和人在日常生活诸多事务中呈现出的合作方式……在新约中,天使只是被视为不言而喻的,而在旧约中,则被具体描绘出来; 天使沿着通向天堂的梯子上下只是众多异象之一……因为旧约是……一个画廊,其中有众多英雄人物值得我们效仿。*Ashmore, Why We Should Study the Old Testament, pp. 252-254.
其实,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传教士开始意识到文学对于传播福音的重要性。林乐知甚至警告,如果传教士无视世俗文学,可能出现另一个黑暗的中世纪*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Press, 1877, pp. 239-240. 另参林乐知:《文学兴国策序》,《万国公报》,1896年5月,第3b—6a页。。传教士中的旧约释经家更倾向于强调旧约的字面意义,而非“劝诫或说教”意义*佚名对《诗篇释义》一书的英文书评,‘Our Book Table’,CR, Vol. 33 (July 1902), p. 361。。他们通常特意就各种旧约译本和旧约研究的工具书的语言和风格加以评论,通俗简单的语言风格则受到称赞。 以《旧约课略》为例,该书译自一本盛行英国的旧约历史教材,作者是格雷兹布鲁克(Michael George Glazebrook,1853—1926)。译者顺应当时中国社会对官话作品的需求,在译文中涉及圣经经文的地方选用了美国圣公会施约瑟(Samuel I.J. Schereschewsky,1831—1906)的旧约官话译本。若按严复所倡信达雅的翻译标准,该译本在这几方面均属上乘*关于该译本的风格,参Cao Jian, ‘The Chinese Mandarin Bible: Exegesis and Bible Translating,in The Bible Translator’, Vol.57, No.3 (July 2006), pp. 122-138。。在译本的引言中,美国公理会主教伯驾(John S. Burdon,1826—1907)写道:“旧约原文的生动、简明和优美是无与伦比的,哪怕在翻译成其他语言之后。我们希望让中国基督徒们熟悉圣经讲述故事的方式。”*伯驾所论转引自《旧约课略》的英文书评,参‘Our Book Table’, CR, Vol. 24 (March 1893), p. 140。的确,在介绍圣经时,与天主教传教士不同,新教传教士更多地引用故事,而非教义;更注重圣经叙事,而非信经的诠释系统*Martin E. Marty, Protestantism,in Mircea Eliade, ed., Encyclopedia of Religions,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1987, p. 28.。毕竟,圣经故事揭示了圣经记录历史事件的特性:圣经更大程度上是被叙述的历史。
二、19世纪的新教圣经汉译
如同佛教的中国化,西方宗教的处境化调适也始于翻译活动,始于选用特定的、具有可塑性外延意义的字词来传达异文化观念。这样,在华传教士就与周围远非被动的环境开始了相互作用的关系*Fairbank, Introduction: The Many Faces, p. 10.。与在华天主教传教士直至1953年才出版完整的中文圣经不同*究其原因,参Nicholas Standaert,‘The Bible in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a’,《世界汉学》卷3,2005年4月,第64—86页。关于天主教的圣经节译,详见Albert J. Garnier, Chinese Versions of the Bible, Shanghai: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1934, pp. 2-14; Jost Oliver Zetzsche, The Bible in China: The History of the Union Version or the Culmination of Protestant Missionary Bible Translation in China, Sankt Augustin: Institut Monumenta Serica, 1999, pp. 25-31 and 418-422; Arnulf Camps, Father Gabriele M. Allegra, O.F.M. (1907-1976) and the Studium Biblicum Franciscanum: The First Complete Chinese Catholic Translation of the Bible, Irene Eber et al., eds., Bible in Modern China: The Literary and Intellectual Impact, Sankt Augustin: Institut Monumenta Serica, 1999, pp. 55-76。,新教传教士从19世纪初来到中国的那一刻起就极为重视圣经的翻译和发行。这原本就是他们传教事工的内在要求,何况此时此地遭遇的中华文明高度发达并赋予书面文字极高的地位。同时,传教士意识到,仅仅通过说教,基督的信息无法以文字的形式保留下来,因而尚嫌不足;必须通过书面文本巩固基督的信息*Eber, Introduction, Eber et al., eds., Bible in Modern China, p. 14.。结果到了19世纪末,他们已完成多达七部新旧约全书的中文译本和数量繁多的选译本*译本目录可参:A Catalogue of Scriptures in the Languages of China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provided by Hubert W. Spillett, comp., London: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1975;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by Alexander Wylie, Philadelphia, 1876; and Catalogue of Publications by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China by A. Wylie, Shanghai: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of Customs, 1876. 至于用方言、少数民族语和拉丁字母拼音所作的翻译,由于它们在使用和发行方面多受限制,不在本文讨论范围。。
第一部完整的中文圣经是由两位浸礼会传教士,即英国的马殊曼(Joshua Marshman,1768—1837)和助手拉沙尔(Joannes Lassar,1781—?)于1822年在印度塞兰坡(Serampore)完成的。在翻译的最初几年里,他们手头没有任何中文资料,且因华人顾问的语文水平欠佳,马殊曼译本文字生硬,词语贫乏,语法不规范,风格也粗糙*John Wherry, Historical Summary of the Different Versions of the Scriptures,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7-20, 1890,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Press, 1890, p. 45.。加之翻译和出版发行工作都是在境外进行的,译本的影响非常有限。
第二部完整的中文圣经,同时也是中国境内的第一部,由伦敦布道会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和米怜(William Milne,1785—1822)完成,1823年出版。这部译本的情况比马殊曼译本也好不了多少。尽管它在英国获得好评,但美国人却对它多有诟病,并且因为语言上的欠缺也没有赢得中国人的青睐。主要翻译者马礼逊是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他住在广州,所接触的粤语与许多汉方言,包括官话,有很大区别。尽管相信中文圣经必须遵循汉语的写作风格,他也没能及时意识到汉语存在风格上的不同*Zetzsche, The Bible in China, p. 20.。加之马礼逊和米怜都没能充分利用中国顾问,译本出版仓促,此译本对于许多传教士和读者来说仍不理想*关于马礼逊的说明,参Zetzsche, The Bible in China, p.64。。
出于对马殊曼和马礼逊译本的不满,麦都思、郭实腊、裨治文和马礼逊之子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1814—1844),在1830年代末完成了第三部中文圣经全译本。这个译本为1840年代在华使用的主要汉译本。麦都思提倡,圣经翻译不应局限于原文语意,而应重视它在非基督教文化中的表达*关于麦都思的说明,参Zetzsche, The Bible in China, p.20。。然而,新约部分因语言不够通俗招致英国人的批评;同时,以郭实腊为主翻译的旧约部分,也被认为缺乏细心和准确的推敲*相关评论,参麦都思于1849年6月30日和10月8日致伦敦传教会的信,Zetzsche, The Bible in China,pp.70-71。。
第一次鸦片战争及相关条约签署(1839—1942)后,传教士和所属差会抓紧了在圣经翻译方面的协商合作,并于1843年在香港召开了第一届传教士大会。会议决定,中文圣经应该“在汉语习惯用法允许的范围内,使意思、风格和手法忠实于希伯来和希腊原文”*Zetzsche, The Bible in China,p.79,并参与会代表所作的其他决定。。有关如何统一翻译诸如“God”、“gods”和“Spirit”这类词汇的问题,首次被提出并加以讨论,但意见分歧很大。还出于不同差会的差异,大会代表后来分裂为两派。第一派当中同属伦敦会的麦都思、米怜、施敦力(John Stronach,1810—1888)和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于1854年翻译了旧约*即伦敦会旧约译本(the London Mission Version OT)。。它与两年前麦都思、裨治文和米怜为主完成的新约翻译合并,称为委办译本(theDelegatesVersion),成为第四部中文圣经全译本。
在语言风格上,委办译本大大优于之前的译本,并广泛使用多年。然而,由于它主要针对的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中文读者,许多评论认为它的文言程度过高。并且一些人认为,它对原文不够忠实,所采用的许多词汇更适于表述中国的哲学*Zetzsche, The Bible in China, p. 103,106-107,120.。相比之下,第二派当中美国公理会裨治文和美国北长老会克陛存(Michael S. Culbertson,1819—1862)完成的译本(1859年的新约和1862年的旧约)则更忠实于原文,对神学生和牧师更有价值。然而,这第五部中文圣经全译本的语言风格含糊而粗糙,远不及委办译本雅致*Zetzsche, The Bible in China, p. 103,106-107,120.。它最终只被美国圣经公会选定,主要为美国传教士所用。
由于不愿意就“baptism”一词的翻译作出让步,浸礼会传教士最终于1868年退出传教士大会,并由高德(Josiah Goddard,1813—1854)、怜为仁(William Dean,1807—1895)和罗梯尔(Edward C. Lord,1817—1887)完成了浸礼会自己的全译本,成为第六部中文圣经译本。因为该译本不是新教的主流译本,故不为大部分传教士所知,且几乎不为后来的圣经译者参考*Zetzsche, The Bible in China, p. 103,106-107,120.。
在19世纪,旧约翻译多用“浅文理”(即浅近文言),以图在赢得儒士们的尊重的同时,又不至于使阅读过于艰涩,从而拥有更多的读者。但考虑到《旧约诗篇》和《旧约箴言》的原文为诗歌体,故译文采纳“深文理”,而它的书评这样评价了文言的优势:
至少对于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他们的整个思维程序都是基于文言这一广受推崇的更高雅的书面风格或由其形成。中国学者醉心于这种风格,几乎无法忍受任何其他的风格……它优美、精炼、表达力强,聪明的读者不喜欢长篇累牍,而这种风格恰恰能以寥寥数语替代之。*文见于 ‘Our Book Table’, CR, Vol. 29 (June 1898), p. 301.
可见,传教士译者一方面会根据原文的体裁,另一方面也会根据读者的阅读能力和习惯决定译文的语言风格。
然而,传教对口语风格的译本的需求日益增长。英国海外圣经公会所属的上海通讯委员会建议用官话翻译圣经。应此建议,在施约瑟的发动下,北京翻译委员会于1864年成立*Irene Eber, The Jewish Bishop and the Chinese Bible: S.I.J. Schereschewsky (1831-1906), Leiden: Brill, 1999, p. 146.。该委员会由美国圣公会白汉理(Henry Blodget,1825—1903)、英国圣公会包尔滕(J.S. Burdon)、英国伦敦会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美国长老会丁韪良(W.A.P. Martin,1827—1916)和施约瑟组成。与之前的各翻译团队相比,他们彼此合作更为宽容密切。委员会还聘请了学问良好的中国学者,以图通过他们的合作,用既不过于书面化也不过于口语化的中文习语进行翻译*Irene Eber, The Jewish Bishop and the Chinese Bible, p. 109-110.关于委员会的更多详情,参pp. 107-123。。十年后的1874年,完整的官话圣经一经面世便大获成功,并在此后的四十多年里(其间于1899年修订),这第七部全译本成为在中国使用最多最广的中文圣经。
从以上回顾可知,新教传教士对圣经的反复翻译使其越来越具有可读性。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在教会期刊ChineseRepository的一篇文章中,一位未署名的作者先谈到圣经译者应“对圣经的原文、经书的形式和结构、古代犹太人的风俗习惯、圣地的地理以及圣经批评等都有非同寻常的了解”,然后讨论将圣经这一外民族的古籍译成中文这一新习得的、完全不同的另一外民族语言时所面临的各种艰巨困难,并承认外国人绝难成就优雅的译文*佚名: ‘The Bible: Its Adaptation to the Moral Condition of Man; with Remarks on the Qualifications of Translators and the Style Most Proper for a Version of the Scriptures in Chinese’,Chinese Repository, No. 7 (November 1835), pp. 299-304.。据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描述,不仅习得汉语离不开中国老师,而且在没有图书馆和辞典的情况下,当一位传教士掌握了宗教词汇,“他更须始终警惕因用词不当造成的含糊……以免贻笑大方,使作者的意图大打折扣。这样一来,他的老师兼同工就成为不可替代的了”*Fairbank, Introduction: The Place, p. 7.。事实上,所有的译本在不同程度上都不得不是传教士和他们的中国顾问合作的成果*早在18世纪,耶稣会士霍雷蒂(Carlo Horatii,1673—1759)就已反对天主教传教士独自翻译圣经,而坚持认为汉译圣经应在欧洲传教士的辅助下,主要由中国同工承担,以使翻译做到“信实、优雅和庄严”。 Bernward Willeke, ‘Das Werden der chinesischen katholischen Bibel’,Neue Zeitschrift für Missionswissenschaft XIV (1960), p. 285。Willeke是在麦传世(Francesco Jovino,1677—1737)于1726年2月13日写给霍雷蒂的信中发现霍雷蒂这一立场的。。除了语言的润饰,中国顾问也常参与术语的讨论,有传教士提倡:
在这一以及其他许多方面我们都应当乐于学习和接受这些中国学者的观点。我们可以就这些词汇与之商榷,如天使、使徒、洗礼、教会、良心、皈依、约、罪、神圣、拣选、传道人、上帝、地狱、圣洁、心、怜悯、使者、弥赛亚、理智、神秘、献祭、祷告、祭司、先知、讲道、悔改、安息日、牺牲、圣徒、灵魂,等等*佚名:‘Chinese Version of the Holy Scriptures: Need Revision; List of Words Claiming Particular Attention; Proposed Meetings of Delegates’,Chinese Repository, Vol. 15, No. 2 (February 1846), p. 109.
而中国顾问在考虑选择某个词的翻译时,依据的是《佩文韵府》一类的权威*佚名:‘Revision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Bible; Remarks on the Words for God, Father, Son, Spirit, Soul, Prophet, Baptism and Sabbath’,Chinese Repository, Vol. 15, No. 4 (April 1846), p. 163.。让我们通过读马礼逊自己的汇报来了解这一合作过程:
接着,我与不谙英文的中国助手把它重新看一遍。他针对语言提出必要的意见。译文据此修改并整理出清稿……然后,我独自读它……先在稿纸上标记每一处改动,以及每一处与原文看上去不一致的地方,然后同时咨询拉沙尔先生和中国助手,与他们一同讨论直至消除每一个疑点并调整每一处脱节。此后,整理出另一份清稿。读过之后,我交由犬子约翰检查,因为他对汉语惯用法的掌握比我好。他认可后,整理出一式两份清稿,一份给我的中国助手,一份给拉沙尔先生,以便指出他们认为不妥的地方……接着,我在另一份清稿上,让我的中国助手根据他所理解的意思添加标点;我予以检查,若他的标点与我的理解相符,就将稿子交给出版方。排版后的清样先送交中国助手,看是否有误,然后交给拉沙尔先生,再由我自己读过之后,最后令其出版……前前后后的改校离不开四个人:拉沙尔先生、中国助手、我们父子;每人独自鉴定,不受另外三人的干扰。*佚名:‘Chinese Version of the Bible: the Manuscript in the British Museum; One Version Undertaken in Bengel, and Another in China; with Brief Notices of the Means and Measures Employed to Publish the Scriptures in Chinese Previous to A.D. 1830’, Chinese Repository, Vol. 4, No. 6 (October 1835), p. 254.
咨询中国顾问的传教士不仅有圣经译者,还有相关评论人。英国慕雅德(Arthur E. Moule, 1836—1918)主教声明,在他评议施约瑟译本的语言风格时曾咨询中国学者的感受*Bishop Moule, ‘On Cert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ree Versions of Holy Scripture Published by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CR, Vol.14 (September-October 1883), p. 412.。而《约伯释义》的书评赞扬该书的语言风格在顺应中国读者的思维方式的同时,还能采用他们的语言表达方式,效仿汉语典籍,以传输神对人的启示*佚名:‘Our Book Table-Book of Job’, CR, Vol.25 (March 1894), pp.92-93.。
众多中文圣经译本无一为真正的直译,而均有不同程度的转换。从上述史料可以看出,将圣经译成中文和中国同工的参与颇具意义。首先,对圣经的理解和诠释是由传教士和中国同工共同完成的。其次,翻译的过程充分说明在理解和诠释当中顾及语境的必要性。诚如费正清所言:“中国人的参与是新教中国化的第一步,而中文词汇的恰当使用是第二步。”*Fairbank, Introduction: The Place, p.9.再次,提高了圣经汉译的可读性,使之更易于接近中国读者,继而使他们展开讨论,推广汉语圣经诠释活动。汉译旧约的接受和应用的一个主要前提就是可读性*可读性不仅指语言明晰,让读者懂得经文所表达的意思,还指能引起读者反应,特别是独立的创造性的文字活动。参Irene Eber, Introduction,Bible in Modern China, pp. 13-26。,其效果已为19至20世纪的中国读者日益广泛和深入诠释、利用圣经的事实所见证。这也说明,汉语圣经的译介成为汉语圣经诠释活动的开展和传统的形成的良好开端与榜样。
结 语
旧约进入中国文化环境,首先表现在它的引介和翻译。这些诠释活动显示,不同文化传统的兼容性为跨文化交流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因为处境化过程中的选择、接纳和整合要求是多元化的,且跨文化思维意味着挣脱各种一元解释的桎梏。然而,在意义架构中,中国思想传统和基督新教的神学传统既推动又在不同程度上限定了汉语旧约诠释者对希伯来圣经经文、古代以色列历史和民族的理解。虽然援引中国传统词语系统,西方传教士只是为了在保持传统基督教神学和圣经诠释的前提下提高中文旧约的可读性,赢得中国读者对基督宗教及圣经的尊重。
这样,诠释者的意识形态、立场和方法也就不容忽视。将旧约的汉语诠释文本放回其原初的历史和语境中,对它们作出与其本来语境最切合的理解和解释,是必不可少的。这正是本文的任务,即从诠释性文本的起源和它被接受(认知)的情况两个层面探寻文本的意义。可以说,传教士的圣经诠释性文本,以古代以色列历史和人物为例,不论是介绍还是翻译,实际上都是严格按照基督教史观,并参考儒家史观而设计、书写的准历史著作。这样构建出的古代以色列历史叙事和创造出的古代以色列历史传统,对希伯来圣经的原始面貌充满了想象和误解,却被当成了历史真实,并在时局的激荡之下直接促成了19至20世纪中国读者心中犹太这一典型性“他者”的生成。
【责任编辑:李青果;责任校对:李青果,张慕华】
2016—06—15
曹 坚,中山大学哲学系(广州 510275)。
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