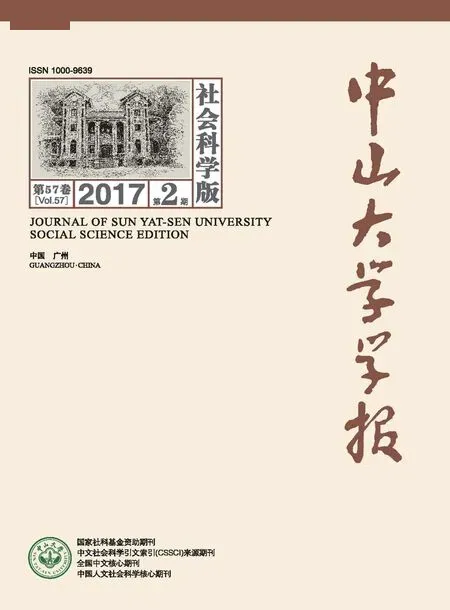摩尼教符咒从波斯到阿拉伯和中国福建的流传*
尤 小 羽
摩尼教符咒从波斯到阿拉伯和中国福建的流传*
尤 小 羽
作为一种高度复杂、包罗丰富的宗教思想体系,摩尼教在数术方面以往不甚突出,但根据历史记载和出土发现,摩尼教在大体系之外的确有小传统,巫术、咒语便是其中的一类。国际学者对中古伊朗语和阿拉伯符咒的研究,为进一步梳理语义解释和转译过程提供了基础。近年新发现的汉传明教系统的闽东霞浦文书中,有专门的祷雨仪式书,印证了唐代史籍中摩尼师参与地方祈雨的事实。霞浦文书中屡见的中古伊朗语源的汉字音写咒语,使我们看到甚至在近古时代的中国东南沿海含有语言上和形态上的古摩尼教因素的符咒仍为人传用的事实,特别是使用它们的当地语境,揭示了数术在摩尼教的传承、嬗变过程中所显示出适应新的文化生态的能力。另外,晋江苏内村五都水尾宫的祭祀法物也为认识摩尼教与数术活动的关系提供了鲜活的材料。
摩尼教; 数术; 吐鲁番文献; 霞浦文书; 霞浦《祷雨疏奏申牒状式》; 明流; 五都水尾宫(福建晋江苏内村)
一、摩尼教与数术
摩尼教有“道德宗教”的美名*陈垣:《摩尼教入中国考》,《陈垣学术论文集》第1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70页。,并不以数术(占卜、巫术)著称,摩尼本人也并不提倡巫术,但在摩尼教的创世说中,却不乏神异之事。公元719年,一位慕阇——摩尼教最高教阶神职人员——随吐火罗国使团到达长安之时,就被看成是一个“解天文人”:
开元七年六月大食国吐火罗国康国南天竺国遣使朝贡,其吐火罗国支汗那王帝賒上表献解天文人大慕阇。其人智慧幽深,问无不知。伏乞天恩,唤取慕阇,亲问臣等事意及诸教法,知其人有如此之艺能,望请令其供奉并置一法堂,依本教供养。*《宋本册府元龟》(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卷971外臣部朝贡四,第3848页;卷997外臣部技术,第 4025页。
“天文”在中古相当于广义的astronomy,沙畹、伯希和译注这段摩尼教史料时便是如此处理的*É. Chavannes-P. Pelliot, ‘Un traité manichan retrouvé en Chine’, JA 1913, p. 177;[法]沙畹、伯希和著,冯承钧译:《摩尼教流行中国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7页。。他们的做法固然不错,但具体到摩尼教教义,慕阇掌握之中的“天文”应该指的是该教二宗三际论的核心部分——创世说(cosmogony)*有关学说,详见Werner Sundermann, ‘Cosmogony and cosmology in Manicheism’, Encyclopdia Iranica, Vol. VI, pp. 310-315.。据6世纪拜占庭宫廷文官普罗考皮厄斯(Procopius)记载,聂斯托利教长老Barsymes不仅“对巫师和恶神大感兴味”,甚至还“深深地沉迷于摩尼教”*Jes P. Asmussen, Manichaean literature, representative texts chiefly from Middle Persian and Parthian writings, Delmar (New York): Scholars’ Facsimiles & Reprints, 1975, pp. 44, 147 n. 38.。同样也是在宫廷,唐室因为天下大旱,曾求助于摩尼师的法术,上演了皇上希望外来的和尚能呼风唤雨以解旱灾的一幕:“贞元十五年(799)四月,以久旱,令摩尼师祈雨。”*《唐会要》卷49“摩尼寺”条,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864页。
这一件事,历史记载有歧互不同之处。据《旧唐书》记载:“贞元十五年四月丁丑,以久旱令阴阳人法术祈雨。”*《旧唐书》卷13,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90页。这里没有提及摩尼师。沙畹、伯希和曾表示疑惑,认为对同一事件的不一致记载,有可能暗示时人将摩尼师看作阴阳术士。但是,对此事也有同时提及阴阳人、摩尼师的记录。据《册府元龟》记载:“贞元十五年四月,以久旱令阴阳术士陈混常、吕广顺及摩尼师祈雨。”*《宋本册府元龟》卷144帝王部弭灾二,第 227页。
岑仲勉先生就此作《摩尼师与阴阳人》予以考辩,认为收入《册府元龟》的记录是完整的因而也是可信的:“阴阳人与摩尼师显分两途,《旧书》、《会要》各取其一节耳。”*岑仲勉:《唐史余渖》,上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0年,第130—131页。阴阳术士两人留下了名字,未提名的摩尼师或许是入唐西域人。祈雨法术为回鹘人所习知善能,吐鲁番出土文献中多有涉及*Peter Zieme, ‘Alttürkische Fragmente über den Regenstein’, Appendix to: dám Molnár, Weather-magic in Inner Asia.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Research Institute for Inner Asian Studies, 1994, pp. 147-151.伯希和获敦煌粟特语写本P3,是一部中亚当地制作的祈雨书。参E. Benveniste, Mission Pelliot en Asie Centrale, vol. iii, Textes Sogdiens, edites, traduits et commentes. Paris: P. Geuthner, 1940; W. B. Henning, ‘The Sogdian Texts of Pari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1/4 (1946), pp. 713-740.。回鹘人对摩尼教在唐境中的传播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与唐代官方关系密切,其间曾以一技之长受邀参与祈雨仪式也属可能。
摩尼教(明教)与数术曾有关涉的史实,还有一条时代较晚的材料证明:“会昌中汰僧,明教在汰中。有呼禄法师者来入福唐,授侣三山,游方泉郡,卒葬郡北山下。至道中,怀安士人李廷裕得佛像于京城卜肆,鬻以五十千钱,而瑞相遂传闽中。”*何乔远编撰:《闽书》卷7《方域志》“华表山”条,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72页。摩尼光佛的画像得之于北宋太宗至道年间(995—997)开封的算卦店铺,可见当时民间对这一外来宗教画像的法力有特别的信仰。
事实上,摩尼教的占卜、巫术材料确有遗存:吐鲁番出土摩尼教文书中有两件中古伊朗语的解除术法符咒(德藏摩尼教写本文献M 781和M 1202)、一件征兆占文本(M 556),还有阿拉伯语一件巫方,出自大约16世纪成书的一部伊斯兰医书。汉文材料方面现有近年发现的霞浦文书《祷雨疏》。M 781和M 1202是由恒宁于1947年首次刊布的*W. B. Henning, ‘Two Manichan magical texts with an excursus on the Parthian ending -ēndēh’,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Vol.12/1, 1947, pp. 39-66.。 M 781是一件中古波斯语咒书残篇,包括了相对独立的两个文本:其一M 781i是调伏热病的咒语,针对的神怪名为Pašku;其二M 781ii是针对家中恶灵的护身咒,着重于对保护神的描述。M 1202为一件帕提亚语避邪护身符咒,针对的是家中恶灵,其背面主体内容为摩尼教夜叉名录。书页的上半部分保存不佳,墨色较淡,多处难以辨认。恒宁推断残片或写于6世纪。M 556征兆占文本是一块较小的残片,由芮柯和宗德曼两位学者在1997年合作研究、刊布*Chr. Reck & W. Sundermann, ‘Ein illustrierter mittelpersischer manichäischer Omen-Text aus Turfan [M 556]’, Zentralasiatische Studien, Band 27, 1997, pp. 7-23.。其写本格式特别,以朱砂色栏线绘制成格,文字工整地填写在栏格内,文本配有非常精美的彩绘插图,既具有摩尼教工笔画(miniature,又译为“细密画”)的特点,人物表现上也显示出相当明显的汉风绘画造型的特征。阿拉伯语的巫方出自Jalāl al-Dīn ‘Abdmān(1445—1505)所纂医书汇编Kitābmafīibbikma,其中有三个章节含有对治恶灵的咒方。施瓦茨在2002年发表的文章中指出,这些恶灵的名字终溯源到古犹太语中的坠落天使(看守者)和毁灭妇女的巨人,集中体现在医书中“对治Tabi’a(Fī-‘ilāj-al-tābi-‘a)”一章中的一段辅助咒语*Martin Schwartz,‘Qumran, Turfan, Arabic magic, and Noah’s name’, Res Orientales 14 (Charmes et sortilèges) 2002, pp. 231-238.。医书取材自伊斯兰阿拉伯语中的原始巫方资料,极有可能是经摩尼教阿拉伯语巫方文献中的医方辗转而来,该阿拉伯语版本译自摩尼撰写的叙利亚语《巨人书》的中古波斯语本,摩尼本重塑了亚兰文中看守者和巨人的传说。霞浦文书《祷雨疏》,原题“祷雨疏 奏申牒状式 后学陈宝华存修”,传出自福建宁德市霞浦县,目前存于私人之手。
二、热病咒与护身咒(M 781 i-ii)
中古波斯语M781目前只有恒宁一家的释读,阿斯姆森1975年的《摩尼教文献》一书全文照引,本文也据恒宁译文转译为汉文*参见马小鹤:《摩尼教四天王考——福建霞浦文书研究》,《霞浦文书研究》,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15—116页;马小鹤:《摩尼教中的夷数(耶稣)》,《霞浦文书研究》,第296页。:
(i正面)因子……光明者(复数)。愿他永生。(上文结束)抵御热病和[热病?]之灵的咒语:它的名字是以德拉(Idrā)。它有三种相和格里芬神怪一样的翅。它居住在……里和人的脑子(?)里。(如此)就有了热病的名字。它生于水中……和尘埃里……如此就…… (i背面)[若热病之灵]不[主动]离开,那么它将从某甲之子某乙的[身体]出来,远遁消失,以友人耶稣之名义、以其最高的圣父之名义、以圣灵之名义、初人(First Reflexion,先意)之名义、以圣神颉利(ēl)之名义、以报伯(Baubō)之名义、以诶里支()的儿子摩冺(Mūmīn)*霞浦文书有一种未定名的“无名科册”(共156页),其上册第14页出现“缚逸天王末斯信法王摩冺明使”,摩冺正是M781中的Mūmīn。之名义、以弥诃逸(Michael)、卢缚逸(Raphael)和迦缚啰逸(Gabriel)之名义、以饕餮之名义、以万军之主(Sabaoth)和……[之名义]……(ii正面)富列董(Frēdōn)将摧灭……一切。我有三相,还有火的腹(?)。我手握锋利灵活的斧头,身佩锐剑利刃。我有急速的话语和天使的耳力……那钢铁锻就的七把匕首我紧攥在手……强大……坚硬的那些…… (ii背面)……家中的一切……家中的一切神冥,家中的一切恶灵,家中的一切怒贼:我将重击他们和他们的已然匍匐脚下的奴仆,他们无法举起手臂来抵抗我。我将吸走他们的光亮到我的光明里,我将取走他们的力量加添到我身中。攻击……的死亡……正谛视着他们……

M 781 ii是一段摧伏家中恶灵的护身咒,以描述保护神的形象和力量为主要内容。保护神名为富列董,如恒宁在文中引言部分所述:“因为翻译者轻率地使用了一些名称,将与当地信仰相联的神祗随之引入,善知识与神侍者也一并带入。属于这类附加成分的有伊朗的大医圣富列董(Frēdōn,阿维斯陀经中称Oraētaona),他在摩尼教祈祷辞中与琐罗亚斯德教符咒中同样普遍。”*Henning, ‘Two Manichan magical texts’, p. 39; 参见马小鹤:《摩尼教、基督教、佛教中的“大医王”研究》,《欧亚学刊》第1辑,第243—258页。咒语使用的语汇多数可在其他语言的摩尼教文献中找到对应形式,如其中的三变身与七把匕首。末尾处的吸走光亮云云,都是摩尼教经典习见的采集光明因子这一母题的变化形式。
三、大力咒与摩尼教的夜叉名录(M 1202)
M 1202与M 781性质一样,旨在驱魔辟邪,但M 781着重保护神的描述,M 1202则是提供了一份摩尼教的夜叉名录。正面内容为符咒内容,背面为夜叉名单*译释参见徐文堪、马小鹤:《摩尼教“大神咒”研究——帕提亚文文书M1202再考释》,《史林》2004年第6期, 第101—102页。:
(正面)以你的名义,按你的旨意,遵从你的号令,凭借你的神力,主夷数基督。以救世主众神的使者末摩尼之名,以你的圣主之名,被赞颂被祝福的圣灵,他摧灭魔鬼和黑暗力量。以弥诃逸、瑟罗逸(Sera’el)、卢缚逸和迦缚啰逸之名……伽富提努斯(Qaftinus)、天使巴西穆斯(Bar-Simus)……以唵逸(An-el)、达逸(Dad-el)、阿拔逸(Abar-el)、尼萨逸(Nisad-el)和罗福逸(Raf-el)之名义,[他们将毁灭]你们这些魔鬼、夜叉、裴黎(peris)、恶鬼(drujs)、罗刹、黑暗之相和恶灵。暗夜之子、恐与怖之子、痛与病之子、……和年长的,从大力和话语前……远离佩戴着辟邪符的这个人,逃吧,……,消失吧,畏惧吧,走的远远的……

文本里明确直呼“末摩尼”,将这篇咒语的摩尼教关联揭示无遗。文中还有几处术语的使用体现了明显的摩尼教特征。z’wr(zāwar)一词,恒宁认为是全文的关键字眼,咒语所针对的邪恶对象都将在zāwar面前逃离,在佩戴本符咒的人面前逃离,因此zāwar既是咒语所述的“坚固力”(firm power),又是符咒本身*Henning, ‘Two Manichan magical texts’,p. 52.。在汉文摩尼教文献《下部赞》中有一段音译文字,其中有一句“夷萨乌卢诜,祚路欝于呬”,吉田丰揭明“祚路”对应的原文:zwr,词义power(力)。该句中的其他音译词也分别由不同学者读出,“夷萨”为yzd,义god、divinity(神、清净)*Y. Yoshida, ‘Manichaean Aramaic in the Chinese hymnscroll’,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46, 1983, pp. 326-331.;“乌卢诜”为rwšn,义light(光)*[日]石田幹之助:《敦煌发现〈摩尼光佛教法仪略〉に见ぇたる二三の言语に就ぃこ》,《白鸟博士还历记念东洋史论丛》,1924,pp. 157-172;此据氏著《东亚文化史丛考》,东京:东洋文库,1973年,第287—289页.;“于呬”为whyh*E. Waldschmidt & W. Lentz, Die Stellung Jesu im Manichäismus, Abhandlungen der Preuβ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26, Nr. 4, S. 85.,义wisdom(智慧)。合并观之,这句音译文与汉文摩尼教文献中的“清净光明,大力智慧”八字偈语(七字韵语的下部赞作“清净光明大力惠”)完全符合。恒宁将这件辟邪符咒迳称为zāwar,我们姑且可译为“大力咒”。另一个恶鬼所要避走远遁的是sxwn,恒宁译作word(话语)。“话语”(sxwn)一词在摩尼教经典中有其特殊的用义与内涵,其在汉文摩尼教文献中的译名据考证为“语藏”,见于敦煌写本《摩尼教残经》,原句为“于语藏中加被智惠”,其语源由宗德曼揭明为帕提亚语saxwantanbr,可能译自古叙利亚语gwšm’,义近于拉丁文的corpus。因此“语藏”在《惠明经》中“指代的是整个摩尼教教义文献”*王丁:《陈寅恪的“语藏”——跋〈陈寅恪致傅斯年论国文试题书〉》,《科学文化评论》第2卷,2005年第1期,第69—70页。。《下部赞》中有一偈颂《初声赞文》,头两句为:于喝思,苏昏喝思。其中于为wcn,义为声;喝思为hsyng,义为初(primeval);苏昏即为sxwn,义为语词(word)。因此在这件符咒中,sxwn一词指的是符咒内容。回到这件辟邪符本身,先称颂夷数(耶稣)后称颂末摩尼,这样的先后顺序提示了夷数与符咒的关系更为紧密直接,宗德曼曾指出此处呼告的主夷数基督属于耶稣的第四种身份:末世耶稣(the eschatological Jesus)。据吐鲁番文书M 35,他将作为救世主统治人类120年*Werner Sundermann, ‘Christ in Manichaeism’,Encyclopdia Iranica, Vol. V, 1991, p. 537b.。
M 1202的背面文本主体为夜叉名录,恒宁参引烈维的研究对其结构作了详细的解释:名录中每一个小时都由一位占据某个国家的夜叉掌管,他拥有成千后代,以某种食物为食。这件原本应由24节构成的名录仅存5节,其残片与《月藏经》紧密相联。但目前看来,没有一部佛教文献如这件摩尼教残片一样,可以从中看到包含五种因素的名录:时刻、夜叉、国家、数目和食物*Henning, ‘Two Manichan magical texts’,p. 48.。名录中的夜叉名及国家名都可在《月藏经》及《孔雀王咒经》中找到出处。徐文堪、马小鹤在恒宁释读的基础上,据《孔雀王咒经》将其中的Puškavur译作富楼沙富罗国(Purusapura),将Džartabuhr译作羯咤(Jatāpura),Kucātr因无典籍着落,二位学者拟译成库查特拉。此外,他们还详析了第七、八时中的“食花”、“食果”,分别引梵文、汉文、回鹘文、藏文及西夏文中佛经中的饿鬼名单中的“食华鬼”和“食果鬼”为例,进一步强调这份夜叉名录与佛教的联系*徐文堪、马小鹤:《摩尼教“大神咒”研究——帕提亚文文书M1202再考释》,《史林》2004年第6期, 第101—102页。。可以说,这份名录从结构到内容都是摩尼教借用佛教因素的表现,但其中颇可注意的是第七时掌管脂那的夜叉。
四、阿拉伯语咒语文献中的摩尼教内容
M 781和M 1202中都出现了以 -el为词尾的天使名,出自犹太传统。伊斯兰阿拉伯医书中的巫方则表明了古希伯来的恶天使和巨人的名字,通过摩尼教的中古波斯语传承中介,逐渐变成《巨人书》里的摩尼教阿拉伯语译本,它们曾用于法术,终变成伊斯兰阿拉伯巫方医书源流的一部分。施瓦茨认为“对治Tabi’a(Fī-‘ilāj-al-tābi-‘a)”一章中的辅助咒语以伊斯兰教义为框架,咒语描述的是邪恶的天上窃听者。他逐字对译这篇咒语,同时尽力重现咒语中的原有音韵特点,如韵尾、头韵和谐音(rhyme, alliteration and assonance)的表现。对于咒语中出现的七个神祇名,他从年份较早的刊行本中的拼写着手,比较摩尼教中古波斯语版本或亚兰语构词形式重构潜在的阿拉伯语拼写。以下依据英译文迻译:
这是大卫之子所罗门之令:二者和平!以真主的名义,凭藉安拉,来自安拉,归于安拉,认主独一,清真无二,没有胜利者惟有安拉,万物非主,惟有真主,更无他神。我命尔等,你们这些众所周知的灵怪,你们有武器和磨利的长矛,蹿到风中从天上窃听地上,你们这些带着闪电和旌旗的,我用威名真言命令你们,那些名字缠着你们的脖子,你们只能遵令1. 玛忒辣逸(*mtry’yl),2. 古拔逸(*kwkb’yl),3. 斋珂逸(*zyqyl),4. 护拔阿毗施(hwb’byš),5. 以勒以弥施(jljmyš),6. 滥(r’hm),7. 噶德来逸(*jdry’yl)*以上七个阿拉伯语名字的转写只是表示其大略音值。。你们这些住在北方和湿热南方的鬼精灵怪,不论大小长幼统统下来,下到地面,愿大地不支持你们,苍穹也不护佑你们。
施瓦茨对咒语所列的七个名字进行了词形重构及语义解释。第1、2、3的名字中的 -yl,均屡见于亚兰文《巨人书》,为阿拉伯语、摩尼教中古波斯语继承,也是这两种语言天使名的常见词尾。1和3属于堕落天使,它们教导人类;2和3是邪恶艺术之师天使。这三个天使名还体现了其潜在的气象特质,这与咒语中对“乘风者”的描述相合,也与摩尼教对巨人后代的描述一致。1中的 *mtr在亚兰语和叙利亚语中义为雨;2中的kwkb-为叙利亚语的星;3中的*zyq-是叙利亚语的闪电。4是一个错讹形式,可构拟为亚兰语的hwbbš,是吉尔伽美什的恶魔对头胡姆巴巴(Humbaba)。5、6、7是巨人名字,6据其可能的阿拉伯语形式或义为连绵细雨,7可还原成gdry’l,即《以诺书》(Enoch)中的Gādre’el(噶德赖逸)*Schwartz, ‘Qumran, Turfan, Arabic magic, and Noah’s name’, pp. 233-234.。第4和第6个名字的阿拉伯语拼写是建立在摩尼教中古波斯语的基础上的,阿拉伯语名单表明了摩尼教包括《巨人书》在内所引用的原始素材都源于亚兰文的一系列文本。同时,该章还出现了将咒语所针对的“热病”按某个时间单位及气象状态区分的情况,如对治上午中段时间的热病“灰尘”,对治中午的热病“阴云”,对治下午的热病(未提特征),其咒语和结尾词各不相同。
五、闽地摩尼教中的数术
东南沿海地区的摩尼教流传至明代时,闽地“民间习其术者,行符咒,名师氏法,不甚显云”*何乔远:《闽书》卷7《方域志》“华表山”条,第172页。。可以印证这一记载真实性的是福建霞浦文书,其中有摩尼教数术活动的发现,既有咒语,也包括一件明确含有摩尼教内容的祈雨文检。
霞浦文书《祷雨疏奏申牒状式》(以下简称《祷雨疏》),全册71页,行文遵循道教表文格式,使用敬空平阙书式,内容包括祈雨疏文的用语、所请神明称谓及表奏事项,附以夹行小字注明书写体式,前60余页书法谨严,此后似掺有其他书手字迹,略显潦草。首页破损,第2页标题“牒皮圣眼”,为文检中关牒所呈请的神司目录(“眼”、“目”同义),如福宁州及福安县城隍大王、雷公电母等与祈雨保苗直接相关的诸职能神。学者据福宁州、福安县这两个地名的线索对抄本的成书年代进行了推测*林悟殊:《霞浦科仪本〈奏教主〉形成年代考》,《九州学林》第3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05页;杨富学:《林瞪及其在中国摩尼教史上的地位》,《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1期,第115页。。第2页还写明“祈雨司额”作“大云祈雨坛”,谢恩时写“电光植福坛”。全册按神祇地位分成奏、申、牒、状四类疏文,第3至第7页是这四类疏文的封皮式样,第8页至第71页为各类疏文的具体样本,详列斋醮祈雨中诸项科仪如迎龙佛、谢雨中筵、谢雨完满等仪式的祝祷词。举行祈雨的地方叫瑞山堂。《祷雨疏》所列章奏为祈雨仪式中给帝尊的文书,文书所奏告的帝尊之一为道教的昊天金阙至尊玉皇大帝,另一奏告对象则为“摩尼正教”。所奏请的神明除道教系统中的众多神祇外,还可见佛教中的独觉佛、观音势至菩萨。尤为引人注意的是在《奏三清》一节中引入摩尼教的“苏醒活命夷数和佛、灵明大天电光王佛、太上真天摩尼光佛”,《申唤应》中列有俱孚大将、嗪皎真人、四梵天王、八部护法,而洞天兴福度师、济南四九真人则指向闽东“明教门”系谱中的宋人林瞪。特别发人兴味的是,《祷雨疏》中多次将主持祈雨的术士称为“明流”,如《请龙佛祈雨谢恩词意式》(第30—31页)“于厶月厶日,命请明流赍持香信,远叩某龙圣井,祷请感应行雨龙王菩萨爰及随龙土地”。明流指闽地“明教门”、“明教会”中人,语言上盖脱胎于“缁流”、“道流”的构词法。他们的职业是“传教”,清初有明流吴法正与其子“传教”吴法广父子(《请龙佛设供词意》),可见明教中人在祈雨斋醮中所起的作用。现将第9—10页“安座请雨疏式”节录如下:

霞浦文书《安座请雨疏式》
安座请雨疏式
右臣厶一介么微,冒干天听谨奏为祈雨事。今据 通乡贯 奉
光明正教下祈雨济禾乞熟会首某众等竭衷拜恳,俯历丹忱,冒干洪造,所称意者,言念生逢圣世,忝处人伦,蒙天地盖载深恩,感神明维持厚德,茲居霄壤,专务田园……
疏文首句标明“摩尼正教”,则摩尼教介入祈雨活动无疑。“正明内院”未见于现存汉文摩尼教史料及敦煌摩尼教经典,但在载有林瞪入“明教门”一事的《济南堂上万林氏宗谱》中记林瞪加封为“贞明内院立正真君”*参见陈进国、林鋆:《明教的新发现——福建霞浦县摩尼教史迹辨析》,李少文、雷子人主编:《不止于艺——中央美院“艺文课堂”名家讲演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44—345页及图1林氏宗谱局部照片。。贞训正*《故训汇纂》,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第2174页。,“正明”当等同于“贞明”。究其原因,霞浦文书所据底本中该词疑原为“贞明”,因避宋仁宗(名祯)之讳写作“正明”*参陈垣:《史讳举例》,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第154—155页。。成书于仁宗时期的《云笈七签》序中有言:“大中祥符年间,朝廷续降到福建等州道书明使摩尼经等”,后世多以此为据,认为其时摩尼经假托道教名入《道藏》。因此“贞明内院”避帝讳改字极为可能。这种可能性则将此抄本所据底本的年代推定至宋仁宗迤后时期。主持祈雨的两位主事渝沙、睍达,这两个词不是人名,而是摩尼教的僧俗身份称谓。逾沙是你逾沙的省文,你逾沙是帕提亚语ngwš’g的音写*[日]吉田豊:《汉译マニ教文献における汉字音写された中世イラン语について(上)》,《內陆アジア言语の研究》2, 1986年,no. 65,31。,义为“净信听者”,也就是摩尼教的在家信徒,见于《下部赞》第410行“你逾沙忏悔文”、未刊屏南文书“你俞沙(健)”(方册,第7页)*你俞沙健显系耨沙喭(《摩尼光佛教法仪略》“耨沙喭,译云一切浄信听者”)的异译,原形为帕提亚语ngw’g及中古波斯语nywš’g的复数形式ngwš’g’n 暨nywš’g’n。以上渝沙、睍达两词的考证,承王丁老师教示。。睍达,即摩尼教僧侣称谓dynd’r[日]吉田豊:《汉译マニ教文献における汉字音写された中世イラン语について(上)》,《內陆アジア言语の研究》2, 1986年,no. 65,31。(参回鹘语dentar),义为“持教者”,在汉文摩尼教经籍中又音译为“电达”,意译为“师僧”。《安座请雨》中这一僧俗联袂主持祈雨活动的模式,令人想起前述唐代祈雨活动中的阴阳术士和摩尼师。

摩尼教肇始于波斯,其数术文献发现在吐鲁番和阿拉伯地区,而远至中国东南沿海的泉州晋江苏内村*参见王媛媛:《中国东南摩尼教研究评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5年第7期,第11—20页。,亦有摩尼教的咒语流传。晋江文博专家粘良图先生曾在田野调查中做了如下记录:苏内村乩师在家奉祀摩尼光佛雕像。逢有人前来卜日问病时,他扶乩作法,“供给印有摩尼光佛形象、八卦形象的符纸,指定地方张贴或焚烧以镇宅驱邪”。苏内村民把刻于草庵的摩尼教十六字偈称为“摩尼公咒”,相信念此咒语可定心性、祛邪鬼,并附有一套“催咒”手诀*粘良图:《晋江草庵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8页。。霞浦文书中保存的汉字转写“咒语”,事实上很多属于宗教文体中的祈祷文,称之为咒语,并不完全恰当。摩尼教的普通信从者不谙教理教义的究竟,在他们眼中,三际中暗晦化明的“生出”(emanations)注定是多神论的舞台;摩尼教对神名加以“对译”,虽则减低了传教难度,但正是这一方便法门却又带来比附不当、牵强附会的风险*Henning, ‘Two Manichan magical texts’, p. 39.。就像在祷文、符咒中植入外语语词或段落属于宗教生活中的普遍现象*Fritz Graf著,王伟译:《古代世界的巫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44页。一样,不仅术士、法师们借助这个手段可以增强其神学背景的正宗性,信奉者人群也往往在念诵他们不明其义的天语神咒之时,格外信其具有不可思议的神力。神灵魔鬼的名字诘屈聱牙,摩尼教初传中原之时,道明等译者就主张汉译摩尼教的偈、赞之文“义理幽玄,宜从依梵”(《下部赞》,行176)。也就是说,唱祷之际应以摩尼教会官方原语为依归,真正的原因倒不是教理教义“义理幽玄”故不易翻译(深奥的《摩尼教残经》获得成功的意译便是明证),而在于成堆的神祇专名除了音译别无他法。摩尼教如此,佛陀释迦牟尼的宗教也是如此。垂至明清之际的霞浦明教内容抄本尚保存了若干在术语内容乃至音韵上相当古老成分的西亚摩尼教咒文面貌,为这一入华外来宗教能够延续千年的历史真相提供了新的例证*为了解福建民间摩尼教数术活动和其他信仰方式的遗存,笔者于2016年2月探访了粘良图先生首先发现的泉州晋江苏内村境主宫。经向村人了解,所谓境主宫,当地人称为“水尾宫”(笔者见到宫中悬挂有“五都水尾宫”锦缎横幅),为崇拜祭祀摩尼光佛、都天灵相、秦皎明使、境主公、十八真人之场所。每逢农历(当地称为“古历”)三月二十三日举行秦皎明使生日纪念法会,其时尚有近三个月的时间,但村民已经开始为此募集功德金,张榜公布,标题为“秦皎明使圣诞捐资芳名”,参与人数约有百人之众。水尾宫有红纸手书的联语:“秦明共戴尧天舜日,皎使咸霑慧露慈风”,句首用拆分重组的方式嵌藏“秦皎明使”这个名字。水尾宫神龛中的墨色手绘摩尼光佛像,造型完全因袭草庵的摩尼光佛形象。供桌上有一对筊杯,用于供前来祭拜的人投掷于地,以杯的正背面组合判断问卜成事的吉凶(参《晋江草庵研究》第93页),上有契刻文字:“草奄2003年”,大约是表明该筊杯从一公里外的草庵请来的,这也表明五都水尾宫与明教胜地草庵之间的从属关系。。
【责任编辑:李青果;责任校对:李青果,张慕华】
2016—11—01
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古代数术的论证模式”(14JJD720011) 作者简介:尤小羽,中山大学哲学系(广州 510275)。
10.13471/j.cnki.jsysusse.2017.02.010
本文作者曾得到廉亚明(Ralph Kauz)教授的支持,获得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DAAD)奖学金,到波恩大学访学,得以顺利完成前期工作。2016年3月有幸得到林鋆先生的邀请,前往霞浦参观明教遗址与文物。本文使用的霞浦未刊资料也经林鋆先生授权发表于此。统此申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