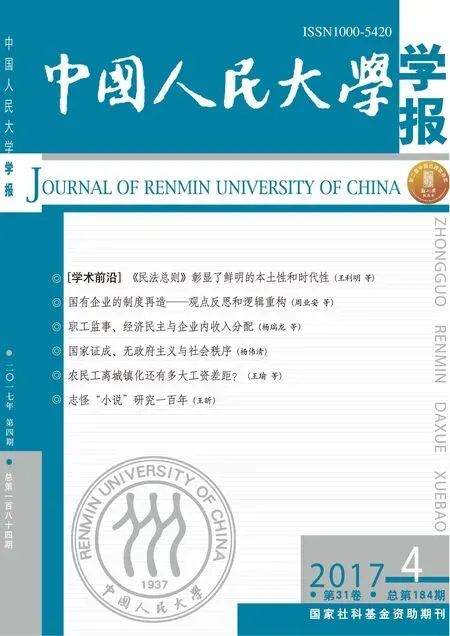国有企业的制度再造
——观点反思和逻辑重构
周业安 高 岭
国有企业的制度再造
——观点反思和逻辑重构
周业安 高 岭
国有企业的改革史同时也是一部争论史,这些争论集中于国有企业的性质、效率、改革路径和治理结构四个方面。为阐明国有企业制度再造的方向,需要对相关研究进行回顾和探讨。首先,国有企业是一种社会化程度最高的企业组织形式,国有企业与利益相关者论视角下的公司治理结构相适应。其次,围绕国有企业效率的相关研究忽视了国有企业的路径依赖问题,也没有分离出规模、垄断、政治关联等因素的影响,因而断言国有企业的效率高低需要谨慎。再次,国有企业改革路径的主导倾向是渐进式改革模式,但迄今还缺乏一个有说服力的理论框架来有效解释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共存共进的特征事实。因此,未来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研究任重道远。
国有企业;社会化;利益相关者;路径依赖
一、引言
国有企业从最开始以承包制为核心的局部改革到以股份制公司制为核心的制度重构,经历了三十余年的风风雨雨。改革让国有企业焕发新生,虽然众多低效率的国有企业被淘汰,但在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的国有企业不仅大大提高了自身的竞争力,而且还持续快速地发展壮大,成长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型企业。三十余年的改革开放实践表明,只有坚持市场化导向的改革才能做大做强国有企业,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综观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历程,所取得的成绩令人瞩目。但是,国有企业仍存在一些老问题,比如“预算软约束”[1]。老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新的问题已经涌现。如何在新的国际竞争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中保持充足的竞争力,是未来国有企业改革必须解决的问题。
回顾国有企业三十余年的改革历程,承包制只能称得上治标,谈不上治本。治本是从股份制公司制改革开始的。[2]自此之后,国有企业开始按照市场化导向原则进行现代企业制度的重构。这个制度重构过程迄今仍在持续,整个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初步的股份制改造和公司化阶段(1992—1997),以试点和推广为特征;第二阶段是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把大型国有企业作为改革的重点对象,核心是引入国有控股公司模式实现大型国有企业的集团化(1998—2001);第三个阶段是把国有资产经营管理体制的重构作为核心内容,建立国有资产“出资人”制度(2002—2012);第四个阶段可称之为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阶段(2013年至今),这个阶段仍在进行当中,归纳起来有四个方面的主要内容:一是突出做大做强战略;二是把混合所有制改革设定为主线;三是贯彻顶层设计思想,推行分类改革;四是强化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作用,并作为国企改革的基本原则。
四个阶段的改革体现了国有企业渐进式的制度重构路径,这条改革路径从最开始股份制、公司制的基本制度雏形的构建,到后来针对国有企业自身的性质和特征逐步给予明确诠释,国有企业改革路径逐步走向成熟。这些改革始终围绕一个核心思想展开,那就是国有企业的制度重构本质上是市场化导向的制度设计。这体现在最开始的股份制、公司制的试行到后来的混合所有制和控股公司模式的推广,这些制度设计都是基于市场经济原则展开的,但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并不等于说放弃国有企业的性质。分类改革和党的领导作为重大政治原则的顶层设计思路表明,国有企业的改革必须基于国有企业的性质展开,不能把国有企业等价为普通的市场经济组织。国有企业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微观经济领域的具体化,其功能不仅在于提供公共物品和外部性产品和服务,更重要的是,国有企业是治理社会经济的重要载体,是社会经济政策在微观领域的延伸,这种角色定位决定了国有企业的制度重构必须有别于普通的市场经济组织。因此,在讨论国有企业的制度创新时,必须以国有企业性质为基础,以市场化导向为目标,兼顾效率和公平。
不过,尽管国有企业改革经历了三十余年风风雨雨,改革的思路日益明确,改革的经验教训也异常丰富,但围绕国有企业的一些基本问题的讨论依然存在很多争议。这些争论可以归结为四个方面:国有企业的性质、国有企业的效率、国有企业的改革路径以及国有企业的治理模式。只有在这四个方面达成共识,国有企业改革才有可能真正走向成熟。本文的目的就是要对当前国企改革存在的这些争论进行总结和评析,以期深化对新时期国企的制度再造问题的认识。
二、国有企业的性质:企业利润最大化还是社会利益最大化?
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的争论首先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国有企业的性质界定。实际上,单从法律意义上说,国有企业的性质无须讨论,但由于这个问题涉及国企改革的目标问题,而后者决定了改革的方向和路径,所以国有企业的性质又显得复杂了。从企业理论的发展史看,围绕企业目标的争论也一直存在。新古典经济学坚持企业必须追求利润最大化(准确地说是股东利益最大化),而反新古典范式的学者则认为利润最大化并非企业的唯一目标,企业还需要承担社会责任,尤其对公众公司来说更是如此。企业作为一般化的市场经济组织尚且存在性质的困扰,何况国有企业这种特殊的经济组织?
国有企业改革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对国有企业性质和国企改革目标的争论。迄今为止,关于国有企业性质的讨论存在三种代表性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过去国有企业兼有生产、社会保障、社会福利和社会管理多种职能,本质上是“社区单位”,这一特征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起步和深化,国有企业的这些社会职能逐步分离出来,由政府办社会,而国有企业回归到企业本身。[3]第二种观点认为,国有企业的本质特征就在于除了经济目标之外还有社会目标,以体现国家意志和人民整体利益的要求。这就要求国有企业除了自身的营利目标,还要服务于国家的宏观调控、产业政策,体现公有制经济的决定性力量,成为社会的“公平标杆”(除收入分配之外还涉及员工就业的稳定性、劳保福利、社会保障等方面)[4],以及克服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并且国有企业的双重目标并不冲突,国有企业按照利润最大化的目标经营,国有资产才能保值增值,从而才能在市场竞争中生存和发展,才能有效地完成其承担的社会职能,完成社会目标[5]。第三种观点认为,应分类看待国有企业的性质,这种分类观点承认国有企业具有利润最大化和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双重目标,竞争性国有企业应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主,而非竞争性国有企业则应以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为主。即竞争性行业的国有企业的经济目标优于社会目标(非经济目标),垄断性行业的国有企业的社会目标(非经济目标)优于经济目标。[6]
从现有关于国有企业性质的讨论看,大多数观点承认国有企业存在双重目标,这是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本质区别。这种争论和国外关于企业是否承担社会责任的看法类似。一个经常被忽视的问题是,对新古典范式而言,企业是一个生产函数,即便如此,利润最大化目标也仅仅在充分竞争市场上才得以实现,并且此时利润最大化和社会福利最大化并不冲突。利润最大化和社会责任假说的偏离是由于非竞争因素的出现而引起的,无论是垄断、信息约束还是交易成本等因素,或者外部性和公共品等,都会导致两个目标的冲突。因此,关于企业性质的讨论的核心是我们面对理论上的企业还是现实中的企业?这一点实际上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那里都得到了明确的回答。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说,企业是社会关系的一个单元,并非孤立的单纯的市场经济组织,这种社会性导致了企业不可能仅仅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看,企业是相关参与人的契约的集合,各个契约方共同的利益最大化才是企业所必须面对的。
新古典范式和反新古典范式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企业究竟是一个单纯的生产组织还是一个包含分配功能的经济组织?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来说,企业都包含了一个分配功能,分配功能会反过来作用于生产功能。从这个角度看,反新古典范式的理论有类似之处,不同的地方仅仅在于对制度的理解。从反新古典范式的视角看,新古典范式所强调的企业的生产功能是内生于企业这个经济组织的,生产并非是一个投入转化成产出的纯技术过程,中间还包含了对这个转化过程的激励,而激励来自制度因素,即决定分配过程和分配结果的生产关系或者契约关系。如果注意到分配功能的引入并不是简单地给企业增加一个功能而已,分配功能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关系,具有社会性,就可以发现新古典范式中的企业作为一种生产函数,忽略了社会性,从而陷入利润最大化假说的教条当中。因此,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并非是针对利润最大化假说,而是由现实中的企业所具有的生产和分配的二重性所决定的。
对现实中的企业来说,社会性是一个关键问题。在市场环境中,当一个单人企业逐步扩展成多人企业时,一方面,雇员因为数量的增加而形成群体,从而其社会性在劳动市场上被放大,劳动市场不再是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而是嵌入在一定的社会结构和制度中的市场,雇员自身的人口学特征通过某种社会认同机制和社会经济特征匹配,从而形成一个个群体,也就是社会阶层。单个雇员在企业中的行为会刻上其所在群体的烙印,因而雇员的劳动决策不再是简单地按照新古典的理性经济人的方式展开,而是按照社会人或者行为人的模式展开,前者体现为一种纯社会行为,后者体现为一种有限理性行为,比如社会比较等。另一方面,出资者(雇主)因为数量的增加也形成群体,特别是随着资产证券化的过程以及通过资本市场实现证券的社会化的过程,导致现实的企业逐步进化为“公众公司”,这种类型的公司具有两个基本制度特征:一是股权分散化形成股权的社会化,雇主群体转化为普通家庭作为出资人身份(股东)的群体;二是股权匿名化抹去了雇主的人口学特征,高度简化为单纯的出资人身份,这种出资人的身份和作为雇员的家庭的身份通常是重叠的,因而很难简单地通过劳资关系来甄别两个完全独立的和对立的社会层级。也就是说,雇员和雇主的双重社会化导致了单个人的社会角色的多元化和复杂化,单个人的社会身份相互叠加,同时归属于多个群体。这是劳动市场和资本市场社会化的真正意义。
企业身处社会化的劳动市场和资本市场当中,无法像新古典企业那样成为一个原子化的理性经济人,而是进化为具有一定社会性的行为人,这种行为人的目标不再是单纯的利润最大化,而是同时兼顾各方参与人的权益,这其实就是社会责任的体现。所以,即便是市场中的非国有企业也具有不同程度的社会性,具有相应的社会责任。当这种社会化扩展到一定程度,“社会企业”*按照维基百科的定义,社会企业(The Social Enterprise)是指采用商业化战略来最大限度地改善人类和环境福祉的组织,这可能包括最大限度地提高社会影响,同时为外部股东赚取利润。社会企业可以分为营利性或非营利性两种类型,也可能呈现出多种组织形式,这要取决于所在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比如合作社、互助组织、协会、商业公司、自愿者组织、慈善机构等等。参见https://en.wikipedia.org/wiki/Social_enterprise。就会随之产生,而企业社会化的极致就是国有企业,无论是社会企业还是国有企业,社会责任都会伴随着企业社会化程度的提高而相应提升。因此我们认为,国有企业的性质可以理解为社会化程度最高的企业形式,其目标构成中必须包含社会利益。在现有的理论中,把国有企业等同于社会化不足的企业的思路与新的企业理论相悖;分类看待国有企业的思路同样忽略了社会化这个关键的因素;为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辩护的观点则没有理解国有企业和市场中的“公众公司”之间的共性,过于强调国有企业的特性,反而走向了过度社会化的理论陷阱,也缺乏说服力。对国有企业性质的理解必须能够同时解释市场环境和非市场环境下的企业性质,这就需要同时避开格兰诺维特所讲的低度社会化和过度社会化这两个极端*可参阅:Mark Granovetter.“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85, 91(3):481-510;马克·格兰诺维特:《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8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寻求适度社会化的企业理论解释。
三、国有企业的效率:经济特征决定还是所有制决定?
在国有企业的研究中,效率是另一个核心问题。市场化改革起因于国有企业的普遍低效率,而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非国有企业的兴起及其和国有企业的竞争,再加上国有企业自身的改制转型,导致国企的数量相较于改革之前大幅度下降,从宏观的角度看,企业的所有制结构不再单一化,而是体现为国有、国有控股、国有参股以及非国有四种形式并存,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从企业总量上看,国企占比逐年下降,但从制造业上市公司看,国企占比反而占据多数。国企数量的下降并不能说明国有企业普遍缺乏竞争力,恰恰相反,这说明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国有企业自身经历了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大量的中小型国有企业由于缺乏效率而被淘汰,大量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则因为自身的竞争优势反而生存下来,并得以发展壮大。即便是在市场竞争最为激烈的制造业,国有企业也依然发挥着主体作用,并非不堪一击。
如果从工业企业总数看,国有企业似乎竞争力较弱;如果从制造业上市公司总数看,国有企业似乎至少可以和非国有企业同台竞技,甚至占据一定优势。这种数据上的矛盾引发了研究者的困惑,国有企业究竟是高效率还是低效率?一些研究者已经注意到,尽管市场化改革之前国有企业低效率是一个共识性问题,但经过市场化改革,国有企业的效率已经大大提升,甚至比非国有企业更有效率。[7]另一些研究者则认为,尽管市场化改革之后国有企业的效率有了明显改善,但相比非国有企业仍然要低。[8]两种观点争论的核心在于,假如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存在效率上的差异,那么这种差异究竟是由所有制决定的,还是由企业共有的一些经济因素决定的?
企业效率的所有制决定论最早来自委托代理理论的应用。这种理论认为,国有企业的委托代理结构存在两个致命的缺陷:一是所有者(初始委托人)是模糊的,无法形成有效监督[9];二是层层代理严重放大了代理问题,从而代理成本随之剧增,导致监督无效[10]。研究者通过企业数据对所有制决定论进行了检验,首先,以财务指标(比如总资产收益率、净资产利润率)衡量企业的效率,经验研究结果显示,国有产权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负效应[11],而民营化改革则会显著改进企业效率[12]。其次,如果用技术效率或全要素生产率(TFP)衡量效率,经验研究结果同样显示,国有因素对于企业效率具有显著的负效应。[13]最后,如果以代理成本衡量效率,研究发现在竞争性行业中,国有产权的代理成本最高[14];国有企业的代理成本带来的效率损失达60%~70%[15]。但所有制决定论的经验研究结果并未达成共识。所有制因素带来的企业效率差异可能会因为某些经济因素的变化而发生改变,比如企业效率差异随企业规模的扩大而缩小了[16]。并且一些基于上市公司数据的研究发现,国有股对公司绩效存在积极效应[17],国有股权对公司的绩效具有二重性或呈现U型状态[18],等等。
和所有制决定论不同,另一些研究者认为,企业的经济特征对效率的影响更大,且更为根本。其理由是:第一,国有企业问题不是产权制度带来的,而是因为缺乏一个公平的充分竞争的外部环境。[19]第二,国有企业问题的根源在于从计划经济继承下来的以国家为中介的融资体制,即“国家融资”,这一体制导致了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和政策性负担。[20]第三,国有企业的效率主要来自企业规模等经济因素[21],并且国有企业的生产活动满足“卡尔多—维尔顿定律”,比非国有企业具有更高的动态规模效益[22]。第四,国有企业在宏观效率上具有比较优势。[23]即便是在微观效率上,虽然所有制决定论认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效率上有明显的差距[24],但现有文献对国有企业的效率的度量忽视了更重要的钱德勒—拉佐尼克传统强调的生产性效率[25]。
迄今为止,关于国有企业效率的争论来自两个经验事实,一是通过对比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相关数据,发现非国有企业普遍效率更高,这是国有企业低效率的直接证据;二是通过扩大效率的定义,引入宏观效率,来为国有企业的效率辩护。但这两个经验事实都存在缺陷。首先,在对比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数据时,研究者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路径依赖问题。国有企业是从旧体制存续下来,参与到市场竞争的,和非国有企业相比,竞争的起点不同,承担的历史包袱也不同,在研究的过程中,只有把这个历史因素分离出去,才能实现可比性。简单地通过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就会掩盖可比性这个因素。其次,在讨论国企效率时引入宏观效率这个定义不够严谨。按照现有的相关文献的理解,所谓宏观效率,就是指企业资源配置效率之外的某种效率,按照前述企业性质的论述,这在本质上就是社会责任的体现,也就是说,企业承担了社会责任。但宏观效率的定义和企业社会责任之间存在本质差异,宏观效率可以理解为国有企业作为总体对宏观经济总量产生了影响,比如就业;而社会责任是国企个体在社会性上的资源配置结果。作为个体的国企的社会责任效应加总是否等同于宏观效率?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假如按照现行的研究思路,通过总量数据来讨论国企的宏观效率则是不可行的,因为无法分离出国企的制度特征以外的其他因素的影响,所以,基于总量数据推断国企的宏观效率是一个伪命题。真正要研究国企的宏观效率,需要对国企微观层面的社会性资源配置及其效果进行测度,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则需要权衡资源在企业利润目标和社会目标之间的配置所可能产生的效率冲突或效率增进。再次,迄今的研究都忽略了一个关键事实,即当国有企业逐步退出,数量下降到一定程度时,政府对国有企业监督的效率会递增,并可能在某个拐点上呈现出边际递增的状态,这会大幅度降低国有企业的代理成本,改进国有企业的效率。而迄今的研究并没有关注到国企数量变化所导致的效率条件的根本性变化。
在关于国有企业效率的研究中,选取经济特征指标也需要进行仔细甄别。迄今的研究比较重视三个关键因素:一是规模,二是政企关系,三是垄断。首先讨论规模因素。的确,泛泛地谈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所有制差别毫无意义,只有具备可比性才能进行比较。对企业来说,如果要比较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所有制因素上的效率差别,就必须控制所有其他影响效率的因素,而规模可能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实际上,质疑和否定国有企业有效率的理论都是基于代理成本假说,但在市场环境下,对于大规模的企业来说,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代理成本都是同样巨大的,或者说随着代理链条的增加,代理成本边际上的增加很小。也就是说,对大规模的企业,即便国有企业的代理链条比非国有企业长很多,但代理成本也可能相差无几。何况国有企业可以通过减少数量来提高监督效率,降低代理成本。不过,单纯地讨论企业的规模的影响似乎也有问题,因为规模总是和政企关系以及垄断联系在一起的。规模很大的企业通常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垄断性,垄断租金是企业高边际利润的来源。因此,在比较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时,需要分离出企业的垄断租金,或者说只有比较同等垄断势力下的不同所有制企业,才有可能找到效率差别的制度根源。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政企关系,有时也叫“政治关联”。“政治关联”假说认为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影响企业的效率,但这个影响是双重的,政企关系有可能导致企业软约束,会导致政企合谋,甚至腐败,正如通常批评国有企业时所说的那样。但不可否认,政企关系也可能给企业带来效率的改进,比如带来数量更多、成本更低的资源等等。假定国有企业在政企关系方面天生地优于非国有企业缺乏相关的经验证据,实际上不仅是中国大陆的企业,整个东亚以及欧洲很多国家和地区的企业都普遍存在政企关系,这点已经有广泛的学术研究。所以,我们不能主观上假定政府只把援助之手伸向国有企业,其实现实中的非国有企业也常常得到政府的扶助。规模越大的企业可能政企关系越强,因此,在讨论规模问题时,还需要分离出政企关系这个因素。
总之,研究国有企业的效率问题时,首先需要明确一个特征事实,那就是市场化之前的国企和市场化之后的处于市场竞争当中的国企是完全不同的。在具体研究上,我们真正需要做的事情是实现可比性。在理论上,应该给定一定数量的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公平竞争,假定国有企业的效率随着国有企业的数量的变化而改变,国有企业的纵向监督效率提升,从而导致国有企业的效率发生改变。在理论分析层面,我们还要区分最优效率边界和现实的效率;然后,讨论现实的效率与最优效率边界的差距,这实际上是拉佐尼克的配置性效率和生产性效率的定义。也就是说,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比较应该是最优效率边界的比较和现实效率的比较。在经验研究上,我们需要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数据进行整合,以分离出各种非常规变量的影响,形成可比的统计口径,然后才能进行比较,而不是简单地用工业企业数据或者上市公司数据进行比较。
四、国有企业的改革路径:全面私有化还是分类改革?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针对国有企业改革路径的讨论也是一直争论不休。这种关于改革路径的争论可以简单地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激进改革路径,另一类是渐进改革路径。但对渐进改革路径也还存在争议,即渐进改革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实际上,围绕改革路径的争论本质上是对改革的终极目标的争论。无论是激进改革还是渐进改革,都有两个目标可以选择,一是全面私有化目标,二是分类改革目标。前者强调国有企业全部退出,后者则强调国有企业在一些行业退出,在另一些行业则继续保留。如果对这两种改革路径的争论进行深入解剖,就能够发现这种争论其实非常不成熟,甚至很不严谨。
首先看第一种改革思路。全面私有化方案的理论依据是前述的所有制决定论,即国有产权是导致国有企业低效率的根源,国有企业改革不是是否保留国有企业的问题,而是何时退出以及如何退出的问题。[26]这种思路的逻辑很简单,本质上就是休克疗法的翻版,而迄今相关经济体的改革实践已经表明,休克疗法并没有表现出普遍的效率改进,或者准确地说,休克疗法同样有其效率条件。
其次,全面私有化改革的经验证据本身受到质疑,这种观点忽视了国有股权还存在“帮助之手”[27],并且非国有企业效率相对较高主要体现在竞争性行业[28]。国有控股模式在社会效益上有比较优势。[29]也正是因为对全面私有化的思路争议颇大,一些学者提出了渐进改革的思路,这种思路认为国有企业具有多样性,在不同的行业领域其效率表现也不同,并且在一些特定的行业,不能完全以效率标准作为改革的依据,还要考虑公平等问题,因而需要分类对待。渐进改革的思路被称为“分类改革”的模式。[30]这种分类改革的思路充分考虑到了国有企业的异质性以及效率上的分化,并考虑到了国有企业的性质,因而在理论上逐渐得到大部分人的认同, 他们把国有企业区分为商业类和公益类,或者区分为竞争类、功能类和公共服务类,或者类似的变体。[31]
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践过程中,分类改革模式占据了主导地位,现有的国有企业政策设计思路可以概括为四个核心元素:市场化导向、股份制公司化、分类改革及混合所有制,这四个元素恰恰体现了分类改革模式的内涵。不过,如果具体到理论层面,无论是激进改革模式还是分类改革模式,都存在一些认识上的误区。首先,改革是针对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有企业还是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的国有企业?全面私有化模式试图通过对计划经济时代的国有企业进行全面的快速的私有化,来重构市场化的企业基础,但这种设想的前提是市场制度能够在一个较短时期内全面建构,这恰恰隐含地假定了有一个充分理性的计划者存在,因而和计划经济思路并无本质区别。事实上,制度是一个逐步演进的过程,具有历史性,这一时间维度和新古典范式相悖,而全面私有化改革不过是新古典范式的一种表达而已。新古典范式自身的理论错误必然导致激进改革模式的错误,这一点在过去并没有被深入剖析。其次,无论是遵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遵循制度经济学,都不会认可制度能够完全人为设计的说法,制度的某些元素可以创设,但制度的整体只能逐步演化。这就使得分类改革具有合理的理论支撑。但过去持分类改革观点的研究者并没有意识到这个理论支撑的存在,而只是就事论事地提出改革的方案,这就使得渐进改革方案本身存在模糊性。原因在于,渐进改革的目标是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共存共进,还是通过渐进的方式逐步实现私有化?最后,两种思路都忽略了两个重要事实:其一,在既定的改革节点上,国有企业并非都无效率,既然如此,对于有效率的国企来说,就不存在私有化的动因;其二,迄今学术界并无明确的证据表明,在一些特定行业和特定领域非国有企业必然优于国有企业,比如在高度垄断的行业以及在公共品、公益品等领域,这同样使得这些领域的国有企业私有化动因不足。所以,总体上看,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经验上,分类改革模式的依据更充分,但迄今为止,关于分类改革模式的论证还缺乏相应的理论基础。
尤其重要的是,在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所呈现出的特征事实中,有一条被研究者完全忽略了,那就是的确存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共存共进的情况,一些行业得以快速崛起并在国际上占据比较优势,根本原因就在于此,而现行的关于国有企业的理论研究则完全忽略了这一特征事实。我们认为,一个有说服力的渐进式改革理论逻辑必须能够同时解释国企和非国企互斥或者共存共进的特征事实,并且能够同时解释市场环境和非市场环境下国企改革路径的异同。正确的渐进式改革的目标并非最终将国企完全私有化,也不是简单地以行业来区分,人为地设定某些行业必须完全私有化,某些行业必须完全国有化,而是要在国企和非国企之间寻求一条合作之路。也就是说,国企改革需要建立一个关于分类改革模式下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共存共进的理论基础。
五、国有企业的治理模式:股权至上模式还是利益相关者模式?
企业的目标决定了相应的治理结构,过去有关治理结构的讨论一直存在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种被称为“股东至上主义”;另一种被称为“利益相关者论”。国内关于企业治理结构的争论最早开始于张维迎、周其仁和杨瑞龙、周业安等。在张维迎看来,企业的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必须匹配,由于资本是真正的风险承担者,因而拥有控制权。[32]这种股东至上主义遭到了周其仁和杨瑞龙、周业安等人的反驳。周其仁认为,人力资本具有关系专用性,是“专用资产”,同样可以获得控制权。[33]而杨瑞龙、周业安从科斯等人的企业理论出发,认为企业是利益相关者之间缔结的一系列契约关系的集合,契约的不完全性导致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在不同的环境下会承担各自的风险,这就产生了“或有产权”问题。或有产权的出现会导致控制权随风险分担的变化而自动转让或谈判转让。[34]进一步看,企业的生命力不是来自股东,而是来自包含股东在内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长期合作,这要求公司的治理结构是多边的共同治理模式和相机治理模式的有机结合。[35]
企业治理结构的两种观点之争实际上是企业目标之争的延续。股东至上主义是利润最大化的翻版,而利益相关者论则是社会责任说的体现。在充分竞争的假定下,股东至上主义是正确的,但这只是一种理想状态,问题的关键在于理论是停留在“黑板”上,还是回归到现实中?科斯当年批评新古典范式是“黑板经济学”,就是强调理论必须直面现实。[36]现实的企业会存在各种侵权行为,以及难以确权的状态,此时就会产生契约的某种空白区域,也就是不完全性。这种不完全性既无法事前约定,也无法通过某种市场机制或第三方执行机制来界定,只能通过生产过程中的利益相关者各方动态的谈判来解决。承认这一点,是分析企业治理结构的出发点。在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上,新古典范式仅仅看到权益项,假定负债项是明晰的。但现实中的企业的负债项是不完全的契约,即便是短期和长期负债项也存在不完全性,从而银行等债权人也有获得控制权的可能性。而对于其他应付类债务来说,或有产权的存在同样是其获得控制权的根据。因此,一个动态的企业治理结构理论必须包含这种潜在的控制权让渡机制,从而可以在事前体现为参与治理(也就是共同治理),事中体现为相机治理(控制权的某种随时随机让渡机制)。
就国有企业来说,强调利益相关者学说尤其重要。国有企业的高度社会化性质决定了其必须追求社会利益,这体现为利润目标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目标的内在一致性,而保证这种一致性的制度前提是建立高度社会化的治理结构,共同治理和相机治理的有机结合构成这种治理结构。国有企业过去的一些制度设计,比如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合理化建议制度等等,都是共同治理机制的一种体现。但过去的治理结构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延伸,容易陷入等级僵化和官僚化的陷阱。市场环境中的国有企业脱离了计划体制的基础,因而治理结构的设计就需要打破僵化的等级,对管理者进行有效监督,这就不仅仅需要自上而下的外部监督,更重要的是要建立自下而上的内部监督机制,特别是企业内部的民主化机制。同时,要考虑到不同类型的债权人参与治理的渠道和机制。
六、结论
迄今为止,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国有企业的性质、国有企业的效率、国有企业的改革路径和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围绕理论和经验证据,关于这四个方面问题的争论持续不断。出现争论的原因在于缺乏一个合理的理论基础。本文认为,国有企业的性质是一个核心问题,而目前围绕这个核心问题的认识,要么基于新古典范式,要么基于传统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忽略了新企业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可能存在的某种共性,而对于理论的单一执念往往限制了研究者自身的视野。实际上,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新企业理论,都反对新古典企业理论,都强调企业的社会性,它们的区别在于对企业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性质的理解以及对社会性程度的看法存在差异。如果能够找到这种共性,那么,对国有企业性质的讨论就要简单得多。国有企业作为一种社会化程度最高的企业组织形式,在理论上可以通过契约化来实现生产和分配的内在一致性。而在现实当中,其中一方的权利优势(比如官僚化、资本的力量等)可能会破坏契约关系,从而需要相应的制度安排来保障。这种制度保障就是治理结构。我们认为,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体现为利益相关者论视角下的共同治理和相机治理有机结合的模式,而不可能是新古典范式下的股东至上主义模式,因而对国有企业来说,不可能把利润最大化作为唯一的目标,而是要追求利润最大化和社会利益之间的一致性,也就是说,在最弱的意义上,国有企业需要按社会责任假说行事。
研究者争论的另一个焦点是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大多数观点认为,和非国有企业相比,国有企业效率低是一个客观事实。而反对者认为,对国有企业的效率评价不能仅仅看其微观效率,而是要看宏观效率。我们认为,围绕国有企业效率的研究忽略了一些重要的因素,导致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在不可比的前提下进行比较,其结论也就缺乏说服力。首先,现有的研究没有考虑国有企业的路径依赖问题;其次,现有的研究没有仔细分离出规模、政企关系、垄断等因素的影响。不过,国有企业宏观效率的提法也是不妥当的,因为宏观效率很难通过总量数据进行分离和测度。这就需要通过微观数据来谨慎测度国企在利润目标和社会目标上各自的资源配置及其效应。在数据处理上分离出政府和企业的政策往来以及国企自身生产经营活动的结果,只有对这些数据进行仔细的分离,才能够推算出国有企业的社会利益。另外,在国有企业数量逐步减少的过程中,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监督效率也会逐步提升。但迄今的经验研究都没有分离这些效应。由于对国有企业效率的经验研究还缺乏合理的技术与方法,有关国有企业效率问题的争论还将继续下去,断言所有制对企业效率有重要影响还为时过早。由于对国有企业效率的争议本身就很模糊,直接导致了国有企业改革路径的选择也存在模糊性。早期关于激进改革模式和渐进改革模式的争论实际上是新古典范式与理论直觉的争论,虽然渐进改革思路占据主导地位,但渐进改革模式本身存在模糊性,产生这种模糊性的原因在于忽略了国企和非国企共存共进这一客观存在的特征事实,并且也没有建立一个理论基础来证明渐进改革过程中国企和非国企共存共进的合理性与可行性。鉴于此,未来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1] 郑江淮:《国有企业预算约束硬化了吗?——对1996—2000年信贷约束政策有效性的实证研究》,载《经济研究》,2001(8):53-60;龚强、徐朝阳:《政策性负担与长期预算软约束》,载《经济研究》,2008(2):44-55。
[2] 张荣刚:《积极推行股份制,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载《经济研究》,1997(11):9。
[3] 刘世锦:《中国国有企业的性质与改革逻辑》,载《经济研究》,1995(4):29-33。
[4] 金碚:《三论国有企业是特殊企业》,载《中国工业经济》,1999(7):5-9;金碚:《论国有企业改革再定位》,载《中国工业经济》,2010(4):5-13。
[5] 张晨、张宇:《“市场失灵”不是国有经济存在的依据——兼论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5):38-44。
[6] 杨瑞龙:《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理论思考》,载《经济研究》,1995(2):13-22;黄速建、余菁:《国有企业的性质、目标与社会责任》,载《中国工业经济》,2006(2):68-76。
[7] 张晨、张宇:《国有企业是低效率的吗》,载《经济学家》,2011(2):16-25;林岗、张晨:《关于进一步推进国有经济改革发展的一些意见》,载《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3(2):5-15。
[8] 刘小玄、李利英:《企业产权变革的效率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2):4-16;杨汝岱:《中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载《经济研究》,2015(2):61-73。
[9] 张春霖:《存在道德风险的委托代理关系:理论分析及其应用中的问题》,载《经济研究》,1995(8):5-8;张维迎:《控制权损失的不可补偿性与国有企业兼并中的产权障碍》,载《经济研究》,1998(7):3-5。
[10] 张维迎、吴有昌、马捷:《公有制经济中的委托人—代理人关系:理论分析和政策含义》,载《经济研究》,1995(4):10-20。
[11] 刘小玄:《中国转轨经济中的产权结构和市场结构——产业绩效水平的决定因素》, 载《经济研究》,2003(1):21-29。
[12] 陆挺、刘小玄:《企业改制模式和改制绩效——基于企业数据调查的经验分析》,载《经济研究》,2005(6):94-102。
[13] 刘小玄:《中国工业企业的所有制结构对效率差异的影响——1995年全国工业企业普查数据的实证分析》,载《经济研究》,2000(2):17-25;刘小玄:《民营化改制对中国产业效率的效果分析——2001年全国普查工业数据的分析》,载《经济研究》,2004(8):16-26。
[14][16] 李寿喜:《产权、代理成本和代理效率》,载《经济研究》,2007(1):102-112。
[15] 平新乔等:《中国国有企业代理成本的实证分析》,载《经济研究》,2003(11):42-53。
[17] 周业安:《金融抑制对中国企业融资能力影响的实证研究》,载《经济研究》,1999(2):17-18;Qian Sun, et al:“How Does Government Ownership Affect Firm Performance?Evidence from China’s Privatization Experience”.JournalofBusiness,Finance&Accounting, 2002,29(1):1-27.
[18] Tian,Lihui:“Government Shareholding and the Value of China’s Modern Firms”.William Davidson Institute Working Paper No.395,2001.
[19] 林毅夫、李周:《现代企业制度的内涵与国有企业改革方向》,载《经济研究》,1997(3):3-9;林毅夫、李志赟:《政策性负担、道德风险与预算软约束》,载《经济研究》,2004(2):17-26。
[20] 张春霖:《国有企业改革与国家融资》,载《经济研究》,1997(4):3-10。
[21] 谢富胜、李双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的定位》,载《教学与研究》,2010(5):9-14。
[22][25] Dic Lo,and Guicai,Li.“China’s Economic Growth, 1978—2007: Structural-institutional Changes and Efficiency Attributes”.JournalofPostKeynesianEconomics,2011,34(1):59-78.
[23] 刘元春:《国有企业宏观效率论——理论及其验证》,载《中国社会科学》,2001(5):69-81;刘元春:《国有企业的“效率悖论”及其深层次的解释》,载《中国工业经济》,2001(7):31-39。
[24] 刘瑞明:《中国的国有企业效率:一个文献综述》,载《世界经济》,2013(11):136-154。
[26] 刘小玄:《国有企业民营化的均衡模型》,载《经济研究》,2003(9):21-31;张军、罗长远、冯俊:《市场结构、成本差异与国有企业的民营化进程》,载《中国社会科学》,2003(5):4-15。
[27] 李涛:《混合所有制公司中的国有股权——论国有股减持的理论基础》,载《经济研究》,2002(8):19-27。
[28] 陈晓、江东:《股权多元化、公司业绩与行业竞争性》,载《经济研究》,2000(8):28-35。
[29] 白重恩、路江涌、陶志刚:《国有企业改制效果的实证研究》,载《经济研究》,2006(8):4-13。
[30] 杨瑞龙:《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理论思考》,载《经济研究》,1995(2):13-22。
[31] 黄群慧、余菁:《新时期的新思路:国有企业分类改革与治理》,载《中国工业经济》,2013(11):5-16;高明华等:《国有企业分类改革与分类治理——基于七家国有企业的调研》,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4(2):19-33。
[32] 张维迎:《所有制、治理结构及委托—代理关系——兼评崔之元和周其仁的一些观点》,载《经济研究》,1996(9):3-15。
[33] 周其仁:《市场里的企业: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载《经济研究》,1996(6):71-79。
[34] 杨瑞龙、周业安:《一个关于企业所有权安排的规范性分析框架及其理论含义——兼评张维迎、周其仁及崔之元的一些观点》,载《经济研究》,1997(1):12-21。
[35] 杨瑞龙、周业安:《论利益相关者合作逻辑下的企业共同治理机制》,载《中国工业经济》,1998(1):38-41。
[36] 罗纳德·H·科斯:《生产的制度结构》,载《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 武京闽)
Institution Reengineering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 Ideas Rethinking and the Theoretical Logic Reconstruction
ZHOU Ye-an,GAO Ling
(School of Econom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The history of reforms of state-own enterprises (SOES) is full of controversies, which mainly concern such issues as the nature, efficiency, reform path and governance structure of SOEs.To clarify the direction of reforms of SOEs, this paper makes critical review of related research around four theses.It is found that SOEs are a kind of organizations with highly socialized forms, which are in line with the stakeholder theory of corporate governance.Second, the existing research on the efficiency of SOEs ignored the issue of their path dependence.Besides, scales, monopolies and political connections are not isolated from other influence factors.Therefore we need to be prudent in asserting whether SOEs have low or high efficiencies.Finally, SOEs have followed a gradual reform path in practice, but so far there is still no convincing theoretical framework to argue for the stylized facts that SOEs and non-SOEs are able to coexist with development.Thus the future research on the reform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till has a long way to go.
state-owned enterprise(SOEs);socialization; stakeholders; path dependence
周业安: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高岭: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