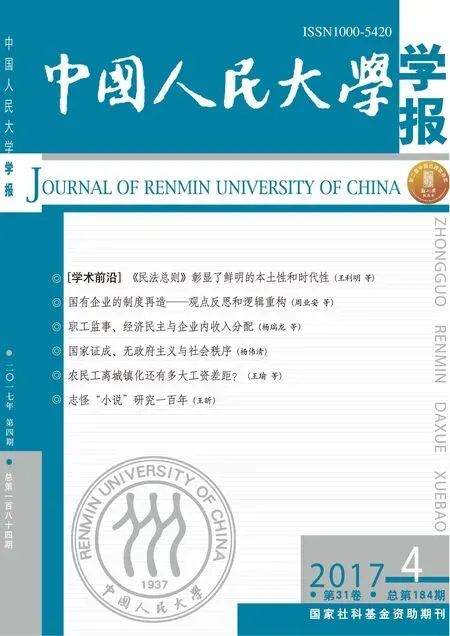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户籍制度的“双二属性”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
杨菊华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户籍制度的“双二属性”与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
杨菊华
城镇与乡村、本土与外来的区隔构成户籍制度的“双二属性”,加上附着于其上的外溢特征,使得国内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既面临国际移民融合的共性问题,也面临中国式的融合困境。其中,乡—城流动人口相较于城—城流动人口,更是多重弱势身份交叠,融入进程更为坎坷,融合前景更不确定。总量巨大的流动人口与流入地主流人群和制度安排之间的断裂隐藏着巨大的社会风险,也是新型城镇化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必须扫除的重大障碍。突破户籍墙、结构墙和理念墙,跨越人为设置的各类边界,推动群体关系从隔离到嵌入,是新型城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它既是社会融合的本质特性,也是实现社会融合的根本途径。
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社会融入;户籍制度“双二属性”;新型城镇化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总数超过2.45亿人,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8%。流动成为流动者及受其影响之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在改变个体生存和发展状况的同时也带来了深刻的人口、经济和社会变化,主要表现在:改变了中国人口的地域分布状况,成为在低生育率和低死亡率情景下国内人口区域变动的主导要素;改变了地域之间人口的年龄结构和老龄化程度,以及地区之间的性别结构和通婚模式,成为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区域发展的一个核心要素。
随着流动模式的改变,许多流动人口“并不流动”,从计划返乡转向渴望融入流入地社会。为此,中央政府反复强调,必须从维护最广大民众根本利益的高度出发,落实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动流动人口的融入进程,提升新型城镇化质量,实现“共享”发展。作为“十三五”时期政府社会管理创新的目标之一,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要旨和重要检验标尺,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成为一个具有全程性、全局性和现实紧迫性的重大战略议题。
社会融合是指通过个体之间、群体之间、文化之间互相接触、竞争、冲突、适应[1],流动人口逐步实现经济整合、社会互动、文化交融和心理认同的过程,也是一个制度排斥逐渐减弱和人群机会差异逐渐消弭的过程,其间,宗教文化、资本禀赋、职场能力、制度因素等都是重要的影响要素。[2]对国内流动人口而言,“户籍墙”[3]是制约融合进程的本源性障碍,文化要素和自身主观因素也会阻碍流动人口的融合[4]。户籍制度改革的滞后性,制度和观念的不包容性依旧是融合进程中的“坚铁”[5],导致流动人口缺乏实现融合的财力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权利资本,进而使得他们(主要是指农民工)面临“被边缘化”和“自边缘化”[6]的双重困境。无形的隔离墙(即文化和理念的排斥)和有形的隔离墙(即制度有意或无意的制约)[7]使得流动人口的融合路径狭窄,最终能实现融合、成为真正“本地人”者少之又少。
现有研究对流动人口户籍制度中的“城—乡”属性有较为丰富的论述,但仅有极少数研究关注到其“内—外”属性。流动人口也是一个高度分化的群体,内部分化严重,表现为:不仅有“农民工”,还有大量的随迁家属;不仅有乡—城流动人口,还有约四分之一的城—城流动人口,故户籍制度的“内—外”属性对流动人口而言同样重要。那么,户籍制度城—乡、内—外“双二属性”如何影响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目前以居住证制度为载体和抓手的户籍制度改革可否破解流动人口融合过程中的障碍,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步伐?怎样有效突破融合进程中的“三堵墙”?凡此皆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推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进程、提高其融合水平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本文的分析思路如下:首先剖析户籍制度的“双二属性”及其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带来的排斥效应;其次,探析户籍制度改革的基本状况,重点论述户籍制度改革存在的问题及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进程的影响,并提出突破区隔、跨越并立、共享机会和共有权利、实现人群嵌入的途径,探寻推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突破口;最后,对融合困境隐含的潜在的社会风险提出初步思考。近年来西方国家频发的移民恶性事件表明,社会的融合传递着成功经验,而断裂则引发失败教训。流动人口若长期无法融入流入地社会,可能会进一步激化社会分化,引发社会矛盾,激发或加剧他们的“失范”行为,形成社会冲突与动荡的隐患,危及社会和谐与稳定。故此,关于户籍制度、结构排斥及其衍生制度阻碍流动人口的融合进程的途径和机制等诸多问题,亟须政府、社会和学界高度关注。
二、户籍制度的“双二属性”与“双重排斥效应”
社会融合本源性的要义是,少数族裔文化与主流文化的交融汇合,这也是国际移民融合研究的核心内涵。作为一个多元一统的国度,中国以汉民族为主,国内多数流动人口并无太大的语言障碍和宗教隔阂,但却面临因制度隔离带来的独特的融合困境。
(一)户籍制度的“双二属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思路和模式是,将农村作为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建设的劳动力蓄水池,劳动者游走于城与乡之间,漂泊在东中西部地域之间,需时便取用,不需时便闲置,这种“两栖化”模式使得流入地社会无须为流动人口提供平等的福利和服务待遇。这种现象又与地区分割密切联系在一起。地区公共资源的配置主要依据身份关系,不同身份之人对应着有差别的公共服务和公共福利。尽管在市场化过程中,就业制度对外来人口的排斥大大减弱,但一些流入地依旧遵循“先城镇、后农村,先本地、后外地”的用工原则,在就业岗位上对流动人口进行限制。流动人口主要在体制外就业,集中在次级劳动力市场,难以进入主流劳动力市场,进而被排斥在社会保障和住房保障制度之外,导致流动人口与本地市民在居住条件等方面产生隔阂,阻碍二者的互动与接纳。
户籍制度是中国特色“流动人口”产生的制度根源。户籍制度不仅具有社会普遍关心的单纯的城—乡“二元”属性,而且具有“双二元”属性,即既有“城镇—乡村”的户籍类型,也有“本地—外来”的户籍地点。[8]户籍制度基于人口管理的目标对个人信息进行登记本身并无不可,但基于户籍的身份制度却超过了把人区分为“是谁”、“从哪里来”、“与他人是何关系”的普通范畴,成为资源配置、服务享有和福利可得的标尺。作为具有极强张力的制度,户籍带来的影响辐射到人们经济生产和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造成城市与农村的断裂,市民与农民的鸿沟,本地与外来的隔离。换言之,在户籍制度的规范中,人不仅被标记为城里人、农村人,而且被标记为某个具体地点的城里人或农村人,使人一生下来就被赋予了四种有差别的身份(见图1)。当这种身份区隔与人口流动结合在一起时,就形成了四类具有等级高低之分的人群,一个国家有“四个社会”。与之对应的分别是本地城镇户籍人口、本地农村户籍人口、城—城流动人口和乡—城流动人口。

图1 户籍制度的“双二属性”
可见,如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9]一样,户籍制度的“双二属性”对现地的四类人群进行的等级划分,使之形成核心—半核心—半边缘—边缘的群体构架(见图2)。其中,乡—城流动人口与现地户籍农民和城—城流动人口在身份上存在交叉,或同为农村人口,或同为外来人口;城—城流动人口与乡—城流动人口和现地城镇市民在身份上也有所交集,或同为外来人口,或同为城镇居民。

图2 户籍制度的“双二属性”与人群等级划分
户籍制度的双重属性不仅将本地城镇户籍市民和乡—城流动人口完全隔离开来,也将本地农村人口与外来农村人口隔离开来(尽管他们拥有相同的户籍类型),还将外来城镇人口与本地城镇市民隔离开来(虽然他们拥有同样的户籍类型)。在流入地资源和福利享有方面,本地城镇户籍居民坐拥作为本地人和城市人的双重利益。相对于城—城流动人口,他们具有作为本地人的优势;对于本地农村人,他们又是城市人。本地城镇户籍是他们对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享有的“入场券”,并使他们成为现地公共资源和社会服务的最直接和最大的受益者。
现地的农业户籍人口虽不在城市公共管理体制之内,但城市的扩张和发展也给他们带来越来越多的实际利益,并可能一夜之间成为当地的“新富人群”。这种优势资源的获取对外来人口而言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学历高素质强的城—城流动人口亦不例外。从这个意义上讲,城—城流动人口与本地市民的关系更为复杂。有时,城—城流动人口处于半边缘地位;有时,本地农村户籍人口处于半边缘地位,二者在资源的可及和享用方面相互交错,互有优劣。但凡涉及稀缺公共资源的分配,城—城流动人口就位居弱势,处于半边缘地位。而当市场力量更强(即个体禀赋因素能发挥更大作用)时,城—城流动人口作为城里人的优势才可能显现出来,地位超过本地农村人,处于半核心地位。可见,在承担着多种制度带给他们的不确定风险时,城—城流动人口也获得一定的向上流动机会。
可见,“双二属性”所带来的排斥既针对农村人,也针对来自其他城市的外来人。在“双二属性”的作用下,改变了生活场域和职业的(乡—城)流动人口被排斥在现地体制之外,游走于城市体系与农村体系、体制内与体制外、正规市场与非正规市场、传统产业与现代产业之间,在生活地域、工作职业与社会网络等方面与现地户籍人口处于区隔甚至割裂状态。[10]
(二)城乡差分与基于户籍类型的排斥
城—乡、内—外的“双二属性”带来“农村人效应”和“外来人效应”,对流动人口或形成单一的“外地人排斥”效应,或形成“外地人”和“农村人”的“双重排斥”效应。
乡—城流动人口居于金字塔的底端,既属于空间形态上的外来人口,也属于制度安排上的农村人口,同时由于自身资本缺失的局限(而这也与户籍有关),与其他人群难有交集。虽与本地农村人口拥有相同户籍,但他们却多了“外来人”的标签;虽与城—城流动人口拥有相同的流动身份,但他们却多了“乡下人”或“农民工”的标签,是多重弱势身份交叠、最边缘化的一类人群。
因此,户籍制度的排斥首先是针对乡—城流动人口的,而这一排斥的根源首先在于户籍性质(即类型),而当前社会主要关注农民工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2014年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显示,在子女教育方面,城—城流动儿童的在园比例显著高于乡—城流动儿童;在流动人口整体受到排斥的情况下,乡—城流动人口子女教育受到的排斥更为明显:与城—城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相比,很多人只能选择私立学校,甚至少量群体只能选择打工子弟幼儿园;在收入方面,在业乡—城流动人口的月收入不仅低于本地市民的平均水平,还比城—城流动人口约低900元;乡—城流动人口在流入地拥有住房的比例仅有7.65%,比城—城流动人口低16个百分点;在社会保障水平方面,乡—城流动人口各类保险的参与比例均不及本地市民的一半,只有8.4%的乡—城流动人口拥有住房公积金,仅略超过城—城流动人口(30.2%)的1/4。
可见,对乡—城流动人口而言,基于户籍制度的“双重排斥”不仅使他们难以平等享受经济社会改革发展的成果,而且也限制了其他方面的融合,表现为:他们与本地人口除了业务往来外,多数没有发生真正的接触和互动;作为弱势群体,他们很难对现地文化带来积极的贡献;作为受到排斥的外来人口,他们也难以对现地产生真正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三)内外之别与基于户籍地点的排斥
基于户籍地点的排斥,不仅限于本地—外来的简单区分,还可从跨省、省内跨市和市内跨县这一行政区划维度进行细致的分析。
如图3所示,结构性排斥随着人口流动跨越区域的扩大而愈发彰显。若以行政县(市、区)界作为界定流动人口地域标识的话,则相较于省内跨市流动人口而言,市内跨县的流动人口可享受到当地更优质的公共资源和更多样的社会服务;进而,相较于跨省流动人口而言,省内跨市的流动人口又可享受当地相对更多样和更优质的公共资源与服务。

图3 “内外之别”与公共资源和社会服务的配置
从教育方面来看,若孩子在省内流动,面临的各级各类教育(尤其是高考)制度的障碍不大,但一旦跨省,情况就发生了质的变化:越是优质教育资源较多之地,学前教育和高等教育对外地考生设置的准入门槛往往也越高。从求职就业的门槛来看,一些地方(如北京)对于单位招收外地户籍毕业生有明确规定,即每招收一个外地户籍生,就必须搭配一个本地户籍生,反之却不然。从社会保障制度来看,社会保险的转移支付往往以地级市为界分,市内流动者在保障接续上面临的障碍较小,而跨市,尤其是跨省,则会带来极大不便,甚至难以执行和落实。如果说从高保障地区向低保障地区的转移有较大可能性的话,那么,从低保障水平地区向高保障水平地区的转移即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极其困难的。正因为如此,若不考虑资源禀赋等个体差异的话,流动人口在现地所能享受的(优质)福利和服务随着按行政制度划分的户籍地点与居住地点差距的加大而呈现出漏斗式的减少。
即便禀赋极高且具有高度正向选择性的城—城流动人口,也未能摆脱外地户籍给他们在现地生活带来的障碍和流入地社会的结构性排斥。他们大多是从中西部城市来到东部发达城市,追求自由平等、公平正义,渴望体面工作、有尊严地生活,希望通过隐忍和自身努力来实现梦想。的确,较高且超过本地市民平均水平的人力资本积淀可以给他们带来更高的收入和社会保障水平,但是,虽然生存境遇好于乡—城流动人口,但制度的不认同带来的政治、经济、公共服务与福利、社会网络等方面的排斥,加上政治资本和组织资本获得途径的堵塞,使得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依旧被挤压在流入地的主流社会之外,尤其是难以正常获取必须凭本地户口才能享受的权利和资源。在吸引了大量来自其他城市和乡村的流动人口、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沿海地区和大城市,本地农村户籍的“含金量”甚至超过外地城市户口。户籍制度的“内—外之别”,以及显性或隐性的地方保护政策和措施的普遍存在,构成城—城流动人口实现融入的最大制度障碍。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多个调查数据的分析结果都表明,尽管城—城流动人口的工资性收入高于本地市民的平均水平,但通过劳动合同和工作时间测量的劳动保护、通过职业类型透视出来的社会声望、通过社会保障折射出来的社会保护、通过住房体现出的生存尊严等都反映出,城—城流动人口在人力资本更高的情况下,亦未被等同对待。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在流入地学习、工作和生活了多年,但一纸“外地”户籍却将其排斥在外,具有较高的边缘化风险。
三、突破边界、实现嵌入是社会融合的根本途径
个体差异和群体差异是十分正常的现象。但是,因制度设计不合理所带来的资源垄断和不公平的利益竞争,由此形成的个体之间和群体之间机会的不公,以及因机会不公所导致的个人发展能力之差别却是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是实现融合的本源性障碍。因此,推动流动人口的融合进程,首先必须破解户籍制度这面“玻璃幕墙”[11]。它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却无处不在,横亘在农民与市民之间,阻隔在本地人口与外来人群之间。为此,许多学者提出,需要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以社区为依托、互动为根本,加强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12];重视流动人口的自然性和干预性融合,鼓励其主动参与双向融合,推动其渐进性和多维度融合[13];充分考虑流动人口内部结构的复杂性,提供匹配流动人口不同亚群体的制度安排、城市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14];等等。过去几年中,部分大城市为实现人口管理目标,逐渐推行居住证制度。2014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也正式公布。但是笔者认为,目前的户籍制度改革并未从根本上触及制约流动人口实现融合的制度障碍。
(一)户籍制度改革的现状
近年,国家和地方政府在户籍制度改革方面都进行了有益的尝试[15],制度本身及其外延经历了由表及里的变化,从暂住证到居住证、从计划分配到积分落户,旨在打通从农村到城市、从中西部地区到东部地区的道路,破解户籍这面“玻璃幕墙”。在国家层面,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近几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强调,要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下称《规划》)提出:“按照尊重意愿、自主选择,因地制宜、分步推进,存量优先、带动增量的原则,以农业转移人口为重点,兼顾高校和职业技术院校毕业生、城镇间异地就业人员和城区城郊农业人口,统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2016年1月1日颁布的《居住证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规定,在全国推行居住证制度,并以居住证为载体,各地必须积极创造条件,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和便利向常住人口全覆盖,逐步提高居住证持有人享有的公共服务水平,打通居住证持有人通过积分等方式落户的通道。
同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明确提出:“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放宽城镇落户条件,建立健全‘人地钱’挂钩政策。居住证具有很高的含金量,要加快覆盖未落户的城镇常住人口,使他们依法享有居住地义务教育、就业、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 推进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和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建立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把符合条件的外来人口逐步纳入公租房供应范围”。
新型城镇化规划和居住证制度是我国户籍制度改革迈向深水区的重要步骤,表明了政府推动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推进新型城镇化的信念和决心。
(二)户籍制度改革并未发挥应有效应
由于户籍制度改革涉及稀缺优质资源的再分配,所以也是外来人和本地人等多个利益集团多方博弈的过程。在博弈的过程中,外来人口处于绝对的弱势,也使得目前的户籍制度改革存在四大相互关联的问题,延宕了流动人口的融入进程。
一是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落户指标紧缩、大门紧闭。《规划》的户籍改革原则是:“以合法稳定就业和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等为前置条件,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城区人口50万~100万的城市落户限制,合理放开城区人口100万~300万的大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城区人口300万~500万的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城区人口5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条例》几乎完全延续了这一原则,规定持证后在大城市落户仍有限制,城区人口500万以上特大城市落户标准最严苛,需根据当地综合承载力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以稳定就业和住所、参加社保年限、连续居住年限等为主要指标。因省会城市或东部发达地区大城市的人口规模基本都超过这个下限,仅此一项,就将绝大多数流动人口排斥在(特)大城市门外。目前的这种顶层制度设计透视出的是对流动人口赤裸裸的拒入。对不同级别的城市设置略有差异的落户标准可以理解,但时下这种“一刀切式”的大门紧锁政策和机械性的做法,不留空间和余地,违背了人口流动的自然法则,具有倒退性和掠夺性的特点。更重要的是,敞开还是关闭大门是政策理念和价值导向的外化,而这种理念会直接作用于制度墙和结构墙的高耸或消融,带来一系列的衍生效果。
二是小城市(镇)户籍制度改革收效甚微。户口即利益,超(特)大城市的户籍更是绑定了流动人口的利益。小城市(镇)、中西部地区的大城市的户籍管理较为宽松,通过购房或积分形式即可入户,但这些城市的优质文教卫生资源较少,劳动力市场不够发达和规范,经济上难以形成规模效应,人们对未来的发展前景不乐观,且在短期内,这种差距很难发生彻底扭转。这种状况对本地人,尤其是青年人缺乏吸引力,连本地人都留不住,更不用说吸引外来人口了。
相反,一个城市的经济越发达,就越可能为流动人口提供更好的就业机会、更高的收入水平、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好地发挥自己潜能并得到认可的机会,也就更可能成为流动人口大量聚集之地,成为面临严峻融入问题的地区。大城市对入户申请者的就业背景、就业时间以及受教育程度等提出较高的要求,而乡—城流动人口群体几乎达不到这个条件,所以除中小城市外,落户政策与乡—城流动人口关系甚微,即积分落户制实际上是将占到全部流动人口四分之三的底层流动人口排斥在外。城市越大,落户越难。中小城市若能提供较高水平的公共服务,则有利于这些地方聚集人口。
三是地方改革有名无实的多,户籍改革“去福利化”的少。首先,地方政府进行的户籍制度改革多是将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统称为“居民”,对户口所附着的福利和服务并未有实质性的变革。其次,各地落户积分的条目很多,但多向高端人群倾斜,教育水平和社会保险缴纳在积分中的权重很高,具有很强的倾斜性,所以几乎将大部分城—城流动人口和绝大部分乡—城流动人口拒之门外。事实上,在(超、特)大城市,积分落户政策不仅浮于表面,甚或沦为政府管人控人的“政策工具”,成为显性排斥政策的隐性替代品。[16]
差别化的落户政策驱动不同城市设置不同的落户标准,而这种政策为流动人口设置闸门和分流装置,给不同城市不同的开放程度,以及接纳流动人口的自由,进而使得积分落户制“雷声大、雨点小”,本质上还是服务于人口控制。的确,一些大城市户籍制度改革和人口调控的目标是,“控制人口,不控制人才”,而另一些大城市(如北京)则是“既控制人口,也控制人才”,这就直接影响到积分落户政策的实施。特(超)大城市通过表面的户籍制度改革,树立“作为”形象,摆出“政治上正确”的姿态,但实际上却如“蜻蜓点水”、流于形式,远未实现“去福利化”。无论是积分落户,还是其他形式的户籍制度改革,对流动人口的平等覆盖依旧大多停留在理念层面。各地出台的更为具象的积分落户政策,可能也是顺应中央精神而不得不为的应付之策,其本质依旧是要维护现地既得利益群体的利益[17],或在不触动既得利益者既得利益的前提下对流动人口略加“施舍”。实践经验表明,不是从暂住证变为居住证,甚至也不是户口变了,标示农民身份的土地没有了,一切区隔就自然而然地抹平了。如果说20年前,通过地域流动还有可能实现社会流动的话,那么时下,这样的可能性不仅没有增大,反而更为狭小,本地人在理所当然地享受流动人口的付出时,却强制地将流动人口拒绝在公共福祉的大门之外。
四是户籍制度改革带来的公共服务均等化具有一定的“有效维持不平等”性质。流动人口目前可享受的福利多为边缘性福利,并未真正触动利益格局的调整和再分配,且“梯次渐进式”福利享受机制更可能成为外来人口享受进一步福利的玻璃天花板。以随迁子女的义务教育为例。出生人口数量的减少,降低了适龄儿童的就学人数;一些资源较丰厚且较优质的公立学校可吸纳更多学生就读,而地理位置较差且质量较低的公立学校可能面临关、停、并、转的风险。为保证学校存续,学校和教育管理部门不得不转向流动儿童。从某种意义上看,不是学校给流动儿童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而是流动儿童为部分公立学校提供了生存的机会。而在流入人口集中的特大城市,流动儿童大多只能就读于质量较差、本地孩子淘汰下来的幼儿园、小学或中学,高考也受限制。更有甚者,随迁子女的教育也成为人口调控的重要手段。比如,2014年北京市规定,流动人口子女入学须数证俱全:身份证、出生证、户口簿、暂住证(或居住证)、务工证、住房合同、借读证等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具体操作中约需提交20余种证件及几十种税票、明细、单据文件,并需街道、教委、工商、税务、城建、公安等多个部门的层层审核,一处不清,则前功尽弃;自有住房而无暂住证者,孩子不能上学;社保居住不同区者,孩子不能上学……同年,北京市教委发布十五条,严令各校不得接收无正式学籍的学生;2015年实行电子学籍卡,通过限制非京籍学生,减少低端人口流入或将他们驱赶出去。这就使得流动人口,尤其是乡—城流动人口仅有四种选择:或把子女留在老家,成为留守儿童的一分子;或不能适龄上学;或将孩子送入一个本地孩子不愿上的公立学校或办学条件(尤其是软件)较差的私立学校,接受质量较低的教育;或干脆让年龄稍大的孩子辍学在家或过早地进入劳动力市场。流动人口的子女接受优质教育的途径被阻断,既未实现相对公平,更谈不上绝对公平,不仅使得(乡—城)流动人口自身的生存发展空间十分逼仄,也阻隔了后代的融合前景,还不利于“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发展。
制度难破及因此而起的代际传承是我国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和新型城镇化步履维艰的主要原因。推动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和新型城镇化发展,必须从社会和谐的整体角度出发,突破城市利益、本地人群体利益的限制,扭转已有户籍制度改革浮于表面和形式的状况,从根本上破除影响各层次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障碍,赋予他们平等的市民权利。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推动新型城镇化的发展。
(三)破除制度、结构和理念三堵墙,实现机会均等
长期以来,国家层面和地区层面均通过户籍制度,建立了一整套城与乡、内与外的区隔性的管理体制,造成了本地城镇户籍人口、本地农业户籍人口、城—城流动人口和乡—城流动人口四类群体之间的割裂,阻碍了流动人口的融合进程和新型城镇化的步伐。推进流动人口的融合进程,必须打破区隔,实现嵌入式融合*就好像将各面颜色相同但相互隔离的魔方,转化为一个不同颜色相互交错、并存林立的锦砖或马赛克,进而形成片与片之间互相嵌入的多彩拼图。。
在户籍制度的基础上,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主要面临制度墙、结构墙和理念墙(或称“边界”)的阻碍。制度墙主要是指户籍及其附属制度,前者对人群进行标记,而后者则通过各项福利和服务将不同人群隔离开来;同时,人群的身份不同,隔离墙有厚有薄,隔离度有深有浅。结构墙同样来源于户籍制度,也与地方经济、社会、文化构成密不可分;制度墙越厚重,结构墙也会越坚固。理念墙则是在制度墙和结构墙共同作用下产生的人群之间的互动认知心态的偏差;与具象的制度和结构墙相比,理念墙也更为隐蔽。
要破解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困局,必须冲破三堵“墙”,跨越由此形成的区隔边界,推动不同人群之间的关系实现从魔方状态向锦砖状态的转变,最终实现嵌入式发展。锦砖模式是指打破制度墙和结构墙带来的人群区隔,推动族群和人群之间的互动;拼图模式则是在拆除制度墙和隔离墙的基础上,进一步消除理念墙的区隔,实现人群之间的嵌入交往,真正实现心与心的沟通、文化与文化的交融。
具体来说,一方面,只有制度和结构的“长坚之铁”真正消融,理念墙才能真正拆除;另一方面,理念墙的消融,也会使制度墙和结构墙失去依托。对于理念墙,本地人在墙内,流动人口在墙外,二者的相互对立态度或彼此的漠视共同架起这面高墙,因此,此墙的摧毁也需要墙内和墙外之人的共同努力。美国社会学家Milton Gordon提出人群融合的七个阶段,其中的两个阶段是本地人对移民的接纳态度和行为,表明社会融合是本地与外来双方的适应与接纳过程,既需要流动人口本身的主动性和融入意愿,也需要流入地人群的包容和接纳。[18]只有流动人口做出积极的融入努力,只有本地市民消除对流动人口的偏见,只有消除结构性障碍、制度性歧视、政策性排斥,流动人口才能适应、融入流入地社会中,才能实现社会的良性整合,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此外,流动人口的融合能力对于融合进程和结果也至关重要,包括人力资本的提升,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有效建构等,限于篇幅,本文不对此做进一步的阐释。
四、余论:谨防社会阶层的固化风险
在过去30多年中,中国社会,特别是流入地政府对待流动人口的态度一直处于变动之中,从最初把他们视为“盲流”,到视为劳动力,再到视为有家有口的“人”,中间经历了较为曲折的过程。这两(三)代流动人口在出血流汗创造中国经济奇迹的同时,始终未能摆脱与主流社会相隔离、缺乏有尊严生活和较少向上流动希望的弱势地位。在个体层面,虽然由于先赋要素、融入的努力程度、偶然的机会运气等千差万别,使得每个流动人口在流入地机遇会有所不同,融合的轨迹起点和终点也有先有后,但是,社会融合既需要流动人口自身的努力,也需要流入地居民的包容与接纳,更需要国家层面和地区层面公共政策的制度性安排。在融合这条路上,流动人口拥有与本地市民均等的机会和公平的权利,既是融合的前提条件,更是社会公正中的题中应有之义。
然而,如前所言,实际情况是,人口的地域流动制约虽多已消除,但流动人口面临的很多切实的障碍却未消解,讨薪、维权、子女上学、社会保障、居住隔离等诸多问题都困扰着他们,高质量的组织参与和政治权利等对他们来说更是遥不可及,一些资源丰富之地设置极高的准入门槛,对他们的进入实行管制——高端人才可进,低端人口严控。哪怕是高端人才(如高科技领域的城—城流动人口),也只能以外来人身份在特(超)大城市生活。除少数人外,积分落户遥不可及,户籍及其附着制度的“长坚之铁”依旧将他们排斥于现地社会之外,向上流动机会受阻,社会融合进程步履维艰。
如果说第一代流动人口流动的目的是给后辈创造更美好的未来,并在自己老去后返回家乡的话,那么,很多在城市出生、成长的第二代和第三代流动人口则与城市的联系极为紧密。然而,目前社会上“劳力吸纳、福利拒入”的制度、态度和行为,使得多数第二代和第三代流动人口依旧只能重蹈父辈的流动轨迹,梦想难圆。媒体曾通过一双鞋子来描述农民工的代际轮回。一如时下的新生代一样,20世纪80和90年代,年轻、意气风发、满怀勇气和理想、对未来充满期许的进城农民,与这个城市唯一的联系,就是他脚上的那双在彼时廉价、平常但需用现金购买的“回力牌”球鞋,那也是他们生活于城市的见证,是现代性和城市人的标志。如今,老一代农民工虽然还穿着“回力牌”球鞋,但他们与城市的关系并未发生本质变化。而“农二代”、“农三代”等称呼,也很好地诠释了父辈经历的延续和社会阶层的代际传递。新一代的流动人口虽穿着与城市同龄人类似的球鞋,但他们与现地的关联一如前辈,疏离甚至断裂。几代人有的只是因岁月变迁和时间流逝带来的生活阅历之别和时代之烙印,而难有社会地位的上升。
社会学理论告诉我们,社会分层具有固化性和代际传递性:父母或家庭的社会阶层地位越高,子女获得更高或保持已有社会地位的可能性就越大;社会阶层越低,子女也越难以摆脱既有的社会阶层地位。虽然中国社会的变革激活了竞争机制,个人的能力禀赋可以在社会流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从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子承父业”的代际传承模式,但在权利支配模式未变、群体利益结构稳定的情景下,社会地位的固化与传承依旧凸显。时下,第二代和第三代流动人口虽有融入意愿并付出融入努力,但结果却一如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Sisyphus)一样,怀着把巨石推上山的梦想,但现实总是使其一次次滚落山下。生活在留有祖辈和父辈青春记忆和奋斗足迹的城市,子代和孙辈往往也只留下一个类似的“背影”。乡—城流动人口作为现地社会的新底层代表,各种弱势通过世代传递而传续到子代甚至孙辈身上,“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流动儿童若不能平等地接受教育,将会带来一系列负面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二代、三代乡—城流动人口难以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难以获得职业发展和职位升迁,难以收获像样的收入,难以得到稳定的社会保障,难以培育与本地市民进行真正交往互动的社会资本,没有资格实现组织参与和政治参与,最终无法实现对现地社会的认同。如若出现这种情况,将会导致二代、三代乡—城流动人口既脱嵌于传统的“乡土情结”(失去了传统纽带的支持网络),也被流入地社会的制度安排所抛弃,生活于现地社会的制度围墙之外,“无所皈依”。这不仅会导致他们在个体层面难以实现社会融入,群体层面难以实现社会融合,而且还存在部分流动人口向下流动的可能性。
这种现实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社会公平正义理念背道而驰,而且从长远来看,缺乏改变底层命运的机会可能带来严重的社会隐患。轻者形成负面的亚文化圈,犯下“自我救赎式”的失范行为,而失去改变自己贫困地位的机会所带来的危害可能更大。人们被唤醒或自觉之后,就会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核心要素,一旦触发,就会势不可挡,引发难以掌控和极其严峻的社会后果。
因此,无论是出于对流动人口及其家庭成员福祉的关切,还是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大局出发,政府和社会都必须真正关注流动人口的融合问题。推进该群体的社会融合,就是要突破前述的“三堵墙”,实现制度边界、结构边界、理念边界的跨越与重构。无论哪一堵墙,要拆之、平之、融之、化之实非易事。这也提醒我们,社会融合并非一朝一夕之事,甚至亦非一两代人的努力就可实现,而是一个长期、艰难且复杂的过程。需要有长期性和前瞻性的战略眼光,在理想目标上,有追求天下大同的气魄和决心;在融合过程中,立足现实革故鼎新,通过福利政策的共享和个体的主观努力,扫除融合道路上的诸多“坚铁”,形成人群之间的良性互动。渐进式也好,矫枉过正式也罢,小打小闹、蜻蜓点水式的改良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只有革命性的变革,才能真正动摇“三堵墙”带来的区隔,实现社会边界的跨越。
[1] Park, R.“Human Migration and the Marginal Man”.The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1928(6):881-893.
[2][13] 任远、乔楠:《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过程、测量及影响因素》,载《人口研究》,2010(2)。
[3] 刘传江、程建林:《双重“户籍墙”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载《经济学家》,2009(10)。
[4] 庄士成、王莉:《社会融合困境与城镇化“陷阱”:一个经济社会学的分析视角》,载《经济问题探索》,2014(11)。
[5][8] 杨菊华:《中国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2015(2)。
[6][7][12][14] 杨菊华、王毅杰、刘传江、陈友华、王谦等:《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双重户籍墙”情景下何以可为?》,载《人口与发展》,2014(3)。
[9] Wallerstein, I.TheModernWorldSystem:CapitalistAgricultureandtheOriginsoftheEuropeanWorldEconomyintheSixteenthCentur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4.
[10] 徐祖荣:《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障碍分析》,载《党政干部学刊》,2008(9)。
[11] 悦中山、李树茁:《中国流动人口融合政策评估——基于均等化指数和落户指数的分析》,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6(6)。
[15] 刘丽:《“居住证”能否让人“四海为家”》,载《人民论坛》,2015(21)。
[16] 熊万胜:《新户籍制度改革与我国户籍制度的功能转型》,载《社会科学》,2015(2)。
[17] 彭希哲、赵德余、郭秀云:《户籍制度改革的政治经济学思考》,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
[18] Gordon,Milton.AssimilationinAmericanLife:TheRoleofRace,Religion,andNationalOrigin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
(责任编辑 武京闽)
Double-Dual Property of Hukou System and Social Integration of Internal Migrants in the Context of New-Blueprint Urbanization in China
YANG Ju-hua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Population Studi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
In addition to similar issues that international migrants face, internal migrants in China encounter unique difficulties and complexities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integration due to the “double-dual property of Hukou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structural and attitudinal barriers brought about by Hukou at the place of destination.The multiple and overlapping disadvantages of rural-to-urban migrants render them to be more difficult to be integrated into the host society.Current Hukou reform, particularly the policy of “integral settled” (ji-fen-luo-hu) adopted in metropolis, becomes the new and “politically correct” means of social exclusion, although it seems to provide an opportunity for migrants to be integrated.We propose that overturning the institutional, structural, and attitudinal walls, transforming the boundary and enhancing embedment across various segments of the population is the fundamental and inevitable way to facilitate social integration of migrants.Key words: internal migrants; assimilation; integration; double-dual property of the Hukou system; segregation
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研究”(13JZD02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发展状况动态监测研究”(15AZD053)
杨菊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老年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北京 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