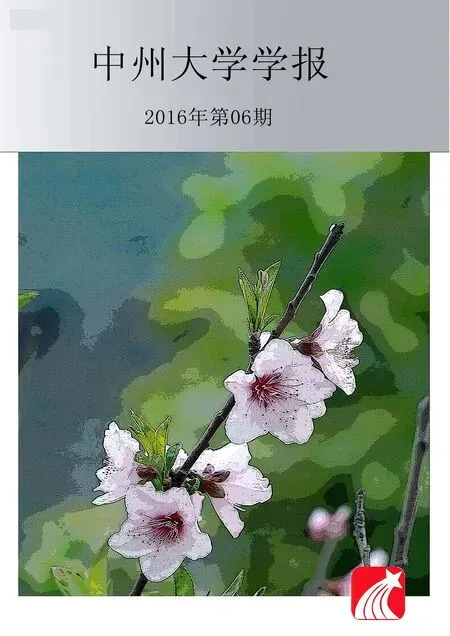《九歌》的“巫”文化研究
林 祁,张雪雁
(厦门理工学院 外国语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0)
《九歌》的“巫”文化研究
林 祁,张雪雁
(厦门理工学院 外国语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0)
巫文化是人类最早的文化形态之一,《楚辞·九歌》乃为我国巫文化的杰出代表作品。 本文将《九歌》置于远古巫文化的视野中重读,从“巫神形象”“巫与祭”“群众狂欢”“乐与舞”四个方面梳理《九歌》与“巫”文化,阐述与辨析其艺术价值以及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巫文化;屈原;《九歌》;艺术价值
一、引言
穿越古老的历史时空,原始而神秘的巫文化在屈原的《九歌》中融化为瑰丽的爱情故事,它将神秘奇特的巫性思维与文学的审美思维整合起来,使古老而淳朴的巫文化以更加绚烂多彩的姿态走进了世人的视野,带给人无限奇妙的想象与美的感受。
艺术的最高境界不是对客观事物的直观描写,也不是对现实世界的联想,而是将事物的内在规律高度抽象,赋予其无限的生命力和丰富的情感世界。在过去的研究中,学者们多从文学角度对《九歌》进行剖析,亦或是从艺术角度探讨其文化背景,笔者则将其置身于南楚“巫”文化的大时代背景,对巫文化的起源、发展进行梳理,分析和探讨屈原《九歌》的创作背景与意义,从“巫神形象”“巫与祭”“群众狂欢”“乐与舞”四个方面阐述《九歌》中的“巫”文化,并对其艺术价值进行辨析与追述,探析先民们纯朴的思维模式和真挚的情感。
二、巫文化溯源
(一)巫文化的起源与发展
巫文化,作为人类最早的文化形态之一,从未消亡,穿越古老的历史时空,至今仍然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以及行为表现。
20世纪3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旧石器时代的山顶洞遗址发现了我国最早的巫术遗址。据史料记载及文化研究,巫文化从萌芽至今至少已有18000年的历史了。
许慎《说文解字》对巫的解释为:“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1]
巫为象形字,甲骨文的“巫”像是巫师作法所用的一种道具,形态酷似横竖相交的两根木棍,有沟通天地之意(见图1)。而小篆则象是女巫两只舞动的衣袖,颇有舞袖翩翩的姿态(见图2),这或许是因为舞蹈与巫祭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此外,以歌舞降神,亦是南楚先民在祭祀典礼中常用的手段。巫祝往往可以通过颂咏、歌唱、舞蹈或其他方式见到鬼神,甚至使鬼神附体,具有不同于常人的与鬼神沟通的特殊能力。

图1 甲骨文“巫”
图2 小篆“巫”
《诗经·小雅·楚茨》说“工祝致告,徂赉孝孙”[2],意为“司仪致词,赐福给主祭的孝子贤孙”;《楚辞·天问》当中亦有“工祝招君,背行先些”[3]的语句,王逸将其注释为“男巫曰祝。”[4]在现代汉语里,“巫”和“祝”二者的意思是相近的,可互相替换,都表示用乐、舞等富有美感的形式,使被祭祀的对象得到极度的宽慰与欢愉,从而使祭祀者的祈求、愿望得到满足。
巫文化的产生应该追溯到远古社会人类对于自然客体以及人类本身的原始探索与认知,是人类为了证明自身与他人或与外部自然所存在着的某种玄妙的对应关系而想象、创造出来的一种媒介。
关于这一点,恩格斯曾有一段极为精辟的阐述:“在远古时代,人们还完全不知道自己身体的构造,而且受梦中景象的影响,于是产生了一种观念:他们的思维和感觉不是他们身体的活动,而是一种独特的、寓于这个身体之中而在人死亡时就离开身体的灵魂的活动。从这时候起,人们不得不思考这种灵魂对外部世界的关系。既然灵魂在死时离开肉体而继续活着,那么就没有任何理由去设想它本身还会死亡,那样就产生了灵魂不死的概念。”[5]
据此,人们认为不死不灭的灵魂在离开肉体后会变成鬼神,并且继续对人类的生命、生产活动产生影响。灵魂或化为神,操控着自然气候、地理变化,左右着人类生命活动的一切环境;或化为人间鬼魅影响着人的思维及肉体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地震、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人的疾病、晕厥等各种痛苦都被认为是在鬼祟的作用下才产生的。
在史前时期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情况下,人们对自然极度依赖,于是对鬼神采取了两种态度:
一是崇拜、敬畏、依赖鬼神,将自然客体神灵化,通过敬拜求告以祈求神助。这便是宗教的雏形,具有消极意味。
二是想要控制和影响鬼神,通过巫师借助某种神秘的超自然力量,来制衡鬼神的作用,从而控制自然客体。此即原始巫术,相对具有积极意义。
然而,由于古代人类对自身、对自然、对鬼神的认识常常处于一种混乱且不稳定的状态,时而敬畏鬼神,时而又想控制鬼神,抑或是两者同时用之,所以巫术与原始宗教的界限十分模糊,难以准确划分。尤其是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宗教与巫术更是相辅相成,相互渗透,有着密的相关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二者可以说是相互促进的。
(二)巫文化的内容与价值
巫文化是人类精神文明的早期印记,充满着神秘色彩且内容极其丰富,可以说是人类童年时期中最为辉煌灿烂的集体记忆之一,不仅反映了先民的思维方式、情感诉求,同时还见证了人类文明漫长的发展历程。
在中国,巫出现的时代早于文明史,《艺文类聚·卷七十五》引《古史考》的记载曰:“庖牺氏作,始有筮。”管维良先生曾在《三峡巫文化初探》一文中将巫文化的具体内容概括为以下五个部分:
一为宗教,包括巫教、巫术、崇拜、祭祀等活动;
二为风俗,包括巫风、巫俗、丧俗、禁忌等;
三为艺术,包括巫歌、巫舞、傩戏等;
四为文学,包括巫书、神话、传说等;
五为综合部分,包括巫医、文字、巫画等。
笔者与管维良先生的观点大致相同,只是在归属划分上,笔者认为第二部分的丧俗、禁忌应与巫俗归为一类,第四部分巫画应该归为艺术类。此外,巫术与宗教互相渗透,巫术是否应该被视为宗教的附属,仍有待商榷。
巫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精神现象,与神灵祭祀、宗教活动的演进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后相当长的时期里,由漫长的原始巫术时代所塑造出来的意识结构仍然发生着作用,影响着人们的生活、生产方式,比如巫文化中的自然崇拜所孕育出的“天人合一”的理念,又比如巫术起源与盐、药文化,还比如由巫术仪式发展而来的歌、舞、戏等形式多样的艺术文化。在中华大地上繁衍生息的巫文化对我国阴阳学说、老庄思想、屈原诗歌、宗教、医学等的产生、发展与演变不断产生着影响,极大地丰富了华夏民族的哲学、科技和艺术。所以看似神秘荒诞的巫文化从某种意义上在不断地推动着华夏民族的成长。
三、巫文化与《九歌》的创作
(一)巫文化对屈原创作的影响
屈原是战国时期楚国贵族,与楚王同宗共祖,曾担任三闾大夫、左徒兼管内政外交大事。
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相对和谐平缓的历史变迁,东夷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传承,随着时间的沉淀与累积,楚国先民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意识和民族传统,使楚民族保留了比较原始的习俗和信仰——“巫”。屈原生长于巫风盛行的楚国,难免受到原始巫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因而我们不难看出其作品融合了许多巫文化元素,充满了神话色彩。而他的思维方式、创作表现形式、诗歌感情色彩等方面也都充斥着一种浓厚的巫风色彩。
在此,笔者将屈原所受的巫文化影响归为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生长环境的熏陶。屈原生于战国末期楚国丹阳,即今天的湖北宜昌市秭归县,属于长江三峡中的巫峡地域,与巫文化的发源地巫山地段十分的接近。
其二,社会环境的影响。战国时期,与中原各国的相对独立以及楚原始氏族形态的保留,使得楚国巫风弥漫,浸渍朝野,而作为楚国贵族的屈原,不可能不受影响。
其三,流放湘西,受沅湘地区的巫文化的感染。
总而言之,屈原与“巫”有着不解之缘,所以他的文学作品在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中也总是有意无意地将巫文化元素吸收、融合在内。
(二)《九歌》的创作背景与意图
关于《九歌》的创作背景与意义,王逸《九歌序》认为:“《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作《九歌》之曲。上陈事神之敬,下见己之冤结,托之以讽谏。故其文意不同,章句杂错,而广异义焉。”[4]
朱熹在《楚辞集注》中表示基本同意王逸之说。不过,王逸说屈原作《九歌》是因为民俗祀歌鄙陋,所以为才作《九歌》之曲,并未说《九歌》是屈原对民间祀歌的改作。而朱熹则认为《九歌》是屈原因沅湘祀歌“词既鄙俚,而其阴阳人鬼之间,又或不能无亵慢荒淫之杂。原既放逐,见而感之,故颇为更定其词,去其泰甚,而又因彼事神之心,以寄吾忠君爱国眷恋不忘之意”[6]。
对于《九歌》的意图,各家所说纷杂,按王逸、朱熹的传统说法,《九歌》的定型是由屈原完成,以诗明志,充满了拳拳爱国之心。近世以来的学人多持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九歌》是国家祀典所用的祀神之歌;另一种则认为《九歌》并非祀歌,而是娱神、或者说娱祀神者之歌。金开诚先生稍微折中,认为《九歌》一面是娱神,一面娱人。
在这里,笔者与钱树棠先生在《九歌析论》的中观点一致,且只把《九歌》当作屈原所记录的巫风仪式中的巫歌来看,就歌论歌,并不挖掘屈原的潜台词,及前代学者分析的给予讽谏及爱国等感情色彩。
四、《九歌》中的巫元素
(一)《九歌》中的巫神形象
根据钱先生的见解,我们将《九歌》中的神定义为巫术结构里的巫神形象。需要提及的一点是:《九歌》的标题并非文题,而是祭祀簿上注明祭祀何神要唱何辞,是用来标明用场的。分析巫神形象对理解《九歌》的巫术背景和艺术构思都有很大的帮助。
东皇太一,楚国民间所信奉的民间天神,他与王公贵族们所奉祀的昊天上帝十分不同。《诗经》中的昊天上帝是以广袤无垠的天空为象征的,他是人间帝王的抽象化,也是政治体制的人格化。[7]他被认为是至善至美的,然而却无人提起他是仁慈和蔼的;他被认为是至公至正的,然而人们却觉得他是恩威莫测的。谁也无法看清他的真面目,谁也无法弄清他的心思。王公大臣们尚且要对他毕恭毕敬、顶礼膜拜,一般老百姓更是诚惶诚恐,远远地跪在贵族们的后面,五体投地祈求恩泽。而《九歌》中的东皇太一是以天边一轮红日为象征的,并且只是偏居一隅的“东皇”,他是楚国老百姓心中最为尊贵的神灵。《东皇太一》篇中写道:“灵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满堂;五音纷兮繁会,君欣欣兮乐康。”在这里,东皇太一的形象被模糊化,而祭祀过程与场景则被具体细化。由于对东皇太一的祭祀本身就是民间的娱神活动,所以歌辞写得一片欢腾。宏大而虚幻的形象与人民欢腾气氛相交合,充分说明了东皇太一与昊天上帝在本质上完全不同,他是和谐吉祥的象征。
云中君不是云神,也不是雨露之神,而是云的化身,住在云端里凭借云气显示休咎的神灵,掌管着人间福泽。在《九歌》中,女巫作为“神妻”使用通灵术,将自己奉献与云中君,为其寓体,之后人们便可向通灵后的女巫卜问求福。从云的自然神,到云神的人格化,最后成为云中君的巫术化,云中君的巫神形象由此体现在世人眼前。
湘君与湘夫人是被认为是一类神,而且是夫妻神。湘君是湘水之神,住在九嶷山上,而湘夫人则是洞庭之神,住在君山上。之所以祭湘夫人时使用湘君之辞,祭湘君时使用湘夫人之辞,是因为所祭祀的主神须由陪祭神出面邀请。
大司命,掌管生死离合之神。在上古巫文化时期,人们认为寿命有着天生定数,因善恶而增减,因而大司命这一巫神形象便体现了当时人们的生死观念和灵魂观念。与时代文化有关,《九歌》里大司命虽然负责导引亡魂,不免沾染死丧之色,却不像有后世所述的阴阳判官那样狰狞面目,左手握着功过簿,右手执着生死笔。相反,他无所爱憎,洒脱自如却又和蔼可亲,毫无凶神气息。还需一提的是,南楚的大司命与威灵显赫的中原地区司命不同,他不是大星官,而是一位洒脱而风趣的民间司命,在当时楚人心目中是活生生的,亲切又有人情味。
少司命,高禖神的化身,掌管着爱情婚姻与生育。在这里人们不免会思考大司命与少司命的关系:司命神即掌管与人生命相关事物的神灵。最早大、少司命是同一个司命,后来由于司命神既管夭寿又管婚恋,人民群众恐其工作忙碌不协调,故将分化为两个,且分工明确。大、少司命巫神的形象便由此开始进行区分——首先年辈不同,其次分工不同。
东君,日神,抑或可以称之为娇日神。这是因为在《九歌》中东君尽显女性之美——日出时“暾将出兮东方,照吾槛兮扶桑”的娇嗔显现出女儿离家的惆怅,日落时“羌声色兮娱人,观者儋兮忘归”的盛景则侧面展现了女性英姿飒爽之美。而在《东君》古老却盛大的祭祀歌舞中,我们不难看出楚先民们对太阳神的无限崇拜与狂热。在《诗·齐风》中说:“东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宋玉的《神女赋》说:“其始来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从这些古老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在那时期人们总是将朝日与美人互相比拟的。笔者认为这可能与当时社会是处在由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转变、交错的时期,所以人的思想观念难免还留有先古的影子。在母系社会,女子是社会的核心,所以日神一职也相应是由女性来担任。例如《山海经·大荒南经》:“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日欲于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8]可见日神应该原为女神。《九歌》中多写东君的女性之美,可谓是保留了远古日神不少的神秘色彩。
河伯,黄河水神。在这一篇中,河伯虽是主祭神,但歌辞咏叹的中心却是河伯所娶的“美人”。关于河伯所迎娶的究竟是何人,有人认为是女水神洛神,也有人认为是活生生的人。笔者与钱树棠先生保持一致,更赞同后者的观点,认为本篇讲述的就是河伯娶妻的故事。《河伯》歌辞中提到美人与河伯畅游湖海时惊羡道:“鱼鳞屋兮龙堂,紫贝阙兮朱宫,灵何为兮水中。”若是宓妃,她与河伯同为水神,怎么会对习以为常的“鱼鳞屋、龙堂、贝阙、珠宫”感到惊奇呢?更不用说问出“何为”二字了。虽然人们以现在的目光去看“河伯娶亲”是极端野蛮荒诞的迷信,是残忍的杀戮,但是我们不能就此而无视甚至歪曲《河伯》创作的原貌。透过现象看本质,不得不说《九歌》生动地展现出了巫风盛行下古人的思维模式。
山鬼,女山神。在这一篇中,山鬼的巫神形象被淡化,更多的是被描绘成“既含睇兮又宜笑,予幕予兮善窈窕”的温婉美丽、婀娜多姿的女子,更侧重其“怨公子兮怅忘归,君思我兮不得闲”的思念恋人的情愫。
《九歌》的后两篇则由礼祀巫神转为祭奠亡灵:《国殇》是为哀悼反秦战争中阵亡将士而作的悼亡辞;《礼魂》是礼敬鬼魂之曲,是一首普通的祭祖歌。
(二)《九歌》中的巫与祭
巫术与祭祀都出于先民们简单、直接而近乎荒诞的想象,产生于荒蛮偏远地区和下层民间社会,也很少受到正统文教的影响,具有野生性和单一性。
英国文化人类学家弗雷泽曾在《金枝》一书中把事物超越时空距离,通过神秘感应而相互产生作用的巫术统称为“交感巫术”。“交感巫术”的工作原理有二:“一为‘相似律’,凡是相似的事物都能互相感应,凡是相似的行为都能产生同样的效果。从相似律出发,巫师认为仅是通过模仿就能实现任何目的的巫术叫做‘顺势巫术’或‘模仿巫术’;二为‘接触律’,物体一但接触便会保持永远的联系,即使实际接触被切断,它们仍可以跨越距离相互作用。通过接触而施加影响的巫术叫做‘接触巫术’。”[9]
古人祭神,无不期望神可以降临于人世。其招神途径大致为:一、赞颂祭祀之敬与祀物之美;二、载歌载舞,搬演神祇的一些故事。前者容易理解,而后者则是原始思维使然。因为远古时期人类相信,通过“模拟”神灵的一些事迹,可以使神灵感知并来享受他们的祭祀。
《九歌》里的巫常常为灵巫,即神灵附体。如《东皇太一》中的灵巫,作为活偶像,伴随着群众集体祭祀活动,用诗歌乐舞,把神的音容笑貌、性格个性表现得栩栩如生。
有时巫师会扮演陪祭神,邀请主祭神出场——如《湘君》《湘夫人》两篇中,祭湘夫人用湘君之辞,祭湘君用湘夫人之辞。古人祭祀,虽祭品丰盛,却仍担心神灵不肯赏光。所以为了避免所请神灵不来,或匆匆离去,甚至一去不返,古人就会邀请一位跟所请主祭神关系最密切的神灵作陪祭神从而使神灵愉悦。人们认为让与神灵亲近的伴侣出面邀请主祭神,总比自己出面要灵验得多。由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祭湘君时,要由女巫扮演成湘夫人来取悦他,而祭湘夫人时,要由男巫扮演成她的丈夫湘君来拉拢她了。
还有时巫师会干脆以神妻的身份,作神的寄寓体,传达神谕。《云中君》中首句写道:“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末句又写道:“思夫君兮太息,极劳心兮忡忡。”这位美丽迷人的女巫在祭典开始的几个时辰前便在以兰蕙汁液制成香汤中浸泡,以使全身散发出沁人心脾的花草香。她穿上纹饰华丽的礼服,腰间佩戴着剔透的佩玉,庄重典雅地迎候云中君住进“寿宫”(云中君降临的神殿)。工祝敲起清脆动听的编钟,演奏起婉转撩人的丝竹琴瑟,跳跃的烛火与玲珑的玉器交相辉映,巫女在祭台的杯盏间翩翩起舞。待云中君离去后,她柔肠百转地叹息思念,期盼着他的再次到来。以女巫充当神妻在古代民间信仰里是人们非常注重的事,因此这女巫作为云中君的神妻,定居在寿宫里接受祷祝传示神谕,她只能侍奉云中君这一位尊神,她的身体专属于云中君。
(三)《九歌》中的群众狂欢
巫神,群众心理活动的外射产物。
在原始社会时期,人们了解自然,大多是通过观察与想象两种途径,而巫神也自然而然的产生了。人类无法驾驭变化万千、神秘莫测的自然,可人类有自己的生活,有希望长寿、婚姻幸福、子孙绵延、福泽庇佑等各种各样的愿望。所以每个人都期望着自己可以有座隐形的大靠山,来帮助自己解决困难、躲避灾难。这时候人民群众就会想象这世界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神灵,掌管人世间不同的事务,可以帮助人类实现一切愿望。那么该如何与天神取得联系呢?那就是巫,可以通灵的人成为了连接人与神的媒介。
《九歌》中的巫神,身上满载着群众的狂热幻想和爱戴之情。
掌管爱情婚姻、生育后代等大事的神其实就是楚国先民们的自我写照——他们认为对于这些事情,神与人是一样重视并为之喜悦的。虽然楚巫文化中的神与古希腊神话中的人神形性不尽相同,但是楚国民间群众所创造出来的巫神却是人类可以亲近的。人们了解巫神的脾性,甚至可以设法取悦神灵,与神交流,倾诉心愿,祈求恩泽。而另一方面,神似乎也愿与百姓为亲为友,与民同乐,体恤他们的疾苦,有求必应。
此外,《九歌》中的巫神与后世群众所捧出来的神灵非常不同,后世把神偶像化了,由个人用香烛纸箔跟神直接祈求祷告,而《九歌》中的巫神,并没有什么木石偶像,而是以巫师作为活偶像,由他用诗歌乐舞将神灵的音容笑貌、个性行为进行生动的描述,并伴随着群众虔诚、狂热的集体活动体现出来。从迎东皇太一时的“五音纷兮繁会,君欣欣兮乐康”,到歌颂东君时的“羌声色兮娱人,观者儋兮忘归”,再到祭祀山鬼时的“留灵修兮儋忘归,岁既晏兮孰华予”,我们都不难看出“人是神的影子,神是人的写照,人神共愉”这样古朴可爱的自然崇拜。
(四)《九歌》中的乐与舞
“巫,以舞降神者也”。古代巫觋在祭祀活动中所表演的舞蹈被称为巫舞。巫常在舞蹈中扮演不同角色,形象鲜明,具有视觉冲击和无限美感,既可以娱乐神,又可以娱乐众人,所以舞蹈常常被当作祭祀活动中的重要手段。
前文曾提及:从起源上来分析,《九歌》的性质是巫歌。但是随着时间的变迁,以及后世多种文化元素的融入,再经过屈原的加工润色,《九歌》已不再是原始、纯粹的巫歌了。有学者认为《九歌》是祭歌,而笔者则认为《九歌》并不同于一般的祭歌。祭祀的巫歌与巫舞表演,是伴随着祭祀仪式进行的,并随仪式的变化而变化,只有组合起来才能成为从内容到形式上完整的祭歌。祭歌总是从各个方面铺叙描绘神的无限法力,并多用赋体反复致颂赞之辞,如《汉书·郊祀志》中的《郊祀歌》,而九歌并非此类。
屈原所创作《九歌》是一组杂辑起来的神戏唱辞,隐分场次,只有曲文,没有科白。现在我们只能通过《九歌》的歌辞上下文意思来设想歌舞场景。
在《九歌》中,巫觋通常容貌姣好,常常扮演神的形象,身着华美礼服,佩带精美玉饰,香气迷人,手持长剑,翩然起舞,深得神灵的喜爱。其典型代表便是《东皇太一》中所描绘的祭天神的灵巫——“灵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满堂”。与之描写手法相近的还有《云中君》的“灵连蜷兮既留,烂昭昭兮未央”。“偃蹇”与“连蜷”都是典型的舞蹈动作,王逸注曰:“偃蹇,舞貌。”又注:“偃蹇,委屈貌。”洪兴祖补注曰:“灵偃蹇兮姣服,言神降而托于巫也。”[10]又注:“连蜷,巫迎神引导貌。”总的来讲,“偃蹇”“连蜷”有“屈伸律动姿态”的意味,充满了视觉效果,充分展现了舞姿的舒张自如与体态的流畅柔美。屈原的《九歌》中所描写的礼祀场景,充满着浓郁的民间乡土气息,当时祭祀活动歌舞升平、美轮美奂且充满浪漫气息的的盛大场景也毫无保留地展示在世人面前。
五、结语
刘勰曾在《文心雕龙·知音》中提到:“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11]审美是通过形象和情感来实现的,在巫风盛行的时代背景下,《九歌》侧重于描绘神的形象和心态,藉以抒发人间的温情。偶尔一两句对神的神功盛德、法力道行的歌颂也使得文章情节更加丰富、灵动。
正如学者孙大知所言:“屈原的时代是巫文化的时代,屈原的作品反映了巫文化的特点,而《九歌》则是典型的祭祀诗歌,可以称为巫文化的代表作。”[12]艺术的《九歌》是置身于大时代的巫文化背景之下而创作的佳作,也为后世文学、艺术提供了不竭的创作源泉,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巫文化熏陶下的奇妙幻想幻化为屈原《九歌》中神与神的依偎爱恋,人与神的和乐共融。浪漫华丽的辞藻背后满载着对自然、对生命、对生活的热爱与希冀,这便是巫文化中的《九歌》与《九歌》中的巫文化流传至今最大的艺术价值。
[1]许慎.说文解字[Z].北京:中华书局,1963.
[2]朱熹.诗经集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3]王夫之.楚辞通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4]王逸.楚辞章句[M].北京:中华书局,2007.
[5]〔德〕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M].张仲实,译.北京:北平解放出版社,1949.
[6]朱熹.楚辞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7]钱树棠.九歌析论[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3.
[8]袁珂.山海经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
[9]〔英〕詹姆斯·乔治·弗雷泽.金枝[M].赵阳,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0.
[10]洪兴祖.楚辞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1]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2013.
[12]孙大知.《九歌》是巫文化的代表作[J].玉溪师专学报,1995.
[13]郭沫若.屈原研究[M].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3.
[14]胡新声.中国古代巫术[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15]宋兆麟.巫与祭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16]〔瑞士〕弗里茨·格拉夫.古代世界的巫术[M].王伟,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17]王志.屈原与巫文化关系研究[D].吉林:吉林大学,2006.
[18]张喻.论楚辞《九歌》中的自然崇拜[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4.
[19]张琴.中国古代的巫及巫术仪式研究[D].重庆:重庆大学,2012.
[20]罗义群.《少司命》的审美虚像与创造[J].黔东南民族师专学报,1996(3).
[21]潘啸龙,陈玉洁.《九歌》性质辨析[J].长江学术,2006(4):64-70.
[22]侯虹斌.《九歌》的舞蹈动作及其与原始祭祀的关系[J].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2000(3).
[23]黄丹.浅谈《九歌》中的南楚巫祭文化[J].贵州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7).
[24]陆代武.论屈原辞赋及其巫文化[J].广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2).
(责任编辑 许峻)
Study on the Witchery Culture in Jiuge
LIN Qi,ZHANG Xue-y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Xiame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Xiamen Fujian 361000, China)
Witchery culture is one of humans’ earliest cultural forms.Jiugeof Chu-ci poems is a representative works of the witchery culture in China.Jiugeis rerea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ancient witchery culture and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witchery culture from four aspects: the image of sorcerer, witchcraft and worship ceremony, the mass carnival, song and dance,then recounts and analyzes the artistic value ofJiugeas well as it’s infuence on the later literature and art.
witchery culture; Qu Yuan;Jiuge; artistic value
2016-10-12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日本新华侨华人文学三十年”(13BZW135)及 “华侨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专项经费资助项目”(HQHRYB2015-06)
林祁(1957—),女,福建厦门人,文学博士,厦门理工学院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
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6.06.002
I207.22
A
1008-3715(2016)06-000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