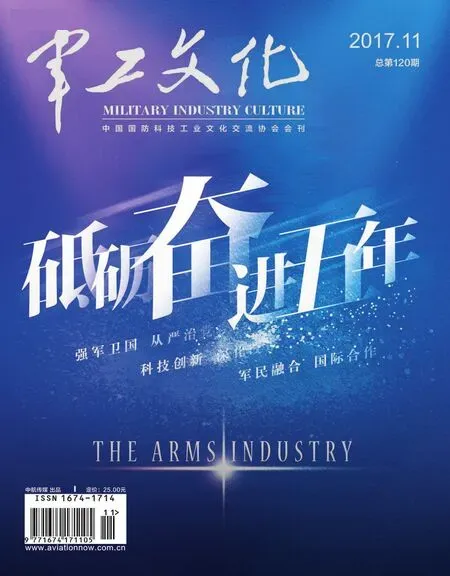父亲的二胡
文/楚秀月
在六十年代初期,这把二胡,随着父亲,从河南某个偏僻的小山村,来到荒凉辽阔的漠北安家落户。
琴筒上暗红色的漆,斑驳得像月夜树林里照在地上的月光;琴杆也旧几乎分不出颜色,倒是露出了红木的本色,弓子是原配的,弦却是新的,在弓子的某一头随意地挽了一个结,结里裹着生活的粗糙;一滩儿松香不规则地糊在它该待的地方,被弦子拉过的地方磨下一道沟,些许的细小粉末泛着白色,凹糟里落着永远都无法清理的陈旧的灰。
这把二胡,在六十年代初期,随着坚决响应国家支边政策的父亲,从河南某个偏僻的小山村,来到荒凉辽阔的漠北安家落户。
打我记事起,父亲闲下了,就喜欢在既是卧室又是客厅的屋里,一边拉着他的二胡,一边扯着嗓子唱家乡的豫剧。
那个年代,文化娱乐活动少之又少,父亲一唱起来,我的玩伴们,也就寻着声音凑热闹来了,男娃娃女娃娃,高低胖瘦,站的站,坐的坐,围了半屋子。
毫无疑问,二胡的音质非常差,发出的那些声音,时而像个淘气的孩子在走路,不是东拐一下,就是西拐一下;时而又像深夜里夫妻在吵架,不是妇高一声,就是夫低一声,但一点都不影响我们这群孩子如醉如痴地陶醉其中。
父亲个子不高,声音却洪亮,一开腔,虽说不上震石穿云,却也字正腔圆抑扬顿挫,面对着围拢在他身边的这十几个半大不小的孩子,父亲没有丝毫马虎。
“嗯!啊啊!”父亲总是在清嗓子的时候,先用眼晴把我们全部扫视一遍,之后端起写字台上的大茶缸,美美地喝上一大口茶,再把左腿上的二胡,调在靠近自己腹部的位置,让蒙皮的一端,略微向右前方偏斜,而这时候的琴杆,也略向左前方倾斜着;挺直腰板后,父亲又看我们一眼,微微低下头,把目光放在二胡的弦子上,抬起右臂,脸也侧到右边去,把右手往外轻轻划出去,依依呀呀的二胡声,便响起来了。
因着唱段的不同,父亲的起腔也是不同的。每遇开心的时候,父亲喜欢高起腔,让自己的声音,随着二胡的旋律猛地发出来,一下就抢了二胡的风头,甚至于让早已做好倾听准备的我们,浑身一激灵。我们在惊吓中,相互对视一眼,继而明白,我的父亲,是在故意逗我们,便有参差的笑声,盖住了其它。父亲不开心的时候,也是有的。这时的父亲,就比平日严肃了许多,脸沉下来,眼神里满是迷茫的光,会压低自己的嗓音,让发音的部位靠后些,沉沉的声音渐渐地婉转出来,又迂回几次,声音才会高起来,渐渐大过二胡的音律。
父亲唱得最多的就是《花木兰》片段。那时的父亲,在我们这帮孩子的眼里,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名角。
父亲唱完一曲,也会给围在他身旁的小听众们讲常香玉的故事。父亲讲了一遍又一遍:“捐了一架飞机,捐了一架飞机啊!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父亲大张着嘴,眼睛弯成了一条缝,把这句话反反复复说了很多遍,仿佛说着自己的亲人一般,仿佛比自己捐了一架飞机还要高兴。
坐在一边纳鞋底的母亲,这时候总会抬起手,把手里的锥子,顺着自己浓密的头发划一下,然后抬起头,望一眼兴高采烈的父亲,黑黑的眸子里,有了昔日里不曾有过的光彩。
父亲的这把二胡,给我的童年生活带来了无比的快乐;父亲的这把二胡,让小时候的我,对美好的事物有了深深的依恋与追求;父亲的这把二胡,更是打开了我内心深处对外面世界的了解与渴望。
经历了几次搬家,那把颇有文艺范儿的二胡,早已不知去向,父亲也在2004年初夏的时候,埋葬在了自己母亲的坟边。
我不知在另一个世界,父亲会不会想念自己的那把二胡,而我,只要想起父亲的时候,就会想起父亲的二胡,就会想起父亲挺直身板为我们拉二胡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