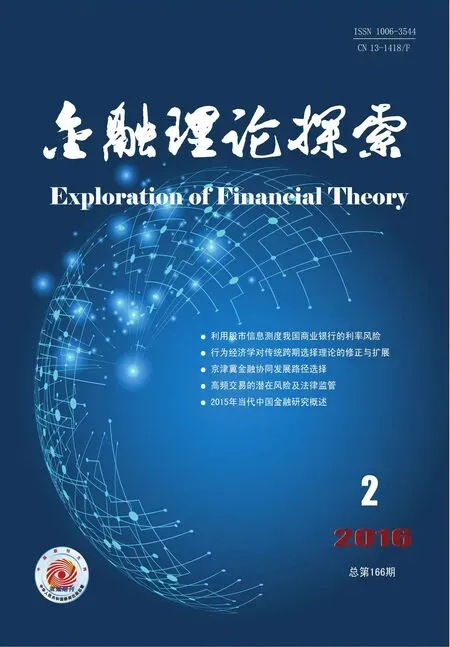2015年当代中国金融研究概述
赵学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836)
2015年当代中国金融研究概述
赵学军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836)
摘要:本文主要选取2015年以实证研究为主的中国金融前沿问题较有代表性的部分文章,从金融改革与发展的逻辑、货币政策实施的规律及效果、通货膨胀的成因及影响、农村金融体制的变迁及改革、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等方面,介绍了当代中国金融研究的热点问题、主要观点及相关的研究进展。
关键词:当代;中国;金融
一、金融改革与发展研究
中国的金融改革一直是学者与政府官员谈论的热点话题。展望未来金融改革的方向,需要理清金融改革的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撰文论述中国金融改革发展的逻辑。他认为,20世纪80年代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早期,金融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引进市场经济金融体系的基本结构。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和中期,金融改革发展的主要特征是建立符合市场经济的金融市场和组织结构的基本框架。在亚洲金融风暴期间,金融改革和发展的主要内容是健康化、规范化和专业化。但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中国金融改革和发展的主要工作转为配合国家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冲击,特别是配合国家推出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全球金融危机后期,金融改革是着力推动金融业市场化、国际化、多元化。中国金融改革有很强的逻辑性,需要通过健康化、规范化和专业化等一系列深刻有力的调整,才能逐步迈向市场化、国际化、多元化的阶段。[1]
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扬副院长撰文分析了中国在冲破经济发展资金瓶颈方面的经验。他指出,改革的不断深入,从制度层面推动了储蓄率和投资率的上升。首先,市场化改革的一个直接结果,是投资主体从以国有经济单位为主向多元化主体转变。其次,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导致就业人口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享受的各种福利待遇逐步减少,必然要求居民预先增加储蓄,提高自身支付能力。供给主体的转变和市场机制对计划机制的逐步取代,极大地刺激了全社会的投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向居民倾斜、居民的货币化收入水平快速上升、居民预防性储蓄比重不断提高、居民负债率较低等,均对中国储蓄率的长期上升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1978~1994年短短的17年中,中国现代金融机构体系和股票市场、货币市场、债券市场的建立,为提高中国的储蓄率开辟了宽广的渠道。城市人口和就业人口的增加,同样推动了储蓄率和投资率的上升。[2]张杰、杨连星分析了当前中国压制性金融体制的特征及其困境。文章指出,中国金融体系形成三个层次:一是以国有大银行为主的垄断性质金融中介以及以服务国有经济为主的金融机构体系;二是以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为主的影子银行体系;三是以民间借贷为主的非正式金融体系。造成压制性金融体制的主要原因是:政府过度干预信贷市场以及政府对金融资源的控制权力超越市场的合理边界;现阶段政府干预和控制下的金融体系,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不能满足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对金融体系的内在需求,并且在相当程度上呈现出金融体系“低端路径锁定”和“利益集团俘获”特征;现阶段金融体系自身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成为加剧中国金融压制体系形成的助推器。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相割裂,风险收益获得者与最终承担者相割裂,金融体系发展与经济运行需求相脱离。金融压制体系导致诸多严重后果:对实体经济造成相当程度的“掠夺效应”,阻碍了制造业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抑制了制造业部门转型升级的内生动力;导致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持续下降以及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能力的弱化;加剧了经济运行风险和经济领域泡沫的膨胀。[3]
傅勇、李良松分析了中国金融发展中中央与地方分权的逻辑。他们认为,金融集权和分权与经济管理体制变化密切相关。建国初期,为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重点工程建设,政府建立了高度集中统一的金融体制来筹集资金。这种金融体制对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确立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起到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后,为充分调动地方积极性,中央不得不向地方放权,地方政府具有推动当地经济快速增长的强大动力,地方政府也具有了支配金融资源的强烈愿望。这也是地方政府要求大力发展地方性金融机构的根本原因。但是,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目标函数并不一致,若中央将金融权力过度让与地方将容易造成金融三乱和经济过热。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完善,市场与政府作用边界将会更加清晰,政府不会直接参与金融资源分配,尤其是地方政府官员考核体系进一步优化后,地方政府干预金融资源分配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可能会下降。中央和地方的金融分权将会逐渐完善。[4]
刘鹏回顾了中国商业银行变革转型的历程,认为商业银行改革开放与整个经济市场化的进程息息相关。商业银行业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现代商业银行体系初步建立(1979~1993年)、商业化改革与发展(1994~2002年)、市场化改革与发展(2003年至今)。在第一阶段,国家加强了对金融业(主要是国有银行)的控制,促使其承担政策性职责,行使财政职能,国家汲取金融能力的上升替代了国家汲取财政能力的下降。这体现为:在动员资源过程中,金融业替代税收功能;在资源配置过程中,金融业替代财政功能。但内化了的成本体现为巨额不良资产。在第二个阶段,专业银行转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国有银行补充资本金和剥离不良资产。在第三个阶段,商业银行对出口和投资需求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支持,也实现了自身的规模扩张和快速发展。但2011年以来,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出现背离,金融空转和脱离实体经济的问题开始突出,系统性风险开始积聚。[5]
二、货币政策研究
在货币政策研究方面,学者们讨论的多是货币政策的实施规律、实施效果、货币政策的影响因素、货币流通速度变化等问题。
黄宪、王旭东研究了我国央行货币政策实施力度和节奏的规律。他们分析了中国人民银行30年来所运用的数量型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并对这两类货币政策调控效果演进趋势和时变特征进行实证检验。认为,央行对于数量型工具的使用较为慎重,但经济面临较大冲击时往往会高频度、高强度地加以使用;央行对价格型工具运用的节奏要“均匀”得多。当经济出现“滞涨”时,央行多采用扩张性但是较“温和”的价格型操作方式。从时变性和演进性角度来看,数量型货币政策对产出的调控效应有所提高,对价格水平的调控效应总体保持稳定;价格型货币政策在复苏期对于产出的作用效力更高,在下行期的作用时滞更短,对价格水平实施调控的效果呈现出时滞期缩短且稳定性提高的趋势。[6]
因区域经济水平的差异,货币政策在实施中会导致差异化结果。牛晓健等人将我国31个省份分为东中西三个地区,通过建立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检验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结论是: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差异程度随时间而变化。在西部大开发前,三个地区对于货币政策的响应强度顺序按经济发达程度依次减小,而在西部大开发后,西部地区对货币政策的敏感度有所提高,特别是价格水平的波动更强。[7]
范建军从“升降息”制度讨论我国货币政策实施中存在的问题。他认为,由于货币领域市场化改革的时间不长,上海银行间市场同业拆放利率作为市场基准利率的作用还未发挥出来,其走势一直处于无序波动状态。我国在存、贷款利率管制的领域主要有两个:一是房地产按揭贷款利率;二是商业银行的存款利率。央行针对存贷款基准利率所进行的“升降息”操作,主要影响的是两大行业——房地产业和银行业。由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此类“降息”活动不会导致整个银行体系信贷能力的提升和实体经济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因而无助于从根本上扭转实体经济持续低迷的局面。当前货币政策之所以呈现“无序”状态,主要出自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目前央行仍以广义货币M2增速作为货币政策调控的中介目标;二是央行仍以CPI指数作为评判通胀形势的标准。[8]
周远、纪春明研究了我国货币政策的价格效应与产出效应,认为2008年以来,货币供给变动对物价水平波动有一定的影响,存在价格效应。物价变动与货币供给变动存在长期且较显著的正相关性,而且物价变动也会引发货币供给的反向调整,以平抑物价水平的过度波动。货币供给变动对工业企业增加值增速影响较明显,产出变化与货币供给变动存在较长期的正相关性,货币呈现出一定的非中性特征。[9]
谢太峰、樊若琛采用2002年至2014年月度数据,检验了广义货币供应量与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的关系。认为,货币供应量与银行同业拆借利率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不是基于市场对货币供求的反应;银行大量放贷是拉动货币供应量增长的内在机制。这表明,我国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不是真正基于市场对货币供求的反应,而是一种“被动”调节,即由大量对外贸易顺差和资本流入所形成的。[10]
罗煜估算了中国真实货币流通速度。他通过投入产出表和资金流量表估算实体经济交易总流量,通过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支付结算数据估算各层次货币流通总量,估算2000~2012年不同口径的货币流通速度。在考虑了金融交易因素后,上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的货币流通速度没有如大多数研究所认为的那样持续大幅下降,而是呈现出一种先降后升的趋势,特别是2006年之后货币流通速度总体呈平稳上升趋势。短期内,实体经济对金融市场的货币流通速度有一定预测能力,但长期内实体经济和货币流通速度并无稳定的关联性。在实体经济内部,流通货币量、实际交易量、价格水平和货币流通速度之间仍旧可以保持稳定的关系。[11]
王延军、温娇秀分析了产业结构对货币流通速度变化的影响。认为,产业结构变动是货币流通速度变慢的重要原因,产业结构变动的趋势预示着未来的货币流通速度将会进一步放缓。金融主管部门在制定相应的货币政策时,应该关注货币流通速度,关注产业结构和货币流通速度之间的关系。[12]
李炳、袁威实证分析了1996年1月至2013 年5月期间货币信贷结构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认为,货币信贷结构均在特定时点开始对产出和通货膨胀率产生机理性影响;货币结构与信贷期限结构对实际产出分别具有较弱的正向和负向机理性影响,对通货膨胀率均具有一定程度的正向机理性影响,并且货币信贷结构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程度明显大于货币信贷总量。他们发现货币结构与信贷期限结构对“中国货币迷失之谜”均具有很强的解释力。[13]
三、通货膨胀研究
2015年学者们讨论中国通货膨胀的文章明显少于去年与前年。学者们在实证研究中国通货膨胀时,主要集中在分析造成通货膨胀的原因、如何测定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的影响等方面。
王飞分析我国货币供给是否是通货膨胀的格兰杰原因。他通过对2009年第1季度至2015年通胀率预测误差的分析发现,央行货币供给行为在引发和抑制通胀率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连续的、大幅度的货币超发会造成未来一段时期内较严重的通货膨胀,而连续的稳健、偏紧的货币供给能有效地降低通货膨胀压力。因此,对于我国货币供给和通胀率之间的关系,传统的货币主义的观点仍然是有效的。[14]
李鹏、杜亚斌从财政支出视角,对我国通货膨胀的财政属性进行研究。提出,在控制货币供给量和经济周期影响后,我国财政支出与CPI之间总体上具有正向变动关系;财政支出对CPI的影响在短期内较不稳定,但中长期非常显著,具有时变特征,物价上涨具有浓重的“财政色彩”。1998年推出的积极财政政策对CPI的短期影响较大,而2008年推出的积极财政政策对CPI的中长期影响更明显;同时,投资性和消费性财政支出对CPI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因此,我国通货膨胀不仅仅是一种货币现象,更是一种财政现象。[15]
荣幸子、蔡宏宇选取1994~2013年的数据,实证分析财政政策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发现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的经济一直保持着较快的增长速度,但在绝大多数的年份里财政收支处于赤字状态,这对债务的发行以及维持政府财政预算平衡造成了一定的压力。赤字以及债务率不断扩大,会对通货膨胀造成上行的潜力。[16]
李俊成、蔡春春分析了社会融资规模与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他们利用2002~2013年社会融资规模数据,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法和VAR模型,对社会融资结构与通货膨胀的关系进行了稳健性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股票、债券等社会融资方式对通货膨胀有正向影响,且其影响作用无太大差异,通货膨胀受外币贷款和股票融资冲击和贡献最大,说明我国通货膨胀外生性明显,并受到金融市场的影响。[17]
杨光辉、汤贵明采用中国2001年1月至2013 年5月八个分类商品CPI同比增长率的月度数据,构建中国核心通货膨胀测算模型,并估计核心通货膨胀率。测算数据表明,中国的核心通货膨胀与CPI呈现出基本一致的波谷、波峰和波动频率,且中国的核心通货膨胀对CPI起到了“削峰平谷”的作用,反映了通货膨胀具有潜在和长期的趋势。中国月度核心通货膨胀的波动幅度小于CPI波动幅度。月度核心通货膨胀和月度CPI呈现出不同的趋势特点。核心通货膨胀惯性的大小客观地决定了核心通货膨胀对货币政策变化的反应速度。我国货币政策应该重点关注核心通货膨胀。[18]
罗云、代晓静对1978~2012年的核心通货膨胀率进行估算,认为CPI标准差为6.015,而1985~2012年间CPI标准差为6.709,核心通货膨胀率的标准差为4.903。核心通货膨胀率变动轨迹与CPI基本一致。绝大多数年份的核心通货膨胀率都低于CPI,表明核心通货膨胀率能更好地反映价格水平的长期趋势。[19]
汤丹对中国2001年1月至2014年3月核心通货膨胀率进行估算,结果表明估计的核心通货膨胀率具有较小的波动性,能够更好地反映该样本时期通货膨胀率的长期变化趋势,同CPI相比具有更好的政策参考价值。[20]
刘旭运用1978~2013年的各年度统计数据,估算我国通货膨胀的门限值,认为我国的通货膨胀门限值为5%。当通货膨胀率大于5%时,通货膨胀会给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我国通货膨胀的门限值明显高于发达国家的1%~3%,宏观调控能力还有待提升,货币政策还不够成熟。[21]
刘子寅、范科才从非线性视角出发,选取1996 年1月至2009年4月数据,分析汇率传递与通货膨胀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发现汇率变动对通胀具有显著的“门限效应”,门限值为-0.1%(月度通胀率)。不同通胀环境下,汇率变动对通胀产生了非对称性影响,即通胀变化超过门限值时的汇率传递效应大于通胀变化低于门限值时的情形。货币冲击与国内需求冲击对CPI的影响也受到通胀环境的影响,并且两类冲击给CPI带来的影响程度明显大于汇率冲击带来的影响。[22]
实现并且维持低通货膨胀还是有成本的,因为低通货膨胀也可能造成短期产出减少、失业率上升以及相关社会问题。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之间的权衡,成为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的核心要素。赖溟溟、姜岩采用总供给曲线法的简化形式——菲利普斯曲线法,利用年度和季度数据计算我国年度和季度的牺牲率。牺牲率主要是指趋势通货膨胀率变化造成实际产出损失的百分比,衡量了一国反通货膨胀的产出成本。他们估计年度菲利普斯曲线的区间为1979~2010年,估计季度菲利普斯曲线的区间为1994年1季度至2012 年4季度。估算结果是,我国1978~2012年的牺牲率为0.69,1994~2012年的牺牲率为1.96,略低于19个OECD国家1985~1998年的平均水平,年度牺牲率大于季度牺牲率。[23]
四、农村金融研究
在农村金融实证性研究方面,一些学者分析了农村金融体制的变迁、农村信用社的发展与改革等问题。
赖闽苏、刘青等人论述了农村金融体制变迁及其绩效。认为,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演变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初始、发展和逐步成熟三个阶段,整个过程表现出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推进,农村金融化程度不断提高,表现为金融资产总量增加、结构改善以及金融相关率上升等。总体上看我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绩效是低下的。一方面,农村金融体系未能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资金需求,另一方面农村金融机构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1978年以来,随着农村金融体系改革不断深化,农村金融化程度不断提高,但其功能逐渐异化为攫取农村资金,严重损害了农村经济的自我发展能力。[24]
易棉阳、贺丽讨论了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的逻辑起点问题。认为,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合作化运动实际上是中国版的苏联集体化运动,因此,在理论起点上既不是国际公认的合作原则,也不完全是马恩列的合作理论,而主要是斯大林的集体化理论。从新中国建立到1953年信用合作高潮前,较好地坚持了自愿原则,农业合作运动全面展开以后,自愿原则遭到了破坏。在合作运动高潮中普遍设立的农村信用合作社,不是农民自愿组合而成,而是政府强制捏合,实际控制者要么是政府基层官员,要么是受政府支配的内部人,广大社员既不具有知情权和参与权,也不具有决策权,背离了民主管理原则。此外,受苏联集体化运动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农村信用合作运动过程中,为了达到对农村旧势力专政的目的,农村信用合作社也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25]
余霞民对农村金融改革中增量改革和存量改革作了比较。2003年新一轮农村金融改革启动后,一种是以农村信用社和农业银行改革为代表的存量改革,即对农村金融体系中的现有机构进行全面改革,提高其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支农水平;另一种是2006年以后以设立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以及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组织为代表的增量改革,目的在于通过新设机构丰富农村金融体系,提高金融服务“三农”水平。认为,在增量改革方面,虽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对整体的农村金融改革贡献很小。存量改革则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改革绩效主要体现在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能力方面,但其他指标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二是存量改革的边际绩效呈现递减的趋势,农村金融存量改革的空间越来越小。[26]
黄惠春、李静以江苏省33个县域的农村金融市场以及33家农村信用社2000~2011年的面板数据为基础,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利率市场化进程中农村金融机构市场势力对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认为,利率市场化会提高农村金融市场的贷款价格,其上升幅度与农村信用社市场势力有关;利率市场化对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的影响与农村金融市场竞争程度、农村信用社市场势力密切相关;提高金融机构风险控制水平和营运能力有利于降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27]
五、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探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从以前的学术文献看,研究不同地区的学者得出的结论相左。2015年这方面的研究仍在拓展,一是部分学者继续研究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二是部分学者运用地方的统计资料,分析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特别是以前研究较为薄弱的新疆、西藏、宁夏、内蒙古等民族自治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张羽、赵鑫使用省级面板数据,探究1999~2012年间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联机制,并据此统计了样本期间内部分欠发达省区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依存关系,认为农村经济增长与农村金融发展水平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差异。东部地区农村经济发展状况略强于中部地区,二者均显著优于西部地区,说明我国东强西弱的格局依旧没有改变。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间存在两种相反的关联区值,当农村金融发展水平低于门槛值时,农村金融相关率的上升会抑制农村经济增长;而当农村金融发展水平超越门槛值后,农村金融相关率的上升能够拉动农村经济增长。[28]
杨青、刘维忠利用1996~2012年新疆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统计数据,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定量分析新疆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发现,新疆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特别是对农林牧渔总产值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具有很大影响。其中,农业贷款规模的影响尤为突出,农村金融机构贷款规模的影响次之,农村金融机构存款规模的影响较小,未有效形成对农业的直接支持;农业保险规模的影响也较小,对农业的支持力度较弱;乡镇企业贷款规模的影响最小,乡镇企业贷款规模对农村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小。[29]
程呈、祝国平分析了吉林省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他们选取1986~2011年吉林省的相关数据,通过建立VAR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吉林省农村经济增长与农村金融发展之间存在内生关系,农村经济增长对农村金融规模单方面产生促进作用,农村金融发展各个变量指标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30]邱立军、徐伟川也利用吉林省1978~201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吉林省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虽然二者之间存在一种长期的均衡关系,但是农村金融发展制约经济发展。[31]
唐雨虹、齐天翔运用1978~2013年相关金融经济统计数据,对西藏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论表明,西藏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始终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而西藏经济增长反作用于金融发展却具有滞后效应。格兰杰因果检验则表明西藏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在较长期限内互为因果的假设成立,但短期假设并不成立。[32]
郭研探讨了内蒙古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文章研究的时段为1985~2013年,结论是:短期内经济增速的变化受到金融发展水平变化的正向影响,但长期看,经济增速的变化仍然主要依赖于经济自身的增长,金融发展水平的影响相对很小,即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较小;短期内金融发展水平的变化受到经济增速变化的负向影响,即经济发展速度快于金融发展速度,使两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表现为金融发展水平相对于经济增速变化出现下降,但从长期看,金融发展水平不仅受自身变动的影响,经济增速的加快对金融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33]
王黎欣利用宁夏1999~2013年的数据,分析了宁夏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宁夏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和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都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34]
六、其他方面的实证研究
实证研究金融市场发展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是饶明与何德旭、唐清泉与巫岑、安世友的文章。
饶明、何德旭分析了中国股票市场改革与创新发展的逻辑。文章提出,中国股票市场从无到有的发展,基本上是沿着政府和市场共同推动的渐进方式演进。政府既是股票市场的培育者,又是股票市场的监管者,这使得我国股票市场运行中具有显著的政策特征。股票市场改革与创新发展的过程,也体现着体制因素与市场因素的互动和博弈,即市场化改革往往要出台政策放松相应的体制管制,市场自主演进中出现问题之后再出台政策措施予以规范。我国股票市场远非成熟市场,因此,其改革与创新发展还具有长期性,体制与市场的互动也具有长期性,其趋势是体制因素淡化,市场因素强化。[35]
唐清泉、巫岑分析了银行业结构与企业创新活动的融资约束问题。他们以2002~2009年沪深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为样本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是:银行业竞争性的市场结构有助于缓解企业研发投资的融资约束;相比固定资产投资,银行业竞争性市场结构对于缓解企业研发融资约束的作用更加显著;银行业竞争性市场结构对于缓解企业研发融资约束的作用在民营、高科技、小型企业中表现得更加显著。这些研究结论证实了银行竞争使得企业研发投资对内部资金的依赖度减弱,而对贷款的依赖度增强。[36]
安世友探讨了中国银行业市场结构演变的金融稳定效应问题。他用熵值来量化银行业市场结构的集中程度,选取我国16家有代表性的银行,计算银行业市场结构2001~2012年的熵值走势。结果表明,我国银行业市场结构的集中程度与风险之间的关系是负相关的,较高的银行业市场集中度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我国银行业体系的稳定程度。样本数据的时间区间内,正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时点,但事实证明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银行业的风险传染程度十分有限。集中度高的银行业市场具有较高的风险免疫能力。[37]
研究人民币汇率、外汇方面,主要有许家云与佟家栋、罗素梅与张逸佳的文章。
许家云、佟家栋研究了人民币汇率与企业生产率变动的关系。他们基于2000~2007年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和高度细化的海关数据,考察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结论是: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对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的净效应为正,其通过企业资本劳动要素配置效应、企业选择效应、规模经济效应以及人力资本提升效应,对制造业企业的生产率提升产生了积极影响;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因企业出口与否、贸易方式、技术水平和所有制的不同而具有显著的异质性;作为人民币汇率影响企业生产率的制约因素,企业融资能力越强,人民币汇率升值对企业生产率的积极影响越大。[38]
罗素梅、张逸佳分析了中国高额外汇储备的决定机制及可持续性问题。认为,决定我国高额外汇储备的主要因素有出口总额、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汇率和人民币利率,而可持续性的决定机制是出口导向机制、长期利益分享机制和短期套利机制,这三种机制的存在决定了高额外汇储备可持续性的短期波动和长期趋势。出口是影响外汇储备可持续性直接的、短期的因素,外商直接投资和人民币汇率是外汇储备长期的决定因素,而人民币利率既是短期因素又是长期因素。随着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及金融开放的进一步加快,外汇储备规模将会发生明显的变化。[39]
此外,赵学军研究了经济体制转型与国有企业商业信用融资变迁问题,提出,随着当代中国经济体制的两次转型,国有企业利用商业信用融资的动机渐变,政府对国有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规制也发生了大的变化。计划经济时期,国有企业利用商业信用融资在市场力量与政府政策角力的夹缝中残存,商业信用融资方式发生了变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鼓励国有企业运用票据化商业信用融资,但市场对于商业票据融资却踯躅不前。只有协调好市场力量与政府的作用,企业商业信用融资才能真正创新。[40]
参考文献:
[1]周小川.金融改革发展及其内在逻辑[J].中国金融,2015(19).
[2]李扬.冲破经济发展的资金瓶颈[J].中国金融,2015(19).
[3]张杰,杨连星.中国金融压制体制的形成、困境与改革逻辑[J].人文杂志,2015(12).
[4]傅勇,李良松.金融分权的逻辑:地方干预与中央集中的视角[J].上海金融,2015(10).
[5]刘鹏.商业银行变革转型历程[J].中国金融,2015(3).
[6]黄宪,王旭东.我国央行货币政策实施力度和节奏的规律及效果研究——基于历史演进和时变分析的视角[J].金融研究,2015(11).
[7]牛晓健,武帅,朱树艳.中国货币政策区域效应的实证研究——基于1985-2013年的数据[J].上海经济研究,2015(9).
[8]范建军.从“升降息”制度看我国货币政策存在的问题[J].中国发展观察,2015(11).
[9]周远,纪春明.我国货币政策的价格效应与产出效应研究——基于2008-2015年我国货币政策实施效力分析[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5(7).
[10]谢太峰,樊若琛.我国货币供应量与利率关系的实证分析[J].征信,2015(10).
[11]罗煜.中国真实货币流通速度估算[J].金融研究,2015(3).
[12]王延军,温娇秀.产业结构变动与我国货币流通速度研究[J].上海金融,2015(1).
[13]李炳,袁威.货币信贷结构对宏观经济的机理性影响——兼对“中国货币迷失之谜”的再解释[J].金融研究,2015(11).
[14]王飞,我国货币供给是否是通货膨胀的格兰杰原因:新的解释[J].上海金融,2015(4).
[15]李鹏,杜亚斌.我国通货膨胀是一种财政现象吗——基于财政支出视角的时变参数研究[J].财贸研究,2015(3).
[16]荣幸子,蔡宏宇.我国财政政策与通货膨胀——基于价格水平的财政决定理论的实证分析[J].财政研究,2015(1).
[17]李俊成,蔡春春.社会融资结构与通货膨胀的关系研究——基于VAR的经验证据[J].上海金融,2015(6).
[18]杨光辉,汤贵明.基于DFI模型的中国核心通货膨胀的测度[J].统计与决策,2015(23).
[19]罗云,代晓静.长期约束下的核心通货膨胀率的估算[J].统计与决策,2015(2).
[20]汤丹.基于SVAR模型的中国核心通货膨胀估计及预测评价研究[J].宏观经济研究,2015(1).
[21]刘旭.中国通货膨胀门限值的实证检验[J].中国市场,2015 (21).
[22]刘子寅,范科才.汇率传递与通货膨胀动态的非线性关系研究(1996-2009年)[J].世界经济研究,2015(5).
[23]赖溟溟,姜岩.中国反通货膨胀成本的估算及其政策含义[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43(4).
[24]赖闽苏,刘青,曹玲.农村金融体制变迁及其绩效考察(1978-2003)[J].中国集体经济,2015(13).
[25]易棉阳,贺丽.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的逻辑起点[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
[26]余霞民.农村金融改革绩效评估:增量改革和存量改革的比较[J].浙江金融,2015(10).
[27]黄惠春,李静.利率市场化、市场势力与农村金融市场效率损失[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
[28]张羽,赵鑫.农村金融发展拉动了农村经济增长吗[J].社会科学战线,2015(10).
[29]杨青,刘维忠,龙涛.新疆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关联性[J].贵州农业科学,2015(5).
[30]程呈,祝国平.吉林省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吉林工商学院学报,2015(3).
[31]邱立军,徐伟川.吉林省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湖北农业科学,2015(11).
[32]唐雨虹,齐天翔.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基于西藏1978-2013年的实证分析[J].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2).
[33]郭研.内蒙古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VAR模型的解释[J].北方金融,2015(1).
[34]王黎欣.宁夏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J].经济研究导刊,2015(22).
[35]饶明,何德旭.中国股票市场改革与创新发展的逻辑[J].当代经济科学,2015(6).
[36]唐清泉,巫岑.银行业结构与企业创新活动的融资约束[J].金融研究,2015(7).
[37]安世友.中国银行业市场结构演变的金融稳定效应研究[J].财经理论与实践,2015(7).
[38]许家云,佟家栋.人民币汇率与企业生产率变动——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J].金融研究,2015(10).
[39]罗素梅,张逸佳.中国高额外汇储备的决定机制及可持续性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5(4).
[40]赵学军.经济体制转型与国有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变迁[J].中国经济史研究,2105(6).
(责任编辑:卢艳茹;校对:龙会芳)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544(2016)02-0073-08
收稿日期:2016-02-28
作者简介:赵学军,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研究室主任,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金融。
Review of China’s Contemporary Financial Research in 2015
Zhao Xuejun
(Institute of Economic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836,China)
Abstract:The paper mainly selected some representative articles which engaged in empirical studies of some advanced problems in China’s financial development in 2015.And the paper also introduced hot issues,major perspectives and related research progress in contemporary China’s financialresearchfromtheperspectivesoffinancialreformanddevelopmentlogic,the implementation rules and effectiveness of monetary policy,the cause and influence of inflation,the systematic changes and reform of rural finance,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Key words:contemporary;China;fin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