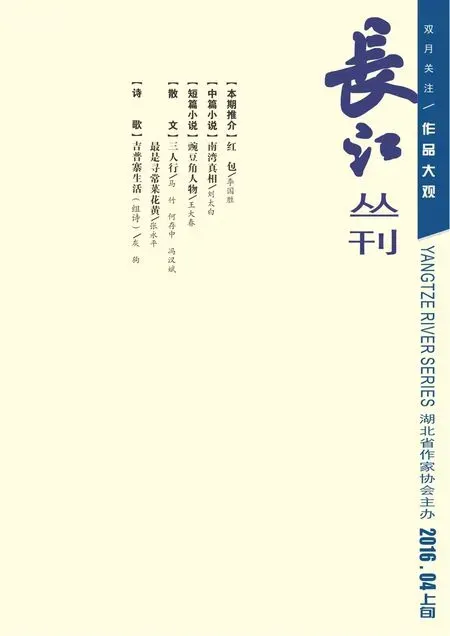狠人及其他
■张 丽
狠人及其他
■张 丽
张丽,湖北省作协会员。湖北省第三届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有小说入选《微型小说选刊》《小小说选刊》《中外百年经典微型小说大系》《中国微型小说百年经典》《中国当代闪小说超值经典珍藏书系》《2010年中国微型小说精选》《2010年中国时文精选》《2011中国年度微型小说》《2011年中国手机小说精选(闪小说年选)》《2012年中国微型小说精选》《2013年中国微型小说精选》等。出版散文集《像鸽子那样飞》,小小说集《幸福的柠檬》等。

一
享福丧事的锣鼓声远没有他娶媳妇时喧嚣高亢,唢呐的声调一咏三叹,悲悲切切,像是在替菊诉说心中的往事。操办丧事的还是那些乡邻,小卖部的驼子、上湾的狠人,还有下湾的李媒婆和牛贩子瘪三也在。当初,中湾人热热闹闹到赵棚山里把菊娶回来做享福的媳妇,特别是李媒婆,磨光了嘴皮,跑断了胯子,来来去去马不停蹄地撮合,才用一堆堆彩礼换来享福和菊的婚事前所未有的热闹和富足,八抬大轿,18件嫁奁,娶亲的排了一条冲,喇叭唢呐吹了两天两夜,鞭炮屑像成群的红蜻蜓翻飞。很多人说,人这辈子,一生风光一回,值了!
如今,不得不无比庄重地为享福安排后事。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谁料到享福命短,是无福之人。哀乐如阴云笼罩庭院,把人的心吹得凉嗖嗖的。李媒婆的巧嘴似乎僵化了,少有开腔,驼子一轮轮给亲戚递烟倒茶,黄毛狗跟着钻进钻出。堂屋的主事没一刻清闲。他张罗过无数回红白喜事,哪些人去设灵堂,哪些“八脚”上山给享福挖井(井即墓坑。“八脚”就是八个男人,从挖井到抬棺去埋,少一个不行),哪些人去借桌椅板凳,早已在心里合计好了。狠人叼着烟走来走去,不时对主事指手划脚。他看不得主事的沉稳,更看不惯一村人围着主事转。河村是狠人的地盘,做主的应该是我狠人。狠人想着,脸上的肌肉拧在一起,那处刀疤更加瘆人。
“您歇会,抽支烟。”驼子哈着腰过来,给狠人递上一支烟。转身时,又往狠人的口袋里塞了一包红塔山。
哀乐在角角落落冲撞回旋,搅得菊肝肠寸断,眼泪如断线的珠子。叹自己三十不到的好年华守寡,哀一双儿女往后可怎么过?才五六年的光景,结婚的喜庆还没有在人们心头散去,那句“值了”还在耳边回响呢,一切就换了模样。
二
菊是赵棚山里人,做姑娘时相貌出众,又很傲气,当地人叫她精怪。她浓眉大眼,说话清脆悦耳,笑起来河水都跟着“咕咕咕”翻泡泡。
那年“看家”(本地风俗,相亲时女方要到男方家看家境),媒婆问菊啥想法,菊故作为难说:“选亲不如选媒,您当媒人我当然放心,家是看上了,就是他长相差了点。”媒婆嘴巴抹了油:“你这女娃子额头上长了眼睛,三只眼看人,人家是个独苗,瘦是瘦点,坑眉凹眼也不缺那一点,他吃公家饭的,大伯又当官,前途大得很,几多人想我撮合我还不答应呢!”菊不需要媒婆说得那么细,堂姐芳的男人就是享福学校的老师,芳早把享福根正苗红,大伯是公社书记的家底透露给菊了。况且是享福先看上了菊,就算媒婆替别人撮合,享福也不会答应。
菊第一次到享福家,由媒婆带着,在房子里三间外三间里看。那土改分得的乡绅玉鄂的房子,青砖瓦、马头墙,高门大户有气势。菊看得心花怒放,可她不表露出来。享福不一样,他跟前跟后,一味赔笑脸,尽说好听的。菊看不上享福的馋样,又觉得很受用。自己一个山里丫头把禾畈地堂堂教师抓在巴掌心里,当然得显摆显摆。菊不温不火,享福如热锅上的蚂蚁等不得,逮住机会就去菊家帮忙做事。动作不怎么利索,那份认真劲可是真的。享福是独儿,家里6个姐妹,平时当老师,没有做过农活。他来,大包小包带东西,到田间地头,一文弱书生样,当然不要他做事。不做事站站,菊家人觉得有脸面。逢年过节享福也会来事,布料、猪肉、糕点挑好的往菊家送。
猴子不上树,多打一会儿锣。享福的殷勤得到回报。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冬日,菊嫁给了享福。那天的场景与今儿何其相似,还是这房子,还是那些帮忙的人……只是那日翘起拇指说值了的人,看到菊和两个哭泣的孩子,也不由得叹息摇头。
三
“八脚”吃了早饭上山挖井去了,狠人想去后山瞧瞧,又怕菊知晓后不高兴。病怏怏的享福终于去了。六年里,他和菊吃一锅饭,睡一个床,夫妻成双结对,点点滴滴,时时处处对狠人都是煎熬。享福算个毬,要不是有他大伯这个老家伙当后台,能娶到菊?狠人眼睁睁地看到一朵鲜花在牛粪上开花结果,空叹自己徒有狠人的虚名。在一冲人面前人五人六,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就是要不到菊的一张好脸色。
就说八脚吧,挑上的八个男将谁有我狠人的劲头大?不要我去还看不得。狠人厌烦主事挑选八脚那套话:人要善,心要实,办事要牢靠,为人要有好口碑,否则,对亡人的后代不利,更恼火菊没拿自己当事。“穷鸡巴讲究,过的么日子能瞒得过我?驴子拉屎外面光,总有一天,老子要扯下你的遮羞布,让你乖乖爬上我的炕头……”狠人瞟了一眼菊,恨恨地丢下烟头,用脚踩熄。
人一悲伤,各种滋味涌上心头,哭丧给了菊发泄的出口。她哭诉:我苦命的人啊,你没享到福啊,你说了跟我到白头的呀,我的亲人!你咋这么狠心哪,亲人呐……那长一声短一声揪心的哭诉,在场的人跟着抹眼泪。驼子听得心寒,悄悄躲进灶屋去烧火。他明白,菊诉的是享福,哭的是自己。
尽管关起门过日子,好不好在各人心里,值不值别人说了不算。在一个湾里生活,享福的家底驼子清楚,享福一贯的品性驼子也知晓。这些年,别人看不起驼子,菊从来没把他看外。菊的苦,驼子哪有不知?
菊是过了门才晓得享福除了上课,纯粹一懒人,啥事不会做也不做。家境也不是以前看家的宽绰,那些排场都是花了代价的,是出嫁的姐姐们凑钱让弟弟风光。菊是个心气高的人,享福做不得事,毕竟是文化人,要维护脸面。暗地里两人吵得天翻地覆,走出门与隔壁左右邻居说说笑笑。菊的嘴对享福像刀子不饶人,双手却像耙子会持家,过日子是好手,种田,喂猪、养鸡、放牛,样样能干。享福餐餐有热饭暖胃,夜夜有老婆暖身,女儿出生了,又生了儿子。日子看似顺汤顺水,菊红润丰满,伢们活蹦乱跳,可享福越来越瘦,瘦得像枯干的木柴。村里人纳闷,怎的一个屋里吃饭,菊像是吸血鬼,吸干了男人?这可不得了,定亲的时候,就不停地要彩礼,要了三年呐,硬是把享福家要空了。这嫁过来也不消停,要人命呢!果然,享福得了绝症。癌,没得诊。花去几万做了手术,菊向娘家借,向亲戚乡邻借,说哪怕卖房子也会还的。男人的命延续了一年,还是走了。很多人说,菊不值,用大几万块换男人一年的活头,不值。
四
享福走了,菊落得一大匝借条、两个孩子、还有享福的双亲。老的老,小的小,扔下吧,有自己的骨肉,良心上过不去还遭人骂。可一个外姓女人又结了扎,这大的拖累,往后的日子怎么过?才三十不到呐,有人建议菊坐堂招夫,找一个招郎。招郎是鄂北山区的叫法,意思是入赘、倒插门的女婿。菊才点头呢,狠人就托李媒婆上门。说不嫌弃菊带两个娃娃,也不打算生育自己的孩子,愿意为菊担担子,给她一家子当靠山。菊早就知道狠人的心思,大伯在的时候,狠人不敢放肆,享福活着的时候是公家人,狠人也有些怕处。而今,两人都去了,一家老小谁撑腰?菊不甘心嫁给狠人,又不敢明着回绝,只好推脱说夫妻一场,起码守丧到享福三年满。
嘴上说守丧三年,暗地里,菊见过几个男人。对方对菊是满意的,一听说要做招郎就没有下文。事实明摆着,在河村,且不说菊家是一乱摊子,就是年轻姑娘也难找个招郎。若不是穷得没饭吃,谁会改名换姓离亲别友倒插门?更别说替别人养两个娃子。时间一天天过去,狠人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耐心和勤快。菊才赶牛到地里,狠人就套上犁耙耕地,菊带着孩子捆草头,狠人一担担往稻场挑,就连吃水也帮菊挑满水缸。一来二去的,不光河村,整条冲都知道狠人在等菊,菊迟早是狠人碗里的一盘菜,谁还敢起心思?
狠人做得理直气壮,菊却矮了三分。不知不觉,河村人看菊的眼神躲躲闪闪,说话的语气客气中显出生分。似乎菊从一个受人同情的弱者变成了狠人的同谋,让大家不得不保持距离。只有驼子看见菊还是点头微笑。一次,菊倒了阳气般到小卖部买了盐要走,驼子叫住了她,说:这是别人送我的四盒脑心舒,我不喜欢那个味,喝不进,给你拿去!菊抬头,眼里有泪,说不要。驼子宽慰地笑说,我是你耀祖叔呐!
驼子的小卖部在路边,和公共茅厕共一个山墙,恰好和菊的房子隔一个池塘相对。小卖部旁边有几棵夹竹桃,粉白的花朵直逼人眼。菊一个人的时候,坐在屋里能瞅见看书的驼子。想象桃花下少年耀祖的模样,五官应该还是这样端正,皮肤该是白净中更加少嫩,只是脊背——挺直的话,应和他老子一样玉树临风吧?驼子让菊看过父亲玉鄂的画像,确实如湾里老人们说的那样,俊得让人愤恨老天爷偏心。人俊又有思辨奇才,小小的河村岂能容下铁嘴大状师玉鄂?玉鄂自绝于人民时,唯一的愿望是请乡亲们放过年幼的儿子,但享福的大伯要把革命进行到底。地主崽子耀祖名字招摇不说,骨子里也不安分,要把他打趴下,永世不得翻身。驼子除了看书的习惯和别人不一样,菊看不出他的不安分。菊喜欢有文化的人,楚剧里五子登科中状元是何等荣耀,小姐公子花前月下是何等浪漫,要是耀祖……菊看着想着,兀自笑起来,一抬头,狠人正盯着自己,脸上阴森森的。
一天,儿子突然跑回来说,耀祖爹养了多年的黄毛狗被人毒死了。
五
享福三年满后,菊招了狠人。
“狠人”做招郎之前是有名字的,只是村里人不敢喊。一来,狠人有恶相。一张脸,丑陋不说,纵横狰狞道道疤痕;一双眼睛,鹰样阴沉沉透着寒光。再就是有劣迹,似乎是应证那句“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狠人在号子里呆过的信息,他还没回河村,就传遍了沟沟坎坎。
狠人初回河村,就在唯一的吃水塘丢了包炸药,那一声炮响,满塘翻起白花花的鱼肚皮,他把鱼弄到集市卖了换烟酒,看中谁家的鸡鸭逮住就杀了吃,村民敢怒不敢言,见了他绕道走。夜里有小伢吵夜,大人就呵斥,再哭,狠人来了!一句话比哄、拍、抱,打还灵验。狠人的狠气最初是相貌带来,虽说不能以貌取人,一个五大三粗的爷们,疤脸、鹰眼、寡语、冷言,总让人不寒而栗。他呢,似乎偏要名正言顺,取名“黄三梗子”。黄当然是享福的姓,狠人做的是菊的招郎,是顶替享福,享福姓黄,狠人就姓黄。姓没有异议,名字蹊跷,三梗子不是三梗子蛇么,毒气大着呢!有毒气总不能叫毒人吧,叫他狠人,是畏惧也是抬举。你狠我怕你,惹不起躲得起。硬是碰上对了脸,挤出笑容打个招呼。河村上中下三个大湾,姓虽不同,场面上还是一家人。村人与狠人打招呼,狠人也是笑脸相迎。笑和笑不同,这边是小心翼翼,和颜悦色,那边似笑非笑,面目猥琐。有人就猜,狠人到底因何坐牢?杀人?不会,那得填命。打砸抢?有些像,不然,哪来的伤疤?至于小偷小摸,还轮不上去蹲号子。
河村人对狠人看似疏远,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心里却好奇得很。暗地里揣测、打听他的喜好和行径。瘪三是个牛贩子,习惯于走夜路,溜墙角。一次他偷偷趴在菊家后窗听房,原以为能探些夫妻之秘做下酒谈资,冷不丁耳朵被拧住,嘴巴还没叫出声,被塞进一破鞋板。瘪三扭头挣扎,眼见是狠人,想求饶嘴巴堵着,一股臭气直冲鼻子。狠人像猫捉弄老鼠般,拨弄瘪三的下巴:“想看,嗯?进屋。”瘪三双腿筛糠。“不。不看,路过!”几个字从鞋缝挤出,沙土细溜溜直往喉咙里钻,咳不出吞不得。狠人呸了他一口,朝他裤裆掏一把,扔下一句:“小东西。”慢悠悠踱步回屋。
有了狠人,中湾仿佛突然安静了。就说以往吧,一碗饭,大家不约而同端到池塘边,坐在杨柳下,天南地北瞎侃,侃到碗底朝天还要下几盘石子棋。两人下,一圈人观阵,七嘴八舌。意见不一起争执,从湾这头能传到那头。有的家里婆娘怕红脸的,老远站在门口喊:“回来添饭哟,我要收碗。”日子如水面上的夹竹桃花悠闲安逸。如今可不同了,哪怕一溜人在塘边说得正欢,狠人来了,只拣个角落蹲下,不做声不做气,立马全部噤声。这时的安静像雾霾让人沉闷,透不过气。有人悻悻然站起,拍拍屁股,向家屋的方向喊:“哎,回来了”。又补一句:添饭去的!就好比必须有个解释才能脱身。接着,又有人起来,似乎是随意地走,却把碗倒过来敲一敲,证明是空的,不得不走。然后,池塘边如泄洪,呼啦冲走一大片。只留下狠人,贪婪地吸烟。
六
狠人的闹腾,菊都能忍。她唯一不能忍的是狠人三番五次去向驼子赊账。
狠人烟瘾大,一天5包。5包是小卖部驼子说出来的。驼子开小卖部,狠人天天去,只买烟酒。烟是白沙的,红梅的,酒买本地吊酒。狠人每天来小卖部至少5趟,第一趟是早上,驼子刚开门,他是掏钱的。鄂北讲禁忌,做生意靠第一把,若赊钱卖家折本买主丢人。可他不给足数,比如红梅一包5元,他给4.5元。驼子说:“五块呐!”狠人不说话,点一根烟,深吸,再对着驼子的脸吐出,驼子呛得连连咳嗽,身子一下下矮下去。余下的四包就是走形式,狠人走进土坯屋喊,拿白沙,记账。驼子给他,他等驼子拿账本,驼子写了烟和钱数,他接过来签字,歪歪扭扭画三横,像三梗子蛇。一天至少十二根短短的横线。等一页签满了,他再来赊账,驼子嘀咕,你欠300多呐。狠人不耐烦,乜着眼甩一句:“收了粮食再说”。卖完粮,还是来赊账。驼子和他理论,狠人讪笑道:“黄毛狗啥滋味,记得不?你栽这些夹竹桃有毒,想不想尝尝毒气?”
菊是从儿子嘴里知道狠人欠账赌狠的,更加有了愧疚。住着耀祖的祖屋,自己的两个男人与耀祖为敌。土改时,乡绅玉鄂被斗死了,唯一的独苗,7岁的耀祖充当主劳力修大坝,挑土推石头,做不动就挨凑,柔嫩的腰板压成了驼子。菊早就听说驼子沦落到今天,与享福的大伯有关系。大伯搞水利建设有功,没人翻历史帐。斗地主是全国大形势,修大坝也是为子孙后代造福,但是整人可轻可重,把一个孩子整成驼子实在寒心。而狠人,就因为菊和驼子走近一点,毒死了驼子相依为命的黄毛狗,还一而再再而三拿东西不认账。为了还账,只要得空,菊就到东山头帮人摘棉花,到祝站帮人插秧割谷。打趟短工赚几百元回来,耀祖看到黑瘦的菊直叹息,要她先去还享福生病欠下的老账。菊取下驼子挂在墙上的账本,一页页翻过去,看到狠人签的“三”字,条条如吐信子的毒蛇,手不住地发抖。驼子一把抢过,当面呼啦啦撕成碎片。
七
驼子的小卖部在池塘那边,是借公共茅厕搭的间土坯屋。往往村舍这边炊烟袅袅,厕所那边冷锅冷灶。夹竹桃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驼子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煮一次饭管三顿。屋里杂货不多,一个货柜贴着床,有买东西的,站着或坐着顺手递过去。他话少,不笑,也看不出悲戚。大多时候,驼子呆在小卖部,翻看那些泛黄的书,书在他的床下面,总看总有。
小卖部生意勉强维持生计,一方面他本钱少,有残疾,想扩大,一些重物挑不动。另一方面河村人习惯于上街,看看热闹,顺便把油盐酱醋带回来。去小卖部最多的人是狠人,他不需要现钱就能拿到想要的东西。河村人常常看见狠人在小卖部溜达,暗地里叹息驼子遭殃。只有驼子知道,狠人并不是每次去他的小卖部。驼子是通过小木窗发现不对路的,狠人人高马大的从窗口闪过去,却好久不回转。就是拉屎也花不了半晌吧?驼子纳闷了几回,一次傍晚时分,终于看不进书,他趴在窗口往外看,这一看,心惊胆寒:狠人正贴在拐角的外墙朝女厕所偷窥!驼子擦擦眼睛再瞅,狠人正看得起劲。天杀的!驼子骂了句,锅盖般的后背重重顶在墙上。
驼子怀揣着秘密,寝食难安。他已经患了和狠人相似的偷窥癖,只不过,狠人看的厕所里的女人、或者女孩,他看的是狠人的丑态。好像怕狠人识破,狠人再来买烟酒,驼子不提赊账的事,要什么都给。他讨好地给狠人介绍一种高粱吊酒,狠人喝了说这酒对路子,再买,再喝。狠人不仅有烟瘾,酒瘾也越来越大,醉了酒要么呼呼大睡,要么摇摇晃晃转悠。菊是说不得的,怕他发酒疯打骂,说了也不凑效。菊有做不完的农活,女儿姗姗初中毕业,算个帮手,儿子读五年级,爱学习,有空就去驼子那里找书看。姗姗像她爸爸高、瘦,又像菊爱俏,本来就好看,今天戴朵花,明天扎条红丝巾。别的女伢还没开知呢,她就会打扮了。菊几次问她哪来的钱买花呀朵的,她总能敷衍过去,菊也没空闲细思量。
那天,姗姗来小卖部买发卡,低头在一盒头饰里翻来覆去的挑。她穿的娃娃领短袖,脖子白白的,长长的,驼子在柜台里面站着,无意中瞥见姗姗像早熟的春桃。露出胸脯鼓胀胀的,像两个白瓷碗倒扣,白得汪眼睛,又像冒气的白馒头,散发诱人的香。
“就买这对,这是钱。”姗姗把钱放柜台上要出屋了驼子才回过神。下意识地,他喊:哎……姗姗回转来,驼子结结巴巴:“听说——南方好赚钱,有了钱想啥买啥,你——是不是也去看看?”
这以后,每次姗姗来买东西,驼子都要说些出外打工的好处,听得姗姗莫名其妙。姗姗也发现,小卖部的好东西越来越多了。就说那个蝴蝶发卡吧,镶的珠子一颗颗,烙她的心呐。姗姗摸了几回,驼子看她舍不得放下,就说,你跟我实心实意讲几句话,我就把它送你。姗姗抬眼,似乎不信。驼子吸了口气,不看姗姗,问道:他——总是给钱你?姗姗有些惊愕,突然明白似的脸红点头。“他给钱你,要你做啥不?”驼子晃着发卡问。“不要我的啥,就摸摸,还夸我水嫩……”。姗姗的脸红扑扑的,驼子心惊肉跳。“傻伢呐,不能让他摸!我这好东西多,你要喜欢就听我的,想啥拿啥。”姗姗不做声,眼睛忍不住看货柜。“不要让他挨你的身子,他要摸你,就告你妈去,要不然,你会嫁不出去的!”姗姗低下头。驼子把发卡给她,轻声说:“拿着吧,早点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最好读读书。”
驼子暗地里关注狠人的一举一动。正如他担心的那样,姗姗刚走进女厕所,在拐角的墙外就出现了那双贪婪的眼睛。
驼子坐不住了,他叫菊让姗姗去南方,菊说一个人忙不来。驼子无心呆在土屋,去街上进货的时候,有意无意打听一些江湖异人,和他们偷偷交朋友。他舍得下本钱,那些跑江湖的见识多,多少有点本事,酒足饭饱就许诺,只要驼子哥一句话,白道黑道拼到底。
八
狠人完了,被三梗子蛇咬了!这是午饭时间,池塘边聚满了人。好长时间大家因为狠人不敢来,现在因为狠人又聚在一起。
“真是邪乎,倒在女厕所旁边,好像是被夹竹桃枝划伤绊倒的。”
“是啊,倒地上了,被蛇咬了额头,眼睛都伤了。”
“你说,从哪里来的毒蛇呢?狠人去女厕所干啥来?”
“那哪说得清!反正呐,人不能犯冲。你说他叫个啥三梗子,简直是欺侮毒蛇到家了。”
池塘埂上议论纷纷,驼子的小卖部寂静无声。狠人痛得叫天骂地被送到医院。回来后,一只眼空了。
年底,有姐妹邀姗姗去深圳打工,菊想留她在家里做帮手,无奈孩大不由娘,由她去了。
九
几年后,夹竹桃花开得正艳的夏天,驼子突然去世。那时候,鄂北还没实行火葬,土葬需要八脚挖井。葬驼子的八脚中狠人算了一个。狠人是第一次当八脚,驼子死得急,天气又热,村里年轻人在外面打工,村支书找八脚,硬是凑不成数,是菊把狠人凑上的。菊正在为奔丧的人做饭,她把锅铲一放说,我男人在屋里,我叫他来。狠人要当八脚,其他七个虽然有些不自在,想着驼子孤老一生,没有后人,没什么禁忌,也不好说什么。八个人挖井,都吭哧吭哧使劲,没人说话。突然,狠人的铁锹下血光飞溅,大伙一看,一条碗口粗的蛇被斩掉了两截。蛇身上的三条花纹在阳光下触目惊心,狠人吓得面如土色,一头栽在地上。那个深夜,菊被狠人变调的哭叫惊醒:耀祖叔,饶命啦——夹竹桃,不是我……
小卖部的夹竹桃树越长越繁茂,那些粉白的、猩红的花朵飘落到茅房上,大路上,又被风吹进池塘。塘边柳树下聚满了聊天的人。菊在石埠头上洗衣服,有人闻到了衣服里若有若无的臭气,问菊,当家的好久没出来了,好些没?菊摇摇花白的头。
好事的瘪三掐指一算,狠人中风瘫痪三年多了,再也日不了天,狠不起来了,如果菊不尽心服侍,狠人的那个“小东西”也该生蛆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