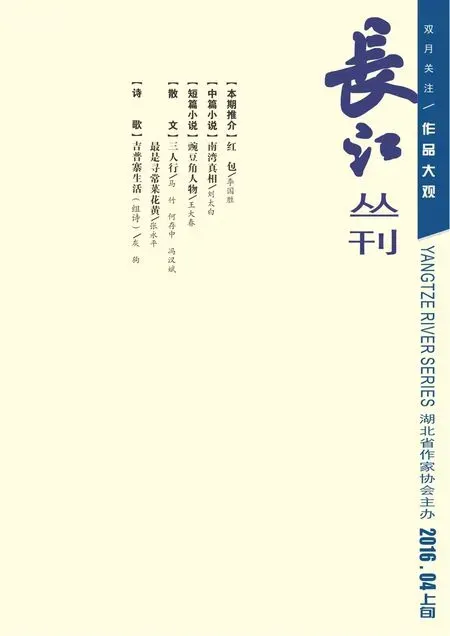豌豆角人物
■王大春
豌豆角人物
■王大春
王大春,男,湖北襄阳人,现供职于媒体。在《长江文艺》《短篇小说》《野草》《短小说》及《今古传奇故事版》《故事家》等报刊发表有小说、故事、寓言百余篇。有小小说、寓言分别入选各选刊及年度作品集并获奖。

村名叫豌豆角。
村如其名。似不经意地地遗落在山坳里,年深月久,竟也出土发芽,长出一派气势,葳蕤茁壮。然村名却沿用下来,至今。
豌豆角有三十来户人家,其中以李姓居多,呈颗粒状遍布豌豆秧之上,经年累月,已渐趋饱和,虽压得其不堪重负,却也艰难地撑了下来。
一年又一年。
活宝
在豌豆角,傻丁是一个活宝。
傻丁长着一张娃娃脸,圆圆的,胖胖的,见了人就笑,喜眯喜眯地,极快乐的样子。一个人的时候,傻丁也笑,咧了嘴,无声地笑。
刚生下来的时候,傻丁就显得有些弱智,眼珠子老半天都不会转圈,他爹差一点把他扔进了簸箕洼。到了上学的年龄,傻丁更显出与众不同来,常常在教室里尿了裤子,或是一连放十几个响屁,臭得老师只好提前下课。念了八年书,傻丁才读到小学三年级,老师们都把他当编外生,不计数的。其时,傻丁的嘴唇上已长出一层黑黑的茸毛,像个小男人了。傻丁娘见儿子成天在孩子堆里打闹,知道再读下去也是白搭,就找到村长说情,求给傻丁找点事做,好挣点工分。村长沉吟片刻,把村里那只半大牛犊子交给了傻丁。于是,傻丁的战场转移到了山坡上。每天,他牵着那头半大犊子,赶到后山,把牛绳往牛颈上一盘,在牛屁股上猛拍一巴掌,牛便寻个有好草的处,低头海吃。有时候,傻丁往草坡上一倒,呼呼大睡;有时候,他则反反复复地朝山坡上冲剌,嘴里“嗨嗨”有声,发泄着精力;有时候,傻丁也“卧住”、“起来”地摆布小牛犊子,倒也像模像样。
冬闲的时候,村里人都扎堆讲古,不用放牛的傻丁也往一块凑,伸长颈子,入神地听,两眼珠纹丝不动。
有人就拿话逗他,傻丁,赶明儿娶个媳妇跟谁睡?
跟你睡。傻丁喜眯喜眯地笑。
跟你睡哟!问的人装得极愤慨地反驳。
跟你睡跟你睡跟你睡。傻丁一口气说完,占了极大便宜似的,跟众人一同大笑。
傻丁成了豌豆角人茶余饭后的笑料,也因有了傻丁,村人们闲暇的日子里才有了诸多的快乐。晚上各自回了家,蜷在被窝里,与老婆做起那事时,提起傻丁,也抖抖地笑,兀自长了三分精神。如果不是那个偶然事件的发生,在豌豆角人的眼里,傻丁永远是那个既憨且傻的长不大的活宝。
那天,福生在用傻丁的那条牯牛犁地。那个半大犊子,如今已长成一头高大壮硕的牯牛,犁起地来也十分生猛,掌犁的人跟在后面,只差小跑才撵得上,一天下来常常累得半死。福生虽说是好把式,使唤起这头牯牛来,也被折腾得头晕脚软。傻丁在地埂上看得笑逐颜开,拍着巴掌,“啊啊”地叫,那公牛听了,愈发地来劲,狠不得甩开四蹄狂奔。眼看着一块地犁得像秃子的头皮,青一块白一块,人也累得接不上气,福生来了火,他挥动鞭子,对准牛屁股,狠狠地抽了几下。这下,牯牛不干了,它扬起脖子,“哞”地一声吼叫,一下子挣脱了福生手中的犁把,撒开四蹄,狂跑起来,把福生拽了个狗啃泥。等福生爬起来,那牯牛拖着犁铧已经跑上了河堤,身后留下一趟深深浅浅的犁印子。正在河堤上歇气的几个妇女,忽见一头牯牛疯了样跑来,顿时惊得呆了,叽叽喳喳的说笑也倏地哑了。
牯牛离人群越来越近,眼看着就要撞上几个妇女。远处,有几个犁地的男人也伸长了颈子,傻了样呆看。
这时,就听一个声音炸雷样响起,“卧住,卧住”,有人扭头看去,却是傻丁。他嘴里张惶地叫着,从田埂上急慌慌地跑过来。可是,红了眼的牯牛,这会儿哪里还听他的使唤,眼看着就要撞上人群,只见傻丁塌着腰,吸口气,瞄准了,狠狠地向牯牛撞去,愣是把那头牯牛撞得一个趔趄,差点摔倒。那群妇女们这才醒过神来,“哇哇”叫着,四散开去。再看傻丁,却被牯牛拖着的犁铧硬生生地从大腿上犁过,骨头茬子清晰可见,一股血珠子冒出来,霎时间把地面染得一片腥红。等福生跑来抱起傻丁时,他咧着嘴,还喜眯喜眯地笑了一下,脸上是极灿烂的表情。
当天,傻丁被送到县医院抢救,豌豆角人自发地你五块我十块地捐钱,凑了五百多块,交给了傻丁娘。
傻丁出院后,大腿落下了残疾,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远远看去,像是一个罗圈腿的企鹅,极滑稽。重活路是干不成了,队里就派他守仓库。其实,仓库里一年四季也就农忙时堆点粮食,平时里都空着,没有可看的东西,但村人们却一致推举让傻丁守仓库。没事时,大伙还凑到仓库来讲古。傻丁还是跟原来样,侧了耳朵听,喜眯喜眯地笑,却再也没人拿他调侃打趣了。
也有例外,他的外号傻丁再也没人叫了,他的大名李伟志却是在豌豆角里叫开了。
木匠奎
李生奎二十啷当岁的时候,便仗着一手顶呱呱的木匠手艺在方圆几十里扬了名。大到上梁打柜,小到起桶箍盆,李生奎样样是拿得起放得下,那物件,做出来就是不一样,掌柜的看着舒心,用着称心,有了活,都愿意请他。
那年地里刚起秋,后庄黄家洼的黄老邪派人来请李生奎去打家具,说是闺女要在冬月十八出嫁,打套上好的家具作嫁奁。谁想,家具打好了,那姑娘却死活不肯嫁啦。咋,小木匠李生奎和她好上了。
姑娘叫水月,长得明眸皓齿,秀丽端庄,颇有点大家闺秀的气质。没事的时候,水月就坐在场院里边绣花边看李生奎操刨弄斧。
哧啦!李生奎推一刨。
吱溜!水月拽一针。
一张一弛,颇合韵味。有时候,水月瞄得急了眼,针扎了手;有时候,李生奎看得走了神,锯断了榫,一来二去,两人好上了。
待嫁的闺女退婚,这在豌豆角是件很丢人的事,黄老邪在当地也称得上是大户,这份人可丢不起,就质问水月不嫁的理由。水月也知道瞒不过,一五一十地给父亲讲了。黄老邪这个气呀:好你个李生奎,挣了工钱,还要拐上我女儿,捎带着赚套嫁妆,你可真会盘算啊!可这毕竟不是光彩事,传出去更不好听,黄老邪只好打碎门牙往肚里咽。
这天晚上,黄老邪请李生奎吃饭。三杯酒落肚,黄老邪说,生奎呀,这活快完工了,可我还有一件事想劳烦你。李生奎知道不会有什么好事,他有准备,就问,啥事?
黄老邪咽下一口酒,说,这件事呢,说大也大,说小也小,说麻烦也麻烦,说省事也省事……
李生奎放下筷子,双手放在膝头上,说,黄叔,你说的事,我也晓得。我想哩,你老人家大人大量,莫怪罪我,就成全我和水月吧!我会一辈子对她好,保她一辈子不受罪吃苦。
黄老邪乜斜着眼:对她好?就凭你,你拿什么对她好?你有啥资本?
李生奎依旧低眉顺眼:黄叔,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你就……
你还有脸跟我说这话?这下,黄老邪翻了脸,眼里寒光闪闪,你狗日的简直是欺人太甚,拆了别人的婚,还有脸这样说。亏你说得出口,你这是人做的事吗?
李生奎“扑通”一下跪在黄老邪的面前:黄叔,我喜欢水月,水月也喜欢我,我们都是真心的,你就成全我俩吧!难道你眼睁睁看着水月嫁给一个她不喜欢的人,让她一辈子不快活吗?
这话说到了黄老邪的疼处。本来哩,这桩婚是下湾的朱媒婆上门来说下的,没多久,水月就想悔了,说那人这不中那不行,一大堆的理由,可黄老邪看那人家境好,又受了人家重头彩礼,就不准水月悔婚,还要逼着她早早嫁了。没想到,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请个木匠上门做嫁奁,竟和水月对上了眼。这倒是黄老邪没有料到的。
黄老邪看着跪在面前的李生奎,本想一脚把他踢翻在地,再仔细想想,也怨自己闺女不争气,他强压住火气,问,李生奎,你是个做手艺的,四乡八村到处跑,谁敢保证你以后还会不会做下这样的事?话里明显对李生奎的人品有了轻视。
李生奎也知道这事做得不厚道,可眼下,他又不好辩解,他嗫嚅着,黄叔,我是单身,水月也没嫁,我们两厢情愿,往后的事,你就看着吧,我要是负了水月,天打五雷轰!
黄老邪端起酒杯,呷了一小口,沉吟不语。他在琢磨,这退婚以后,彩礼咋法退?对外有个啥说法?唉,真是丢了面子又折钱啊!这时,水月从里屋走了出来,她“扑通”跪在父亲面前,磕了三个响头,说,爹,反正我是铁了心跟生奎走,你就是不答应,不认我这个闺女了,也还是我爹,我也会照样养你一辈子。先前订婚的彩礼钱,生奎也说了,都由他来出。
黄老邪见事已至此,知道多说无益,他长长地叹口气,摇摇头,走了出去。两个月后,李生奎请了一班响器,把水月热热闹闹地娶回了家。这件事后,李生奎的名声一下子在四乡八村传得更远了,有人更是拿这事编了个歇后语:李生奎的手艺——赚的不是钱!
有一回,我见大人们说起这个歇后语时,都“嘎嘎”地瞅着李生奎笑,少不更事的我恭恭敬敬跑到李生奎面前,问他是啥意思?李生奎在我的脑袋上敲了一记,说,个小兔崽子,胆子不小,敢拿叔来说事。我摸着脑袋,跟着一圈人莫名其妙地笑了。
蒋四爷
蒋四爷是个外来户。
从地理上来说,豌豆角属于穷乡僻壤,外乡人入籍,多不会选择这地方,可是,蒋四爷偏偏就选了豌豆角。他在李拐子屋角旁的一块空场上,先是搭起两间草屋,和老婆孩子住了进去,几年后,他又盖了三间干打垒的正屋,接了几桌客,算是成了规规矩矩的豌豆角人。
后来,混得熟了,豌豆角人才发现蒋四爷不光是个人才,还是个怪才。豌豆角三面环山,一面环水,虽说地势偏远,但是,只要人勤快,能吃苦,就饿不到肚子。白天里,蒋四爷忙生产队里的活计,晚上,他不是上山捉野物,就是下河去逮鱼摸虾,也不知他使了什么法子,只要出门,就没有空手回来过。特别是到了夏天,他门前的场院里,经常是晒着一簸箕一簸箕炕熟了的白条鱼,我嘴馋,没事就爱踅摸到蒋四爷家玩,他总是抓了大把的鱼干给我,吃饱了,临走时,又给我装满满一兜带回家。有一回,我正在菜园子里偷黄瓜吃,看到蒋四爷扛着铁锹板,走到一块田埂上,他四处瞄瞄,然后,拿锹把朝一个胳膊粗的洞里狠劲捅去,顿时,几只乌龟从另一个洞口窜了出来,蒋四爷扯根藤条挨个穿了,拎在手里,哼着小调回家去了。只把我看得目瞪口呆。
除了他的神,蒋四爷的“鬼”才真正让人称奇。豌豆角地处山区,村人胆子本来就大,大人小孩走夜路都是家常便饭,可是,却没人有蒋四爷的胆子大。一回,二赖子和蒋四爷打赌,说只要蒋四爷到老坟场上睡一夜,就输他五斤香油。平时里,村人都指着吃菜籽油过活,这芝麻磨出来的香油,不到过年待客,是没人舍得吃的,这赌注很是诱人。蒋四爷听了,笑笑,只当玩笑。其他人却起哄,要二赖子说话算话。二赖子发了狠,说只要蒋四爷敢上山睡一夜,他绝对说一算一。这下,没了退路,蒋四爷只好点头,说,赌可以打,油我就不要你的了。大家都不容易,你留着自家吃吧!
听他这样说,二赖子以为蒋四爷心虚,越发嚣张起来。他跑回屋,提来刚刚磨下的五斤香油,交给长生说,这油放你那儿,谁他妈不兑现谁就是龟孙子。
话说到这个份上,蒋四爷笑笑应下了。天傍黑,他夹着一床布单,径直去了老坟场。还专门选了两个坟堆中间的位置睡下。半夜里,有人跑去查看,回来说,蒋四爷睡得那个香呀,呼噜扯得比猫头鹰的叫声还要响。他们故意弄出些怪动静,蒋四爷也只是侧个身,嘴里“巴嗒”几声,又睡了。赢了赌局,蒋四爷也死活没要二赖子的五斤香油。
自那以后,豌豆角再没人敢和蒋四爷打赌了。蒋四爷的为人却也让人更加佩服了。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就是这么个胆大命硬的人,却在阴沟里翻了船。那是个夏天的夜里,蒋四爷照例一个人下河去逮鱼。他在回水湾里,下了几个竹笼子,快半夜时,他带去的鱼篓子都装满了。蒋四爷看这回火旺鱼多,就脱了裤子,扎紧裤脚,权作口袋来装鱼。大约到了后半夜,蒋四爷看实在没处可装了,才恋恋不舍地收了竹笼子,他把鱼篓背在背上,把装鱼的裤子骑在肩上,兴冲冲地往回走。
到了簸箕洼,他看到前面有一团绿荧荧的“鬼火”在晃晃悠悠地漂荡,山上林子里还传来几声“鬼”叫。本来呢,这“鬼火”、“鬼叫”,在豌豆角是寻常事,走夜路时经常会碰到。那“鬼火”用现代科学来解释,是人和动物的尸骨里磷的自燃;至于“鬼”叫,谁分得清是啥野物在叫唤哩。蒋四爷那天也是高兴,来了兴致,他学着那叫声,高一嗓子低一嗓子地对着叫了起来。说来也怪,他叫得欢,那“鬼”也叫得欢,像比赛似的。后来,我听我爹说,那天夜里,豌豆角人只听到一声接一声的“鬼”叫,高高低低,长长短短,一村人都不晓得是哪个人得罪了哪路大仙,个个吓得蒙着头睡,早晨起来,都像画了黑眼圈,没有睡好。
第二天,身板壮得像头公牛的蒋四爷就病倒了。发烧,还说胡话,谁也听不清。赤脚医生来给他打了针拿了药,也不见效。蒋四奶去请来大仙,又是烧纸钱,又是求娘娘,还到承恩寺去上了香,就是不见起色。蒋四爷壮硕的身胚眼看着瘦成了门板。到了冬月里,蒋四爷竟是一口气没上来,眼一闭脚一蹬走了。
后来,村子里有风言风语,说那夜的“鬼”叫,是二赖子捣鬼,来逗弄蒋四爷,想挽回输了赌局的面子。没想到,胆子贼大的蒋四爷却栽在这上面了。蒋家后人曾找二赖子查证,二赖子当然死活不承认做过这勾当。
从那以后,豌豆角再也没人斗狠打赌了,再也没有人做鬼做神地吓唬人了。都信了一句老话:人吓人,吓死人!
刘四秀
刘四秀是一个女人,但她这样的女人,在豌豆角,绝对是独一份。
刘四秀是从羊村嫁到豌豆角的,她的男人叫李四喜,一个小眉小眼的小个子男人,说话也温温软软的,不管是在老人还是孩子面前,他从来没说过半句大话。刘四秀却与他男人相反,长得高高大大,脸盘子也是圆圆方方的,说起话来粗喉咙大嗓,做起事也是风风火火的。屋里屋外的活她做了多半,李四喜至多给她打个下手,还总是落在后头,被她时不时吼上几嗓子,也不恼。两个人的日子过得倒也乐和。我妈就常感叹说,这人呀,还真是奇了怪了,男人女相,娶个女人还偏偏男相!
村子里,有男人打起老婆来,总是拿刘四秀作比:你看看人家,样样活拿得起放得下,瞧瞧你,拈不得轻拿不得重,还天天跟老子对着干,想骑在老子头上作威作福,你休想。接着便是一阵“砰砰”的暴响和女人呼爹叫娘的哭叫。
于是,女人们聚在一堆,就争相说刘四秀的坏话。
“个男人婆样,除了一把子力气,还能有个啥?”
“哪个男人娶了她,只怕是要悔死哩!你看她,奶子没得奶子腰身没得腰身屁股没得屁股,说起话来像只母鸭样,哪个男人看得上她?”
……
刘四秀也察觉到豌豆角人异样的目光,她也不恼,该干啥干啥,该吃啥吃啥,还喜欢和男人李四喜手挽着手在村子转圈子。李四喜总是昂头抬胸,小脚步迈得相当精神,脸上也是神采熠熠,刘四秀说话时,他仰着小脸,眼神烁烁的,全是得意与满足。村里人便总是在半掩着的门缝里,偷偷朝外窥视,嘴角差不多咧到耳根子了。到了夏天,豌豆角的婆娘们都喜欢穿着大裤衩,光着上身,在村子里乱走,任凭两个奶子像两颗地雷样在胸前来回晃悠,把男人们看得眼晕。刘四秀却从不这样,她上身至少要穿件汗衫,才肯出门。这又让婆娘们有了说舌的由头。
“五黄六月里,还捂尸样,身子不敢露出来见人,保不准有啥见不得人的。”
还有人更尖酸刻薄:“女人男相,有啥怕的,脱光了也没人看呢!”
当然,这话都是避着刘四秀说的,她肯定是听不到,不知道她听到了,会有啥样的反应。更稀奇的是,刘四秀还会吃烟喝酒,烟瘾大酒量也大。逢年过节,两口子一瓶酒,她喝掉大半没得事,男人喝小半,还要醉上小两天。有一回,我坐船过河去村部上学,刘四秀也在船上。正准备开船时,来了个外村人,他上了船,就和船老板套近乎,递上一根纸烟,又给另外两个同船的男人发了烟。然后,四个男人有说有笑地在那儿吞云吐雾。这时,就见刘四秀从身上掏出一盒烟来,挨着给船上的人递烟,连我们几个小学生也没漏下。我们自是不接,不会吸,也不敢吸。这下,外村人懵了,他傻子样站在船头,不晓得咋样应对这个事。刘四秀还上前给那人点上火:来,吸一口!
那人脸上羞得像蒙了一块红布,船还没拢岸,他就跳下去,一溜烟跑了。刘四秀看着那人的背影,鼻孔里哼一声,说,还男人呐,都不晓得一点规矩。哼!话语里很是不屑。回家后,我把这事说给父亲听,他也说那外村人礼数做得不周全,对刘四秀回敬的这一招,他没说啥,只是笑笑,点了点头。
刘四秀就这么在豌豆角生活着,时间久了,大家都习惯了,也就不再背后乱说她的坏话。她和李四喜的日子依旧过得平淡又从容,舒展也随意。
后来,我考上学,到外地去读书,放假时回来一趟,也是来去匆匆。参加工作后,事多不说,还要忙着恋爱,更是难得回一趟家。等我两年后带着女朋友回到豌豆角,却听说刘四秀和李四喜离婚了,还是李四喜提出来离的。刘四秀和李四喜一直没有小孩,男人提出离婚,她也没有和男人吵闹,两个人一起和和气气地到乡里法庭去办了手续,就分开了。刘四秀住在分得的一间偏屋里,和李四喜毗邻而居,倒也相安无事。这时候,农村承包到户好几年了,听说,刘四秀还经常帮着李四喜侍弄他的几亩责任田,晚上的时候,两个人也还出门在村里子转圈子,肩并肩,只是不再手拉手。李四喜眼里和脸上的神色倒也依旧,但刘四秀的脚步却没有了往日的劲健。
我曾问过母亲,刘四秀两口子好好的,为啥要离婚?母亲叹了口气,说,这是命啊!再不多说。
又过了两年,我回去过年,竟听说刘四秀死了。说那天早晨她还随人去乡里赶了集,买了头油、雪花膏、香胰子,回来又是洗头洗澡又是抹雪花膏,弄得浑身香喷喷的,傍黑,她和李四喜在村子里转圈子时,她还拉了李四喜的手,脸上是喜气洋洋。没想到,当天晚上,正吃着饭,突然溜到桌子底下,就这么走了。
母亲给我说这些时,一个劲地说,走了好,走了好啊!人咋样活,都是一辈子。刘四秀这也是一辈子啊!
拐子三
拐子三姓甚名谁,除了老村长周会计外,就没人知道了。村里连三岁小孩都叫他拐子三。拐子三从来不恼。
拐子三是光棍。三岁上爹抓了壮丁,从此生死不明,娘刚把他抚养成人,就撒手归西了。拐子三出去浪荡了十年,依旧光棍一人回来了。那年月,人没人材,钱没钱财,娶个媳妇,谈何容易。就这么着,他破罐子破摔,遂成为地道的老光棍。
身为光棍的拐子三有两大嗜好:一是抹牌,二是喝酒。你就是十来岁的小孩,只要邀他抹牌,他也欣然入座,且能不吃晌饭。后来,村子里有人赌钱,他也来。赢一盘,一分钱。一天下来,也能赢上一毛大几的,于是,逢人便嘘:嗬嗬,赢了一毛六。那神情,活像捡了金元宝。
拐子三特能喝酒,却从不喝自己的——他没钱买酒——谁家来了客,他相跟着往一块凑,吃饭时也不晓得走。主人客套一句,他嘴里推辞着,凳子已随着屁股移到了桌边。日子久了,村人都摸住了他的脾性,都鄙视他,拐子三的酒源遂绝。
谁都以为拐子三就这么窝窝囊囊地过一辈子,没有想到的是,不期而遇的一件事,彻底改变了拐子三的命运。
那个春天的早晨,福生娘、六婶和几个嫂子正在老槐树下纳鞋底,嘴里张家长李家短扯闲话,正说到热闹处,就听得耳边一串“叮铃铃”的脆响。几个人惊诧地抬起头,才发现面前站着个穿制服的人,六婶认得,是乡里的邮递员,姓陈。
老陈一脸惶色,很着急地向大伙打听:豌豆角有没有叫李天东的人?几个人你看我,我看你,都摇头说没有。偏巧老村长拉牛打这儿过,连忙说:有这人有这人,拐子三就叫李天东。
——啊!一堆人这才恍然大悟。
老陈告诉老村长,有李天东的一封信,是从台湾寄来的,可能是他的什么亲戚寻亲来了。立马有人贼快地去喊拐子三。
果然好事!
拐子三请人念过信后,高兴得差点没晕过去。原来,他大难不死的老爹现在台湾,而且拥有一家工厂,是个千万大富翁。他在信中告诉儿子,他想在秋天的时候回来探亲,一偿多年思乡之苦。
这消息像一阵风,很快传遍了四乡八村。拐子三的七姑八姨表姐表弟得到信息,像赶集一样,纷至沓来,好不热火,把个豌豆角挤得踉踉跄跄。乡里分管统战工作的副乡长(据说是拐子三表姨的二女婿的大表哥的叔伯兄弟)听说情况后,也亲自来豌豆角过问此事。他很仔细地看过拐子三的食宿条件后,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不行不行,这绝对不行,就这条件,让老爷子回来看见了会咋想……副乡长的后半句话没说出来,但那意思人人都听得明白。
也难怪,这还是一间土改时分的土坯房,屋内潮湿阴暗,霉气冲人,灶台上,一片狼籍,残菜剩饭已发出馊味,唯一让人感到有生命力的,就是蚊蝇的嗡嗡声。
拐子三也曾多次找过村里要求换房,都被新上任的村长拒绝了。这回,副乡长发了话,当即,村里拿钱,乡里派车,买砖、运石、拉灰……不到半个月,两间新崭崭的砖瓦房落成了。
就这样,拐子三搭他尚没见面的老爹的福气,住进了豌豆角独一无二的青砖大瓦房,惹得一村人只嘬牙花子,好像在遗憾当初自己的老爹咋没被抓壮丁。随后,村长召开了村民大会。村长在会上强调说:从今以后,再听到谁喊拐子三,罚款三块。就这样,就连拐子三都差点忘记了的名字又重新叫响了。
“天东……”
“东哥……”
“东叔……”
“东爷……”
拐子三(应该叫李天东了,为行文方便,只好得罪)头顶的麻雀窝,不晓得几时搬了家,油光可鉴的头发服服帖帖地趴在脑门上;睡不醒的眼睛也配上了一副一百多块的变色镜,中山装取代了藏污纳垢的棉大衣,“人要衣装,马要鞍装”这句话可真是没错,此时的拐子三,起码年轻了十岁,而且还有股学者的派头。
热心的福生娘要为拐子三牵根红线,满以为是十拿九稳的事,谁想,拐子三竟一口回绝了:不成不成,咱这都半截子入土的人了,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还要个婆娘做啥?福生娘长叹一声,怏怏地蹀躞而去。下湾的朱媒婆寻上门来,鼓动她那如簧巧舌,任凭她说得天花乱坠,拐子三也毫不松口。
没有人喊拐子三抹牌了,接他喝酒的倒是每天不断。他每天吃了玩,玩了吃,嘴里常哼着不成调的曲子在村子里转悠。逢着星期天,拐子三便极力撺掇那帮半大小子们凑一牌局,却都不从,也不语,远远地站了,瞧。实在无趣,他便掏出身上的零钱逗孩子:……来,叫声爹,叫了我给钱!手中的镍币不停地抖动,哗哗直响。
孩子们并不眼热,婆娘们却直了眼:哪个不给是龟孙子!
喊了我就给。
叫,根儿,叫他爹,叫了拿钱去买糖吃。
叫根儿的孩子心说,这不是我爹呀!嘴里却已叫出声来:爹!
哎……!拐子三撇腔撇调地应一声,把钱丢给孩子,又去逗弄下一个。
若有调皮胆大些的孩子叫他一声“拐子三”,他眼一翻,嘴一努,骂道:日你娘,拐子三是你喊的么?我是你爷,你叫你爷拐子三?孩子们被他的怪模样唬住,再不敢喊。
豌豆角人都觉得拐子三变了个人,又不知道变在哪儿,一切似乎都在情理之中。
时光在无聊中悄悄遁去。一夜北风,地上像下了层树叶雨,老槐树又孤零零地立在那儿。在村人们的企盼中,拐子三的老爹没有回来,姗姗而至的是一封信。信中说,他由于风烛残年,最近又旧病复发,住进了医院,即便痊愈,只怕也受不了颠簸之苦,不能回来了……
拐子三似乎并不显得失望。感到失望的倒是乡亲们,一个个蔫头耷脑,好像是他们的老爹不能回来一样。
好几日,豌豆角难得听见大人孩子的笑骂声。偶尔,有谁家的孩子扯着嗓子刚哭出声,又像被猛然掐住脖子,倏地静了下去,间或有父母们火爆爆的呵骂夹杂其中。太阳白惨惨的,风也干燥燥的,似乎划根火柴就能点燃。好闷的天!
一转眼,冬天也就那么来了,匆匆地,慢慢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