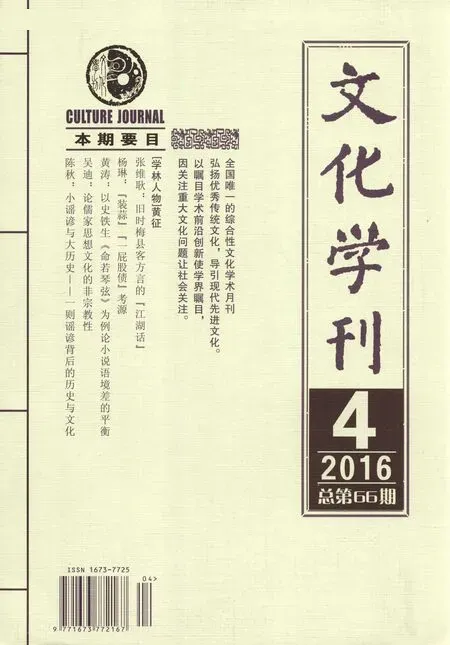黄征自述
——我与敦煌学研究
黄 征
【学林人物】
黄征自述
——我与敦煌学研究
黄 征
我与敦煌学,如果要追溯源头,那要回到1980年秋我在杭州师范学院中文系读本科的时候。我是杭师院第一届本科生,当时教学条件很差,我们经常搬个椅子到农田里看书,图书馆也没有几本可看的书。我大学一年级是做作家梦,但是看了王国维先生《人间词话》后觉得自己也属于不适合词章的人,于是就开始转入研究。我先是对现代文学感兴趣,《新文学史料》每期必买,鲁迅杂文反复研读,可是大二之后,我的学术兴趣从现代文学转到了古典文学,也就是我考上大学之前最喜欢的唐宋诗词之类,而当时张锡厚先生的《敦煌文学》小册子刚出版不久,我就买了一本坐在一间朝北的我称之为“北斗居”的宿舍床头阅读,感觉非常新鲜有趣。这是我最早受到的敦煌学启蒙吧,当时怎么也想不到后来竟一辈子从事敦煌学研究了。与此同时,为了弥补学校图书少的缺陷,我在中文系开了介绍信,经常骑半小时自行车到西湖孤山的浙江图书馆古籍部阅读古书,那里的图书管理员老朱师傅、陈华师傅不厌其烦地为我把一摞摞的线装书搬进搬出,诸如许国霖《敦煌杂录》、刘复《敦煌掇琐》、罗振玉《敦煌零拾》等,以及繁体竖排的新古籍如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敦煌曲子词集》、任二北《敦煌曲校录》之类,都是在那里才有机会阅读的。我一边阅读,一边翻卡片柜目录,把想读的书都做了详细的分类目录,逐渐形成了学科体系的基本概念。当时读的书其实目标不是很明确,有感兴趣的就借出来翻阅,多半属于浏览。不过敦煌的材料,尤其是敦煌曲子词的校勘解读,我完整抄录了好几种,包括朱祖谋《强村丛书·云谣集》、冒广生《新斠云谣集杂曲子》等,手抄本现在还保存着。我在孤山古籍部还遇到了现在已故的陈植锷先生,当时他正在撰写硕士论文,他问我看古书想做什么,我说主要是感兴趣而已,准备写一篇《六言诗初探》。于是他建议我考研,介绍我去找钱志熙,说钱志熙刚考取研究生,有考研经验,我可以去跟他聊聊。这样我后来与钱志熙(现任北大教授)成为朋友,几年后经过努力也考上了杭州大学研究生。
我1985年秋考入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生班。当时读书很清苦,尤其古典文献学,我们进门第一堂课,沈文倬先生就说做这个学问发不了财,但也饿不死,基本上靠国家养着,要耐得住寂寞。果然,有的同学觉得学这个没用,后来做了报社记者,还有的则改行当了律师,不过,我一直顶着家庭压力,孜孜不倦地读书学习,从未动摇。我觉得有那么好的导师条件,不多学点学问,实在太可惜了。我在1986年的时候,因为听了郭在贻先生的训诂学课和《说文解字》课,开始比较多地接触敦煌文献语言材料,做起了敦煌曲子词、王梵志诗和变文的俗字、俗语词研究,并到郭先生家里单独求教。郭先生给了我许多鼓励和指导,我当时写的每一篇论文都经过郭先生的批改审订,所谓“金针度人”,衣钵传授,终身难忘。1987年春,在郭先生家里,我见到了师兄张涌泉,当时张师兄正与郭先生商量合作校勘《敦煌变文集》的科研计划,张师兄提议可以与我一起在郭先生指导下来做这个合作项目。郭先生很高兴,觉得这个合作团队会很强。其实直到那一天我才知道我们将进行一场上规模的合作研究,我也才第一次与张涌泉师兄见面谈论。我不知道他从哪里听说我的研学状况,也许是从同学那里,也许是从郭先生那里,反正第一次见面他就认为我跟他合作能行,他说此前与一位女同学合作比较费劲。郭先生与张师兄都是急性子,在他们的带领下,我也慢慢加快了步伐。就在1987年这一年,中国训诂学会在富阳举行大会,会上王锳教授提议重新校对整理《敦煌变文集》,出版一个新本子,并且认为我们的三人组合是最强的。于是我们正式提出了“敦煌学三书”的计划,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快马加鞭研究起来。由于专心做学问,因此我毕业工作都没有去找,后来郭先生说不要找了,他建议我留校到中文系古汉语古典文献教研室任教。就这样,我成了郭先生与张师兄的同事,合作团队更加紧密,阅读敦煌写本缩微胶卷并撰写校释论文的速度快得惊人,以至于季羡林先生也很快看到我们的成果。1990年在北京举行敦煌学研讨会,我与季羡林先生都在语言组讨论,当我读完论文的时候,季老拿着我手写复印的论文问我:“你就是黄征啊?怎么是个小伙子,看论文我还以为是个七十多岁的老先生,心里奇怪怎么还有我不认识的老先生呢?”原来我们那时候写论文都跟导师学习,文章用的是浅白文言,老气横秋的,看不出是年轻人写的。季先生还对我毕恭毕敬书写的论文字体大为称赞,他说这真是你手写的吗?像是印出来的差不多。不仅季羡林先生给我们很多鼓励和奖掖,其它老先生也都对我们坐冷板凳的精神多有褒奖。记得2000年的夏天,饶宗颐先生路过杭州,通过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毛昭晰找到我,说到了杭州,就想见见几个人,其中敦煌学方面就有我。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饶宗颐先生,此前他主编的新文丰出版公司的敦煌学丛书邀请我出过一本《敦煌语文丛说》,书名是饶先生亲自改定的,序言是他亲笔书写的。他在序言里有对我的评价,也说了他与我的导师姜亮夫、蒋礼鸿和郭在贻先生的情谊。
我的写作能够称得上“文章”的,大概可以分类如下:一是诗词、散文,主要创作于中学毕业到上大学之际;二是古典文学、现代文学的研究论文,主要是大学期间所作,发表了一半,例如我的论著目录中的《六言诗初探》《绝妙佳词〈采莲曲〉》等;三是训诂校勘学论文,是硕士研究生期间才开始写的论文类型,例如《“爝火不息”解》《“踏破贺阑山缺”句法解》《“摄弊衣冠”的“摄”》《释“减”“仅”》等;四是敦煌俗文学作品与俗字、俗语词、俗音等的专题研究,是在1986年(硕士生的第二年)跟随郭在贻先生研习训诂学、敦煌语言文字学后开始写的,《敦煌陈写本晋竺法护译〈佛说生经〉校释》《敦煌文学〈儿郎伟〉辑录校注》《〈王梵志诗校辑〉商补》《王梵志诗校释商补》等一批论文像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这第四类的论文,可以说是一发而不可收,年年有余,以至于今。我一直认为我们古典文献专业的研究生,论文质量是比较上乘的,大多言之有物,而且实际投入的精力比许多学科的要多,可是我们一开始往往很不自信。我在第一次见郭在贻先生时就很不自信,问的第一个问题是:“我做训诂学研究会有成就吗?”因为我本科毕业于师范学院,研究生读的是研究生班(二年制),感觉比别人差一截。没有想到郭先生平时话不多,这次却足足花费了半个小时来打消我的自卑和疑虑,使我一下子“长高了”许多。在后来的岁月里,我一直很有信心,也很努力,眼看着从许多同学、同事身边走过,赶在了他们的前面,所以我至今念念不忘我的导师郭在贻先生,是他真正把我带上学术之路。我还记得1988年郭在贻师特别告诫我:“不要只成个敦煌学家。”我体会那意思,是要我不忘训诂校勘学的老本行,敦煌学对我而言只是跟训诂校勘学相关联的学科。后来,我一直遵循这个原则,即以训诂校勘学为根底,去研究、解决敦煌文献中的问题。事实上也证明,从敦煌学到敦煌学是很容易流于浮浅的,研究者应该各自以本专业的优势来钻研敦煌学,使敦煌学的发展不断向纵深发展,同时也不断拓宽其研究领域。
说到我的老师,我真觉得很幸运。在我读大学本科阶段,后二年我特别喜欢古典文学,杭州师范学院的樊维刚、罗仲鼎先生给了我很多的指点,并且也使我逐渐留意训诂知识。1985年,我进入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研究生班,由于是个七个人的班,而且学制二年,导师不固定,所以第一年全靠自己摸索。不过我也因此感到很幸运:姜亮夫先生是我们挂名导师,沈文倬、刘操南、龚贤明、郭在贻、张金泉等都是我们的任课教师,而且还邀请了数学、建筑学专家沈康身先生给我们上古典建筑史,不仅很开眼界,而且结识了比别人多的老师。我们的毕业论文指导是由自己选择导师的,我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郭在贻先生指导,所以真正给我直接指导的是郭在贻先生。当然,我也广泛钻研其它先生的著作,尤其是姜亮夫、蒋礼鸿先生的著作,他们都是敦煌学的著名专家,也都是文字、音韵、训诂学家,而且还都是书法家。两年学习后我顺利毕业,并且在郭在贻先生的推荐下留校到中文系工作,第三年在工作岗位上通过论文答辩(当时对研究生班的特殊规定)。1989年,郭在贻先生因病去世。1990年,我在没有人愿意读博士学位的情况下,考取蒋礼鸿先生指导的汉语史训诂学方向博士生,因此,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先生都是我的导师。我之所以以训诂校勘学为根底,而又从事敦煌文献、敦煌语言文字学研究,是直接受到了三位导师的影响。
1990年,我在职考取蒋礼鸿先生指导的汉语史训诂学博士生,并且受导师影响加入了九三学社。我的导师蒋礼鸿先生夫妇、郭在贻先生、洪湛侯先生,还有师兄颜洽茂先生,我们同在中文系古汉语古典文献教研室,都是九三学社社员。蒋先生对我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我大概1981在杭师院读本科的时候就与傅杰同学一起跑到杭州大学蹭课,听过蒋先生的古代汉语课程。当时蒋先生正襟危坐,声音清亮,教室鸦雀无声。不过当时我再也没有想到十年后能够成为蒋先生的入门弟子。因为我们那时候觉得蒋先生辈分太高,不敢叨扰老先生,所以也就只能蹭蹭课而已。蒋先生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是指引我学术道路的明灯,他以精湛的考证与缜密的推理折服了我,我想我一辈子都达不到那个高度,不过,我们在《敦煌变文校注》等著作中,亦步亦趋,用同样的方法,却也取得了可观的成绩。蒋先生的理论研究似乎没有多少文字,但是实际上都贯穿在一字一词一句的考证解读中了。他的汉语史研究一纵一横两条线索的理论,看起来就几十个字,但是却远远超过有的人洋洋洒洒数百万言的专著。他的关于中国俗字研究的导言,虽然只是一篇论文,而且发表后很久被人遗忘,现在看到真是远见卓识,甩人半个世纪。他的训诂研究“释义”“通文”“解惑”“溯源”四个层次理论,对我也很有启迪意义,我在做研究时也总是力图做到不独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蒋先生严谨的科学精神,我觉得一方面来自干嘉学派的考据传统,一方面来自九三学社民主与科学的思想理论。我在这两方面都受到了熏陶。
最近浙江大学出版社约我出一本《敦煌语言文献研究》,收入我前十年在浙江的研究成果。文集中的《敦煌写本整理应遵循的原则》,分别强调了“尊重原卷”“不掠人之美”、“寻求确证”“精通写本文字符号系统”四个方面,是我自己努力遵循的原则,也是给其它研究者的参考和友情提示;《敦煌写本异文综析》分别对“因字形关系而引起的异文”和“因字音关系而引起的异文”“因词义关系而引起的异文”作了举例分析,实际上表达了我对俗字、俗语词、俗音等的基本认识,是我后来研究这些问题的立足点。我的文章谈宏观问题的比较少,所以这两篇只反映了我的一些主要观点。《敦煌变文释词》《敦煌俗语词辑释》等文,是我在训诂学上的部分成果,力求做到符合“有所发明”“无征不信”的原则。这方面的更多成果,我主要融会在《敦煌变文校注》等大部头的著作中了。《“踏破贺兰山缺”——近代汉语中的一种特殊句式VC1 + N + C2》是我在敦煌口语语法研究方面的努力,堪称“训诂式的语法研究”。我在这方面成果不多,但是很特别,引起许多语法研究者的浓厚兴趣。《敦煌俗音考辨》开辟了敦煌俗音方面研究的新路子,分别归纳出“秀才识字读半边”“字音不正读别字”和“音义乖互读又音”三个俗音生成的模式,《语言学年鉴(1994)》曾经予以关注。《王梵志诗校释商补》等是我硕士学位论文的主要内容,后来又完成《王梵志诗校释补议》,是对晚出诸书的补订和商榷。《〈敦煌歌辞总编〉校释商榷》等是我在敦煌歌辞校勘方面的见解,《辑注本〈启颜录〉匡补》《〈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匡补》等是我对于几种重要敦煌学著作在校勘、训诂等方面的订补意见。另有《〈敦煌愿文集〉辑校中的一些问题》分别探讨了敦煌愿文的性质、价值和辑录整理的必要性,《敦煌愿文的整理和结集》叙述了《敦煌愿文集》收集的范围、编辑的体例和主要内容,是我开辟敦煌愿文研究的重要计划细节;《敦煌愿文考论》等篇,着重探讨了敦煌愿文的名义、篇名、范本及其术语,都是具有开创性的研究。《敦煌愿文〈儿郎伟〉辑考》等篇,首次完整校录全部敦煌本《儿郎伟》作品,并对其中民俗、历史、语言、文学等方面的问题进行探索,后来广为学者们引用,饶宗颐先生在为《敦煌语文丛说》作序时曾说“犹喜继起有人,黄君征以整理《儿郎伟》有声于时,其尤杰出者也”。《敦煌陈写本晋竺法护译〈佛说生经〉残卷P.2965校释》是我在敦煌佛经的校释、考证方面的初步尝试,也是我发表的第一篇敦煌学论文,重点是考证其中的俗字、俗语词。该文以原文校释的形式出现,出版社的编辑当我面就表示颇为不屑,但是郭在贻先生却大加称赏,说“用来作为毕业论文也完全够了”,对我真是莫大的鼓励。
2016-3-22
【责任编辑:王 崇】

汉 白虎纹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