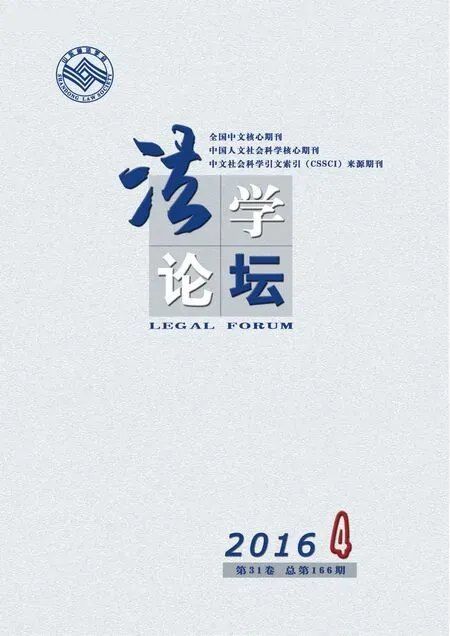欧洲人权法院对艺术表达自由的规制
——以争议艺术判例为切入点
[英]魏 华
(山东大学 法学院,山东济南 250100)
欧洲人权法院对艺术表达自由的规制
——以争议艺术判例为切入点
[英]魏华
(山东大学 法学院,山东济南 250100)
摘要:欧洲人权法院对“裁量余地原则”的保守理解以及对艺术作为特殊表达方式的缺乏认同,导致它屡次丧失为表达自由、尤其艺术表达自由明确更宽容规则的机会。相比它对所谓不道德及涉及宗教艺术表达的苛刻对待,它对带有政治意图艺术表达的另眼看待和绝对保护给人以不同形式的表达自由有高低贵贱之分的错误印象。对现代艺术的潜意识排斥、对缔约国人权进行实质监督和强制管辖意愿的缺失,使欧洲人权法院在表达自由裁判上坚守着保守立场。
关键词:欧洲人权法院;争议艺术;裁量余地原则;表达自由
“表达自由”是人类最基本的权利之一,是人格及自主性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常被简单等同于“言论自由”,但严谨地说,前者比后者更全面地诠释了以自由表达个人观点及意愿为目的的权利,除了通常理解的“言论”外,还有多种其他行使这项权利的方式,比如通过诗歌、美术、舞蹈、歌曲、照片、影像作品等表达情感或思想。换言之,艺术,是表达自由很重要的一种行动方式。要对艺术表达予以恰当的法律保护,无疑需要对“艺术”的定义、范畴及表现方式有所了解,以明确保护对象。但这恰恰是问题所在:艺术难以界定——什么是艺术、什么行为是艺术表达、艺术的好坏优劣标准历来众说纷纭。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包括但不仅限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休谟、康德、叔本华、黑格尔、尼采、佛洛依德、海德格尔、本雅明等等——都对艺术的本质是什么、艺术表达为了什么、审美标准如何制定等核心问题做过详细探讨,但观点却大相径庭。*参见Thomas E. Wartenberg, The Nature of Art: An Anthology, 3rd edition, Cengage Learning, 2011.可见该领域问题之深奥和复杂。尤其是进入后现代艺术时代,有争议的超出传统艺术内涵与范围的作品纷纷出现,艺术的界定更加困难。
艺术作品通过文字、颜色、画面、声音等向外界传递信息,表达观点——不仅表达美学的、艺术的观点,也可用来表达政治态度和立场,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途径与方式。但艺术表达自由却是最不受人权学者关注、保护最不完善的一种表达形式,无论是国际人权法条,还是区域人权判例,对它的保护都可用“吝啬”来形容,其国际地位与言论自由(尤其政治言论自由)毫无可比性,不可同日而语。虽然欧洲人权法院曾明确表示,不同表达方式不分主次、不分等级、同等重要,*Thorgeison v. Iceland (1992) 14 EHRR 843.但其判例所揭示的现实却与之截然相反:除了仅有的个别例外,*Karata v. Turkey [1999] ECHR 23168/94. 文章第三部分会对该案进行详细分析,阐述其作为艺术表达自由领域在欧洲人权法院唯一胜诉案的理由。“艺术表达自由遭到侵犯”这一申诉理由几乎从未在欧洲人权法院胜诉过。本文以《欧洲人权公约》为背景,以人权法院相关判例为切入点,分析其规制艺术表达自由的具体理由及方法,探究在欧洲人权体系中保护艺术表达自由的难点所在,探讨改进方法。
一、艺术表达的本质功能及限制原则
艺术表达自由在国际、区域、国内法律体系中,是作为“表达自由”或“言论自由”的一个组成部分抑或文化权利的一种得以直接或间接受保护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这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第27条规定人人有权参加社会文化生活和享受艺术,所创作的科学、文学或美术作品所产生的精神、物质利益应受保护。*http://www.un.org/zh/universal-declaration-human-rights/index.html. 最后浏览日期:2015年12月27日。《欧洲人权公约》是欧洲最重要的人权文件,也是世界上第一份区域人权公约,其第10条第1款规定人人享有表达自由,包括保持主张的自由,以及在不受公共机关干预和不分国界的情况下接受并传播消息和思想的自由;但第10条第2款也明确阐述了言论表达自由并非无界线,而是受成员国法律所规定的程序、条件、限制或惩罚所约束,受在民主社会中为了国家安全、领土完整或公共安全利益,为防止混乱或犯罪,保护健康或道德,维护他人的名誉或权利,防止情报泄漏,或者为了维护司法权威与公正性所需要的约束。*http://www.coe.int/web/human-rights-convention. 最后浏览日期:2015年12月27日。在欧洲人权保护框架体系中,履行公约责任、保护人权的义务由各缔约国承担,欧洲人权法院予以监督,在一定程度上可实施强制管辖。自1998年起,人权法院开始实施个人申诉管辖权,任何自然人、非政府组织或个人团体如果认为自己的公约权利遭到了来自国家公权力的侵害,且申诉案件的国内救济已经穷尽,均有权直接向人权法院提起申诉,缔约国不得以任何形式妨碍这项权利的行使。一旦受理,人权法院会根据《欧洲人权公约》的根本宗旨和具体条款,重新审理涉案缔约国法院的相关判决。*欧洲人权法院也审理缔约国对缔约国的指控。这不属于本文范畴。遍览以艺术表达自由为诉因的判决,我们会发现,“对道德的保护”往往是此类案件的主要争点和司法裁判的主要依据。需要追问的是:限制艺术表达自由的道德标准是否充分考虑了这一表达形式的特殊性?进而要追问:限制艺术表达自由的道德标准底线如何划定?
用法律规制艺术表达、为艺术表达方式及内容划定所谓道德底线的难点归根结底来源于艺术的本质。哲学家们尝试用三种不同路径探索艺术本质问题:*参见Thomas E. Wartenberg, The Nature of Art: An Anthology, 3rd edition, Cengage Learning, 2011, p.8.第一种最普遍,即给艺术下定义,回答“艺术是什么?”。这一源于亚里士多德的“本质主义”路径认为艺术的本质特征可从理论角度加以界定和分析,世间多样的艺术形式其实都有共同的本质或本性,可以归入同一概念和理论系统;判定某件物品是否艺术品,只需要找到这种本质特征。随着20世纪早期分析哲学的兴起,哲学界开始用“分类方式”和“评价方式”判断艺术,前者用以区分艺术和非艺术,后者用以界定好艺术和不好的艺术,但现实中二者并不总容易区分开来。
与“本质主义”相对立的第二种探索艺术本质的路径,是兴起于20世纪后半叶的“反本质主义”,它从根本上质疑定义艺术的可能性。理论家们用现代艺术、后现代艺术的例子来说明艺术的本性决定了它不可界定:追求新奇、挑战传统是现代艺术的主流价值观,艺术家们竭尽所能、持续不断、以多种多样的表达手法冲破传统界线、挑战信念、表达自己的观点。在这个后现代主义时代,一根斜靠在美术馆墙壁上的竹竿是“艺术”;用一亿颗手绘陶瓷葵花子铺满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1000平方米展厅的地板是“艺术”;马塞尔·杜尚在一个工厂批量生产的小便池上随意签上一个名字,并将其命名为《泉》后送去展览,也是“艺术”。*参见Susie Hodge, Why Your Five Year Old Could Not Have Done That: Modern Art Explained, Thames and Hudson, 2012. 该书对颠覆传统的现代艺术作品进行了选择性展示和分析。此外,后现代艺术还强调行动与参与,由此派生了多种多样、新潮迭出的行为艺术、观念艺术、装置艺术等等新的艺术表现手法,使艺术不再是静观的、以艺术家为主导,一切都在参与者的行动中得以生成、进行、变化、不断产生新的景观和意义。*参见陈旭光:《艺术为什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2页。这正是艺术、尤其现代及后现代艺术与一般表达、言论的不同之处——前者更多样,界线更模糊,方式更多,影响亦更不可预测和控制。可见,现代及后现代艺术和柏拉图所定义的“模仿”不再有丝毫关系。这些从根本上对本质主义和传统艺术表现手法的挑战和冲击,是否意味着艺术哲学理论作为分析工具已全然失效?如果是这样,我们又该如何理解“艺术”? 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保护的“艺术表达自由”到底是谁的自由、什么样的自由?
这些问题指向源于黑格尔的第三种思想路径:艺术会在不同的历史、文化、社会和政治背景中经历一系列的发展阶段,因此人们既不该试图去给艺术下一个一成不变、单一而抽象的定义,也不必去过分纠结艺术的具体内容,而应专注于艺术的社会角色、它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它的目的、以及社会条件的改变对艺术本质的改变所起的作用。*参见Thomas E. Wartenberg, The Nature of Art: An Anthology, 3rd edition, Cengage Learning, 2011, p.11.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所广泛持有的观点,对他们而言,理解艺术在具体时代背景下的实际功能——即“艺术为了什么”、“艺术的目的是什么”——远比知道它该叫什么、是什么要重要。
文章第二部分的案例会揭示,正是这第三种路径所强调的艺术强大的社会功能和目的,使“艺术表达”成为需要法律规制的对象,而这种社会功能的原动力则来源于艺术传统和基本观念的变化甚至颠覆。传统认为,艺术和日常事物不沾边,完全分离,高高在上并因此具有欣赏价值,尤其应与政治划清界限,否则即是对崇高艺术的侵犯和亵渎。而自上世纪60年代起,西方艺术开始进入一个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发展阶段的革命性时代,艺术家们开始不再让艺术有别于生活,而要让它跟生活一样真实、普通、不完美;他们开始以最普通的日常俗物为素材进行艺术创作,不再重视艺术的外表和观感,是刻意要把艺术从高贵的地位上拽到现实中来,最真实直白地表达想法,反映生活——由此,艺术成为观点表达,新兴艺术实践(比如上文提到的杜尚的《泉》)对传统艺术理论的无情抨击和全面挑战,使得观者在不安、嘲讽和质问“这也叫艺术?!”的同时,不知不觉地、自愿或被迫地开始重新思考艺术基本概念、范畴、欣赏标准和功能作用。
正是在这样的变化中,艺术开始与现实密不可分,开始反映现实中的黑暗和不公,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哈贝马斯说艺术能满足人们被解放的意愿,从不必要的、压迫性的社会文化传统和政治束缚中解脱出来。无论这种意愿是否正当合理,有的貌似挑战的行为也未必是有意识的,但既然要“解放”,就需要有意或无意地挑战已经固化的社会准则和底线,甚至站在社会的对立面谴责和挑战主流思想和行为准则——正是在这种情境中,艺术表达会产生争议、冲击社会传统、挑战传统道德、不为社会所容,社会将以“保护道德”或“维护和平氛围”为名限制和压抑这种挑战。但规制不当、规制过度,即侵犯艺术表达自由。
自由都有不可逾越的界线,但界线该划在哪里导致了不休的争论。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用他的“伤害原则”(the harm principle)为自由划定了边界,其实也为艺术表达自由及其规制划定了边界: “人类之所以有理有权可以个别地或者集体地对其中任何分子的行动自由进行干涉,唯一的目的只是自我防卫。这就是说,对于文明群体中的任一成员,所以能够施用一种权力以反其意志而不失为正当,唯一的目的只是要防止对他人的危害。若说为了那人自己的好处,不论是物质上的或者是精神上的好处,那不成为充足的理由。”*[英] 约翰·密尔:《论自由》,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0、11页。也就是说,政府和社会限制艺术表达自由的唯一合法理由,是防止它对“他人”造成危害;艺术表达的公共性又决定了“他人”所指的并非独立的个人,而是整个社会群体;且“危害”所指的并非身体上的伤害,而是心灵上的、道德上的。
欧洲人权法院在审理涉及艺术表达自由的案件时明显使用“伤害原则”(尽管下文案例揭示出它对该原则的理解和使用有前后矛盾之处),并依次考察对涉案艺术表达的限制是否符合以下三个条件:(1)涉案艺术表达违反了明确的国家法相关规定;(2)当局限制表达的目的合理合法;(3)该限制在一个民主社会是必须的。下文将注意力集中在欧洲人权法院对两类艺术表达形式的分析和判决上,一类是所谓不道德的艺术表达,另一类是带有政治目的、抒发政见的艺术表达。
二、裁量余地原则及对艺术表达的道德审判
“裁量余地原则”(margin of appreciation)是人权法院在审理该领域案件时与“伤害原则”配套使用的一个国际人权法通行原则,也是能够准确阐述人权法院和各缔约国关系的一个核心概念。就艺术表达自由来说,各缔约国因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等原因和环境的差异,对艺术、道德、艺术与道德的关系、道德标准、保护道德的方式等有各自不同的理解。为表达对差异的尊重,也为避免过度干涉缔约国主权,人权法院在判例中遵从“裁量余地原则”,给予缔约国充分的空间和自由去根据国情制定限制自由、规制行为的标准和方法,以避免过度干预。在涉及争议艺术表达触犯主流道德底线的案件中给予缔约国的自由度尤其大。这种做法一方面体现了对国家主权的尊重,使区域人权机构的监督和“干预”在政治上得到主权国家认可和接受;但另一方面,起码在艺术表达自由领域,这种做法也助长了缔约国的家长作风,为墨守成规提供了理由,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人权法院监督、解释公约和指引方向的功能。下文案例会揭示:欧洲人权法院在比较棘手的艺术表达自由裁判问题上,当涉及道德时,已形成了尽量不推翻缔约国法院判决的习惯。这一规律的出现,貌似可以将其归因为缔约国多是法治健全、尊重人权的发达国家,它们的法庭判决通常已根据本国特殊性尤其对道德标准的理解做过公正的利益平衡。但如果我们深入到这些判决的背后就会发现这一解释可能仅是表层的,在更深层次上法院的保守判决是源自法律人对艺术缺乏了解所导致的;尤其是艺术与法律在思维方式和表达路径上的格格不入,使得无论是缔约国法院还是欧洲人权法院在面对争议艺术表达形式时都容易基于“公共安全利益,防止混乱或犯罪,保护健康或道德”等理由进入道德审判误区,从而丧失因应社会发展变迁更主动、更准确、导向性更明确地阐释、发展公约权利的机会。
Handyside v. United Kingdom (1976)案*Handyside v. United Kingdom ECHR A 24 (1976) 1 EHRR 737.是欧洲人权裁判领域的一个经典案例,原因在于判词第49段对表达自由做出了方向性阐释:“表达自由不应只适用于那些获得好评的、不得罪人或者无关痛痒的信息或观点,也应适用于那些得罪人的、甚至让人感到惊讶和不安的信息或观点。”*“Freedom of expression […] is applicable not only to ‘information’ or ‘ideas’ that are favourably received or regarded as inoffensive or as a matter of indifference, but also to those that offend, shock or disturb the State or any sector of the population.”欧洲人权法院虽然阐释了表达自由的真谛,但最终并没有做出支持申诉人的裁决。本判决由于阐释了表达自由原则和“裁量余地原则”而成为一个备受关注与广泛引用的经典,所以在进入争议艺术案例讨论之前首先需要就此案例作一介绍和分析。本案申诉人是备受争议的《小红教科书》(The Little Red Schoolbook)的英国出版商。这本由两位丹麦老师写给未成年人的作品,鼓励孩子们质疑、挑战社会成规,并指导他们具体如何去做,尤其如何在学校里挑战成年人的权威,伸张自己的权利;此外,该书200多页的篇幅中有26页讲授性知识,30多页涉及毒品和酒精。不难理解,自出版之日起该书就遭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抨击和批判,瑞士一度禁止该书进口,法国和意大利亦把它列为禁书,希腊出版商因出版此书而坐牢,教宗批评此书不道德。英国法院依据《淫秽出版物法》(Obscene Publications Act 1959)要求英国出版商立刻停止发售该书,并予以罚款,同时收缴所有出版物及相关宣传品。*但英国政府后来允许了删节后的第二版的出版。法庭上的专家证人并未一致认定该出版物的内容必然会使人腐化堕落,也不否认书中有正面的、以传授知识为目的的内容,但考虑到书中正面内容与大量儿童不宜的内容掺杂在一起,而书的意向读者是正处于特殊成长时期、缺乏判断力的未成年人,且书的公开出版导致受影响的孩子会很多,所以法庭作出了上述判决。上诉法院维持原判后,英国出版商以《欧洲人权公约》第10条赋予的表达自由遭到侵害为由,将案子申诉至欧洲人权法院。
欧洲人权法院以13比1维持英国法院的判决,认定英国为“保护道德”而对申诉人表达、出版自由所设的限制没有超出《欧洲人权公约》第10条第2款允许的范围,因此没有侵犯公约权利。法院强调,欧洲没有统一的道德标准,各缔约国有滋生于各自传统和文化的道德标准和底线,因此各国保护道德的相关法律法规亦各不相同,当然也不会一成不变,而是会随着时间推延及社会发展不断更新。缔约国相关机构和法院与社会有直接、持续的接触,对本国文化所赋予道德的内涵、它的演变及社会认知的转变更加敏感,理解更加透彻到位,因此比人权法院的国际法官们更有资格判断某一表达方式是否触碰了道德底线,是否应该合理限制。
这一判决理由无疑是“裁量余地原则”的最充分体现。但笔者认为法院强调的判决理由实质上是一种不必要的驳回申诉的托词。欧洲人权法院实质上是自我放弃了在类似案件上的实质审查权,这与《欧洲人权公约》精神和设置欧洲人权法院的初衷显然不一致。在此类案件中,作为缔约国的申诉人恰恰是认为在缔约国遭受了国内陈旧、过窄道德标准的不当限制,才申诉到欧洲人权法院,申诉人认为国际法官们置身于缔约国之外,受缔约国道德标准影响较小,在道德问题上地位、态度相对中立,期盼他们能依照《公约》推翻缔约国过窄道德标准的不当限制。所以,笔者认为《小红教科书》一案的关键点不在于上述理由而在于表达的对象、传播和影响范围,如果《小红教科书》的意向读者不是还在学校读书、好奇心强、理解能力有限且自我保护能力有限的孩子,判决未必会是如此;而且如果它在被禁前没有热卖,即影响范围如果不大,判决也可能不同。
但X Ltd and Y v. United Kingdom (1982)似乎证明了针对某个特定人群所进行的、传播范围极窄的艺术表达并不能幸免,此案是艺术表达与亵渎宗教交织在一起的一个案件。在本案中,申诉人X和Y分别是英国同性恋杂志Gay News的出版商和编辑,他们在其中一期杂志上刊登了一首描写想象中耶稣生前和死后同性性行为细节的诗,并附有一张插图予以形象展示。英国法院尽管认定X和Y没有亵渎神灵的主观意愿,但依然判处X和Y亵渎诽谤神教罪(blasphemy)成立并依法予以处罚,二人上诉但被驳回,于是向当时的欧洲人权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 of Human Rights)提起申诉,抗议英国侵犯了《欧洲人权公约》第九条赋予他们的思想和宗教自由,以及第10条赋予的表达自由。
但人权委员会认为英国法院的相关判决没有侵害申诉人的公约权利,并提出当审视缔约国法院判决是否违反《公约》时不仅应参照列举限制公约自由合法理由的《公约》第10条第2款,还应参照第7条,即任何人的行为在其发生时如果依据国内法或国际法不构成刑事犯罪,不得被认定为刑事犯罪。而人权委员会认定,X和Y的行为依照英国法律已构成刑事犯罪,且国家保护人民宗教情感不受不当攻击的义务决定了英国法院的判决是适当且必要的,并未超出第10条第2款所规定的范围和尺度。
值得商榷的是,在认定保护人民宗教感情不受伤害为限制表达自由的合法理由时,人权委员会似乎并没有仔细斟酌这首诗的影响范围: Gay News是个发行量很小、读者仅限于同性恋人群、没有任何影响力的杂志,有宗教信仰的信徒去翻阅这本杂志从而遭到这首诗和插图冒犯和伤害的概率基本为零,即密尔“伤害原则”中所讲到的“对他人造成伤害”的几率基本为零。此外,人权委员会也没有考虑诗歌作为艺术表达形式的特殊性,即它所描述的并非事实,而纯粹是为了用文艺的描述手法形成一种氛围以激起读者的一种反应,类似对幽默作品的反应。
另一个关于艺术创作亵渎诽谤神教的争议判决,是Choudhury v. United Kingdom (1991)案*Choudhury v. United Kingdom (1991), (17439/90) 12 Human Rights Law Journal 172.。英国穆斯林公民Choudhury要求英国法院以亵渎诽谤神教罪处理著名幻想型小说《撒旦诗篇》的作者拉什迪和出版商企鹅书店,因为该书亵渎了伊斯兰教和先知默罕默德。但英国法院予以拒绝,并指出英国的亵渎神教罪只适用于基督教,不保护伊斯兰。欧洲人权委员会支持英国法院的判决,认定它没有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第9条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规定。虽然此案只涉及《公约》第9条,它对第10条的适用也有深远影响,因为它的导火索是一本小说,属于艺术创作表达自由的范畴。假设申诉人不是穆斯林而是基督徒,申诉理由是一本小说亵渎了基督教,那么人权委员会就需要判断一本建立在幻想之上、杜撰的但却无疑映射事实的艺术作品从理论上能否构成亵渎神教罪。可见,欧洲人权法院支持英国法院判决的根本原因在于英国国内法“亵渎神教罪”罪名的特定性。
同样,Müller and Others v. Switzerland (1988)案*Müller and Others v. Switzerland 13 EHRR 212 (24/5/1988).也涉及到规制艺术表达自由到底是要保护谁,保护什么,以及保护到什么程度的问题。第一申诉人是位画家,在另外九位申诉人筹办的一次画展中展出了三幅画。瑞士当局在接到两宗投诉后认为画作淫秽、对观者构成道德上的冒犯,并以此为由没收了画作并处以罚款。欧洲人权法院在判决中虽然承认社会道德观念在近些年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但画作中对性行为、尤其人兽性行为的粗野刻画和展示依旧会冒犯拥有正常敏感程度的主流人群的性道德观,所以认为瑞士当局的处理理由成立,遂以6比1判决申诉人败诉,判定瑞士没有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第10条。这一判决体现了人权法院对裁量余地原则的坚守。但需要强调的是,这次画展所展出的争议画作并没有引起社会舆论的激烈冲突,恰恰相反,媒体完全是一边倒地站在画家一边。此外,涉案画家一直在瑞士其他城市展出类似画作,从未引起当局类似的干涉和禁止。可见,这三幅画对所谓社会道德的冲击并没有强烈到需要禁止的地步。再说,这三幅画作是在一个有限的空间、有限的时间段内被展出的——为期仅两个月的画展——因此能看到它们的人数极为有限,来参观者也通常会是艺术家或爱好者,他们没有普通人那么容易被争议艺术表达所冒犯。但遗憾的是,法院并没有充分考虑这些因素。
Otto-Preminger Institute v. Austria (1994) 案*Otto-Preminger Institute v. Austria (1994), 19 EHRR 34, [1994] ECHR 26. 类似案例还有Wingrove v. United Kingdom [1997] 24 EHRR 1。是涉及影视艺术作品的一个重要案例。申诉人在奥地利城市因斯布鲁克经营的艺术影院准备上映一部名为《爱的盛典》(Das Liebeskinzil)的争议影片,并在事先发布的宣传资料中将影片目的描述为“以讽刺手法揭示基督教信仰的荒谬”和“研究宗教信仰和世俗压迫机制之间的关系”。影片将上帝描绘成一个糊涂愚蠢的人,将耶稣和圣母玛利亚均塑造成了智力不健全的人。天主教会提出抗议,奥地利当局在电影上映前将其收缴。奥地利法庭认为收缴影片的做法是适当的,因为影院犯了奥地利刑法中的“贬低亵渎宗教教义”罪,尽管《奥地利基本法》(Austrian Basic Law)第17条a款明确保护艺术表达自由。欧洲人权法院维持了奥地利法院的判决,认为当局为维护人民宗教感情可以依法限制对宗教进行无理攻击的电影的播出。尽管奥地利是个保守的天主教国家,这个判决还是令人有些意外。这部影片被它的发起人明确定义为“艺术电影”,只在小众的“艺术影院”内小范围上映,观众极为有限。这就如同画展中的画作,只有那些专门为了欣赏艺术作品的人才会自主选择走入特定的艺术场所,他们通常有特定的审美标准、心理、态度和观念,对“冒犯”、尤其艺术产生的“冒犯”有非主流的理解和驾驭能力;任何有强烈宗教信仰、不希望看这部影片的人,都不可能看到它,即密尔“伤害原则”中所讲的“对他人造成伤害”的几率很小;而一部能够“贬低亵渎宗教教义”的影片需要有一定的曝光度和收视率,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是“公害”。
欧洲人权法院在艺术表达亵渎神教领域的保守在I.A. v. Turkey (2005)案*Unreported, decision of the European Court on 13 September 2005.中得以延续。申诉人因其出版的小说中提到先知默罕默德不禁止人尸交和人兽交而被土耳其法院判处两年徒刑,后改为罚款。人权法院在判词中强调对“挑衅性语言”和“谩骂攻击”要予以区别,前者应被容忍,后者应被限制,并与土耳其法院观点一致,认为此书的部分内容已超越表达自由的底线,伤害了穆斯林的宗教感情。因为土耳其当局并未收缴出版物,而只是对申诉人进行了少量罚款,人权法院以4比3判定土耳其当局的做法适当,并未侵犯《欧洲人权公约》第10条中的表达自由权。
人权法院对“挑衅性语言”和“谩骂攻击”的区别在Tatlav v Turkey(2006)案*Unreported, decision of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on 2 May 2006.中亦起了决定性作用。申诉人因其出版的一本书中阐述了宗教以神灵的名义使一切社会不公合法化的观点而在土耳其被判刑。人权法院一致判定土耳其当局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第10条,因为该书只是对宗教进行严厉批判,并没有进行谩骂攻击,尽管信徒们可能会被这些尖刻评论所冒犯,但那不足以构成限制申诉人表达自由的理由。影响人权法院判断的另一重要原因是该书的前四版并未被当局禁止,第五版因遭到一个人投诉而导致当局启动司法程序。
近年来欧洲人权法院似乎对艺术作为一种特殊表达方式的认同感有所加强,态度有所转变。在Alnak v. Turkey (2005)案*http://www.rtdh.eu/pdf/alinak_c_turquie_20050329.pdf . 最后浏览日期:2015年12月28日。中,一位土耳其前议员撰写了一部描写土耳其东南部舍尔纳克省一村庄的村民被当局以酷刑对待的小说,遭到土耳其当局收缴并禁止发行,因为书的内容煽动民族仇恨和地域歧视。欧洲人权法院认为申诉人的出版物虽然是杜撰的小说,但含有不少现实的内容,杜撰与纪实边界不清晰,从字面上理解很可能导致对抗情绪甚至暴力事件,尤其在安全局势严峻的土耳其东南地区更是如此。但要判断它在现实中是否真会导致恶劣影响时,人权法院强调涉案的表达方式是一本小说,与大众媒体相比所面向的是一个窄得多的公共空间,传播范围有限。而《欧洲人权公约》第10条不仅保护表达的实质内容和具体信息,也保护表达的具体方式。申诉人的作品虽然是根据真实事件所著,但归根结底是一本小说,土耳其当局对该艺术作品的禁止和处罚不符合《公约》第10条所允许的限制条件,对申诉人文化权利及表达自由的干涉与当局所追求的目的不成比例,侵害了申诉人公约权利。*https://wcd.coe.int/ViewDoc.jsp?id=862667&Site=COE. 最后浏览日期:2015年12月28日。与此案十分类似但判决结果相反的是Lindon, Otchakovsky-Laurens and July v. France (2007) 21279/02, [2007] ECHR 836——因为涉案小说中涉及真实人名及事件的内容过多,导致小说已不为小说,人权法院认定法国法院判处申诉人诽谤罪的做法并未侵害其《公约》第10条权利。
同样,在Vereinigung Bildender Kunstler v. Austria (2007)案*(2008) 47 EHRR 189.中,维也纳一个美术家协会在100周年纪念展览上展出了一幅奥地利画家Otto Mühl的画作,这是一幅34位名人的集体照,其中包括德兰修女、奥地利红衣大主教以及几位奥地利自由党政客——均是裸体且正在进行性行为。这幅画在奥地利引起很大争议,后被一位观众泼红油漆破坏。1998年6月,画作中被作为原型嘲弄的其中一位自由党政客Meischberger将美术家协会告上法庭,指控这幅画不仅侵犯了他的肖像权,还侮辱贬低了他的政治身份。在一审败诉后,奥地利上诉法院和最高院做出裁决,永久禁止美术家协会展出这幅画,并要求他们对Meischberger进行经济赔偿。美术家协会向欧洲人权法院提起申诉。*https://wcd.coe.int/ViewDoc.jsp?id=1086359&Site=COE. 最后浏览日期:2015年12月28日。人权法院同意该画的确粗暴地描绘了Meischberger,但同时强调该画是一幅讽刺漫画作品,是艺术表达及社会评论的一种正当方式。此外,该画并不涉及Meischberger真实的私生活,而是指向他作为政治家的社会生活,可被理解为画家对其政党的抨击。再说,在Meischberger提起诉讼前画面就已被泼上红油漆,他已被完全覆盖,写照已不复存在。最后,人权法院认为奥地利法院的禁令不限时间和空间,太过严苛,与其所欲达到的目的不成比例,最终判定美术家协会的《公约》第10条所赋予的表达自由受到了不当干扰和侵害。
从以上这些代表性案例可以看出:第一,总的来说,《欧洲人权公约》作为捍卫艺术表达自由的盾牌在欧洲人权法院的作用是有限的,因为人权法院对“裁量余地原则”的坚守和使用导致它不会轻易以捍卫艺术表达自由为由推翻缔约国法院的原始判决,这就使得艺术家群体不会轻易向人权法院申诉,因为胜诉可能性很低。第二,有主流宗教信仰的欧洲国家对本宗教的题材极为敏感,总以严肃态度予以对待,对轻蔑态度和讽刺艺术手法通常会予以法律制裁——对宗教情感的尊重高于对艺术表达自由的保护;对针对弱势群体(比如未成年人、穆斯林)有意无意进行攻击或伤害的艺术表达也可能会予以规制。但话又说回来,这些案例是欧洲广泛、频繁的现代艺术活动的极个别个案,还有大量的同样存在争议的作品由于没有原告启动程序就不会进入法庭,所以没有被限制的无疑是大多数。第三,后两个案例反映出近年来人权法院似乎越来越愿意细致分析艺术与其他表达方式的不同之处,并以此作为裁决依据。如下文将详细揭示,无论是对缔约国法院还是对欧洲人权法院来说,艺术表达的具体目的在判断是否应予保护时起决定性作用,法院对含有政治元素、带有政治目的的艺术表达总是予以高度保护,《欧洲人权条约》第10条第2款基本不限制政治言论以及对公众关心问题的公开讨论,因此人权法院对明确表达政治意图的艺术作品会给予最大自由空间,留给缔约国法院极小的裁量余地。
三、政治元素决定艺术表达自由的界线
艺术与政治愈发紧密的联系开始于“让艺术成为观念表达、成就观念性艺术”的上世纪60年代——艺术不仅要解放艺术本身、反传统艺术,也开始反映艺术家对现实社会的思考与政治性意见。艺术因其政治元素而未被《欧洲人权条约》缔约国限制的一个经典案例,是轰动西方及穆斯林世界、被丹麦首相称为二战以来丹麦最严重国际关系事件的“穆罕穆德漫画事件”。尽管该事件并没有被申诉到欧洲人权法院,但它对下文对人权法院判例的继续分析起关键作用,需要先予分析。
丹麦销量最大的日报《日德兰邮报》在2005年9月30日刊登出12幅题为《穆罕穆德真容》(Muhammeds ansigt)的讽刺伊斯兰教和先知默罕默德的漫画,引起穆斯林世界极度不满,*在伊斯兰教中,描绘先知图像即亵渎先知,是最严重的犯罪。不仅导致全世界范围穆斯林民众的抗议,也带来了伊斯兰极端分子的恐怖袭击威胁。2005年10月27日,丹麦穆斯林组织联名向丹麦警局*在丹麦,警察局和检察院是合二为一的机构,警局既负责侦破案件,也负责提起公诉。控诉《日德兰邮报》触犯丹麦刑法第140条和第226b条。第140条禁止在公众场合取笑、讽刺和侮辱在丹麦境内一切合法存在的宗教。在实践中,该条款很少使用,在丹麦历史上仅有1938年的一个反犹太组织因违反该条款被定罪。第226b条禁止基于种族、肤色、国籍、族群、宗教信仰或性取向侮辱、威胁或贬低他人。2006年1月6日,丹麦维堡公诉人认定这组漫画没有触犯丹麦刑法并终止了对事件的调查。他强调,漫画的主题有很高的公众关注度,丹麦案例法对新闻工作者发表或评论这类主题的自由予以高度保护;此外,在判定一个行为是否触犯刑律时,必须要考虑言论表达自由的重要性;当然,自由表达时必须顾及他人不受侮辱和贬低的权利。穆斯林组织向上级机关继续申诉,但丹麦检查公署主任维持了维堡公诉人的决定。
尽管获得了官方和主流舆论的支持,但面对巨大压力,《日德兰邮报》主编还是选择于2006年1月底发表公开信致歉。但德国、瑞典、比利时、挪威、西班牙、美国等国家纷纷转载了这组漫画,对《日德兰邮报》予以声援,捍卫表达自由。丹麦政府尽管谴责漫画的表现手法,但也强调了丹麦人的幽默风趣以及捍卫言论自由、表达自由和民主的重要性。这导致穆斯林世界的抵触情绪进一步升温,最终引发了世界范围的暴力示威、焚烧教堂、袭击外国大使馆、劫持人质等暴力恐怖事件。
这个事件与前文所分析的几个亵渎神教罪案例的区别在于:第一,它并非司法判例,未经丹麦法院审理,因此国内司法救济路径并未穷尽,不得申诉至欧洲人权法院;第二,丹麦的亵渎神教罪保护丹麦境内所有合法存在的宗教,不像英国在废除该罪名前只保护基督教;第三,前文几个被判亵渎神教罪的艺术作品都是为艺术而艺术,不含政治目的;而这组漫画的目的明确,即对伊斯兰教部分教义及一些信徒的极端行为进行批判,同时对丹麦新闻工作者因恐惧而导致的“自我言论审查”(self-censorship)程度进行一次测试性调查。*有42位漫画家受邀为《日德兰邮报》画这组漫画,15位回复,3位拒绝,最终有12位交稿。漫画的说明文字这样解释这组漫画的目的:“一些穆斯林拒绝现代世俗社会,却要求社会赋予他们一个特殊的位置,对他们的宗教感情予以特别关注和特殊对待。这与现代民主和言论自由不相符合。现代社会中每个人都应做好准备忍受辱骂、嘲弄和嘲笑。这当然是不幸的,人们不该不惜代价去伤害他人的宗教情感。但这在当前并非最重要的,我们正从一个大滑坡上下滑,无人知晓何处是自我言论审查的尽头。这就是《日德兰邮报》邀请丹麦漫画家联盟成员按他们所看到的样子绘制穆罕默德的原因所在。”*Flemming Rose, “Muhammeds ansigt”, Jyllands-Posten(《日德兰邮报》), 2005年9月29日。第四,前文几个案例中的艺术作品都是孤立事件,而这组漫画则是由一系列新闻事件构成的、正在进行中的关于伊斯兰教与西方民主之间矛盾关系讨论中的一个环节。这样一来,漫画不再单纯是艺术表达形式,而成了在西方具有至高无上地位的政治言论表达。
政治元素同样突出、也是欧洲人权法院迄今为止艺术表达自由领域申诉人获胜的屈指可数的判例之一,是Karata v. Turkey (1999)案。*Karata v. Turkey [1999] ECHR 23168/94.与以上案例不同,这个案子所涉及的不是危害公共道德,而是煽动罪。 申诉人是库尔德裔土耳其人,在伊斯坦布尔发表了一本题为《暴乱之歌》(The Song of a Rebellion)的诗集,被土耳其国家安全法庭(Turkish National Security Court)以进行分裂宣传为由定罪入狱一年零八个月,诗集被收缴。他以土耳其当局侵害了他《欧洲人权公约》第10条赋予的表达自由为由通过当时的欧洲人权委员会向欧洲人权法院提起申诉。
人权委员会出人意料地站在了土耳其当局一方,认为土耳其当局虽然限制了申诉人的表达自由,但没有超出《公约》第10条第2款允许的范围,是基于国家安全考虑的合法、必要手段。*Karata v. Turkey [1999] ECHR 23168/94.委员会承认,诗歌作为信息传达方式的确使本案有别于普通的煽动罪案件,但就算艺术表达再特殊、再有别于普通表达方式,诗歌的部分内容煽动武装叛乱、美化殉道是不争的事实,部分表达方式甚至给人以支持分裂国家的暴力行为、呼吁对土耳其政府发动武装斗争的印象。因此,人权委员会认为土耳其当局完全有理由以危害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为由对此诗及其作者予以惩处。
欧洲人权法院多数法官站在了人权委员会的对立面,以12比5判定土耳其当局违反了《欧洲人权公约》第10条对表达自由的规定。法院虽然承认涉案诗歌在个别地方显得激进暴力,但认为是诗人为达到最佳效果而进行的刻意创作,并强调《公约》第10条保护具有攻击性的、令人震惊和不安的艺术表达内容和方式。虽然国家安全是合法限制表达自由的理由,土耳其东南部的安全局势也使当局有理由对煽动暴力、危害公共安全和国家领土完整的行为及言论格外敏感而进行规制;但法院认为,申诉人是独立的个体,用诗歌的手法看似表达了一些激进观点,但与广播电视不同,诗歌的读者非常少,对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的危害很受限。此外,申诉人一直强调艺术自主性,即他的诗歌只是艺术创作,其中所描绘内容不代表个人观点。人权法院也认为他在诗中表达了对政治局势的深深不安,而非号召和煽动暴力冲突。因此,经过多方面权衡,人权法院认定土耳其法院的判决与申诉人诗歌所造成的危害不成比例,不合理地限制了《欧洲人权公约》所赋予的表达自由。
这个案例的特别之处在于,欧洲人权法院极少如此关注艺术表达形式有别于其他表现形式的特殊性,也极少如此强调艺术表达的具体语境。如果人权法院在文章第二部分所分析的案例中也采取同样态度,沿用在这个案子中对密尔“伤害原则”的理解,对伤害采用很实际的度量方法——有限的传播意味着有限的伤害——几个案例的判决结果也许会截然相反(比如Otto-Preminger Institute v. Austria,Müller and Others v. Switzerland,X Ltd and Y v. United Kingdom)。
由此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在欧洲人权法院面前,争议艺术表达有一个政治层面显然是巨大优势,这与法院案例所揭示的“政治表达是最需要保护的表达”的思想相吻合。但是保护艺术表达自由仅仅因为政治元素是有问题的,这样一来,“艺术”被等同于了“政治意见”的形式,也就失去了艺术表达自由保护的独立意义。第二,艺术表达自由作为《欧洲人权公约》第10条中表达自由的一个子类别似乎并没有得到明确司法认可,再加上人权法院的法官们并不遵循判例法原则,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Karata v. Turkey中的法律推理和最终结论丝毫没有之前同领域判例的影子。这意味着人权法院没有、近期内也不会形成一套线条清晰、针对艺术表达自由的普遍性规则,这不利于该领域问题精致、高效的解决,艺术表达自由特别是争议艺术表达自由仍将长期处于荆棘丛生的状态。
结语
19世纪末尤其20世纪60年代以来,新潮迭出的现代艺术、后现代艺术对传统美学和艺术理论展开了强劲、全方位的冲击。这一巨变仿佛是马克思天才预言之验证:“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崇敬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页。与旧时不同,如今的艺术表达形式多样,目的也多样。现代争议艺术不是为了表达美,至少不再是单一的表达传统的定式的美,而更多的是为了表达本身,不仅表达对主流艺术标准、定式和束缚的观点和看法,也表达对社会现实的意见和看法;它没有统一的美的标准和表达方法,而是一种因人而异的、直白的宣泄情感和意见表达,这并非风俗习惯或美学理论可以准确界定。因此,它是否该是自由的,取决于情感宣泄和意见表达是否该是自由的,它自由的合法边界也是情感宣泄和意见表达的边界。
显然,从典型判例可以看出,欧洲人权法院在处理此领域案件时仍然坚持传统艺术概念,更倾向于门罗·比尔兹利的“艺术即带有审美意图的美感展示”观点;*Thomas E. Wartenberg, The Nature of Art: An Anthology, 3rd edition, Cengage Learning, 2011, Chapter 20.艺术表达自由也不是人权法院关注的重点,判例非常有限。对主要案例的分析既直观展现了人权法院的风格和理念,也反映了更深层次、可能无解的疑难问题。第一,相比艺术表达自由,人权法院对政治言论自由和宗教情感维护明显高看一眼,尽管它对此予以明确否认。第二,人权法院对密尔“伤害原则”有极为狭窄的理解,导致其极易维护缔约国对涉及性主题的艺术表达进行道德审判,而这背后的主要技术原因是它对公共空间里的“含性元素的争议艺术”与“色情”不加区分,尤其对它们的目的不予以细致甄别,由此生成了“一切含有露骨性元素的争议艺术表达均违反公共道德法则”的不当法律假定。这一假定一旦稳固而成为习惯,法官们将不再去细致分析两个概念的区别、剖析涉案艺术表达到底对谁产生了什么具体危害,而是自动采用适用于“色情”的危害标准来衡量争议艺术表达的危害性,这导致有的“危害”可能纯粹是想象出来的。
这种判决理路背后的深层原因有三:首先,欧洲人权法院过于保守、克制。关于人权法院到底该是什么风格——以国家主权为重,以“裁量余地原则”为上,还是按照《欧洲人权公约》的初衷,真正成为《公约》的执行机构,对缔约国履行公约责任和义务进行实质监督和强制管辖,或者避免二元思维,在两种风格间寻找平衡?但平衡点在哪里一直争议不断。面对不同的公约权利,人权法院有不同的态度。比如,在引渡恐怖分子问题上,出于对他们回到母国后可能遭到迫害的担忧,人权法院总是站在缔约国的对立面,为引渡设置层层法律和政治障碍;*参见[英]魏华、张兰兰:《论正当反恐法律机制的创建》, 载《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但面对涉及道德标准的表达自由,尤其艺术表达自由,人权法院基本站在缔约国一边。至于为何政治权利可以有超越主权的统一标准,而与政治权利不可分割但触及道德底线的艺术表达自由就得以本地标准为上,并没有建立起具有说服力的理据。
与此相关的第二个深层原因是,与其他国际人权法律文书相比,《欧洲人权公约》及兑现公约权利的具体实践中,“文化艺术权利”这一权利实体的可诉性缺乏应有的细致支撑。《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美洲人权公约》以及《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中都有对文化艺术权利的专门具体规定;而《欧洲人权公约》第10条仅仅暗示、映射了对艺术表达自由的保护。这种定位无疑是欧洲人权法院难以对缔约国以保护道德为由侵害艺术表达自由予以实质性审查的主要障碍。
欧洲人权法院对艺术表达自由过度规制的第三个深层原因关乎法律和艺术的关系。法律以节制、纪律和控制为追求,界限清晰;而艺术(尤其后现代艺术、争议艺术)关乎想象力、创造力、嬉闹、宣泄情绪乃至挑战传统定式的底线——也就是说,法律和艺术的特征、目的、行为方式、是非标准都大相径庭、格格不入、没有可比性。前者为后者划定合适的活动范围,相当于要求法律用客观标准衡量一个由主观喜好构建的错综复杂的世界的意义及好坏,这起码需要法官有更系统的艺术知识储备,特别是对争议艺术要有足够的宽容精神和开放态度,以增进对艺术表达的价值和特殊功能的了解,将之融入到往往充斥着习惯性道德偏见和过度保守的裁决中去,审视和重新划定艺术表达自由的合理界线。当然,这需要欧洲人权法院的法官们有明确规则的意愿。
[责任编辑:王德福]
收稿日期:2016-05-10
作者简介:[英]魏华(Hanna H. Wei)(1981-),女,广东广州人,法学博士,山东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法理学、政治哲学、人权学。
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8003(2016)04-0151-10
Subject: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Regulation of Freedom of Expression——The Example of Controversial Art
Author & unit:Hanna H. Wei
(Law School of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00, China)
Abstract: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lack of appreciation of modern art coupled with its conservative interpretation of margin of appreciation have caused it repeatedly and consciously to miss opportunities to lay down more coherentrules for the protection of freedom of expression especially toleration of controversial artistic expression. The underlying reason is not only the rejection of modern and post-modern art forms, but also the lack of will meaningfully to exercise its Convention-sanctioned duty to oversee and regulate human rights issues of member states.
Key words: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controversial art; margin of appreciation; freedom of expres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