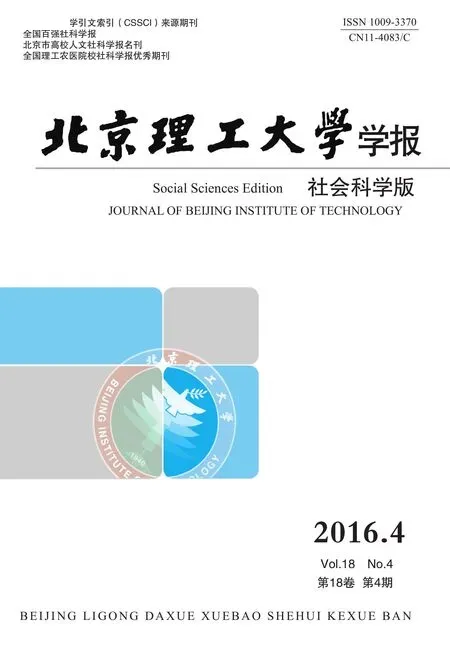讯问中录音录像制度适用问题研究
——以念斌案为视角
谢登科
(吉林大学 法学院,长春 130012)
讯问中录音录像制度适用问题研究
——以念斌案为视角
谢登科
(吉林大学法学院,长春 130012)
讯问中录音录像制度对于规范讯问行为、保障犯罪嫌疑人权益具有重要意义。讯问中录音录像的证据种类归属不清、审查机制不健全、程序性制裁阙如等问题,给司法实践造成诸多混乱。念斌案中存在这些问题。讯问中录音录像在证明程序性事实时属于视听资料,证明实体性事实时属于供述,其双重属性具有层次性。对于严重违反录音录像制度的行为,应给予程序性制裁、否定其证据能力。在与讯问笔录存在实质性差异的情况下,录音录像具有比讯问笔录更强的证明力。以录音录像所记载的供述内容作为定案根据时,仍然应遵循口供补强规则。
录音录像;证据种类;证据能力;证明力;程序性证明
中国《刑事诉讼法》第121条规定了讯问中录音录像制度。但讯问中录音录像存在证据种类归属不清、审查机制不健全、程序性制裁阙如等问题,这些问题也出现在念斌案①目前,社会各界对于念斌案的报道和探讨较多,由于各自所处立场不同,对于该案的报道和评价也存在较大差异。为保障相关信息的客观性与真实性,本文中对念斌案相关信息的引用和阐释,全部来源于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8月22日作出的(2012)闽刑终字第10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中。念斌案最终因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改判无罪,而被社会各界誉为“法治标本”[1]。
一、录音录像的证据种类:供述?视听资料?
证据种类是法律规定的证据的不同表现形式。学界关于是以证据自身性质、存在方式为基础,还是以运用证据来证明案件事实的行为为基础划定不同证据种类,存在争议[2]。从现有制度来看,这种争议并未传导至立法层面。中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第2款规定了8种证据。讯问中录音录像属于视听资料,还是属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实务界和理论界均存在较大争议,这种争议在念斌案中亦得到体现。在念斌案中,控辩审三方对于录音录像的证据种类认识,亦存在分歧。控诉方主要将录音录像用于证实“念斌第1次交代投毒作案时的部分审讯经过”,虽未明确阐述讯问中录音录像所属的证据种类,但对“审讯经过”的证明主要是依靠录音录像所记载的信息来证明案件事实。因此,控诉方将讯问中录音录像作为视听资料。辩护方亦从这一证据种类角度展开反驳、质证。而法院认为“念斌第一次有罪供述的笔录内容与在案的审讯录像内容不完全一致,且审讯录像内容不完整”,未明确表明讯问中录音录像所属的证据种类。法院主要将录音录像视为固定犯罪嫌疑人有罪供述的方式、手段,在本质上与讯问笔录并无差异,因此,法院是将讯问中录音录像视为犯罪嫌疑人供述。
不同证据种类,在收集举证方式、审查判断方法、适用证据规则等方面存在差异。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例,若将录音录像视为供述,就适用言词证据的强制性排除规则;若将其视为视听资料,则不适用《刑事诉讼法》第53条规定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②《刑事诉讼法》第53条规定了对非法言词证据的强制性排除,对非法实物证据的裁量性排除。而该条规定的实物证据仅限于物证、书证,却不包括视听资料。。在念斌案中,控辩审三方对于讯问中录音录像的认识差异,可能会直接影响对审查判断方法、证据规则适用等方面的差异。学术界对讯问中录音录像属于何种证据种类,亦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讯问中录音录像仅仅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陈述内容的记载,是固定和保全供述的方式,在本质上仍然属于供述,而不是视听资料[3]。有学者将讯问中录音录像归为视听资料[4]。还有观点认为录音录像属于综合证据[5]。
证据种类区分的重要依据之一是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关联性。关联性是证据对案件事实所具有的实质性证明作用。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性并非固定不变,它是一个关系范畴,是作为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关系而存在,只有在特定背景下才有意义。因此,证据的关联性常常需要考虑特定的案件事实,证明对象(待证事实)不同,相同证据与案件之间的关联性也不尽相同。当探讨讯问中录音录像属于何种证据种类的问题时,暗含了一个基本前提:承认其是证据。关于讯问中的录音录像是否属于证据?有观点主张,中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才是证据,而讯问中的录音录像仅仅是侦查机关固定讯问过程的方式,并不能用来证明案件事实,不属于刑诉法规定的法定证据。该观点对“案件事实”作了狭义理解,将其局限于实体性事实。不过,从证明对象角度来看,作为证明对象的案件事实,既包括实体性事实,比如对被告人定罪量刑的相关事实,也包括程序性事实,比如管辖、回避、证据收集程序合法性等事实。而讯问中录音录像同时承载着案件的实体性事实和程序性事实两种信息:一方面,记载了犯罪嫌疑人在讯问中对犯罪事实供述或者辩解的信息;另一方面,记载了侦查人员讯问方式、过程、表情、神态等信息。在刑事诉讼中,不仅存在实体性证明,还存在程序性证明[6]。因此,无论从实体性事实还是从程序性事实来看,讯问中录音录像都属于证据。讯问中录音录像与案件事实的关联性,亦可在上述两个层面展开:第一、实体性事实。讯问中录音录像并不是在犯罪过程中产生的,而是在刑事诉讼程序中产生的,它是对侦查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过程的客观、全面记录,其中包括犯罪嫌疑人对案件事实的供述。讯问中录音录像没有对案件实体性事实的直接记载、固定,它对实体性事实的证明主要是借由犯罪嫌疑人供述或者辩解内容来发挥作用,它是对供述的固定、保全方式,在本质上仍然属于供述,而不是独立的证据种类。第二,程序性事实。讯问是收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的必经程序。讯问中录音录像是对侦查人员讯问行为的客观、全面记录,当控辩双方对讯问行为合法性存在争议时,可以用来证明该程序性争议事实。录音录像对于讯问行为合法性的程序性证明,不是借助于犯罪嫌疑人对案件实体性事实的供述或者辩解,而是借助于其自身对讯问过程的客观记载,它通过图像、声音等元素组合起来反映案件程序性事实,展示讯问程序中相关人员的行为细节等信息。因此,录音录像用于对讯问行为合法性的程序性证明时,在证据种类上属于视听资料。在念斌案中,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对讯问中录音录像列为“物证”。这里的“物证”是广义物证即实物证据,不是狭义物证即刑诉法第48条第2款规定的物证。实物证据包括物证、书证、视听资料。录音录像不是以其外部特征或者物理属性来证明案件事实,不是狭义物证,而是证明讯问行为是否合法这一程序性问题的视听资料,属于广义物证。
根据证明对象不同,讯问中录音录像可分别归为供述、视听资料两个证据种类。在念斌案中,控辩双方将讯问中录音录像视为视听资料,而法院将其视为供述,均具有合理性。但是,录音录像分别基于对程序性事实和实体性事实的证明作用,才能列为供述、视听资料。在念斌中,控辩双方对讯问行为合法性存在争议,由此衍生出录音录像能否作为认定讯问行为合法性证据的争议,因此,法院裁判亦应围绕此问题展开。而法院在裁判中关于录音录像的论述,显然回避了讯问行为合法性这一程序性问题,直接从实体层面考察录音录像记载的内容与讯问笔录是否相符,考察供述与其他间接证据的关系。如果仅从讯问中录音录像与案件实体性事实之间的关系来看,法院将其视为供述并没有问题。但法院作为居中裁判者应围绕控辩双方的争议问题进行裁判,否则就可能悖离其被动、中立地位。控辩双方将录音录像作为视听资料来证明讯问行为合法性的程序问题,法院却回避对该程序性争议的裁判而直接作出实体性裁判,显然有悖于其被动、中立地位。另外,从程序与实体的关系来看,应遵循“先程序,后实体”原则,优先处理程序性问题。这就决定了讯问中录音录像的双重证据属性间具有层次性,先作为视听资料发挥其程序性证明功效,然后再作为供述来证明案件的实体性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于2010年联合制定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5条:“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开庭审理前或者庭审中,提出被告人审判前供述是非法取得的,法庭在公诉人宣读起诉书之后,应当先行当庭调查。”[7]。“先行审查”原则决定了首先应将录音录像作为视听资料用于证明讯问行为合法性。因此,法院直接审查录音录像中的供述内容,有悖于对程序性问题的“先行审查”原则。
二、录音录像的证据能力:自身合法性的证明
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须具有证据能力和证明力,讯问中录音录像亦不例外。对不同种类的证据而言,其证据能力获得既存在共通因素,比如都要求经过控辩双方质证,也存在各自独特的要素。影响供述证据能力的主要因素是供述的自愿性或者任意性。全程录音录像可以打破讯问空间的封闭性,阻吓刑讯逼供、威胁、欺骗等损害供述自愿性的行为[8],但录音录像本身并不直接影响供述的自愿性。因此,以讯问中录音录像来证明实体性事实时,其证据能力通常不是争议的焦点。另外,作为记录、固定供述方式的录音录像与作为视听资料的录音录像,二者在证据能力的审查方面亦存在相同之处。影响视听资料证据能力的主要因素包括视听资料的来源是否合法、是否为原件、制作过程是否合法、有无增删剪辑等等。在以录音录像来证明讯问行为合法性时,其在证据种类上属于视听资料。讯问中录音录像作为视听资料证明讯问行为合法性时,其证据能力往往成为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
在念斌案中,对于录音录像能否作为认定讯问行为合法性的根据,控辩双方存在重大争议。控诉方认为:“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的物证检验意见,证实该审讯录像光盘记载的内容未经过剪辑、整合技术处理。”意在证明讯问中录音录像没有经过任何剪辑,可以作为认定讯问行为合法的根据。辩护方认为:“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关于审讯录像光盘检验情况的说明函,提出该中心说明的其检验的审讯录像光盘内容未经过剪辑、整合技术处理,与内容中断的在案审讯录像不相符,在案的审讯录像与物证检验意见均不能作为定案根据。”辩护人意在证明在案的录音录像经过剪辑、与送检的录音录像不相符合,不能作为认定讯问行为合法的根据。双方对于录音录像是否经过剪辑、删减存在分歧。经过鉴定机构鉴定,如果认为讯问中录音录像全面、完整、持续,没有经过剪辑、删减,则可以作为认定讯问行为是否合法的根据。反之,则不能作为认定该程序性事实的根据。如果案卷中的录音录像与送检的录音录像不一致,则不能保证鉴定意见的真实性、可靠性。因此,辩护方主张《物证检验意见》和讯问中录音录像均“不能作为定案根据”。这两份证据“不能作为定案根据”所指向的证明对象并不相同。《物证检验意见》“不能作为定案根据”是指其不能作为认定讯问中录音录像具有证据能力的根据,这主要是源于在案录音录像与送检录音录像不符、无法保障鉴定意见的可靠性。而讯问中录音录像“不能作为定案根据”是指其不能作为认定讯问行为合法性的根据,这主要源于讯问中录音录像的证据能力无法得到证明。
在念斌案中辩护方能发现讯问中录音录像中断的重要前提,是其有机会查阅、复制、请求法庭播放录音录像。讯问中录音录像属于证据材料,就应在移送审查起诉、提起公诉时列入卷宗移送至检察院、法院,辩护律师亦应有权查阅、复制。庭审中,控辩双方对供述内容或者讯问行为合法性发生争议,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有权请求当庭播放录音录像。当庭播放、给予控辩双方质证的机会,是讯问中录音录像获得证据能力另一必要条件。但从讯问中录音录像制度的实践运行来看,其移送、播放存在问题:第一,对录音录像不移送或者选择性移送。有的侦查机关不向检察院移送录音录像,检察院不向法院移送。即便法院要求检察院移送时,有的检察院也不是对录音录像全部移送,而是避重就轻选择对控诉有利的移送。在念斌案中就存在这种情况,甚至出现了作为检材的录音录像和当庭播放录音录像不一致的情形。第二,辩护方无法查阅、复制录音录像。有些检察院在移送卷宗和证据材料时,会将录音录像一并移送法院,但却将其列入侦查工作卷宗或者秘密侦查卷宗,这两种卷宗被称为“侦查内卷”[9]。“侦查内卷”是相对于“侦查外卷”而言的,侦查外卷主要是侦查正卷。侦查正卷主要包括诉讼文书和证据材料,而侦查内卷则主要包括线索材料、侦查报告、审批手续等不对外公开的材料。将录音录像列入侦查内卷,就意味着它是禁止辩护律师查阅、复制的。第三,庭审不播放或者选择性播放录音录像。对录音录像移送、播放中存在的违法行为,可通过宣告相关诉讼行为无效或者证据不具有证据能力,给予违法者相应的程序性制裁。侦查机关、检察机关拒绝移送的,法院可推定侦查机关在讯问中没有录音录像,如果控诉方无法证明供述收集的合法性,则该供述应推定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法院无正当理由拒绝辩护律师查阅、复制录音录像,或者拒绝当庭播放录音录像。辩护方提出上诉时,二审法院可以一审法院“程序违法”为由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通过程序性制裁强化录音录像移送、播放制度的刚性,仅是从外在因素着手。从侦查角度出发,侦查人员不愿意移送在很大程度上亦是源于合理需求。如果讯问中录音录像制度不能回应侦查人员的合理需求,则在实践中必然遭遇失灵的命运。实践中侦查机关不愿移送或者不愿公开讯问中录音录像主要存在如下正当理由:讯问录音录像中涉及其他案件线索,当庭播放可能影响对其他案件的侦破;当庭播放会泄露侦查人员身份,存在威胁侦查人员人身安全的风险;侦查人员使用了相关讯问策略或技巧,当庭播放将会公开这些讯问策略、技巧,影响以后对类似案件的侦破。上述正当理由并非存在于所有刑事案件之中,因此,不能成为阻碍录音录像移送、当庭播放的绝对理由。对存在上述正当事由的案件,采取必要的技术手段完全可以化解相关风险。在移送、播放录音录像过程中,可限制播放范围,也可对录音录像做适当技术处理,比如采取音频变声或者图像部分马赛克化。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简称《刑诉法解释》)第101条规定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可以“有针对性地播放讯问过程的录音录像”。这主要是考虑到讯问中录音录像动辄十几小时、甚至更长时间,全部播放将严重影响庭审效率,而且也没有必要全部播放。司法实践中,围绕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提出的相关线索或者材料,有针对性地播放审查,既能有效审查被告人供述的合法性,也能提高诉讼效率。
三、录音录像的证明力:与讯问笔录的关系
讯问中录音录像对讯问行为合法性的证明,主要是通过其自身所记载的声音、图像等信息来发挥作用。在保障录音录像具有证据能力的前提下,它往往比较真实、可靠,证明力相对较高。因此,对于程序性问题的证明而言,讯问中录音录像的证明力通常不是争议的焦点。但在证明实体性问题时,录音录像的证明力则常常成为争议的焦点:第一,录音录像与讯问笔录存在实质性差异时,何者证明力更大;第二,录音录像所记载的供述内容与其他证据无法印证时,如何处理。上述问题在念斌案中均有涉及。在该案中,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集中于录音录像的证据能力问题,而法院在判决论理中未涉及录音录像的证据能力,直接论证了其证明力问题。法院认为:“念斌第一次有罪供述的笔录内容与在案的审讯录像内容不完全一致,且审讯录像内容不完整。念斌庭前多次供述的鼠药来源一节,其中关于卖鼠药人的特征、年龄、鼠药包装袋规格以及批发香烟的时间等情节,与证人证言不相符;供述的将鼠药水投放在铝壶水中一节,如上所述认定铝壶水有毒根据不确实,形不成印证;供述把鼠药放在货架上毒老鼠一节,从货架表面与旁边地面上提取的灰尘中均未能检出鼠药成分,亦形不成印证;供述的作案工具、剩余鼠药,均未能查获。本院认为,念斌的庭前供述和辩解存在反复,庭前供述与其他证据不能相互印证,不足以采信。”法院该裁判部分对录音录像证明力的两个问题均作了论述。
关于讯问中录音录像与讯问笔录的关系,从本质上看,讯问笔录和录音录像都是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讯问过程的固定方式。固定的目的是为了保障讯问在事后的可检验性,为法院审查讯问的合法性提供根据。但是,固定方式的差异决定了二者之间也存在较大差别。讯问笔录是由侦查人员对讯问中相关信息通过书写方式予以固定,而录音录像则是由机器设备通过电子符号的方式予以固定。这两种讯问固定方式各有利弊。讯问笔录是由人对讯问过程予以固定,经由记录人员加工整理,其内容可能更具逻辑性、简洁明了[10]。讯问是侦查人员和犯罪嫌疑人的交互行为,空间相对封闭,缺乏其他人员在场。虽然在特定案件中可能存在其他人员在场,比如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的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11],但这些制度不具有普适性,不能适用于其他类型的刑事案件。另外,中国尚未建立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的律师在场制度,因此,笔录就成为法院审查讯问行为合法性重要根据。但是,由于存在人为因素,讯问笔录主观性较强,可能会因记录人员聆听、记忆、书写等客观因素,或是记录人员所处立场、角度等主观差异,导致笔录内容悖离犯罪嫌疑人供述内容。另外,笔录仅是对供述内容的记载,而无法反映犯罪嫌疑人陈述时的表情、语调、动作、情绪等信息。因此,单纯依据笔录很难充分审查讯问行为合法性。作为录音录像载体的机器设备则不同,它可以对讯问过程作全程、同步记录,既记录陈述或者供述内容,还记载陈述时的表情、语调、动作、情绪等信息。即使对录音录像有删减或者改动,也会留有相关痕迹,通过鉴定仍然有机会发现。在庭审质证中,通过现场播放可将录音录像所记载的内容展示给裁判者,让裁判者对讯问过程和相关内容有较为清晰、直观的认知。因此,相对于讯问笔录而言,录音录像的信息更为全面、客观、真实。但是,录音录像可能会因为侦查人员讯问或者犯罪嫌疑人供述缺乏逻辑,而导致其记载的信息缺乏逻辑。对于重大、疑难、复杂的案件,往往需经多次讯问而多次录音录像,导致其记载的信息琐碎、冗长,不利于及时、高效查找相关信息。从实践来看,在有些刑事案件的处理中,由于录音录像过于冗长,法庭出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之考量而拒绝当庭播放录音录像,这直接导致讯问中录音录像丧失其应有的制约功能。
鉴于讯问笔录和录音录像各自的利弊,录音录像无法完全替代讯问笔录。由于讯问笔录在内容上的逻辑性、简洁性,在用犯罪嫌疑人供述证明定罪量刑的实体性问题时,可首选以讯问笔录为证据材料。当控辩双方对于供述内容发生分歧、争议时,则可根据录音录像作为审查供述内容的证据材料。《刑诉法解释》第80条第2款规定“必要时,可以调取讯问过程的录音录像”对被告人供述和辩解进行审查,就体现了主要根据讯问笔录审查供述内容。对于笔录中记载的供述内容,可通过录音录像予以补正。当讯问笔录与录音录像记载内容存在实质差异时,由于录音录像具有全程性、同步性、持续性,它的证明力大于讯问笔录,应以录音录像替代讯问笔录作为认定供述内容的证据材料。虽然,录音录像在用来审查供述内容时处于补充地位,但并不意味着其处于无足轻重的角色。录音录像类似于“影子杀手”的地位,它轻易不会出现,一旦出现则可能会对最终裁判结果产生决定性影响。在证明讯问行为合法性这一程序性问题,录音录像则与讯问笔录处于同等地位,录音录像的证明力仍然大于讯问笔录。《刑诉法解释》第101条将讯问笔录、录音录像同时列为证明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证据,并无主次之分。讯问空间的封闭性决定了能用于证明讯问行为合法性的证据相对不多,而讯问笔录和录音录像则是直接证明该程序性问题的重要证据。但是,鉴于录音录像的全程性、同步性、持续性,它在证明该程序性问题的证明力也更强。当然,录音录像证明力更强的前提是其具有证据能力,这要求录音录像的制作须符合法定程序。录音录像应符合全程性、同步性、连续性的要求,不存在人为的删减、编辑或者不连续录制,也不存在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将犯罪嫌疑人制服后录音录像的情形。因此,只有在录音录像具有证据能力、与讯问笔录存在实质性差异的情况下,才承认它具有比讯问笔录更强的证明力。
在念斌案中,由于录音录像的不完整,法院并未认定其具有更强的证明力。无论是讯问笔录,还是录音录像,法院均未将其记载的供述内容作为定案根据,主要原因在于供述不能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正如前文所述,讯问中录音录像对实体性事实的证明主要是借由犯罪嫌疑人供述或辩解内容来发挥作用,它是对供述的固定、保全方式,在本质上仍然属于供述,而不是一个独立的证据种类。运用讯问中录音录像来证明实体性问题时,仍然应当遵循口供补强规则。当录音录像记载的供述内容,无法通过其他证据补强时,不能作为认定被告人有罪的依据。因此,无法获得其他证据的有效补强,是念斌案中法院不采信其供述内容的重要原因。
[1]刘武俊.念斌无罪释放具标本意义[N].人民法院报,2014-09-01(2).
[2]孙远.论法定证据种类概念之无价值[J].当代法学,2014(2):99-106.
[3]何家弘,刘品新.证据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180.
[4]陈光中.证据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201.
[5]潘申明,魏修臣.侦查讯问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证据属性及其规范[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0(6):82-87.
[6]闵春雷.刑事诉讼中的程序性证明[J].法学研究,2008(5):139-148.
[7]张军.刑事证据规则理解与适用[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314-317.
[8]董坤.违反录音录像规定讯问笔录证据能力研究[J].法学家,2014(2):127-139.
[9]张丽红.论讯问录音录像制度功能的反思[J].法律适用,2014(8):70-75.
[10]吴纪奎.论警讯录音录像证据[J].证据科学,2013(3):65-74.
[11]谢登科.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的实践困境与出路——基于典型案例的实证分析[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 (3):110-115.
[责任编辑:箫姚]
Analysis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Rule of Videotaping of Interrog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ianbin’s Judgment
XIE Dengke
(School of law,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12,China)
The rule of videotaping of interrogation will help to regulate the behaviors of interrogation and to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suspects in criminal procedure.However,it has drawbacks including the vague of category,the deficiency of judicial review,the lack of procedural sanction etc.The videotape of interrogation belongs to audio-visual material on proof of procedural matters,while it’s confession on proof of substance matters.It’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procedural sanction for serious violations of the rule by depriving its evidence capability.In the case of substantive differences between interrogation record and videotape,the latter has stronger probative value.Based on videotape of interrogation to establish facts,it still should follow the corroboration rule.
videotaping of interrogation;category of evidence;evidence capability;weight of evidence;procedural proof
D915.3
A
1009-3370(2016)04-0144-05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6.0421
2015-10-26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资助“刑事简易程序实证研究”(15CFX031);中国法学会重点专项课题“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CLS2015C07);吉林大学廉政建设专项研究课题“纪检监察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研究”(2014LZY017)
谢登科(1980—),男,法学博士,国家“2011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吉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吉林大学司法数据应用研究中心研究员,E-mail:xdkjlu@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