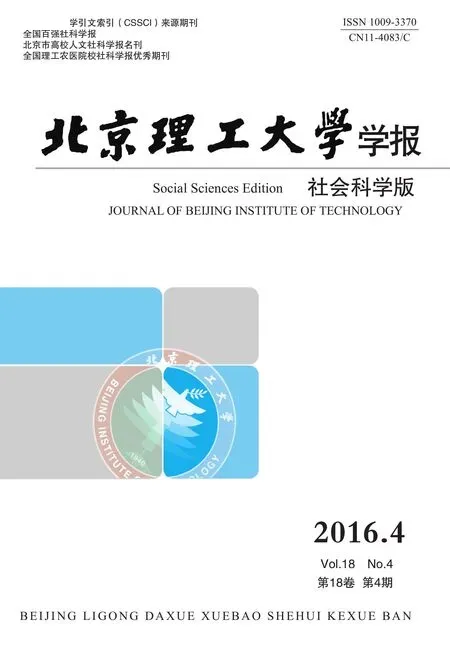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学热”的话语转型与历史反思
裴萱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学热”的话语转型与历史反思
裴萱
(河南大学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中国20世纪80年代“美学热”的生成与延展来自于感性审美与政治意识形态的二元对抗。人性启蒙和感性解放的历史诉求都通过美学的知识形态得以充分表达,此种学术场景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至20世纪90年代产生了变革。美学被边缘化的原因,一方面是总体化国家领导策略的调整,另一方面则是知识分子公共启蒙的分化。面对市场伦理对大众文化的推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渗透以及文学审美实践的影响,大众审美文化以面向大众的姿态、平等多元的共存理念和审美意识形态的介入性视角给美学的发展带来的新的契机,形成了从“终结”到“延续”的历时性叙事,“美学热”的精神理念与启蒙热情将持久地影响未来美学的发展。反思从“美学热”到审美文化的美学谱系,也存在“光晕丧失”和“主体困惑”等理论缺失,但也显出更加开放和多元的美学思考空间。
美学热;二元对抗;启蒙;审美文化;意识形态
20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作为一个开放性的知识话语体系,从“告别历史”的人道主义讨论出发,最终通向了更高层次的现代化人学启蒙和审美文化的开阔景观。充满激情的美学、文学和文化的学术场景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至20世纪90年代产生了分化与变革,伴随着文化场景的更改和学科场域伦理的确立,美学知识话语的启蒙性与公共性逐步转型,“美学研究在原来的问题和思路范围内已进入一个滞徊的状态。”[1]美学自身也经历从对抗政治的人道主义价值取向,到主体性的审美自律,再到更加学科性和专业性的审美主义过程。“随着80年代后期的展开,知识界不断追寻着时代的当下问题,在美学之外连续形成新的热点。相形之下,美学领域则犹如一块弃地”[2]。
一、美的弥散:二元对抗性的消解与公共启蒙的分化
纵观“美学热”,二元对抗式的逻辑框架与现代性文化启蒙的焦虑成为其合法性依据。“审美”与“国家意识形态”之间构成了显著的对抗关系,而以此辐射出的文化主义与国家主义、场域伦理与政治伦理以及个人话语与主义话语之间的对抗 “渗透”于“美学热”的各个场域之中。“在80年代初,‘自我’‘个人’,一如‘人道主义’,都是某种集体性的话语,某种名之为‘启蒙’的话语乌托邦。”[3]美学热潮肩负的新启蒙历史使命被看做是对王国维、蔡元培等现代性审美启蒙的“延续”。20世纪90年代初期逐步消解,根源是二元对抗的消解和公共性启蒙的分化。国家话语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步改变了文艺“工具论”和美学“反映论”的直接干涉,转向文化领导权意识形态渗透以及与市场和大众文化之间的“交换伦理”;从公共性启蒙而言,包括美学家和文学家等在内的知识分子自身也经历了分化的历程,这是导致“对抗性”消泯的重要维度。
在新中国成立后17年时期,总体化国家意志要求“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美学领域的“美学大讨论”直接“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确立唯物论和认识论的美学理论。20世纪80年代新时期,思想解放的潮流促使文艺政策转向“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其中伴随着“清污运动”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呈现出与美学的感性启蒙相互影响和胶着的面貌。20世纪90年代以来,官方面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革进行自身的反思与调整。20世纪80年代延续下来的民间性和个体性审美风格不断消解神圣的宏大叙事,审美文化和市场伦理秩序不断成熟,总体化的国家意志必须寻求新的审美和文艺承载,“赎买”与“交换”就成为崭新的文化领导权策略。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文化霸权”)清晰地阐释了国家意志与市民社会之间的文化领导权关系。市民社会作为国家和社会个体之间的阶层,是广泛开展文化交流和文化争夺的场域,“在这众多的民间团体(分两类:自然的,及契约的或志愿的)之中,有一个或者一个以上的团体,相对地或绝对地起主导作用”[4]。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和“交往原则”凸显了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融合和多元共存。“公民相互之间进行对谈,从而把事物表达出来,并使之形象化;……公共领域(Polis)则为个性提供了广阔的表现空间。”[5]
国家相关部门设立一系列文艺奖项,直接体现了意识形态对精英文化的取舍与把控;对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重新改编与传播,对电影电视播出时间和内容的限制等等,都“无形”中确保社会主义文化价值观的“核心”地位和主旋律色彩。影片《建国大业》《建党伟业》等就实现了政治意识形态和市场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高额的票房收入和传播范围也印证了文化领导权的可行性与操作性。意识形态已经悄然渗透进充满悬疑色彩的有商业价值和艺术价值相生共赢的典范之作,胡编臆想的低劣“雷剧”。“手撕鬼子”“夺命铁砂掌”“神箭手”等桥段,“类似的‘雷剧’、‘神剧’的不断出现,正逐渐娱乐着中华民族的抗战历史记忆,这种状况也引起了广大民众、官方与学术界的强烈不满”[6]。广电总局对主旋律影视剧播放时间的调控、“五个一工程奖”“金鸡奖”“百花奖”等一系列评价机制的侧重等等都保证了国家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把控效应①据统计,自2000年以来广电总局先后出台多项行政指令和措施,调控影视传媒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从而给大众文化和传媒的健康、有序、合理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与保障。比如:2002年3月8日,广电总局下令停播《流星花园》;2004年4月21日,广电总局发布《关于禁止播出电脑网络游戏类节目的通知》;2006年8月,广电总局下令9月1日起各级电视台黄金时间不得播出境外动画片;2007年1月,从2月份起的至少8个月时间内,规定卫视黄金档只能播放主旋律影视作品;2007年8月10日,广电总局责令江苏人民广播电台、南京人民广播电台、合肥人民广播电台、淮安市电视台等四个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发出全国通报批评,同时下发《违规播出机构处罚通知书》,责令其立即停止擅增的频率(道)播出;2007年9月20日,广电总局正式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群众参与的选拔类广播电视活动和节目的管理的通知》,调整以湖南卫视"超级女声"为代表的选秀电视节目过度流行的趋势;2008年2月20日,广电总局发文,自2008年5月1日起,全国各级电视台所有频道不得播出的境外动画片时段,由原来的17:00—20:00延长至17:00—21:00;2008年3月,广电总局发文《广电总局关于重申电影审查标准的通知》,进一步明细了影片审查的标准;2010年6月9日,广电总局发布了《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婚恋交友类电视节目的管理通知》;2014年4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出《总局对卫视综合频道黄金时段电视剧播出方式进行调整》等等。。政治意识形态也更加侧重审美与文艺的情感性、多元化和个体价值,试图在市场和文艺的平衡与“同谋”中,实现自身的价值理念,正如霍尔对大众文化特性的界定:“存在着一场由主导文化发起的持续的和肯定的不均衡、不平等的斗争,不断要去破坏和重组大众文化。”[7]总体化国家文化领导权的调整是促使“美学热”终结的重要一维。
在“美学热”的知识启蒙中,出现了众多的理论流派和美学理论,但“青春体”的学术激情一以贯之。知识分子以真诚的审美想象和心怀天下的启蒙视角完成了美学 的“青春体”学术理念,试图以知识话语的“公用性”唤醒民众并且与宏大的政治意识形态进行对抗。“当作为‘社会代言人’的知识群体逐渐在这一新秩序中获取着自身的‘历史与阶级意识’时,普泛性的人性、主体性或美学的表述,……是一个特定社会阶层的知识群体的主体想象。”[8]知识分子和新启蒙的状况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和20世纪90年代产生了严重的分裂与弥散,文化政治变革的失败、市场经济和消费伦理的勃兴、犬儒化思想的盛行,都使得理想化的现代性文化启蒙遭遇挫折,这也正是“美学热”消泯的重要原因所在。在知识分子场域分化进程中,一部分知识分子积极面向世俗中的市场价值和消费导向,在与市场的结盟中完成了审美话语的多元化价值取向;一部分知识分子依然坚守批判性和启蒙性的知识话语,在对人文精神失落的反思中建构更高层意义上对社会和现实的批判,由此所形成的“人文精神大论战”构成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较为显性的文化景观,并且呈现出世俗的功利主义和超越性的精神理念相互分化的场景,神圣与世俗、精英启蒙与大众狂欢、精神解放与欲望解放同时共存,20世纪80年代所塑造的完美的人性理想和共存于启蒙精神中的审美自由开始解体。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伴随着“后学”的兴起和审美文化的凸显,“启蒙有无必要”和“谁有资格启蒙”的话题被反复追问②对启蒙的质疑与追问一方面是启蒙共同体和知识分子话语权转型与分化的结果,另一方面源自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和世俗化伦理的出现。由此,对话交往和主体间性等新的启蒙策略在后现代场景中得以重构。1992年左右的学术规范讨论、1994年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论争、1997年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证等,都可以视为对20世纪80年代启蒙共同体和知识分子话语权的“解构”与“重构”。他们剥离了“审美”对抗“政治”的二元框架,而是通过对西方后学理论的借鉴与延展,将视角放在更为广阔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民主与自由、文化与霸权、社会公正、经济伦理、民族与殖民、时间与空间等问题上。经过90年代启蒙的不断分化、交往与对话进程,80年代所形成的知识分子“统一”的话语权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自由平等的知识主体建构和“弥散”、“播撒”的学术景观。而知识分子在80年代不断加强的“介入性”“启蒙性”“反思性”与“批判性”话语权特质却保留并延续下来。。在大众传媒和消费主义的时代中,膨胀的信息和丰富的文化给民众提供了大量可供接受和选择的契机,从而能够跳过“启蒙者”获得知识学资源。影像传媒、科普文化、历史记录、学者明星等也纷纷以通俗和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完成了向日常生活的渗透;流行音乐、娱乐节目等也以身体性和感官化使得大众“沉沦”其中,感受身体的愉悦与快感。李泽厚作为20世纪80年代实践美学的代表人物,在20世纪90年代也以“告别革命”的姿态呈现出启蒙自身的 “无力感”,“这次社会转型,实际上是从官本位社会转向金本位社会。所谓金本,就是以经济为本。……我不太相信上层建筑革命、意识形态、文化批判这套东西能使中国问题得到解决。……我现在大谈吃饭哲学,反对斗争哲学,就是注重这个‘本’”[9];王富仁也从鲁迅研究的知识学背景出发,表达了精英意识无可奈何沦落的惋惜,“这样一个世界上我们已经无蒙可启,我们鲁迅研究者所能述说的那些社会历史和社会思想的名词和概念,连十几岁的小孩子都已经背得滚瓜烂熟,能够实现的都已经实现,不能实现的连我们自己也已经无力实现”[10]。在后现代平面化和多元化的语境中,“启蒙”自身似乎已经呈现出无力之感,只能通过“跨越边界和填平鸿沟”①“跨越边界”主要意为日常生活与审美的界限正在逐渐消失,其理论来自费瑟斯通的“消费社会”命题、贝尔对后现代艺术状况的思索;“填平鸿沟”来自詹姆逊对后现代主义艺术“平面化”“无深度感”的论证、波德里亚对符号“仿像”和“超美学”的界定。的努力建构起“弥散”和“星丛”式的后现代知识谱系。当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通过“联姻”而不分彼此之后,精英化的启蒙也就面临合法化的危机。
知识分子的话语权面临政治与商业的双重“夹击”,经历了不断分化和多元化的场景,“启蒙共同体”也已经宣告破裂,“人文精神大讨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争都体现了此种分裂的表征。如果说知识分子在20世纪80年代“美学热”和“文化热”的语境中从社会的边缘走向核心,以告别历史和美学批判的视角重塑匡时济世的历史承担;那么20世纪80年代末期到20世纪90年代的世俗化转向历程中,崇高的使命与批判的激情再次成为了“无意义”。多元化的自由经济和市场伦理取消了知识分子“振臂一呼”的启蒙豪情与激情,也消解了以文化和思想影响政治意识形态的努力。其实,不仅仅是自身政治地位和知识精英的受挫,更为重要的是市场伦理的经济性和实用性成为衡量价值的最新标准。日益崛起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对知识分子的启蒙话语进行质疑的同时,也希望以一种更加开放、自由和平等的姿态进入大众的生活,于是才出现了面向世俗化的努力和彰显生活世界的尝试。知识分子逐步放弃了“启”的高度,也不再将普通大众定位于“蒙”的一方,而是以主体间性和平等交流的姿态完成新的形象塑造与地位转型。鲍曼在《从立法者到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中给知识分子的当代转型进行定位,从“立法者”到“阐释者”的发展谱系也契合了“美学热”之后知识分子的形象重塑。“阐释者”要求在后学语境中,以平等的姿态和主体交流的前提来完成对现象的阐释,破除宏大的、自律性话语霸权,从而增强自身对社会和历史的阐释力度。“扮演着传统的文化立法者角色的知识分子,必然是一个悲剧式的、无家可归的漂泊者。”[11]所以,在“阐释者”的思想引领下,知识分子或者放弃了启蒙的姿态,或者将启蒙理念蕴含于深刻的审美文化场域之中,并且在对世俗化和生活化的肯定中,完成知识分子自身的反思与转型。
二、美的救赎:审美文化与美学的价值重塑
伴随着对抗性的消失,改弦易辙的是美学的“热潮”而并非美学本身,20世纪80年代初步形成的感性生命体验、身体话语、大众文化则逐步从“潜藏”的地位迈向清晰。20世纪90年代实现了本体化的转型。直接契合了日益成熟的市场伦理和多元分化的社会场景,通过“交换”和“赎买”获得一定程度上国家意识形态的支持,从“对抗性”的美学价值转向了“生活性”的交往。此种意义上的“文化”更多的是吸取了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概念,兴起于大工业生产语境和消费社会中的、以现代传媒为主要承载并且引发了大规模公众参与的文化,呈现出与官方的主流文化、知识界的精英文化相对立的面貌。波普艺术和大众文化具有“普遍的(为广大观众而设计)、短暂的(短期内消解掉)、可放弃的(容易被忘掉)、低成本、批量生产”[12]的特质。在大众文化中,不仅仅形成了众多通俗化的产品,更是确证了大众的文化地位和权力话语,形成了从政治到商业,从技术到审美等宏大的空间场域。“文化远不止是对新的生产方法或对新兴工业本身的反应。它还关注在此过程中形成的种种新的个人及社会关系”[13],此种“关系”被表述为个体化的“情感结构”:“它所表征的是社会经验的动态性,因此也常常与那些相对凝固了的主导的、残余的构型显现对立的姿态”[14]。“90年代是一个精英主义消褪、世俗理性普及、商业伦理建构、文化产业登场的时代,大众文化在这诸多因素的作用下成长壮大”[15],不同学科在此间性互涉、不同的主体在此相互交流、新观念与新方法此起彼伏。所以,对“美学热”应当跳出绝对化的时间层面的划分和人性启蒙的局限,应该以生成性、流变性和谱系性的视角发掘其历史影响与文化想象,这样就为“重返80年代”提供了强大的知识学资源和“以古鉴今”的学术动力。
面对美学“热潮”的消解和美学自身的价值重塑,大众审美文化大致可以划分为若干维度。
其一,是来自市场和技术对审美文化的塑造。产生于文化工业和市场伦理中的大众文化以批量复制和市场营销的方式完成“艺术品”的身份转换,“生活性”和“平面化”的特质成为核心。“在现在的社会里,这种文化和工业,和贸易金钱不正是紧密相联的吗?所谓媒介、大众文化和法兰克福学派所称的‘文化工业’,难道不是像生产汽车一样制造出来的吗?因此,在我们的时代里,我们面临着新的‘文化文本’。”[16]大众文化在文化工业的语境中产生,以普通大众为基本的接受对象,并以大批量复制的影视、广播、印刷等传播媒介实现模式化和平面化的文化产品生产,传统艺术中独一无二的“光晕”效应和精英话语已经逐步被摒弃,是“为大众消费而制作出来的,因而它有着标准化和拟个性化的特色”[17]。在现代技术条件和消费市场的影响下,流行歌曲、摇滚乐、肥皂剧和畅销书籍等通过批量复制和商业运作的方式走进千家万户,生产者、传播者和消费者也逐步泾渭分明,相互分离,并且纳入资本和市场流通的框架之中。这样,大众文化从精英启蒙话语的裂隙中应运而生,以市场伦理作为生产和消费的基本准则,强化了使普通民众沉浸其中的感官性和通俗性,并构建个体崭新的 “存在”面貌,形成了与政治意识形态相对抗的宏大民间群体。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大众文化不仅同精英文化一同构成了美学意识形态的反抗话语,更是以势不可当的力度不断消解精英文化的领域,最终造成了“美学热”被边缘化的历史景观,审美也逐步走向了日常生活的领域,“各种物质——技术的方式,压抑着人性的实现。而艺术,作为充满了各种想象力、可能性的‘幻象’世界,则表达着人性中尚未被控制的潜能,表达着人性崭新的局面”[18]。“自1980—1998年,中国的广播电台、电视台分别从原来的106家、38家增长为1 244家、880家,分别增长10.7倍、22.2倍;电视人口覆盖率从49.5%增至87.5%,增长37.9个百分点。有线电视网已遍布中国绝大部分城市”[19]。文化产业借助于高新科技的迅速发展和市场消费的不断深入而获得了更加丰富和多元的空间。由此,审美启蒙的原则就逐步让位于市场的商业伦理、身体的感性体验以及日常生活的实用化价值取向,美学与大众文化相结合形成新的审美文化概念。日常生活审美化、艺术与生活的界限消失、生活中的感性因子和修辞化的艺术形式、从服装到影视的审美表达、对人体感性欲望的肯定等等,这些都成为审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躲避崇高”正是对这一时期审美观念的概括与集中化表达,这不仅仅是大众在后现代生活中多元化和自由化的主动选择,更是市场伦理、商品经济与文化工业的内在要求。
其二,美学也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渗透与转型。自“五四”启蒙运动时期王国维、宗白华、朱光潜、蔡元培等美学先驱对西方美学资源的融合与改造开始,中国的美学面貌就一直受到德国古典美学和启蒙主义话语的影响,以审美的无功利和纯粹性涉入美学研究之中;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同样是从本体论的高度对美的本质和美的问题进行“自上而下”的界定,总体上并没有超越认识论范畴的二元对立框架。20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通过实践美学与文艺美学的建构,完成了美学从认识论到实践论的初步转型,并且也将超验的美学理论“拉回地面”,更加关注主体的思想解放和自由生存。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大众文化的崛起和审美文化场景的出现,都有着和西方相似的后现代文化景观。再加之在“译介热”中对福柯、海德格尔、德里达等理论的译介与重视,“后学”在中国20世纪90年代之后也再次成为学界热议的话题。那么美学在卸下启蒙精英的“光环”和审美自律的现代性体察之后,就需要面对话语延异、主体间性、星丛播撒以及颠覆结构的文化景观。在此过程中,美学不仅仅需要以“未完成的现代性”姿态继续保持从法兰克福学派延续下来的“否定性”与“反抗性”,而且还要以经验化和多元化的视角更加关注身体、感性、心理、生活和环境,由此,美学就必须和后现代文化思潮进行“联姻”,从而保持自身属性的合法性价值,“从罗列和寻找一系列美的特质转变到对审美主体的审美经验进行描绘”[20]。比如舒斯特曼的身体美学从主体的身体出发,将审美经验同性经验进行联系,试图通过身体的快感协调美感,以此来实现美学在后现代时期的复兴;伽达默尔从审美的创造和接受出发,重新界定了人与世界的关系,破除了认识论视域中的话语霸权,重新建构对话和交流的意义世界;韦尔施通过对“非美学”和“超越美学”话题的论述,提出了应该以平等和公正的视角来对待迥异于传统美学的“异质化”主张,并在多元化美学的体验中进入伦理学意义上的“善”的诉求。这样,就重拾了美学的介入性和阐释性,“这种艺术不再提倡征服的伦理学,它提倡的是公正的伦理学”[21]96。由此,在西方“后学”的译介和影响下,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美学面貌也呈现出更加重视身体、重视环境和重视生活的维度,进一步实现了从认识论美学到实践论美学,再到存在论、语言论以及审美文化等美学样态的转型。实践美学的主体性和实践本体性构成了启蒙语境中告别历史的美学对抗与意识形态;而后实践美学则将意识形态对抗的思索直接转化为主体与世界、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存在论层面的意义体察,以主体间性的视角和现象学的方法来完成自身的美学建构,并以开放性的态度和现实化的视角试图将美学同其他学科领域进行融合互涉,具有了宽泛的审美文化意蕴。“超越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确立审美的超越性;超越意识美学与身体美学,建立身心一体的美学;超越主体性美学与无主体性美学,建立主体间性美学”[22],从而为美学自身的发展提供了理论路径。
其三,美学受到了文学与审美实践的挑战与影响。不仅仅是社会、哲学和文化思潮对美学的发展有着形塑作用,文学与审美实践同样也以“自下而上”的态势促使文论和美学自身阐释方法的转变和话语内涵的转型。伴随知识分子对于自身启蒙性的瓦解和精英话语的失落,文学创作本身在20世纪90年代也呈现出多元化、通俗化和生活化的面貌,“知识分子在90年代以后的落差是巨大的,几乎是从现代化设计的参与者和大众精神生活导师的位置上跌落下来,而包括一部分文学读者在内的大众,则越来越沉入世俗化的生活中。……关于文学‘边缘化’的叙述便是对这种现象的沮丧表述”[23]。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实践而言,知识分子的激情和启蒙的动力回应着美学和文化的现代化焦虑与启蒙。《北方的河》正是塑造了一代青年的热血和梦想,对人文地理的学科坚守和对祖国山河改变的向往共同凝聚在颇具男性气息的荷尔蒙分泌中。这种蓬勃的生命动力不仅仅完成了知识分子的宣言,更是以超越凡俗爱情的力量获得了精英式的体察。“他举起自己的诗稿,在粗粝的风啸声中朗读起来。他读着,激动地挥着手臂。狂风卷起雪雾,把他的诗句远远抛向河心。他读着,觉得自己幼稚的诗句在胸膛里升华,在朗诵中完美。”[24]同样,北岛的《回答》中也充满了知识分子胸怀天下、忧国忧民的情感,“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25]。即使是在新历史主义、寻根文学和先锋小说中,依然体现出知识分子的焦虑和变革现实的努力,从《红高粱》的民间大地谱写,到《绝对信号》中现代舞台技巧的尝试;从《山上的小屋》“他人即地狱”的荒诞性焦虑体验到影片《黄土地》的文化反思,都呈现出强烈的主体意识与启蒙情怀。王蒙的《春之声》则是将宏大意识形态与个体的生存处境、先进的知识技术与落后的社会面貌、知识分子主体的价值选择和启蒙话语结合较好的艺术作品,同时在形式上也借用了“意识流”的表现手法,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春之声》全篇贯穿着改革的理念和知识分子的内心独白,从德国考察回国的工程师岳子峰回乡探亲,坐在闷罐车中展开了一系列带有关键词性质的回忆,北京的高级宾馆、《泉水叮咚响》、三叉客机、地主、西门子公司、土特产、百货公司、法兰克福、父亲、《春之声圆舞曲》等等,传统与现代、落后与先进、乡土与国际、愚昧与知识之间产生了强烈的对比和反差,但知识分子对故园的热爱和乡情的眷恋却一以贯之。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实践呈现为“价值多元”和“共生共存”的多维面貌,在这其中有商品经济浪潮的冲击、有审美趣味的分化、有现代性启蒙话语的延续,还有艺术形式上的探索与多元,此种“无名”[26]的审美特征取代了20世纪80年代“二元对抗”的激进场景。“90年代文化结构的变化(多元、多样或无序),为人的发展和文学的发展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当时间和空间敞开之后,文学从相对单一的文化体系中解放出来。”[23]16《活着》正是以一种“无主体”“无中心”“无信仰”态势完成了后现代意义上文学启蒙话语的“自我解构”。主人公富贵在经历了一次次屈辱、不幸、压抑和痛苦之后,已全然消解了对时代和社会的批判意识,只是麻木而休克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过着今后的生活,所谓“啼得血流无用处,不如缄口过残春”正是此意。“权力不仅存在于上级法院的审查中,而且深深地、巧妙地渗透在整个社会网络中。”[27]不仅如此,影片《大话西游》《大红灯笼高高挂》等影片在改编原著的同时,强化了“无厘头”的生活气息和色彩浓重的形象窥视,呈现出审美后现代转向的努力。而与知识分子对审美自律的消解不同,另一派文学实践则以感性的轻松和“痞子”式的生存完成了向市场的靠拢和类似注射 “麻醉剂”与“兴奋剂”的快感,比如王蒙的《暗杀》、洪峰的《苦界》、张抗抗的《情爱画廊》、王朔的《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空中小姐》等小说文本凸显了主体的感官性与身体性。影片《编辑部的故事》《爱你没商量》《大太监李莲英》《有话好好说》等也都剥离了艺术内容与审美形式层面的深度探索,转向了市场效应和大众生活场景。由此,泛审美化和通俗化的浪潮已经席卷了整体上的审美与艺术实践,而美学若要保持与生活之间的“介入性”力度,必须深入到审美文化语境之中,以现实的姿态来完成更高层意义的追寻。韦尔施也曾预言:“不能否认,与日俱增的复杂性会使美学变得更加困难,但是,既然不再局限于那么一些问题,美学会与其他学科产生更强烈的撞击与交流,获得新的研究领域。”[21]123
三、美的反思与美的未来:在政治意识形态与主体感性生活之间艰难前行
美学经历的从人道主义到主体性哲学再到审美伦理的理论进程,最终归结为一场面向个体性自由和人生本体论的抵抗诗学。如果说“二元对抗”维度的消解、政治意识形态控制的变革、知识分子公共启蒙的转型以及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影响构成了“美学热”弥散和美的救赎的外在影响因素,那么还必须从内部学科性的视角对其“未完成性”进行反思,从而给美的未来寻求新的发展空间。现代高等教育的产生、知识的学科化进程以及“形式化”抽象等等,都宣告了近代理性的强大规训力量和无可逆转的现代性进程。从中国“五四”时期的美学塑形到20世纪80年代“美学热”审美伦理,都在文化启蒙的语境中不断开拓美学自身的场域空间,甚至将其提升至“宗教救赎”的层面。实践美学的确立,文艺美学的扩张以及西方非理性美学的“感性化”与“个体化”的渗透都呈现出从审美自律到审美主义的理论谱系。本来,不同的学科有其相对独立性和差异性的知识学对象,但是“美学热”的结果恰恰是美学“随意”辐射进几乎所有的人文社会学科之中,甚至出现了所谓的 “军事美学”“法律美学”“爱情美学”“新闻美学”,“美学热”潮中的急功近利和滥俗倾向相伴而生。由此,审美主义和审美至上的理念就深刻影响到了以文学艺术和文学理论为核心的知识领域,但是“美学化”的学科场景在消褪了“二元对抗”的政治性诉求和激进式人学启蒙的光环之后,在学理层面能否成立、能否带给后现代时期主体真正的自由成为待考察的疑问。比如伴随20世纪90年代学科体制的不断成熟,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都逐渐成为新的反思主体性的知识场域,而审美意识形态、审美体验、审美意识、文学形象、意义价值、审美情感等审美自律论关键术语依然成为文论界的核心范畴,那么片面地借用审美技巧和美学范畴进行阐释当下多元文化现象显得基石不足、高蹈虚空。如果说美学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给文学艺术建构了一个独立于政治和社会之外的价值准则和合法性依据(诸如刘再复的文学主体性理论),那么它却无法弥合宏观层面的审美超越和微观层面的审美形式二者之间的裂痕,也会在后学时代的文化浪潮中逐步成为敝帚自珍的孤芳自赏。“擅长从总体性的人类解放论进行批判的理论却拙于文学文本的形式分析,而擅长文学文本的形式分析的理论又缺乏总体性的社会历史视野。”[28]所以,“美学热”有其历史性的积极作用,也给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的美学、文学和文论发展带来了一定的问题。面对“美学热”自身的反思和文化语境外在要求,审美文化以其强大的开放性完成了审美意识形态的符号彰显与意义表征实践。美学在经历了精英式的启蒙话语之后,需要重塑意识形态的功能进而延续自身的自由性与反抗性;而政治意识形态和市场伦理也要借助大众文化的广阔空间,通过“弥散”的形式渗透进主体的生活领域之中,审美文化便成为多重意识形态交汇的“合力”场域。
美学蕴含着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审美形式作为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层面的一种“符号系统”,往往在审美自律的范畴中透露出某种具有“象征”意义的体系,从而获得更为长久的历史合法性价值。众所周知,文学和审美本身是通过话语蕴藉和艺术形象来彰显其审美特质的,而文本自身则具有大量的社会、政治、经济、历史、文化,乃至于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为艺术而艺术”“绝对自律”的艺术其实是不存在的。《红楼梦》可谓中国古典文学之顶峰,其中依然充斥着大量甚至是琐屑的日常生活场景描写和社会政治层面的明指暗讽,而美学的意义正是在对审美符号的“破译”中彰显了超越性和自由化的人性力量;而20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在倡导形象思维和审美自律的同时,依然指向告别历史和对抗政治的美学“诉求”,意识形态功能成为其生成和发展的潜在动力。美学的意识形态性恰如康德所界定的“无功利之功利性”,并且伴随着美学发展的始终。伊格尔顿在《美学意识形态》中也指明了任何美学层面的追求也必然有着指向现实层面和“符号化”破译的努力,所以审美意识形态就成为了思想“斗争”和“角逐”的场所。对于当前意识形态的理解,已经超越了具有阶级斗争性质的“虚假理念”,而是更多地将其还原为一种精神体系、思想理念和符号系统,“凡是意识形态的都是一种符号,而且这种符号属于现实的一个‘物质部分’或‘物质中介’”[29]。意识形态就成为了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精神生产和信仰表征,是具有生成性和流动性的话语与符号体系。所以,当美学和意识形态领域相融合,一方面通过情感和感性有机协调和调整社会个体与总体之间的法律、政治和社会关系,另一方面也可以与话语霸权“同谋”,通过影响主体的精神领域和价值选择完成宏大话语的统摄。“语言与具象艺术对政治权力的象征再一次进入到中国当代艺术家的视野之中,他们希望通过艺术来参与到权力的运作之中,并纠正权力的滥用。”[30]从鲍姆嘉通的感性对理性“殖民化”的对抗,到布尔迪厄所认为的审美趣味与社会阶层之间的区隔;从迪基的艺术制度和艺术共同体的表述,到费瑟斯通对消费文化的反思与体察,都体现出审美意识形态在阐释美学现象和维持审美理念方面的线索和脉络。
进入后现代时期,西方和中国都开始了消解权威、消解精英式的审美文化运动,以文本间性的视野和符号传播的方式对既定经典和霸权进行质疑与重构,从而彰显出更加平等、民主和自由的审美意识形态景观,审美文化也成为审美意识形态新的“承载”与“表达”方式。固然,审美文化中的意识形态具有新型的“政治控制”和“商业渗透”的功能,但话语霸权同样可以激发大众阵营通过美学意识形态进行自我反抗,“对抗性”依然“潜藏”于后现代文化语境中。众所周知,无论中国和西方,美学和文化的主导话语基本上是由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精英(elite)完成的,知识分子和上层管理者可能不一定具备经济领域的统摄,但是却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启蒙者与研究者,比如西方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中国的“古文运动”“五四运动”以及新时期的“美学热”等等,知识分子以胸怀天下、济世利民的责任感完成了“自上而下”的话语启蒙。进入现代和后现代社会以来,市民社会的崛起、知识分化的场景、个体自由的彰显、平等交流的诉求、民主宪政的追寻、商品浪潮的席卷等等,都促使“大众”的重新出场和文化的再次转型。新生的大众阶层要求破除所有的知识霸权和精英话语,并试图通过一种新型的文化样态和美学面貌来满足主体日常生活的需要。而正是在此种“对抗”的二元对立关系中,大众文化的审美意识形态具有了合法性存在的价值,也成为后现代美学发展的时代契机。美学在从“庙堂”向“广场”的转型过程中,“广场”重新成为美学弥散和对抗霸权的话语空间,并且集合了众多后现代文化资源中的“不确定”形态,从而以“价值论”重新回归至审美意识形态的理论视域中。“美学的价值判断必须在肉体的本能欲望当中重新发现其真正的基础”[31],动态的“体验论”美学契合了后现代时期的审美经验和反抗维度。由此,伊格尔顿、雅斯贝斯、福柯、布尔迪厄、韦尔施、詹姆逊、桑塔格、汤林森等后现代理论家纷纷从政治、市场、消费、文化、哲学、地域等不同领域完成了美学意识形态话语的反思性与对抗性,他们往往立足于大众和边缘群体的视角,以解构主义和文化研究为契机,建立了以多元化对抗一元化、以自由性对抗总体化、以边缘化对抗中心化的理论体系,呼应了大众审美文化的立足点和价值取向。审视未来,审美意识形态将伴随着大众审美文化的崛起和与霸权式文化格局的对抗,终将实现美学层面的主体性自由和人文性的解放。
可以看出,“美学热”之后的大众审美文化的兴起不仅仅是美学自身发展和变革的需要,更是审美意识形态的表征实践、总体化政治规训的变革、市场经济和文化工业的持续发展和市民社会逐步形成等综合作用的结果。在从“美学热”到大众“审美文化”的美学谱系流变中,也存在一些历史维度的遗憾与缺失,我们应当在后现代“泛审美”语境中保持清醒的认知。第一,美学“光晕”的丧失。20世纪80年代“美学热”其实是审美现代性在中国逐渐明晰的过程,公共性文化启蒙的姿态占据了审美的方方面面。与之相伴的是现代艺术的探索、知识分子的激情“启蒙”以及审美对抗政治的策略,这些都内化为如同本雅明所提出的本真化“光晕”效果。而在审美文化的语境中,以“光晕”为核心的经典、启蒙、超越等纷纷走下圣坛,主体沉浸在影像的感官化复制、消费的符号化认同、新潮娱乐的刺激以及无边的赛博时空之中。“理想的俗化现象表明了如下事实,即发达工业社会面临各种理想物质化的可能。该社会的各种能力正在逐渐缩小对人的条件加以描绘、理想化和说明的高尚领域。高层文化变成物质文化的组成部分。在此过程中,它丧失了更大部分真理。”[32]第二,审美“主体”的困惑。“美学热”中实践美学的确立、文艺美学的超越、审美自律的反思以及文学主体的建构等,都从不同维度确证了主体自身的实践性与反思性。而这一功能在审美文化中却被弱化。文化工业秉承的是自动化的生产方式和同质性的受众群体,个体往往是在“伪个性”“伪自由”的仿像中被动地接受各种文化符号,这就直接把20世纪80年代主体主动参与的“集会”“诗社”“沙龙”等公共领域悄然转化为“单向度投射”的被动空间。“任何文化生产者都处于特定的生产空间之中,无论他是否愿意,他的生产总是在某种程度上来自于他在这个空间中的位置。”[33]这不仅是对“美学热”主体实践性启蒙话语的中断,也阻碍了美学价值的延展,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的思索。
审美文化如同一把“双刃剑”,既给中国当下的美学发展提供“兴盛”的契机;同时也需要对20世纪80年代“美学热”的价值进行传承,并对不足之处进行弥补,总体呈现出压抑性与反抗性、受控性和自由性相融合的场景。无论是传承、发展还是反思、批判,审美文化都是未来美学话语释放的重要领域。王蒙曾在对王朔的评判中表达了对未来审美理念的激情憧憬:“我们政治运动一次又一次地与多么神圣的东西——主义、忠诚、党籍、称号直到生命——开了玩笑……是他们先残酷地‘玩’了起来的!其次才有王朔。多几个王朔也许能少几个高喊着‘捍卫江青同志’去杀人与被杀的红卫兵。王朔的玩世言论尤其是红卫兵精神与样板戏精神的反动。……他撕破了一些伪崇高的假面。”[34]所以,审美文化空间可以被政治意识形态所规训和干涉,但是其内蕴的美学超越性、自由性和人文性也一以贯之地延续下来。如果说现代性语境下的审美自律提供了较为显著的二元对抗,那么在后现代性的生活领域中,审美广泛地同政治、伦理、道德、规范等融合在一起,形成水乳交融般的融合关系。这样美学中的多元性、情感性和灵活性就可以从“内部”直接瓦解政治意识形态的“虚伪”和商品市场伦理的“媚俗”,从而给维系主体性完满的生存状况与面貌。由康德所设置的审美与伦理的“鸿沟”在后现代时期已经荡然无存,那么以审美作为后现代日常生活的“症候”,可以随时提醒我们超越现实并且实现精神的自由。“因此,艺术和审美体验就成为知识、经验及生活价值意义的主要范式。”[35]由此,美学就成为众多因素和价值取向的“合力场域”,时刻给生存的主体们进行感性的提醒和面向自由的努力。20世纪80年代“美学热”作为建国以来一次较大的思想解放和激进的浪潮,以启蒙的热情和美学的精神持续而深刻地影响着未来美学的流变:“那是一个充满理想、充满创造性、文学艺术繁荣、美学上充满探索精神的时代。这个时代出现的‘美学热’,以及在‘美学热’中积累下来的种种思想成果,是中国美学界永久的财富。”[36]
[1]赵汀阳.语言和语言之外·编者按[J].哲学研究,1987(3):74-80.
[2]祝东力.精神之旅:新时期以来的美学与知识分子[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153.
[3]戴锦华.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81.
[4]葛兰西.葛兰西文选:1916—1935[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445-446.
[5]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4.
[6]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抗日战争题材影视剧生产与消费调查研究[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4:2.
[7]斯图亚特·霍尔.马琼,译.解构“大众”笔记[M]//赵勇.大众文化理论新编.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99.
[8]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03.
[9]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M].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4:13-15.
[10]王富仁.摸索鲁迅的灵魂——读解洪祥《近代理性·现代孤独·科学理性》[J].鲁迅研究月刊,2005(2):76-79.
[11]齐格蒙·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M].洪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210.
[12]安德鲁·格雷厄姆-狄克逊.理查德·汉密尔顿——波普之父[J].高岭,译.世界美术,1992(1):11-14.
[13]RAYMOND W.Culture and society1780—1950[M].New York:Columbia UP,1958:252-258.
[14]李丽.雷蒙·威廉斯的“情感结构”理论析论[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123-128.
[15]冯黎明,刘科军.文化视域的扩展与文化观念的转型[J].中国文化研究,2010(1):168-174.
[16]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M].唐小兵,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3.
[17]杭之.一苇集[M].北京:三联书店,1991:141.
[18]李小兵.我在,我思:世纪之交的文化与哲学[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74.
[19]陈立旭.当代中国文化产业发展历程审视[J].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3(3):51.
[20]朱狄.当代西方美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235.
[21]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M].陆扬,张岩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
[22]杨春时.走向“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美学”[J].学术月刊,2010(5):91-95.
[23]王尧.关于“九十年代文学”的再认识[J].文艺研究,2012(12):15-25.
[24]张承志.北方的河[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110.
[25]北岛.北岛诗选[M].广州:新世纪出版社,1986:26.
[26]陈思和.试论90年代文学的无名特征及其当代性[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1):21-26.
[27]福柯.知识分子与权力[M]//福柯集.杜小真,编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206.
[28]冯黎明.文学研究的学科自主性与知识学依据问题[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2):36-43.
[29]王一川.语言的乌托邦:20世纪西方语言论美学探究[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263.
[30]柯蒂斯·卡特.视觉文化与符号力量——中国当代艺术与政治的关系[J].杨一博,译.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1):193-198.
[31]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M].王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253.
[32]郝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54.
[33]PIERRE B.Of interest and relative autonomy of symbolic power[J].Working Papers and Proceedings of the Center for Psychosocial Studies(Chicago).1988(20):1-11.
[34]王蒙.躲避崇高[J].读书,1993(1):10-17.
[35]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刘精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180.
[36]高建平.日常生活审美化与美学的复兴[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6):34-44.
[责任编辑:箫姚]
The Dispersion and Reflection of the Great Upsurge of Aesthetics since the 1980s
PEI Xuan
(College of Literature,Henan University,Kaifeng Henan 475001,China)
The Chinese Great Upsurge of Aesthetics in the 1980s generation and extending from the binary confrontation between perceptual aesthetic and political ideology.The history requirements of the human enlightenment and emotional liberation,had fully expressed through the aesthetic knowledge form.This youthful passion of academic scene had differentiation and changed in the late 1980s to 1990s.Examined reason why aesthetic had marginalized,we realized that on the one hand is the adjustment of overall national cultural leadership strategy,on the other hand is the differentiation of public enlightenment intellectuals.In the face of ethics promotion of popular culture,market penetration of postmodernism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literary aesthetic practice,aesthetic culture brings new opportunity to the development of aesthetics which through the attitude of the public,equal pluralistic coexistence theory and interventional perspective of aesthetic ideology,had formed diachronic narrative from the“end”to “continuation”.The spirit of philosophy and enlightenment enthusiasm of Great Upsurge of Aesthetics will also affect aesthetics’future process.Reflection spectrum from the Great Upsurge of Aesthetics to aesthetic culture,there were some theoretical defects such as“halo”loss and“subject confusion”,but it also give us more open and pluralistic aesthetic thinking space.
the great upsurge of aesthetics;binary confrontation;enlightenment;aesthetic culture;ideology
I01
A
1009-3370(2016)04-0155-09
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6.0423
2015-11-27
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 “文化现代性视域中的艺术自律问题研究”(10BZW002);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016M592277);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空间美学的建构与后现代美学理论新变”(2016-qn-081)
裴萱(1985—),男,文学博士,博士后,副教授,E-mail:75638083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