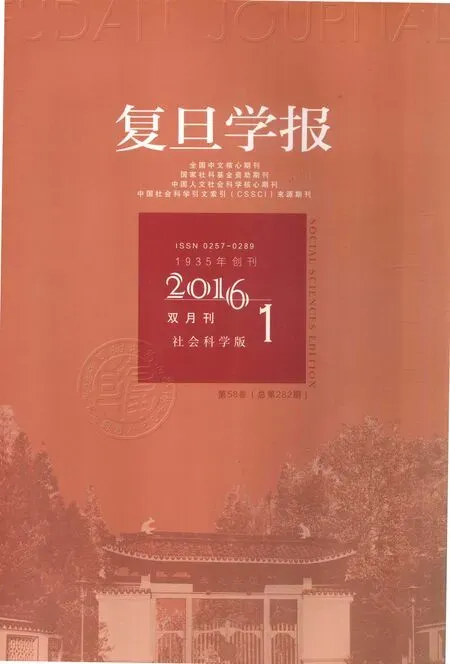《汉志》与早期书籍形态之变迁
徐建委(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2)
《汉志》与早期书籍形态之变迁
徐建委
(中国人民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2)
20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甘肃武威、湖南马王堆、河北定县、安徽阜阳等地均有西汉六艺经书的简或帛写本发现。有趣的是,这些经书的新出文本与今本或《汉志》所录本有很大的差异。马王堆帛书《周易》卦序不同于今本,阜阳《诗经》与四家异,《仪礼》的篇次亦不同于大戴、小戴之编,定州《论语》与《鲁论语》、《古论语》互有异同,这些新出的西汉六艺文本似乎都未见于《汉书·艺文志》。那么,这些版本《汉志》失载?还是它们属于《汉志》之外、刘向未见的民间他种别传之经书?上述两个问题的提出,实在是出于对《汉书·艺文志》的误读。
在传统目录学常识中,《汉书·艺文志》与《隋书·经籍志》一类后世的史志目录被视为同一类型的文献,因此,当有新出土文献面世之时,学者们总会习惯于按图索骥,为其寻找《汉志》目录中的对应书籍。不管是否存在真正的对应书籍,这种做法就学理而论是有所偏差的。原因在于,《汉志》乃是刘向校书之新书目录,而非未央宫原藏旧书目录。此虽极为显见之问题,却多不为学界所重。此处,仅就《汉志》这部新书目录与旧书之关系,粗陈己见。
刘向整理中秘书的情形,主要可参《汉书·艺文志》、《刘向传》、《别录》佚文、阮孝绪《七录序》等文献。简而言之:
其一,刘向以中秘书为整理对象,官府、大臣、民间之书,仅供参校,中书无者,或中书本完善者,刘向并不做整理,自然无整理记录,因而亦不见载于《七略》与《汉志》。故《汉志》未见之书,不能视为刘向未见之书。《楚辞》为刘向所编,中古文《易》、费氏《易》为刘向参用,《张侯论》为刘向所习见,均未见《汉志》。
其二,刘向所校诸书,每种常有多个传本,传本之间差异颇大,每本所含篇数及篇次、每篇所含章数及章次、每章文字多有不同,因而刘向的校书几乎属于重编,特别是六艺经书之外的传、记、诸子与诗赋(兵书、数术、方技类图书分别由任宏、尹咸、李柱国负责)。
其三,刘向以恢复、保留文献原始面貌为目的,对文本的改动,主要改正错讹字句,调整篇、章编次,对于明显的异文,则予以保留,《晏子》之编为其中显例。因而,刘向校书的目的主要是整理出一部善本,结果亦是如此。这也是传世周秦文献主要以刘向校本为祖本的原因。①彼时五经、诸子、诗赋古文本并行于世,且无王朝特别尊崇刘校本的记载,绝大多数校本最后逐渐取代古本,自然是因其优善所致。
其四,《汉志》因据《七略》,《七略》出于《别录》。故《汉志》所载图书除班固新入三家五十篇外,均为刘向新校之书。新书相比于整理之前之旧书,面目已全然改观。《汉志》表面上虽然是考镜源流的目录,实则记录了有哪些文献在西汉末年发生了文本形式上的巨大变革。
其五,刘向之前,与篇的别行相似,以单章形式存在的文本也是当时主要的文献类型之一,有出土简帛为证。同时,章也是刘向校书中原则上不作改动的单元(讹字除外)。经由刘向对中秘书的整理,秘府所藏单章文献群被“归化”入诸子传记,作为独立文献类型存在的单章便在刘向的文献系谱中被“过滤”掉了。因后世文献以刘向校本为主,故单章形式的文献群逐渐失传。原本此类文献群乃是战国秦汉之间的“公共素材”,因其消失,诸子传记之书失去了“第三方”文献证据,不利于后人对战国秦汉学术史的理解。又因各古书之间互见文献极多,失去单章文献群,极易误导后人依据古书之先后,重建一条本不存在的传承或代际之路。另外,因这类文献群的存在,也使得战国秦汉古书与其“作者”、“时代”的对应变得模糊。
其六,六艺、诸子、诗赋的整理情况并不相同。就六艺传记(如《礼记》、《乐记》之类)、诸子两大类文献而言,刘向整理出的文本,乃是一类文献的综合归束之本。即《汉志》六艺、诸子书目除六艺经本之外,多数书目标识或代表了战国秦汉的某一类文献,而非某一部书(汉代人所作传、记除外)。诸子书除《吕氏春秋》《淮南子》外,此种特点尤为明显。六艺经本的情况则颇为特殊,需要略加辨析。
若将《汉志》“六艺略”前后文略作比对,就会发现书目与其小序载录诸经之家派竟不一致。五经之中,《书》《诗》《春秋》书目与小序一致,但《易》《礼》不同。小序所言学官中所习《易》经为施、孟、梁丘、京房四家,书目不载京房经;《礼》经是大、小戴、庆氏三家,但书目却为后氏、戴氏二家。小序在五经之后,并于五经之末均云“某某立于学官”,似刘氏父子所校经书与学官所立之学有关。然《易》《礼》书目与小序的差异似乎说明,书目又与小序无关。
不过,考案《汉书》,我们会发现上述《易》《礼》今文经书目与小序的不同,与各家学问立于学官时间先后还是存在联系。据《汉书·宣帝纪》、《儒林传赞》、刘歆《让太常博士书》、《后汉书·章帝纪》建初四年十一月诏等文献,知西汉五经博士所教习之经典,武帝至宣帝前期为齐、鲁、韩三家《诗》,欧阳《尚书》,后氏《礼》,杨氏《易》,《公羊春秋》。宣帝时期又立大、小夏侯《尚书》,施、孟、梁丘《易》,大、小戴《礼》,《榖梁春秋》。其中《榖梁》,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四种,为甘露三年诸儒讲《五经》同异后立。元帝时,京氏《易》又立,《汉书·艺文志》小序所言正是至此时而止。如《易》类小序称“讫于宣、元”,《书》类小序称“讫孝宣世”,《礼》类亦称“讫孝宣世”。
如此,则《汉志》小序叙事迄于元帝之时。相比于小序,《汉志》书目部分的记载则止于汉宣帝之时,元帝所立京氏《易》则不在目中。
但是除了上述诸家文本外,西汉武帝、昭帝时代学官中还有其他的经文在讲习,这些文本并未载录于《汉志》。学官之外的经文本更是多不见录。其中尤以《易》经本为多。考按《史记》《汉书》,知西汉时《易》经本至少有:中古文本、杨氏本、施氏本、孟氏本、梁丘氏本(三家皆祖田王孙)、京氏本、韩氏本、费氏本、高氏本、淮南本、救氏本等十一个。这十一个传本,都不难见到。且除杨氏本、韩氏本外,其他各本都在刘向校书所涉的知识区域之内。但列于《汉书·艺文志》书目的只有施、孟、梁丘三家。
问题是,刘向校书在汉成帝时,然其所校却集中于汉宣帝时期秘府所藏诸本,非世间所有经本。依刘向校书常例,似只在汉宣帝时,秘府入藏过今文诸家的五经文本。缘何如此?汉制,博士属太常,乃是外官。博士于学官所掌诸经,亦属外官系统。据《七略》佚文,太常又有藏书之处,故博士诸经文本当藏于太常。何种机缘使得博士诸经有机会进入未央宫之石渠阁呢?联系诸本多为宣帝时之传本,我们很容易发现甘露三年石渠辩经之会,正是这些文本入藏石渠的契机。特别是在《汉书·艺文志》、《书》、《礼》、《春秋》、《论语》、《孝经》五类文献的经、传、说之后,均有石渠《议奏》存录,显示出经部文献是以石渠会议的条奏为总结的结构特点。
据《汉书》记载,曾参与石渠会议的学者有萧望之、韦玄成、刘向、薛广德等二十三人。他们所习诸经与《汉书·艺文志》所载文本的家派几乎一一对应。由此判断,刘向所校五经文献,多数是在石渠会议之时入藏中秘。或者说,刘向所校五经秘书主要是石渠会议所集、所议、所藏之本。《汉书·艺文志》曰:“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可知汉武帝时曾有大量图籍入藏秘府,但《六艺略》部分的主要文本却是汉宣帝时入藏,这是深可注意的。
故《汉志》所录六艺经本,只是西汉众多传本中宣帝时期的代表文本,在此之外,尚有许多传本(包括一些非常主流的传本)是在《汉志》之外的。但是,后世所用六艺经本,除了《周易》用费氏,《礼记》用小戴外,其他均上承《汉志》所录本,故知刘向整理之经本,东汉以后逐渐成为主流文本(学官内教习乃为主因),非《汉志》所录本渐次失传。
相对准确地看待《汉志》书单的方式,乃是将其视为一个个庞杂的文献群落的代表,而非一部部今天意义上的单一、自足的书。这些群落在西汉以后,逐渐被优善的刘向校本所取代,文本逐渐单一化和经典化,完成了早期文本由类群向单书的过渡。
这个过渡并非秉承了单一模式,而是约略可以看出三种情形。其一,规模相对成熟的古书,如《诗》《礼》《老子》《论语》等,在西汉有多个传本,经刘向、刘歆父子校录、缮写,传本因此而单一,他本逐渐消失。如刘向校经书以石渠阁辩经诸家为主,《诗》即以齐、鲁、韩为主,兼及河间所献《毛诗》,诸如阜阳汉简本《诗》等他本,则渐不为后人所见。《老子》亦有多个传本,简帛所见及严遵本均为《德经》在上,《道经》在下。据《混元圣纪》所引刘向《别录》,刘向校定本上、下经之次序,及八十一章的分章与今本正同,知今本源出刘向校本。刘向之后,《老子》传本逐渐单一,河上公本、魏晋王弼本结构均承刘向本,他本渐次失传,仅幸存半部严遵《老子指归》矣。
其二,内容、篇章大体成型,但尚未成为一部相对完整著作的一类古书,如《荀子》《管子》《晏子》《庄子》《韩非子》等,西汉时代之前流传于世的,是一些相对成熟的篇或篇组。如《管子》中的《轻重》《九府》、《韩非子》中的《孤愤》《五蠹》等,且各本特定某篇中,章数、章次、内容等互有异同。刘向校书时,这些以“孙卿子书”“管子书”“晏子书”等为名的篇或篇组,被汇总统一,去除重复,勘校成编,成为《孙卿子新书》《管子新书》《晏子新书》等卷帙、篇次、章次定型的书籍。此余嘉锡先生《古书通例》言之颇详。
其三,还有一些单独流传的章或章组,虽具备单章或数章为一篇的形式,各章内容上亦大体相近,有的也有篇或章的题名,如马王堆帛书《老子》卷前四篇古佚书,但这些材料不像“孙卿子书”“管子书”,没有一种共识的类名,即它们不是一部或几部书籍,而是一种无固定归属的材料类文献。刘向父子将这些材料以类相从,重编为一种全新的书籍,如《战国策》《新序》《说苑》《百家》等,其篇次、章次等也为新定。阅《战国策叙录》《说苑叙录》,亦可知矣。
要之,《汉志》乃是刘向、刘歆父子所校“新书”之目录,而非西汉当世所传文献(或曰“旧书”)目录。《汉志》书目的实质,有两点尤为关键:其一,它记录了西汉末年有哪些文献的文本形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而非西汉末年曾有哪些书流传。其二,《汉志》更近于一部“类目”,而非“书目”,即它虽然不是当时所有文献的记录,却可以反映当时世传文献的主体类型。这两个方面,前人多未加留意或重视不足,故对《汉志》颇多误读之处。反观学术史、文学史、思想史诸领域,我们会发现,迄今为止,周秦汉相关问题的研究多在《汉志》框架内展开,即便近几十年来大量出土文献的面世,也依然未改变《汉志》模式的主导地位。然而致命的问题是,没有充分考虑上述两个方面,就将《汉志》的书目结构默认为周秦汉学术和文献的基础背景,虽是对《汉志》书目性质的轻微的误读,却使得我们对周秦汉文献的认识,以及对其的处理方式发生了比较严重的偏差。即便仅仅是学理性的偏差,对于整体的研究而言,也足以具有根本的破坏性了。因此,重视并明晰《汉志》的性质,并有效地利用之,会在周秦汉学术、文学研究领域,促生一种新的问题方式。
徐建委,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易代之际文学思想研究”(项目批准号:14ZDB073)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