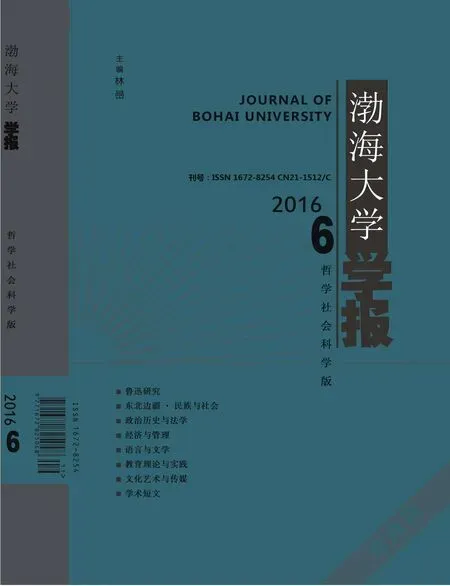论《史记》神话母题的类型、性质及意义
王宪昭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北京100732)
论《史记》神话母题的类型、性质及意义
王宪昭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北京100732)
《史记》作为具有文学特征的历史著作,叙事中使用了大量神话母题。这些母题主要涉及特定历史人物的出身、重大历史事件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天命、征兆、祭祀等。尽管此类母题并非客观历史,却具有写史的文化真实性,对其进行深入探讨对推进中国神话学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意义。
史记;神话母题;母题类型;历史真实
西汉司马迁的《史记》本质上属于历史著作,不仅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而且获得了“史家之绝唱”美誉。众所周知,《史记》涉及大量的神话。“神话”相对“历史”而言,有的认为属于民间文学,有的认为是一个跨学科文类,呈现出复杂的内涵和外延。依据马克思对希腊神话的评价,人们大多认为神话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1]本文所使用的母题主要指“神话叙事过程中最自然并可以进行语义分析的基本元素。这些元素可以在神话的各种传承渠道中独立存在,也能在其它文类或文化产品中得以再现或重新组合。”[2]之所以在表述上采用“神话母题”而不使用“神话”的概念,主要源于神话母题与《史记》神话叙事的碎片化属性的内在联系,从而有效避免过分纠缠于《史记》神话叙事的完整性或把神话与真实历史事件机械对照。
一、《史记》中应用神话母题的主要类型
《史记》作为我国弥足珍贵的历史著作,内容驳杂而丰富,包括彰表历代帝王政绩的十二本纪,记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的三十世家,记载重要人物和地区性事件七十列传以及十表、八书,共计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在如此宏大的叙事中所涉猎的神话母题是相当丰富的,尽管不同的体例中神话母题有所不同,但总体而言,比较明显的母题类型大致有如下几种。
1.文化祖先、帝王或其他人物神奇的出生类母题这类母题的使用也许与《论语》中倡导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有关,这一思想影响到许多文人思考和表达观念时特别注重出身来历中的正名。《史记》中的许多“特定历史人物”①在记述中都应用了神话母题,特别是关于一个朝代始祖的神话叙事尤其关注其非凡出身或来历,如《史记卷三·殷本纪第三》②中记述:“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也有关于帝王诞生的神话叙事,如汉高祖是他的母亲感蛟龙而诞生等。
2.描述重大历史事件应用的图腾、神灵类母题如《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一》叙述:“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这里的黄帝使用各种动物与炎帝作战,借用了保留在神话叙事中的动物图腾母题,实质上是以该动物为图腾的几个部落名称。在《书第六·封禅》中关于一些事件的叙述也使用了有关神灵的神话母题。
3.阐释君权天授、天命难违等命运先验类母题这类母题几乎成为贯穿《史记》的核心线索,书中往往用这一母题阐释天授君权和朝代更替,同时也用这一母题解释人的等级的形成以及重大历史事件的原因。如《史记·三代世表》中借助褚先生的话说“诗言契生于卵,后稷人迹者,欲见其有天命精诚之意耳。”这种观念来源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将天神崇拜进一步社会化,将天神或天的意志具体体现在帝王身上。对此,关于三皇五帝的记载,大多有类似的观念,司马迁在《年表第一·三代世表》的评论中道出自己的主张:“天命难言,非圣人莫能见。舜、禹、契、后稷皆黄帝子孙也。黄帝策天命而治天下,德泽深后世,故其子孙皆复立为天子,是天之报有德也。人不知,以为氾从布衣匹夫起耳。夫布衣匹夫安能无故而起王天下乎?其有天命然。”这种“命运天定的”母题几乎贯穿《史记》对所有重大社会问题的解释,如在《书第二·乐》中提出的“天尊地卑,君臣定矣。高卑已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小大殊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则性命不同矣。”这些关于天命的神话母题自然为统治者的统治与社会等级的划分提供了理论依据。正源于此,司马迁才会肆无忌惮的把汉高祖刘邦说成是刘媪感蛟龙所生的“天子”,而不是“刘媪”与“刘老太公”的儿子,这种看似荒诞不经的历史神话化正有力地说明了“帝王天命”“天子感生”的神话母题在封建时代社会意识形态建构中的重要作用。
4.解释社会现象、社会生活中的征兆、巫术、祭祀类母题这类神话母题数量较多。征兆母题方面,如《书第四·历》中说,至孝文帝时,鲁人公孙臣以终始五德上书说:“汉得土德,宜更元,改正朔,易服色。当有瑞,瑞黄龙见”。征兆母题在《书第五·天官》中更是到处可见,如“天一、枪、棓、矛、盾动摇,角大,兵起。”“西宫咸池,曰天五潢。五潢,五帝车舍。火入,旱;金,兵;水,水。中有三柱;柱不具,兵起。”“北宫玄武,虚、危。危为盖屋;虚为哭泣之事。”这里都把星象的变化作为人间的兵乱、兴衰等的征兆。巫术母题方面,《史记》中也有一些提及巫术的作用以及巫术通神的记述。如《本纪第十二·孝武帝》中记载,齐人少翁以鬼神方见汉武帝。因武帝“所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术盖夜致王夫人及灶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见焉。于是乃拜少翁为文成将军,赏赐甚多,以客礼礼之。”文成告诉武帝曰:“上即欲与神通,宫室被服不象神,神物不至。”虽然后来少翁因弄虚作假被诛杀,但说明在汉代流行通过巫术可以使生者与死者相见的母题。祭祀母题方面,祭祀源于神话的神灵存在母题,无论是早期神话的“万物有灵”的多神,还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产生的神的等级定位以及最高神观念或神的一元观,都会有必要的祭祀与之相适应。如《书第六·封禅》中记载的始皇东游海上,所礼祠的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齐。天齐渊水,居临菑南郊山下者。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盖天好阴,祠之必于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畤;地贵阳,祭之必于泽中圜丘云。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东平陆监乡,齐之西境也。四曰阴主,祠三山。五曰阳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之莱山。皆在齐北,并勃海。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最居齐东北隅,以迎日出云。八曰四时主,祠琅邪。”这些祭祀对象及其礼仪大多承前启后地使用了特定的神的名称性母题,并广泛融入到后世的许多民俗事象之中。
二、《史记》中神话母题的本质体现了艺术真实
《史记》中神话母题的本质是一种虚构。毋庸讳言,任何神话母题都不能与客观事象建立机械的一一对应关系,《史记》也不例外。尽管作者采取历史的手法对以往流传的三皇五帝的神话叙事进行了整合,形成了一个看似符合历史的文化祖先谱系,但就目前考证结果而言,这只能是司马迁建立在某种逻辑思维上的主观推断。我们从《史记》对史前文明时期的人物塑造中的跨时空安排,可以证明这一结论。如关于大禹的情况,一方面把大禹说成是夏代开国者启的父亲,另一方面《史记卷三·殷本纪第三》又记载“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宽。’”将商代的祖先契记述为禹的辅臣。《史记》删除了鲧腹生禹的记载,只是从族谱的关系加以说明,如《本纪第二·夏》中说:“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禹之曾大父昌意及父鲧皆不得在帝位,为人臣。”“(舜)行视鲧之治水无状,乃殛鲧于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诛为是。于是舜举鲧子禹,而使续鲧之业。”禹的生平事迹时间跨度大,行动范围广,绝非一个具体的人物可以在有生之年完成的事业。我们如果与其他文献神话及民俗神话中的大禹作对照,不难发现,禹有时出现在西部羌族地区,有时在黄河下游开山治水,有时又到浙江绍兴会稽山并与涂山女子结婚,后来出现在贵州布依族地区,成为布依族六月六祭祀的对象,甚至还有定九州之宏业。其实,禹本来是一个大禹族,外族的人就会管这个族的人都叫“禹”,如禹族派去治水的人所到之处,人们就说“禹”到了这里,死后为之建造一个大禹陵或把这个地方命名一个与“禹”有关的名字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黄帝”“蚩尤”“尧”“舜”等神话中常出现的母题也是如此。作为特定的名称并不是一个人的专指,而是以其命名的一个族称,许多事迹或文行出处都会箭垛式地归功于这个族称的名下。
记史性神话母题体现的不是“历史真实”却蕴含着“文化真实”。所谓“文化真实”主要是指文化产品在历史人物形象塑造、历史事件叙述或社会生活描绘的基础上,对历史文化精神的正确表达和合理阐释,主要内容上与历史发展规律相一致,与人类对自身历史的认知相吻合。尽管有研究者直言不讳地提出:“今天凡是有史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帝系姓》《晋语》《五帝德》《五帝本纪》与《三皇本纪》等古籍所载的古史是靠不住的,从黄帝到大禹的帝系是伪史。”[3]但一个连“伪史”都没有的民族肯定不是一个优秀的民族。当人类对于史前文明历史的复原束手无策的时候,世代口耳相传的神话也许能为人们打开一线洞天,对于许多记史性神话母题所涉及的具体史料而言,不会是真实历史的传话筒和录像仪,而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高度凝练和再创造。不仅民间神话如此,进入史书文献的神话也难逃“再创造”的窠臼。《史记》中曾记述“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徵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如果“黄帝战蚩尤”作为一个客观历史,则需要实证支撑,但如果作为一个神话母题,那么就有了另外的丰富内涵。如目前许多研究者认为,苗族是古代“三苗”“九黎”的后裔,把“蚩尤”作为苗族的文化祖先,同时也不能忽视,苗族是众多支系的组合体,如黔东南东部方言中叫老祖宗为“榜香尤”,湘西方言区则称“剖尤”“九黎蚩尤”,云贵川西部方言区更直接称“蚩尤”。再如其他神话记载的蚩尤“人身牛蹄,四目六手”“铜头铁额,食沙石子”以及把他说成是少昊末期的“九黎之君”“古之天子”,事实上都是后世的文献编纂者或口头传承者借助于某些历史事实,进行的有目的的文化选择和再创造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的研究者在具体研究中并没有正确认识和理解记史性神话“真实性”的实质。梁启超曾经提出:“中国人对于神话有二种态度,一种把神话与历史合在一起,以致历史很不正确;一种因为神话扰乱历史真相,便加以排斥。”[4]客观而论,神话中可以包含着历史事实,历史叙事中也可以借助神话,“历史”与“神话”对立统一的,之所以产生“对立”是因为二者关于对象的表述方法截然不同,之所以说二者可以“统一”,是因为各自的创作者和受众都坚信表述的真实,历史讲求具象的真实,而神话则关注抽象的真实。由此可见,不少学者提出先秦典籍中有关三皇五帝的记载均不是历史,而是战国至两汉时期文人编造的神话或传说,这种说法只看到问题的一个方面,将三皇五帝看成是历史上的具体的人,而事实上他们是神话载体给后世流传的“一类人”的名称,若试图与个体对号入座,必将违背神话创作精神。因此,能否坚持辩证的唯物史观和能否坚持科学公正的神话观,首先要认清历史真实与神话的“文化真实”的本质,而不是取其形而丢其实。同样,《史记》中应用巫术、征兆等神话母题则说明西汉时期时人鬼神信仰的客观存在,也可以看作是现实历史的客观真实的反映。
关于记史性神话的形成,顾颉刚认为“禹是西周时就有的,尧舜是到春秋末年才起来的。越是起得后,越是排在前面。等到有了伏羲、神农之后,尧舜又成了晚辈,更不必说禹了。我就建立了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5]这类对神话与历史关系的推测自然有其道理,特别是在某些要求历史人物与社会意识形态结合的时期,这类将神话“古为今用”的现象就越加明显。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许多神话人物与历史人物的联姻往往会有多种原因,像上面顾颉刚提出的“禹”与“尧舜”的关系,尽管“尧舜”在春秋时期影响力变大,但在此前的神话系统中并非不存在,而是尧舜禹都是作为一个历史阶段的族群名称而出现的,这些组织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影响可能此消彼长,在不同地域发生了不同的影响,在后世的文化表述中出现有目的的选择而已,就神话的本质与信史之间也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恰恰相反,许多经典化或类型化的历史事件却被口耳相承的神话以一种不自觉的形式有效保存下来。由此我们认为,司马迁的《史记》中的神话母题并非完全脱离历史的虚构,而是历史或时人意识形态的真实写照,应属于文化真实或文学创作真实的范畴。
三、《史记》中神话母题的神话学价值
《史记》中使用的一系列神话母题既体现了作者的理性,也表明了神话的理性,正如黑格尔所说:“神话是想象的产物,但不是任性(Wilkür)的产物,虽说在这里任性也有其一定的地位。但神话的主要内容是想象化的理性的作品,这种理性以本质作为对象,但除了凭藉感性的表象方式外,尚没有别的机能去把握它;因此神灵便被想像成人的形状。神话可以为了艺术、诗歌等而被研究。但思维的精神必须寻求那潜伏在神话里面的实质的内容、思想、哲学原则,一如我们须在自然里面去寻求理性一样。”[6]所以解读《史记》中的神话,需要从神话固有的文化内涵和传承本身加以探讨。
《史记》神话母题为我们考察口头神话与文献神话的关系提供了借鉴。《史记》对神话的取舍使我们看到,神话在民间口头与文献之间的转化变异体现了特定时代的话语选择。以《史记》开篇叙述的黄帝为例,从目前文献中关于黄帝的图腾有多种说法,其中较为典型的有黄帝轩辕氏、黄帝有熊氏、黄帝帝鸿氏等,那么黄帝以熊为图腾是口头神话中一个基本母题,在人类早期社会中以“熊”等动物为族体标志的情形相当普遍。从《史记》记载的黄帝统领以熊、罴、貔、貅、貙、虎等6个部落与炎帝作战,并把熊放第一位,也足以看出“熊”部落在军事联盟中的重要地位,虽然黄帝的父亲少典也称“有熊氏”,如《史记集解》谯周曾解释“有熊国君,少典之子也。”但《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一》则只说:“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循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明显舍去了关于“熊图腾”这类神话母题,这与当时宣扬封建帝王的“真龙天子”观念是一致的。至于黄帝的“熊图腾”我们可以在《史记》以外的许多神话碎片中找出其传承轨迹,如作为黄帝后裔的鲧,死后回归图腾化为黄熊,而鲧的定九州的儿子大禹在治水时也是化身为熊开山运石疏浚河道,显然这不是民间叙事的艺术虚构,而是源于人死返回祖先故土的死后化身图腾的神话思维。中国北方许多少数民族的神话传说也从不同层面证明这一点,如不仅鄂温克族、鄂伦春族、满族、赫哲族等满-通古斯民族都流传着人与母熊婚生的后代繁衍本民族的神话,而且朝鲜族、达斡尔族、蒙古族、维吾尔族等口头神话、有关史料或民俗中也有相关的记载,甚至在傈僳族、珞巴族、仫佬族、怒族等南方少数民族神话传说中同样有女子直接与熊结婚而繁衍熊氏族的母题。这类情况都说明了在史前文明特别是神话时代的历史叙事中出现的图腾母题都是客观现实的反映,体现出人类在文化表现上自我意识的觉醒。
司马迁在处理神话母题与历史的关系时主体上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并且试图为我们找到一种对待口头神话记史的方法论。正如司马迁在《本纪第一·五帝》结尾处所说:“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这既交代了《史记》中如何在写史时利用民间口头神话的积极态度,也从另一个侧面强调了重视民间口头文化的重要性。
《史记》对神话母题的应用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神话与文化的关系。通过比较神话学方法我们不难发现,成书于西汉时期的《史记》,尽管当时的背景是谶纬之学盛行,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流意识却更关注客观世界和社会秩序本身,一些科学观念和唯物思想已经萌芽,特别是孔子提倡的不语“怪力乱神”在主流意识中也很有市场。然而从《史记》对神话的应用来看,无疑是成功的,除了在历史书写方面树立了文学表达方式,而且还留下了把神话介入社会意识形态的有力论据。一方面《史记》对神话母题的应用反映了口头神话向文献神话的转化;另一方面也适应了特定时代的文化环境与受众需求,为我们全面考察神话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素材。神话母题在漫长的口承历史和文化创造中已逐渐积淀为人类潜意识。司马迁所处的汉代作为儒家神学的谶纬之学在官方非常盛行,谶是方士们造作的图录隐语,纬则是以神学观念附会和解释儒家经书,并在后来逐渐演化为民间普遍流行的庙宇或道观裹求神问卜,以及解释人的生老病死等一系列问题,诸如汉墓中大量的殉葬品和绘画,也表明司马迁所处的时代借助于鬼神观念干涉社会意识形态的社会风气。正如顾颉刚所提出的:“汉代人的思想骨干,是阴阳五行,无论在宗教上,在政治上,在学术上,没有不用这一套方式的。”[7]这类情况正好说明了历史上政权与神权合一,甚至“政教合一”所发挥的作用。这类君权神授的母题在许多少数民族历史典籍中也颇为常见。
通过《史记》神话的认知对神话学研究会产生不少启迪。关于神话的概念直至今日仍存在大量的争议,有的认为神话是虚构,有的认为神话是写实,有的认为神话只存在于特定的演述语境中,有的认为神话是与历史叙事相一致的记忆载体,究其原因往往是因为观察神话的角度不同而导致“横看成岭侧成峰”的结果。那么,如何找出研讨问题的一个共同点就成为解决问题并推进学科发展的一个关键点。通过对《史记》中神话母题的观察,我们也许会找到一线洞天,即神话概念源于神话创造者与接受者的共同作用。如《史记》中关于帝王出生的神话客观叙事与写史文献中的“神圣传奇”给人的启迪。这种现象在少数民族的记史性作品中也有大量论据,如蒙古族有探索族源的作品说,女始祖是梅花鹿豁阿·马阑勒(美丽的母鹿),她不仅开创了成吉思汗祖先居统治地位的“黄金家族”孛儿只斤族,而且开创了整个蒙古民族。[8]有神话作品说,成吉思汗的根源,是奉上天之命而生的苍色狼与他的妻子惨白色鹿渡过腾汲思水,到斡难河源头的不峏罕山前住下后繁衍的牧人之汗。[9]另则作品说,萨满有个儿子叫阔阔出,自称能预言未来的事情,对成吉思汗说:“神命你为普世的君主!”他还将“成吉思汗”的称号授予他,并说:“神降旨说:你的名字必须如此!”[10]还有作品说,成吉思汗的祖先孛端察儿是因日光穿过蒙古包进入女子阿阑豁阿的腹中,由此感孕而生。[11]同是叙述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祖先,但所用的神话母题各不相同,开始的单一的梅花鹿作为女祖先,注重的是母系时代以梅花鹿为图腾女性族体群,反映了男性的缺失;后来的苍狼与白鹿婚生成吉思汗家族反映了男女始祖族外婚的情形,而接下来的萨满巫师对成吉思汗的降旨,说明君权借助神权的社会组织形式;而女子感天上的光生成吉思汗的祖先则说明君权天授思想的滥觞。这种情况与《史记》中某些帝王诞生母题有同工异曲之妙。通过对类似母题的比较,我们也会进一步认识《史记》神话母题的神话学价值。
①特定历史人物,人们对《史记》中的“特定历史人物”会有不同的断定,如中国学术史上的“疑古派”认为《史记》中所写的历史人物是虚构的,而“信古派”则认为这些人物真实存在,“释古派”则吸收上面两种观点进行折中式的解释。本文从神话学的视角只关心其存在的文化意义,对此不做真伪之辨。
②本文引文中使用的《史记》版本为司马迁《史记》,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所涉及具体章节在行文中标出。
[1]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762.
[2]王宪昭.中国神话母题W编目[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21.
[3]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251.
[4]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饮冰室专集.上海:中华书局,1926:99.
[5]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26-58.
[6]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M].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97.
[7]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1.
[8]A.Π.奥克拉德尼科夫.博格多乌拉山麓石崖上的蒙古古代人像、铭文和图形[C]//吕大吉,何耀华.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蒙古族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643-644.
[9]额尔登泰,乌云达赉.蒙古秘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1.
[10]拉施特.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M].余大钧,周建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273.
[11]Γ.P.加尔达诺娃.喇嘛教前的布里亚特宗教信仰[M].宋长宏,译.诺沃西比尔斯克:科学出版社西伯利亚分社,1987:14-20.
(责任编辑 陈方方)
I207.73K204.2
A
1672-8254(2016)06-0086-05
2016-08-15
王宪昭(1966—),男,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从事中国神话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