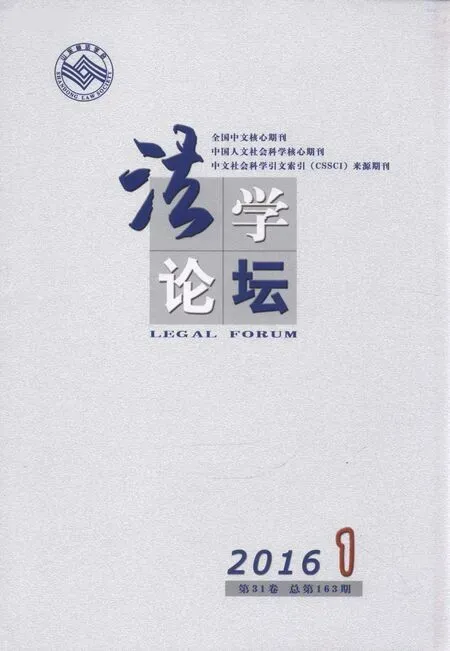解释学法学与法律解释学
谢 晖
(中南大学 法学院,湖南长沙 410083)
【学术视点】
解释学法学与法律解释学
谢晖
(中南大学 法学院,湖南长沙 410083)
摘要:解释学法学和法律解释学是在解释法律和法律解释这两个不同的基础性概念和事实中引申出来的概念。作为两种不同的学问,两者无论在研究对象、学科分类、社会(学科)功能以及解释特征上都是明显不同的。区分两者的基本意义,就是要分清在法学研究中对精神性法律实践和物质性法律实践的等量关注,并以此为基础,区分法哲学和法律哲学这两种并不相同的学问。
关键词:解释法律法律解释解释学法学法律解释学精神性法律实践物质性法律实践
笔者在《论解释法律与法律解释》*该文刊载于《法学研究》2000年第5期。一文中,具体地谈到了解释法律与法律解释两者之间的区分,并认为两者分别与法哲学与法理学相关联。进一步的分析可以是:由解释法律所形成的学问应称之为解释学法学;而由法律解释所形成的学问应称之为法律解释学。虽然,解释法律和法律解释分别关联着法哲学和法理学,并且无论法哲学也罢、法理学也罢,在放大的“解释”立场去理解,毫无疑问,都牵扯到对法律现象和法律解释现象的解释,都是有关解释的学问。然而,我们仍然要说,即使解释哲学在20世纪贫瘠的哲学土壤上矗立了一根令人振奋的高高的标杆,*虽然,在人类的20世纪,科学发达到了一个前人难以想象的地步,同时,哲学在这个时代也有明显的贡献,也出现了一系列彪炳史册的哲学大家,如人们耳熟能详的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哈贝马斯、马尔库塞、杜威、罗尔斯、哈耶克、罗素、爱因斯坦、萨特、尼采、福柯、波普、拉卡脱斯……但一方面,和这个时代科学的突飞猛进相比较,另一方面,和以前两个世纪哲学的辉煌成就相比较,20世纪仍然可以称之为是一个哲学贫困的时代。也许,其它学科的日益繁荣,使哲学独霸学问的历史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也就是说,哲学能够引起人们无限兴趣的时代及人们利用此而制造的哲学霸权主义不可能再恢复。尽管事实如此,但人们还是追怀那哲学兴盛的时代。但它仍然不是、也不可能是哲学的全部。它可能在某种意义上超越了以往的哲学,但它并没有取代以往的哲学。同样,法哲学和法理学并不可能全部由解释哲学的语言所取代。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借用解释哲学的语言来分析两种不同的法学学问,即解释学法学与法律解释学,但我们没有权利阻止、更没有资格否定运用其它哲学理论所构筑的法学也可能是法哲学或法理学。厘定了本文关于解释学在法学研究中的运用之“域”,可以令我们更好地理解解释学法学与法律解释学的区别。
单从名称来看,解释学法学与法律解释学除了文字组合的差别外,在意涵上难以分出其区别。确实,要在两个文字接近的概念间作出其意涵的区别,是一件并不容易的事,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放弃这种区分。只要解释学法学与法律解释学所表达的本体内容不是同一的,就有必要对两者进行学理意涵的区分。那么,两者究竟有哪些区分?
一、从研究对象看解释学法学与法律解释学的区分
一门学科区别于其它学科的关键,在于不同学科的研究对象的差异。倘若研究对象完全相同、或者大部分相同,就只能是同一学科,而构不成不同的学科。解释学法学与法律解释学分别属于交叉学科(法学与哲学)与法学这两大学科的具体内容,因此,两者所研究的必然是不同的对象。这样,就构成了两者各自成为一门学科的前提。
解释学法学*根据笔者目前的阅读范围,在我国较早地以成文方式论述解释学法学的是梁治平。他是在论述解释学法学与法律解释的方法论以及法解释学三者的关系中论述解释学法学的。他认为:“解释学法学即是以哲学解释学运用于法学的尝试,因此,解释学法学与法律解释的方法论的关系,大体上可比之于哲学解释学与传统解释学的关系。”梁治平:《解释学法学与法律解释的方法论》,载梁治平(编):《法律解释问题》,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87—104页。的研究对象是一切法律现象及其背后的决定这些法律现象的自然的或社会的事实。法律现象是指以法律规范为核心与前提的人类规范化的生活实践。因为对法律规范的理解和解释不同,所以,就形成了关于法律现象的不同见解。比如,在价值法学看来,法律应反映人类的普遍的道义要求。当法律和人类的普遍的道义要求相背反时,不应是道义屈服于法律,相反,道义必须去矫正法律。事实上,价值法学在这里设置了一种凌驾于法律之上的规范准则,一旦实在法违反它,即意味着道德价值准则取得了实际的实在法的地位。显然,按照价值法学,法律现象的范围就大为扩展。它包括了人类的一切具有普遍性的道德及道德生活和实在的法律及法律生活。*参见张乃根著:《西方法哲学史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下文中皆同)第一编;沈宗灵著:《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下文中皆同)第二编;张文显著:《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下文中皆同)第一章。而社会法学派则认为,法律不仅仅是实在的形成规范文本的国家意志,规范文本只是死的文字规则,与此相对应,还应有“活的法”或者“行动中的法”。依据对法律的此种理解,社会法学特别青睐民间法。所谓民间法,就是活生生地流传于民间的用来规范人们日常公共行为、解决人们之间纠纷的习惯规范。不难发现,按照社会法学的立场,法律现象的范围几乎包括了人类的一切“活动的”规范秩序。包括国家实在法秩序、民间实在法秩序和人类道德秩序。*参见张乃根著:《西方法哲学史纲》第9、11、12;沈宗灵著:《现代西方法理学》第四编;张文显著:《二十世纪西方法学哲学思潮研究》第3章。这样,法律现象就可以被解释为人类的一切有效的规范实践和规范生活。
当然,一般地说来,“纯粹”的法学家还是比较欣赏规范法学——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关于法律的观点:法律就是主权者的命令。*说明这种一般性,并不表明作者对于法律的态度就是站在规范法学的立场上。事实上,基于理想与现实相统一的立场,我更加倾向于对价值法学和社会法学加以调和,从而确定法律的范围,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说明法律现象的内涵与外延。当然,这种调和是不容易的,特别是在社会法学总是要实证某种存在的合理性,而价值法学则总是要说明某种理想的必要性的情形下。尽管在人类的秩序形成机制中,并不是国家法独霸地起作用,但自从人类进入国家化的文明形态以来,不论在君主主权时代(国家)还是民主主权时代(国家),可实证的、并且影响最大的法律每每是以国家的名义制定的。所以,价值法学基于人类理想和正义的追求而进行的批判,往往是以国家实在法为靶子的;社会法学基于人类生活的现实经验之实证所进行的批判,也往往以国家实在法为对象。不过,我们要说的是:人们完全可以对实在法抱着一种轻视甚至否定的立场,但是,轻视的前提是正视,否定的基础是肯定。因此,价值法学也罢、社会法学也罢,他们都不是以存在的实证立场去否定国家实在法,而是在功能的实证角度提出对国家实在法的质疑或否定。法学发展的事实证明,价值法学的繁荣和社会法学的兴盛都未削弱、也不可能真正削弱国家实在法的功能,而且在这个号称国际政治朝多极化方向发展的时代,国家实在法的作用反倒成为国家利益保护的规范基础,因而其实际作用反而加强。所以,就价值法学与社会法学的实际功能而言,他们只是分别提出了改进国家实在法功能的方略,而不是否定了国家实在法,并且也不可能(哪怕在功能视角)否定国家实在法。这正是规范法学——分析实证主义法学之所以能与前两种法学流派鼎足三立、并且在事实上规范法学还往往占据先机的原因所在。规范法学所理解的法律现象,严格局限于国家的实在法。因此,在规范法学家眼里,道德价值理想和社会习俗规范都构不成解释学法学的解释对象。*参见张乃根著:《西方法哲学史纲》第7、13章;沈宗灵著:《现代西方法理学》第三编;张文显著:《现代西方法理学》第2章。
笔者在前文中,只是一般性地交待了我们比较熟悉的西方三大主流法学流派关于法律现象的不同观点。20世纪以来西方的非主流法学可以说真正达到了那种学派林立的境地,这其中就包含了不同的法学流派对法律现象截然不同的理解和解释。以上的交待旨在说明:法律现象作为解释学法学的主要对象,对它的不同设定就决定着解释法律的内容之宽狭、性质之别异。因此,如果对法学作一实证考察的话,我们将会发现,只要是流派化的法学,很难有共同的法律现象观念。
笔者以为,法律现象是以法律规范为前提和核心的人类制度实践系统。*此前,我曾提出了关于法律现象的定性的回答,认为法律现象是“法律这一客观事物之本质的外在表现,是法律的外部联系的总和,其特点是具有直观性、表象性。”参见谢晖著:《法学范畴的矛盾辨思》,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8页以下。它的具体内容包括法律规范、规范意识、法律主体、法律行为和法律反馈(监督)。法律现象之为解释学法学的对象,当然地包含了如上诸方面的内容。即解释学法学不但要解释法律规范,而且也要解释由法律规范所带来的一切社会现象。这就是解释学法学所要解释的法律现象,也就是解释学法学对法律现象的解释内容。
解释学法学不但要解释法律现象,而且要解释法律现象所赖以产生、发展和变化的深层原因。这种深层原因,就是解释学法学对法律现象的发展线索、脉搏和规律的解释。特别是对法律为何产生、何能产生以及其历史的存在限度、作用限度等等的解释。当然,由于解释者的前见的差异、立场的不同、学养的区别以及在更为广阔的意义上的法律文化的影响,对法律发展规律问题的学理解释也许会显得千差万别。甚至每个流派的解释在一定意义上讲,缺乏一种通约和公度的标准。因此,解释的客观性在这里是相对的,而解释的主观性却成了绝对的。但正是在这种对法律发展规律的不同解释中,我们可以进一步地领略解释学法学的魅力,可以在某种多元性中求得法学思维的进步和发展。
法律解释学的研究对象不是笼统意义的法律现象,而是法律现象中的一种,即法律解释现象*目前国内出版的有关法律解释学的书,很少对法律解释学的对象问题作出解释,甚至也很少使用法律解释学这一概念。就笔者目前所掌握的材料,以成文方式提出过法(律)解释学一词和类似词的有梁彗星(参见梁慧星著:《民法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陈弘毅(参见陈弘毅著:《法治、启蒙与现代法的精神》,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6-61页)、梁治平(参见梁治平(编):《法律解释问题》,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87-104页)、陈金钊(参见陈金钊著:《法律解释的哲理》,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6页)、季卫东(参见季卫东著:《法治秩序的建构》,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7-144页)、郑戈(参见梁治平(编):《法律解释问题》,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65-86页。他用的是“法律解释理论”)等学者。而对法律解释学的对象(而不是法律解释的对象)作出过专门探讨和研究的是陈金钊(参见本注引陈金钊书)。不过,在陈著中,我们可以明显发现他把解释学法学的对象和法律解释学的对象混为一谈。。有法律必然有解释,这既取决于法律自身无可避免的缺陷以及由这种缺陷可能引发的人们之间的行为冲突,也取决于人类理解能力的有限及由这种有限所导致的人们之间的理解冲突,还取决于人们为了维护法律的权威和秩序而通过解释实现法律统一性的要求。但是,法律解释现象,即使我们抛开了解释法律*直到目前,对解释法律与法律解释的混淆使用仍是一个严重的事实。这对我们理解和区分解释学法学和法律解释学带来了困难。但是,它们两者的区别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如果我们进一步探讨、了解解释学法学和法律解释学之区别的话。参见谢晖:《论解释法律与法律解释》,载《法学研究》2000年第5期。的内容,也还是一个相当广泛的概念,特别是在当代中国。就一般情形言,我们可以发现:既存在着有权解释,又存在着学者对法律的学理解释,还存在着普通学者对法律的解释;既存在着以司法为主导的解释(特别是在西方世界),也存在着以法学家为主导的解释(如在当代世界依然现实有效的伊斯兰教法中),还存在着以立法为主导的解释(如当代中国的法律解释体制);既存在着作者中心主义的法律解释,也存在着文本(法律)中心主义的法律解释,还存在着读者中心主义的法律解释……可见,法律解释学的对象,涉及一切法律解释现象。但是,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法律解释现象,法学家切不能 “眉毛胡子一把抓”,而应当有轻重缓急之分。当然,具体到不同的法律解释学的作者,他们对究竟哪些对象之与法律解释学的建立更为重要,有一个权衡选择的过程。但一般地说来,法律解释学的目的,主要在于对法律解释问题进行理性的指导。特别是给司法活动中的法律解释行为提供必须的方法和观念。因此,如果说整个法学都是应用学科的话,那么,法律解释学就更强调应用性。法律解释学的目的不是(或主要不是)给人们提供精神享验,而是给法律实践提供理论对策。
法律解释学不是简单描述法律解释现象。它作为一种学问,当然要深入到法律解释现象的具有一般性、共同性、规律性和普遍性的问题中去,即法律解释学要能够对人们解释法律的行为提供或产生必要的理论指导,需从法律解释的现象中得出法律解释的一般性、共同性、普遍性和规律性的结论。这样,法律解释学的对象就从法律解释现象延伸、拓展到有关这一现象的一般性问题中。在法律解释学内部,对法律解释现象的研究只是它的手段,而通过法律解释现象抽象、上升到对其一般性问题的认识,是它的目的。
二、从学科分类看解释学法学与法律解释学的区分
这里提出学科分类问题,是要解决解释学法学和法律解释学的学科归属问题。从两个词汇的表面看去,两者都紧密地关联着法学,似乎都应是法学的分支学科(三级学科)。但在笔者看来,两者各自有其学科归属。简单地说,解释学法学应当归属于某种意义上的交叉学科,而法律解释学则理所当然地是法学(特别是法理学)的应有内容。对这一结论的论证和回答,还需要进入到两者的更为广阔的知识视野中去。
解释学法学是以20世纪勃兴的解释学哲学的原理和方法来分析、理解和解释法律现象及其内在发展的学科。解释学哲学(也有人称哲学解释学)可以说是人类哲学思维的最新视野。它的集大成者是德国的“跨世纪”哲人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该书在我国出版了两个译本,其一是由王才勇翻译的该书的第一部分,由辽宁人民出版社于1987年出版;其二是由洪汉鼎翻译的该书的全译本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其中上卷于1992年出版,全书于1999年出版。另外,伽氏的著作在我国翻译出版的还有《哲学解释学》,由夏镇平、宋健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伽达默尔集》,由严平编选,邓安庆等翻译,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版。这些著作大都集中于伽氏的哲学解释学理论。伽翁不但梳理了人文-精神科学之核心观念和概念的历史,梳理了解释学作为精神科学重要内容的发展历程,而且富有创造性地将普通解释学发展成为解释学哲学。*当然,哲学解释学的创生,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并不是伽氏一家的贡献。伽氏只是它的集大成者。在他之前有施莱尔马赫、狄尔泰等解释学大师;同时,他所师承的海德格尔以及海氏所师承的胡塞尔等都对解释学的哲学化作出了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讲,伽氏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完成哲学解释学的。在他的同时代,法国的保罗·利科、他的同胞哈贝马斯等在不同的层面或视角也对哲学解释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从而使这门学问更具有世界性。其特点是把人类的理解和解释置于人类存在的本体视角,从而使理解和解释获得了在哲学殿堂中以本体论身份立足的资格,克服了以前的解释学长期以来把理解和解释置于方法论的习惯。哲学解释学的创生,毫无疑问,是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事件之一。它已经成为一种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学说。即使在我国,也有一些从事现、当代西方哲学和现、当代西方文学艺术的学者投身于哲学解释学的介绍和研究工作。*其中在我国研究哲学解释学的代表性著作是:张汝伦著:《意义的探究——当代西方释义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殷鼎著:《理解的命运:解释学初论》,三联书店1988年版。另外,一大批西方哲学解释学的著作也已经在我国翻译出版。当我们简要地了解了解释学哲学的发展之后,进一步的问题是:解释学法学既然以解释学哲学的原理和方法探讨、解释法律现象及其一般性问题,那么,它究竟应属于法学还是属于哲学(解释学哲学)?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使我想到了与此问题相象的法哲学的归属问题。
法哲学作为用哲学的理念和方法来观察、理解、论述法律现象的学问,对它的学科归属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学者中有不同的处理。例如,在德国,长期以来,秉承古希腊理性主义哲学和法学理念与传统的学者,总是将法哲学置于哲学体系中。至今在德国的不少大学中,法哲学课程是由哲学系的教授们讲授的,从而形成了所谓哲学家的法哲学。但在同一国度,另有一些秉承近、现代科学实证主义传统的法学家,则主张将法哲学置于法学学科中,从而形成了所谓法学家的法哲学。而在大陆法系的其它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法哲学大都被归置于法学学科中。*对此,可参见舒国滢:《走出概念的泥淖——“法理学”与“法哲学”之辨》,载舒国滢著:《在法律的边缘》,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05-118页。舒氏虽未直接提供法哲学归属的材料,但其论文对我们了解有关法哲学的学科归属有帮助。也可参见笔者在《法思辨:法哲学的基本精神》(载郑永流主编:《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中的论述。但即使如此,对法哲学的具体学科归属仍然是争论频仍的问题。即使在我国的法学家中间,这一问题的争论也照例存在。笔者认为,在学科分化并不太明显的时代,一门学问的出现,只能进行非此即彼的学科归属,这具有合理性。但在学科分化现象越来越烈的历史时代,还需要这种非此即彼的学科分类方式吗?事实上,所谓交叉学科的出现,就是为了克服并解决根据过度的分析传统所带来的一些新兴学科分类上的困难。因此,法哲学的学科分类不应当墨守成规地、非此即彼地放置于既有的学科分类框架里,而应当有新的思路。这一思路就是交叉学科。
谈论法哲学的学科归属,旨在进一步说明解释学法学的学科归属。几乎同法哲学一样,解释学法学也有一个究竟归属于解释学哲学(哲学)还是归属于法理学(法学)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在事实上必然会是见仁见智、各有说辞的。笔者目前还没有看到有关就解释学法学的归属问题进行研讨的论著,这种情形只能说明该种学问至少在我国尚未引起充分的、足够的重视,而并不说明笔者所提出的问题是个假问题。同时,这也不妨碍我们对解释学法学的学科归属问题作几种假设的不同回答。
第一种假设是有人把解释学法学归属于解释学哲学的范畴。其理由是解释学法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系从解释学哲学那里引借而来。一门学问究竟应归属于哪一学科?这取决于其分析方法和由这一分析方法所得出的基本原理。既然解释学法学借用了解释学哲学的分析方法和原理,那么,将其归属于解释学哲学(哲学)这一学科体系中,也是无可厚非的。然而,问题是这一假设的理由是否充足。一门学问借用了其它学科的分析方法和基本原理到何种程度才能归属于所引借的学科?*可资我们思考这一问题的例证有制度经济学和经济分析学法学。它们大体上都以经济学的方法(特别是成本-效益分析方法)来解释法律制度问题,但前者大体上是经济学的领域,后者却被置于法学的领域。这里明显地存在我在文中提出的同样的问题。相关论著,参见[美]康芒斯著:《制度经济学》(上、下册),于树生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美]R·科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美]理查德·A·波斯纳著:《法律的经济分析》(上、下),蒋兆康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等。解释学法学是否没有自己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而一味地借用解释学哲学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既然解释学法学应当归属于解释学哲学,那么,为什么还要把其称之为“法学”,而不称之为“哲学”……倘若对这些问题不能作出进一步的回答,那么,这种假设的说服力也就相应地减弱。
第二种假设是有人把解释学法学归属于法学的范畴。其理由是解释学法学的对象是法律现象及其一般性问题,而不是其它。同时,解释学法学虽然借用了解释学哲学的分析方法和基本原理,但它并不是对被借用者的简单套用,相反,它在运用被借用者的基础上,形成了足以作为一门学问的独特的原理和方法。不但如此,而且解释学哲学在创生时,也借用了古老的法律解释方法和原理,以至于在解释学哲学中,“法学诠释学”(即我们所讲的解释学法学)具有“典范意义”。*参见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471页以下。表面上看来,这一假设在理由论证上似乎振振有词,但它也存在着需要继续回答的问题。例如:在没有哲学解释学时也有发达的解释法律的行为,但为什么那时的解释法律行为及其结果不叫解释学法学?没有解释学哲学基础和方法支持的解释学法学能够独立地存在吗?既然解释学法学应当归属于法学范畴,那么,它应当被视为法学发展的事件还是哲学发展的事件?这些问题,看上去似乎书呆子气十足,但如果不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这一假设的成立也成问题。
既然前述假设都成问题,那么,如何处理解释学法学的学科归属问题呢?这需要我们略微探讨一下前述假设成问题的症结所在。可以说,前述假设的问题就在于:事实上,解释学法学的存在,既离不开解释学哲学的原理框架和分析工具,同时也难以脱离开法学的固有对象——法律现象及其一般性问题而成立。但另一方面,它又不是解释学哲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与法学的固有对象之间的简单的结合。可以说,运用解释学哲学的一般方法和原理来解释法律现象及其意义问题,是一个不同学理之间的有机结合过程。严格说来,解释学法学既不属于解释学哲学(哲学),也不属于法理学(法学),而是介于解释学哲学和法理学之间的一门学科。如果说,受近代以来科学实证主义的严重影响使得学科科际分界过分明显,*对此,作为法学家的伯尔曼不无忧郁地指出:“隐藏在这种把法律与宗教截然分离的做法后面的乃是在过去九个世纪里曾经一再威胁着西方人整体性的二元思维模式。主体全然分离于客体,人疏离于行为,精神疏离于物质,情感疏离于理智,意识形态疏离于权力,个体疏离于社会。对这些二元论的克服,便是未来希望之所在。我们所期待的新时代乃是一个综合的时代。”“我们已将世界分割成不同的部分,但它们并非互不相关、独立自存的不同实体;一旦我们把它们截然分割开来,使其相互封闭,则它们会反过来禁锢和窒息我们自身。”[美]伯尔曼著:《法律与宗教》之“导言”,梁治平译,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31、33页。为了克服这种分割的缺陷,他在分析西方法律发展史上作出了巨大努力。参见[美]伯尔曼著:《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这说明,普遍联系的观点对我们的分析而言并未过时。从而需要人们设法克服的话,那么,所谓交叉学科一词的出现就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事件。正是在此种背景下,把解释学法学从单向度的学科归类模式中解放出来,而把它置于交叉学科——解释学哲学(哲学)与法理学(法学)的交叉学科,就显得理所当然了。解释学法学既不能属于解释学哲学(哲学),也不能属于法理学(法学),它是两者优化杂交的产儿,它应有自己独特的学科归属。
然而,法律解释学却是法理学的固有内容,它理所当然地需要归属于法理学(法学)。对它的论述,需要我们从简要地回顾法学和法律解释的历程中进行。众所周知,法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几乎可以说,有了法律就有相关的法律思考,即有相关的法学。也许,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上,法学的表现形式不尽相同(如历史越往前推,法学越明显地存在于所谓“元典”当中,反之,越往后推,特别是近代科际分化明显以来,法学与无所不包的“元典”越来越远,同时,法学有了自己的“元典”),但学者们在不同时代总是能提出和法律相关的问题。*关于法学起源及其发展问题,可参见古棣、周英著:《法和法学发生学——法和法学的历史探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不过,该书对法学的论述,严重地受到国家主义法律观的羁绊。另可参看何勤华著:《西方法学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法学的最直观的问题是对已经存在的法律作出解释。因此,解释法律是法学最基本的使命。在中国,一种学问延续其生命的基本方式就是世世代代相传的解释。我们的先人为我们大体留下了六大学术遗产,即经学、文学、律学、佛学、医学和兵学。在这六大学术遗产中,除医学和兵学相对而言其创造性著述和对经典的解释性著述并存外,其它诸种学问大都是对既存的经典(或法典)的解释,这样,在中国古代,学问就是以对元典的解释为主要存在形态的。从而经解、律解、诗(文)解、佛解成为中国古代“解释学”的四大支柱。所以,人们把中国古代的“纯粹法学”,又称之为律学。可见,在中国古代律学中,对法律的解释构成了它的真正骨干。*但令人遗憾的是,在有关中国古代法学的著述(如各种版本的《中国法律思想史》)中,有关律学的专门论述少的可怜,这使人有理由怀疑相关著作是否在论述中国古代的“法律思想”;同样,在已经名垂青史的思想家的论著中寻章摘句、拼凑罗列的“法律思想”,能否大致地(而不是真实地)反映这些思想家对法律的见解,也很成问题。令人高兴的是:据闻,在何勤华教授即将完成的《中国法学史》中,对律学在中国法学中的地位有较充分的体现。至于西方法学,同样也是在对法律(如罗马法、教会法等)的解释中发展起来的。世界上最早的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波伦亚大学就是以讲解和传授法学起家的。法律解释传统的积累,形成了人们进一步对法律解释方法和技巧的深刻关注,由此便形成了法理学的骨干内容。直到今天,真正的法学家(而不是同时兼跨法学与其它学科的学者)所垂青的仍然是对法律规范进行系统分析的法理学。能否这样说:离开了法律解释的法理学,至少是残缺不全的法理学;离开了法律解释的法理学,也是缺乏实证基础的法理学。法理学的发达,离不开对法律解释现象进行再解释、再建构、再创作的发达。法学的发展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关于法律解释及其学理研究的发展史。由此便决定了法律解释学对法理学(法学)的当然归属。
在解释学法学与法律解释学的不同学科归属中,我们可进一步看出两者之不同。
三、从社会功能(作用)看解释学法学与法律解释学的区分
作为两种不同的学问,解释学法学与法律解释学在功能上也不相同,这就构成了区分两者的又一基础。我们知道,不论解释法律还是法律解释,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追求对认知或理解对象的真理性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讲,解释法律与法律解释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都有违伽达默尔之解释学哲学。*伽达默尔以《真理与方法》一书名世,但他既反对把理解与解释视为方法,也否定在“精神科学”领域里通过理解与解释能够达致所谓真理。据该书中文全译者洪汉鼎在“全国法律解释学学术研讨会”(2000年8月·青岛)上介绍:当他向伽氏提起翻译该书时,伽氏并不以为然。伽氏对不同文字间的可译性持相当的怀疑态度。这在其《真理与方法》中有所反映。他多次强调:“谁真正掌握了一门语言,那就无需再翻译,甚至可以说,任何翻译都似乎是不可能的……完满地使用语言就包含着如下意思,即我们无需再把自己的母语译成另外一门语言,或把另外这门语言译成自己的母语,而是用外语进行思维。”“翻译所涉及的是解释(Auslegung),而不是重现(Mitvollzug)。对于读者来说,照耀在本文上的乃是从另一种语言而来的新的光。对翻译所提出的‘信’(Treue)的要求不可能消除语言所具有的根本区别。”[参见该书下卷,第491、492页,不过,在1995年伽氏对洪汉鼎先生的回信中,他对翻译有更进一层的论述:“现在我们确实要学会克服对一种语言或另一种语言的中心主义。你无疑在盖尔德赛策教授那里对诠释学历史有了深入的认识,因而我非常赞同你的努力(引者按:指翻译《真理与方法》一书的努力)。”参见洪汉鼎著:《理解的真理》,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69—370页。对翻译持“不可能性”看法的学者不止加氏,在其他许多学者那里都存在。如奎因认为翻译具有“不确定性”(参见[美]W.V.奎因著:《真之追求》,王路译,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1页以下);戴维森认为:没有信仰、价值观和理解方式之共同基础,就没有可翻译性。(参见[美]戴维森著:《真理、意义、行动与事件》,牟博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麦金泰尔则更进一步主张不仅不同语言间具有不可翻译性,而且在同一语言的不同的时代也具有不可翻译性(参见[美]阿拉斯戴尔·麦金泰尔著:《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万俊人译,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但是,解释法律与法律解释的这种共同性并不能肯定两者在功能上是相同、甚至相近的。由此进一步的逻辑推导是解释学法学与法律解释学在功能上也不可能是相同的。那么,两者的功能各自是什么呢?
解释学法学是对法律的一种哲学认知方式。它是有关法律的智慧之学。尽管解释学法学并不能垄断人们对法律的哲学认知和智慧,就像存在主义法学、康德主义法学、黑格尔主义法学……照样不能垄断人们对法律的哲学认知和智慧一样。然而,解释学法学毕竟是要以哲学的镜子照亮法律的殿堂,甚至还可能会解构、颠覆法律!从此不难发现,解释学法学固然要关注法律存在的现实,但它对法律存在现实的关注,不是亦步亦趋地揭示文本的微言大义,而是要在学理上提供一种关于法律理解的多面性和解释法律不肯定性。人们不能期待解释法律的唯一性和肯定性,更不能强求这种唯一性和肯定性的实现。解释学法学闪烁着人类理解和解释法律的哲学智慧,但这种闪烁不是像白炽灯一样强光刺眼,而是像七彩灯那样令人入迷。解释法律的这种特征,就决定了解释学法学的功能不是、或不仅仅是为了我们诸多的法官、律师、检察官、议员、以及行政官所期待的“理论指导实践”。当然,这样说,并不否定解释学法学的探讨,在客观上可能对法律、特别是立法产生实际的影响和作用,也不否定不少从事解释学法学的哲学家或法学家对自己所钟情的事业怀着一种“致用”的渴求。但是,我更倾向于从事解释学法学的人怀着一种关爱自己生命的态度去探讨解释学法学。也就是说,把解释学法学和自己存在的生命本体紧密联系起来。它不能是人们为了混碗饭吃的手段,而是理解与解释——一种生命存在对法律根据、法律规范结构、人的规范需要和存在……的隐喻的解破或揭示,因此,它的基本功能在于解释者的精神游戏和思维对弈;在于研讨人类关于法和法律的思维方式、思维结构;在于学问的历险与探求——极而言之,是“为了学问而学问”。
说解释学法学的功能,是解释者的精神游戏和思维对弈,也许会被误认为是将解释过程作为其功能。这种质疑,乍看之下,是有道理的,因为所谓游戏,就是一个游戏者和程序相伴的过程。程序对游戏起着一种严肃的作用,因为有了严肃的程序,游戏在过程中就可以显现其功能。在本质上讲,解释法律作为游戏,与艺术作品创作和鉴赏中的游戏并没有什么差异。*伽达默尔把游戏作为本体论诠释学的入门,他认为:“如果我们就与艺术经验的关系而谈论游戏,那么,游戏并不指态度,甚而不指创造活动或鉴赏活动的情绪状态,更不是指在游戏活动中所实现的某种主体性的自由,而是指艺术作品本身的存在方式。”“只有当游戏者全神贯注于游戏时,游戏活动才会实现它所具有的目的,使得游戏完全成为游戏的,不是从游戏中生发出来的与严肃的关联,而只是在游戏时的严肃。谁不能严肃地对待游戏,谁就是游戏的破坏者。”(参见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130、131页)。可见,只有在严肃地对待游戏的过程中,游戏的使命、作用、意义才得以显现,才能形成足以令人称道的游戏效果。虽然,自表面看去,解释法律的活动所体现的只是解释者自治地理解的法律,但是,解释者并不因为是在进行精神游戏或思维对弈而显得自娱自乐。因为解释者在与法律现象及其背后的支配因素进行对话或游戏时,还会逻辑地出现第三者——解释的读者(游戏的观者)。因此,解释法律既体现着解释者对待游戏的态度,也体现着观者对游戏的兴趣。解释法律的最严肃和最值得称道的成果就是形成关于法律的学说。*诚然,并不是说所有解释法律的活动都会形成有关法律的学说型成果。因为解释法律既可以是正襟危坐在书斋里的学者的严肃游戏,也可能是一位激情四溢的案件当事人对法律的真诚或愤恨。但是,本文所探讨的解释法律主要是前者,因为只有前者,才可能编织为解释学法学。解释学法学就是解释法律这一游戏过程的文本型成果。但是,这一成果的形成,并不意味着解释法律这一游戏的完结,恰恰相反,它只是游戏的一个驿站,并且由它导开了更大规模的游戏——作者、文本和读者之间的游戏。于是,解释学法学的功能或作用就以更大的规模展开了。可以认为,解释学法学的具体成果影响的大小,端在于人们对这一成果之游戏参与程度、参与规模和参与的持久状况。当解释法律的成果只有作者一人的参与,而他人无法参与或不愿参与时,可能表明两种情形:或者是不能道人的旷世奇作(但只要它的文本存在,迟早会引起观者的参与);或者是对解释法律之游戏过程缺乏严肃。不难想象,前种情况出现的可能较小,但后种情形并不难见。这可从反面证明解释法律活动即使作为解释者自治地对法律的理解和解释,也同样会汇入社会其他主体的精神中去。这时,解释法律及解释学法学就产生了对社会的功能或作用。
把研讨人类关于法和法律的思维结构和思维方式作为解释学法学的使命和预期的作用,并不难以理解。因为人类认识史,就是一个薪火相续的过程。这对解释法律而言照样适用。特别是人类在“轴心时代”*所谓“轴心时代”或“黄金时代”,是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等西方学者用来描述人类历史自距今大约3000—2500年这段历史时期文明发展的情形。众所周知,在这段时期,世界文明从东到西不约而同地产生了一系列辉耀千古的伟大思想家和不朽著作。例如在中国有百家争鸣,同时中国文化的“元典”大体上产生在那个时代。在古印度,产生了佛陀和一系列影响后世的佛经。在古波斯,产生了著名的袄教(拜火教,全称琐罗亚斯德教。参见元文琪著:《二元神论:古波斯宗教神话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在中东,产生了犹太教和《旧约》。在希腊,产生了在其后几乎影响到全人类的经典人物和著作。重要的是,从此以后,人类文明便进入到了一个成熟的新天地。所创造的具有“元典”性的成文的思维文本,奠定了人类其后对世界认知的思维框架。即使在法学领域也是一样,所以,今天当我们谈到法治时,言必称亚里士多德、称管子;但谈到人治时,又言必称柏拉图、称孟子……今天蔚为大观的法学,究其历史发展,原来就建立在点滴积累之上。真所谓溪流汇大江、积土垒高山。在这个意义上讲,人类只有首先保守点什么,才能开新出什么。不抱有某种保守观念,就不可能有开新。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每个人的创造性劳动,往往是站在前辈人成功的肩上的。解释学法学的作用之一,就是要对人类关于法和法律的思维结构和思维方式作出系统的反思和解释。就此而言,解释学法学的对象不仅是法律现象及其背后的决定因素,而且还有人们世世代代对法律及其背后因素的思维成果。可以说,当解释学法学以法律现象及其背后的决定因素为对象时,解释学法学是对外部世界的探讨;但当解释学法学以人类对法和法律的思维成果为研究对象时,解释学法学则是在理解、反思和解释自己。从而解释学法学变成了对人类关于法和法律智慧的学说。我们知道,如果说法是不依赖于人的意志而客观存在的事物的规定性的话,那么法律就是人类对法认知的产物。*关于法与法律的联系与区别,在我国近年来多有论述。大体上形成两种观点,其一是形式与内容区别说,如孙国华就持此论。另一种是本质区别说,如郭道晖等学者就持此论。笔者对两者的解说,参见谢晖著:《法律信仰的理念与基础》,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73页以下。也就是说,法律是人类智慧的产物,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法律的这种特征,决定了解释法律创新的艰难。这意味着解释学法学如果要能为人类留下足以称道的思维智慧,就必须设法超越法律自身的智慧;就不但要深入人类的法律思维结构和思维方式中,而且要达到“青出于蓝胜于蓝”的效果。否则,人类对法律的理解和解释就很难超越法律自身的智慧水平和思维限定。解释学法学的这种功能和作用,进一步发展就是极而言之的“为学问而学问”的功用。
“为学问而学问”在我国长期以来曾遭到人们不断的非议。今天它仍然没有获得人们“同情的理解”。*1997年,在沈阳召开的一次法学研讨会上,一位法学编辑在会上发言时,主张为学问而学问的观点。在会议闭幕式上,该编辑所在的单位领导在会议总结时,对该编辑及其观点从领导的视角(而不是学术的视角)提出了“严肃而激烈”的批评。但对解释学法学而言,如果它要发挥某种人们期待的对法律实践的指导作用,则首先要形成精细的、系统的学问,即首先要在这门学问内部能形成自圆其说的解释体系和解释机理。从此意义上说,只有为“学问而学问”,才能“为实践而学问”。“为学问而学问”并不影响在客观上实现为“实践而学问”。反之,在一定意义上讲,只有做到为学问而学问,只有发挥解释学法学的现实批判精神,才能更好地在客观上实现为实践而学问。这里便引出了解释学法学对法律实践的、特别是法律适用的作用问题。
笔者认为,解释学法学并不追求对法律实践的直接指导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解释学法学不对法律实践产生作用,而只对法律学理和法律思维产生作用。事实上,解释学法学所产生的学理的或思维的作用,必然间接地会辐射到法律实践中去。不过其过程应是漫长的、其实效是久远的、其特征是间接的。也就是说,对于法律实践而言,不能期望解释学法学立竿见影地对它起到指导作用。这是解释学法学与法律解释学在对法律实践的功用上的基本区别。解释学法学对法律实践作用的这种长时效特征,有时可以穿越漫长的时空。就像产生自远古的某种学说至今仍然对我们的思维习惯、行为方式产生着具体的作用一样。
法律解释学的作用主要是直接指导人们的法律实践。这也是与前文关于法律解释学的研究对象相关的。法律解释学的研究对象是法律解释现象。而法律解释现象不论是所谓“正式解释”还是“非正式解释”,归根结底,都主要是为了使现行的、实在的法律能更通俗地展示在世人面前,能被更多的人所了解。对法律的非正式解释(无权解释)也有可能是由学有专长的法学专家进行的,从而也有可能形成系统化的学理,但其目的和作用是为了更好地使人们理解现行的或曾经存在的实在法。这就使它与解释法律的现实批判精神严格区别开来。可见,即使非正式解释,也主要以指导法律实践、特别是法律适用为使命。至于正式解释(有权解释),它本身是一种国家的权力行为,是一种体制化的解释,而不是法学家自治的学理行为,即使某些法学家解释法律的学理行为要成为正式解释,也离不开权力的作用和支持。*我们知道,不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世界,都有一些法学家对现行的实在法的解释被当权者赋予了法律效力。例如在古代,就有罗马帝国将一些法学家的解释(有些甚至不仅仅是法律解释,而且还是解释法律的内容)赋予了法律效力;在当代,欧洲一些国家仍然赋予一些法学家的法律学说以法律效力。即使在我国,一些著名法学家(主要是从事部门法的学者,尤其当他们幸运地参与过某部部门法的起草时)对于具体法条的解释,也深受司法实践的重视,甚至有些法院的判决就直接以法学家的解释为准绳。但在这里,都明显地渗透了国家权力的作用。因此,法学家的法律解释之所以产生法律效力,不是一个必然的结果,而是受权力操纵的结果。它把法学家的解释限于一种由权力所设定的体制中。这就与解释学法学对法律实践的作用机理明显有别。法律解释学既然以具有明显法律实践作用的法律解释现象为研究对象,那么,它的功能也相应地与其研究对象的功能相协调。固然,法律解释学可能对现存的法律解释现象作出反思、提出批判,但这种反思与批判并不能达到否定法律解释的程度。一旦到了那种程度,则进到了解释法律的地盘。这正是法律解释学更注重法律解释的技术研究,而并不注重法律学理和思想创造的原因所在。如果法律解释学不能对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实践起到实际的指导作用,不能对人们,特别是进行正式解释的人们提供一种解释的技巧和工具,那么,法律解释学就没有发挥其作用,或者它并没有深入到法律解释的世界。与此同时,法律解释学对法律实践,特别是法律解释的实践的作用,应当是立竿见影的。即只要人们掌握了法律解释学所提供的解释法律的原理和技巧,就能立马对法律解释的实践产生正面的作用。这与解释学法学对法律实践作用的长时效性也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另外,法律解释学对法律实践的作用,主要不是一种观念的启迪,而是实际的操作技巧的传授。正因为这样,法律解释学不能、也不可能像解释学法学那样,做到“为学问而学问”,追求强烈的实践效果,这既是从事法律解释学的学者应有的出发点,也应是他们所期待的目标和结果。所以,从事法律解释学的学者总是具有某种“入世”精神的。但从事解释学法学的学者未必要具有这种“入世”精神。有时,拥有某种“出世”精神,反倒是从事解释学法学所必须具备的素质。否则,就难以做到解释法律时的“板凳要坐十年冷”。
由上述论证可进一步得出的结论是:法律解释学必然是应用性的,解释学法学则不以应用性为当然追求。这就是两者在作用和功能上的区别。
四、从解释特征看解释学法学与法律解释学的区别
在前文的论述中,我们大体上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解释学法学更多地关联着解释法律的活动,尽管并不是说一切解释法律的人类行为都可以(或有资格)成为解释学法学的观察视野,但能够肯定的是解释学法学的视野必然是人类解释法律的行为。其宗旨是在解释哲学的框架下探讨人的规范存在。而法律解释学则更多地关联着法律解释活动,它旨在为人类解释法律的活动提供一种现实可用的方法和技巧。由此也决定了两者在学科归属上的差异。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两种不同性状的解释。
虽然,解释学法学和法律解释学都涉及解释一词,但是,这里的解释在性状上各有千秋。人们在探究解释问题时,一般认为解释具有两个属性,即解释的客观性和解释的主观性。解释学哲学诞生之前的解释学,大都以追求作者或文本的原意为目的,认为人类的理解和解释总会接近甚至复制作者或文本的原意,因此,解释不但具有客观性,而且寻求解释对象的客观性是解释学的最高任务。解释者究其实质只是复制作者或文本客观性的机器。解释者不存在和不应存在自我的理解,从而解释者不能有自治性。然而,解释学哲学的产生,使先前解释学的这种“过分的自负”受到了致命的一击,从此以后,哲学解释学中弥漫的是“作者死了”的说辞。特别是伽达默尔赋予“偏见”以合法性,使人类的任何理解与解释都在客观上只能被限制在“前见”的框架下得到了系统的哲学论证。从此,那种确定的意义世界遇到了空前未有的挑战。只要有理解,理解就会不同;同样,只要有解释,解释就会相异。于是,解释只剩下了主观性,或者说解释的主观性成了绝对的,而其客观性成了相对的。*参见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二部分,特别是341页以下;殷鼎著:《理解的命运:解释学初论》,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页以下。张汝伦著:《意义的探究——当代西方释义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页以下。这种两极化的关于解释属性的学说,在那些对解释学哲学有一定了解的我国法学学人中亦有所体现。*如苏力的《解释的难题:对几种法律文本解释方法的追问》、郑戈的《解释法律的社会构造》以及刘星的《法律解释中的大众话语与精英话语——法律现代性引出的一个问题》(上述论文均载于梁治平(编):《法律解释问题》,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抱着怀疑精神来审视解释(法律)现象。然而,更多的法学学人,在论述法律解释时所谈到的解释却是既讲客观性,也论主观性,并且一般地说,从事法律解释学的人还不太欣赏过分注重法律解释的主观性。克服解释的主观性,寻求客观性或确定性,应是法律解释的追求。从而也成为以它为研究对象的法律解释学的追求。*参见梁彗星:《民法解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65页以下;陈金钊:《法律解释的哲理》,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6页以下,以及张志铭著:《法律解释操作分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页以下,特别是其中的第58页以下的内容。那么,为什么会造成解释学法学和法律解释学中的解释具有如此明显不同的性状呢?一言以蔽之,在于两种学科本身的要求。
解释学法学是站在法律之外的立场上理解、分析和解释法律。所谓“法律之外”的立场,就是说它并不拘泥于实在法的限定,相反,它还要以某种理想或某种与实在法明显并不合辙的社会现实来说明、否定或矫正实在法的合法性。虽然,在这里我们也许可以发现另一种客观性,即解释者对社会现实观察与解释的客观性,但解释学法学并不强求、也不可能强求人们对社会现实解释的唯一性。同样,解释学法学也不强求人们解释法律的唯一性。不论价值法学所青睐的自然法、社会法学所欣赏的民间法还是规范法学所垂注的实在法,都是解释学法学能予以包容的。但这种情况在法律解释学那里就是不敢想象的。这种站在法律之外观察、理解和解释法律的情形,并不以实现苏轼所讲的在庐山外面观庐山的那种效果为目的。*众所周知,苏轼有名诗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轼:《题西林壁》)。言外之意是说,要识庐山真面目,须到庐山外面去。要做一名旁观者来解释对象。相反,由于在法律外面观察法律、理解法律和解释法律,就为解释者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理解空间,从而使解释的视野更为开阔,使解释的视角更为多元化。这种情形,必然使解释学法学中所讲的解释在现象上更为主观。也许这种情形在解释者的视角里能够提供建立一种良善法律的根据,从而体现出另种意义的客观性。然而,对于实在法而言,它始终都是主观的。它有可能帮助人们在立法上建立一种好的法律,但对于既有的实在法而言,它是一种削弱甚至“破坏”的力量。这正是在一个社会动乱或变革的时代里人们一般倾向于实在法律之外的价值呼唤、社会实证,但在社会稳定的时代人们更倾向于对实在法进行规范分析的原因所在。
同时,解释学法学之解释法律,旨在建立一种法学的学问体系。任何学问体系,不可能以一元化为归宿。对学问的一元化要求,往往是一种政治权力行为,而不可能是学术行为。或许,在某个学派内部,“掌门人”要求自己的门人谨守某种一元化的教条,但这样的学派,往往距衰落不远。在学问世界之所以难以达成同一的立场、共同的认识,端在于学问的解释主体是以某种“前见”为解释的根据的。固然,解释主体面对的往往是同一对象,但即使是对同一对象的解释,也逃不过其对该对象之“前见”的制肘。这就使解释学法学中的解释一词不可避免地加重了主观性的色彩。或许有人会问,难道法律解释中的解释主体在解释时就不带有前见吗?这个问题很好!既然前见普遍存在于阅读、理解和解释者身上,那么,法律解释的主体也不例外地受前见的影响。但问题在于,一方面,法律解释主体不能自行选择解释的文本,它的解释对象是确定的,那就是现实的法律。这样,就使得在法律解释之时,解释者受前见制肘的能力大为减弱;另一方面,为了克服前见对于法律解释可能造成的解释主观化的影响,解释法律(特别是其中的正式解释,而法律解释学之研究法律解释,主要是以正式解释为对象的)往往采取国家权力安排下的体制化模式。因此解释体制问题也就成了法律解释学必须关注的对象。*例如,张志铭以中国为例,探讨了法律解释权与解释体制(参见张志铭著:《法律解释操作分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20页以下);董嗥在其专著中则专章论述了“司法解释体制”(参见董嗥著:《司法解释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80页以下)。在该体制中,解释主体、解释权力、解释的效力等等都被法定化。这就尽可能地把法律解释限定在法律的“客观”意义世界,也能较好地防止法律解释的恣意、放任。由于对法律解释学之解释的性状在后文中还要论述,我们还是回到解释学法学之解释的主观性状中。
解释学法学在解释性状上的主观性,决定了解释学法学自身的特征。这就是在解释学法学中,哪怕解释者对法律抱有一种放任、恣意的立场,只要其在逻辑上能够达到自圆其说、在论证上能够严密有力,则并不妨碍其解释的成立。也并不妨碍其构成为解释学法学中的一种学说。可见,解释学法学在其解释的主观性基础上必然造成其学问体系的开放性,开放性是解释学法学的另一个重要特征。
至于法律解释学中解释一词的特征,在前文论述解释学法学之解释的特征时,笔者已经涉及,这就是它对客观性(或确定性)的追求。下面,笔者将继续探讨这一特征的原因。
法律解释学中解释一词的的客观性要求,既与法律解释学的研究对象相关联,也与法律解释学的任务相关联。就法律解释学的研究对象而言,我们已经知道,它是以法律解释现象为研究对象的。但就法律解释而言,它则以一个国家现行的实在法(当然,由于国际组织和国际法的发展,在当代法律解释中还出现了国际法解释问题,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特别是国际法的法理问题,很值得法理学进一步思考和研究*对此,我曾在《“入世”与法律的世界意识》一文中提出过呼吁,但也仅停留在呼吁上。对我国学者而言,国际法法理的研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该文原载于《法制日报》1999年11月25日,转载于《法理学、法史学》2000年第1期和《新华文摘》2000年第2期。)为解释对象。法律是一种以稳定性、确定性为特征的行为规范,这是由于法律的任务就是要使人们的行为服从于规则的治理,就是要通过规则治理实现人们之间交往行动的秩序和自由。法律自身的这种特征,使得法律往往以准确的、明晰的和大体确定的语言得以表现。虽然,法律也存在它的隐喻,但那是解释学法学所要揭示的任务。在现实法律世界中,不需要通过法律解释来揭示法律的奥秘,而只需要通过解释法律来进一步明确法律文本的字面含义,从而使人们能更好地理解、应用法律规范,实现立法所期待的秩序。既然法律在文本上是以准确、明晰的文字来表达的,那么,法律解释的解释者就有可能、有能力实现法律解释的客观性。在一定意义上说,法律解释的客观性与它的合法性是相通的。或者说法律解释的客观性就是指广义的合法性(当然,自狭义而言,法律解释的合法性实际上就是指法律解释要符合相关的解释程序、解释主体、解释权的规定)。法律解释的客观性,就是要揭示解释对象——法律文本的真实含义,就是要使解释出来的语言文字符合法律的规定。可见,法律解释之客观性在广义上与其合法性的一致。总之,法律语言的特点,不但为法律解释的客观性提供了一种可能,而且也使它的实现比解释法律之客观性的实现要容易得多。*当然,这并不是说法律解释完全是客观的,也不是说它可以无所遗漏地揭示法律的意义。法律解释同法律一样,既然是人的思维的产品,是人类智慧的结晶,那么,它具有主观性因素在其中也就并不难以理解。同样的是解释法律虽然以主观性为特征,但它并非没有客观性。每个人借以揭示的根据是客观的、每个人解释的结果也是客观的。从此意义上讲,解释法律的主观性就是以客观方式展示解释者的主观思想。它不但不排斥客观性,而且必须依借客观性。法律解释的此一客观性特征,决定了法律解释学在总体上追求客观性的特征。可以说,当法律解释学向人们宣告它主要是为法律解释行为提供一种技术指导时,其追求客观便昭然若揭。
就法律解释学的任务而言,它不是发散性地给人们提供一种理论或思想指导,即它不仅作用于人们的意识世界,而且更要作用于人们的行为世界。即法律解释学要能具体地指导人们对法律的解释活动。法律解释学的任务是与法律解释的任务紧密相关的。法律解释的任务就是为了法律在人们行为中的更好应用,特别是在司法实践中的更好应用。它与法律一样,是直接规范人们行为的,正是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有法律效力的)法律解释是最后的法律,是“行动中的法律”或“活的法律”。只要法律的运行倚赖于法律解释,就说明法律的文本只是纸上的法;就说明实际上是法律解释最后完成了真正的立法;也就说明了法律秩序的形成,直接取决于法律解释。如果说法律本身具有明晰性、准确性和确定性的话,那么,法律解释就是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要顺利实现解释法律的这一崇高使命,必须具有解释方法的指导,同时借用这种解释方法应能够通达法律的客观殿堂。能够帮助人们达到法律之客观殿堂的,就是法律解释学,就是这一学科对人们提供的解释方法和解释技巧。因此,如果创造不出能较为便捷地认知、理解、揭示、通达法律客观性的方法和技巧,那么,法律解释学就没有完成其应有的任务。而要完成这一任务,就不能离开法律解释学的客观、实用、方便和效率。
在解释学法学与法律解释学之解释的差异中,我们进一步揭示了两者之间的差异和区分。这种差异和区分是客观存在的,我在这里的论述只是使客观存在的两者的差异得以用理论性的言论表现出来。那么,通过理论方式区分两者的意义何在呢?
五、区分解释学法学与法律解释学的意义
一种理论的解说,只有具备明确的意义时,才能不仅使理论变得更为圆润,而且也对实践产生实际的、更大的影响。虽然,笔者主张在研讨学问时研究者应尽量放弃某种功利因素的考虑,从而使其能够轻松地进入学术的研讨状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笔者反对学理的意义设定,也不意味着笔者否定理论必然与实践的关联。相反,笔者所要反对的是那种只能满足研究者的孤芳自赏、而对其它社会主体不发生实际作用的理论。
具体到解释学法学与法律解释学,对它们在理论上加以区分的意义追问也许显得更为必要。因为在中国新近的法学研究中,一种对于“纯粹概念”辨思的非议与日俱增,似乎进行概念的学理思辨就是不联系实际,就是说些假、大、空的道理。好像只有在田埂上的描述或公民中的访谈才有实际意义,才不落文人的酸腐俗套。这种对概念辨别的否定就体现在所谓“超越概念主义法学”的口号上。笔者觉得,一方面,诚如卡西尔所言,“人是符号的动物”,*参见[德]恩斯特·卡西尔著:《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34页以下。它可以被进一步解说为人是概念的动物。概念既是人类认识对象的最基本的方式和结果,而且也是人类生活区别于其它动物生存的基本特征。缺乏对概念的辨思与梳理,人类交往就寸步难行。人类文明就是在对概念的辨别和梳理中渐积渐进的;就是通过一系列概念符号使人们的思维更便捷、行为更方便、理解更准确、解释更清晰;就是通过概念的辨析使人类的行为选择少一些成本付出、多一些利益所得。另一方面,就我国的法学而言,还远远没有进入到所谓概念法学的境地。概念的明晰和说理的透彻与我们的法学还有一定距离。在这种背景下,对概念辨析的任何否定、担忧、恐惧,未免显得自作多情。由此就可能把我们引领到解释学法学与法律解释学辨析的意义世界中。
解释学法学与法律解释学的概念辨析,首要意义是说明两种不同的认识实践(人类的精神性实践)。在《法思辨的实践经验基础》一文中,笔者曾将人类实践经验划分为“物质性实践”和“精神性实践”两个方面。*该文刊载于郑永流主编:《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解释学法学与法律解释学在总体上说来,都是人类“精神性法律实践”的表现。但它们所涉及的对象——法律及其背后的人类需求和社会事实、法律解释及其体制化的规则等——却是物质性的社会实践和精神性的法律实践共同存在的。社会需求与社会事实是最原始、最“纯朴”的物质性社会实践之表现,法律则在上述物质性社会实践的基础上经过了一番主体的思维加工和意识梳理。因此,它介于“物质性社会实践”和“精神性法律实践”之间。法律解释是解释者对法律这一精神产品所进行的说明,它更接近于“精神性法律实践”。从此可以发现,在解释学法学与法律解释学的研究对象上,学问的实际层次较高(解释学法学),它所涉及的对象则较广,而对象经过主体精神过滤的程度却较浅。反之,学问的层次较低(法律解释学),则其涉及的对象也较狭,但对象受主体精神加工的程度却较深。如果从这种现象出发来理解解释学法学和法律解释学,也许我们还会错误地发现,法律解释学比解释学法学在学问的层次和深度上更高一个档次。但只要我们更进一步地追究解释学法学的对象时,就会发现,解释学法学是在法律这一人类的精神实践经验基础上反思它所赖以存在的社会根基,因此,解释学法学自身作为一种人类精神性的实践,其突出的特点是反思性,它不以法律的表象为根据来解释法律,而是以法律所存在的广阔的社会需求和社会事实为根据来解释法律。这就形成了解释学法学作为人类思维活动的基本特色。但是,以法律解释现象为研究对象的法律解释学,更倾向于一种对法律解释之原理、技巧、方法的经验描述,从而它并不追求法律解释背后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动因。由此可见,法律解释学与解释学法学相比较,它并不是反思性的,而是描述性的。因此,在层次上也就不可能高于后者。
解释学法学和法律解释学作为人类的精神性实践所表现出来的上述不同特征,可促使我们进一步把两者作为不同的学科来看待。在我国的法学中,法律解释学的一些内容虽然可以在其中找到,但它的体系化尚不明显。在已经产生的一些法律解释学的著作中,可以说往往把解释学法学的部分内容掺和进去,从而使人感觉到在该学问的高深处和浅显处的反差太大。这样,既妨碍对高深的和解释法律相关的问题之专门研究,也影响建立一种有利于指导法律解释实践的法律解释学。而在我国的交叉学科中,目前并不存在一种解释学法学。这使得哲学家们在涉及其它学科时总能够侃侃而谈,但在涉及到法学时,则往往戛然止步。我觉得,无论从一个民族的精神思维而言,还是从一个国家的法制建设而言,如果不能从哲学的高度反思法律问题、理解和解释法律,那么,既是这个民族精神思维的悲哀,也是这个国家法制建设的不幸。解释学法学和法律解释学的辨思和区分,就是要在我国法学中倡导对法律解释的深入研究,建立一门对法律实践、特别是解释法律的实践具有独特裨益的法律解释学。同时,也就是要在我国交叉学科中倡导对于法律及其存在根据、解释法律现象等的深入研究,建立一门能真正反思法律的学问体系,从而使我们民族思维中对法律的整体的、哲理化的忽视得以补救。也许在有些人看来这是一种大而无当的理想和期待,但人类的存在,就贵在有对未来的理想和对明天的期待。
解释学法学与法律解释学区分的最为功利性的意义就是实现对人们关于法律的精神教化和技术武装。其中关于法律的精神教化的功利作用主要是由解释学法学实现的;而关于法律的技术武装的功利作用主要是由法律解释学实现的。如果没有解释学法学的精神教化功能,那么,法治有可能与人们的精神世界就不相关联,从而法治只是人之精神的外在物;同样,如果没有法律解释学的技术武装,法律也许只能以粗糙的形象存在,既不能引起人们对它的兴趣,也不能发挥它更为系统的社会作用。这样一来,解释学法学与法律解释学的区分在其各自的意义基础上似乎更能发挥两者之间的意义整合,从而既使法律成为人类存在的本体的、精神的根据和目的,又使法律成为人类存在的方便的、有效的工具。
对解释学法学与法律解释学之区分的此种意义的解说,只能在法学家(哲学家)们建立起了足以称之为解释学法学和法律解释学的学术成果(相关学科)时才能进一步得到实证。笔者预测,这种实证结果对中国而言并非遥遥无期,而是为期不远的。
[责任编辑:魏治勋]
收稿日期:2015-11-09
作者简介:谢晖(1964-),男,甘肃天水人,中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法理学。
中图分类号:D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8003(2016)01-0031-13
Subject:Law of Hermeneutics and Legal Hermeneutics
Author & unit:XIE Hui
(School of Law,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3,China)
Abstract:Law of hermeneutics and legal hermeneutics are two different concepts which are expounded by two different basic concepts of interpreting the law and legal?interpretation. As two different kinds of knowledge, both are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in the object of study, subject classification, the social function and the explanation characteristic. The basic meaning of distinguishing them is to distinguish the spiritual legal practice and material legal practice in legal research, and on this basis, to distinguish different kinds of knowledge, which are philosophy of right and legal philosophy.
Key words:interpreting the law; legal interpretation; law of hermeneutics; legal hermeneutics; spiritual law practice; material legal pract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