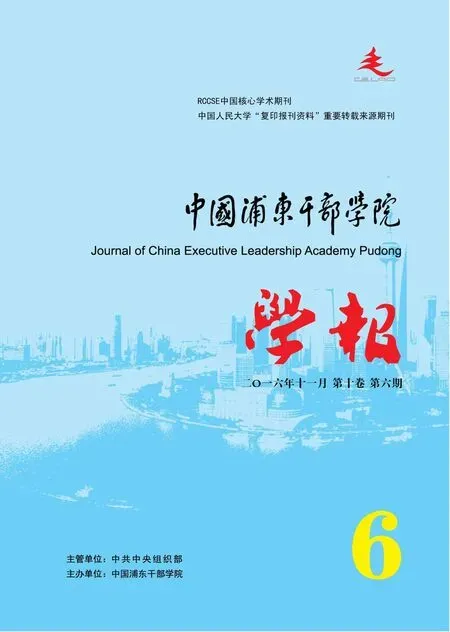欧洲家庭发展和家庭政策的变迁及启示
穆光宗,常青松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北京100871;香港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行政学系)
欧洲家庭发展和家庭政策的变迁及启示
穆光宗,常青松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北京100871;香港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行政学系)
20世纪以来,欧洲各国的家庭结构与规模、居住安排、婚姻关系、代际关系、家庭类型及生活方式等都在发生着显著的变化,欧洲各国普遍出现了家庭结构残缺化、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家庭关系离散化、家庭冲突趋强化、家庭角色失范化以及家庭支持脆弱化等家庭问题。本文梳理了家庭发展和问题的历史变迁,从鼓励生育政策、老年福利政策、家庭救助政策等三个方面阐述了欧洲家庭政策的主要内容及做法。欧洲家庭政策的变迁和取向启示我们,政府通过家庭向社会成员提供的福利支持影响最为直接,社会成效也最为显著。最后提出了完善中国家庭政策的路径选择,即转向发展型,降低家庭发展风险,增强家庭发展能力。
家庭政策;欧洲;少子老龄化;幸福家庭
在国外,家庭政策的研究始于20世纪40年代。由于20世纪初欧洲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把人口政策的焦点转向家庭层面来分析。①奠定家庭政策研究基础的有David Glass于1940年出版的《欧洲的人口政策与人口流动》、Berelson在1974年出版的《发达国家的人口政策》、Kanmerman及Kahn在1978年出版的《十四个国家的政府与家庭》等。人口政策和家庭政策既有重合又有区别。人口政策主要探究人口的生育、死亡、迁移等人口变量及其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的关系。比如各国推行的优生优育的政策属于人口政策,但家庭生育服务与儿童照料等措施则是家庭政策的研究范畴。到了20世纪80年代至今,西方专门讨论家庭政策的学术成果大量涌现,这些著作在理论和方法上都为家庭政策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1世纪初,家庭政策研究在中国逐渐兴起和发展起来。无论是从施政角度还是从学术探索的角度而言,对家庭政策概念进行科学界定都显得十分必要。然而,由于家庭概念的复杂性、政策目标的多样性以及决策环境的差异性,从而使得家庭政策概念的界定长期处于争议之中。[1]
家庭政策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家庭政策包括所有直接或间接对家庭产生影响的政策与项目,是决策者为了确保家庭的效能,针对家庭并为了家庭所采取的全部政策措施。换言之,家庭政策就是人口、经济、健康、福利及社会政策等落实到家庭层面的集合体现。[2](P5)为了避免广义家庭政策概念在应用时的不确定性及缺乏可操作性,学者倾向于使用狭义的家庭政策概念,即针对家庭福利并对家庭资源或家庭行为产生影响的政策。譬如,为了实现提高生育率、削减贫困率和进行收入再分配等目标,家庭政策需要依赖各种手段,如普遍津贴、目标津贴、补助服务与各种特殊规则等。[3](P154)归纳而言,家庭政策具有网络管理的机制、针对私人指向的问题取向及动态的发展特征。[4](P33-35)本文所讨论的欧洲家庭政策也是在狭义定义的基础上进行梳理和探究的。
一、欧洲家庭发展的变迁
20世纪以来,随着欧洲各国人口和社会经济状况的发展,欧洲各国的家庭结构与规模、居住安排、家庭婚姻、代际关系、家庭类型及生活方式等都在发生着显著的变化。
第一,生育少子化导致欧洲家庭的结构核心化和规模小型化。由表1可知,20世纪中期欧洲各主要发达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大都基本维持在人口更替水平左右,但是到了21世纪初,各国总和生育率进一步降低,意大利和德国2010年的总和生育率水平分别为1.48和1.46,显然掉入了低生育率的水平。低生育率必然导致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有些国家甚至连续几年出现人口负增长或者零增长。生育少子化使得欧洲家庭朝着结构核心化和规模缩小化的态势进一步发展。
第二,欧洲各国的人口老龄化加剧导致家庭的居住空巢化。相比于20世纪中期,各国的平均预期寿命的增长幅度都达到了10年以上,平均预期寿命全部在80岁以上,甚至有进一步增长的空间。人口寿命的延长必然导致人口顶部老龄化甚至高龄化的发展,老年抚养比也会进一步提高。由表1可知,德国和意大利再过30年的老年抚养比将达到60%以上。人口老龄化给欧洲各国的家庭将带来沉重的养老负担。欧洲各国将出现越来越多的空巢家庭,特别是老年独居户会日益增多。

表1 .中国及欧洲主要国家部分人口统计指标变化及对比
第三,欧洲家庭内部的婚姻关系也有显著的变化。一是婚龄期的男女性初婚人数持续下降,从1960年至1995年结婚率从7.47‰下降至5.22‰。在婚姻缔结人数下降的同时,青年初婚平均年龄上升。二是不以生育为动机的非婚生活联合体或非婚同居生活方式蔚然成风。三是离婚人数持续上升,从1960年至1995年欧盟成员国离婚率从0.73‰上升至1.91‰,这反映了各国的婚姻与家庭存在严重的危机。[3]
第四,欧洲完整家庭数量下降,单亲家庭数量不断增加。其中,不乏身患重病、身有残疾者和鳏寡孤独老人,也有相当比例的单亲父母与孩子单独生活。他们特别依赖于法律上的社会福利保险以及社会援助。同时,同性恋家庭、丁克家庭等也在与日俱增。
第五,欧洲家庭成员个人主义文化盛行。欧洲各国的人口流动逐渐增加,子女在成年后大都离开父母,经济上自立门户,家庭成员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少。婚姻被看作是子女个人的事情,在婚姻生活中人们也在追求个人的自我感受,家庭不再是一个人一生的寄托。
第六,家庭结构小型化。家庭结构由大家庭向小家庭的演变,主要表现为家庭人口数量减少,多代家庭在家庭结构中的比重下降,丁克家庭、单身家庭、单亲家庭的比重不断上升等等。在家庭结构小型化的同时,家庭结构还呈现出以核心化家庭为主,小家庭式样愈益多样化的趋势。单亲家庭越来越多,欧共体在20世纪90年代单亲家庭在有孩子的家庭中所占的比例至少为10%。[5](P65)单亲家庭的户主大多是女性,特别是单独带孩子生活的母亲在瑞典1985年就达到了母亲总数的16.5%。[6](P48)单身家庭无法依靠家庭保障解决疾病、养老和失业问题,是社会保障需要关照的最直接群体。
第七,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家庭作为人类社会的最基本细胞,长期以来承担了养老的基本功能。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生育率和死亡率大幅度下降,人口老龄化加剧,家庭结构发生了急剧变化,这势必对传统家庭养老方式产生巨大冲击。家庭的小型化冲击了传统的以家为中心的养老文化,淡化了家的精神寄托功能。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子女提早离开家庭,“空巢”家庭主体年轻化,“空巢期”明显延长,家庭养老功能进一步弱化。缺乏精神慰藉、生活无人照料、经济困难这三大问题困扰着空巢家庭中的老人,家庭养老显得被动而无力。[7]日趋严峻的老年空巢家庭对家庭保障提出的新要求是当代多数家庭所无法满足的,老年人因家庭“空巢”而引发的心理不适现象,如孤独、抑郁、焦虑、烦躁等在城市已经成为比较突出的老年心理问题。
第八,家庭关系离散化。子女和父母的代际关系发生了转变,原来由父母抚养子女和子女赡养老人的双向反馈模式发生蜕变,现在更多的是父母抚养子代的单一模式。欧洲各国的人口流动水平逐渐增加,子女在成年后大都离开父母,经济上自立门户,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渐趋离散。由于分开居住模式的影响,代际关系已经从过去面对面的亲密互动转变为有距离的间接互动。随着居住安排的现代化变革,养老的成本在与日俱增,子女赡养父母的可能性减少,家庭的亲子关系也正在经受严峻的考验。婚姻被看作是子女个人的事情,在婚姻生活中人们也在追求个人的自我感受,家庭不再是一个人一生的寄托。晚婚率、离婚率上升和平均初婚年龄提高、不婚和同居现象增多标志着传统婚姻的历史性转型:从家庭责任型婚姻向个人享乐型婚姻的转变,由此带来了性伴关系的混乱和家庭关系的脆弱。[8](P137)
第九,家庭冲突强化。近年来对欧洲家庭暴力、家庭虐待的报道屡见不鲜。在英国克雷福德郡57个家庭中的125名儿童,因受到性虐待而向为他们进行体检的医生求助。其中有27名儿童离开了他们的父母而被送往儿童保护中心,有67名处在法院的保护之下。在英国,一个郡发生这样一种空前数量的儿童性虐案例实在令人发指。[9](P112)家庭暴力和家庭虐待虽然早已有之,但是现代人们受男权专制思想的影响、特立独行的生活方式、暴力文化的耳濡目染、家庭成员经济依赖关系的弱化以及社会生活压力加大导致的“现代心理病”等等因素都在使家庭冲突愈益激化。家庭关系不再和谐使大多数家庭成员选择离婚,甚至在家庭暴力中发生伤亡的现象也屡见不鲜。
第十,家庭角色失范化。家庭责任感正在经受两种严峻的考验:一种是客观原因导致的家庭角色紧张,一种是主观情感上的失责表现。首先,客观上家庭成员常常陷入家庭角色和工作角色的冲突之中。有研究发现,对于那些刚刚当上爸爸的人来说,他们压力的最大来源就是感到对工作的需求和对家庭的责任之间的冲突;随着第一个孩子的出生,男人们可能增加他们的工作时间,女人们可能减少他们的工作时间,孩子对于降低那些专职的妻子的比例产生了明显的、巨大的影响。[9](P70)工作压力加大、居住安排分离、孝文化衰退、代际关系向子代倾斜等因素都加剧了子女行孝“力不从心”的困境。其次,在欧洲,同居文化逐渐成为了人们可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同居的夫妇可能打算结婚,也有可能根本没想过要结婚。“夫妻”逐渐被“同伴”“重要的人”“共同生活的男女朋友”等词汇所代替。
第十一,家庭支持脆弱化。欧洲家庭支持弱化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家庭的经济支持相对减弱,另一个方面就是家庭的社会网络资本越来越小。在家庭收入方面,由于物价的升高以及高额的税负,许多家庭的生活成本在逐年提高。这种经济支持减弱的现象对于单亲女性家庭的影响更为明显。以瑞典为例,在孩子7岁以下的在业妇女中,有67%以上的人干的是半工,而男人中只有10.5%的人干的是半工。工作时间的差异造成了收入的差异:在1987年,妇女平均收入是男人的69%,虽然那些干全工的妇女的收入达到了男人的80%。[6](P47)在社会网络资本方面,家庭不仅是具有血缘和姻缘的亲属结成的自然交往圈,而且还具有因地缘、业缘和情缘关系的邻里、同事及朋友等连成的社会网络。有研究表明,家庭的社会网络资本对于家庭的福利具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低收入家庭和残缺家庭。[9](P186)由于家庭的生育率逐年降低,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将不再拥有兄弟姐妹等亲属关系,新时代的家庭拥有的社会网络资本正在逐渐减少,家庭抵抗风险的能力也逐渐弱化。
二、欧洲家庭政策的变迁
综上所述,受人口结构和社会经济文化的制约,欧洲家庭的结构、功能、角色、对内成员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外的社会网络等都有了新的变化,欧洲各国普遍出现了家庭结构残缺化、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家庭关系离散化、家庭冲突趋强化、家庭角色失范化以及家庭支持脆弱化等问题。这些问题同时又反过来对欧洲的社会保障制度、经济发展、生活方式、政府决策、社会秩序及文化等各个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
随着欧洲经济社会的变迁,欧洲家庭政策的历史演变大致经过工业革命与家庭政策的雏形、家庭政策的发展与成熟及家庭政策的调整与巩固三个阶段。[4](P46-61)
16世纪后期工业革命的爆发使疾病、伤残、年迈、失业等原因造成的社会问题逐渐普遍,统治者逐渐认识到必须通过家庭纽带、教会慈善服务等才能解决这些棘手的社会问题。于是补救模式的家庭政策产生了,这种家庭政策具有自上而下的施舍济贫性质。
20世纪60年代中期,政府逐渐认识到必须采取直接针对家庭的扶助计划才能帮助家庭摆脱贫困和提高生育率。各国相继出台了限制避孕及堕胎、为母子提供健康及服务、为家庭提供财政支持、提升产假计划等等,使家庭政策进一步向成熟方向发展。
20世纪后工业化时期,家庭政策进入了调整与巩固时期,各国家庭政策普遍具有贫困再发现与政策的针对性,妇女运动浪潮和家庭政策向妇幼权利的倾斜等特征。扩大家庭财政支持力度、生育调控立法的自由化发展、公共儿童照料服务、产假等家庭政策得到了实施与完善。在工业革命初期,家庭政策主要为了保护贫困家庭的生存需要;在工业化深入发展的时期,家庭政策主要在于满足家庭的社会关系及社会归属感的需求;在后工业化时期,家庭政策致力于满足人们更深层次的需求,逐渐向着以人为本的国家政策机制转化。[4](P46-61)总之,家庭政策反映了在不同时代因素等客观条件的影响下人们对需求的历史演变进程。
由于欧洲家庭变迁出现的种种问题,欧洲各国逐渐把家庭政策的焦点转移在应对这些问题上:对于家庭结构核心化,各国实施了鼓励生育、对有未成年子女家庭进行补贴等政策;对于家庭传统功能弱化并且外移的问题,各国政府大力推进机构养老扶助、社区照料等家庭政策;对于家庭关系离散化问题,各国广泛开展家庭生活教育等服务;针对家庭暴力与虐待问题,各国相继实施了儿童保护服务、受害者庇护服务以及破裂婚姻调节服务;针对家庭角色紧张与冲突问题,各国一边鼓励人们提高生育水平,一边通过各种手段平衡人们的工作与家庭责任的关系;针对家庭支持系统脆弱化的问题,各国政府广泛开展了家庭友好计划,或者用经济补贴,或者通过各种手段提高家庭成员的社会参与水平。总而言之,欧洲家庭政策的重点主要包括了鼓励生育政策、老年福利政策、家庭救助政策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鼓励生育政策
生育率过低导致社会劳动力不足近年来一直困扰着欧洲各国的发展。为此,欧洲各国在产假、生育补助金、医疗保健、儿童津贴、儿童照料服务、法律法规等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用以提高妇女的生育率水平,提高生育妇女及儿童的家庭福利。
(1)延长产假。欧洲国家相继延长法定产假,使母亲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照顾婴幼儿的成长,缓解生育和工作之间的紧张压力。荷兰、挪威、德国、瑞典等发达国家把产假延长至1至2年,并且可以由父亲或者母亲轮流休假照顾孩子。一些欧洲国家还在产假期满后实行半休性质的抚育制度,瑞典和比利时的半休期期限分别长达8年和5年。
(2)生育补助金。按照国际劳工组织的《生育保护公约》的规定,生育补助金应达到本人原工资的66%以上,而欧洲各国几乎都实行较高的生育补助金制度,德国是100%,瑞典和法国的也在90%和84%。
(3)儿童补贴制度。子女越多的家庭享受的补贴也就越多。一般到4个孩子为止,补贴的资金完全来自国家的财政开支。比利时政府规定,对生育4个孩子的家庭,政府发给17万比利时法郎的免税家庭补贴。法国为了鼓励生育,给生三个孩子以上的家庭以产假补贴、入学补贴、特种教育补贴等。
(4)医疗保健服务。生育医疗保健大多数被纳入医疗保健项目中,有保险机构承担生育医疗保健的费用。在生育的整个期间内,各国政府会针对生育保健给予必要的技术、信息、知识和物质的支持。
(5)儿童照料服务。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丹麦、法国、意大利和比利时,超过85%的孩子接受了儿童照料公共服务。到90年代,法国、卢森堡、比利时、意大利和丹麦的比例都超过了90%,比例最低的希腊也达到了46%。总的看来,所有欧盟成员国的学龄前孩子接受福利性儿童照料公共服务的比例都有明显提高。[10]
(6)健全法律法规。许多欧洲发达国家在保障育龄妇女权益及母子健康方面的法律法规比较健全,有《劳动法》《促进就业法》《社会保障法》《社会保险法》《生育保险法》以及扶助单亲及母子福利的立法。欧洲各国执法较严厉,生育妇女和儿童的合法权益得到了很好的保障。
(二)老年福利政策
随着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和生育少子化的发展,积极应对老龄化的挑战一直得到了欧洲各国政府及社会的高度重视。各国政府在实施一般的养老保险的同时,还通过寡居母亲补贴、高龄补贴、补充养老金、老年服务、机构养老、老年住房补助、节日津贴、交通优惠等形式增加老年人的福利。
(1)基本养老保险。以英国为例,受保人退休后,除了领取基本养老金,还可以在附加养老金和企业职业养老金中任选一种。
(2)寡居母亲补贴。女性的生存优势使得老年寡居的妇女与日俱增。在英国,如果男性受保人死亡时,遗属可享受相应保险待遇,主要有寡妇一次性补贴和寡居母亲补贴。
(3)高龄补贴。高龄补贴就是对年满80周岁的老年人进行经济补贴的制度。
(4)补充养老金。这是针对低收入的老年人实施的一项有针对性的社会救济。通常凡年满60周岁,私人储蓄低于一定水平,就可以申请补充性的养老金。
(5)老年服务。在欧洲老年市场和老龄产业十分发达,根据老年人的特殊需求,政府和社会提供了各种老年服务,例如家政服务、家庭护理、代烹食品、医疗保健等等。
(6)机构养老。以法国为例,市场上有三种养老机构可供老年人根据自身的需求和条件进行选择。第一种是各级政府管理的公立养老院,以追求社会利益为目的;第二种是由政府补贴的私人养老院,这种养老院不以营利为目的,是微利产业;第三种是商业性的养老机构,这种养老机构比较高端,拥有很多个性化的专业服务。
(7)老年住房补贴。老年人退休后,仍然可以根据家庭人口数目的变化、家庭经济收入的变化及房租标准申请住房补贴。住房补贴通常有三种形式:减收房租、发放补贴、减少房地产税。
(8)节日补贴。在欧洲各国,每逢节日前夕,独居老人和病残老人大多都可以享受政府发放的节日补贴,并伴有社工上门进行精神慰藉。
(9)交通优待。达到国家法定年龄的老年人都可以申请老年交通优待政策。老年人可以通过持老年证明购买到优惠或者免费的交通票证。
(三)家庭救助政策
家庭救助是构筑整个社会“安全网”的重要举措,目的是为了帮助困难家庭维持最低生活水平、在最短的时间内依靠家庭成员的力量达到自救的程度。欧洲各国的家庭救助政策门类齐全,基本覆盖了各种相对弱势的人群。以英国为例,英国的家庭救助始于1601年制定的旧《济贫法》,1843年又制定了新的《济贫法》,1933年、1948年、1976年又相继出台了《失业救济法》《国民救助法》和《补充救助法》。社会救助的项目涉及低收入家庭救助、老龄救助、失业救助、儿童救助、疾病救助等等。英国政府规定,凡年满16周岁的英国公民都可以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申请家庭救助。
德国的家庭救助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对被救助家庭的衣、食、住、行、家庭用具、取暖等方面的救助;另一类是对特殊困难家庭实施救助。德国的家庭救助计划包含的门类齐全、内容丰富,对提高家庭的生活水平,健全家庭的生育、养老、经济等功能,改善家庭成员的关系等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三、欧洲经验对中国的启示
(一)完善中国家庭政策的意义
家庭政策具有不可替代性。家庭是社会生活的细胞,是社会健康发展的基础,是个人福利最初始的提供场所。在历史上非制度化的福利供给中,家庭既是福利的组织者和实施者,也是家庭成员享受福利最可靠持久的源泉。从欧洲家庭政策所提供的福利中可以看出,在现代社会福利体系中,家庭政策的福利功能也是不可或缺的,甚至是无法取代的。
与国家等提供的福利相比,家庭福利保障的优点在于:首先,家庭福利保障功能主要通过赡养关系实现,这个过程是靠家庭成员之间长期共同生活的感情维系的,具有自觉自愿性,具有低成本而高效率的特点;其次,家庭福利更能满足受助人或受益人的需求。[11](P159)家庭是一个人社会化伊始的场所,是国家社会生活的最小载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欧洲各国的家庭政策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政府和社会通过家庭向社会成员提供福利支持影响最为直接,社会成效也最为显著。可以说,任何国家建立的正式福利制度都无法取代家庭的福利功能和责任,政府只是在不同程度上用不同的方式方法分担了家庭福利的某些功能。因此,我国要加强家庭功能的建设,完善家庭的结构和功能,增强家庭的福利水平,使困难的家庭得到帮助,使健康的家庭得到发展。
中国家庭政策现阶段的发展具有以下问题:第一,缺乏普遍的专门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家庭政策;第二,家庭政策呈现出碎片化特征;第三,缺乏具体、操作性强的政策内容安排;第四,各项与家庭福利相关的政策基本是补充型和残补式的;第五,缺乏对家庭在税收政策方面的支持,没有发挥家庭政策对社会利益再分配的功能。[12]总而言之,我国家庭政策内容过于狭隘、功能比较单一、理论指导比较缺乏、视野偏重于短期、体系碎片化明显。[13]因此,进一步完善中国的家庭政策迫在眉睫。
(二)中国家庭政策发展的路径选择
借鉴欧洲各国的经验,我国家庭政策的发展需要在保障水平、功能定位、体系安排及价值取向等方面进行改善。
首先,家庭政策的保障水平要与当前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目前,我国应该进一步完善普惠型的家庭福利政策。欧洲各国的家庭保障水平都比较高,这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经济基础之上的。欧洲各国高水平的社会保障水平和经济发展持续低迷的矛盾日益突出,政府的财政压力十分巨大,不得不纷纷进行社保改革以缓解当前的窘迫局面。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的增长,但是我国人口众多、结构失衡、需求复杂等问题使我国很难在现阶段实施类似欧洲较高的家庭福利水平,如果那样将会给我国经济的发展带来沉重的负担。所以,一方面要努力发展经济,经济发展是提高家庭福利水平的基本保障;另一方面又要使家庭政策所提供的福利水平与国情相适应,要随着经济的增长逐渐提高家庭政策的保障水平,循序渐进,有序发展。
其次,由欧洲的经验可以得到启示:家庭政策的定位在于健全家庭的功能发展,而不仅仅是完善弱势群体的救济方法。家庭政策体系安排从补充型导向转为发展型导向。中国的家庭福利政策基本是补充型和残补式的。中国仍然停留在家庭的自我保障阶段,目前的家庭政策主要针对计划生育残缺家庭、贫困家庭等,社会福利项目或行动也较多集中于特殊儿童家庭,而结构较为完整的家庭更多依靠自我保障。所以,中国应该转变家庭政策的发展思路,家庭政策体系安排从补充型导向转为发展型导向。相应的家庭政策从纯粹的满足家庭的经济需求转向满足家庭非货币化的福利需求,从满足家庭最基本的生存需求转向建构家庭的结构和功能,提升家庭的发展能力。[12]
再次,我国的家庭政策也要担当起应对少子老龄化的重任,及早调控,在风险陆续爆发之前把损失减到最小化。面对家庭的变化,原有的以家庭自我保障为主的社会福利安排已经无法适应家庭变化带来的巨大社会需求,政府需要探索建立新的福利政策安排,来应对家庭功能及其投射到需求层面的变化,加强对家庭照料功能的支持和扶助。少子老龄化给中国家庭的发展带来了许多挑战。家庭的传统养老功能日益退化,家庭的结构核心化导致的问题层出不穷。欧洲各国现如今大力鼓励生育和加强养老保障的做法为我国敲响了警钟。独生子女家庭和社会是充满风险的,并且风险正在逐渐显现。尽管家庭的某些功能在弱化甚至丧失,但是育儿、养老和病残家庭成员的照料仍然是家庭的重要功能。因此,家庭政策应该充分考虑和评估家庭成员的抚养负担,鼓励家庭成员之间的互相照顾,对承担育儿、照料老人和病残家庭成员的家庭给予支持,包括补贴、减免税收及其他方面的政策支持,在制度设计层面对家庭实现有效的支持,构建家庭友好型的支持政策。[12]
最后,幸福家庭应该是家庭政策建设的落脚点。幸福家庭的建设就是要让痛苦的家庭得到关怀,让困难的家庭得到扶助,让需要的家庭得到服务,让健康的家庭得到发展,让所有的家庭得到保障。幸福的家庭一定是健康的家庭,它至少包括了五个评价标准:第一,家庭成员的身心健康;第二,家庭结构的完整且安全;第三,家庭内部关系的幸福发展;第四,家庭功能的健全保障;第五,家庭与社会的关系和谐发展。提高家庭的发展能力是家庭政策的题中应有之义。家庭发展能力包括了健康发展能力、生育养育能力、团结互助能力、学习工作能力、抵御风险能力、道德自律能力和自我保障能力。[14]“幸福中国幸福家”体现了人口发展的家庭视角、价值取向和政策导向。家庭政策以幸福家庭建设为落脚点,将有利于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家庭的幸福发展、人口的优化发展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1]吕亚军,刘欣.家庭政策概念的辨析[J].河西学院学报,2009,(6).
[2]Aldous,J.,Dumon,W.A.&Johnson,K.,The politics and programs of family policy:United States and European Perspective[M]. Leuven:Leuven University Press,1980.
[3]Hantrais,L.,Family Policy Matters.Responding to family change in Europe[M].Bristol:The Policy Press,2004.
[4]吕亚军.欧盟层面家庭政策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5]Kiely,Family Policy:European Perspectives[M].Dublin:Family Study Centre,1991.
[6]周艳玲.全球视角:妇女、家庭与公共政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7]何芸,李建权.家庭结构变迁对养老模式的影响[J].社会工作,2007,(1).
[8]穆光宗.家庭养老制度的传统与变革——基于东亚与东南亚地区的一项比较研究[M].北京:华龄出版社,2004.
[9][加]大卫·切尔.家庭生活的社会学[M].彭铟旎,译.北京:中华书局,2005.
[10]吕亚军,刘欣.浅析欧盟成员国家庭友好政策[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9,(1).
[11]范斌.福利社会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12]吴帆.第二次人口转变背景下的中国家庭变迁及政策思考[J].广东社会科学,2012(2).
[13]刘中一.我国现阶段家庭福利政策的选择——基于提高家庭发展能力的思考[J].党政干部学刊,2011,(8).
[14]穆光宗.论家庭幸福发展[J].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2,(1).
[15]邹根宝.社会保障制度——欧盟国家的经验与改革[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
[16]顾俊礼.福利国家论析——以欧洲为背景的比较研究[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
[17]邵芬.欧盟诸国社会保障制度研究[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
[18]田丰.当代中国家庭生命周期[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19]钟仁耀.社会救助与社会福利[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
[20]费梅萍.社会保障概论[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
[21]周建明.社会政策:欧洲的启示与对中国的挑战[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
[22]Zimmerman,S.L,Understandingfamilypolicy:theoretical approaches[M].California and England:Sage Publications,Lnc, 1988.
[23]Hantraits,L.&Letablier,Families and Family Policies in Europe [M].London and New York:Longman,1996.
[责任编辑 郭彦英]
Changes in European Family and Family Policies
MU Guang-zong1,CHANG Qing-song2
(1.Institute of Population Research,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China;2.Department of Social Work and Social Administration,University of Hong Kong,Hongkong,China)
Since the 19th century,families of European countries have gone through tremendous changes in family structure and size, living conditions,marriage,relation between generations,types of family and life-style.Some common family problems emerged in European countries such as incomplete family structure,less caring for the elderly,weak relationship,intensified conflicts,the lack of responsibility and support of family members.The paper has made a historic review of family issues and family policies adopted by European countries with a major focus on pro-naturalist policy,welfare policy for the elderly and assistance for needy families.The changes in family policies of European countries suggested that the government support for citizens through family welfare has made a remarkable social impact.Finally,the paper makes suggestions to improve family policies in China,such as more focused on family growth,reducing the risk and enhancing the capacity for family development.
family policy;Europe;aging society with fewer children;happy family
D57/58;C924.1
A
1674-0955(2016)06-0112-08
2016-04-28
穆光宗(1964-),男,浙江象山人,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人口理论与社会政策,人口与发展,社会老年学;常青松(1988-),男,河南焦作人,香港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行政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人口与发展,老龄与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