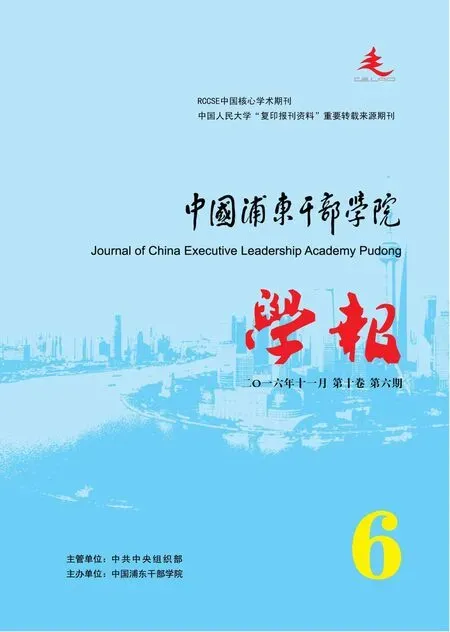论“一国两制”下中央对港澳特区的全面管治权
魏淑君,张小帅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学研究部,上海201204)
论“一国两制”下中央对港澳特区的全面管治权
魏淑君,张小帅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学研究部,上海201204)
我国是单一制国家,港澳特区的主权属于中国,在“一国两制”下,中央对港澳特区拥有全面管治权。中央对港澳特区的全面管治权以宪法和港澳基本法为规范基础,负有维护“一国”与“两制”的重要使命。中央全面管治权包括授予港澳特区的高度自治权和中央直接行使的权力。而中央直接行使的权力中,部分权力能够监督港澳特区的高度自治权,部分权力能够变更港澳特区的高度自治权。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中央要依法、适时行使管治权。
香港;澳门;管治权;监督;变更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2014年6月发表的《“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中指出,中央对香港特区拥有全面管治权,其中既包括中央对香港特区直接行使的权力,亦包括授予香港特区的高度自治权,而对香港特区的高度自治权,中央则享有监督权。《白皮书》中的论述同样适用于中央对澳门特区的管治权。本文拟先从理论上探讨中央全面管治权之政治基础、规范基础与价值所在,然后通过对宪法与港澳基本法的文本分析,来对中央全面管治权进行类型化研究。
一、中央全面管治权之政治基础、规范基础与价值所在
“一国两制”下中央全面管治权是指在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下,根据宪法与港澳基本法的规定,中央对港澳特区进行管辖和治理的权力。中央全面管治权具有政治基础和规范基础:其政治基础在于香港与澳门的主权属于中国,而中国属于单一制国家;其规范基础在于宪法与港澳基本法所构建的授权框架。同时,中央管治权的全面性肩负着维护“一国两制”的重要使命。
(一)中央全面管治权之政治基础
中央对港澳特区拥有全面管治权,其政治基础建立在两个方面:一个是香港与澳门的主权属于中国;另一个是我国是单一制国家。
首先,在主权与治权的关系中,主权是治权的基础和前提,没有主权就没有治权,有了主权才谈得上治权。香港与澳门的主权属于中国,这为代表国家主权的中央行使对港澳特区的管治权提供了正当性。据此,有学者将中央管治权称为“主权性管治权”。[1]其一,中国政府坚决不承认英国、葡萄牙与晚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效力,这直接否定了英国、葡萄牙政府对香港、澳门的主权主张的正当性。其二,1997年6月26日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接收原香港政府资产的决定》规定,中央人民政府授权即将成立的香港特区政府接收和负责核对港英政府的全部资产和债务,并根据香港特区的有关法律自主地进行管理。1999年12月18日,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授权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接收原澳门政府资产的决定》规定,中央人民政府授权澳门特区政府自1999年12月20日起接收和负责核对原澳门政府的全部资产和债务,并根据澳门特区有关法律自主地进行管理。这说明港英和葡澳政府的资产是先转移给中国政府,然后由代表国家主权的中央人民政府授权港澳特区政府进行接收,而在香港特区政府与港英政府之间、澳门特区政府与葡澳政府之间并不存在私相授受的关系。[2](P16)其三,港澳基本法中存在着诸多关于香港与澳门的主权属于中国的规定,其中既有原则性规定,也有具体的权力分配规定。前者如港澳基本法序言载明香港、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后者如港澳基本法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对港澳特区行政长官享有任命权等。[3]
其次,主权权力的大小决定着治权范围的宽窄。联邦制与单一制是对国家结构形式的典型分类。在联邦制国家,联邦的组成单位通过宪法授予联邦有限的主权权力,联邦也只有在这些有限的主权权力范围之内才能对各组成单位进行管辖和治理。例如,在典型的联邦制国家美国,宪法明确规定了联邦的权力范围,并且规定凡未授予联邦的权力由各州保留。[4](P224-225)这样,联邦只能在宪法所规定的权力范围之内,对各州和美国公民进行管辖和治理,否则就可能违宪。在准国家的政治体欧盟,欧盟的成员国通过相关条约授予欧盟若干主权权力,欧盟只能在这些主权权力的范围之内才能够对其成员国及其公民进行管辖和治理。但在单一制国家,主权在中央,中央的权力是本源性、全面性的,地方没有任何固有的权力,地方的权力来自中央的授权,并且这种授权也仅是“权力行使的转移,而非权力本身的转移”。[5](P174)在授权之后,中央对授予地方的权力仍享有监督、变更和取消之权。正是这种主权权力的本源性、全面性决定了在单一制国家,中央对地方的管治权必然是全面的。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在“一国两制”下,港澳特区没有任何固有的权力,其所享有的高度自治权来自代表国家主权的中央的授权。中央对港澳特区的主权权力具有全面性、本源性,同时,在授权之后,中央仍然有权监督、变更和撤消港澳特区的高度自治权。
因此,基于港澳特区的主权属于中国,而我国又是单一制国家,所以中央对港澳特区的管治权具有全面性。
(二)中央全面管治权之规范基础
基于我国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在“一国两制”方针的指导下,宪法与港澳基本法在中央与港澳特区之间构建了一种授权框架,这一授权框架充分说明了中央对港澳特区管治权的全面性。
首先,宪法第31条构建了宪法上的授权框架。宪法第31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相对于宪法其他条文,第31条可以说是一个“但书”。[6](P82)该但书具有授权性质,实际上包含两个层面的授权:一个是宪法层面的授权,另一个是法律层面的授权。[7]宪法层面的授权是指制宪权对宪定权的授权。制宪权与宪定权具有不同的涵义,制宪权决定着宪定权,宪定权来自制宪权。卡尔·施密特认为:“制宪权是一种政治意志,凭借其权力或权威,制宪权主体能够对自身政治存在的类型和形式作出具体的总决断,也就是说,能够决定整个政治统一体的存在。”[8](P84-85)“制宪权是一切权力的本源,凭借共同体的存在就当然存在,是不可分割、不可转让的。宪定权是派生的,可以分割,端赖宪法而存在,受宪法之制约,断不能染指宪法。”[9](P133)既然制宪权主体能够决定整个政治统一体的存在形式,当然更有权决定该政治统一体中的特定部分的存在形式。就此而言,在1982年宪法颁布之时,制宪权主体完全可以在该宪法中直接规定港澳特区的存在形式。然而,由于当时“一国两制”方针刚提出不久,还不是太成熟,香港与澳门尚处于殖民统治之下,港澳特区尚未成立,并且还有诸多不确定因素。因此,制宪者在颁布1982年宪法之时,无法在其中明确规定港澳特区实行什么样的制度和政策,唯有通过第31条将此权力授予全国人大。而全国人大凭借第31条的授权则获得一项宪定权,即要根据香港与澳门的具体情况来规定其在回归后实行什么样的制度和政策。同时,根据宪法第31条中的“以法律规定”的表述可知,全国人大获得的这项宪定权实际上包含着法律保留的意思,即全国人大在构建港澳特区实行的制度和政策时,只能采取法律的形式,而不得采用法规、规章等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形式。就法律层面的授权而言,由于“一国两制”方针要求港澳特区实行与内地相区别的资本主义制度和政策,要求授予港澳特区高度自治权,这就要求全国人大必须制定一部授权法,授予港澳特区高度自治权,这样一部授予港澳特区高度自治权的授权法无疑就是港澳基本法。
其次,港澳基本法中诸多的授权条款和多种授权方式构建了港澳基本法上的授权框架。在授权条款方面,港澳基本法条款中有的直接以“授权”、有的则用“可”“自行”等来表述授权涵义。[10](P133)如港澳基本法第2条均规定:全国人大授权港澳特区依照港澳基本法的规定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港澳基本法第23条均规定:港澳特区应自行立法禁止……在授权方式方面,港澳基本法采用了综合性授权、具体事项授权和进一步授权等多种授权方式。[10](P131)所谓综合性授权,顾名思义,就是不列举具体事项,而采取的一种概括性的授权方式,如前述港澳基本法第2条的规定。所谓具体事项授权,就是港澳基本法在授权的相关规定中具体列明了需要授权的相关事项。如香港基本法第13条第3款规定,中央人民政府授权香港特区依照本法自行处理有关的对外事务。所谓进一步授权,就是根据港澳基本法第20条的规定,港澳特区还可以享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中央人民政府授予的其他权力。
(三)中央全面管治权之价值所在
“目的是全部法律的创造者。每条法律规则的产生都源于一种目的,即一种实际的动机”,“法律是根据人们欲实现某些可欲的结果的意志而有意识地制定的”。也就是说,“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为了有意识地达到某个特定目的而制定的”。[11](P109)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宪法和港澳特区宪制性法律的港澳基本法,其在港澳特区的实施同样具有目的取向性。中央管治权是中央依据宪法和港澳基本法所享有的,国家之所以通过宪法和港澳基本法赋予中央管治权以全面性,是为了维护“一国两制”,其中既需要维护“一国”,亦需要维护“两制”。
在“一国两制”中,“一国”是“两制”存在的前提和基础。“一国”并不是指一个抽象的、虚拟的国家,而是指按照国家的宪法所确立的具体的、现实的国家。这个国家除了是民族、历史和文化意义上的国家之外,还是政治主权意义上的国家。[12](P34)“两制”就是内地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与港澳特区实行的资本主义制度和政策。中央管治权的全面性旨在维护“一国两制”,是说中央要通过行使全面管治权,来保证港澳特区实行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得影响内地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保证港澳特区的高度自治权在港澳基本法规定的轨道内运行,不得超越高度自治权去追求“完全自治”,不得危害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进而危及“一国”的存在;同时也要保证内地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得影响港澳特区实行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要维护“一国”就必须维护国家统一、增进国家认同。在近代史上,中国的国家观逐渐由传统的天下式的国家观转变成近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式的国家观。而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正在进行现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建设的中国并未对香港与澳门行使过主权,另一方面生活于殖民统治下的港澳居民并未参与祖国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过程,导致其对祖国产生了疏离感和国家认同危机。虽然香港与澳门的回归解决了其主权归属问题,但这种对祖国的疏离感和国家认同危机并没有随着回归而自动消失,甚至在近几年有不断恶化的趋势。而要弥合港澳居民与祖国之间的隔阂,增进港澳居民的国家认同,单单靠授予港澳特区高度自治权难以完成,中央必须拥有全面管治权。
二、中央全面管治权之内容
《白皮书》提到了中央直接行使的权力与中央监督权,有学者将两者置于并列的地位。[13]但笔者认为,在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下,国家对香港与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后,中央对港澳地区即拥有了全面管治权,也正是基于此,中央才可以把其中的部分管治权授权给港澳特区,形成港澳特区的高度自治权,同时中央保留没有授出的权力,形成中央直接行使的权力。[14]实际上,从《白皮书》的论述可以看出,中央直接行使的权力是相对于高度自治权而言的,而中央监督权仅是中央直接行使的权力中能够对港澳特区的高度自治权发挥监督作用的那部分权力,因此,中央直接行使的权力与中央监督权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15]除了中央监督权之外,中央直接行使的权力还包括中央变更权和其他权力。
(一)中央授予港澳特区高度自治权
高度自治权是港澳基本法上的主要权力形态,也是“一国两制”中“两制”的法律体现。根据港澳基本法的规定,港澳特区的高度自治权的内容极其广泛,包括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可以说,港澳特区享有的自治权的程度之高甚至要超过联邦制国家的州。例如,联邦制国家的州通常不享有终审权,并且要实行全国统一的货币,而港澳特区却享有终审权,并且具有自己单独的货币。但即便如此,港澳特区的高度自治权仍非其本身所固有,并非建基于主权之上,而是来自代表国家主权的中央的授权。这种授权仅是“权力行使的转移,而非权力本身的转移”。[14]基于中央与港澳特区的授权框架,中央在授予港澳特区高度自治权之后,仍然可以凭借其所享有的管治权来变更甚至取消港澳特区的高度自治权,将授予港澳特区的高度自治权重新收回中央。
(二)中央直接行使的权力
所谓中央直接行使的权力,顾名思义,就是中央可以直接对港澳特区行使的权力,也是没有授予给港澳特区的权力。在这里首先区分两个概念,即“生效”与“实施”。当中央行使管治权作出相关决定,该决定依据其本身所规定的生效时间生效之时,同样亦开始对港澳特区生效。但对港澳特区生效,并非就意味着该决定必然可以直接在港澳特区实施。在“一国两制”环境下,根据港澳基本法的规定,中央行使不同管治权作出的不同决定,有的可以直接在港澳特区实施,有的则必须借助于港澳特区的相关高度自治权才能在港澳特区实施。据此,可以将中央直接行使的权力分为两类:
一类是所作决定可以直接在港澳特区实施的权力。就此类中央直接行使的权力而言,其在港澳特区的实施无须借助于港澳特区的相关高度自治权。例如,根据香港基本法第13条和第14条的规定,香港特区的国防和外交事务由中央人民政府负责,香港特区在这两类事务中非经授权则不享有任何权力。中央作出的国防和外交行为可以直接在香港特区生效实施。又如,全国人大设立港澳特区、全国人大对香港基本法所作的修改、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基本法所作的解释、中央人民政府对行政长官和香港特区政府主要官员的任免等,这些均可以直接在香港特区实施,无须借助于香港特区的相关高度自治权。此类权力还包括全国人大确定港澳特区全国人大代表的名额和产生办法的权力、全国人大常委会废除香港与澳门原有法律的权力、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港澳特区战争状态和紧急状态的决定权、中央人民政府根据港澳基本法第18条第4款的规定将有关全国性法律在港澳特区实施的命令权,以及中央人民政府对港澳特区发出指令的权力等。
另一类是所作决定需要借助于港澳特区的相关高度自治权才能实施的权力。对这部分中央直接行使的权力而言,如果没有港澳特区相关高度自治权的配合,尽管中央行使这部分管治权所作决定对港澳特区仍然有效,但却无法直接在港澳特区实施。例如,根据香港基本法第18条第1、2、3款的规定,相关全国性法律可以通过列于附件三,在香港特区实施。在此过程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和香港特区均享有相应权力。其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征询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和香港特区政府的意见后,可以直接增减列于附件三的全国性法律。但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将相关全国性法律列于附件三之后,这些全国性法律并未立即在香港特区实施,而是要待香港特区在当地公布或者立法之后才能实施。这说明,全国性法律要在香港特区实施,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列入权与香港特区的公布权或者立法权必须相配合才行。缺少了香港特区的公布或者立法,全国性法律尽管被列入了附件三,仍然无法在香港特区实施。
(三)中央对港澳特区高度自治权的监督权
所谓中央对港澳特区高度自治权的监督权,简称中央监督权,是指对港澳特区的高度自治权发挥着监督作用的中央管治权。中央监督权属于中央直接行使的权力。在行使时间点上,通常是港澳特区高度自治权行使在先,中央监督权行使在后,中央监督权对港澳特区高度自治权的运行状况进行监督,中央监督权与港澳特区高度自治权组成一个权力束,共同完成一个权力使命,即确保港澳特区的高度自治权始终在港澳基本法规定的轨道内运行。中央监督权主要包括基本法解释权、港澳特区宪制发展决定权、人事任免权、法律备案审查权和特定事项备案权等权力。由于中央对香港特区的监督权与对澳门特区的监督权基本相同,以下就以中央对香港特区的监督权为例来进行论述。
香港基本法第158条规定了香港基本法的解释权。该条第1款从整体上明确了香港基本法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据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对香港基本法的所有条款进行解释,并且可以主动解释,这种解释是“政治性的主权与法律性的治权的结合”。[16]第2款和第3款则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香港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香港基本法关于香港特区自治范围内的条款自行解释,同时,也可对其他条款进行解释。但如果是需要对香港基本法中关于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务或中央和香港特区关系的条款进行解释,并且该解释会影响案件的判决,那么在对该案件作出不可上诉的终局判决前,香港终审法院要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有关条款进行解释。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解释对香港法院之后的判决具有约束力。据此,如果全国人大常委会认为香港法院作出的基本法解释不准确的话,那么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推翻香港法院的基本法解释,自己作出一个权威的基本法解释。因此可以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基本法解释权对香港法院的基本法解释权起到监督作用。不过,由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授权香港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自治范围内的条款自行解释,对于香港法院就这部分条款作出的解释,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当予以尊重。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法院的基本法解释权的监督应当主要聚焦于香港法院对非自治范围内的条款的解释。
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特区宪制发展决定权,是指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和立法会议员的产生办法以及立法会法案、议案的表决程序是否需要修改以及如何修改的决定权,也就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是否需要修改以及如何修改的决定权。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尽管对其自身的修改程序进行了规定,但这种规定存在模糊之处,如没有明确指出由谁确定是否需要修改以及由谁提出修改法案等问题。为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04年作出相关解释,[17]明确阐述了附件一和附件二的“五步曲”的修改程序:第一步,由行政长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报告,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附件一和附件二是否需要进行修改;第二步,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是否可就附件一和附件二进行修改;第三步,如果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可就附件一和附件二进行修改,则香港特区政府向立法会提出修改附件一和附件二的议案,并经全体立法会议员三分之二多数通过;第四步,行政长官同意经立法会通过的议案;第五步,行政长官将有关法案报全国人大常委会,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或者备案。[18]其中,第三步和第四步中香港特区享有制定议案的权力,而第五步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则享有对香港特区制定议案的批准备案权。这种批准备案权并非形式性的,而是实质性的,即全国人大常委会既可以对香港特区立法会通过、行政长官同意的附件一和附件二的修改议案作出批准或备案的决定,此时附件一和附件二的修改即生效,具有法律效力;也可以作出不批准或不备案的决定,此时附件一和附件二的修改则不生效,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批准备案权就对香港特区的制定议案权发挥监督作用。
中央对香港特区的人事任免权包括两种,即中央人民政府对香港特区行政长官的任免权和中央人民政府对香港特区政府主要官员的任免权。就中央人民政府对行政长官的任命权而言,根据香港基本法关于行政长官产生过程的相关规定,香港特区的行政长官在当地通过选举或者协商产生之后,要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才算正式的行政长官。中央人民政府对行政长官的任命权并非形式性的权力,而是一种实质性的权力。[19]因而,在行政长官产生的过程中,香港特区的选举或协商的权力与中央人民政府的任命权就形成一个权力束,来共同完成产生行政长官这个权力使命。在其中,中央人民政府对行政长官的实质性的任命权,其实就是对香港特区选举或者协商产生行政长官的权力的一种监督权,即如果选举或者协商产生的行政长官候任者是一个爱国爱港者,那么中央人民政府就会任命,反之,中央人民政府就不会任命。就中央人民政府对行政长官的免职权而言,根据香港基本法第73条第(9)项的规定可知,在行政长官的免职过程中,立法会的弹劾权与中央人民政府的免职权组成一个权力束,共同完成行政长官的免职。其中,中央人民政府的免职权就是对立法会的弹劾权的一种监督权。也就是说,如果中央人民政府认为行政长官不应该被免职,那么即便立法会通过了对行政长官的弹劾案,中央人民政府亦可维持行政长官继续履职。就中央人民政府对香港特区政府主要官员的任免权而言,根据香港基本法第48条第(5)项的规定,行政长官的提名权与建议权和中央人民政府的任免权构成一个权力束,共同完成香港特区政府主要官员的任免过程。其中,中央人民政府的任免权就对行政长官的提名权和建议权起到监督作用,也就是说,中央人民政府如果认为行政长官提名的主要官员人选或者针对特定主要官员的免职建议不合理,那么中央人民政府可以不任命或者不免职。
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特区立法会的立法拥有备案审查权。根据香港基本法第17条第2款和第3款的规定,香港特区立法会制定的法律要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对报送备案的法律进行审查。虽然备案不影响该法律的生效,但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征询其所属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的意见后,如果认为报送备案的法律不符合香港基本法中关于中央管理的事务及中央和香港特区关系的条款,那么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将该法律发回,但不能进行修改。这种发回会使得该法律立即失效,但除另有规定外,该法律的失效没有溯及力。这说明,香港特区立法会的立法权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备案审查权构成一个权力束,共同完成整个过程。在其中,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备案审查权其实就是对香港特区立法会立法权的一种监督权。只不过,这种监督只能针对香港特区立法会的立法是否符合香港基本法中关于中央管理的事务及中央和香港特区关系的条款,而对于是否符合香港基本法自治范围内的条款,全国人大常委会则无权监督。
此外,香港基本法还规定了诸多香港特区需要报送中央进行备案的事项,包括香港终审法院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免要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香港特区财政预算、决算要报中央人民政府备案,香港特区设立驻外机构要报中央人民政府备案等。尽管这些备案更多地仅是形式上的,但其仍然体现了中央对香港特区高度自治权的监督。
(四)中央对港澳特区高度自治权的变更权
所谓中央对港澳特区高度自治权的变更权,简称中央变更权,是指为了使港澳特区高度自治权的权力内容能够与港澳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需要相适应,中央对港澳特区的高度自治权进行变更的权力。中央变更权与中央监督权均属于中央直接行使的权力。为了使港澳特区高度自治权的权力内容能够与其社会发展需要相适应,港澳基本法为港澳特区高度自治权的变更提供了两种制度化的渠道,分别是港澳基本法第20条规定的进一步授权的权力、第159条规定的基本法修改权。由于港澳基本法的相关规定基本相同,以下仅以香港基本法的规定为例进行论述。
根据香港基本法第20条的规定,在香港特区根据香港基本法的规定所享有的原有高度自治权的基础上,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中央人民政府还可以授予香港特区其他权力。这里需要探讨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中央进一步授予香港特区的权力需要满足什么条件?第二个是中央进一步授予香港特区的权力的性质是什么,是构成香港特区的高度自治权还是普通权力?就第一个问题而言,笔者认为这些权力需要满足如下三个条件:其一是这些权力的内容不属于香港基本法明确规定的原有高度自治权。显然,如果这些权力的内容属于香港基本法明确规定的原有高度自治权,那么就不存在进一步授权的必要,香港特区径直行使这些权力即可。其二,这些权力的内容属于“两制”范畴,在应然程度上应当属于香港特区的高度自治权。如果这些权力的内容属于“一国”范畴,那么就应当由中央直接行使,无需亦不得授予香港特区。因此,只有当这些权力的内容属于“两制”范畴时,中央才可以对香港特区进一步授权,补充香港特区高度自治权的内容。其三,这些权力的内容不得与香港特区原有高度自治权相冲突。香港特区高度自治权的协调性对于其高度自治权的顺利运行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央进一步授予的权力因而不得与香港特区原有高度自治权相冲突,否则即不得授予。因此,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中央人民政府根据香港基本法第20条的规定,可以增加香港特区所享有的权力。就第二个问题而言,笔者认为,可以将中央依据香港基本法第20条授予给香港特区的权力定性为香港特区的高度自治权,因为这些权力是根据香港特区实际情况的需要而授予的,香港特区之外的全国其他地方一般不享有这些权力。但即便如此,这些权力仍然与香港特区根据香港基本法所享有的原有高度自治权存在差别。因为香港特区的原有高度自治权受到香港基本法第159条规定的修改程序的强有力保障,除非通过香港基本法规定的修改程序对香港基本法进行修改,否则不得变更香港特区的原有高度自治权。但中央依据香港基本法第20条授予给香港特区的权力并不受到香港基本法修改程序的保障,也就是说,谁依据香港基本法第20条对香港特区进行了授权,谁就可以单独、直接变更、取消这项授权。
根据香港基本法第159条的规定,香港基本法的修改权属于全国人大,提案权主体有三个,分别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区。其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所提修改议案应根据其内部议事规则和《立法法》的相关规定提出,而香港特区所提修改议案的程序则较为复杂,即必须先经香港特区全国人大代表三分之二多数、立法会全体议员三分之二多数和行政长官同意,才能交由香港特区出席全国人大的代表团向全国人大提出。从中可以看出,香港特区全国人大代表和立法会议员发挥着同样重要的作用。基于“一国两制”原则,香港特区全国人大代表作为全国人大的组成人员,“在香港不能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或名义对香港政府管理的事务发表看法”,[20]否则容易造成中央干预香港事务的现象。但是,香港基本法作为我国的一部基本法律,修改香港基本法无疑不属于香港特区自治范围内的事务,而属于全国人大的权限范围。根据《立法法》第15条第1款的规定可知,由香港特区全国人大代表组成的代表团,享有向全国人大提出议案的权力。要保证香港特区全国人大代表这一权力的正确行使,就必须使其参与到香港特区所提议案的提出程序之中,赋予其对所提议案提出程序的实质参与权(即三分之二多数同意)和形式参与权(即最后由其向全国人大提出该修改议案)。当然,不论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央人民政府,还是香港特区所提出的修改议案,都必须先交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研究并提出意见,然后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研究过的修改议案列入全国人大议程,由全国人大按照法定程序予以修改。据此,在实践当中,如果中央无法通过对香港特区进一步授权来使香港特区高度自治权的权力内容与香港特区的社会发展需要相适应的话,或者需要授予的权力本身与香港基本法规定的原有高度自治权相冲突,或者香港特区已不适宜继续享有某项高度自治权,那么全国人大即可通过香港基本法第159条规定的修改程序对香港基本法进行修改,以变更香港特区的高度自治权,使其权力内容与香港特区的社会发展需要相适应。
需要说明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对香港基本法的解释,亦可以在一定程度内使香港基本法的文本规定适应香港社会的变迁,[21](P394-395)适应香港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的需要。因此,基本法解释权、进一步授权的权力、基本法修改权均能够使香港特区的高度自治权与其社会发展需要相适应。在运用这些权力时,要尽量维护香港基本法的稳定性与权威性。基本法解释权与进一步授权的权力有助于维护香港基本法的稳定性与权威性,基本法修改权有助于维护香港基本法的权威性。因此,首先要考虑运用基本法解释权对香港基本法进行解释,无法达到目的时,再考虑对香港特区进一步授权,如果仍然无法达到目的,则需要考虑对香港基本法进行修改。
(五)香港基本法未规定权力属于中央
关于香港基本法未规定权力的称谓,有学者称之为“剩余权力”;[22]也有学者认为“剩余权力”一词适用于联邦制国家,不适用于单一制国家,该学者将香港基本法未规定的权力称为“保留性的本源权力”。[23]笔者直接从描述的角度,将其称为香港基本法未规定权力。关于香港基本法未规定权力的归属,在香港基本法起草期间,曾有意见要求香港基本法明文规定其未规定权力属于香港特区所有。[24](P116)这一要求无疑不符合我国的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如前所述,在单一制国家,中央与地方是一种授权与被授权关系,地方的权力均来自中央的授权,地方没有固有的权力,凡是未授予地方的权力就由中央保留。这一授权与被授权关系亦体现在香港基本法的相关规定中。如前所述,香港基本法的诸多条款体现了其授权性,中央正是通过香港基本法来对香港特区进行授权,香港特区据此获得中央授予的高度自治权。而中央未通过香港基本法授予香港特区的权力,就由中央保留。这亦可以从香港基本法第20条的规定看出。香港基本法第20条规定:香港特区可享有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常委会及中央人民政府授予的其他权力。该条规定包含如下三层涵义:其一,香港基本法未规定的权力由中央保留,否则就不存在中央再进一步授权香港特区的问题了;其二,若香港基本法未规定的权力涉及到香港特区的高度自治,需要由香港特区行使,那么中央就根据香港基本法第20条的规定,将相关权力授予香港特区;其三,若香港基本法未规定权力不涉及香港特区高度自治,不需要由香港特区行使,那么中央就无须再对香港特区进行授权。因此,香港基本法未规定权力归属于中央,香港特区非经授权,不得行使香港基本法未规定权力。
三、余论
香港与澳门曾经长期处于殖民统治之下,在这期间,国家从未对其行使过主权。香港、澳门回归之后,国家恢复行使主权,依照宪法与港澳基本法的规定,中央对港澳特区享有全面管治权。这种全面管治权承载着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的重要使命。为此,中央就需要依法、适时地行使其对港澳特区的全面管治权,以使港澳特区的高度自治权在宪法与港澳基本法的轨道内行使。
[1]郝铁川.从国家主权与历史传统看香港特区政治体制[J].法学. 2015,(11).
[2]黄志勇.港澳基本法要论[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
[3]祝捷,章小杉.主权、国家安全与政制改革:“港独”的《基本法》防控机制[J].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4).
[4]周叶中.宪法(第三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5]王禹.论恢复行使主权[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6]骆伟建,王禹.澳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文选(基本法卷)[G].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7]周叶中,张小帅.再论全国人大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国家安全立法权[J].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4).
[8][德]卡尔·施密特.宪法学说[M].刘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9]陈端洪.制宪权与根本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
[10]邹平学,等.香港基本法实践问题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11][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12]骆伟建.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新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13]周挺.论中央监督权的正当性、范围与行使的法治化建议[J].港澳研究.2016,(3).
[14]王禹.“一国两制”下中央对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权[J].港澳研究.2016,(2).
[15]许昌.中央对特别行政区直接行使的权力的分类研究[J].港澳研究.2016,(3).
[16]郑贤君.隐含权力:普通法对香港政制的影响——解释权的民主性[J].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6,(1).
[17]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条和附件二第三条的解释[EB/OL]. http://www.hmo.gov.cn/Contents/Channel_438/2013/0221/25633/ content_25633.htm,2016-04-23.
[18]二零一七年行政长官及二零一六年立法会产生办法咨询文件[EB/OL].http://www.2017.gov.hk/tc/consult/document.html,2016-04-23.
[19]韩大元,黄明涛.论中央人民政府对香港特区行政长官的任命权[J].港澳研究.2014,(1).
[20]甘超英.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的地位和作用[J].法学家.2001,(6).
[21]韩大元.比较宪法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22]李元起,黄若谷.论特别行政区制度下的“剩余权力”问题[J].北方法学.2008,(2).
[23]张定淮,孟东.是“剩余权力”,还是“保留性的本源权力”——中央与港、澳特区权力关系中一个值得关注的提法[G]//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第7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24]王叔文.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导论[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
[责任编辑 闫明]
The Central Government’s Overall Jurisdiction over Hong Kong and Macao under the Policy of“One Country,Two Systems”
WEI Shu-jun&ZHANG Xiao-shuai
(China Executive Leadership Academy,Pudong,Shanghai 201204,China)
The sovereignty of the Two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of Hong Kong and Macao belongs to China,the country with a unitary system of government.Under the policy of“One Country,Two Systems”,the Central Government exercises overall jurisdiction over Hong Kong and Macao.With a historic mission of national unity and two systems,the exercise of jurisdiction should base on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Basic Law of Hong Kong and Macao.The Central Government’s overall jurisdiction include the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granted to Hong Kong and Macao and the power directly exercis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The power directly exercis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can both supervise and modify the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of these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s.The Central Government should exercise jurisdic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Basic Law to safeguard the national sovereignty,security and development interests and to maintain the long-term prosperity of Hong Kong and Macao.
Hong Kong;Macao;jurisdiction;supervision;modification
D618
A
1674-0955(2016)06-0103-09
2016-09-10
本文系中国浦东干部学院院级课题(CELAP2015-YJ-14)阶段性成果
魏淑君(1970-),女,山东潍坊人,法学博士,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学研究部教授;张小帅(1989-),男,河南许昌人,法学博士,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学研究部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