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与“翻译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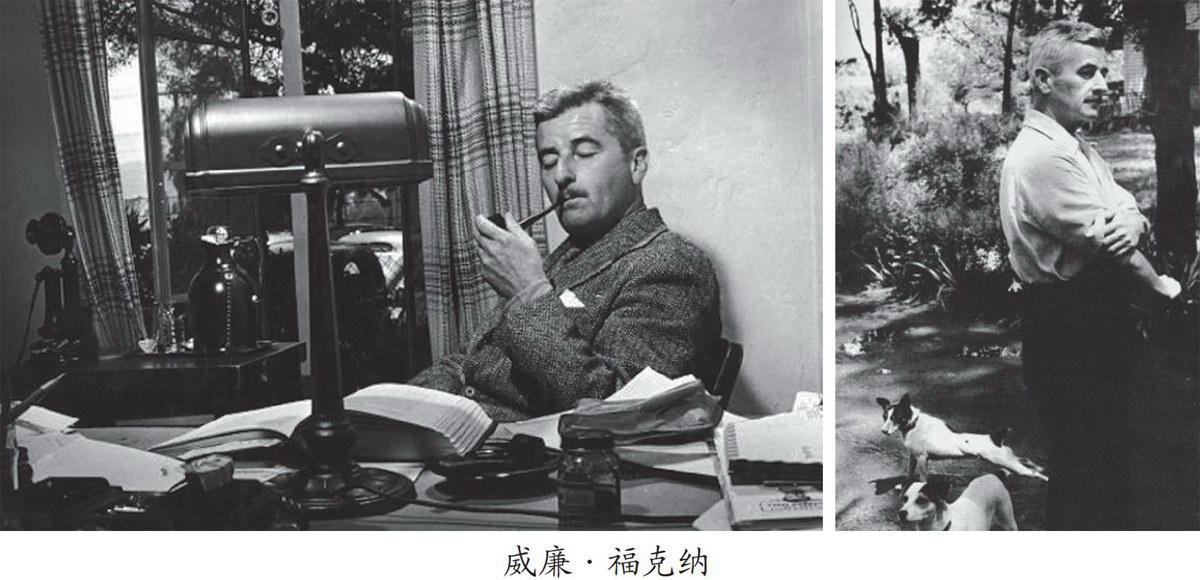
1
翻译跟许多别的事情一样,常常难就难在度的把握。不同的译家,对这个“度”往往心里有杆秤。
杨必先生译《名利场》,把一个good译得花团锦簇,点化出“虔诚的教徒,慈爱的父母,孝顺的儿女,贤良的妻子,尽职的丈夫”的译句。
傅雷先生服膺一条原则“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法文中一个femme,在《高老头》里分别译作女人、太太、老婆、娘儿们、婆娘、妇女、小妇人、少女、小娇娘、老妈子、小媳妇儿、妙人儿等等,想必傅雷先生认为,巴尔扎克倘若用中文写作的话,是会换这许多字眼的。许钧先生译六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名士风流》时,则反其道而行之,遇到法文sourire,统统译为“微笑”或“微微一笑”,决不用莞尔一笑、嫣然一笑、笑吟吟、笑眯眯之类的译法。他的立论是:“法语中关于‘笑的表达法也极为丰富,为何波伏娃只用‘sourire一词,不丰富其表达手段呢?这里无疑有她刻意追求的风格及以此风格为一定的表达目的服务的问。”
2
有一年小提琴家阿卡多来沪演出,并在音乐学院开“大师班”。一位学生演奏了巴赫的《无伴奏小提琴奏鸣曲》,技巧不错,而且音色很美。曲终,阿卡多先生点评说:“如果是拉柴可夫斯基,非常好。拉巴赫不能这样揉弦。”“揉弦太好是个问题。”也就是说,音色华丽,正是缺点所在。在当代的小提琴演奏家中,阿卡多往往被视作炫技型的,但大师毕竟是大师,他首先看重的毕竟是艺术的感觉。
余华这样写他心仪的福克纳:“他不会被那些突然来到的漂亮句式,还有艳丽的词语所迷惑,他用不着眨眼睛就会明白这些句式和词语都是披着羊皮的狼,它们的来到只会使他的叙述变得似是而非和滑稽可笑。”这真是好作家的三折肱之言。
译者也要考虑怎样“揉弦”,明白什么是“披着羊皮的狼”。
3
普鲁斯特的语言堪称精妙,但从总体来说他写得并不华丽。往华丽的路子去铺陈译文,怕是难以传达那种令人赞叹的精妙之处的。
新小说派的作品,在文学观念上很前卫,而作品所用的语言多为规范的法语,用词尤以准确见长。格里耶的小说《吉恩》据说最初就是应约为中学生写的(每章围绕一个语法概念来写,也就是说,这种语法现象的例句在这一章里反复出现,使这一章成为“例章”)。所以新小说派的作品,似也不宜译得花哨。听人称赞克洛德·西蒙的作品有朦胧美,我颇有些怀疑那是把原本还能看懂的句子变得“朦胧”了。
4
“翻译度”,是杨绛先生仿照难度、甜度的说法创造的词儿。举例来说,“可是看到(事情)被拖延着未实现……”比较达意,但翻译度仍嫌不足;“可是迟迟不见动静……”比前两种译法更信也更达,而翻译度也更大。
她说,有的译者以为离原文越近越安全,也就是说,“翻译度”愈小愈妥,“‘死译‘硬译‘直译大约都是认为‘翻译度愈小愈妥的表现”。而翻译度愈小,在意思的表达上就离得愈远。“原意不达,就是不信。畅达的译文未必信,辞不达意的译文必定不信。我相信这也是翻译的常识了。”
本文摘录自《译边草》(周克希著);文章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