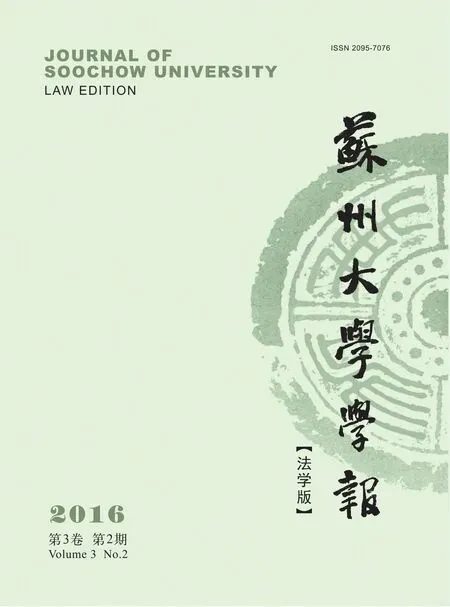“民法典时刻”的自然法—从《法国民法典》编纂看自然法话语的使用与变迁
朱明哲
“民法典时刻”的自然法—从《法国民法典》编纂看自然法话语的使用与变迁
朱明哲*
《法国民法典》的编纂过程不仅具有民法学上的意义,同时也是一个法哲学更新的过程。《民法典》起草中出现的各个草案、对各草案的讨论以及其后的学说发展都表明,通过运用自然法的话语,19世纪的法哲学表现出了和启蒙时代法哲学截然不同的特点。在形式上,关于自然法的讨论实际上让民法既成了一个独立于其他法律渊源的体系,也让成文法成为各种法律渊源中最为重要者。但是学说仍然借残留在《民法典》中的自然法滥觞,以法律解释之名创制规范。实质上,民法学家对自然法的讨论让新政权的民法就其内核而言更像是传统秩序的延续。这种“告别革命”的现象在家庭法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
自然法;民法典;法国大革命;婚姻财产制;离婚
一、导论
民法典起草的争论于2015年再次成为我国学术研究的热点。①根据“中国知网”检索显示,2015年发表的论文中,题名包含“民法典”者凡136篇,这个数字在2014年为79,而2007—2013都维持在50篇左右。上一次讨论的高峰乃是2003—2004年,两年间共有240篇论文题目中包含“民法典”。法典化在一个总括性的问题上和理论法学息息相关:法典化作为法实践上的重大变革,是否伴随着法理论的革新?例如,1814年德国关于法典编纂的讨论虽然并未催生德国的民法典,却促使历史法学派形成了自己的核心论点和组织。②参见舒国滢:《德国1814年法典编纂论战与历史法学的形成》,载《清华法学》2016年第1期。但是关于《法国民法典》之创生在法律理论方面的重要性,尚不见诸讨论。对这部“不仅是资本主义世界最早的民法典,也是世界上最长寿的民法典”③王云霞:《〈法国民法典〉的时代精神探析》,载《法学家》2004年第2期。立法的过程进行考察,对我国民法和法理学界显然都会有所助益。
通过研究法国自然法学说史,本文希望推进我们对两个问题的理解。第一,在君主制和共和制更迭的过程中,也就是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到1804年《法国民法典》生效的这段时间内,是否出现了任何法哲学意义上的重大发展。①关于政治与法政哲学之间的关系,研究已经汗牛充栋,本文不拟赘述。惟望推荐一写就于法国混乱之19世纪的文本:Théodore Jouffroy,《Comment les dogmes finissent》,Globe,mai 1825,II,mai/1825.这份非常不起眼的文本用精炼的语言概括了每一个理论须臾的生命中无限广阔的实践可能性。第二,法哲学如何与法实践相关。初步的答案乃是:法哲学话语的运用——具体而言,自然法话语的应用——在“法典化时代”确立了成文法在众多法源中的优势地位,从而使法实践从法源多元时代迈向了成文法时代;法学家对法哲学话语的掌握和实践让(广义理解的)“法”形成了一个独立于其他社会场的独特领域。不仅如此,法哲学也帮助民法典的起草者论证了关于法典实质内容的主张。
目前我国针对法典化的讨论主要围绕立法技术展开。虽然间或也有涉及立法精神或者立法宗旨的研究,但主要的努力要么并不意在处理法哲学问题,要么过于概括而无法进行任何批判性的讨论。②例外自然是存在的。如谢鸿飞:《中国民法典的生活世界、价值体系与立法表达》,载《清华法学》2014年第6期;张谷:《对当前民法典编纂的反思》,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挂一漏万在所难免,尚祈见谅。直到最近,针对法典化与法哲学的讨论才进入学术视野。③参见石佳友:《法典化的智慧——波塔利斯、法哲学与中国民法法典化》,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考虑到这一点,找到上述两个问题合理回答的意义或许并不仅仅局限在学说史上。
但一个先导性的问题或许是,为什么要把自然法话语作为研究的对象?下文将要表明,作为实证法的成文法之所以在法实践中如此重要,恰恰是因为自然法话语的运用。实际上,把实证法想象成自然法的对立面,是一种典型的用现代人的目光投射古人的做法。一直到中世纪晚期,法哲学家或多或少都是自然法学家。如果说“自然法 ”(或者一种普遍而理想的法律秩序)因为在古典哲学、罗马法文献和中世纪经院哲学中不断使用而具有一个虽然模糊但总体而言可以辨识的核心主张的话,那么“实证法”在现代以前所指称的对象并不明确。在中世纪,复兴的罗马法、地方习惯、经院法和王国的立法在属人和属地两方面主张着交叠的管辖权。文艺复兴的到来为欧洲打开了通向文学、艺术和科学的达道,然而曾经带领欧洲精神文明前进的法学却走上了一段逆旅。民族国家作为新的政治组织方式出现在欧洲版图上,让以前碎片化但是相互交叠的管辖权分布逐渐变得清晰而彼此独立,分开它们的恰恰是民族国家犬牙交错的疆界。④Philippe Jestaz et Christophe Jamin,La doctrine,Dalloz,2004,pp. 39-69.到了17世纪,专制王权逐渐在法国确立,看似与传统彻底决裂的法国大革命其实不过延续了中央集权、乾纲独断的统一立法模式。1804年生效的《法国民法典》标志着法国法典化一个阶段的结束,也象征着一个漫长的法典化世纪的开始。⑤关于欧洲的法典化,参见[德]茨威格特、克茨:《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33页以下;并参见谢怀栻:《大陆法国家民法典研究》,载《外国法译评》1994年第3期~1995年第4期。目前对法典化的研究看起来尚有较强的欧洲中心主义倾向。但是法典化作为1804年到1945年这段时期全世界最重要的法律现象之一,却是无可争议的。其中尤以民法典最为引人注目。关于日本于1896年生效的民法典的研究,参见小柳春一郎「民法典の誕生」広中俊雄=星野英一編『民法典の百年I』6頁(有斐閣、1998年);池田真朗「民法典の歴史」『ボワソナードとその民法』77頁(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11年)。中文作品可以参见[日]荻野奈绪:《法国法对日本民法的影响》,朱明哲译,载许章润、翟志勇主编:《历史法学》(第十卷),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何勤华、曲阳:《传统与近代性之间——〈日本民法典〉编纂过程与问题研究》,载《清华法治论衡》(第2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关于我国清末到民国时期民法典的研究,见张生:《中国近代民法法典化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然而关于世界范围内法典化的研究汗牛充栋,此处仅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廖举数例,挂一漏万,在所难免,仍乞方家见谅。
这一历史进程至少在大陆法国家形成了一套以立法为核心的实证法体系。《瑞士民法典》第1条的规定便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一)凡本法在文字上或解释上有相应规定的任何法律问题,一律适用本法。(二)如本法没有可以适用的规定,法官应依据习惯法,无习惯法时,应依据他作为立法者所规定的规范裁判之。(三)于此情形,法官应遵循公认的学理与判例。”⑥译文参见谢怀栻:《大陆国家民法典研究》,载《外国法译丛》1995年第2期。关于这一条的研究,亦可参见李敏:《〈瑞士民法典〉“著名的”第一条——基于法思想、方法论和司法实务的研究》,载《比较法研究》2015年第4期。表面上看,这是对某种程度的法律多元主义的承认,并且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法国民法典》的立法至上主义。①一个有趣的史实是,尽管《瑞士民法典》的起草者胡贝尔(Eugen Huber,1849—1923)认为自己借鉴了惹尼(François Gény,1861—1959)1899年在《实证私法的解释方法与法源》(Méthode d'interprétation et sources en droit privé positif)中提出的法律渊源理论,但惹尼在本书再版时特别附录一篇文章,主张自己并不认同《瑞士民法典》第1条的立法技术。François Gény,《Les pouvoirs du juge d’après le Code civil suisse du 10 décembre 1907(Chapitre troisième de l’épilogue)》,inMéthode d’interprétation et sources en droit privé positif:essai critique,Paris,Librairie générale de droit et de jurisprudence,1919,vol. II/II,pp. 308-329.然而两种说法之间,毕竟同时涉及此一地彼一地的跨语境实践和此一时彼一时的时间流变,所以很难说到底是胡贝尔一厢情愿还是惹尼改弦更张,其中原委,颇值玩味。然而其实质则是赋予了制定法绝对的优先地位。②参见李敏:《〈瑞士民法典〉“著名的”第一条——基于法思想、方法论和司法实务的研究》,载《比较法研究》2015年第4期。类似的表达并不仅仅限于民法典。《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第1款也规定:“法院对于陈诉各项争端,应依国际法裁判之,裁判时应适用:(子)不论普通或特别国际协约,确立诉讼当事国明白承认之规条者。(丑)国际习惯,作为通例之证明而经接受为法律者。(寅)一般法律原则为文明各国所承认者。(卯)在第五十九条规定之下,司法判例及各国权威最高之公法学家学说,作为确定法律原则之补助资料者。”③关于国际法上的实证主义,参见Awalou Ouedrago,《Le positivisme en droit international:fondement épistémologique d’un paradigme mécaniciste》,Revue générale du droit,2010,vol. 40,pp. 505-540.可以说至少在大陆法国家,我们所知的法律实证主义根植于民法典的时代。
上述论断意味着,我们可以从民法典的编纂入手,考察一套自然法话语和今天我们所知的实证主义的关系。在“自然法-实证法”这一概念上的对应模模糊糊地形成后,两者之间的关系就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不断变化。在另外的文章中,笔者曾经试图提出过一个极简主义的类型学总结。

表1 不同时期自然法学说的类型学④朱明哲:《三十五年来自然法讨论发展路向》,载《清华法治论衡》(第23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该表最初的形式,见Mingzhe Zhu,Le droit naturel dans la doctrine civiliste de 1880 à 1940,Thèse de doctorat,Sciences Po.,Paris,2015,p. 7.
可以看出,如是归纳仅仅能够概括欧亚大陆最西端一小块区域的情况,但恰恰忽略了法典编纂这一时刻的重要意义。虽然当今的历史研究往往强调长时段的考察,但是实证法体系和法律思想往往是在对突发事件的应对中形成的。战争⑤仅需举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例子就足以说明战时经济对私法的影响。参见Janwillem Oosterhuis,“Unexpected Circumstances arising from World War I and its Aftermath:‘Open’ versus ‘Closed’ Legal Systems”,Erasmus Law Review,2014,vol. 7,no 2,pp. 67-79;David Deroussin,“The Great War and Private Law:A Delayed Effect”,Comparative Legal History,2014,vol. 2,no 2,pp. 184-214;Victor Basch,La guerre de 1914 et le droit,Paris,Ligue des droits de l’homme & du citoyen,1915.、政治危机⑥例如,汉诺威公国宪法危机所激发的“哥廷根七君子”事件便促使历史法学派发展出了自己的公法学说,参见Alfred Dufour,L’histoire du droit entre philosophie et histoire des idées,Bruylant,2003,p. 665.等等事件都可能引起实证法和法律思想的突变。在西欧的语境中,法典编纂毕竟是一形塑当今实证法体系的进程。一个政治体的法典编纂对法律的影响并不一定亚于任何战争和政治危机。所以,研究法典编纂的过程中自然法话语的使用,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法律思想的变迁、从而更加正确地看待民法典起草。
在1793—1802年这段民法典起草的岁月里,这个我们可以称为“民法典时刻”的关头,自然法也经历了从语义到语用的变革。五份草案在十年间你方唱罢我登场,其中康巴塞雷斯(Jean-Jacques-Régis de Cambacérès,1753—1824)主导了前三份草案的起草工作,雅克米诺(Jean-Ignace Jacqueminot,1754—1813)带领的委员会受命起草了第四份于史学上并不受重视的草案①石佳友在他专门研究法国民法制定程序的文章中甚至没有提到这一草案。参见石佳友:《法国民法典制定的程序问题研究》,载《比较法研究》2015年第3期。考虑到这一草案很快就让位于波塔利斯更重要也更有生命力的草案,忽视它也完全是可以理解的处理。,最后成为1804年《民法典》底本的则是四人委员会②包括了波塔利斯(Jean-Etienne-Marie Portalis,1746—1807)、特龙歇(François-Denis Tronchet,1723—1806)、普雷阿梅纽(Félix-Julien-Jean-Bigot de Préamuneu,1747—1825)和马尔维尔(Jacques de Maleville,1741—1824)。提出的《1801年草案》。为了回答本文开头提出的两个问题,下文将把研究的对象集中于《法国民法典》编纂过程中使用的五份草案、最后的文本以及对各草案的说明资料,并集中考察其中对自然法话语的使用。费内(Antoine Fenet,1799—1876)所编纂的《民法典准备资料汇编》(Recueilcomplet des travaux préparatoires du Code civil)为我们展现了围绕民法典的内容展开的所有正式辩论。为了方便起见,本文并不打算对每个具体制度都加以考察,而是把重心限制在“民法典时刻”的法律观和对以婚姻为中心的家庭制度的讨论中。前者揭示的是民法与自然法在形式上的关系,后者则将展现自然法话语对民法中某个具体制度的意义。
民法典的可能文本从强调政治宣告性和激进主义意识形态的革命立法,逐渐转向了一种把守旧的意识形态隐藏在分析性的法律技术和法律概念之下的立法模式。③对《法国民法典》所表现的意识形态,一直争议不断。阿尔瑙主张民法典实际上是一确定了资产阶级社会秩序的结构André-Jean Arnaud,Essai d’analyse structurale du code civil français:la règle du jeu dans la paix bourgeoise,Paris,Pichon et Durand-Auzias,1973;André-Jean Arnaud,《La tradition française dans la théorie du droit des civilistes in La philosophie du droit aujourd’hui》,Archives de Philosophie du Droit,1988,vol. 33,pp. 261-281;雅曼认为一种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民法思想直到19世纪中叶才发展起来Christophe Jamin,《Plaidoyer pour le solidarisme contractuel》,inLe contrat au début du XXIème siècle,Paris,LGDJ,2001,pp. 441-472;更多的争议参见AMSELEK P.,C. GRZEGORCZYK,et A.-J. ARNAUD(dir.),Controverses autour de l’ontologie du droit,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89,p. 228.我国学者倾向于把《法国民法典》看成一份融合了财产法上的革命、自由主义精神和家庭法上传统观念的文本,参见王云霞:《〈法国民法典〉的时代精神探析》,载《法学家》2004年第2期;晚近的研究参见石佳友:《法典化的智慧——波塔利斯、法哲学与中国民法法典化》,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通过确立民法相对于自然法等其他规范领域的独立性,也通过灵活地运用继受自旧制度法学的自然法话语,法学家从形式和实质两方面避免了民法成为政治意志的附庸。在大革命时代承载着一套解放诉求的自然法话语,于“民法典时刻 ”迅速与革命传统决裂,而重新获得了前革命时代保守的、强调等级秩序的内核。只不过这种政治倾向并不仅仅表现为以自然法为说辞支持或者反对某一种规则——这是本文以下内容要讨论的一个方面。它更重要而且持久的意义在于从方法论上重新定义了自然法和民法典之间的关系。一方面,经由自然法辩护的法律规范成为了实证法的组成部分,并因此割断了它们与自然法在道理上的联系,而变成了效力完全由政治权威保证的规范。另一方面,学理上则发展出了用自然法来解释实证法的主张。一种把自然法和立法者创造物对立起来的思想已经在1800年出现萌芽。不过,两者关系在当时的理论叙述中比许多人想象得复杂。自然法不但支撑着实证法的具体内容,而且时刻准备在实证法出现漏洞的时候进行续造工作。
依笔者浅见,法典文本所确定的秩序自然需要考虑原则性的规定,但也要对种种例外和细则进行考察,而且不应把财产法和家庭法看作两个截然对立的部分,因为家庭法中恰恰包含了许多财产性法律的制度,已婚妇女的财产权就是其中最明显的例子。阿尔瑙对文本的结构分析实际上以今天人们对具体语词意义及各条文之间的重要性理解为前提,颇有以今度古之嫌。相反,雅曼关于19世纪中叶才出现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民法理念的主张颇值赞同。窃以为1804年的法典文本所确定的是一种贯彻着家长主义和父权制精神的社会秩序。具体论述容日后另行撰文。
二、与民法并存的自然法
首先要来探讨的是形式问题,即民法与自然法之关系问题。解决此问题的关键乃在1801年的《委员会草案》。1789年革命后的法国一直处于政治动荡中。第一帝国(1799—1815)建立以前,虽然康巴赛雷斯起草了三部民法典草案,但法国并没有足够稳定的中央立法机构让民法典生效并施行。①关于这一段历史,参见[法]乔治·杜比主编:《法国史:从起源到当代(中卷)》,吕一民等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813-863页。具体关于1799年康巴赛雷斯的三部法典草案,参见石佳友:《法国民法典制定的程序问题研究》,载《比较法研究》2015年第3期。1800年8 月11日(共和历八年热月24日),拿破仑成立了起草委员会。委员会随后提交的《1801年草案》便是日后民法典的雏形,波塔利斯著名的《法典起草委员会在国会面前的关于民法典草案的演讲》所辩护的正是这一份草案。和1804年生效的文本不同的是,本草案包含了通常认为由波塔利斯起草的39条《序编》。《序编》中特别处理了民法与万民法、自然法关系的问题,而“自然法”这个术语并不见于康巴塞雷斯的草案②虽然康氏的草案没有处理自然法问题,但他在草案说明中使用了自然法的话语。而且康氏草案的在法律渊源方面的核心问题乃是民法与公法的区别问题。和《民法典》最后的文本。令人感兴趣的是,两份文本的对比,或者更确切地说,《序编》从《民法典》中撤出,究竟能向我们揭示何种理论发展的脉络?这一问题的解答蕴藏在《民法典》起草的文件中,但要理解这些文件,却又不得不把它们看作一个更大的群体(后革命时代的民法学家)之意见表达,并置回一个更长历史时段(比如“长十九世纪”)中检验。姑且于此提出两项观点。(一)自然法从《民法典》中退场,说明民法话语中关于立法和自然法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改变:立法成了各种法律渊源中最主要的一种,只要不明显地与自然法冲突即可,不再需要从自然法中推演而来。(二)“法”与“成文法”的区分作为自然法思想的滥觞,留在了《民法典》文本中,为日后法学界以“法”之名偏离“成文法”提供了依据。
民法史的研究者很容易把波塔利斯放在神话人物的地位上,同样受到神化的还有归于他名下的那篇脍炙人口的《法典起草委员会在国会面前的关于民法典草案的演讲》。用优美而具有高度文学色彩的语言,委员会阐明了法典的任务和各部分起草的考虑,以至于人们希望在波塔利斯这样一个本质上是实践家的人身上找出一个对民法和法哲学有整体思考的理论家。他也确实是《民法典》起草委员会中最重要的成员,代表委员会向资政院、最高法院和立法会三个不同的政治实体汇报。③Pierre-Antoine Fenet,《Précis historique sur la confection du Code Civil》,inRecueil complet des travaux préparatoires du Code civil,Paris,Videcoq,1836,vol.I,pp. xxxv - cxxxviij.人们往往没有意识到的是,我们在赞美波塔利斯的同时,却也含蓄地指出了背后的不可能:写作优秀的法哲学作品、起草法典以及随之而来的说服工作,都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任何人无法在1799到1801年这短短的时间内同时完成这两项工作。史学研究逐渐承认,波塔利斯在民法典时刻更多是一位政治家,而此前则是一位罗马法意义上的法学家——零星地写一些评注,大部分时间都在提供法律建议。④Bernard Betgnier,《Potalis et le droit naturel dans le code civil》,Revue d’histoire des facultés de droit et de la science juridique,1988,no 6,pp. 77-101.他如此忙碌以至于大部分作品实际上都是由他口述、秘书执笔整理而成的。《演讲》现在流传的文本更是此后对许多分散作品的整合而形成的。⑤Bernard Betgnier,《Potalis et le droit naturel dans le code civil》,Revue d’histoire des facultés de droit et de la science juridique,1988,no 6,pp. 77-101.所以,把波塔利斯(以及其他民法典的起草者)看作一个具有独创精神的理论家,并希望从他的书写中找到什么划时代的观点,是注定失败的努力。
但那些归在他名下的作品恰恰因此而尤其值得研究。正因为他的作品缺乏独创性,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他同时代的人所共同接受的观念。正因为当时的民法学家缺乏改天换地的野心,我们可以通过他们的话语考察“民法典时刻”貌似剧烈的制度变迁表象下缓和而坚定的观念更迭。换句话说,波塔利斯及其他“伟大”民法学家名下的话语,正因为(在哲学的意义上)如此平庸,而(在思想史的意义上)如此有价值。
(一)《1801年草案》“序编”中的法律定义
最终没能进入《民法典》文本的《序编》,以“关于法与各法律”(Du droit et des lois)为题,明确地区分了一般性的“法”的概念和作为法之组成部分的“法律”。该草案的第1条定义了自然法:“存在一种普遍且恒常的法,作为所有实定法之源。这种法就是自然理性,因为后者统治着所有的人。”它的第2条和第3条则强调了万民法:“全体人民承认一种外部的法,或曰万民法,而他们自有一仅仅适用于他们的内部法。(第2条)外部法或万民法,乃是在不同民族彼此交往时所得见的规则之集合。在这些规则中,有一些仅根据各种一般的衡平原则,另一些则是由普遍的实践或者条约确定的。前者构成自然万民法,后者构成实在万民法。(第3条)”第4条则是关于法律渊源的规定:“一国内部法包括普世法、仅仅在其管辖范围内有效的特别法律以及那些作为法律之补充部分的习惯或习俗组成。”至于什么是法律,则定义在第6条:“在所有的国家,法律是立法权对内部制度和共同利益做出的庄严宣告。”下文中,除非是出于忠实地引用原文的需要,将仅仅使用“自然法”,而不再是“自然法与万民法”。因为是波塔利斯自己强调“自然法和万民法之区别并非在于内容,而在于适用——对所有人都无限适用的理性叫做自然法,而在事关各国关系的问题时则称为万民法”。①Jean-Etienne-Marie Portalis,《Discours préliminaire prononcé par Portalis,le 24 thermidor an 8,lors de la présentation du projet arrêté par la commission du gouvernement》,inRecueil complet des travaux préparatoires du Code civil,Paris,Videcoq,1836,vol.I,pp. 463-524.
除此之外,第一编第5条规定“外国人在法国享受所有自然法、万民法和严格意义之民法上的利益,除非公法对此做出修改”。同一编第31条:“他们(因为死亡宣告而失去民事能力的人)仍然拥有自然法和万民法上的行为能力。所以他们可以为商业给付、买卖、赠与、交换,为不动产租赁,为接待,请求损害赔偿和债务清偿。”换言之,起草者承认不管成文法是否规定都存在的自然权利。
虽然上述文字目前都不见诸《民法典》,但它们并非不重要,恰恰相反,这些已经深埋历史故纸堆中的话语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子,使今天的研究者可以探究先辈的观念。
可以说,从表面上看,在“法与各法律”的标题下,后来未能进入《民法典》的《序编》中,前四条要解决的是法的渊源问题,并指出吾人所称“法”者,非仅限于立法,尚包括自然法和万民法(包括了现在所说的国际私法和国际公法②关于所为“万民法”的内容,参见Félix Senn,De la Justice et du droit. Explication de la définition traditionnelle de la justice,suivie d’une étude sur la distinction du « jus naturale » et du « jus gentium »,Paris,Recueil Sirey,1927,p.96.)。相反,“在一国有效的法律包括了国内法和普世法”这样的宣告出现于《民法典》看起来多少有些突兀。国内法是立法者所能够改变的,而普世法则是立法者所无法变更的。根据这四条所表达的法概念论,各国的立法——包括《民法典》——原本就无法改变包括自然法和万民法的普世法的存在、效力和内容。那在《民法典》中为此宣告,岂不是叠床架屋?
突兀和混乱有其自身的价值。
实际上,上揭四个条文之间的内在关系向我们展现了一个关于自然法的更深层的理解。这种理解至少由两个不同的面向构成。一方面,它暗示了民法相对于自然法和万民法的独立性,也就是拒绝了前革命时代曾经流行的把民法视为自然法推导而来之产物的思路,并与此同时拒绝了用自然权利为毁掉一个旧世界张目的革命话语。另一方面,它则暗示了对法典化时代自然法之实证效力的担忧。委员会草案小心翼翼地在否认民法之独立性和否认自然法之实在性的两种倾向之间保持着平衡,避免全然支持某一种哲学倾向,倒也是彼时情势所需。
《草案》出台后,首先发到终审法院和各个上诉法院,由法官进行审议。在各上诉法院的意见中,“序章”中严格来说算是法律理论的规定毫不意外地受到了批评①有时候,批评者使用的语言还相当直接。比如巴黎的代表便指出,“草案虽然反映了作者卓著的声望,但它也确实需要大幅修改才能变得完美”。《Observations faites des commissaires du tribunal d’appel séant à Paris》,in Recueil complet des travaux préparatoires du Code civil,Paris,Videcoq,1836,vol.V,pp. 91-292.。而批评恰恰来自于起草者希望通过折衷而避免的更明确的两种倾向:一种倾向虽然也支持民法典的起草,但坚持启蒙哲学所鼓吹的“实在法必须以自然法为最终源泉”主张;另一种倾向则坚决反对在民法中涉及自然法的观念。
来自巴黎上诉法院的代表强烈主张第一种观念。在他们提出的修正稿中②有趣的是,如果说人们批评《草案》学究气太重,巴黎草案相比之下就更像一本教科书了,而且是一本法律理论的教科书。大量的条款处理的不仅仅是民法上所特有的定义,还有各种法律的分类、法律体系的构成、不同部门法所规制的内容,甚至立法权的行使,大有用《民法典》取代宪法的架势。,第2条明确指出:“自然理性所施加的规则组成自然法,这些规则是所有成文法(lois écrites)的基础,后者必须或多或少是自然公正的结果。”③《Observations faites des commissaires du tribunal d’appel séant à Paris》,in Recueil complet des travaux préparatoires du Code civil,Paris,Videcoq,1836,vol.V,pp. 91-292.孤立地看,这一条和《草案》第1条的宣告没有太多的不同。但因为巴黎修正稿并没有像《草案》那样明确提出实证法或成文法作为一种独立于自然法而存在的法律渊源,所以巴黎人的主张实际上认可了自然法作为成文法之前提的地位。一边是“实证法之源”,另一边是“成文法的基础”,虽然在今人眼中无甚区别(反正自然法已经成了“踩着高跷的扯淡”),而在时人心中却实在是形虽相近,意已千里。从“实在法”到“成文法”的意义转换且不去谈它,《草案》中的表达,不过是说实证法的内容最终要经受自然法的检验,而能够满足自然法的要求的规则可以有许多——这也说明了为什么需要特别指出存在于“仅仅在一国管辖范围内有效”的国内法。换言之,《草案》仅仅满足于说明未来的民法典之内容即便在自然法的角度看也可以接受。而巴黎人关于自然法是成文法基础的主张实际上是承认后者是经由前者演绎而来。况且,不同于《草案》接受的“检验模式”,巴黎修改稿的“演绎模式”意味着所有符合自然法的规则都从自然公正的概念中得来,那么所有的成文法都会包括大致一样的内容。
和巴黎的上诉法院不同,有些上诉法院的代表坚决反对实证法和自然法之间的区别。“第31、32、33、34条必须彻底修改。它们的基础是人们所为之法律行为可以区分为属于自然法与万民法和属于严格意义之民法两类。事项区分已经不能令人信服,并不应该出现在我们的民法典中。”④Observations des tribunaux d’appel,No1er,Rapport fait au tribunal d’appel séant à Agen,par MM. Marraud,Lafontan,Miquel et Tartanac,in Recueil complet des travaux préparatoires du Code civil,Paris,Videcoq,1836,vol.III.里昂的法官也认为“所有从旧法延续下来的问题全都来源于我们其实并没有办法区分严格意义的民法与自然法或万民法。”⑤Observations des tribunaux d’appel,No17,Observations présentées par les commissaires nommés par le tribunal d’appel de Lyon,in Recueil complet des travaux préparatoires du Code civil,Paris,Videcoq,1836,vol.IV.绝不能说这些代表否定自然法的存在,康巴塞雷斯也没有在他的草案里处理自然法的概念,但他的立法说明里则多次诉诸自然法。更符合历史的说法应该是这些代表确信自然法的存在,但他们不认为民法可以从自然法中独立出来,也不认为民法典——作为人的创造物——有能力解决属于自然法的问题。而且,既然他们讨论的是关于是否存在“自然法上的行为能力”和“民法上的行为能力”之间明确的区分,那些反对在民法典中单独宣告实证法和自然法划分的代表毋宁是在主张民法典只能够处理民法上的行为能力,而必须把属于自然法的事务留给自然法去解决。在讨论中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说他们中的任何一位会主张民法和自然法在效力上的分离,只能说他们出于立法技术的考虑认为这是一个无法在《民法典》中规定的事项。
而从更广的历史视角来看,来自各个地方上诉法院的意见遵循的是一套前法典化时代的逻辑,而《草案》则昭示了属于法典时刻的思路。前已述及,法国大革命以前的欧洲是法律多元性的天国。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的欧洲经历了政治和学术的双重转型。民族国家的出现让过去经院法、罗马法、习惯法并存的情况变得更加复杂,而物理和数学方法的兴起则促使启蒙思想家希望用一套从理性演绎而来的法典统一离散的法律实践。①关于这段历史,参见舒国滢:《17、18世纪欧洲自然法学说——方法、知识谱系与作用》,载《比较法研究》2014年第5期,并参见舒国滢:《欧洲人文主义法学的方法论与知识谱系》,载《清华法学》2014年第1期。多玛(Jean Domat,1625—1695)和波蒂埃(Robert Pothier,1699—1772)两位法国法学家就是其中的翘楚。巴黎的代表坚持的是启蒙时代从自然法推演出实证法的思路,里昂和其他地方上诉法院的代表则倾向于多元论的立场,认为民法和自然法截然分离,是各种法律渊源中独立的组成部分。但无论哪种看法,都处于前法典化时代的思想范畴。
这种思路在法典化的时代无法维系,并不是因为启蒙主义自然法的知识论主张已经破产,而是因为《民法典》确确实实包含了许多革命意识形态所添附的内容。其中最典型者莫过于离婚。婚姻从罗马法时代起便是契约的产物,而革命时代的自然法话语一反罗马法上婚姻契约不可撤销的学说,而从契约自由的角度出发对婚姻至少在可撤销性方面和其他契约一视同仁。②David Deroussin,Histoire du droit privé:XVIe-XXIe siècle,Paris,Ellipses Marketing,2010,pp. 60-69.所以,《草案》的起草者——同时也是日后《民法典》的起草者才有必要稍微改变一下确认自然法的方式。回顾一下康巴塞雷斯的三份草案,我们会发现自然法这个概念并没有出现。所以在时人眼中,自然法的存在并不是一个需要通过民法典来回答的问题。但起草者仍然采取了这种毋宁是背离传统的方式陈述他们对自然法的理解,其原因恰恰是因为他们意识到《草案》的内容中包含了需要诉诸自然法而得到证成的内容。至于具体是哪些规则,且留待后面的部分讨论。特别重要的毋宁是,《草案》中关于自然法作为实证法之源而非演绎之公理性前提的表述,已经与此前的自然法传统分道扬镳,迈向了可能容纳民族国家不同政治性决定的另一种自然法理论。正是这种自然法理论在此后的日子里为伯伦知理(Johann Bluntschli,1808—1881)等公法学家提供了叙述的可能性。在这里,旧时代渐渐远去,新时代即将到来,两者的脚步声混在一起,回荡在法学的殿堂。
(二)礼失而求诸野:从《民法典》退场后的自然法思想
“比麦克白低微,可是你的地位在他之上。不像麦克白那样幸运,可是比他更有福。你虽然不是国王,你的子孙将要君临一国。”③《麦克白》第三场。本译文采用朱生豪译文,《莎士比亚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麦克白》中女巫对班柯的预言恰好也道出了《序编》在民法史上的地位。虽然并没有出现在法典正文中,《序编》的内容却因为保存在了民法学说中,而拥有了至少和《民法典》相似的生命力。
简单地翻阅19世纪重要的民法教科书便不难发现,法国民法学者几乎无法在不处理《序编》所涉及问题的情况下讲授民法学的知识体系。此正所谓“功夫在诗外”。从德尔万古(Claude ÉtienneDelvincourt,1762—1831)开创性的作品起,学者在解释《民法典》时总要先处理《民法典》所没有谈的问题,即“法的一般定义”、“实证法与自然法之区分”、“民法之独立性”。④Claude Étienne Delvincourt,Institutes de droit civil français,conformément aux dispositions du Code Napoléon,Paris,P. Gueffier,1808,vol.I.第一部体系化地阐释《民法典》的教科书,迪朗东(Alexandre Duranton,1783—1866)跨时代的作品也延续了这一思路,在正式进入各个民法条文的讨论之前,先处理起草委员会本来需要在《序编》中加以解决的问题。⑤Alexandre Duranton,Cours de droit français suivant le Code civil,Paris,Videcoq,1844.享有“注释王子”美誉的德莫隆布(Charles Demolombe)则扩张了关于一般法律定义和分类问题的篇幅,使其成为教科书中相对独立的部分。⑥Charles Demolombe,Cours de Code civil,Paris,Pedone Lauriel,1845.到了世纪之交,新的教学规定免除了民法学家逐条注释《民法典》的义务,此时影响至为深远的教科书已经专辟“引论”作为独立于民法典解释的部分。①Ambroise Colin et Henri Capitant,Cours élémentaire de droit civil français. Tome 1er,Paris,Dalloz,1930.本书最早版本乃出版于1897年,本文参考的是第5版。实际上本书各个版本在体例安排上并无大的区别。更为现代的教科书则在“一般法律理论”下,分五章讨论法律理论的问题。其中第一章几乎完整包含了委员会草案中《序章》的内容,并有所添加:法的定义、法律与道德、法的形成、实证法与自然法、实证法的分类。②Henri Capitant,Introduction à l’étude du droit civil:notions générales,Paris,A. Pédone,1929.
按照金山直树的说法,19世纪是一个自然法式微而实证主义兴起的时代。③Naoki Kanayama,《Les civilistes français et le droit naturel au XIXe siècle》,Revue d’histoire des facultés de droit et de la science juridique,1989,vol. 8,pp. 129-154.此说依管见并无不妥,但语词使用上的困惑让情况或许比他想象的要复杂一些。“自然法”一词的命运和《序编》极为相似。随着《序编》淡出《民法典》文本,自然法的地位也从演绎式地推导实证法变成了消极地评价实证法。似乎,自然法的概念从《民法典》最终文本中退出可以视为成文法的胜利。但是,“法”和“成文法”或者“立法”之间的区别却留在了法学之中,并让“法”在某种意义上发挥着过去由自然法承载的批判功能。用波塔利斯的话总结来说便是:“法是普遍理性,是在事物本质之上建立的最高理性。成文法/立法是或者必须只能是降格为实在的规则和个别规定的法。”④Jean-Etienne-Marie Portalis,《Discours préliminaire prononcé par Portalis,le 24 thermidor an 8,lors de la présentation du projet arrêté par la commission du gouvernement》,in Recueil complet des travaux préparatoires du Code civil,Paris,Videcoq,1836,vol.I,.
法与实证法的区分最终以隐晦的方式留在了《民法典》的第4条——“审判员借口没有法律或法律不明确、不完备而拒绝受理者,得依拒绝审判罪追诉之”。第4条的脚本,《草案》的第14条原载:“在法律中没有可以适用的规定时,法官就成了一名执行公正的人;他不得以成文法的沉默、不清楚或不足为借口拒绝裁判,他在此时适用永恒不变的理性。该规定仅限于民事领域,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及于刑事领域。”从《草案》的第14条到《民法典》的第4条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公正”、“永恒不变的理性”和对法典可能存在漏洞的明确承认最后都在对草案的攻讦下退出了法典文本。但这条鸿沟并非无法跨越,只不过需要成熟的时机。实际上,在19世纪初,法学家尚以民法典无漏洞为前提评注法典条文的时候,第4条的方法论意义确实没有显现。但草蛇灰线,伏笔千里。波塔利斯之子于1844年再讨论《民法典》和自然法的关系时,就已一针见血地指出,立法的垄断性地位并非绝对:
“无人能对道德义务视而不见,因为自然法是照亮世间所有人之良心的内在光芒……任何人都不能无视法律,但要维系这一信条,且不至于让法律拟制与事实相悖,必须对法律的组合加以留意。要避免不清楚的区分、无用的添附、存疑的解释,要从法律中探求公正的要求,根据逻辑把条文区别分类、论理推演,裨整合各法律为一和谐体系。”⑤Frédéric Portalis,《Essai sur l’utilité de la codification》,in Frédéric Portalis(dir.),Discours,rapports et travaux inédits sur le Code civil,Paris,Joubert,1844,p. v.
自然法和作为自然法同义词的“公平”让人可以把成文法整合成逻辑和价值上都不存在冲突的体系。但这项工作只能由学者完成。⑥Frédéric Portalis,《Essai sur l’utilité de la codification》,in Frédéric Portalis(dir.),Discours,rapports et travaux inédits sur le Code civil,Paris,Joubert,1844,p. v.学说因而假自然法成了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不必屈从立法,虽然“成文法无可置疑的权威”⑦Frédéric Portalis,《Essai sur l’utilité de la codification》,in Frédéric Portalis(dir.),Discours,rapports et travaux inédits sur le Code civil,Paris,Joubert,1844,p. v.仍然是所有学说形式上的后盾。
立法是政治性的,因此必然和意志相连。相反,“法”是理性的,所以无论是在具体的裁判还是在一般性的学理解释中,对成文法的解释和漏洞填补都需要回归到一般意义上的“法”,其背后又是不变的“自然”。波塔利斯因此才强调:
“若每一方面都确切的文本付之阙如,以下的材料就取代了法律:古老、明显而长期存在的实践,类似而不间断的裁决,得到普遍接受的观念或信条。当我们无法得到任何长期存在而为人所知的规则时,当一个全新的事物出现时,我们则回溯到自然法的诸种原则。毕竟立法者的视野有限,而自然之理无穷。自然在关于人类事务所有可能的方面都发挥作用。”①Jean-Etienne-Marie Portalis,《Discours préliminaire prononcé par Portalis,le 24 thermidor an 8,lors de la présentation du projet arrêté par la commission du gouvernement》,in Recueil complet des travaux préparatoires du Code civil,Paris,Videcoq,1836,vol.I,.
所以,《民法典》中兼具概念论和方法论意义的第4条本身就是自然法思想最终留在民法中的一条线索,吊诡地在成文法中规定了不同于成文法、对成文法有检视和补充作用的“法”。如果说关于“序编”的讨论最终在概念上确立了民法成文法的独立地位,并且隐然开启了一个立法中心主义的时代②所谓“立法中心主义”,乃是一种深深嵌刻在19世纪政治实践和宪法学说发展中的思潮,主张在议会民主制下,法律的形式合法性是其正当性的根源。所以经过立法机关以法定方式公布的立法都是法律,而法律也仅仅等同于立法。Guillaume Sacriste,La République des constitutionnalistes:professeurs de droit et légitimation de l’État en France,1870-1914,Paris,Les Presses de Sciences Po,2011,pp. 249-331.,那么第4条则像1789年以前多元实证法时代的遗迹与理性主义哲学的奇妙结合:一方面宣示了成文法之外其他法律渊源的存在,另一方面则肯认了一个抽象性的、涵盖了所有法律渊源的“法”作为各种规范的上位概念。
到了19世纪中后期,当《民法典》的文意射程已经无法解决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法律问题时,漏洞填补的需要和法官裁判的义务一拍即合,而第4条便成了两者的黏合剂。③参见朱明哲:《法国民法学说演进中对立法者认识的变迁》,载《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14年第3期。学说对第4条的研究和解释,同时也打开了回归自然法的大门。既然学说必须重新解释法律的条文俾使之符合社会现实④主此最力者非萨莱耶莫属。见Raymond Saleilles,《L’École historique et droit naturel》,Revue trimestrielle de droit civil,1902,vol. 1,no1,pp. 82-112.,那么成文法实际上便仅仅具有暂时性的和派生性的价值。同样,法学家不能坐视世道人心任意变迁⑤最大的风险,对于法国法学家而言,便是马克思所预言的无产阶级社会的来临。Georges Ripert,《Le socialisme juridique d’Emmanuel Lévy à propos de:La vision socialiste du droit,1926》,Revue critique de législation et de jurisprudence,1928,vol. 48,no1,pp. 21-36.,在19世纪前半段因为《民法典》的强势而湮没无闻的自然法重新有了意义,作为现成的话语工具,让法学家们可以通过借重自然法解释现行法,重掌对社会秩序的定义权,而不至于让重修《民法典》的主张得逞。所以,虽然《民法典》文本没有保留自然法的话语,却在第4条中保留了自然法精神回归的可能性。
三、告别革命的自然法
《民法典》源于革命,却因为其制定而把法国领向一个与革命渐行渐远的时代。在革命的宏大叙事下,政治上便宜行事的需要和稳定政权的需要并没有为私法的独立发展留下足够的空间。而且,革命所张扬的平等精神也力求抹平旧制度下的建立在人之等级关系上的民法规则。然而,法典化的过程却恰恰把社会制度的重塑引向了相反的方向。高举平等大旗的启蒙时代法制却至少在家庭法方面传承了将人区分对待的各种规范。
正因为处在一个新旧交叠的时代,自然法在法典所确定的这一套秩序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毋宁是相当复杂的。在同一份文本中,因为议题的改变和不同部分执笔人的不同⑥复数执笔人的问题在《民法典准备资料汇编》所辑的以各个机构之名义对不同草案提出的“意见”或“观察”中尤其明显。目前我们已经可以通过考据(如当时在该机构中工作的人、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和每个人的观点)和写作风格比较等途径推断少量段落或许出自何人之手,但一方面很少有直接证据让我们确定具体各个篇章和段落的作者,另一方面还有大批的文本我们甚至无法推测可能的作者。,有时候能看到自相矛盾的表述。可是正如前文所言,让我们感兴趣的并不是整理出一套逻辑周延的自然法体系,而是去考察人们希望用“自然法”来做什么,以及,在可能的情况下,评估他们到底做成了什么。对自然法话语的使用恰恰在维护传统家庭方面,阻隔了政治意志对民法的影响,并让19世纪的民法告别了催生《民法典》的革命。
1804年生效的《法国民法典》及作为其先行者的几份草案,无论在具体的规定上留下了多少旧法的痕迹,毕竟是革命法制的产物。它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16世纪开始确立下来的传统家庭组织模式——“对家产之要求的正当性只能来源于婚姻,因为它是唯一一种符合社会体神圣义务的结合形式”①David Deroussin,Histoire du droit privé:XVIe-XXIe siècle,Paris,Ellipses Marketing,2010,p. 5.。家庭法由是需要妥善处理两种不同的关系。第一种乃是家庭与外界的关系,第二种则是家庭内部的关系。②拿破仑虽然没有受过系统的法学教育,但他对民法许多问题的洞见仍令人惊异。比如,他曾评论“民法中关于人的规定只有三种大类:确定每个人在公民社会的地位者;规范夫妻关系者;规范父亲和孩子的关系者”。Pierre-Antoine Fenet,《Précis historique sur la confection du Code Civil》,inRecueil complet des travaux préparatoires du Code civil,Paris,Videcoq,1836,vol.I,p. lxx.第一种关系的核心乃是正当性,实际上便是在何种条件下人能基于身份关系对他人主张财产的给付,而在历史上的主要情形便是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对父母(主要是父亲)的抚养请求权。而第二种关系,则表现为家父对家产的处分权和对子女所为法律行为同意、追认、撤销等权利的行使。相应地,不管在罗马法还是在教会法上,又借由家庭内外两种关系,把传统的家庭组织模式稍加具体化为围绕着不可撤销的婚姻建立起来的家父制。纵观整个法典起草的过程,革命对平等的追求并没有把家子和已婚妇女从家父的权威下解脱出来,但围绕着个人自由形成的话语确实让离婚取代了别居制度,使婚姻有了彻底解除的可能。③或许让解放哲学的拥护者和法国大革命的痴迷者失望的是,离婚作为一项现代欧洲的法律制度并不诞生在1789或1804年。实际上,是普鲁士的开明君主腓力士二世在1752年首次确立了离婚制度。Cf. Max Rheinstein,《Trends in Marriage and Divorce Law of Western Countries》,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1953,vol. 18,no1,pp. 3-19.
不知是否巧合,恰恰是在关于作为家父的夫与妻子之关系和离婚两项上,自然法话语出现得尤其频繁。不过法学家在两个论题上对它的使用却大相径庭。在他们的观念中,作为家父的夫之权威和离婚都可以在自然法上找到根据。如果说他们确实为自然法对家父权威的辩护感到满意的话,在离婚问题上,最终的决定权却并未完全留给自然法。
(一)“自然”的胜利:留在民法中的家父制
首先令人感到不解的是,为何家父与其他家庭成员的区隔可以见容于共和主义对平等的追求。其实根源恰恰在于革命时代的共和主义并非仅仅意味着平等主义,而是同时包含着对人、对空间、对社会的分割与区别。④大革命的画家雅克-路易·达维(Jacques-Louis David,1748—1825)的作品比任何哲学著作都更清楚地表现了19世纪末的人所理解的共和精神。《贺拉斯兄弟之誓》(Le Serment des Horaces,1784)和《扈从给布鲁图斯带回他儿子的尸身》(Les licteursrapportent à Brutus les corps de sesf ls,1789)这两幅珍品中都用廊柱区分开了两个空间:画面左侧的空间属于男人,属于直线,属于公共事务,属于理性、美德和爱国心;而画面右侧的空间则属于妇女,属于曲线,属于家庭,属于情感、软弱和对死亡的恐惧。而两幅画的中心人物不是旁人,正是家父。家父是男性美德的集中体现,也作为家长把家庭与政治社会联系在一起。如果说法国大革命的政治话语首先基于平等主义而致力于否认阶级之间的秩序,一套来自浪漫主义文学的语言、一套把自然权利和共和主义熔于一炉的语言则迅速把革命话语引向了对个人解放的宣扬。这种语言描述了一个自然状态,“在其中,每个个体都是社会性的、平等的,没有人能统治别人,而美德自然而然就能实现。唯一得到承认的就是自然不变的法则”⑤Dan Edelstein,The terror of natural right:republicanism,the cult of nature,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9,p. 11.。但一种父权制思想还是裹挟在同一套话语实践之中。洛克在他的《政府论》(下篇)中已经指出,政治社会的统治者对其臣民所享有的权威,恰恰如同自然社会中的家父对家子享有的权威。大革命的理论家——同时也是洛克的热忱读者——也用着类似的家国同构的语言证成着他们的政治主张。①细节可以参考Lynn Hunt,The Family Romanc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Berkeley,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1992.特别是其中的第二章。所以,如果说大革命的平等理念在表面上消除了旧制度下阶级身份的区别的话,它也强化着罗马法上本来就存在的、围绕着家父建立的不平等关系。
家父可以决定家庭事务,也必须负担对子女的照顾,以家父为核心的传统家庭模式因而可以得到自然法的背书。来自蒙彼利埃的法官便认为波塔利斯呈上的草案在强化了家父权利的同时,却让子女无法从父权处获得足够的基于自然法的照拂。②《Observations faites par les membres de la commission nommée le 21 germinal dernier par le tribunal d’appel séant à Montpellier》,inRecueil complet des travaux préparatoires du Code civil,Paris,Videcoq,1836,vol.IV,pp. 419-589.恰恰是在这个意义上,革命的逻辑给了民法话语告别革命、回到从前的可能性。
甚至,真实的情况可能更糟糕。父母对子女处分财产、缔结婚姻契约的干预当然已经区别了民法上视为有完全理性的人(家长)和理性有所欠缺的人(子女),但最后确定在1804年的《民法典》文本中的法定夫妻共同财产制下,对已婚妇女财产权利的系统性否认更能反映一套呼吁为平等奋斗的自然法话语如何最终催生了不平等的制度。毕竟,个人财产和契约自由乃是《民法典》两大基石。大革命的政治意识形态之阐发,本来就是借重自然法话语高唱个人自由,而私有财产和契约自由恰恰是个人自由之基础。在评论关于遗产法定份额(第三编第二节第三章第16条)的时候,蒙彼利埃的代表主张对遗产的限制就是对物上处分权的限制,而“物的处分权正是财产权题中之义。如果财产权以自然法为基础,那么对物的处分权之限制和克减就是对自然法的违背”③《Observations faites par les membres de la commission nommée le 21 germinal dernier par le tribunal d’appel séant à Montpellier》,inRecueil complet des travaux préparatoires du Code civil,Paris,Videcoq,1836,vol.IV,pp. 419-589.。紧接着,在几段之后,评论者语气有所缓和,说法典草案好歹给继承人之间的协议留下了余地,也算是“自然法对民事立法和公法的胜利”,只不过这种胜利来得不够彻底。④《Observations faites par les membres de la commission nommée le 21 germinal dernier par le tribunal d’appel séant à Montpellier》,inRecueil complet des travaux préparatoires du Code civil,Paris,Videcoq,1836,vol.IV,pp. 419-589.按照蒙彼利埃人的想法,压根就不该对这种事项作出规定。“民事立法,作为公平的同义词或者写就的自然法,绝对不能允许对自然法最为神圣的原则之威胁,那就是财产权,或者物的处分权——那可是所有政治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权利。”⑤《Observations faites par les membres de la commission nommée le 21 germinal dernier par le tribunal d’appel séant à Montpellier》,inRecueil complet des travaux préparatoires du Code civil,Paris,Videcoq,1836,vol.IV,pp. 419-589..换言之,恰恰是在通过婚姻财产制对财产权进行的规制上,19世纪的民法正面地表达了自己:一套关于男女之间自然差异的话语出现在辩论中,让妻成了无法享有完整财产权的主体,也就是不具备完整理性的主体。
对比康巴塞雷斯的三份草案、雅克米诺的草案和《1801年草案》,不难发现对已婚妇女在财产权上的限制越来越多。虽然一开始就把共同财产制定为民法典中婚姻财产制基调的康巴塞雷斯断言“已婚妇女非经丈夫授权既不能处分财产也不能负担义务,这项规则让正当地赋予丈夫的管理权得以成立”⑥Jean-Jacques-Régis de Cambacérès,《Discours préliminaire prononcé par Cambacérès au Conseil des Cinq-Cents,lors de la présentation du troisième projet de Code civil,faite au nom de la commission de la classification des lois》,in Recueil complet des travaux préparatoires du Code civil,Paris,Videcoq,1836,vol.I,pp. 140-177.,但他在本身较为简略的前两个草案中,以平等的名义规定了夫妻双方对财产的共同管理权。出售共同财产需要双方的同意,而单纯的财产保全行为则可以由一方单独完成。“热月党人”夺权之后,平等原则所支持的夫妻对财产的共同管理就无以为继了。康氏的第三份草案规定,丈夫独享处分共同财产的权利①第293条。,而妻连处分自己特有财产都必须经过夫的特别同意②第295条。。《雅克米诺草案》确定了法定共同财产制,这一份在雾月十八政变之后提出的文本(具体的日期是1799年12月21日)延续了康氏第三草案的精神。妇女无论是在共同财产制下还是在分别财产制下,都必须经丈夫书面同意才能进行、拒绝或接受赠与和继承。③第58条,第111条。1801年的草案并没有改变《雅克米诺草案》关于婚姻财产制的安排,只是又把它们细节化了。这些规则最后大部分进入了1804年生效的文本。夫有保护妻的义务,但是妻必须服从夫④《民法典》第213条。本文所引之《民法典》条文,除非特别说明,皆为1804年生效的文本。且文字的使用均参考李浩培、吴传颐、孙鸣岗诸先生所译之《拿破仑法典》,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妇女必须随夫迁徙⑤《民法典》第214条。;共同财产由夫一人管理⑥《民法典》第1421条。;妻若不是商人并且为商业目的的行为,除非经夫同意,否则纵得法院许可亦不影响共同财产⑦《民法典》第1427条。;妻的一切个人财产由夫管理之⑧《民法典》第1428条。;如是种种,不一而足。在20世纪50年代修法以前,它们中的大部分历经百余年未曾变更,虽然其适用在很大程度上因为司法的努力而变得不那么严苛⑨仅举一例:妻所订立之合同需要夫的特别授权,而此授权如为默示,需要夫在整个缔约过程中都实际上身处缔约现场,且知晓对此缔约情势,直到1871年,法院始认为夫在缔约过程中偶然地出现在现场可以视为默示授权(Civ. 26 juillet 1871,DP,1871,1,293)。人常谓大陆法国家以成文法为唯一法源,在法国判例绝无正式法律渊源之地位,实际上1804年的文本能在动荡的19世纪不经大规模修订而适用于变化万端的社会生活,全赖学说、判例协同努力发展出的对条文的解释。。
法国民法典毕竟是在说理和辩论中成型的。前述种种关于作为家长的夫之权利的规定,自然也要在辩论中自我证成。康巴塞雷斯在他的说明中如此解释:“就算平等必须成为社会组织中的所有行为的支配性原则,为了保存自然秩序,也为了防止家庭生活的美满在无尽的争论中消失殆尽,并不算背离了平等”。让共同财产的管理全然“落入妇女手中”则更糟糕,因为那是“违反自然法则的”。⑩Jean-Jacques-Régis de Cambacérès,《Discours préliminaire prononcé par Cambacérès au Conseil des Cinq-Cents,lors de la présentation du troisième projet de Code civil,faite au nom de la commission de la classification des lois》,in Recueil complet des travaux préparatoires du Code civil,Paris,Videcoq,1836,vol.I,pp. 140-177.虽然我们现在的研究还未必能确定地指出为何康氏会经历如此话语转变,但他显然在具有决定作用的第三草案中贯彻了这种男性沙文主义的思想。委员会在说明草案时也简洁而不容置疑地宣布:“丈夫是一家之主。”⑪Jean-Etienne-Marie Portalis,《Discours préliminaire prononcé par Portalis,le 24 thermidor an 8,lors de la présentation du projet arrêté par la commission du gouvernement》,in Recueil complet des travaux préparatoires du Code civil,Paris,Videcoq,1836,vol.I.至于女性,“我们忍受这个性别作为恩典而与生俱来的冒失和轻浮,却不去鼓励任何可能扰乱秩序、违反规矩的行为”⑫Jean-Etienne-Marie Portalis,《Discours préliminaire prononcé par Portalis,le 24 thermidor an 8,lors de la présentation du projet arrêté par la commission du gouvernement》,in Recueil complet des travaux préparatoires du Code civil,Paris,Videcoq,1836,vol.I.。民法起草者波塔利斯的儿子,弗雷德里克·波塔利斯(FrédéricPortalis),总结民法编纂的用处时重复了类似的观念,把女性与“轻浮”、“朝三暮四”和“恶德之诱惑”联系在一起。⑬Jean-Jacques-Régis de Cambacérès,《Discours préliminaire prononcé par Cambacérès au Conseil des Cinq-Cents,lors de la présentation du troisième projet de Code civil,faite au nom de la commission de la classification des lois》,in Recueil complet des travaux préparatoires du Code civil,Paris,Videcoq,1836,vol.I,pp. 140-177.男性自然而然地要比女性更理性、也更审慎,又因为让两个人同时管理财产会导致争吵和婚姻的不稳定,所以只能让婚姻中的一方——也就是夫——独立地管理。
把作为家长的夫权看作基于人类之本质或者自然属性的说法,在后续的辩论中也无处不在。解释立法者意图的记录强调,“根据事物的本质(la nature même des choses),夫是婚姻关系的支配者和主人”①《Présentation au corps législatif,et exposé des motifs,par M. Treilhard》,in Recueil complet des travaux préparatoires du Code civil,Paris,Videcoq,1836,vol.IX,pp. 556-563.,夫的权力不仅仅及于妻和其他家庭成员的人身,也出于自然的原因及于财货。“男人的优势实在是其存在之构成所彰显的,他并没有那么多的需要,因此可以更独立地运用他的时间和才能。法律草案所认可的男性保护权恰恰源于这种优势。”②Jean-Etienne-Marie Portalis,《Exposé des motifs,par le conseiller d’état Portalis》,in Recueil complet des travaux préparatoires du Code civil,Paris,Videcoq,1836,vol.IX,pp.138-181.对于这位民法典之父而言,男性更加自由,因为他们更加强大。所以在两种性别之间,存在着一种自然的不平等,法律的不平等由此得以正当化。③Jean-Etienne-Marie Portalis,《Exposé des motifs,par le conseiller d’état Portalis》,in Recueil complet des travaux préparatoires du Code civil,Paris,Videcoq,1836,vol.IX,pp.138-181.如果男性就其本质而言优于女性,让他们管理财产、成为家长就顺理成章了。毕竟区别对待不同的事物也是正义的要求。即便有些地方的代表——如蒙彼利埃的代表——主张让双方就自己财产享有权利,他们却并没有反对男性在本质上是一种完全理性存在的理论。
于是我们发现,作为成年男子的相对方,已婚女性的处境相对地降低了。且不说革命带来的政治权利往往是男性的专属物,从民法上看,她们也不再享有封建时代认为是自然权利的对自己财产的占有、处分、收益的权利。正是财产权,在19世纪的曙光降临时的民法学界独享绝对性的自然权利之名。造成女性地位整体的相对降低的文化原因,恰恰不是传统主义或者天主教回潮,而是启蒙本身。西哀士和孔多塞在革命前极力想争取的那种深入而积极地涉足社会和政治变革的女性,在医学词汇中成了研究的客体,成了刚健而理智的男性的参照系。④Cf. Yvonne Knibiehler,《Les médecins et la“nature féminine”au temps du Code civil》,Annales. Histoire,Sciences Sociales,1976,vol. 31,no4,pp. 824-845.如果说革命本身曾经带来妇女解放的希望的话,曾经为革命辩护的启蒙话语在政权甫定时则迅速与家父制的传统民法观念结合,迅速形成了不平等的民法制度。
在民法的词汇里,平等的首要意义乃是用来证成民法典的必要性,却掩盖了自然人之间由身份肇致的不平等。在19世纪的话语中,旧制度的臣民依据他们的信仰、种族、地域、身份而成为不同的权利、特权和义务的主体。商业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通婚让不同的群体发展出了共同的利益,从而形成了在思想、荣耀、命运、名称和语言方面都别无二致的人民。⑤Frédéric Portalis,《Essai sur l’utilité de la codification》,op. cit.于是,革命应运而生,它结束了等级制社会、摧毁了贵族特权、沉重地打击了教会、瓦解了领主在农村的奴役网和各种特许经营在城市的垄断经济。⑥参见[法]乔治·杜比主编:《法国史:从起源到当代(中卷)》,吕一民等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848页。法国大革命既是社会革命的产物,本身又带来了更多的社会革命。随着共同利益出现的整体人民要求一个完整的和适用于所有人的法律体系,在其中,“公民在体制内的信心取决于像上帝的正义那样适用于每个人的平等的正义,取决于权利的平等分配,还取决于所有人对共同义务及负担的承受——它们由等级和有管理权的政府形式所决定”。⑦Frédéric Portalis,《Essai sur l’utilité de la codification》,in Frédéric Portalis(dir.),Discours,rapports et travaux inédits sur le Code civil,Paris,Joubert,1844,p. v.弗雷德里克·波塔利斯或有心或无意地道出,《民法典》确实要求人们平等地服从一个法律,但该法律之内容却确定着不平等的社会现实。贯穿整个19世纪的激进主义号称要革思想的命⑧Cf. Émile Poulat,《Socialisme et anticléricalisme. Une enquête socialiste internationale(1902-1903)》,Archives des sciences sociales des religions,1960,vol. 10,no1,pp. 109-131.,却吊诡地在男性沙文主义上与传统主义及为其背书的天主教思想别无二致,两者一拍即合,让催生革命的平等口号实际上变成了成年男性之间的平等。
(二)“自然”的不幸:饱受争议的离婚制度
革命时代的自然法不但为婚姻中的等级制辩护,也同样为离婚辩护。但自然法话语在关于离婚的辩论中却不那么幸运。虽然人们仍然对自然法的内容争议较少,对民法是否有必要对自然法亦步亦趋,则在涉及离婚的争论中明显地发出了两种不同的声音。对于支持离婚的一方,只需要坚持离婚根源于自然法,而民法要以自然法为圭臬就够了。对于反对的一方,他们也可以主张民法之编纂所需要考虑者毕竟不仅仅是自然法,因而对是否引入离婚尚应慎重。争论最终在立法和学理两方面留下了印记。立法上,《民法典》仍然保留了离婚制度,不过程序比起草之初所设想的要复杂了许多。学说上,反对离婚的一方所提出之“民法不必与自然法一致”的观点,确实顺应了现代自然法的构建,一遍又一遍地回响在19世纪民法中,深深嵌刻于一个从规范多元的时代向立法至上时代的变革过程。
康巴塞雷斯在第一份草案的说明中明确指出离婚的自然法渊源:婚姻契约来自自然法,而契约双方的意志就是最为绝对的规则,如果婚姻双方在婚姻生效后改变了意志,那么婚姻就该终结,所以他的草案才设立了相对便宜的离婚程序。①Jean-Jacques-Régis de Cambacérès.《Rapport fait à la Convention nationale,au nom du comité de législation,sur le premier projet de code civil》,in Recueil complet des travaux préparatoires du Code civil,Paris,Videcoq,1836,vol.I,pp. 1-16.他的理解承袭了启蒙思想从婚姻性质和个人自由两个角度支持婚姻的做法。在格老秀斯等人的现代自然法传统下,婚姻只是契约,那么应该和其他契约一样可以撤销②基督化了的罗马法是通过“不可撤销契约”的理论让婚姻契约不同于其他契约的。,对离婚的禁止仅仅是基督教国家的实证法而已,并无自然法的背景——虽然他也没有主张因此撤销离婚禁止。③David Deroussin,Histoire du droit privé:XVIe-XXIe siècle,Paris,Ellipses Marketing,2010,p. 217.孟德斯鸠、伏尔泰和狄德罗则从个人自由的角度谴责婚姻不可撤销性。④David Deroussin,Histoire du droit privé:XVIe-XXIe siècle,Paris,Ellipses Marketing,2010.类似的哲学让“热月党人”当政以前一系列简化离婚手续的立法看上去合情合理。1794年4月23日的法律甚至允许夫妻一方在可以证明对方不在超过6个月的情况下诉请离婚。康氏一草保留了一系列革命法制的成果,其中最重要的便是两愿离婚和以不能容忍的共同生活为由的离婚。⑤《Premier projet de Cambacérès》,in Recueil complet des travaux préparatoires du Code civil,Paris,Videcoq,1836,vol.I,pp. 17-98.
“热月党人”上台后,几乎所有尚未开始审理的离婚申请都悬置了。⑥David Deroussin,Histoire du droit privé:XVIe-XXIe siècle,Paris,Ellipses Marketing,2010,p. 219.尽管波塔利斯强烈反对两愿离婚⑦David Deroussin,Histoire du droit privé:XVIe-XXIe siècle,Paris,Ellipses Marketing,2010.,康巴塞雷斯的第三草案仍然保留了这一制度和共同生活之不可能的离婚事由⑧第325-328条。。雅克米诺草案则出于对不断攀升的离婚率(自然不能与我们今天同日而语),有意让婚姻的诉讼程序变得更加复杂,以免“持续的离婚让婚姻变成一种经过宣誓的同居”⑨Jean-Ignace Jacqueminot,《Idées préminimaires sur le projet de Jacqueminot,présenté par Jacqueminot,au nom de la section de législation》,in Recueil complet des travaux préparatoires du Code civil,Paris,Videcoq,1836,vol.I,p. 331.。1804年的《民法典》最终保留了离婚⑩第229-233条。,只不过离婚程序前所未有地复杂和漫长⑪第234条以下。,并且重新引入了在前革命时代曾经作为离婚替代品的别居制度⑫第306条-311条。。
蒙彼利埃的上诉法院代表在涉及财产权和婚姻财产制的时候还在用自然法作为自己主张的理由,可在讨论到离婚的时候,自然法就要为习惯和风俗让步了:“实证法不能总是自然法则一字一句分毫不差的副本,毕竟社会秩序中有无限的情事在更迭、变化和异动”。提出上述观点后,蒙彼利埃的代表强烈反对在《民法典》中保留离婚制度:
“因此,当禁止离婚的天主教在法国占主导地位时,它要胜过可能许可离婚的自然法;可当这个宗教不再支配法国社会时,也不能说自然法就可以全然压倒民事立法不再予以考虑的宗教信条。毕竟这一信条已经深深地植根于法国人的良心与灵魂,而且它还支配着他们的理性,就算建立它的宗教已经不再是法国的支配性力量。”①《Observations faites par les membres de la commission nommée le 21 germinal dernier par le tribunal d’appel séant à Montpellier》,op. cit.,p. 481.
主张在《民法典》中保留父权制的法学家以自然法为依托,并最终以婚姻财产制的方式建立了婚姻中的等级秩序,从而背离了革命的“平等”主张。呼吁悬置自然法而限制甚至取消离婚制度的声音倒也异曲同工,折射出了反对个人自由的倾向。传统见解认为19世纪早期占据支配地位的是革命的个人主义传统,“社会的发明”是19世纪下半叶才出现的事情。②Jacques Donzelot,L’Invention du social:Essai sur le déclin des passions politiques,Paris,Seuil,1994.我国较早介绍法国法律学说的吴经熊和王伯琦也持此观点,参见朱明哲:《论王伯琦对法国学说的拣选与阐述》,载《清华法学》2015年第1期。以上见解在法国民法社会化的意义上固然是成立的,但在以外于个人的整体来限制个人自由的意义上,却忽视了至少可以追溯到民法典时刻的“执拗的低音”:民法编纂过程中,需要衡平捍卫个人绝对自由的自然法和保护善良风俗的宗教因素。“在婚姻契约中,公民社会始终是其一方当事人,构成了婚姻并且牵连如此之广的契约,竟然会因为缔约方的任性而失效……婚姻倒像是为了离婚而存在的了。”③Frédéric Portalis,《Essai sur l’utilité de la codification》,in Frédéric Portalis(dir.),Discours,rapports et travaux inédits sur le Code civil,Paris,Joubert,1844,p. v.虽然此时使用的“社会”话语之内涵实则是对与天主教相关的风俗、传统的维护,故与此后强调保护经济上不利之群体的民法社会化大相径庭,而两者在反对革命所高唱之个人自由方面,却是殊途同归。
如此说来,波塔利斯在草案说明会上对离婚的理解,恰恰表明了《民法典》中设立离婚制度的意图:
“仅仅是出于语言的需要,我们接受了‘允许’或‘许可’离婚这样的说法。可是准确地说,民法并不允许或者许可离婚,它其实是在避免对离婚的滥用。要是没有法律,人皆为所欲为,如此无边际的自由会伤害公共秩序,正是为了避免无序,法律才介入。”④Jean-Étienne-Marie Portalis,《Causes du divorce;doit-il être maintenu? Séance du 14 vendémiaire an X》,in Frédéric Portalis(dir.),Discours,rapports et travaux inédits sur le Code civil,Paris,Joubert,1844,pp. 343-355.
离婚的自由,当然仍是一种内涵于自然法的自由。但在民法中设立此种制度却不是为了符合自然法的需要,而恰恰是为了避免对自由的滥用危害社会。于是,不仅通过对“自然”的使用,也通过对“自然”的限缩,民法话语逐渐构建出了一个独立的空间,在这一空间中,平等和自由的革命精神都成了民法所评价、限制乃至支配的对象。
四、结论
通过研究《法国民法典》编纂过程中的辩论记录,既可以增益今人对学说史的了解,亦可以推进对法实践整体之理解,兹分述之。
于学说史方面,最关键的贡献乃在于揭示,自然法从启蒙时代至尊至高的位置到19世纪大部分时期于实践上的沉默以及相伴而生的对成文法的推崇,绝非一朝一夕革命性变革所起的改天换日之功。中间十数年法哲学与法典化、现代国家建设、共和制确立等重大政治风波缠绕的历史构成了一个从时间看较短但思想和制度中的冲突与发展密度较高的过渡期。恰恰是在过渡期中,民法成了一个独立而自足的领域,其副作用便是成文法也从此成了现代诸法律渊源之中心。
民法学家曾经希望在法典中处理民法与公法、民法与自然法和万民法之间的关系,并且真的把现在看来完全属于学术探讨的言辞写进了最初的几份草案,而且其各份草案的实质主张不约而同地传递了强调民法独立于自然法、万民法和公法之性质的意思。他们在关于法典内具体条文的讨论中使用自然法话语,虽然并不是每一次自然法话语的使用都意味着让民法规定符合或者追溯到自然法上。但随着继受自旧制度时代的自然法话语之适用,大革命前学说上盛行的“演绎模式”——实证法之规则和有效性来源于自然法,逐步让位于“检验模式”——实证法之规则和有效性只要不明显反于自然法即可。关于家庭的讨论证明,民法学家普遍支持建立在家父制上的家庭模式,并且在离婚自由方面要么态度暧昧、要么强烈反对。在夫妻之间不平等的财产关系既符合时人关于“自然”的理解、也暗合共和主义家国同构之观念时,他们便高举自然法的大旗;而当他们感到无法理性地反驳自然法所确保的绝对的离婚自由时,他们便声称民法并非自然法之副本、需要考虑习惯和风俗云云。我们由此似乎不难补充此前提出的自然法学说类型学。

表2 不同时期自然法学说的类型学(补充后)
我国法学界又一次迎来了民法典起草的争论。那么,法史的探讨可以给今天的制度建设和学术发展带来什么信息?首先,《法国民法典》的起草经验显示,法典文本绝非一与价值无涉的技术性文本,民法也非一独立而自给自足的领域。历史地看,无论是法典编纂还是民法学的发展,都无法摆脱深深嵌入风云诡谲的政治生活的命运。民法制度演进的表面下,意识形态更迭暗流涌动。《法国民法典》的生成和解释的历史,便展现为从家父主义到自由资本主义再迈向社会化的过程,即便其文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并未经历大的变动。而且民法与公法始终处于互动中。谁又能说家庭不是私人生活最核心的领域、关于家庭的种种法律制度不是私法上最重要的领域?但凡国族建设、政权更迭、改弦更张,莫不自家庭法而始。康巴塞雷斯一草中对绝对离婚自由的强调、杨度所谓“毁家立国”的主张①参见杨度:《论国家主义与家族主义之区别》,载刘晴波主编:《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29-533页(原载《帝国日报》1910年12月5日)。并参见陈新宇:《宪政视野下的大清新刑律——杨度〈论国家主义与家族主义之区别〉解读》,载《政法论丛》2014年第6期。乃至民国家庭法上以个人主义和平等主义为皈依②参见史尚宽:《亲属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8页;并参见胡长清:《中国民法亲属论》,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7页。,概莫能外。只是如是政治努力究竟何种程度上能改变家庭,又随各个不同的场域中各方角力的态势而有所不同,不可同日而语。就连在司法和学说依附政治的民国时期③彼时盛行之关于“司法党化”之讨论,即可视为司法权威对政治权威依赖性之表征。参见居正:《司法党化问题》,载《东方杂志》32卷第10号,1935年5月。,离婚判决和社会实践尚多乖于“男女平等”之口号④参见朱汉国:《从离婚诉讼案看民国时期婚姻观念的演进》,载《河北学刊》2013年第6期。,更不必说在法国,立法、司法和学说在家庭领域上所存在的紧张关系。①冲突主要存在于保守的学说和倾向自由化的司法之间。学说在婚姻方面的保守姿态,集中体现在Ernest-Désiré Glasson,Le Mariage civil et le divorce dans les principaux pays de l’Europe,précédé d’un aperçu sur les origines du droit civil moderne,étude de législation comparée,G. Pedone-Lauriel,1879.至于晚近我国学界重提“家”之价值②参见张龑:《何为我们看重的生活意义——家作为法学的一个基本范畴》,载《清华法学》2016年第1期;并参见张龑:《论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家与个体自由原则》,载《中外法学》2013年第4期。,不知又会于我国法政实践上有何回响。
但绝不能说法是政治的附庸,更不能说学术是由政治的角力决定的。一切彻底的政治决定论和半吊子的法社会学研究都忽视了法律实践因为其语言的有限性和专业性而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场域。③Pierre Bourdieu,《La force du droit. Éléments pour une sociologie du champ juridique》,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1986,vol. 64,no 1,pp. 3-19.在法律场中,拥有不同的资本的法律人为了掌握决定法律之限度和法文本最终意义的垄断性权力而竞争,但他们作为一个群体也和从事其他职业的人在更广阔的社会场中竞争着制定社会规则的权力。《法国民法典》各草案的演变和辩论正好展示了一段民法和民法学如何自我隔离于政治的历史。通过对自然法话语的有效运用,民法逐渐从革命时代的热情中冷却,并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于政府权力、特别是立法权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纯粹的政治性考量并不具有先天的正当性。所以,即便否认法实践有政治性或否认法是社会整体的一部分的观点相当可疑,但否认法作为一种特殊的场而多少应和政治的其他部分保持距离也并不多么高明。
其次,法典的编纂者应当意识到法典的出现并不足以扼杀学说的创造力。在波塔利斯为之辩护的草案中,同时认可实在法、自然法、万民法和习惯的法律多元论立场本来为尚在形成期的民法典提供了日后自我发展、自我变迁的论述可能性,但最后生效的《民法典》仍然采取了立法作为唯一正式法源的理论。1804年的文本把中央立法机关的立法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且开启了在民法上延续到19世纪末、在公法领域更是到一战之后才遭到普遍反思的立法至上主义。只不过这种以巴黎法学院排他性的优势地位保障的官方理论④关于巴黎法学院的地位,参见Marc Milet,《La Faculté de droit de Paris sous la Troisième République:une domination sans partage? (1879-1939)》,in Jean-Louis Halpérin(dir.),Paris,capitale juridique(1804-1950):Étude de socio-histoire sur la Faculté de droit de Paris,Rue d’Ulm,2011;Frédéric Audren et Catherine Fillon,《Louis Josserand ou la construction d’une autorité doctrinale》,Revue Trimestrielle de droit civil,2009,no 1,pp. 39-76.,在法律实践中的命运就像布吕赫尔画中坠落的伊卡尔一样,遭遇无处不在的冷落。相反,学说借由法典与社会情势的相互作用重掌在法实践中的权威地位。如果说历史上曾经有哪些时刻学说湮没不闻的话,长时段的考察则向我们揭示,从共和时代的罗马法一直到今天,学说在确定法律的渊源、固定法律解释的方法和确定某个具体的条文和概念如何解释方面的权威是无人分享的。在学说以解释法律为名创造新的规范的时候,自然法恰恰成了为这种做法背书的语言工具。
最后需要提醒的是,本文所专注的仅仅是在西欧一隅发生的法哲学话语演进,各个国家的理论史发展并不具备共时性,而人们有时也会重拾曾经弃若敝履的观念、思维和话语。前文提到,在民法典编纂辩论中,“检验模式”逐渐取代了“演绎模式”成了表述实证法和自然法之关系的话语。但造化弄人,《草案》中“检验模式”倒是帮助《法国民法典》中那些有别于传统法制的成分最终避免了在违背自然法的指责下弃如敝履的命运,可当法典的文本作为从王权压迫中解放的标志,随着拿破仑的军队攻城略地时,一直到后来法国作为最重要的殖民力量之一把《民法典》作为“进步”和“现代”的统治扩张到世界其他的区域时,遵循的却是巴黎上诉法院代表所支持的“演绎模式”的逻辑——所有人的理性都是一样的,一样的理性应当带来一样的法律①Cf. René Demogue et Paul Lerebours-Pigeonnière,《Les progrès du régime pénitentiaire:de l’influence exercée par la comparaison des lois étrangères sur les modifications apportées au régime pénitentiaire sous ses formes diverses,métropolitaines et coloniales》,in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 droit comparé tenu à Paris du 31 juillet au 4 août 1900:procès-verbaux,Paris,Librairie générale de droit et de jurisprudence,1905,p. 167;Semaines sociales de France,Le problème social aux colonies:sommaire des leçons de la XXIIe session des Semaines sociales de France tenue à Marseille du 28 juillet au 3 août 1930,Chronique sociale de France(Lyon),1930.,恍惚间亦是昨日光景。
(责任编辑:许小亮)
Natural Law of “Civil Code Moment”: The Usage and Evolution of Natural Law Discourse in French Civil Code Codif cation
Zhu Ming-zhe
The codification course of French Civil Code is not only of significance in the sense of Civil Law,but also implies development in legal philosophy. Important consequences were achieved in conceptual understandings of law and substances of rules by the discourses of natural law,in different drafts,in verbal processes,as well as in the posterior doctrinal arguments. Unlike scholars in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 who had tried to deduce substantive norms from the eternal and ideal law of nature,civilists argued to defend the independence of civil law by natural law during the Codification period. The Civil Code can therefore be regarded as a realm free from political agenda. Nonetheless,the discourses of natural law themselves are inevitably political in the sense that their usages tend to justify the traditional understanding of family.
Natural Law;Civil Code;French Revolution;Regime of Community;Divorce
D913
A
2095-7076(2016)02-0010-19
*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研究院讲师,巴黎政治学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