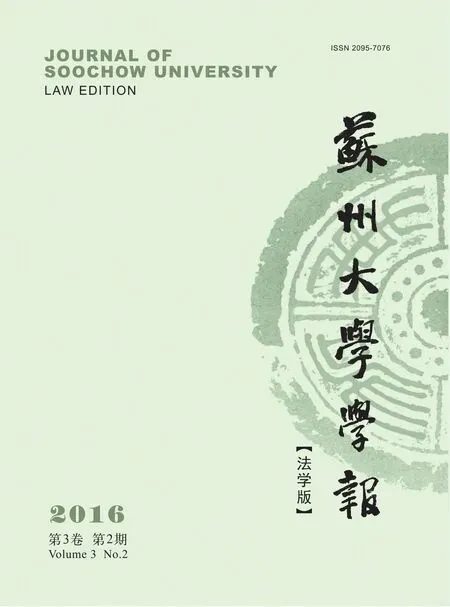寻衅滋事罪规制散布“虚假信息”行为的可行性分析
江奥立
寻衅滋事罪规制散布“虚假信息”行为的可行性分析
江奥立*
针对在网络上散布“虚假信息”、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2013年9月6日两高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依照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2015 年11月1日生效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九)》专门增设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的设立并不意味着寻衅滋事罪完全丧失规制散布“虚假信息”行为的功能。寻衅滋事罪构成要件相当程度的明确性,罪刑法定原则在网络时代的自身“救赎”以及对言论自由的相对性能够消除本罪适用中的观念障碍。承认网络空间是公共场所,并对寻衅滋事罪第4类行为中前后“公共场所”做不同的理解,可以消除其中的技术障碍。
虚假信息;寻衅滋事罪;观念障碍;技术障碍;消解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因网络谣言而引发的恶性事件让人心有余悸,这些事件的发生皆是由于部分网民任意发布、传播真伪难辨的信息,甚至是刻意编造、传播虚假的信息所致。为了遏制这类行为的发生,2013年9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为《解释》)中规定,编造虚假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虚假信息,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或者组织、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应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2015年11月1日生效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九)》,专门就网络谣言行为独立设置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从《解释》到《刑法修正案(九)》,体现了立法者对时下事态的积极反应,同时也反映出其在应对方式上的思考和精进。然而,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的增设并不意味着寻衅滋事罪丧失了规制散布“虚假信息”行为的功能。《刑法修正案(九)》设置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的意义在于,明确该罪的构成要件,即将涉及民众切身利益的重大虚假信息予以罗列,并强调了特定的传播方式。但是,“虚假信息”的内容并不限于险情、疫情、灾情、警情,编造、故意传播其他虚假信息以致严重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亦应为寻衅滋事罪所规制,此其一。其二,“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专为规制“网络谣言”而设,但事实上,并非只有通过“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传播虚假信息才会扰乱社会秩序。对于采用其他方式传播虚假信息,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同样是寻衅滋事罪所规制的对象。其中值得我们重点思考的是,对于在信息网络上发布虚假信息,起哄闹事的行为,适用寻衅滋事罪是否存在着说理上的障碍,对此,学界存在不同的意见。
否定论者认为,对在信息网络上发布虚假信息的行为适用寻衅滋事罪,难以做出合理的解释。理由如下:首先,寻衅滋事罪属于妨碍公共管理秩序的犯罪,根据2013年7月15日公布的《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寻衅滋事发生的地点限于车站、码头、机场、医院、商场、公园、影剧院、展览会、运动场等有形的场所,信息网络只是一种交流平台,不属于公共场所。同时,将网络上散布谣言的行为归结为第293条第4款规定的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有类推适用之嫌。①曲新久:《一个较为科学合理的刑法解释》,载《法制日报》2013年9月12日第7版。其次,“谣言”作为一种言论,不能因其内容“不符合事实”就轻易入罪。宪法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并没有把内容“符合事实”作为受保护的先决条件。传播内容不符事实的消息,也是一种言论,原则上也受宪法和法律保护。②林达:《为什么“散布谣言”不能轻易入罪》,参见http://view.news.qq.com/a/20110314/000048.htm。访问时间: 2013年9月15日。
肯定论者则认为,对在信息网络上发布虚假信息的行为适用寻衅滋事罪,并不存在解释上的障碍。理由在于:第一,现代社会已经进入信息社会,“公共场所”概念作符合信息社会变化的解释是可以接受的。对此,刑法在以往的解释中也存在先例,即将淫秽图片、视频也解释成“淫秽物品”。第二,在信息网络系统空间编造和传播虚假信息,虽然不会造成信息网络系统空间“公共场所”秩序的混乱,但网络信息的传播会直接影响到现实世界。因此,不存在欠缺“公共秩序”混乱要素的问题。③曲新久:《一个较为科学合理的刑法解释》,载《法制日报》2013年9月12日第7版。第三,网络谣言具有极大的迷惑性,不仅可能引发社会恐慌、扰乱社会秩序,还可能对特定群体或者特定行业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即使辟谣之后仍然余害难消。社会危害性的提高使得刑法介入评价成为必要。④于志刚:《制裁谣言的罪名体系需扩大》,参见http://edu.ifeng.com/gaoxiao/detail_2012_02/07/12353793_0.shtml。访问时间:2013 年9月15日。
通过对否定论和肯定论的归纳和总结,可以看出双方在如何把握信息网络化时代罪刑法定原则、如何认识言论自由等问题上存在观念上的冲突,以及在如何解释“虚假信息”、“公共场所”等问题上存在技术上的差异。在本文看来,我们只有回归到以上的冲突和差异,理性分析其中的争议焦点,才能真正解决寻衅滋事罪能否规制发布网络虚假信息行为的功能性问题。下文便就寻衅滋事罪规制网络虚假信息传播行为之观念障碍、技术障碍及其消解问题加以具体论述。
二、寻衅滋事罪规制散布“虚假信息”行为的观念障碍及消解
(一)对寻衅滋事罪的信任危机
1997年《刑法》将流氓罪分解成数个罪名以此来摆脱学界的诟病,但即使如此,作为解构后数个罪名之一的寻衅滋事罪仍引来不少非议。“由于《刑法》第293 条规定了寻衅滋事罪的四种行为类型,内容比较宽泛且使用了‘随意’、‘任意’、‘情节恶劣’、‘情节严重’、‘严重混乱’等需要价值判断的表述,司法机关对本罪的认定产生了许多困难,刑法理论也认为寻衅滋事罪成了一个新的‘口袋罪’”⑤张明楷:《寻衅滋事罪探究》(上篇),载《政治与法律》2008年第1期。。换句话说,刑法对寻衅滋事罪的描述看似条款明晰,事实上可涵摄的范围却无法确定,这种似是而非的规定显然有悖罪刑法定原则对条款明确性的要求。正因为如此,有学者甚至提出,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不具有独特性,司法适用也缺乏可操作性,应该废止该罪名。①参见王良顺:《寻衅滋事罪废止论》,载《法商研究》2005年第4期。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寻衅滋事罪产生了信任危机,认为只要以本罪加以规制的情况都有突破罪刑法定原则的嫌疑。
事实上,这种偏见并不理性,结合寻衅滋事罪所保护的法益,该罪名的构成要件有其独特之处。寻衅滋事罪的保护法益是社会公共秩序,按博登海默的看法,所谓公共秩序,是指社会进程中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一致性、连续性和确定性;另一方面,无序概念则表明存在着断裂(或非连续性)和无规则性的现象。②参见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9页。这样看来,“公共秩序作为具有普遍性的概念,它展示的是公共生活的有序状态和动态平衡的结构。”③陈绍芳:《公共哲学视角的公共秩序价值解析》,载《社会科学家》2009年第1期。喻言之,社会公共秩序成流体状,何谓破坏,何谓不破坏,抽象判断难有定论。寻衅滋事罪规定的四个行为类型,分别从社会交往中人的身体健康、财产安全、活动自由以及社会评价着手,以此作为判断破坏公共秩序的现实载体。如辱骂、恐吓他人的行为,基于《刑法》第293第1款“破坏社会秩序”的规定,仅限于多数人在场的情况。实际上,是与非(有没有破坏公共秩序)的判断并不困难,真正让人无所适从的是危害性程度的辨别,寻衅滋事罪中多处提到“情节恶劣”、“情节严重”、“严重混乱”等表示危害性程度的用语,对这些高度抽象的规范用词的判断势必因人而异。2013年7月15日公布的《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此专门作出详细规定,通过对行为次数、行为方式等的设置,将抽象的综合判断转化成了具体要素的判断。在刑法理论与司法解释的共同努力下,寻衅滋事罪的构成要件已然具备了相当程度的明确性。
(二)信息网络化时代罪刑法定原则的定位
当下刑法解释理论的研究似乎遇到了困境,无形中常有两股呈反向趋势的作用力在不断拉扯着解释者的神经:一方面,罪刑法定原则提出了紧扣文义、严格解释的要求,时刻提醒解释者不要走得太远;另一方面,社会转型期的“青春狂躁症”④陈兴良教授曾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死刑与宪法”系列讲座中提到,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相当于一个人成长过程中的青春期,从小孩到大人转换的年龄,那些对小孩的规范已经约束不了他,但是又没有掌握和适应大人的那些规范,同时又容易叛逆,容易违规。转型期出现的各种状况,犹如青春期孩子常有的“青春狂躁症”。如期而至,引发出各种各样不曾有过的刑法难题。在面对这些问题时,如何权衡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和社会转型时期的现实挑战,是当代刑法解释理论必须考察的重要命题。
当代社会学的研究表明,工业社会经由其本身系统制造的危险而身不由己地突变为风险社会。⑤参见[德]乌尔里西·贝克:《世界风险社会》,吴英姿、孙淑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2页。事实上,除了技术性风险以外,政治社会风险与经济风险等制度化风险也是风险社会中的风险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风险社会中的风险,并不仅仅限于环境与健康,而且包括当代社会生活中一系列相互交织的变革:职业模式的转化、工作危险度的提高、传统与习俗对自我认同影响的不断减弱、传统家庭模式的衰弱和个人关系的民主化。⑥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第四版),赵旭东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2页。其中,网络的发展便是典型一例:发达的网络技术一方面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便利,另一方面也孕育出刑法所不曾关注过的领域,“网络空间”、“虚拟财产”等概念都亟待在刑法规范上找到自己的位置。此种情况下,刑法若仍以安分守己的姿态扮演其在法律体系中的角色,便有自裹手足之嫌。换言之,对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解不能仅仅停留在用语可能含义的探讨上,这是因为,“语言是开放的,它的意义边界并不存在警示的标志;语言本身无法实现自我界定,确定性系由社会实践所赋予。”①劳东燕:《刑法基础的理论展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7页。当社会出现新的事态时,刑法不该以既定的形态从上而下俯瞰,而应该通过由下及上的带有目的性的检视来确定文义的外延,最后实现刑法的社会规制机能。总而言之,社会转型期需要刑法解释负有一定弹性,严格罪刑法定原则的立场不能满足此一要求。
(三)言论自由的相对保护
言论自由是宪法赋予公民的最基本的权利,但这是不是就意味着任何言论都必然受到法律的保护?对此,在立法上,有以美国为代表的绝对保护模式和以德国为代表的相对保护模式之争。其中,美国的绝对保护模式认为,“在言论自由的保护方面,宪法第一修正案禁止普通立法对言论自由进行限制。联邦最高法院可以宣布国会及各州制定的法律,因限制个人宪法上的基本权利的行使而成为违宪的法律,并有权终止执行侵犯个人宪法基本权利之法律的效力,宣告其不具有法律的效力。法院直接适用宪法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从基础上就杜绝了对于言论自由的立法限制。”②邢璐:《德国网络言论自由保护与立法规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载《德国研究》2006年第3期。在著名的“《纽约时报》诉沙利文”一案中,布伦南大法官执笔写道,“尽管存在滥用自由现象,但从长远看,这些自由在一个民主国家,对于促成开明的公民意见和正当的公民行为,可谓至关重要。宪法第一修正案从来不拒绝对不恰当、甚至错误的言论进行保护。在自由争论中,错误意见不可避免,如果自由表达要找到赖以生存的呼吸空间,就必须保护错误意见的表达。”③斯伟江:《你,生逢其时》,参见http://news.ifeng.com/opinion/zhuanlan/siweijiang/detail_2011_08/19/8540468_0.shtml。访问时间:2013 年9月15日。这些观点时刻提醒解释者要对各类言论怀容忍之心。但即便如此,恶意言论也应该受到刑法的规制,具体理由如下:
首先,虽然宪法在赋予公民言论自由的时候没有明确指出恶意言论不受保护,但以宪法的整体精神来讲,任何自由都是有限度、有前提的,若言论表达的效果是损及他人的权利或危害公共秩序的稳定,这些内容势必不为言论自由所包括。从实定法规定了侮辱罪、诽谤罪等来看,对言论的刑法规制并非一概排除。
其次,谣言作为典型的恶意言论存在现实的危害。正如庞勒所指出的那样,“群体永远漫游在无意识的领地,会随时听命于一切暗示,表现出对理性的影响无动于衷的生物所特有的激情,它们失去了一切批判能力,除了极端轻信外再无别的可能。”④[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冯克利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9页。如果这是谣言的传播,人们就会深受其害。详言之,谣言具有以下三大危害:(1)谣言容易左右舆论导向,舆论则衍生道德审判,道德审判将动摇司法的独立性,化解法治壁垒;(2)正所谓“三人成虎”,谣言会使人们的是非观产生混乱;(3)客观事实的发现往往不易,谣言使得真相更加难以揭露。值得关注的是,网络技术就像一个放大镜,将这些危害性瞬间放大很多倍,对此,刑法有必要考虑介入。
再次,学界在讨论言论自由的时候,一般针对言论的价值和言论的界限展开。事实上,言论界限的研究是为了言论价值而服务的,换言之,有什么样的言论价值观就会有什么样的言论界限观。对于言论价值,博克(Robert Bork)归纳为以下四点:(1)促进个人才能之发展;(2)自由表达带来快乐;(3)增进社会的稳定以及(4)保障政治真实之发现与传播。尼莫(Melville B Nimmer)将之归纳为,(1)民主对话功能;(2)自由表达本身即是目的;(3)言论自由是一个社会的安全阀。其中,博克所指的(1)(2)可以概括为尼莫的(2)。⑤转引自侯健:《言论自由及其限度》,载《北大法律评论》2000年第2辑。各家观点虽有不同,但对言论的价值的认识不外乎以下三点:(1)增进知识与获致真理;(2)维持与健全民主政治;(3)维护与促进个人价值。宪法赋予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就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以上三种价值。然而,言论绝对保护的观点无形中违逆了宪法赋权的初衷,最终的目的也无法实现,显然不足以采之。
最后,正如弗兰克福特大法官所指出的那样,绝对的规则必然导致绝对的例外。言论的绝对保护者也并非真正容忍所有的言论。在“《纽约时报》诉沙利文”一案中,联邦最高院判决《纽约时报》胜诉的重要原因是沙利文无法证明对方的恶意,言外之意,只要能够确定行为人的言论是恶意的,该言论就应该得到规制。
三、寻衅滋事罪规制散布“虚假信息”行为的技术障碍及消解
凝固的刑法与流动的社会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疏远,解释的任务在于拉近刑法与社会的距离,使社会现实得到有效的调整。然而,刑法解释不是一劳永逸之事,社会结构的变化、利益格局的调整以及社会冲突的新型化都会促使司法者重新审视刑法。及时回应不断变动的社会所提出的现实需求,是刑法长盛不衰的秘诀。事实上,刑法每次的重生都伴随着不同程度的阵痛,即既有的法规则、法概念与新兴的事态之间的磨合。挖掘寻衅滋事罪在散布“虚假言论”中是否可行,以下几个问题必须要加以厘清与再解释。
(一)寻衅滋事罪视野中的“虚假信息”
《解释》第5条第2款规定:编造虚假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虚假信息,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或者组织、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依照刑法第293条第1款第4项的规定,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条文中并没有就“虚假信息”的内涵做进一步的阐释。然而,寻衅滋事罪保护法益的特点以及网络信息传播的特征客观上给“虚假信息”营造了具体的语境,《解释》中的“虚假信息”需要结合语境进行准确的理解。任何称之为犯罪行为的行为必须具备结果无价值,即犯罪行为本身至少要包含引起危害结果发生的抽象危险,欠缺法益侵害可能性的行为由于不具备违法性根据,刑法便不存在评价的必要。①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20-121页。信息的“虚假性”事实上仍无法充分说明信息的有害性,因此,在本文看来,对寻衅滋事罪视野中“虚假信息”的证成,除了要判断其是否存在虚假性以外,还需要判断该信息是否具备了扰乱社会秩序的潜在危险,具体来讲,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客观上无根据且内容与事实不符的信息具有“虚假性”
从文义上来讲,虚假信息是指与客观事实不符的一类信息。然而,有限的认识能力致使人们无法在任何场合都能精确地把握客观事实。基于个人体验所作的陈述或者基于客观事实作一般经验上的评价,都会因为个体差异而有所不同,这些陈述与评价和客观事实存在出入再正常不过。法谚曰:“法不强人是所难”,此时若将这类情形中的信息评价为本《解释》中的“虚假信息”,显然难以为人所接受。虽然说言论自由是一把双刃剑,在极大促进社会文明进步的同时,也无时无刻不在伤害这个社会,各国以刑治言的例子亦不是少数。然而,“作为民主社会最为核心和重要的宪法权利,言论自由必须得到真正尊重,不得任意剥夺。因此,许多国家在设置以语言作为行为方式的犯罪时,更多的是考虑对言论自由的保护,而不是限制。”②杨文革:《对言论自由的法律保护与对滥用言论自由的法律惩罚》,载《环球法律评论》2009年第1期。因此,对“虚假信息”进行解释时必须要考虑给言论自由留下足够的空间。除此以外,“客观事实”这个概念本身就值得斟酌。正如学者所提到的,“客观事物是客观存在的事物,而事实是人们通过对事物的某种实际情况所作出的判断而被陈述出来的,它是认识的主体——人所获得的一种认识,也就是人所把握的一种知识形式。”③彭漪涟:《事实论》,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既然如此,在客观事实无法被真实完整揭示的场合,民众根据现有的体验或信息作出一般的评价就难说具有“虚假性”。如在“雷锋照片门”中,客观真相已无法查明,民众凭借生活经验和历史知识,如拍照在当时是非常奢侈的,雷锋何以拍那么多张;雷锋手持手电筒看书的照片为何会投下手电筒自身的影子;既然是在被窝里看书,谁又会在被窝里为雷锋拍照等等,以此质疑雷锋形象不可谓不合理。以有无客观根据作为“虚假言论”限缩解释的标准,能较好地解决上述疑问。
2.“虚假信息”需要具有可信性
如果一则信息的内容非常荒谬或者在一般人看来根本不足采信,这样的信息便不具备引起法益侵害的抽象危险,既然如此,传播、散布这类“虚假信息”便不具有刑法评价的意义。虚假信息本身具有可信性是刑法对该类行为进行规制最根本的原因。一般来讲,虚假信息是否具备可信性需要从两个方面来考察:一方面,需要考虑该信息是否具有可理解性。事实上,人们对误导行为内容的解释,不是以其对每个细节仔细分析后得出的印象为准,而是以该行为大略的、整体上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否引人误解进行判断。这种整体印象的判断需要民众对信息本身传达的含义有基本的认识,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民众对信息含义的获取并不一定都来自信息本身,信息所处的语境也能对信息所缺失的含义进行补充。据此,除非存在特定的语境,不能提供完整信息内涵的笼统的信息,比如“北京出事了”、“大家快逃吧”等,是无法形成为民众所理解的基本事实的,更谈不上误信。
另一方面,需要考虑该信息是否具有误导性。寻衅滋事罪视野中的“虚假信息”本身需要蕴含法益侵害的可能,换言之,这里的“虚假信息”必须明确表现其“试图让更多的人相信信息内容”的冲动。在现实生活中,比较典型的误导有两种:第一种是借助与现实事件的关联性误导大众。如2011年2月17日,网络上发布了一篇名为《内地“皮革奶粉”死灰复燃长期食用可致癌》的文章,捏造我国奶制品存在质量问题,使得三聚氰胺事件后,民众又一次紧绷神经,我国奶制品市场因为此谣传再次遭受重挫;又如2011年日本福岛核泄漏事件后,网络上出现“碘盐防辐射”的谣言,一时之间国内兴起“抢盐风波”。第二种是借助“权威”来增加信息的真实性。如“47号公告”事件,发布者以《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征收个人所得税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公告》为形式发布信息,对所谓“国家税务总局2011年第47号公告”做了解读。由于涉及到时下备受关注的“年终奖税收”计算方式,经国内多家媒体转载、放大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与讨论;又如“山西地震”谣言,发布者声称其父的朋友是地震局工作人员,山西地震是内部可靠消息,最后导致山西几十个县市数百万群众在2月20日凌晨开始走上街头“躲避地震”,山西地震官网一度瘫痪。
3.寻衅滋事自身的罪状特征要求“虚假信息”的内容需要与一定场所相关
“对犯罪构成要件的解释结论,必须使符合这种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确实侵犯了刑法规定该犯罪所要保护的法益,从而使刑法规定该犯罪、设立该条文的目的得以实现。”①张明楷:《刑法分则解释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1页。正因为如此,“正确的解释,必须永远同时符合法律的文义与法律的目的,仅仅满足其中一个标准是不够的”②Clausr Roxin,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Band I,4. Aufl.,C. H. Beck 2006,S. 151. 转引自张明楷:《刑法分则解释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6页。。可见,刑法条文的描述与所要保护的法益是我们解释法概念的两个基本点。寻衅滋事罪保护的法益是社会的“公共秩序”,其第4类行为则特意强调是对“公共场所秩序”的保护,很显然,两者所意指的范围并不相同。“虚假信息”的内涵需要结合“公共场所秩序”作进一步的展开。公共场所秩序,是指供不特定多数人进行社会活动的具体平台呈现出有序、稳定的状态,公共场所秩序的混乱则表现出该公共交流平台无法向民众提供正常的交往环境,为了造成这样的危害结果,行为人的行为需要指向一定的场所,并对公共场所原有的稳定有序的状态造成冲击。具言之,这里所提到的“冲击”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外源性,即行为人强行介入到公共场所内部,使该场所被迫停止运行。典型的例子就是行为人在现实世界中起哄闹事,妨害社会生活有序进行;另一种是内发性,即行为人利用群体从众①勒庞在言及个体在群体中的表现时,提到群体中的个体会表现出明显的从众心理,群体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提供给他们的各种意见、想法和信念,他们或者全盘接受,或者一概拒绝,将其视为绝对真理或绝对谬误。(参见[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冯克利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版,第10页。)这种从众心理极易强化原本只是为群体中个别人所接受的信息的真实性,进而被整个群体视为真理。以及趋利避害的心理,使群体对原有的秩序产生不信任感,此时群体自身就会出现逆反行为,原有秩序自然会出现混乱。散布“虚假信息”便是其中一例。但是,无论是以上哪种“冲击”,行为人的行为都必须与一定的场所相联系。对于“外源性”的冲击,由于行为人本身就介入到公共场所之中,这里自然就没必要讨论场所关联性的问题。在“内发性”的场合,如果行为人的信息中没有涉及到一定的场所,目标场所中的群体便无法知悉该“虚假信息”是否与自身相关,这就不可能产生群体的安全感危机,更遑论该场所的群体会自乱阵脚。因此,本文认为,寻衅滋事罪视野中的“虚假信息”其内容需要涉及一定的场所。需要注意的是,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5条同样对散布谣言的行为规定了罚则,但是不同于寻衅滋事罪的是,条文中用了“扰乱公共秩序的”一语,因此,“虚假信息”只要具备了本文所述的“虚假性”和“可信性”,便具有进行行政处罚的可能。然而刑法的规制不可能那么宽泛,刑法作为保障法具有片段性的特征,立法者只对其认为值得刑罚处罚的行为规定在刑法条文中。
(二)网络空间属于寻衅滋事罪中的“公共场所”
学界一般认为,刑法中的“公共场所”是指供公众进行工作、学习、经济、文化、社交、娱乐、体育、参观、医疗、卫生、休息、旅游和满足部分生活需求所使用的一切公用建筑物、场所及其设施的物理性空间。刑法与司法解释在对“公共场所”进行示例时,也只列举了物理性公共场所,如刑法第291条中列明了车站、码头、民用航空站、商场、公园、影剧院、展览会、运动场或其他公共场所,又如在2013年7月15日发布的《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司法解释延续了这种思路,指出“在车站、码头、机场、医院、商场、公园、影剧院、展览会、运动场或者其他公共场所起哄闹事……综合判断是否‘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在本文看来,学界与条文示例对“公共场所”的解读是对前网络时代进行总结与描述的产物,然而,“解释者不可固守先前理解,而应当将自己的先前理解置于正义理念之下、相关条文之间、生活事实之中进行检验”②张明楷:《刑法分则解释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12页。,社会生活的变动为刑法的解释提出新的要求,解释者应该正视这种客观变化,选择符合时代性特征的解释结论。
一方面,传统观点限于社会的发达程度,将“公共场所”限定在车站、码头、机场等具有物理性特征的场所可以理解,然而,随着互联网这一新媒介的产生和信息通讯技术的广泛使用,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以及信息的传播与获取慢慢转移到了网络平台,人们的公共空间得到了极大的延伸,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3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6月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5.91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4.1%,网络行为已不再是纯粹的虚拟行为,其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社会意义。但是,网络社会的形成却使得现有法律非常尴尬。现有立法例、司法解释对法律用语的把握都是以现实空间为模板,因此,解释者对法概念所做的解释无时无刻不掺杂着人们对现实空间体验后的印象,如破坏通信自由罪中的“信件”,一般被理解为书面邮件;又如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中的“淫秽物品”,一般理解为画册、影碟、录音带等实物。网络空间作为新生事物尚未给民众带来充分的体验感,即使某些网络行为的效果与现实行为的效果并无二致,由于体验感的不同,解释者仍有所顾忌。面对这样的困境,重新建构网络型犯罪自身的语言体系并通过立法加以推行的做法并不经济,“当前的唯一可行之路径,是探索传统刑法在信息时代和‘双层社会’中的‘生存’之道,寻求传统刑法的罪名体系套用于网络空间的解决之道。”①于志刚:《“双层社会”中传统刑法的适用空间》,载《法学》2013第10期。本文认为,在努力实现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语言体系相互融合的背景下,“公共场所”本身存在用语发展的趋势,因此,有必要对“公共场所”做扩大解释。②张明楷:《刑法分则解释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7页。即“公共场所,是指不特定人或者多数人可以自由出入的场所”,③张明楷:《寻衅滋事罪探究》(上篇),载《政治与法律》2008年第1期。至于出入场所是为了交换信息、交换物资抑或接受、提供服务在所不问,换言之,公共场所只是供不特定人进行社会活动的平台。网络空间作为信息交换的平台,具有程度极高的开放性,网民可以在第一时间获取最新的消息,同样可以在最快的时间内发布信息,网络空间具备“公共场所”的特征。
另一方面,有观点认为,“如果把网络看成现实,接着会不会出现网上抢劫罪、网上斗殴罪呢?以此可见逻辑之谬。”④丁金坤:《网上寻衅滋事罪,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参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682c26f90102effj.html,访问时间:2013年9月15日。还有观点进一步指出,“即使将寻衅滋事罪中的‘公共场所’与上述犯罪中(文中所指的犯罪是非法携带枪支、弹药、管制刀具、危险物品危及公共安全罪、强奸罪、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交通秩序罪、聚众斗殴罪等罪名。引者注)的‘公共场所’作区别对待,也存在一定的困难。对刑法条文加以解释,除应遵守文义解释外,也应兼顾体系解释。假若同一刑法术语在不同罪名中具有不同的内涵和外延,这不仅增加了理解上的困难,也超出了‘一般国民的预测可能性’,显然是不妥当的。”⑤张向东:《利用信息网络实施寻衅滋事犯罪若干问题探析》,载《法律适用》2013第11期。许多解释者都曾期待着,“如果法律在不同的地方采用相同的概念与规定,则应认为这些概念与规定实际上是一致的。⑥[德]伯阳:《德国公法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4-25页。”但事实上不可能如此,同样的法概念在不同的法规则下可能存在不同解释。如若将强奸罪中的“胁迫”与抢劫罪中的“胁迫”作相同的理解,像以揭发隐私为要挟的胁迫就无法被包含,这势必会缩小强奸罪成立的范围。对法概念的解释除了要联系其所要保护的法益,还需要结合具体的犯罪行为类型,如在聚众斗殴罪中,斗殴是物理性接触,此时就只能把公共场所解释为有形的物理性的场所;而在寻衅滋事罪中,由于行为类型包含恶意言论,如辱骂、恐吓等,因此,对公共场所的理解也就不受物理性的限制。
(三)寻衅滋事罪第4类行为中前后“公共场所”应作区别理解
《刑法》第293条规定,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构成寻衅滋事罪。虽然我们认为网络空间属于公共场所,但这并不意味着条文中所言及的公共场所秩序就是指网络秩序。一般认为,刑法具有片断性的特征,立法者只对其认为具有刑罚处罚性的行为规定为犯罪,法益本身具有违法评价机能和解释论机能,较为明确的法益概念能够保证刑法的片断性在司法中得以延续。寻衅滋事罪之所以一直被人诟病为“口袋罪”,其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其保护法益过于模糊,以至于造成行为只要侵犯社会秩序似乎就能被评价为寻衅滋事罪的假象。在本文看来,“社会法益只是个人法益的集合,是以个人法益为其标准所推论出来的。个人的一切法益都是得到法律的承认和受法律保护的,而社会法益的保护是受到限制的……因此,只有当某种社会利益与个人法益具有同质关系、能够分解成为个人法益(即系个人法益的多数集合)、是促进人类发展的条件且具有重要价值和保护必要时,才能成为刑法保护的社会法益。”⑦张明楷:《法益初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3页。如果将无法分解为个人法益的社会法益作为指导构成要件要素解释的向导,不仅容易导致国家权力的恣意与滥用,而且会使得为保护社会法益而牺牲个人法益将成为常态。因此,对“公共场所秩序”的判断不应该是抽象、笼统的判断,而应该与个人直接的生活利益相联系。
网络空间是现实空间的延伸,现实空间是网络空间生存的基础,虽然越来越多的网络行为被赋予社会意义,并涉及利益的交割,但是网络空间自身的特点局限了其承载更多生活利益的可能。一方面,网络空间是一个虚拟的空间,这种虚拟性意味着民众之间的交流只能通过文字、语言、图片等方式予以实现,物理性的肢体接触在虚拟空间里无法出现;另一方面,网络空间具有开放性的特点,用户可以随时凭借自己的意愿选择参与或者不参与。换言之,民众对网络空间的把握具有完全的主动性,即使网络上色情信息泛滥、恶意言论四起,①色情信息泛滥、恶意言论、网民互骂等被指为典型的扰乱网络秩序的情形。参见魏光峰:《网络秩序论》,载《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网络用户也完全可以视而不见、全身而退。然而,在现实世界中,社会秩序的混乱会使得民众被迫停止生产、经营等,民众并无选择的余地。可见,只有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秩序才能与民众的生活利益相直接挂钩。据此,本文认为,寻衅滋事罪第4类行为,即“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中前后两个“公共场所”应该做相应的区分,具体言之:第一个“公共场所”不仅仅指现实空间,而且还包括网络空间,第二个“公共场所”则指的是现实空间。这里值得思考的是,对同一个条文中的同一个概念做不同的理解,会不会超出国民预测可能性,破坏刑法应有的体系?在本文看来,对条文前后“公共场所”做区别理解仅仅是因为场域上的不同,这并不意味着两者之间是毫不相干的独立空间。如前文所述,“虚假信息”必须与一定的场所相关,网络空间正是为传播这样的信息提供了通道和受众,所以,在具体的场合,网络空间因为其所传播的信息而与特定的现实场所取得了联系,此时,作为公共场所的网络空间是依附于特定的现实空间的。既然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之间存在同质性,自然不会出现民众难以理解法条的情形。
四、小结
治理散布“虚假信息”行为的过程重新引发了我们对言论自由的思考。正如美国大法官卡多佐所说:“作为一个法律概念,自由包含了一个潜在的矛盾。最严格意义上的自由是对法律的否定,因为法律就是约束,无约束则导致无政府状态。另一方面,打破约束的无政府状态将使自由成为强人和寡廉鲜耻之人的专有物。”②[美]本杰明·卡多佐:《法律的成长·法律科学的悖论》,蓝炯、彭冰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54页。绝对的言论自由看似是对人权最高的尊重,实则是在营造另外一种不自由。用寻衅滋事罪中“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混乱”的规定来规制散布“虚假信息”的行为并非不可能:第一,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的构成要件将信息内容、传播方式特定化,无形之中排除了对部分可导致公共场所严重混乱的散布“虚假信息”的行为之规制,寻衅滋事罪中的“起哄闹事”并不排斥言论犯罪,同时始终强调危害结果的现实化,充分补充了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在规制散布“虚假信息”行为过程中的不足;第二,结合寻衅滋事罪的文义以及法益,《解释》中的“虚假信息”需要具备虚假性、可信性和场所关联性;第三,考虑到用语的发展趋势与用语的独立性,将“公共场所”进行扩大解释以致包括“网络空间”是较为合适的选择;第四,“造成公共场所秩序混乱”并非指造成网络秩序的混乱,换言之,寻衅滋事罪第4类行为中前后“公共场所”应作区别理解。
(责任编辑:钱叶六)
Regulating Behaviors of Spreading “False Information”: The Feasibility of Applying the Crime of Provocation
Jiang Ao-li
Behaviors of spreading false information online and disturbing public order are deemed as a crime of provocation,according to the “Interpretations of Several Issues Concerning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of Law in the Handling of Defamation through Information Networks and Other Criminal Cases” issued by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and the Supreme People’s Procuratorate on September 6th,2013. The 9th Amendment to Criminal Law which came into force on November 1th,2015 set a new crime name of Crime of Fabricating and Propagating False Information. This new crime name nevertheless,does not mean that the Crime of Provocation loses its role in regulating spreading false information online. The conceptual obstacles in applying the Crime of Provocation will be resolved by the certainty of its composition elements,self-redemption of the principle of “Nulla Poena Sine Lege” in the era of internet,and relativity of freedom expression. The technical obstacles would also be cleared by admitting the internet as public place and interpreting “public space” in the 4th catalog of behaviors differently.
False Information;Crime of Provocation;Conceptual Obstacles;Technical Obstacles;Resolution
D920.0
A
2095-7076(2016)02-0119-10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公诉处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