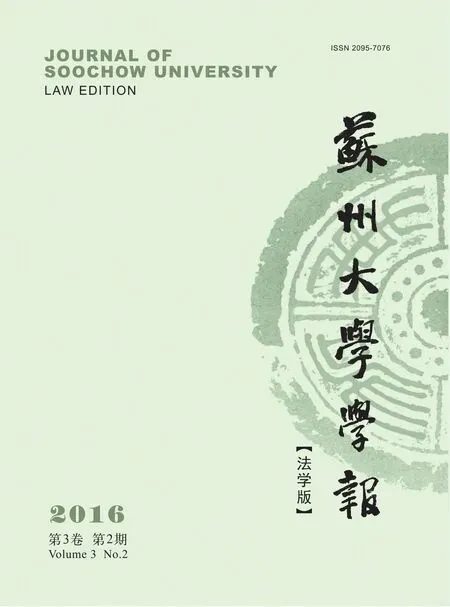以民法典建立“法权共同体”
——兼论民法典中的“自由”
亓同惠
● 本期聚焦:法典编纂的原理与技术
以民法典建立“法权共同体”
——兼论民法典中的“自由”
亓同惠*
在社会主义中国,民法典的编纂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以实证化寻求确定性的民法典,成为市民社会在政治国家中维持并发展自由的中介。民法典承载的自由为政治国家的存续合法性提供基础,为建立法权共同体提供支撑。
民法典;法权共同体;自由
引言
法典化是人类治理经验中极为普遍的技术。制定一部法典,布之于众,是东西方法制发展的制度史和观念史中的常例。对于西方而言,从十二铜表法至《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除后发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秉习判例技术外,以大陆法系为名的罗马法后继者们把法典化推行至欧陆以外的广大地区。对于中国而言,在“缘法而治”或“法制”的意义上,自子产“铸刑鼎”和邓析“作竹刑”开始,从《法经》到《永徽律》再到《大清新刑律》,及至1949年之前形成所谓“六法”体系。尽管在“六法”体系之前,中国传统法律大多民刑不分且技术寒碜,但法典化使得临事制法所标榜的“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治理策略相形见绌,从而繁衍出以唐律为核心的中华法系,由此可见,法典化对于发育中国法律文明功莫大焉。
1949至1978,砸碎国民党时期戮力创制的六法体系之后,30年里以政策代替法律,以政治运动代替政治治理,法律、法典、法规和法条或损毁殆尽或形同虚设。1978年重新上路,依然摆不脱重回六法体系的既有道路,但很显然是一条正确的道路。随着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随着从法制到法治,以及随着公法法典化的完成和宣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①吴邦国:《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大意义和基本经验》,载《求是》2011年第3期。吴邦国指出:“到2010年底,我国已制定现行有效法律236件、行政法规690多件、地方性法规8600多件,并全面完成了对现行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集中清理工作。目前,涵盖社会关系各个方面的法律部门已经齐全,各法律部门中基本的、主要的法律已经制定,相应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比较完备,法律体系内部总体做到科学和谐统一。一个立足中国国情和建设需要、集中体现党和人民意志的,以宪法为统帅,以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的法律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国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实现有法可依”。民法因其与国计民生的先天关联首当其冲地进入了立法者的视野,创制民法典再次成为展示一个大国治理技术日臻完善的标识。基于上述发展脉络,民法典的制定已是大势所趋,同时回首此前种种遭遇,似乎使我们这个在1949年之后对“革命”情有独钟的国家明白了革命(Revolution)的本意,不过是回到周而复始的原点。①[美]汉娜·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31页。革命是手段,其初衷和归宿必然会在某种秩序的建构中显现,并最终放弃对秩序的控制。
如果抛开这些制度史和观念史带来的沉重感和紧迫感,仅以民法典的创制为例,也不能再用“有法可依”来阐明立法意图,因为民法典有着基于法律文本又超越法律文本的自我期许,涉及的范围远超法律文本自身。相对于法律的搜集、汇编、修改或续造,创制民法典是“透过体系性地穷尽安排所有的法律素材,来达成广泛的社会规划”。②[德]弗朗茨·维亚克尔:《近代私法史:以德意志的发展为观察重点》,陈爱娥、黄建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21页。
更进一步说,民法典的理想,在于建立一种规范性秩序,此种秩序合乎理性,具有依照程序可追求的确定性,能够格式化的定分止争。
从国家——社会二元化存在格局出发,在当下制定民法典如火如荼的氛围里,如果试图通过民法的法典化在“法治中国”③所谓“法治中国”,包含着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三个方面,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建设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仅仅建立一个“经济性共识共同体”(Einvenständn isgemeinschaft)——在契约论的语境中,根据目的契约而正当建立的权利体系,以及通过所有权的充分发展所建立起来的经济性共识共同体④[德]马克斯·韦伯:《法律社会学》,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05页。——是不够的。它必须在一个可以衔接国家与社会的更为广阔的层次上寻求一个更为根本也更为有效的基础,以完成其规划社会的理想。
基于此,所谓“以民法典建立法权共同体”,是指民法典以其合法性和实证性作用于政治共同体,在国家和社会两个方面(国家方面的治理、动员、激励和分配,社会方面的自治、服从、抗争和再分配)产生制度性的影响。概言之,通过民法典试图建立的是一个法权共同体,一个权利与义务边界清楚、权力与责任分配正当的共同体,或如马克思所说,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
一、法权和法权共同体
首先要阐明的是法权和法权共同体。
法权在很多时候被理解为权利。比如在康德的著作中,Recht在汉语法学界被译为“权利”,同样的情况出现在英文译本中则多以“rights”或“Justice”去呼应“Recht”,而德文“Recht”则包含法、权利、正义等含义。⑤[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沈叔平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i页。此版本是依据1887年W. Hastie的The Science of Right译出,译者序言中沈叔平先生提到“1887年,黑斯蒂把此书译为《权利科学》;1965年,拉迪译为《正义的形而上学原理》,还有人译为《法律哲学》”,第ii页,由此或许可见各国学者是在按照各自的理解去对应“Recht”一词。对于Recht,康德的定义是“可以理解权利为全部条件,根据这些条件,任何人的有意识的行为,按照一条普遍的自由法则,确实能够和其他人的有意识的行为相协调”,同时提到“权利是与资格相结合的或者是强制的权威相结合的”,是“这样一种可能性:根据普遍法则,普遍的相互的强制,能有与所有人的自由相协调”,⑥参见[德]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沈叔平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40-42页。条件化的法权在此显现为资格、权威和相互强制间存在的某些平衡和妥协。
与康德的条件说不同,费希特定义的法权是一种关系,即每个理性存在者都必须在自己用另一理性存在者的自由限制自己的自由的条件下,用那个关于另一理性存在者的自由的可能性的概念,来限制自己的自由,这种关系叫做法权关系。⑦[德]费希特:《自然法权基础》,谢地坤、程志民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54页。在现实中,尤其是涉及物的归属时,只有至少两个以上的主体都对同一东西感兴趣才涉及法权的产生,否则除了偶尔涉及良心或道义,与法权无关。
黑格尔有关法权的论述,重点在于法权的实在性及其自我否定性。①[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5页。关于法权的实在性,黑格尔强调了两个方面:一个是以标榜市民社会中的自由以成文法为表现的“人的权利”,一个是追随伦理演进以国家涵盖个人、家庭而整体化的“国家权力”,法权的实质意义就在于统合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终身致力于解释黑格尔学说的科耶夫另辟蹊径,将法权的定义放置在 “现象”的框架内并赋予其“行为主义者”和“描述性”的特质:“法权”现象是一位不偏不倚、公正无私的人的“干预”,这种干预在A、B两人发生相互作用时必然出现,并会撤销B对A之行为的反作用行为。②[法]科耶夫:《法权现象学纲要》,邱立波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8页。
在黑格尔的批判者和继承者马克思那里,法权是一个定义极为具体的概念,它与无产阶级在初始阶段的分配问题有关。革命导师认为,在物质条件远未达到共产主义阶段的时期,按照资本主义的“法权”即有差别的、非一刀切的按劳分配,是合理的。③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3-14页。但是这种与分配现实联系紧密的分析,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中产生了极为诡异的成果:围绕“供给制”还是“薪金制”展开了全国性的大论战,始作俑者是张春桥。先发表于1958年《解放》第六期、后经毛泽东批示转载于1958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的文章《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是此次论战的嚆矢。由此,法权的本意自1950年代以来,在中国已经遭到刻意的扭曲,导致的结果是法权概念本身的失聪与禁言。依照此种对法权的理解,政治共同体意义上的国家在马克思的解释中成为“掠夺剥削论”实践模型,它与使国家充当社会福利最大化角色的“契约论”大相径庭。④按照诺斯(Douglass C. North)的解释,从终极的“暴力”运用来说,国家的产生大概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通过契约使国家充当社会福利最大化角色的“契约论”,一种是国家是为使集团、阶级利益最大化而剥削或掠夺其他集团、阶级的代理机构。因为暴力运用及其运用后果的不同,两者存在本质的差别。对于前者,潜在暴力倾向于竞争性的平等分配;对于后者,潜在暴力倾向于垄断性的不平等分配。参见[美]诺斯:《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厉以平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2-23页。
法权不仅仅指权利,至少在1978年代以后的中国法言法语中,它有更深和更广的所指。童之伟教授认为法权事实上包含着权力,即法权是法律权利与法律权力的总和或统一体。支撑这一说法的原因是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权利包含权力——庞德提及的六种权利要素包含着权力,以及可能更为重要的是在第二种要素中权利指的是不仅仅是利益,还要加上保护它的工具。当庞德遗憾地认为并不存在一个在利益加保护工具的层面准确概括此种表达的术语时,法权概念事实上可以承担此种功能。⑤参见童之伟:《法权与宪政》,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20页。
可见,法权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不仅仅是权利问题,还包括权力问题;法权所要运转和发展的前提,不仅仅是自觉的主体,还包括同样资质的他者以及他们之间存在的关系。由此,所谓法权共同体就是依照某种理性原则或策略,使得权利与义务边界清楚、权力与责任分配正当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的秩序具有规范性。而所谓规范性秩序除了是规则之治的基础以外,它同时具有合法性和实证性。
二、民法典的相关因素
依据某种理性原则建设法权共同体的理想,自启蒙运动以来就长盛不衰,民法法典化是此种现代理性化在法治层面上的典型代表。从现代民法法典化的来源来说,由启蒙运动提供的理性,以及接续并将此种理性发扬光大的法国大革命和法国民法典,成为寻根溯源的重要资源。
启蒙运动提供的理性,集中体现在“社会契约论”中。在契约被广泛运用的16世纪,其共识基础是早在13世纪就开始复苏的罗马法及其原则。由此,罗马法特别是契约原则成为人所共知的理论资源。它们渗透到普通人心中,成为理所当然和不证自明的常规,并进而自然而然地获得了合法性和正当性。但把普通的罗马法契约想象为一种国家理论,还需要一种“异中求同”的欲望和能力,而16、17世纪欧洲社会中的主导话语,恰恰就具有这样一种“异中求同”的欲望。它试图发现任何特定对象之间的彼此相似程度,并借此建立一种事物的秩序。因此,契约原则的普遍认同和“对类似的迷恋”,成了社会契约理论得以建立的一个重要条件。此外,契约本身的特质,也决定了它所代表的精神与其预计获得的收益是社会契约理论的现实基础:契约是立约人在立约时的一种理性判断后的选择。①参见苏力:《从契约理论到社会契约理论——一种国家学说的知识考古学》,载《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这种契约精神存在于私法领域和国家建构两个层面,集中显现于民法典之中。当然,法典化并不完全等同于制定民法典。
当立法改革内容广泛并且声称要涵括某一整个法律领域时,该现象就被习惯性地定义为“法典化”,而其产品就是法典。②[以]达芙妮·巴拉克-艾芮茨:《比较视野中的法典化与法律文化》,马建银译,载《清华法学》(第八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但对此也存在不同看法,据王利明教授考证,法典化(codification)一词最早出现在边沁写给亚历山大一世的信中,边沁在信中区分了法典化和立法两个概念。实际的民法立法史实也与之相符合,在法典化的概念出现之前,普鲁士、法国、奥地利等国的民法典业已制定。③参见王利明:《民法典体系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页。由此可见制定民法典与法典化存在不同,前者注重立法行为,后者注重规范的体系化。从启蒙运动的总体背景来看,法典化主要涉及文化和政治两个方面。
在文化方面,法典化运动是强调理性和科学思想的启蒙运动的产物,其目的是创建合乎理性的、条理化和系统化的法律文本。在政治层面上,法国大革命在近代法典化的兴起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大革命的意识形态要求法律改革应以创建一种平等主义的规范秩序为目标,这种秩序将消除法律主体之间基于社会地位、财产等方面的差别。人们认为,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就需要一部简明而系统的新法典,这种渴望在1804年通过《法国民法典》的制定而得到满足。④参见[以]达芙妮·巴拉克-艾芮茨:《比较视野中的法典化与法律文化》,马建银译,载《清华法学》(第八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这部民法典是开启现代法典化大幕的序曲,在其中理性的原则以“法命题”而非“法律规范”的面目彰显。也即,在理性原则的指引下,法典里常见的定义本身不具有“法律规则”性格,而是具有“法命题”性格,这在《法国民法典》中多有展现。法国民法典的多数条款规定和十二铜表法的规定同样意味着警句和立标造铭的作用,而其中更有不少规定像昔日的法谚那样,成为一般大众的日常用语。⑤参见马克斯·韦伯:《法律社会学》,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99页。这些“命题”以原则式的广谱适应性适应于个别问题的实务所需。在韦伯看来,正是理性原则在现代民法典运动中的初始阶段常有的充满矛盾的特质,主权者的意志以一种特殊化的理性主义表达出来。⑥参见马克斯·韦伯:《法律社会学》,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00页。
进一步追溯,主权者的意志即为隐藏在《法国民法典》之后的法国大革命时期确立的人民主权意识,其更深层的根据则在卢梭的“公意”。国家全体成员的经常意志就是公意,⑦[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36页。公意永远公正,且永远以公共利益为依归。⑧[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5页。公意极为重要,因为赋予根据社会契约产生的政治体以“行动和意志”的法律,即由公意产生。⑨[法]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46页。卢梭指出:“我已经说过,对于一个个别的对象是绝不会有公意的。事实上,这种个别的对象不是在国家之内,就是在国家之外。如果它是在国家之外,那末这一外在的意志就其对国家的关系而言,就绝不能是公意;如果这一个别对象是在国家之内,则它便是国家的一部分:这时,全体和它的这一部分之间便以两个分别的存在而形成了一种对比关系,其中的一个就是这一部分,而另一个则是减掉这一部分之后的全体。但是全体减掉一部分之后,就绝不是全体;于是只要这种关系继续存在的话,也就不再有全体而只有不相等的两个部分;由此可见,其中的一方的意志比起另一方来,就绝不会更是公意。但是当全体人民对全体人民作出规定时,他们便只是考虑着他们自己了;如果这时形成了某种对比关系的话,那也只是某种观点之下的整个对象对于另一种观点之下的整个对象之间的关系,而全体却没有任何分裂。这时人们所规定的事情就是公共的,正如作出规定的意志是公意一样。正是这种行为,我就称之为法律”。换言之,理性化选择将产生公意,而公意将产生法律和国家。与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所谋求建立的与宗教世界分庭抗礼的世俗国家一样,理性在契约精神的指引下现实化为自由。姑且不论此种理性化的自由的双刃剑效应,①所谓双刃剑效应是指,法国大革命产生的革命化自由,坚信不砸碎一个旧世界就无法建设一个新世界。这使得相信历史必然性的革命者采取一种与尼采和托克维尔在比较了法国大革命与基督宗教之后大概相同的见解:大革命引领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个历史阶段就是没有上帝的宗教阶段,而以官僚主义的现代国家为偶像。而他们则成为了马基雅维利、罗伯斯庇尔和拿破仑三位一体的新权威,无需德性,以暴力保卫、辖制自由,永远革命。参见凯斯-安塞尔·皮尔逊:《尼采反卢梭——尼采的道德政治思想研究》,宗成河等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第29-30页。仅从《法国民法典》及其后辈《德国民法典》中,由债权和物权所组成的民法世界维持和保护的正是两种自由,即债权的行为自由和物权的所有权自由。这些由理性产生的、体现在民法典中的自由,似乎在现实中背叛了卢梭的公意,但对理解中国自1840年代以来的共同体建构的理论基础,却意义重大。
三、存续合法性
如果说法国大革命起因于旨在解决生计问题的“胃的造反”,那么西方意义上的革命并未脱离自由的本意。在西方,革命是一个天文学术语,它精确的拉丁文原意是指有规律的天体旋转运动。此种运动非人力可及,亦非人力可拒,它不以求新亦不以暴力为特征。毋宁,它既为保守而高贵,应用于人间之事其隐喻在于一种为极少数人所知的政府形式,永恒轮回,周而复始。②参见[美]汉娜·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31页从其本源上看,革命关注的是政治自由的古典回归。
以此革命的本意及其对自由的理解,与卢梭的“公意”进行比对,会发现卢梭要表明他不想重蹈霍布斯聚拢原子式个体后尘的努力,他要以“公意”整合其他意志而成为社会契约论的保障进而成为国家合法性基础的努力,可能是徒劳的。这源于卢梭公意说的两个错误。第一,公意无法整合个体意志。自由的个体所具有的意志是自由的意志,这种具有人格归属性的自由所产生的意志具有独立性,卢梭对公意的理解存在错误,“然而他理解的意志,仅仅是特定的单个人意志(后来的费希特亦同),他所理解的普遍意志也不是意志中绝对合乎理性的东西,而只是共同的东西,即从作为自觉意志的这种单个人意志中产生出来的”。③[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55页。卢梭的错误始于将自由理解为每一个体或然的意志,而自由必须在理性意志的意义上被理解,因为意志本身自在自为。由此,公意不能被视为是个人意志展现的集合,个人意志在集合中始终保存其独特性和绝对性;第二,社会契约构建的是市民社会,而非国家。社会契约论构建的只是市民社会,有必要向真正的国家再进一步,因为社会契约只是使得工具理性实现了建制化。所以卢梭需要安排立法者出场,其任务即在于通过立法,将孤立的个体从市民社会转送到国家。④参见Asher Horowitz,Rousseau,Nature and History,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87,quoted from Robert R. Williams,Hegel’s Ethics of Recognitio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7,p.276.
卢梭的错误在马克思那里得到了修正,尽管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认为,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无法消解的矛盾导致了革命:“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82-83页。但“社会”在中国革命胜利的那天起,即被国家吞没。暴力的革命和革命的暴力,及其可能带来的收益,由此证明了政治共同体的合法性,这与法国大革命并无实质区别。实质的区别在于,法国大革命使用暴力但并不标榜国家暴力,其立国基础仍在自由;中国革命使用暴力并坚信为了“公意”——正是它在确保自由——的母本,为了人民的利益,标榜国家暴力。这使得国家开端的合法性常常陷入一种结果主义的逻辑:如果再有拥有更强暴力的组织声称代表人民,。如何应对?
因此,开端的合法性需要被某种试错式的存续合法性代替,亦即从1978年以来,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始,对中国自有的理性模式进行重构。①1978年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名进行的常识理性重构,瓦解了革命语境中集体压倒个体的道德逻辑,逐步以经济贡献转化政治忠诚,其利害判断标准也进一步功利化。随着1995年的“国企改制”的展开,“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成为更新鲜的利害判断标准,它通过产权归属的重新界定改变着人们对道德和伦理的理解,以至于形成了新的“道德实用主义”和“生产率伦理学”。参见亓同惠:《天下:中国自我规定的技术》,《历史法学》(第十卷),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243-265页。遵循此种重构,以拯救民族危亡、实现人民自由为旗帜的革命,时值今日,发展出一个全新的模式,用经济自由置换了政治自由,存续合法性延缓了对开端合法性的追问。这使得讨论民法典意义上的合法性有了可能,而“社会主义”的国家本质对此种可能性,至少在理论上不谋而合。
“社会主义”一词,1832年首次出现在法国的《地球报》上,用来表述圣西门的学说特征。至19 世纪三四十年代,“社会主义”一词在欧洲流行的时候,它有了更广泛的意义,即凡是根据“人权经济观”和“社会观”来实现某种新社会制度的团体,都被称为社会主义团体。②[英]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第1卷),何瑞丰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8页。这是在法国大革命以来,对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两厢对峙并斗争的反应,也可以说从一开始,社会主义的对手就是国家和国家主义。比如在列宁对“社会主义”定义的公式,“苏维埃政权+普鲁士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教育等等等等+…+ =总和=社会主义”③《列宁选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28页。即表明,社会主义多元化的兼收并蓄并不拘泥于相对一元化的国家政治藩篱。
在经过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之后,同时也经过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批判之后,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批判了多种“社会主义”,它们包括属于“反动的社会主义”的“封建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德国的社会主义”,“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423-433页。“自由主义者”马克思向“社会主义者”马克思转向。通过重新定义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马克思洞见到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一种互为条件的对立关系。这可以概括为以政治国家为中介的,人与其存在的市民社会的矛盾性共存:在政治国家的意义上废除市民社会的种种不平等,但在实际上却要仰仗这些差别维持国家自身的存在。⑤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版,第172页。但发现这种对立,却不足以完成人的解放或者说是对自由的把握,“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版,第189页。
如果说在马克思那里国家在一开始就是社会的对手,那么在已经变成“共产主义者”的恩格斯论述国家的时候,他用的是一个极为激烈的词,“祸害”。恩格斯认为,“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工具,而且在这一点上民主共和国不亚于君主国。国家最好也不过是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中获胜的无产阶级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有能力把这全部国家废物抛掉。”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版,第55页。
通过政治解放所实现的政治国家的自由,是以承认和保护私有财产的市民社会的不自由、不平等为前提的,①马克思认为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也处于同样的对立之中,同宗教克服尘世局限性的方式相同,即它同样不得不重新承认市民社会,恢复市民社会,服从市民社会的统治”。参见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版,第173页。这与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和此后以国家权力推进的种种改革所秉持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并行不悖。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衔接起来的规范体系,注定将回归“社会”社会主义所预设的对悖论性自由——以不自由维护自由——的追求。
四、民法典的实证性
民法典有着较为清晰的类型分类,在继承罗马法传统的基础上,《法国民法典》奉《法学阶梯》为蓝本,《德国民法典》以《学说汇纂》为圭臬,由此繁衍出大陆法系两种不同的民法体系。从清末修律变法开始,至国民党六法体系形成,近现代中国的民法典曾以《中华民国民法典》之名存续了20年。②参见王利明:《民法典体系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08-209页。1949年之后,国民党六法体系被废除,近代资本主义民法传统在中国丧失了存在空间,直到2009年《侵权责任法》独立成编并颁布实施,中国民法似乎重新回到当年受日本民法学者艳羡的起点,那么多实施多年的民法典可供借鉴,实在是可遇而不可求。
此种后发优势,使得当下中国民法典的制定能够深入全面地考虑民法典除了体系完整、结构合理、技术精湛和符合实际等因素外,仍然需要回到民法典为市民社会立法的本质上来,回到自《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以来即孜孜以求的市民社会的自由上来。已成通识的民法基本原则,无论私权神圣、契约自由还是过错责任,在其本质上都是基于个人理性判断后的自在自为,都是个人欲望经由理性束缚后的相互认同,其根本在于自由。而自由在国家与社会的不同语境中,有着不同的含义和功能。
社会意义上的自由更接近于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描述,这是一个“所有的原子个体一律平等,都像每个个体一样,各算是一个个人”时代,是一个个体摆脱了家庭的中介和羁绊而直接现实化的存在形式,同时是一个返回空虚命运的必然性而重又做回自我意识的我的时代。③[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8页。从其哲学基础来说,市民社会的自由是斯多葛主义和怀疑主义交相辉映的结果:斯多葛主义依据主人和奴隶模式的自我意识,把人格——即产生于一切人普遍具有的统治欲和服从心——提供出来,它为法权状态的原则亦即毫无精神的独立性提供了抽象的形式,同把这种逃避现实的独立性锁定于思想而抛弃一切特定存在,使得个人法权只能与自我意识结合;怀疑主义提供了法权的形式,即没有自己特殊内容的把它遇到一种样态繁复的物或财产赋予其所有权的抽象普遍性。④参见[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9-40页。此时的自由成为市民社会法权(“那种无精神的普遍性,承认任何自然状态的性格和存在都具有同等的合法权利”⑤[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48页。)的主要载体。
国家意义上的自由类似于查尔斯·泰勒所论及的“反生理性的自由”。以为自由是可以按照个人的利益经过理性选择后的任意,从而不应受到他人或群体干涉,这样的想法只是一种“机会概念”,一种粗糙的、原始的霍布斯式的概念。⑥参见[加]查尔斯·泰勒:《消极自由有什么错》,达巍译,载达巍等编:《消极自由有什么错》,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70-71页。其粗糙之处在于如果仅仅把自由定义为没有人或人的群体干涉,至少在动机和感觉两个方面存在不恰当的忽视。不受干涉不意味着就是自由,因为自由“还要求你所做的事情不能与你的基本动机或者自我实现背道而驰”,⑦[加]查尔斯·泰勒:《消极自由有什么错》,达巍译,载达巍等编:《消极自由有什么错》,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74页。以及更为重要的我们在社会存在的意义上不可能是或仅仅是生理性的存在,我们实际上都具有黑格尔式的对生物性的“逆反”,即对于哪些东西是至关重要哪些东西是可有可无的评判标准是通过“认同”来树立的。自由只有在超越了生理性考虑才会有意义,①[加]查尔斯·泰勒:《消极自由有什么错》,达巍译,载达巍等编:《消极自由有什么错》,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 84页。因此,个人就不再是自我自由状态的最终裁定者。②泰勒指出,自由不会只是没有外在的障碍,因为也可能有内在的障碍。对自由的内在障碍也不能仅仅按照主体认识的样子来定义,主体不是最终的裁定者。因为对他真正的目标,对什么是他想要摒弃的这个问题,他可能是完全错误的。在这个问题上,如果他是错误的,那么就“自由”一词的有意义层面而言,他就不那么自由。[加]查尔斯·泰勒:《消极自由有什么错》,达巍译,载达巍等编:《消极自由有什么错》,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 90页。
从民法典的意义上看,理性化的民法典需要从市民社会中生发、存续,而市民社会本身是非理性化的。由此,就需要国家通过某种拟制-强制的理性介入其中,以民法典为中介,完成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妥协。在当下中国,如果市民社会要实现自治,那么应该被看重的自由是自我管理的能力,在这种能力具备的前提下致力于促进并维护自由的事业才变得可行。此种“我能”的自由比“我要”的自由重要得多,③启蒙以后,卸掉宗教枷锁的人们也同时丢弃了对上帝的最后一丝实质性的敬畏,在穷困、饥饿的催化下从“胃的造反”走向革命——以自由的暴政反对专制,以共和褫夺独裁。这一畸变从自由转化为自由意念的视角审视具有同样的过程:可见的平等者之间的自由,是一种边际现象(marginal phenomenon),构建了统治除非生命本身及其直接利害或必要性陷入危急而不可逾越的界限。但在古典时期,“我要”与“我能”因为自由在公共空间的可见性并无分别,处于权威的把持下的“我要”仅仅在思想的层面运转,引而不发。但随着世俗和宗教权威的消失“我要”直接从自我立法或是枉顾必然性的限制,显现的以行动取代了“我能”。在此,“我要”其实是一种他者不在场的孤独态势下的自我决断,因为缺少了他者的事先认同或承认而只能在显现之后评价,除了其自我结构的复合性缺陷之外,欲望取代了经由权威过滤的理性才是其本质。法国大革命是“我要”取代“我能”的典型案例,其中自由与权力双双陷入要么为所欲为要么销声匿迹的困境。而美国革命则是一直以“我能”的自我定位建国,国父们所坚持的原则从未将自由或权力减损,相反以创建新罗马的勇气显现了行动的开端力量。参见[美]汉娜·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124-165页。而民法典中对“我能”的背书,即为自由的实证化。从当下中国对民法典制定的热情和投入来看,具有民主意味的立法程序化过程实际上已经显示出所有利益相关者都可能参与其中,从个体利益和群体利益的折冲樽俎中实证化的民法典成为限制自由却更有效提供自由和保护自由的制度安排。如果民法典的自由体现了公民或市民的自我立法,那么对于国家来说则意味着私权与公权两分的正当性,意味着国家及其权力不能随心所欲,从而实现“社会主义”所秉持的以社会规制并最终取代国家的初衷,以及实现哈贝马斯所提及的“统治的最小化”④[德]哈贝马斯:《包容他者》,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59页。。
在更为广阔的法社会学视野中,当民法典把以债权的行为自由和物权的所有权自由实证化之后,就意味着私权的客观化和可见性获得了国家的认同,这种认同使得私法自治具有了共识。此种共识可能在两个方面有效地促进规范性秩序的发展:从个人私权出发,利益交换和处置纠纷拥有了自由但克制的标准,卢曼意义上的“认知性期望”和“规范性期望”产生冲突的机率显著降低;⑤参见[德]尼古拉斯·卢曼:《法社会学》,宾凯、赵春燕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79-90页。从国家公权来说,制度化的排除可能对利益交换和处置纠纷产生不良影响的第三方,使处于交易或纠纷中的参与者采用已有的规范,并为之提供持久有效的集体性的视角。⑥参见[德]尼古拉斯·卢曼:《法社会学》,宾凯、赵春燕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12-113页。
余论:知识再生产
自1978年以来,建立“法治中国”的努力,同时是为建立一个“法权共同体”而努力,时值今日民法典制定如火如荼之际,会发现与这些努力相伴随的是诸多纷争。从土地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经济体制改革—厂长负责制、国企改革—两权分离制等公权宏观层面的争议,到“乌木案”、“狗头金案”、“风光案”等相对微观的权利层面的争议,反映出公权和私权即便在社会主义的背景下依然难以相安无事。
尤其自2007年《物权法》实施之后,以宪法学和民法学的论争为例,在对《宪法》第9条和第10条进行历史、理论、逻辑、语义等多维度的分析中,显示出公法和私法融合性的对峙。或如有学者所洞见,在认同宪法为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设立界线之际,同时也为两者彼此越界埋下隐患,并导致所谓“‘泛宪法思维’与‘超民法思维’的混在与共鸣”和“‘脱宪法思维’与‘泛民法思维’的对比与契合”。①参见林来梵:《近年中国有关宪法与民法关系的四种思维倾向》,载《法政研究》(日本)第75卷第1号。
日本学者寺田浩明指出,对于人们日常社会生活的众多合意,公共权力只是认定其中有限的几种作为允许通过审判获得公共权力保障的契约关系,于是出现了若干种例外的、界线分明的交易类型,成为公共权力向一般人提供的公共服务,或人们需要时就可运用的“公共基础设施”。这样理解的话,契约就并非当事人形成的任何种类的合意,而仅仅意味着由公共权力预设“制作”出来的特定几种合意类型,试图诉诸公共权力保护的当事人只是选择其中某一种形成合意而已。把还未存在的将来状态或未来的事实如同现存的事实一样作为交易对象,为了实现这种交易而由公权力广泛地向交易社会提供有一定担保作用的制度装置。②参见寺田浩明:《权利与怨抑:寺田浩明中国法史论集》,王亚新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0-122页。这反映出私权自治在政治国家中的真实处境,当民法典以实证化的规则体系寻求确定性时,与私权自治建构相伴的,是政治国家对市民社会的筛选、担保和重建。
当社会不得不依照国家为其制定的实证法而运转时,同时也意味着国家要恪守此种实证法划定的边界。对于民法典的制定者来说,所有由法律保护的自由和权利将成为一种“教义式”的自由和权利,而支撑民法典的学说将成为一种所谓的法教义学。③[德]尼古拉斯·卢曼:《宗教教义与社会演化》,刘锋、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8页。如果民法典成为实证化同时是教义化的规则体系,那么其所追求的在多元、复杂且变化的现实关联中寻求或建立某种确定性的长处,通过以国家强制力和法律渊源认同而维持的封闭性,将长久共存。
如果仍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框架内寻找解决的办法,需要再次申明,通过政治解放所实现的政治国家的自由,是以承认和保护私有财产的市民社会的不自由、不平等为前提的。因此,生产资料公有与个人资本(主要但不限于劳动力)私有,也将长久共存存。
由此总结前文,以民法典建设法权共同体将是一个过程,除了私权自治、契约自由和侵权责任等基本原则体系化的背书之外,民法教义世界所形成的共识将成为一种知识。制定民法典,使之参与到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尽可能广阔而细致的治理、交往和博弈的过程中,此种共识性的内部知识的传播成为以法律治理为形式的知识再生产。通过此种事关政治国家-市民社会利益配置和责任配置的知识再生产,我们可能距离优良的法权共同体就为之不远!
(责任编辑:许小亮)
The Establishment of “Community of Droit” by Civil Code
Qi Tong-hui
In socialist China,the establishment of Civil Code has its significance. By the positivistic of rights and duty,the Civil Code will get its certainty and become the intermediary of society and political state to maintain and develop. The freedom hosted by Civil Code can provide the legitimacy of existence for the political state,and also provide the foundation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ommunity of Droit.
Civil Code;Community of Droit;Freedom
D913
A
2095-7076(2016)02-0001-09
*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副教授,西南政法大学人权教育与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