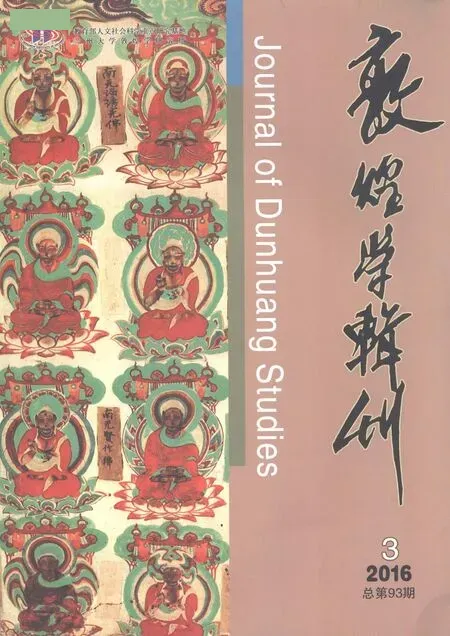古代丝绸之路商队运营面临的危险以及应对措施
李瑞哲
(西北大学 艺术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9)
自汉开始,历经魏晋南北朝隋唐,商人在中国的踪迹屡见于史籍,可以说,追逐商业利益是商人东来西往的一个主要因素。我们在回顾丝绸之路历史的时候,发现对于古代商队活动与运营的情况了解很少,商人是怎样实现他们的贸易的?商队将西方的商品贩易到长安、洛阳等地来换取中国的丝绸,期间运营的过程目前还不是十分清楚,近年来一些出土文书以及入华粟特人的石质葬具上的图像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很好的证据。张庆捷先生利用出土的胡商俑、胡商图与胡商文书对古代胡商做了详细的研究。*张庆捷《北朝隋唐的胡商俑、胡商图与胡商文书》,载荣新江、李孝聪主编《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73-204页;《民族聚会与文明互动——北朝社会的考古学观察》,北京:科学出版社,第141-191页;《北朝入华外商及其贸易活动》,张庆捷、李吉书、李刚主编《4—6世纪北中国与欧亚大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2-36页。荣新江教授对入华粟特人史君墓石质葬具上的商队图像进行了分析研究。*荣新江《北周史君墓石椁所见之粟特商队》,《文物》2005年第3期,第47-56页;收入《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第217-234页。郑燕燕博士对高昌地区粟特商业运营活动,尤其是商队的旅途生活进行了研究。*郑燕燕《论高昌地区粟特商业的运营》,《西域研究》2012年第2期,第14-22页。这些研究为我们了解古代商队在丝绸之路上的活动提供了丰富的信息。
从两汉时代起,中国的丝绢就已经成为丝路贸易的主要商品,这种轻质高利润的商品一开始就为丝路贸易注入了活力。商人是古代丝绸之路上最活跃的因素,由于对商业利润的追求以及为了克服旅途中所面临的危险,他们往往组成商队,由商队首领组织和领导,以商队的形式穿梭于丝绸之路上。在商人中,以粟特人为主的胡商扮演了重要角色。商队在丝路上行走,有时也要在野外宿营,必须采取防范措施,雇佣护卫和保镖,并且与丝绸之路沿线的少数民族政权建立关系。商队在丝路上的运营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笔者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试图对商队在丝路上运营所面临的危险以及应对措施进行分析研究。
一、商队路途面临的危险
胡商面临恶劣的自然环境条件和强盗袭击两方面的威胁,这就要求他们必须组成商队。由于“兴生胡”与生俱来的“兴生贩货,无所不至”的特性,他们不仅要面对来自沙漠、高山、河流等自然环境的阻隔,有时还会遇到贼寇的突袭。为了获得中国的丝绸,商队要通过塔里木盆地的南、北缘,进入河西走廊到达中原。实际上古代商队在丝绸之路上的经营,除了受到丝路沿线自然环境的影响,还要受到中国政局的影响,关于受到中国政局的影响情况在粟特文2号古信札有真实的反映。许多外国商人死于饥荒,“他们已无利可图”,[注][法]魏义天著,王睿译《粟特商人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3页。反映了公元4世纪初中原动乱对入华胡商在商业活动方面的影响。
晋代法显(337-422)从敦煌西行到鄯善,在途径沙河时记载:“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注][东晋]法显撰,章巽校注《法显传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6页。。《北史·西域传》对且末国(今新疆且末县北)的记载:“西北有流沙数百里,夏日有热风,为行旅之患。风之所至,唯老驼预知之,即嗔而聚立,埋其口鼻于沙中。人每以为候,亦即将毡拥蔽鼻口。其风迅駃,斯须过尽,若不防者,必至危毙。”[注]《北史》卷97《西域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209页。自然环境的恶劣,骆驼有预知能力,可以帮助商旅做好提前预防,同时也显示出骆驼作为交通工具的重要性。

敦煌隋代第420窟东披顶部绘制一幅“商人遇盗图”,[注]敦煌文物研究所编《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年,图75。出自《法华经·观音普门品》,画面以连环画形式从左至右展开。属于唐代开凿的第45窟,也绘有一幅“商人遇盗图”。[注]敦煌文物研究所编《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三),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图133。第45窟画面人物皆为深目高鼻、卷发浓须、身穿长衫,远处有山峦。从画面上看,商队的运输工具主要是毛驴。
1959年5月,在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乌恰县以西的一个山崖缝隙间发现947枚波斯萨珊银币、16根金条,可能是商人遇到强盗时紧急掩埋的。[注]李遇春《新疆乌恰发现金条和大批波斯银币》,《考古》1959年第9期,第483页。埋藏时间可能在公元7-8世纪,当时大食进攻中亚,攻灭萨珊王朝,致使大批粟特人和波斯人向东迁徙,乌恰在塔里木盆地南缘通往费尔干纳盆地的丝路沿线上,推测这一地区应该是强盗经常出没的地方。1999年7-9月,青海都兰三号墓发现两件写有墨迹的织物,其中编号99DRNM3:16的是一件罕见的与市场商贸活动有密切关系的道符。道符上的“市”字可能是指中原与吐蕃之间茶马皮货贸易的“交市”、“互市”之市。[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都兰吐蕃墓》,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年,图3,第72页。这个“市”的字体写得比较大,居于中央位置,两侧各有三个曰形护持,系诸符文中最为醒目者,明显地体现出其为诸神的佑护对象。这一发现反映了古代人们知道商业贸易这种活动带有一定风险,可能面临着疾病的困扰,因此往往求助于宗教的力量,即将希望寄托在精神方面,以求平安。
亨利·裕尔(Henri Yule)在其《东域纪程录丛》中记载了东罗马帝国派往突厥的使团在行进途中差一点受到波斯人的伏击。[注][英]裕尔著,[法]考迪埃修订,张绪山译《东域纪程录丛》,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77-178页。使团成员蔡马库斯(Zemarchus)采用迷惑波斯人计谋,顺利返回拜占庭,完成了出使突厥的使命。
沿途强盗的出没,严重威胁着商侣的安全。《汉书·罽宾传》记载:“凡遣使送客者,欲为防护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属汉之国四五,斥候士百余人,五分夜击刀斗自守,尚时为所侵盗。”[注]《汉书》卷96《罽宾传》,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3886页。《宋书》卷九五记载南朝宋时,粟特“大明中遣使献生师子、火浣布、汗血马,道中遇寇,失之”[注]《宋书》卷95《索虏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357-2358页。。从汉代开始,丝路上的强盗就很猖獗,即使人数众多的使团,也常遭抢劫。
官兵为盗匪的现象也时有发生,[注]沙武田《丝绸之路交通贸易图像——以敦煌画商人遇盗图为中心》,《丝绸之路与长安共同研究班发言稿》,第8-13页。《周书》卷五十与《北史》卷九六记载了吐谷浑派往北齐的使团在返回时遇到北周凉州刺史史宁觇的伏击,劫获了大量的胡商与财物,“获其仆射乞伏触扳、将军翟潘密、商胡二百四十人,驼骡六百头,杂彩丝绢以万计”[注]《周书》卷50《异域列传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913页;《北史》卷96《吐谷浑传》,第3187页。。北周伏击吐谷浑派往北齐的使团,这里主要含有较多的政治因素。《魏书·元暹传》记载任凉州刺史时,“贪暴无极,欲规府人及商胡富人财富,诈一台符,讹诸豪等,云欲加赏,一时屠戮,所有资财牲口,悉没自入”[注]《魏书》卷19上《景穆十二王列传》第七上《京兆王》,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45页。。可见,当地的高级官员,利用自身所处的优势地位,参与了抢劫胡商及富豪的行动之中。
《朝野佥载》卷三记载:“定州何名远大富,主官中三驿。每于驿边起店停商,专以袭胡为业,资财巨万,家有绫机五百张。远年老,或不从戎,即家破贫。及如故,即复盛。”[注][唐]张鷟《朝野佥载》卷3,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75页。何名远利用官驿的便利条件“起店停商”,专门袭击胡商致而成“大富”,说明胡商经商的危险性。
《太平广记》“张守珪”条记载:“幽州节度张守珪,少时为河西主将,守玉门关。其军校皆勤勇善斗,每探候深入,颇以劫掠为事。西域胡僧者,自西京造袈裟二十余驮,还天竺国,其徒二十余人。探骑意是罗绵等物,乃劫掠之,杀其众尽。至胡僧,刀棒乱下而不能伤,探者异焉。”[注][北宋]李昉《太平广记》卷329,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2615-2616页。张守珪将本来是袈裟的僧衣误认为丝路重要商品“罗绵等物”,使士兵抢劫僧人团队。
唐代的诗歌中诗人王建《羽林行》对官兵为盗贼现象的描写:“长安恶少出名字,楼下劫商楼上醉。”[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唐诗选》(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97-98页。长安的恶少的坏是出了名的,他们敢于在酒楼下抢劫商人的财物后,马上又跑到酒楼上去狂欢醉饮。天亮他们下班后从皇宫里一出来,就分头藏入五陵一带的松柏中。终于有一天这伙人落网了,按法律规定他们多次杀人本该判处死刑,但皇帝却下赦书释放他们,还说他们有受城之功。当他们被赦的消息在长安城中得到证实,他们便立刻在乡吏簿籍中重新恢复了自己原来的姓名。
中原的政治形势对胡商的经商活动影响很大,粟特文2号古信札反映了公元三世纪初居住在河西走廊一带的粟特人受到匈奴攻入洛阳时被波及情况。洛阳城最后一位皇帝因为饥馑和火灾逃离了洛阳,宫殿付之一炬,城市也遭到了毁灭,洛阳已不复存在,邺城也不复存在,许多印度人、粟特人都死于饥荒。“住在敦煌到金城(今兰州)的这些人,无论是谁——我们仅仅保住了性命,只要活着,而我们是没有家的,年事已高行将弃世的。如果我写信告诉你们中国现在发生的所有事情,这定会令人不胜伤悲,对你们来说,那里已无利可图了。”[注][法]魏义天著,王睿译《粟特商人史》,第23页。中原动乱甚至波及到了河西走廊一带的粟特商人,洛阳在历史上被攻陷的时间有公元190、311和535年,大部分学者都认为信札中所描述的洛阳的情况应该是公元311年。[注]A.Stein , Serindia,Ⅱ, Oxford 1921,pp.671-677. W. B. Henning, “The Date of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s”, BSOAS , X Ⅱ ,1948 ,pp.601-615. J. Harmatta,“Sir Aurel Stein and the Date of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s’”, Jubilee Volume of the Oriental Collection1951-1976 , Budapest 1978 ,pp.73-88; idem . , “Th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for the Date of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s ’”,Studies in the Sources on the History of Pre-Islamic Central Asia,Budapest 1979,pp.75-90; idem.,“Sogdian Sources for the History of Pre—Islamic Central Asia ”,Prolegomena to the Sources on the History of Pre—Islamic Central Asia , Budapest 1979 , pp. 153-165. Frants Grenet and N . Sims—Williams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s”,Transition Periods in Iranian History , Actes du symposium de Fribourg-en-Brisgan(22-24 Mai 1985 )( Leuven, Belgium: E. Peeters, 1987) , pp. 101-122 .参见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286页注释1、2,第287页注释1、2、5。[美]芮乐伟·韩森著,张湛译《丝绸之路新史》,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第150页。由2号信札看出,中原的政局动乱对粟特商人的贸易活动影响很大。信中第二部分是那你槃陀向拨槎迦汇报那斯延没有经过他的允许擅自离开敦煌并且死亡的情况,认为这是对他不当行为的惩罚。[注][法]魏义天著,王睿译《粟特商人史》,第24页。一个商队中,商人的行动必须按照商队首领的经商计划行事,个人行为将会导致致命的后果。粟特文古信札也向我们透露出在中国的粟特商队并不是孤立的,他们与遥远的撒马尔罕之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二、商队在路途中休息与露营
粟特人的经商活动,是一种有组织的活动,他们往往组成商队,结伴而行,并推举出一位商队首领,即萨宝。
辛姆斯·威廉姆斯(Nicholas Sims-Williams)认为:“特别重要的一个例子是伊朗——印度语(Irano-Indian)混合的称号s’rt p’w或srtp’w‘商队首领(caravaneer)’,该词也见于突厥语中,其后缀很明显是伊朗语,但可能并非粟特语,因为在其他粟特语词汇中用的是该后缀的不同形式。正如目前众所周知的是,该单词即为汉语“萨保”或“萨宝”(早期中古音sat-paw,晚期中古音sat-puaw)的原词,它是管理在中国的伊朗语族聚落事务的官员的头衔。最有名的一些萨保的墓葬就是在西安发现的:比如同州萨保安伽、凉州(姑臧)萨保史君(Wirkak),两人都是卒于579年(大象元年)。就史君墓来说,其中发现的汉语、粟特语双语铭文对于确定汉语的“萨保”即为粟特语的s’rt p’w提供了重要证据。”[注][英]尼古拉斯·辛姆斯——威廉姆斯 (Nicholas Sims-Williams)著,毕波译《中国和印度的粟特商人》,周伟洲主编《西北民族论丛》第10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39页。汉语的萨宝或萨保受到粟特文的影响,即来自粟特文s’rt p’w。
吉田丰在粟特文第5封古信札中找到的s’rt p’w,即汉文史料中的萨保,是“队商首领”的意思。史君墓粟特文铭文第6 行,释读为“他从皇帝那里[得到?]凉州萨保(s’rt p’w)的[称号?]”。s’rt p’w在第10、12行也有,吉田丰认为是s’rt p’w,后者见古信札第 5 号,这种拼写似乎是一种补充缩写形式。[注][日]吉田丰《西安新出史君墓志的粟特文部分考释 》,《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北京:中华书局,2005 年,第33页。同时在汉文铭文第1、6、11、12 行四次出现萨保,表明汉文萨保译音应来自粟特文s’rt p’w。萨保汉文音译的语源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 但粟特文s’rt p’w的语源问题仍有待研究。[注]杨军凯《北周史君墓双语铭文及相关问题》,《文物》2013年第8期,第51-52页。佛教经典中出现“萨薄”一词,与中亚以及中原地区的萨宝都与经商活动有关。佛经中的“萨薄”是出海经商的商队组织者或首领,“萨薄”这一称呼后来附会到佛陀身上。认为无论是在北朝、隋唐时期实际担任萨保或萨保府官职的个人本身,抑或唐人墓志中所记载的曾任萨保的其曾祖、祖、父,绝大多数是来自昭武九姓的粟特人。作为例外的翟姓,可能是高车人,也可能是粟特人;目前尚不知鱼国(鱼弘墓的检校萨宝出自鱼国)所在,但应为中亚或中亚北部的国家;焉耆是塔里木盆地的西域王国。所有萨保的出身,没有一个与印度有关,并且在古代文献中,萨保与萨薄是严格区分的。因此,不应在梵文中追寻萨保的原语,众多的粟特人担任萨保一职,更能说明萨保应当来自粟特文的s’rt p’w。[注]荣新江《萨保与萨薄:北朝隋唐胡人聚落首领问题的争论与辨析》,《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第3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140-141页。荣新江先生反对将萨薄与萨宝等同起来,认为两者从来没有出现过混用的现象。从萨薄与萨宝这两个名称来看,虽然梵文中的sārthavāha与商队的聚落首领之间关系不是很密切,而从“萨保”在汉文史料中来看,是以粟特胡人为主的聚落大首领,来管理其内部的政教事务。但也应该看到萨宝与佛教的传播以及佛教在中亚的传播与发展存在一定的关系。
“兴胡”在旅途中常遭抢劫,面对种种来自人为的或自然的灾难威胁,商胡只有结伴而行,才能保证旅途的安全。当商队达到一处丝路沿线的绿洲城市后,会住在驿馆里,当地官方也会提供方便。据敦煌文书P.2005号《沙州都督府图经》记载,敦煌西北有一个“兴胡泊”,“东西十九里,南北九里,深五尺。右在州西北一百一十里。其水咸苦,唯泉堪食,商胡从玉门关道往还居止,因以为号。”[注]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1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8页。沿途补充水,对于商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从湖泊的名称“兴胡泊”来看,因为有泉水,可为商队补充水分,还可休息,该地应该是古代商胡往返必经之地。商队时常要在野外休整或者露宿。Miho、益都图像上骆驼背负的大型包裹,里面可能就是用于露宿的毡帐。[注]郑岩《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264页。他们对于休息或露营的地方是有选择的。
从公元4世纪初到公元8世纪中叶,粟特人是丝绸之路上最为活跃的商业民族,他们一方面要得到北方游牧民族首领的保护;另一方面要求得中国中央和地方官府对他们进行贸易的认可,即发给过所。[注]荣新江《北周史君墓石椁所见之粟特商队》,第54页;《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第233页。绿洲城镇特别重要,它们能够帮助商队顺利地穿过沙漠,这些绿洲城镇可以为商旅提供补给,使商人、牲畜恢复体力,因而成为重要的商业贸易中心。在沿线绿洲城市,他们会入住驿馆、客馆,当地官府会保护他们的安全,到市场进行交易也更为便利。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商队一般是沿着沙漠的边缘或者沿着山边行走,而沿着山边行走,这样会更容易找到水源,很少有商队直接穿过大沙漠。从陆路丝绸之路沿途的遗址进行考察,就会发现商队从长安出发,沿着河西走廊,到敦煌后,分为两道,南道与北道都是沿着塔里木盆地边缘行走的。
西安北周安伽墓石棺床第5幅为野宴商旅图,画幅高63厘米、宽29.7厘米。依内容可分上、下两部分,上半部分雕刻野宴图,下半部刻绘商旅图。[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著《西安北周安伽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32、33页,图二九。商旅图画面中央立三人。左侧者剪发,身着橘红色长袍,双手持一瓶,抬头右视。中间者身着褐色紧身长袍,后背中央及下摆为红色,脚蹬黑色长靴,右肩背一白色口袋。右侧者剪发,身着红色衣,衣袖黑色,腰间束白布,上勒三道黑带,脚蹬黑色长靴。后两人皆背身而立。三人下方两头毛驴背驮黑色口袋左右奔走,左侧有繁茂的树,树下静卧两只羊,右侧骆驼背负重物卧地休息。
史君墓石屏风N1高 0.83米,宽0.25米,画面内容反映的是商队野外露宿和贸易的场景,可分为上下两部分。[注]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北周凉州萨宝史君墓发掘简报》,《文物》2005年第3期,第29页,图五〇。画面上部中心位置为一帐篷,门帘上卷,帘上栖有两只小鸟。帐篷内盘腿坐一男子,头戴宝冠,着翻领窄袖长袍,腰束带,右手握一长杯,左手置于腿上,脚穿长靴。帐篷外树木茂盛,空中有飞翔的两只大雁。帐篷前靠右侧铺设有一椭圆形毯子,上面跪坐一位头戴毡帽的长者,着翻领窄袖长袍,腰束带,带下悬挂腰刀,右手握长杯,左手微前曲,两人对坐,作饮酒状。帐篷两侧有3位侍者,左侧两位,右侧一位。帐篷门前和椭圆形毯子之间卧有一犬,作回首状。帐篷的下方为4个男子率领的商队,有两匹骆驼、两匹马和一头驴,商队中间有2位男子正在交谈,两匹驮载货物的骆驼跪卧于地正在休息。
Miho美术馆收藏石棺床也有一幅商队休息图,画面分上下两部分,上部有两个披长发的突厥人坐在穹窿顶帐篷里,形象高大者可能是一位首领;另一人可能是这位首领的仆人,手中端盘,正在向首领端送食物。帐外有一大罐,有三位披肩长发的人,面向帐篷之门席地而坐;另有两人也是披肩长发,站立,马背上的驮物都被卸下。下部分为狩猎图,有两人正在猎杀奔跑的动物,外侧一人短发,似为粟特人;内侧一人披肩长发,应为突厥人[注]荣新江《Miho美术馆粟特石棺床屏风的图像及其组合》,《艺术史研究》第4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12页,图7b。。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穹窿顶帐篷与安伽墓、史君墓在形制上十分相似。
将商队行进中的场面与狩猎场面放在一起,表现了狩猎与经商是粟特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狩猎能够保持其传统的勇敢、尚武精神,使他们能世代保持其民族特质,而经商是其赖以生存的物质保障,所以说,狩猎与经商活动是粟特人精神和物质生活的反映。
炎热的天气使商队不得不在途中的某一地方进行躲避。法国学者在论述埃及和红海之间的商路及其商贸联系时,举出商队在瓦笛·梅尼白天歇息时刻在背阴处的铭文,因为那里有能遮阳的岩石,其中明确记载商队经过的文字记录有两次,时间为从公元前2年及公元6年。[注][法]博伦著,魏邀宇、吴旻译《经由埃及东部沙漠和红海而建立起来的罗马帝国与东方诸国的商业联系》,《法国汉学》丛书编辑委员会编,陈星灿、米盖拉等主编《考古发掘与历史复原》,《法国汉学》第11辑,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39页,图10。
有一定规模的商队,他们不得不解决一个时刻面临的重大问题,即往来城镇之间的日常驻留问题。商队除了住宿驿站外,经常也在野外露宿,在人口稀少的地方,商队通常使用帐篷宿营,随之也增加了危险性。
三、商队的武装力量——雇用向导和护卫
法国学者布尔努瓦夫人(Luce Boulnois)认为:“每支商队的骆驼数目多寡不等,有50头、100头、甚至多达1000头。商人总喜欢结队而行,这是因为在遇到劫贼的情况下增强抵抗力量。最富有的人养一些弓弩手作为私人保镖,稍穷一点的就出一点钱求助于前者的保护。丝绸驮子特别沉重,而首饰、乳香和香料驮子虽然较轻,却特别贵重,西域胡族居民对此总是垂涎欲滴。”[注][法]布尔努瓦著,耿昇译《丝绸之路》,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第78页。驿站也为商队提供给养,一般地,只有在受到中原王朝管辖与统治的地区才设驿站。对于商队来说,他们也可能分段雇佣向导,或者全程就雇佣一个向导,如果是一个向导,这个向导与商队会存在一种长期的雇佣关系。就护卫来说,商队除了有自己的常备护卫外,再根据路途的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另外再雇佣临时护卫,这种临时护卫除了在当地雇佣外,可能还会由统治这一地区并与商队结成同盟关系的少数民族首领指派。商队中骑马者,要么是这个商队的首领,要么就是护卫,因为马驮不了很多东西,但是马的速度快,机动性强,适合担任侦察或在前探路等重要任务。
西安出土的史君墓商队行进图中走在最前面的两个骑马护卫腿部挂有“胡禄(箭囊)”,明显是护卫。在商队的最前面是两个骑马的男子,其中一位腰上悬挂着箭袋。两匹马后面是两头驮载货物的骆驼,骆驼后面有一头戴船形帽骑在马上的男子,右臂弯曲上举,右手握“千里眼”正在瞭望,[注]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北周凉州萨保史君墓发掘简报》,第20页,图二七(右)。应该是护卫中的首领,看其居于商队的中间位置,起着调度或分配任务的职责,从他骑在马上用“千里眼”观望前方的动作,推测这一段路程比较危险,常有强盗出没。另外,从图像中人物的形象看,商队的成员都是年轻力壮的青年男子,除了旅途的艰难不适合年长者外,安全因素是首先要考虑的。
虽然会雇佣一些武装人员在途中进行保卫,但有时仍然会遇到危险情况。德国学者克林凯特认为:“为了防御这种强盗,最好是和武装的商队结伴同行。旅客可以租用驮畜,也可以雇用向导,他把旅队领到某个地点,在那里又有熟悉下一段旅途的向导可以雇用。付钱的方式可以是铸币,或者如果是在丝路东段,也可以用规模统一的丝束或布匹,因此一路上不得不随身携带大量这类物品。”[注][德]克林凯特著,赵崇民译,贾应逸审校《丝绸古道上的文化》,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第11页。到了唐代显庆三年( 658) 灭西突厥汗国,于龟兹设立安西大都护府,控制整个西域、中亚地区后并在中亚设置羁縻府州。丝路沿线设置馆驿,交通安全畅通,粟特商队可以不必再组成大的商队,短途接力贸易更为有利,商队已没有必要进行长途贸易,小型商队则显得更加方便灵活。
关于商队在野外宿营时采取的防御措施,有“处位中营,四面环护”的记述,[注][唐]慧立、彦悰撰,孙毓棠、谢方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第119-120页。说明商队在野外宿营时,采取“团营”形式。商队需要有一个德高望重的人来处理旅途中的日常事务及随时可能发生的危险,玄奘曾被一支五百人的商队推为商主,可知商主一般由威信较高的人担任,并不一定具有很强的是经济实力。《宋高僧传》卷三《悟空传》中记载悟空回国时在覩火罗国也提到了商队的商主。[注][宋]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51页。
商人采取结队贩运的方式,是由当时的交通状况及社会状况所决定的。丝路沿线自然条件相当恶劣,沿途强盗出没,严重威胁着商侣的安全。商人们只有结成商队,依靠团体的力量,才可能克服长途跋涉,完成兴生求利的任务。中世纪阿拉伯、欧洲商队都配有自带武器的专职保镖。唐代被商人雇佣运输货物、驱驮驮马的“作人”又称作“赶脚”、“脚夫”,他们是商业活动中的主要劳动力,[注]程喜霖《唐代过所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74页。从吐鲁番过所文书可知,往来西域沙碛长途贩运的行客,必须雇佣当地认路而又强壮的作人赶脚。
四、考古资料显示的粟特人与突厥民族之间的关系
粟特人是中古时期活跃在丝绸之路上一支重要的中亚民族,因擅长国际商业活动而长期扮演着丝路沿线物质交换与文化传播的角色,在中西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粟特诸王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是北方游牧汗国的附属国,粟特人的东来贩易,先后受到北方游牧民族,如柔然、嚈哒、突厥、回鹘等汗国的保护,粟特人很早就和突厥人建立了良好关系,这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环境决定的。
公元6世纪后半叶,突厥兴起,将东自中原,西至拜占庭边界的北方大片地区统一在其政权之下,这为粟特人拓展其商业势力创造了良机。粟特商人为了保证他们商队的安全,必须与这些游牧政权保持良好的关系。前辈学者已敏锐地发现伊兰民族与涂兰民族的关系。[注]岑仲勉《突厥史集》(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111页。在Miho博物馆明秀藏品北朝石棺床、虞弘墓、安伽墓中,“均有披长发的阿尔泰系突厥人形象与短发的伊朗系之粟特人或波斯人形象”[注]姜伯勤《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北京:三联出版社,2004年,第107页。。近年来中国境内发现的入华粟特人石棺床上出现的突厥人与粟特人交往的场面,给我们在图像上提供了粟特人与突厥关系密切的有力证据,也为我们了解粟特民族与突厥民族在宗教、文化上的联系提供了新的资料,从而更能印证文献中记载的粟特人在突厥汗国政治、商业活动中的重要作用。
已有学者根据入华粟特人石质葬具上的图像研究了粟特与突厥的密切关系,荣新江先生说:“天山北路和漠北地区是突厥直接统治地区,而塔里木盆地的西域诸王国,也是以西突厥为宗主国。因此,与突厥关系密切的粟特人,必然是要先和突厥人打交道,在突厥汗国庇护下东行贩易。所以粟特聚落首领萨保需要与突厥结盟,来保证商队往来平安,并且稳固殖民聚落组织。”[注]荣新江《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第377页。在古代丝绸之路沿线,哪一个政治势力在商队经过地区处于统治地位,商队就要千方百计与之结好,商队首领与丝路沿线当地游牧政权建立广泛的人际关系,以便获得保护及提供便利并确保商队安全运营。某一段路程要通过这个部族的领地,就要获得当地部落的支持,以便顺利到达下一个目的地。另外,商队首领与当地首领会面的地方,往往是商队休息、补充给养的地方,从入华粟特人石质葬具图像中可以看出丝绸之路上的粟特人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密切关系。
在突厥强盛时,出于对丝路利益的共同兴趣,游牧的突厥族和擅长经商的粟特人经常相互协作,成为6-8世纪“东西方贸易的担当者”。[注]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83、264页。安伽墓石棺床上出现设盟与继承仪式、突厥首领访问粟特部落,粟特萨宝与突厥首领共同宴饮以及共同狩猎的场面。Miho石棺床上有共同组成商队外出经营,突厥人参加粟特葬礼,与粟特人和嚈哒人一起出行的场面。[注]荣新江《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第364-368页。因为在丝路上长途贸易,面临诸多危险,经常会遭到强盗的抢劫,他们必须到得北方游牧民族政权的保护,因此,他们之间的会盟恐怕是一个经常举行的仪式。安伽墓屏风右手第三图,为一波斯系粟特人与突厥人会盟图,[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著《西安北周安伽墓》,第31页,图二八。因为Miho博物馆之北朝祆教画像中的G图,也是会盟图。[注]荣新江《Miho美术馆粟特石棺屏风的图像及其组合》,《艺术史研究》第4辑,第199-221页。图像可解释吐鲁番出土《高昌宁朔将军造寺碑》中“同盟”一词的含义,该碑记载高昌麴氏赴突厥汗庭结为“同盟”,此“同盟”,即流行于游牧部落间的“会盟”。[注]姜伯勤《西安北周萨宝安伽墓图像研究——北周安伽墓画像石图像所见伊兰文化、突厥文化及其与中原文化的互动与交融》,《华学》第5期,第23-25页;收入姜伯勤《中国祆教艺术史研究》,第81-83页。与突厥关系密切的粟特人,必然要先和突厥打交道并搞好关系,在突厥汗国庇护下东西贩易,所以粟特聚落首领萨宝需要与突厥结盟,在粟特聚落萨宝在继承上获得突厥的认可,来保证商队往来安全。
《新唐书·西域传》载何国城楼上绘有突厥可汗。前苏联考古工作者在中亚康国首都阿夫拉西阿卜(Afrasiab)第23考遗址的1号房间内,发现了精美的壁画。德国学者莫德(Markus Mode)对壁画内容进行了研究,认为1号房间的壁画主要表现的是7世纪中叶康国国王拂呼缦(Vargoman)继位的场面,画面上方还特别表现了西突厥可汗,目的是为了体现粟特国王即位的正统性以及对其继承王位的认可。[注]M.Mode,Sogdien und die Herrscher der Welt.Türken,Sasanider und Chinesen in Historiengemälden des 7.Jahrhunderts n,Chr.Aus Alt-Samarqand[=Eurpäische Hochschulschriften.Reihe XXVII.Kunstgeschichte.Bd.162,Frankfurt a.M.(u.a.),1993,p.110. 参见荣新江《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第370页注[1]。壁画中出现的突厥人形象与草原上的突厥石人像非常相似。西墙上除了人物外,还画有立杆,其中右边立杆数目为十,代表西突厥十姓部落,即左五咄陆、右五弩失毕的意思;左边的立杆数为九,代表“昭武九姓”。[注]荣新江《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第371页。在片治肯特(Panjikent)壁画里,也出现了公元6-7世纪的突厥和其他游牧民族的武士形象,在片治肯特2号宫殿遗址发现的哀悼图上有剺面的场面。与《隋书·康国传》记载“婚姻丧制与突厥同”的说法属实。[注]蔡泓生《唐代九姓胡与突厥文化》,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24-25页。粟特本土发现的突厥人形象说明突厥与粟特关系密切,归因于粟特曾经属于突厥汗国的势力范围内的政治原因。“这两种意义相同的图像主题,应当有着共同的来源,即源自突厥开始成为粟特宗主国的时候,大约公元567年以后不久,而这种王位继承仪式的图形,也略微变换了一种模式,成为来到中国内地的胡人聚落首领权威的认定形式。”[注]荣新江《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第377-378页。从出土的石质葬具图像上看,除了表现聚落萨宝之子在继承上获得突厥的认可外,更多的是反映了粟特人与游牧首领共同狩猎、宴饮、会谈、出行的场面,尤其是粟特人与突厥人交往最多。粟特人与突厥首领结盟,最重要的就是为了保护商队在丝绸之路上的运营安全。
魏晋南北朝至隋朝,粟特商队已在中亚撒马尔干至长安的丝绸之路上频繁从事商业活动,这一段时期,中亚、西域先后有许多游牧民族登上历史舞台,中亚、西域一度在他们的统治之下。随着突厥统一漠北以西直到波斯的广大地区,东西贸易进一步繁荣,这时粟特人在国际化贸易中地位更突出。但商贸之道路控制在突厥人手中,为了保证入华贸易的顺畅,粟特人与突厥建立良好的关系是他们所采用的正确措施。
结语
商人采取结队贩运的方式,是由当时的交通状况及社会状况所决定的。粟特人经营的商品因具有高额利润,故而有很大风险。面对来自人为和自然的威胁,他们首先要克服山谷、沙漠、戈壁等险恶环境带来的困难,中古时期丝路路途中还时常会有盗贼出没,这就要求他们必须组成商队结伴而行,雇佣保镖和护卫,所雇用的向导一定对沿途交通地理条件都很熟悉。商队有时会住在丝路沿线绿洲城市的旅店和驿馆中,另外,商队有时也在野外露宿,并采取防范措施,才能保证旅途的安全。
粟特地区在古代经常处在外族势力的控制之中,在这种长时间的环境中,粟特人学会了如何适应新的社会环境以及依附于某一强大政权。从近年来发现的入华粟特人的石质葬具图像上反映的情况看,粟特人还要与游牧民族政权首领保持良好关系,他们的经商活动必须可到少数民族首领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