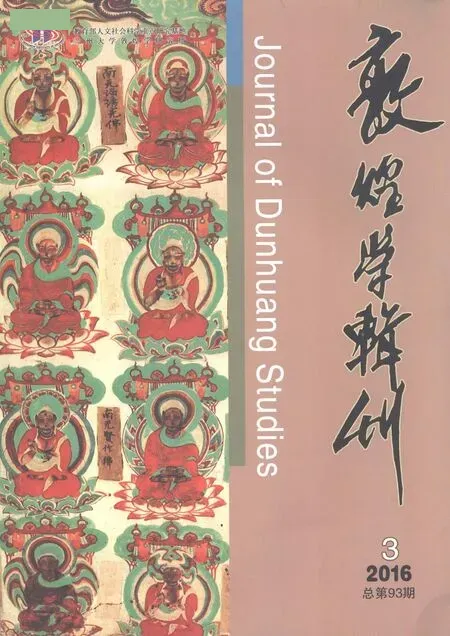敦煌写本《兔园策府》叙录及研究回顾
屈直敏
(兰州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甘肃 兰州 730020)
《兔园策府》又作《兔园册府》、《兔园策》、《兔园册》,唐杜嗣先奉蒋王李恽之命撰,原书早已散佚,敦煌写本《兔园策府》共有5个残卷,保存了该书的序文及第一卷。敦煌写本《兔园策府》的5个残卷散藏于英国伦敦博物馆(编号分别为S.614、S.1086、S.1722)、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编号为P.2573)、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编号为Дх.05438),其中略抄本有S.614、S.1722、P.2573、Дх.05438共4个写卷,双行小注本仅S.1086号1个写卷,且P.2573与S.1722可缀合。
一、写卷叙录
(一)英国伦敦博物馆所藏为:

按:向目题作《菟园册府》卷第一,说明:存132行。[注]向达《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文中简称向目),《图书季刊》新第1卷第4期,1939年12月,第400页;后收入向氏著《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06页。翟目题作《兔园策》第一,说明:存辨天地、正历数、议封禅、征东夷、均州壤五部,末题“巳年四月六日学生索广翼写了”。[注]翟林奈(Lionel Giles)《英国博物馆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文中简称翟目,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s from Tunhuang in the British Museum),伦敦:大英博物馆,1957年,第243页。刘目、施目题作《兔园策》第一,著录为:题记“巳年四月六日学生索广翼写了”,说明:《北梦琐言》十九云:“宰相冯道,形神庸陋……北中村墅,多以《兔园册》教蒙童,(刘岳)以是讥之。然《兔园册》乃徐庾文体,非鄙朴之谈,但家藏一本,人多贱之也”。[注]刘铭恕《斯坦因劫经录》(文中简称刘目),载王重民《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22页。施萍婷《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文中简称施目),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1页。黄目题作《菟园策》第一。[注]黄永武《敦煌遗书最新目录》(文中简称黄目),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6年,第22页。金目题作“《兔园策第一并序》,杜嗣先撰,共104行,首尾完整。题记:巳年四月六日学生索广翼写问□了。说明:1.序文残缺;2.题记后有杂抄‘高门出贵位,好木不良才,思见不得’一行;3.背书‘都卢八卷大□□’及‘索翼进□□园策□□;4.卷背有藏文十行”。[注]金荣华《伦敦藏敦煌汉文卷子目录提要》(文中简称金目)第1册,台北:福记文化图书有限公司,1993年,第52页。考校原卷,该写卷第一部分仅残存序文27行,第二部分残存序文3行,及卷1之《辨天地》、《正历数》、《议封禅》、《征东夷》、《均州壤》5篇。
图版:《敦煌宝藏》第5册,第152-156页;《英藏敦煌文献》第2册,第85-87页。

按:向目题作《菟园策府》,说明:存170行。[注]向达《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第402页;又《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第209页。翟目题作《兔园策府》卷一,说明:残存第2~4篇,可能是7世纪写本。[注]翟林奈《英国博物馆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第243页。刘目、施目题作《兔园册府》,说明:残存议封禅、征东夷及论天地阴阳者三篇。[注]王重民《敦煌遗书总目索引》,第131页。施萍婷《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第34页。黄目题作《兔园册府》。[注]黄永武《敦煌遗书最新目录》,第39页。金目题作“《兔园册府》,存162行,首尾具残。说明:1.中题—议封禅、征东夷;2.内有残缺;3.第七世纪写本”。[注]金荣华《伦敦藏敦煌汉文卷子目录提要》第1册,第52页。考校原卷,该写卷保存了《兔园策府》卷1第2篇《正历数》的一部分、第3篇《议封禅》的全部及第4篇《征东夷》的一部分。
图版:《敦煌宝藏》第8册,第569-574页;《英藏敦煌文献》第2册,第226-233页。
3.S.1722号(翟目7281号):卷子本,有界栏,土褐色纸本,首尾并残,卷长17.25英尺(25.5×525.78cm),存172行,每行17~22字不等,起序文之“一戎,先动云雷之气”,讫第4篇《均州壤》之“鸡犬闻于郊境,谨对。兔园策府第二”。该写卷在《兔园策府》卷1末题“《兔园策府》卷第二”,当是第2卷的开始,惜未能继续抄写,后面续抄毛亨传、郑玄笺《毛诗·周南·关雎诂训传》卷第一,起“周南关雎诂训传第一毛诗国风”,讫“周南之国十有一篇,凡三千九百六十三字”。共抄录了11篇,91行,3963字。两者笔迹相同,当是同一人抄写。
按:向目题作(1)《兔园策府》卷第一,说明:存172行;(2)《毛诗诂训传》,说明:存《周南关雎诂训传》第一,91行。[注]向达《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第405页;又《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第212页。翟目题作(1)《兔园策府》卷第一,说明:《兔园策府》卷第二仅存题名。(2)《毛诗·国风》,说明:首题“周南关雎诂训传第一毛诗国风”,末题:“周南之国十有一篇,凡三千九百六十三字”。[注]翟林奈《英国博物馆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第243页。刘目题作(1)《兔园翰(?)府》卷第一、第二,(2)《毛诗(周南关雎)诂训传》卷第一,《毛诗·国风》。[注]王重民《敦煌遗书总目索引》,第143页。施目题作(1)《兔园策府》卷第一(尾题)、卷第二(首题),(2)《毛诗诂训传》卷第一,尾题:周南之国十有一篇,凡三千九百六十三字。[注]施萍婷《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第52页。黄目题作(1)《兔园策府》卷第一、卷第二,(2)《毛诗周南关雎诂训传》卷第一。[注]黄永武《敦煌遗书最新目录》,第62页。金目题作“《兔园策府》卷第一、二,存173行,首缺尾完;同卷其他资料:(正)毛诗诂训传——国风周南”。[注]金荣华《伦敦藏敦煌汉文卷子目录提要》第1册,第52页。考校原卷,该写卷共有两部分,第1部分仅残存《兔园策府》序文及卷1之“辨天地、正历数、议封禅、征东夷、均州壤”等5篇,卷二仅有题名。第2部分为《毛诗·国风·周南》11篇。《诗经》部分仅有序及经文,并无毛传及郑笺内容,金荣华将其定名为《毛诗并序(周南关雎——麟趾》[注]金荣华《伦敦藏敦煌汉文卷子目录提要》第1册,第24页。、许建平定名为《毛诗(诗大序——麟之趾)》。[注]许建平《敦煌经籍叙录》,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38-139页。另外,黄目、施目及陈铁凡《敦煌本易书诗考略》、张锡厚《敦煌毛诗诂训传的著录与整理研究》以《毛诗》抄于写卷背面,郑阿财、朱凤玉《敦煌蒙书研究》则以《毛诗》抄于写卷正面,《兔园策府》抄于写卷背面,皆误。[注]陈铁凡《敦煌本易书诗考略》,《孟子学报》第17期,1969年,第172页。张锡厚《敦煌毛诗诂训传的著录与整理研究》,《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第44页。郑阿财、朱凤玉《敦煌蒙书研究》,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65页。
图版:《敦煌宝藏》第13册,第77-81页;《英藏敦煌文献》第3册,第120-122页。
(二)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所藏为:
1.P.2573号:卷子本,土褐色纸本,首尾并残,卷中间有残缺,卷长27.1×38.5cm。存16行,每行17~22字不等。首题“《兔园策府》卷第一并序杜嗣先奉教撰”,起“易曰:利用宾于王”,讫“远述幽冥之慌,德未静于”。残片1抄有“高延德状”一通。残片2抄有愿文、符咒两通。
按:罗译伯目题作《兔园策府》(杜嗣先撰)。陆译伯目题作《兔园策府》之起端,杜嗣先撰,背书高延德书牍。[注]P.Pelliot,Catalogue de la collection de Pelliot,manuscrits de Touen-houang(文中简称伯目),罗福苌译《巴黎图书馆所藏敦煌书目》(文中简称罗译伯目),载《国学季刊》第1卷第4期,1923年,第717-750页。陆翔译《巴黎图书馆敦煌写本书目》(文中简称陆译伯目),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7卷6期,1933年,第40页。王目题作《兔园策府》卷第一,说明:存开端十六行,杜嗣先奉教撰,背有高延德书一通。[注]王重民《敦煌遗书总目索引》,第267页。施目题作《兔园策府》卷第一并序,杜嗣先奉教撰,背有高延德状一通,符咒两通。[注]施萍婷《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第324页。黄目题作《兔园策府》卷第一(与斯1722号可缀合),高延德书一通、道教愿文、残书简三残片。[注]黄永武《敦煌遗书最新目录》,第666页。考校原卷,该写卷纸张、字迹与S.1722相同,内容可以衔接,可缀合,缀合后则为首尾完整之《兔园策府》卷第一并序,有题名、卷次、作者及序文。且陆目、王目、施目误将两残片作背面。
图版:《敦煌宝藏》第122册,第168-169页;《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6册,第44页;《敦煌书法丛刊》(东京:二玄社,1983年)第18卷,第68-70页;李德范校录《敦煌西域文献旧照片合校》(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第67页。
(三)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所藏为:

按:该写卷残存第3篇《议封禅》9行,第4篇《征东夷》3行,且下部残缺。
图版:《俄藏敦煌文献》第12册,第139页。
二、误定名为《兔园策府》之写卷考辨
除上述5个写卷之外,还有P.2524、P.4636、S.78、S.79、S.2588、P.2721等6个写卷,有学者将其误拟作《兔园策府》,但其实并非《兔园策府》之属,现试作考辨如下:
分部之P.2524等写卷,王目著录作“《古类书》(不知名),册叶装,存十七叶,内包括三十九部,始‘王’,讫‘神仙’。”但在索引部分,王氏将敦煌写本中不知名类书分为6种,其中“分部”的P.2524、P.4636、S.78、S.79、S.2588等5个写卷,王氏“疑即《兔园策府》”。[注]王重民《敦煌遗书总目索引》,第266、483-484页。刘师培《古类书残卷之二》提要云:“古类书四百五行,前无书名,末有空行二,亦不标书名卷第。……其为何书,今不克考。以《崇文总目》、晁氏《读书记》及《玉海》所引《中兴书目》证之,惟虞世南《兔园册》十卷,纂古今事为四十八门,皆偶俪语;陆贽《备举文言》二十卷,摘经史为偶对类事,共四百五十二门;李途《记室新书》三十卷,采掇故事,缀为偶俪之句,分四百余门,略与此书相似”。[注]刘师培《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共19种),《国粹学报》第79期,1911年,第7-9页;后收入《刘申叔遗书》第63册,1934年南宁武氏校本,1936年印成,第26-29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据南宁武氏校印本影印,第2015-2017页;郑学檬、郑炳林主编《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文献卷(一)》,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第44-47页。胡道静从王重民之说,认为“如果它是《兔园策府》,则《兔园》的部目面貌,已可为我们所掌握”,并引刘氏提要为之佐证。[注]胡道静《中国古代的类书》,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88-90页。罗振玉将该写卷定名为“古类书”,[注]罗振玉《罗振玉校刊群书叙录》,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8年,第329页。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02页。罗译伯目题作“类书断篇”,[注]罗福苌译《巴黎图书馆所藏敦煌书目》,第740页。陆译伯目作“艺文类萃诠说,精写本”[注]陆翔译《巴黎图书馆敦煌写本书目》,第36页。。王三庆《敦煌本古类书语对研究》一书则将P.2524、P.4636、P.4870、S.78、S.79、S.2588等5个写卷定名为《语对》,其中P.2524为较全之写本,其余4个写卷为部分之异抄。[注]王三庆《敦煌本古类书语对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年,第4-12页。又《敦煌类书·研究篇》,台北:丽文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第97-99页。此后,黄永武《敦煌遗书最新目录》、施萍婷《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等均据王氏定名著录。
P.2721号写卷,黄永武《敦煌遗书最新目录》及《敦煌宝藏》题作“《杂抄》一卷并序(即《兔园策府》)[注]黄永武《敦煌遗书最新目录》,第679页;《敦煌宝藏》第123册,第478页。。据该写卷原有题名及学界研究,该写卷实为《杂抄》(或名《珠玉抄》、《益智文》、《随身宝》)无疑,并非《兔园策府》。[注]参见[日]那波利贞《唐钞本〈杂抄〉考——唐代庶民教育史研究の一资料》,《支那学》卷10,1942年,第1-91页,后收入《唐代社会文化史研究》第2编,东京:创文社,1974年,第236-260页。周一良《敦煌写本〈杂抄〉考》,《燕京学报》第35期,1948年,后收入《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又收入周一良著《唐代密宗》,钱文忠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214-222页。张政烺《敦煌写本〈杂抄〉跋》,载《周叔弢先生六十生日纪念论文集》,香港:龙门书店,1950年,第251-257页;后收入《张政烺文史论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48-253页。朱凤玉《敦煌写本〈杂抄〉研究》,《木铎》第12辑,1988年,第120-138页。
三、历代著录及研究回顾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类书类》著录有:《兔园策》10卷,唐虞世南撰。奉王命纂古今事为四十八门,皆偶俪之语。至五代时,行于民间,村野以授学童,故有遗下《兔园册》之诮。[注][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校证》卷2,孙猛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尤袤《遂初堂书目》著录有《兔园册府》,但未著录卷数和作者。[注][宋]尤袤《遂初堂书目·类书类》,丛书集成初编本,第24页。王应麟《困学纪闻》载:《兔园册府》30卷,唐蒋王恽令僚佐杜嗣先仿应科目策,自设问对,引经史为训注。恽,太宗子,故用梁王兔园名其书。冯道《兔园策》谓此也。[注][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全校本)卷14《考史》,[清]翁元圻等注,栾保群等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670页。《宋绍兴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卷1《别集类》及卷2《类书类》均著录有《兔园策》10卷,未著录作者。[注]叶德辉考证《宋绍兴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卷1别集类,又卷2《类书类》,光绪癸卯(1903)仲春叶氏观古堂刊本,第77、52页。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28《经籍考五十五·子部类书》著录有:《兔园策》10卷,按语引晁氏之说。[注][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28《经籍考五十五·子部类书》,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827页。《宋史·艺文志第七》著录为:杜嗣先《兔园策》10卷。同书卷209《艺文志第八》著录为:杜嗣先《兔园策府》30卷。[注]《宋史》卷208《艺文志第七·集部别集类》,又卷209《艺文志第八·集部文史类》,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5352、5408页。陈第《世善堂藏书目录》著录为:虞世南《兔园册》10卷。[注][明]陈第《世善堂藏书目录》卷上《类编类》,丛书集成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38页。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著录为:《兔园策》9卷,未著录作者。[注][日]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总集家》,古逸丛书本,光绪十年(1884)甲申遵义黎氏影旧钞本刊于日本东京,第45页。此外,孙光宪《北梦琐言》[注][宋]孙光宪《北梦琐言》卷19《诙谐所累》,贾二强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349-350页。、《旧五代史·冯道传》[注]《旧五代史》卷126《周书·冯道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656-1657页。、《新五代史·刘岳传》[注]《新五代史》卷55《刘岳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632页。载有宰相冯道遗下《兔园册》之讥,但不载作者及卷数。法藏敦煌写本P.2721、3649《杂抄》载《兔园策》乃杜嗣先撰,但不及卷数。[注]《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7册、第2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002年,第357、229页。英藏敦煌写本S.5658《杂抄》载《兔园策》为杜司先撰(“司”当作“嗣”)。[注]《英藏敦煌文献》第9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4-45页。从上述历代著录可知,关于作者、书名、卷数颇不一致,作者有杜嗣先、虞世南两说,书名有《兔园策》、《兔园册》、《兔园策府》、《兔园册府》四说,卷数有10卷、30卷、9卷三说。由于该书早已散佚,故鲜为人知,然而因敦煌文书中发现了该书的残卷,遂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众多学者纷纷撰文探讨该书的作者、卷数、成书年代及性质。
较早对《兔园策府》进行研究的学者有王国维、那波利贞等,王氏撰《兔园策府》残卷的跋文,对该书的作者、卷数、成书时间进行了简要考述。王氏认为该写卷是贞观时写本,而该书盛行于五代,至宋季尚存。对于作者是杜嗣先还是虞世南,王氏认为“殊未可臆定”,但怀疑并非虞世南所撰,可能是因为虞世南撰有《北堂书钞》而“嫁名于彼”。对该书的卷数,王氏认为“此书盛行之际,或并三十卷为十卷”。其成书时间在李恽“改封蒋王、安州都督”时(贞观七年至永徽三年)。[注]王国维《唐写本〈兔园策府〉残卷跋》,《观堂集林》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1014-1015页;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第205页。按:李恽“改封蒋王、安州都督”在贞观十年,王氏作“贞观七年”,误。参见《旧唐书》卷76《太宗诸子列传》(第2660页)、《旧唐书》卷3《太宗纪下》(第46页)、《新唐书》卷2《太宗皇帝纪》(第36页)。罗振玉编纂《鸣沙石室佚书》共收敦煌遗书18种及提要,不仅刊布了P.2573《兔园策府》的影写本,还将王国维跋文作为该写卷的提要收录。[注]罗振玉《鸣沙石室佚书》,《罗雪堂先生全集三编》第5册,台北:大通书局,1989年,第1559-1560、1953-1954页;又载《敦煌丛刊初集》第6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第401-402、795-796页;《鸣沙石室佚书正续篇》,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45-46、439-440页。日本学者那波利贞移录了P.2573《兔园策府》残卷,并探讨了该书的成书年代及性质,指出该书撰成于永徽三年(652)至上元年中(674-675)约二十年间(即成于显庆、龙朔、麟德、乾封、总章、咸亨年间),是适用于庶民普通教育的教科书。[注][日]那波利贞《唐钞本杂抄考——唐代庶民教育史研究の一资料》,《支那学》卷10,第1-91页,后收入《唐代社会文化史研究》第2编,第236-260页。上述学者仅据P.2573《兔园策府》一个残卷立论,并未见其余4个敦煌写本,故难免有误而遭人批评,如周一良认为“王静安先生《唐写本〈兔园策府〉残卷跋》据卷中‘治’字不缺笔,推断其书成于贞观末蒋王恽为安州都督时。那波氏据‘兔园’之名,谓当是永徽三年蒋王恽除梁州都督后令杜嗣先撰,未免失之于固也”。[注]周一良《敦煌写本〈杂抄〉考》,《燕京学报》第35期,1948年,后收入《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第345-350页;又收入周一良著、钱文忠译《唐代密宗》,第214-222页。1957年吕思勉著《隋唐五代史》亦略涉《兔园策府》,认为该书“题名之异,盖由纂集本非一人,无足为怪,独其卷数不同耳。……合观诸文,知士大夫之尚此书,初盖以供对策之用,然后有所重者,惟在其俪语而不在其训注,盖有录其辞而删其注者,故卷帙止三分之一”。[注]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下),上海:中华书局,1959年初版,198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第1116页。然而吕氏的研究仅据唐宋史料考述,并未提及敦煌写本《兔园策府》。此外,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初探》认为王应麟《困学纪闻》所载《兔园策府》的作者为杜嗣先是正确的,且假定“曾经有过两种本子,至少其中之一是用‘偶俪之语’记‘古今事’,并且广泛流行在民间,用作蒙学读物的”。[注]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初探》,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年,第53-54页。此后,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有学者关注敦煌写本《兔园策府》,并进行深入研究。
20世纪80年代台湾研究敦煌写本《兔园策府》的学者主要有郭长城,所著《敦煌写本〈兔园策府〉叙录》一文,首先对P.2573、S.614、S.1086、S.1722共4个写卷进行了叙录,并对王国维的跋文进行补证,断定该书成书年代的上限在唐太宗时,下限则不得晚于唐昭宗。同时,郭氏还将P.2573、S.1722写卷缀合作为底本,以S.614、S.1086为校本,对敦煌写本《兔园策府》进行了简要校录。[注]郭长城《敦煌本兔园策府叙录》,台湾《敦煌学》第8辑,1984年,第47-63页。又郭氏著《敦煌写本〈兔园策府〉逸注补》一文,主要依李注《文选》之例,据原注体例对敦煌写本《兔园策府》所缺注文进行补注,力求恢复或接近原貌。[注]郭长城《敦煌写本〈兔园策府〉逸注补》,台湾《敦煌学》第9辑,1985年,第83-106页。郭氏在此前研究的基础上,撰成《敦煌写本〈兔园策府〉研究》硕士论文,该文分研究篇、校注篇、附录写本图片三部分,研究篇主要对《兔园策府》的性质、作者、成书时代及背景、流传过程和价值,敦煌写本《兔园策府》写卷缀合、叙录、原注引书及价值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考定该书的作者为杜嗣先,其成书年代当在高宗显庆三年(658)之前,蒋王李恽徙封梁王时,即永徽三年(652),其卷数当以原卷为三十卷,后删并为十卷之说较合于事实,指出该书是在科举以策取士背景下,杜嗣先奉王命而作的自撰式别集,其性质当属于常科之“试策”。敦煌写卷研究部分主是对4个写卷进行叙录、缀合、原注引书及其价值进行全面考察,指出原注引书具有文字校勘、佚书辑校、明学术风尚的价值。校注篇分本文校记、全书校定本、原注补逸三部分,重点在于文字校勘、补全逸注。[注]郭长城《敦煌写本〈兔园策府〉研究》,中国文化大学硕士论文,1985年。
20世纪90年代以降,台湾研究敦煌写本《兔园策府》的学者主要有王三庆、叶国良、郑阿财等。王三庆著《敦煌类书·研究篇》对敦煌写本《兔园策府》做了简要概述,有关该书的作者、成书年代等,皆从郭长城之考论。[注]王三庆《敦煌类书》,第117-119页。王氏概述之文,后经池田温译为日文,收入《敦煌汉文文献·类书》。[注]王三庆《类书·兔园策府》,池田温译,载《讲座敦煌》卷5《敦煌汉文文献》,东京:大东出版社,1992年,第385-386页。又《敦煌类书》之《录文篇》和《校笺篇》分别对敦煌写本《兔园策府》的P.2573(原书误作P.2575)、S.1722、S.614、S.1086共4个写卷进行录文和校注。[注]王三庆《敦煌类书》,录文:第519-536页;校笺:第874-887页。1992年台湾学者叶国良在台北古玩店“寒舍”发现《徐州刺史杜嗣先墓志》原石及其妻墓石实物,并依其格式,抄录原文,于1995年在《台大中文学报》上发表该墓志的录文及考释。据墓志记载,杜嗣先生于贞观八年(634),显(原作“明”,避唐中宗李显讳改)庆三年(658)释褐蒋王府典籤,麟德元年(664)授昭文馆直学士,先天元年(712)九月六日薨,时年79岁,所撰《兔园策府》及杂文笔,合廿卷,见行于时。叶氏认为《兔园策府》撰成于杜嗣先为蒋王僚佐的六、七年间,即其时年25至31岁间。[注]叶国良《唐代墓志考释八则》,《台大中文学报》第7期,1995年,第62-65页;后收入氏著《石学续探》,台北:大安出版社,1999年,第127-133页。然而遗憾的是,学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未注意到叶氏的考释。郑阿财、朱凤玉著《敦煌蒙书研究》一书将《兔园策府》归入习文知识类蒙书,从写本概述、录文、作者与卷数、性质与流传等方面对敦煌写本《兔园策府》进行了考述,认为《兔园策府》的作者为杜嗣先,原作有训注,计“三十卷”,后因删去其注而并为“十卷”。五代时期此书为习文的童蒙读物,后沦为乡野村童用来习文的教材。[注]郑阿财、朱凤玉《敦煌蒙书研究》,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63-279页。此外,郑阿财还在《敦煌蒙书析论》、《敦煌文献与文学》、《敦煌蒙书》等论著中对敦煌写本《兔园策府》4个写卷进行了简要概述。[注]郑阿财《敦煌蒙书析论》,《第二届敦煌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汉学研究中心,1990年,第224页;又《敦煌文献与文学》,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第257页;《敦煌蒙书》,载《敦煌与丝路文化学术讲座》第1辑,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2003年,第128-152页。
20世纪90年代大陆研究敦煌写本《兔园策府》的学者主要有吴枫、周丕显、刘进宝等,吴枫认为“从蒋王恽一生来看,贞观十年到太宗去世,是最得志之时。这期间太宗子魏王泰为抬高自己声誉,于贞观十五年(614)组织人编写《括地志》一书,蒋王恽也极有可能在此期间仿魏王泰而编《兔园策》”。[注]吴枫、郑显文《〈珠玉抄〉考释》,载黄约瑟、刘健明合编《隋唐史论集》,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93年,第214-221页。周丕显《敦煌古钞〈兔园策府〉考析》一文,从蒙书的发展历程、写本概述、古代著录、历代评述、写本过录、个人管窥等六方面,对敦煌写本《兔园策府》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周氏认为《兔园策府》“是为适应唐宋时代农村士子科举考试而编写的应科目策的举业用书,是广泛意义上的蒙书”。[注]周丕显《敦煌古钞〈兔园策府〉考析》,《敦煌学辑刊》1994年第2期,第17-29页;后收入氏著《敦煌文献研究》,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142-165页。刘进宝《敦煌本〈兔园策府·征东夷〉产生的历史背景》一文,指出该书产生于贞观十年(636)至上元中(674-676),而《征东夷》是唐太宗父子面临征伐高丽之困境下的产物。一方面,面对高丽的威胁,不得不积极攻打且多次失败;另一方面是大臣们反对,又不得不解释说明。“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作为太宗之子的蒋王,令其僚佐拟出《征东夷》的策问,既可以让僚佐们广泛讨论,征得各方面的意见,以便供最高统治者参考。又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唐代科举考试注重社会现实、学以致用的积极方面”。[注]刘进宝《敦煌本〈兔园策府·征东夷〉产生的历史背景》,《敦煌研究》1998年第1期,第111-116页;又载《1994年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文集·纪念敦煌研究院成立50周年(宗教文史卷上)》,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333-342页。日本学者本田精一则通过对历代载录《兔园策》的考察,指出《兔园策》有虞世南撰和杜嗣先撰两种,而《兔园策府》则为杜嗣先撰,进而对中国古代庶民儿童教育的初级识字教材和高级教材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述,概述了宋代以降儿童识字材材的系谱。[注][日]本田精一《〈兔园策〉考:村书の研究》,《九州大学东洋史论集》第21号,1993年,第65-101页。杜嗣先墓志的揭出,虽然没有引起大陆及港台学者的重视,但日本学者高桥继男、伊藤宏明、金子修一等却给予了高度关注,并以此为据,对日本国号及遣唐使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注][日]高桥继男《最古“日本”——“杜嗣先墓志”の绍介》,日本专修大学、西北大学合作科研项目编《遣唐史の见た中国と日本》,东京:朝日新闻,2005年,第316-330页;叶国良著《唐〈杜嗣先墓誌〉著録の経緯》,高桥继男译,《専修大学社会知性開発研究センター東アジア世界史研究センター年報》第5号,2011年,第189-191页。伊藤宏明《〈徐州刺史杜嗣先墓志〉杂感》,《鹿儿岛大学法文学部纪要人文学科论集》第63号,2006年,第73-88页。金子修一《杜嗣先墓誌の大象、その他》,《国学院杂志》第109卷第2号,2008年,第27-29页。
2000年以来,大陆学者对敦煌写本《兔园策府》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郝春文编著《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对敦煌写本《兔园策府》的S.614、S.1086、P.2573+S.1722共4个写卷进行了较为精确的释录,并附有校勘记,是目前学界较好的释录本。[注]郝春文《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3卷,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42-354页;第5卷,2006年,第80-111页;第7卷,2010年,第476-498页。笔者曾撰《敦煌本〈兔园策府〉考辨》一文,对《兔园策府》的作者、成书年代、卷数等进行过考订,认为该书有可能是众手所成而题一人之名,其成书年代最晚不迟于贞观十七年(643),至于该书的卷数极有可能原书为有注文的30卷本,后在传抄过程中因删节注文遂成了10卷节略本,《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著录的9卷本有可能是残存的节略本。[注]屈直敏《敦煌本〈兔园策府〉考辨》,《敦煌研究》2001年第3期,第126-129页。由于当时未睹叶国良有关《杜嗣先墓志》的论文,故对成书年代的推测确有不当。王璐的硕士论文《敦煌写本类书〈兔园策府〉探究》,从《兔园策府》的作者、思想内容、性质特点,及其与唐代类书编纂、科举、教育的关系等方面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该文最大的贡献是从《俄藏敦煌文献》中发现了Дх.05438《兔园策府》残片,并据《杜嗣先墓志》考定《兔园策府》的作者为杜嗣先,撰成年代在唐高宗显庆三年(658)至麟德元年(664)之间。[注]王璐《敦煌写本类书〈兔园策府〉探究》,西北师范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论文,2006年。此后,王璐相继发表了《敦煌写本类书〈兔园策府〉考证》、《〈兔园策府〉与唐代类书的编纂》两文。前文主要是在硕士论文的基础上对《兔园策府》的成书年代作了进一步的探讨,认为杜嗣先所撰《兔园策府》是相对于张大素撰《策府》之“旧策”而成的“新策”,其写成年代为公元661至664年间。后文主要探讨了《兔园策府》与唐代类书编纂的关系,指出偶句之类书体例不是自《初学记》,很有可能始自《兔园策府》。[注]王璐《敦煌写本类书〈兔园策府〉考证》,《唐都学刊》2008年第4期,第81-85页;又《〈兔园策府〉与唐代类书的编纂》,《西安文理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第24-27页。牛来颖《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之《儒学章·蒙书》认为《兔园策府》属敦煌蒙书中通俗类书与书抄,并对其写卷进行了简要介绍,指出《兔园策府》的立题“集中了太宗时期煌煌治世的文治武功”,对策提问的重点是“与时事关系之紧密和朝廷命运修关之大事”,“反映太宗、高宗朝廷之重大国策及迫切问题”;特别强调《征东夷》、《均州壤》“与朝政关系最为密切,前者反映出当时朝廷军事征伐高丽的绵长艰辛历程,后者所阐发的均平土宇、任民乐迁的理念”;进而指出《兔园策府》所反映的基本理念,在实际生活中是付诸实施的。[注]张弓主编《敦煌典籍与唐五代历史文化》(上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32-135页。按:张氏认为《兔园策府》写卷包括P.2720V,显然有误。葛继勇《〈兔园策府〉的成书及东传日本》一文,结合敦煌文书、《杜嗣先墓志》和日本文献的相关记载,对《兔园策府》的成书及流播日本等问题进行了梳理,指出杜嗣先撰写《兔园策府》的时间当在其任蒋王僚佐期间,即显庆三年(658)至麟德元年(664)之间,并据墓志载杜嗣先曾参与接待8世纪初来华的日本遣唐使,推测其所著《兔园策府》很可能在8世纪初已传入日本,并作为启蒙教材而广为流播。[注]葛继勇《〈兔园策府〉的成书及东传日本》,《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第196-199页转204页。郭丽《〈兔园策府〉考论——兼论唐代童蒙教育的应试性倾向》一文对《兔园策府》的作者、卷数、成书年代等进行了探讨,且认为发现了Дх.05438号《兔园策府》残片。该文考定《兔园策府》的作者为杜嗣先,成书年代约在龙朔二年(662)至麟德元年(664)年之间,其性质是高级阶段的童蒙教育用书,反映了唐代童蒙教育教材为科举服务的特征和童蒙教育的应试性倾向。[注]郭丽《〈兔园策府〉考论——兼论唐代童蒙教育的应试性倾向》,《敦煌研究》2013年第4期,第93-100页。从郭氏全文的考论及材料的使用来看,并没有超出前人的范围,显然对前人的研究成果关注不够全面。此外,还有一些简要介绍性的研究论文,如:胡道静《中国古代的类书》对《兔园策府》及敦煌石室写本4个写卷进行了简要介绍。[注]胡道静《中国古代的类书》,第118-122页。姜亮夫《莫高窟年表》[注]姜亮夫《莫高窟年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11页。、李冬梅和寒沁《敦煌写本类书概述》[注]李冬梅、寒沁《敦煌写本类书概述》,甘肃省历史学会、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编《史学论丛》第7集,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7-11页。、李冬梅《唐五代敦煌学校部分教学档案简介》[注]李冬梅《唐五代敦煌学校部分教学档案简介》,《敦煌学辑刊》1995年第2期,第66页。、白化文《敦煌遗书中的类书简述》[注]白化文《敦煌遗书中的类书简述》,《中国典籍与文化》1999年第4期,第50-59页。等也对敦煌写本《兔园策府》的写卷及相关内容进行了简要介绍。
从上述可知,敦煌写本《兔园策府》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仍然有些问题值得深入探讨,如对该书内容所反映的社会理念、策问所关注的社会问题及其历史背景等仍有继续深入研究的空间,特别是整理出一个较为完整的录文校注本,为学界提供参考,是目前敦煌学界亟需努力完成的紧迫任务。
——论唐代类书编纂的特点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