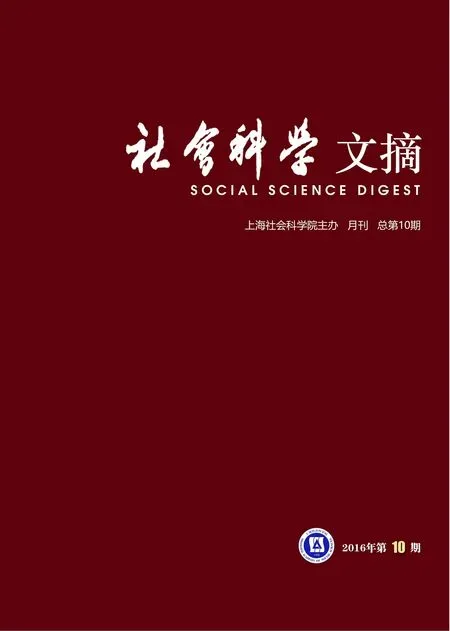政治审慎与作为一种智慧的政治学
文/陈华文
政治审慎与作为一种智慧的政治学
文/陈华文
在政治学说史上,审慎(phronesis,prudence)作为一种古典德性,主要涉及在纷繁复杂的实践活动中对于善的谋划,是一种能够把握理论规范又能结合具体语境予以判断从而正确行动的品质。国内关于审慎的研究多侧重于其哲学分析,不过近些年政治审慎的话语也逐渐被重视,政治学界开始将审慎作为治理之道而讨论相关的政治问题。这种进路实际上是注意到了政治学作为一种智慧的传统,而在这种传统中,审慎毫无疑问是最值得借重的理论资源: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里,审慎和政治学(politik ē)被认为是同样的品质。
在现代语境中重申作为一种智慧的政治学,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现代政治对工具性治理技艺的依赖日益趋重,也将国家推向一种纯粹的缺乏向善性的工具性国家。与此相应的政治理论或是脱离复杂的政治实践,或是将政治实践简化为纯粹应用性的政治技艺。正如哈贝马斯所指出的:“社会哲学在走向科学的道路上丧失了政治学曾经作为智慧和机智所具有的能力。”作为一种在实践中知道伦理上该如何正确行动的理智德性,审慎所包含的实践性、价值关怀和慎思能力,都可能有助于克服国家治理的技艺化、碎片化和抽象化,同时也能让我们更加清晰地发现,政治学在以实践为其品格的同时还需要以哲学为导向。
实践性:政治审慎而非政治技艺
以审慎作为视域理解作为智慧的政治学,最先凸显的问题是政治学的实践品格,而审慎与技艺的区分是理解该问题的重要出发点。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审慎与技艺所处理的都是可变化的事物,而且它们都是合乎理性的品质,但是他通过区分制作与实践而将技艺与审慎对立起来。技艺是制作理性的德性,而审慎则是实践理性的德性。制作的目的是外在于制作活动,而实践的目的则在于其自身。审慎关注的是行动本身,做得好就是目的,是一种能够正确行动的德性。与技艺以某个外在于行动的生成物作为对象不同的是,审慎的对象是人的行动。
在实践与制作之区分的基础上强调审慎与技艺的区别,其政治意义是非常明显的。阿伦特反对以技艺的方式去理解政治活动,人就其是一个技艺者而言已经被工具化了,从而丧失了其价值。政治领域并非是技艺者的工具化世界,而是一个实践者在行动中彰显其德性的公共空间。公民在这种公共空间通过行动向彼此彰显自己的德性。这个意义上的政治所强调的是公民的行动以及公民在行动中所展现的德性,而不是支配性的政治权力结构,审慎德性或判断力因而在其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审慎的实践性对政治智慧提出较高要求,原因在于审慎的实践性不同于科学技术或一般原则的简单应用。审慎在实践中的作用不同于一般原则在具体情境中的应用。洪汉鼎认为实践智慧(审慎的另一种译法)与科学技术的应用是不同的,后者是一种简单的一般对具体的应用,是一种单纯地把个别纳入一般的线性过程;而实践智慧的践行决不是先有明确的一般,再将此一般简单地应用于具体事物,它往往需要根据具体情况去提出一般,并且往往需要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加以修正、补充和发展。审慎的领域,不允许我们简单地通过把具体事例归于普通规则来演绎正确的行为准则,而是需要不断地对具体情境进行考量,每一次行动都是一种判断和推论的过程。
政治审慎首先要注意到在原则的抽象性与实践的复杂性之间存在的鸿沟。任何普遍的规范的意义,只有在其具体化中或通过具体化才能得到真正的判断和确定。行为的全部原理只能是粗略的,而非精确不变的……因而,若强调审慎在道德领域与政治领域的重要意义,必然要注意到根据具体的情境审视一般原则,对之做出相应的调整,具体可以包括确定在此情境中适用何种原则或何种德性,甚或对一般原则予以修改和发展,而非像科学技术那样,把一般观念直接应用于具体条件中。
在这个意义上,审慎的实践性使得审慎作为一种德性,一方面为政治实践中的复杂性所需,另一方面又凸显出政治理论应该具有的实践品格。政治生活是一个复杂的领域,普遍规范的构建是基本的,但规范本身的有效运行也需要能获得正确和良好的实践。审慎的实践性恰要求公民或政治家或官僚等政治行动者对其行动具有反思和判断的能力,这种能力并不应由于制度的构建而被取消。同样,政治理论的现代发展也应吸纳审慎所要求的实践品格,避免割裂理论之普遍性与政治实践的具体情境,构建起一个独占性的真理式一般理论,从而将政治实践简化为一门纯粹应用性的政治技艺。不同于政治技艺,基于审慎的政治智慧则需要一再面对具体的情境。这些区分对于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如何纳入公民的审慎德性以及积极行动、如何纠正法律普遍性所带来的缺陷等重大的国家治理问题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向善性:政治审慎的伦理意义
审慎与技艺在始因上的不同还使得政治审慎与政治技艺之间存在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区分。行为的好是审慎的目的,这意味着审慎的行动必须是达成某种善,而技艺则只是为了生成某种外在于行动的目的,而无关乎其好或坏。审慎以善为目的,审慎者是能够辨清自己的善的人,政治上的审慎者则是能够辨清对城邦为善的政治家。审慎是同善恶有关的品质。因此,即使是一项行为能够完美地实现其目的,但如果行为是坏的,这也难言是善。
可见,审慎与否的判断标准并不在于最终的行动结果,还在于行动过程中的各种精神状态。审慎行为由始至终是德性的彰显过程,因而审慎作为一种德性,它要求行为者具备确定的性情。较之技艺,审慎更强调审慎者本身的伦理德性,也更强调行为本身的好,而不只是通过一个最终的结果来衡量。伽达默尔十分重视审慎与技艺的区别。在他看来,审慎与技艺都是知道何为(knowhow)的品质,但审慎是伦理上知道何为(ethical knowhow),而技艺则是技术上知道何为(technical knowhow),这实际上是强调了以善为目的是审慎与技艺这两种合乎理性的品质最重要的区别。技艺是关于具体行为的考量,是一种“具体的事物”或产物,而审慎则是“一生完全伦理的正直”。
这意味着基于审慎的政治智慧必然要求政治行动者本身具备有德性的品格,以及善在政治实践中也能够自行,而不只是实现某种外在于行动的目的。审慎的目的是实践本身,其所实现的目的最终也是善的,这意味着政治实践的结果也一定是好的。在政治行为的目的上,政治技艺与基于审慎的政治智慧因而有所不同的伦理要求,若认为政治是一种技艺,那么它所实现的是一个外在目的,而这个目的可以是中性的,对目的本身的伦理意义可不做要求。这种政治技艺服膺于政治权力的获取和维系,更容易形成权谋之术,但基于审慎的政治智慧则以善为目的,也要求政治实践本身具有伦理意义。
人类的善:政治审慎与理论智慧的竞争
亚里士多德认为理智德性包括审慎和理论智慧,并通过典范的对比将这两种理智德性对立起来。亚里士多德将阿那克萨戈拉、泰勒斯作为理论智慧的典范,而将伯利克里视为审慎的典范。自然哲学家阿那克萨戈拉与泰勒斯,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对于人类而言为好的事物是无知的;而政治家伯里克利这样的人能够辨清什么事物自身就是善的、对于人类而言是善的。这两种理智德性的对立表明了在道德-政治上的卓越与在哲学上的卓越这两种不同品种之间的竞争性,也进一步凸显了政治与哲学之间的冲突。
理论智慧与审慎的对象有着很大的差别。理论智慧指的是思考世界本质的能力,它关注世界如何运行。知识的对象是由于必然性而存在的事物,因此具有理论智慧的人所思考的是一些普遍的、必然以及永恒不变的东西。审慎所考虑的则恰就是可以变化的事物。亚里士多德认为审慎要考虑的对象是实践活动中的具体事务,而不再是柏拉图关于普遍原则的抽象思考。政治学与审慎关注的是与自己生活之利益相关的事情,而理论智慧思考的则是一些罕见的、重大的、困难的、超乎常人想象而又没有实际用处的事情。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明确指出哲学与政治学和审慎的区别,政治学和审慎要考虑的是人类的事物,是多变的;而哲学则是与所有存在物的善相关的唯一智慧。
亚里士多德将审慎与政治学视为关涉人类的善的品质,又认为理论智慧并不追求对人有益的事务,有理论智慧的人对自己的善和人类的善全不知晓,他们所追求的东西对于人类而言并没有什么用处,那么理论智慧如若不关乎获得幸福的手段,那么它对于追求幸福有何帮助?亚里士多德认为理论智慧并不直接研究幸福的问题,但它事实上也会导致幸福,不过这种方式有如健康本身导致健康一样,而不是通过医术而产生健康。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理论智慧与审慎之间的对立。不过,由于理论智慧本身不会直接关涉幸福的获得问题,那么可以运用理论智慧获得的东西以改进人们的生活进而帮助人们获得幸福的审慎或政治学,在幸福的问题上的权威是否真的能够高于理论智慧?
亚里士多德认为正如医学不优越于健康一样,审慎并不优越于智慧或理智的那个较高部分。这意味着审慎是为了服务理论智慧,而不是命令理论智慧。审慎和政治学都不能因为其对人类善的考虑而超越于理论智慧。政治学是管理和支配城邦的学科,它在城邦的一切事务上都能发布命令,但如若认为它能够命令众神,那也是荒唐的。理论智慧高于审慎,从而也意味着政治活动中所获得的幸福低于从事哲学生活所获得的幸福。
就与理论智慧的比较视域看来,审慎的政治意义也是十分明显的。首先,审慎服务于理论智慧,这意味着审慎和政治学的意义是通过对城邦生活的管理,为城邦生活提供良好的秩序,使得公民能够更好地享受其健康。这种政治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是工具性的,因为它是公民健康或沉思生活的手段。其次,理论智慧高于审慎,这也意味着政治行动者,包括具备审慎德性的政治家和公民,所获得的只是二等的幸福。除了政治生活之外,他们还应该有着更高的境界,政治生活并不是最高等的幸福,还有比其更值得追求的生活方式。
以智慧为要义:政治审慎的哲学导向
前文的叙述容易导向这样一种错误印象:以为政治审慎既然与实践相关,那就完全不需要普遍知识。但事实上,审慎是两种理智德性之一,它也以智慧为其题中要义。审慎本身可以理解为智慧在实践过程中的具体表现。在亚里士多德之前的哲学家们就没有严格区分审慎与智慧。亚里士多德虽然明确区分了审慎与理论智慧,但是他并不想让人们以为审慎只与具体知识相关,而不需要普遍的知识或普遍知识的指导。亚里士多德并不认为普遍的东西对审慎的人并不重要,相反对于审慎而言尤其重要的具体知识需要一种更高的能力来指导它。
政治生活中的判断或谋划应当受到一种政治学的智慧所指导。这里要回应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理论对于审慎的作用。政治家或公民在进行政治谋划或政治判断时,是否完全不需要具备理论?理论究竟是削弱还是增强了政治实践过程中的审慎?有论者指出,“理论”被视为实践的对立面;不少从亚里士多德那里挖掘审慎而持有公民共和倾向的研究者,也否认理论的作用,因为理论始终无法促进公民们在一个共同体之内通过相互的慎思而培育出实践所需要的审慎德性。但是,也有论者指出这种观点恰是误解了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坚持认为,理论通过帮助审慎与那些备受欢迎却具有误导性的观点保持距离并对之进行批判,以抵制共同体或政体中常见的僵化的道德主义,从而能够培育灵活性”。亚里士多德关于雅典政体的归纳分类,以及对最佳政体和什么适合于一个特殊政体所做的详尽讨论,都表明关于政治的普遍性知识对于具有审慎的政治家而言,无疑意义重大。
上述讨论在现代政治语境中所指向的则是政治科学与政治哲学的重要性。任何力图通过突出公民协商而消解政治科学乃至政治哲学的做法都是不明智的。当然,这里并不是要否认公民参与政治的意义,而是力图指出理论本身之于政治判断的重要性。政治中的审慎需要普遍性的知识,唯此才能避免政治实践中因为过于强调情境性而导致政治生活和政治决策的随意性。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政治审慎需要普遍的知识并不意味着以纯粹理想的进路理解甚至支配政治实践。相反,政治领域中应警惕政治理想主义对政治的伤害。从政治学与审慎是同一种品质这个意义上看来,政治理想主义或者任何缺少审慎观念的学说都是不适宜的。他们的批评虽是针对哲学家而言的,但实际上也意味着政治家对完美的追求实际上是不明智的。
政治审慎与实践有关,需要在具体情境中考虑对于人类而言为之善的事物。政治始终是变化不居的世界,任何普遍原则不可能直接适用于具体情境当中,对普遍存在或普遍原则的完美追求与纯粹信念,只会陷入某种浪漫主义当中,反而损害了普遍原则本身。只有基于对具体情况的把握,才能做出良好的政治判断,而不会落入哲学王的恣意决断当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政治审慎就完全不需要普遍知识。与具体事情相关的政治实践仍然需要一种普遍的知识来指导,就此而言政治哲学或政治科学对于政治实践而言仍然是至关重要的。
结语:政治学的经验品格与哲学导向
政治审慎并不能因其总是要考虑变化的具体情境而被简化为应用性的政治技艺,反而正是由于政治审慎是关于公共事务的慎思,更是需要对人类的善有着更为普遍的、根本的把握能力。政治行动者在具体情境中对善的把握也应该受到哲学的指导。哲学构建目的和提供整全性框架,而政治家则在实践中结合其信念与责任,去实现最大的善。正是如此,罗尔斯才认为归纳表达良好社会的恒定条件及真正利益,是学习哲学的人该做的事情,但在实践中辨认出这些条件和利益,则要由政治家来做。就这一点而言,政治家要遵循审慎结合具体情境与普遍性原则的要求,而哲学也正是在它与政治的这种微妙关系中进入了政治。
概而言之,政治学是处理变化的具体事务的能力,它以实践为品格,从而不能是纯粹理想的、抽象的和工具性的;同时,政治学还是一种智慧,它要求政治行动者具有普遍知识,以哲学为导向。只有同时具有具体的知识和普遍的知识,政治学作为一种智慧的能力和伦理意义才充分体现出来:在具体情境中把握对于整个国家乃至人类而言为之善的事物。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摘自《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原题为《政治审慎:重申作为一种智慧的政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