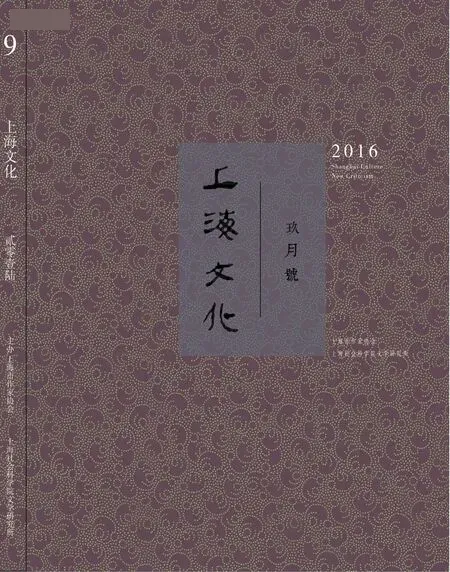《群山之巅》的叙述
张亦辉
《群山之巅》的叙述
张亦辉
1
开篇第一章叫“斩马刀”,端得是个好标题。这样的标题自有一股传奇似的张力与悬念感,对读者的阅读发出了强烈的召唤。
开头第一段出现的人物却不是蒙古骑兵之类,而是乡村屠夫辛七杂(猪杂碎的杂,杂种的杂,七杂这个名字的确暗含着人物谜一样的身世):
龙盏镇的牲畜见着屠夫辛七杂,知道那是它们的末日太阳,都怕,虽说他腰上别着的不是屠刀,而是心爱的烟斗。
一下子用烟斗置换了屠刀,多么迅疾多么别致。人世间不仅有屠刀的寒冷,也有烟斗的温暖。
我想,寒冷中的温暖,差不多就是迟子建所有小说叙事的内在蕴籍。
2
然而接下来并没有写烟斗,而是叙述太阳火点烟:
抽烟斗时他先摸出凸透镜,照向太阳,让阳光赶集似的簌簌聚拢过来,形成燃点,之后摸出一条薄如纸片的桦树皮,伸向凸透镜,引燃它,再点燃烟斗。
王安忆曾说迟子建总是知道生活中哪儿有小说,这话主要是指迟子建的多产以及题材的广泛。的确,迟子建的小说叙事优质高产地进行了三十来年(我记得苏童曾经称赞过迟子建写作状态的罕见的持续性与稳定性),似乎永不会有枯竭之虞。
具体到叙述上,我觉得迟子建的一大特色(几乎是她的风格性标志),是她总能发现并捕捉一些介于真实与虚幻之间的细节或事物,从而使她的叙述显现一种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的品质,一种童话般的轻盈的品质,一种浪漫的诗意的品质。这里的太阳火点烟就是这一类事物与细节的典型。
在叙写这样的事物与细节时,迟子建的语言与文笔格外别致和越轨,她的想象力也格外大胆与妖娆,于是,我们就读到了阳光赶集似的簌簌聚拢过来这样的句子,感受到了迟子建叙述中的独特风格与情趣(这样的笔致在第一章里就可以读到不少,比如稍后写辛七杂不杀家禽,所以鸭子也敢晃着膀子与他并行;辛七杂试刀时砍向一片春天的红柳。刀起刀落之际,一片红柳倏然折腰,倒伏在林地上,宛如落霞。)
而当迟子建顺水推舟地告诉我们:“太阳火烧的烟斗,有股子不寻常的芳香”时,我们还没搞清这是不是生活真实,但却已然沉浸在一种文学性的美妙里了。
3
当然,这一章叫“斩马刀”,所以,写完烟斗与太阳火之后,迟子建的叙述又回到了刀,就像一个出去玩的孩子又回到了家。这样的叙述自有一种一波三折的灵动与随兴,自有一种从容与淡定,也自有一种小说叙事的丰饶与杂多。
作为屠夫,辛七杂应该有许多屠刀,迟子建主要写了两把,一把是九寸杀猪刀(原有的七寸刀宰杀那些绿色养殖的大猪有些局促了);另一把就是斩马刀(逸出屠宰的实用领域,只挂在墙上看,辛七杂“要拥有一把干干净净的刀,不然睡不踏实”)。叙写两把刀的同时,也顺便引出了镇里的两个人物:绣娘和王铁匠。
在叙述斩马刀的时候,迟子建使用的又是那种风格化的诗性语言:
辛七杂将斩马刀磨得雪亮,挂在厅堂的墙上,那面墙从此就拥有了一道永恒的月光,从未黯淡过。
这把没沾过一滴血的斩马刀,那些年杀倒的,不是红柳,就是碧草,锋刃横溢着植物的清香气,好像他家吊着一只香水瓶。
窃以为,童话与诗意,是迟子建小说叙事的另外两个关键词。当然,这里的童话不是简单与稚嫩的意思,而是指涉纯朴与真挚之境。
4
可是,这把月光般的斩马刀,毕竟不是童话里的事物,而是生活中的杀器。先强调它从没沾过一滴血,其实只是迟子建叙述中的欲擒故纵法,按照契诃夫的说法,那把故事前面挂在墙上的枪,在故事的后面一定会打响,这把斩马刀在这一章结束前果然饮血讨命,闯下大祸。
辛七杂的养子辛欣来,用这把斩马刀,杀了辛七杂的妻子王秀满,然后在逃亡深山之前,还强奸了精灵一样的安雪儿,破了龙盏镇的神话。
这个情节,是整部长篇的楔子,它埋下了故事的悬念或种子。
5
安雪儿是绣娘的孙女,法警安平的女儿,她是个侏儒,是个精灵古怪的像是从童话里走出来的人物。迟子建偏爱这样的人物,这样的人物可以说是迟子建小说的标志性符号。通过叙写这样的人物,迟子建告诉我们,平淡的生活中始终有传奇,而生命与人性永远是个谜。
“辛七杂和安雪儿在龙盏镇都是被怕的主儿。辛七杂是被牲畜怕,安雪儿是被人怕。”
因为安雪儿能够预卜人的死期。在迟子建笔下,她几乎是个通灵的人,被人称为“安小仙”,她是龙盏镇的神话。
她从小就显出与众不同,除了喜欢在黑暗中喃喃自语,还喜欢握着炉钩子四处乱窜,敲打那些能发声的器物,在她看来,不发声的事物就是死的,发声的才是活物。当然,许多活的事物在她的敲打下都变成死的了,如玻璃杯、花盆和碗。迟子建特别擅长叙述这样的细节,童话般的,想象独特的,充满文学的趣味与魅力。
这个个子定格在九十二公分的侏儒,还拥有一种天生的无师自通的本领:刻碑。成人后,她就开了个石碑坊,专门给人刻墓碑。
因此,写安雪儿的第二章就叫“制碑人”。
而辛欣来在石碑坊破了安雪儿的真身之后,一夜之间,这个被万口一声地塑造成神的侏儒,就众口一词地被打入了魔鬼的行列。
6
经过了过渡性的第三章“龙山之翼”之后,迟子建的叙述来到了精彩的第四章“两双手”。
这一章,除了讲述几个法警行刑与殡仪馆理容师为死者理容的故事(这几个故事虽然被迟子建的叙述赋予了童话色彩,但都很接地气,颇具时代意义,体现了迟子建的叙事对现实的介入与关注。与迟子建其他偏于历史的长篇不同,《群山之巅》触及了诸多社会问题,直面现实中的黑暗面,比如腐败,比如投毒事件与器官移植等),重点就是叙述了法警安平与理容师李素贞两双手的相遇。
一双是执行死刑的手,一双是为死者理容的手,平时被人嫌弃和冷落,这样的两双手“一经相握,如遇知音,彼此不愿撒手”。两个婚姻情感都有缺憾的不幸男女,就这样相遇并且相爱。两双特异的手(不是常见的目光或抽象的心灵)的邂逅相遇,那种长久相握后感受到的弥足珍贵的温暖,以及随之萌生的爱意,显得那么新颖那么别样,同时又那么真实而感人。
迟子建的小说总是在叙述并呼唤这样的寒冷中的温暖。在北极光闪烁的寒冷之地长大的人,也许会本能地迷恋这样的温暖吧。
在这一章的另一个地方,写到李素贞与那个患肌肉萎缩症瘫痪在床的丈夫时,迟子建又一次叙述了这样的温暖与迷恋:
每当她的手触着死者冰冷的脸颊时,她对丈夫的怜惜,油然而生!尽管他萎缩得形同枯叶,但毕竟还有温度!一个人身上的温度,多么令人迷恋啊。
只有真正洞悉了生死的人才能写出这样的怜惜吧,只有心中有太阳的作家才能写出这样的温度吧!写出了这样的怜惜与温度的迟子建,真的让我想起了契诃夫。
7
精灵的安雪儿湮灭了,可肉体的安雪儿却奇迹般地重新开始了生长。第六章就叫“生长的声音”。
安雪儿先是通过事物的参照(灶台、窗台、衣柜、院子里的柞树与石碑等)发现自己长个了,然后,她看见镜子里的脸和五官也庞大了,而衣服和裤子却都小了,“胸部的扭扣就像火线上的士兵,神经绷得紧紧的”。迟子建的比喻常常如此任性随兴但恰当之极。
接下来,迟子建叙述了安雪儿的惊讶与兴奋:
安雪儿捂着咚咚跳动的心,对着窗外飞来的燕子说:“我长个了”,对着沉默的石碑说:“我长个了”,对着树下的蚂蚁说:“我长个了”,对着夜晚的星星说:“我长个了”,对着她头颅压出的深深的枕痕说:“我长个了”!
你看看,迟子建的叙述总能从燕子、石碑、蚂蚁和夜晚的星星这样的童话般的轻逸与浪漫,迅疾而又安全地降落在“深深的枕痕”这样底蕴独特分量扎实的生活细节之上。这是迟子建的风格,同时也是她的天赋吧。
当然,迟子建还叙述了生长的声音:
夜里躺在床上,万籁俱寂时,她能听见身体生长的声音。她周身的关节嘁哩喀嚓地响,像是举行着生命的大合唱;她的肚腹好像蒸腾着沸水,噗噗直叫;她的指甲嫌疆域不够辽阔,哗哗地拓展着势力范围;她的头发成了拔节的麦子,刷刷地疯长着。
如果说前面几个声音与比喻显得稍稍虚拟与夸张,那么最后把头发比喻成拔节的麦子,却足够硬实而又精准。
这一章还有两处叙述也特别可圈可点。一处是对阳光与早晨的叙述,体现了迟子建对森林的熟稔与观察的细致:
她终于盼来了一个美丽的早晨!阳光好得能看清蜘蛛在树间扯下来的细弱蛛丝。
另一处则是对冬夏太阳的大胆的比喻与想象:
松山地区的冬天,太阳通常很低,低得就像一只吊在头顶的输液瓶,面色昏黄,无精打采。夏天的太阳却不一样了,它经过一个长冬的疗治,再经过一个春天的颐养,丰盈美丽,光芒四射!而且跟安雪儿一样长个儿了,高高在上!
这些叙述都那么自由随兴,那么灵光闪现,同时又那么具有原创性,显现了迟子建的从容与自信,也显现了她自觉的追求以及别样的才情。
8
谈一下迟子建写作中的一个小环节。那就是她时不时地会在叙述的过程中,凭借文字本身的组合、延伸或对俗语进行返璞归真的处理,自然而然地创造了一些叙述妙趣和语言韵味,没有任何刻意的痕迹,仿佛是天然巧合一样,就像是叙述之河中漂来的一段浮木,迟子建顺手把它捞了上来。这样的叙述体现了迟子建写作状态之放松之大气,它有点像作家送给读者的礼物,阅读时我们会禁不住会心一笑。
比如,第二章叙述安平与全凌燕的婚姻:
安平二十二岁结婚,新娘是长青县一小的音乐老师,生得娇小玲珑,名字叫全凌燕,大家说他们是“安全”组合,定能白头偕老。
我们很快就知道这是一种有趣的解嘲,因为这个组合其实一点也不安全。
比如同一章叙述安雪儿长个的情节:
她换下拖鞋时,才发现自己的脚,比个头长得还猛,鞋架上的鞋子,成心跟她过不去似的,全撂脸了,给她小鞋穿。
穿小鞋这个泛指的俗语终于被巧妙地还原为具体结实的生活细节。
再比如,第十四章叙述开布店的刘瘸子给辛开溜出主意:
刘瘸子虽瘸,但出的主意不瘸,辛开溜接受了。
对瘸字的延伸化处理,可谓饶有意趣。
9
细读迟子建的小说,你一定会惊叹于她塑造人物的能力。《群山之巅》写了几十个有名有姓有血有肉的人物,迟子建真正做到了写一个,活一个。那些人物仿佛不是虚构的产物,而是迟子建生活中的亲戚和朋友,是她的外婆,是她的二大爷,是她的表哥表姐,是她的闺蜜,是她两小无猜的童年玩伴,是她的隔壁邻居。
在迟子建的小说里,几乎无法区分谁是主要人物谁是次要人物,仿佛众生平等,就像杂花生树,每朵花都有独特的色彩与清香,每朵花都不一样,每朵花都只是它自己。
即使是一个对故事的进展无甚影响的“戏份”很少的人物,迟子建的叙述也细心周到绝不含糊。比如红日客栈有两个金字招牌,一个是服务员林大花,另一个,就是厨师葛喜宝:
鄂伦春人,四十来岁,扁平脸,小眼睛,大嘴巴,一头鬈毛,又矮又胖,喜欢烈酒。
这幅肖像就画得细致准确,决无半点草率之处,鬈毛对应鄂伦春族,矮胖对应厨师,喜欢烈酒则与接下来的叙事息息相关:
葛喜宝从古约文乡迁居到龙盏镇,是因为他妻子因病去世后,他常常酒后去山上的墓园,睡在妻子的坟旁,也不管年幼的孩子。有一年冬天,他醉倒在坟旁,几近冻僵,被拉烧柴的人救下。葛喜宝活下来了,但被冻掉两个脚趾,从此他走路就跟鸭子一个风格了。安泰的妻子葛秀丽怕弟弟长此下去,会疯癫了,劝他离开古约文乡。赶巧那年刘小红的客栈开张,正缺一个厨师,就把他介绍来了。
通过迟子建的叙述,我们牢牢记住了这个特别的厨师:一个矮胖的、鬈毛的、缺了两个脚趾走路像鸭子的、悲伤于自己的不幸命运的人。但他是红日客栈的金字招牌,他在那儿重新安身立命,他的鄂伦春风味菜烧得好极了。
葛喜宝被冻掉的一定是两个脚趾而不是手指,否则他的烹调技术就会受影响了,他的菜就做不了那么好吃了。
10
细读迟子建的小说,你一定也会惊叹于她对日常生活风俗人情的无限熟稔与无限热爱。
作为一名优秀的作家,迟子建不是在观察生活,更不是在体验生活,而是真正进入了生活融入了生活,这种进入和融入的程度,只有游进水里的鱼可以比拟。
迟子建就生活在生活中,生活是她的文学矿脉,这片蕴藏在高纬度的寒冷之地的矿脉像大海一样不会枯竭,所以,迟子建能够源源不断地从中提炼出文学的黄金和生命的盐。
一个真正熟悉生活热爱生活的作家才能把豆腐写得如此神似如此诱人:
安雪儿盯着老魏的豆腐担子,木板上那些莹莹欲动的豆腐,把她馋坏了。
你再看看迟子建怎么写新摊的煎饼:
新摊的煎饼鲜香酥脆,是小姐的身子,经不起摔打。
辛开溜用犁杖以物易物换了一把钐刀,催生了龙盏镇一年一度的旧货节,你看迟子建对农具对生活器皿如数家珍般的陈列与叙述:
就这样,犁杖换钐刀,镰刀换耙子,镐头换锄头,人们在瑟瑟秋风中以物易物,补充了农具,也收获了快乐。第二年秋末,旧物交换不仅限于农具了,家具、炊具也进了交易集市,箱子换柜子,太师椅换饭桌,碗架换炕琴,茶壶换暖水瓶,洗脸盆换铝皮闷罐,瓷盘换酒盅,品种越来越丰富,旧货集市就此兴起。而到了第三年,旧物交换的范围再次扩大,衣裳鞋帽、家具和学习用品也登台了。花衣服换布鞋,裤子换围裙,花瓶换烛台,镜架换铅笔盒,帽子换手套,储蓄罐换针线盒,甚至铅笔换橡皮,绑腿换头绳,五花八门,无所不有。
这种不厌其烦的叙述,绝不是简单机械的罗列,需要的决不仅仅是耐心与细心,更需要对生活的了解与熟悉,需要对生活的热情与钟爱。读到如此丰富如此杂多的器具与什物,会让我们重新想起生活的芜杂、多样与宽广。我记得加缪在未竟之作《第一个人》的一条自注中说过这样的话:书必须有分量,充满物体与肉体。
顺便来欣赏一下迟子建在《群山之巅》之前创作的长篇《白雪乌鸦》的开头,对一百年前的哈尔滨傅家甸街市的叙述:
霜降在节气中,无疑是唱悲角的。它一出场,傅家甸的街市,有如一条活蹦乱跳的鱼离了水,有点放挺的意思,不那么活色生香了。那些夏日可以露天经营的生意,如理发的,修脚的,洗衣服的,代拟书信的,抽签算命的,点痦子的,画像的,兑换钱的,卖针头线脑的,擦皮鞋的,不得不收场,移到屋内。不过锔缸锔碗的,崩爆米花的,照旧在榆树下忙碌着——他们的活计中有炭火嘛。
我们不妨试着罗列一下童年露天集市的生意种类。你一定想不起居然还有点痦子的!
11
细读迟子建的小说,我们还会惊叹于她对山河自然对动物植物的倾情书写与动人描摹。
迟子建的叙事空间就像是一片原始森林,里边布满了云彩和飞鸟,生长着松树、桦树与柞树,活跃着众多小动物,盛开着各种各样的花朵。
迟子建喜欢在叙述中频频使用比喻修辞,在她笔下,万物有情,而人与自然与花草树木都相通相融,这除了让人想起她在乡村森林长大的童年生涯,也让人想起天人合一的文化传统,让人想起《诗经》中的比兴手法,想起“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在获得鲁迅文学奖的短篇《雾月牛栏》中,迟子建为那头在雾月出生的小牛取的名字叫“卷耳”,我们可以理解成刚出生的小牛耳朵卷卷的可爱样子,但卷耳也是一种野菜的名字,另外,《诗经》的一首诗歌就叫《卷耳》)。我以为迟子建的叙述精髓中,确乎包含着比兴元素。
你看迟子建怎样叙述格罗江:
只要寒流不再成为统治者,这条江便在暖风的爱抚下,春心荡漾,在四月中下旬,涣然冰释。当冰排像熠熠闪光的报春花,从江上呼啸而过,格罗江的眼睛就睁开了……格罗江的眼睛里是少有的深沉、清澈、明媚。
你看迟子建如何叙述那清晰地倒映在江上的白云:
白云倒映在江水的时刻,盘旋在江上的鸥鸟,会俯冲下来,用翅膀轻轻拍打着,它们大约想不通,天上的奇迹,何以到了人间?
安雪儿不知道给松鼠吃什么好,去问单四嫂,迟子建让单四嫂这样回答:
松鼠牙齿好,凡是带壳的东西,它没有不喜好的!松子,瓜子,花生,榛子,核桃,对它来说都是亲娘!
好一个亲娘!
我想重点谈谈迟子建写花。
迟子建最爱写的可能就是花了,她的叙述真有点像是天女在散花。在她的笔下,花几乎是世间一切美好事物的象征。比喻时她总喜欢拿花做喻体,她喜欢写人与花之间的相通相融。
比如,迟子建叙述被强暴后身心恢复期的安雪儿:
绣娘在山中骑马,见多了被马蹄踏过的野花。它们折了腰,花枝零落,抖抖颤颤,一派颓唐。可过不了几天,也许就在一夜之间,那些生命力顽强的,又在清风雨露中傲然抬起了头!绣娘相信安雪儿是这样一枝花儿。
比如,当葛喜宝嘲笑辛开溜的衣服有那么多布丁时,辛开溜抖着白胡子说:
补丁是衣裳的花瓣,每个花瓣都有故事,你懂个屁!
在迟子建笔下,连马蹄印也像花朵:
罗掌柜喜欢雪后骑马,马蹄在雪地留下蹄印,在他眼里是冬天的花朵!
甚至喝完的酒盅也是一朵花:
安平将酒盅口朝向唐眉,让她看底儿,仿佛在向她献上一朵牵牛花。
安雪儿在分娩之前为自己铺的是杜鹃花的花床,以至于要让降生在杜鹃花上的孩子姓杜。
就连弹片也被迟子建比喻成了花:
老人们正在议论辛开溜身上烧出的弹片,它们像逆时令而开的花朵,令人惊奇。
我们知道小说中第八章取名就叫“女人花”;而其中一个人物则叫林大花。
你再看迟子建写雪花:
初雪柔软,会形成妖娆的树挂,这时森林所有的树,又成了花树了!它们这时只开白花,无比灿烂!
你再看看迟子建写窗玻璃上的霜花:
霜花跟云彩脾性相同,姿态妖娆,变幻万千。它们有的像器皿,如锅碗杯盏;有的像动物,如牛马猪羊;有的像植物,如树木花朵;还有的像珠链,像房屋,像星辰,像田垄,像闪电,像人,像飞鸟。一扇挂满了霜花的窗户,就是一个大千世界。
特别有意思的是,迟子建在叙述了人与花与树与自然万物相融相通的同时,却叙述了辛欣来偷来的那把猎枪与子弹的不相配不相融。我认为这种反差与对比是解读《群山之巅》的一个重要隐喻或玄机。
当然,安雪儿这个人物,这个注定要被糟蹋的乡村精灵,是这部小说的另一个隐喻符号。所以,小说的结尾又回到了这个人物。
12
最后一章叫“土地祠”。经过了漫长的叙述的跋涉,小说终于来到了终点。
《群山之巅》的叙述虽然从容弥散,丰盈杂多,但整个故事结构却步步为营丝丝入扣,甚至有些过于完整和工巧,有些事先安排的痕迹。可小说的结尾却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精彩之极,而且惊悚之极。
安雪儿居然再一次被强暴了,在一个大雪天,在土地祠,这一次是那个半痴呆的单夏。安雪儿一边挣扎,一边向土地爷求救。
于是,迟子建写出了最后一句堪称卓越的叙述:
一世界的鹅毛大雪,谁又能听见谁的呼唤!
那种苍茫无助,那种孤独与绝望,那种锥心之痛,那种“莫名的虚空和彻骨的悲凉”(迟子建小说后记中的话),真的让人颤抖不止!这一刻我必须承认,自己的内心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被如此震撼过了。
编辑/张定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