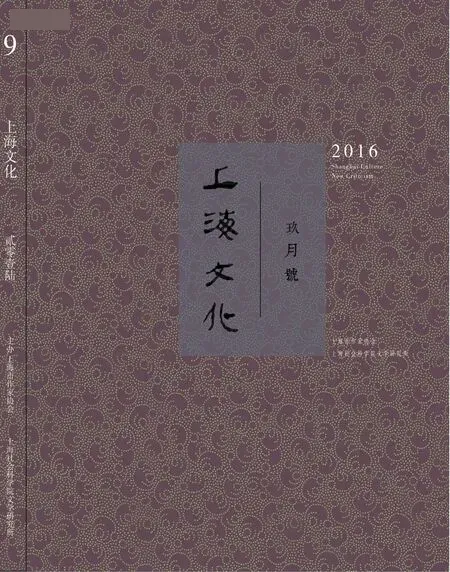钱锺书和当代文学批评
张定浩
钱锺书和当代文学批评
张定浩
钱锺书的一生志业,在文学。然此文学,并非当今从业者多自轻之文学,而是人类心灵基本要求之文学。举凡孔门四科(德行、政事、文学、言语),乃至西方自由七艺(语法,修辞,逻辑,算术,音乐,几何,天文),其中,四科之文学,七艺之修辞,究其内容与钱氏心念之文学并不全然吻合,却堪为其基础,唯有以此基础观之,文学方成为广大精微之文学,而钱氏,才可还原为精诚笃实之钱氏。
钱锺书晚年曾有言,“我的视野很窄,只局限于文学”(《钟叔河<走向世界>序》),又言,“我的原始兴趣所在是文学作品;具体作品引起了一些问题,导使我去探讨文艺理论和文艺史”(《作为美学家的自述》)。此处的“局限”,并非单纯的谦辞,应当视为对自身性情的认识,个人大可局限于文学,但文学本身却不当为任何时下教科书概念所拘囿,依旧可通向一广阔世界。
他二十四岁时曾作《论不隔》一文,援引中西,探讨“不隔”这一理论是如何作为一种中西皆宜的好文学的标准,观其次年负笈英法,借“二西之书”返照中国文学,打通空间之隔;后又于世道艰难之际沉潜经史,借古典著作映鉴现代文心,打通时间之隔,仿佛是将自身作为“不隔”的一生实践。然文学之“不隔”,仍要有文学之约束为伴。钱锺书1980年代补订早年《谈艺录》,批评王国维《红楼梦评论》强以哲学、社会学之眼考察文学,“吾辈穷气尽力,欲使小说、诗歌、戏剧,与哲学、历史、社会学等为一家。参禅贵活,为学知止,要能舍筏登岸,毋如抱梁溺水也”,盖为阅世之语。或许可以说,不隔与知止,是钱锺书对于当代治文学者最恒久有益的提醒。
然今日读者即便从文学的角度来研读钱锺书,亦常只将其放在古典文学批评的领域里观照,此正是其隔,因为类似艾略特论17世纪玄学派诗人、布鲁姆论莎士比亚、博尔赫斯论但丁之类的文章,可绝不会被这类读者误认为是古典文学批评而弃之一隅的。很多人一方面“锱铢必较”地将中国文学细分为古代、近代、现代和当代(甚至连“70后”和“80后”都可以变成两种文学),另一方面,又“远人无目”般将西方文学当作一个模糊的整体。他们像一切视力不好的人,心里存着一个庞大逼人的远方,和困厄狭仄的现在,于是深陷莫须有的焦灼之中。与此同时,他们也像一切视力不好的人,急切地索求一副观看文学的眼镜,哪怕指鹿为马,何惧邯郸学步,遂将文学转换成一波波历史批评、社会学批评和文化理论批评的材料,这是其不知止。
而文学批评的要义之一,本就在于锻炼强健我们的内在视觉,和更为精准细腻、远近如一的感受力。文学批评没有任何理论和方法可言,或者说,文学批评唯一的理论就是观看和感受,唯一的方法,就是比较。古人云,“观千剑而识器”,又云“触物圆览”,今日文学批评家所热衷的问题意识、现象观察、时代焦虑,往往只是“读书太少”的缘故,一个人看到的越少,越不够周全,就越容易下判断,一个人越快下了判断,能进一步看到的东西也就越少。
李劼曾举出陈寅恪和哈罗德·布鲁姆的例子,来贬低钱锺书,认为钱氏“没有思想和自由,所以只好学问了”,此种轻薄之辞,时下销路甚广,在我看来,只能视之为论者在思想、自由和学问三个层面的三重无知。陈寅恪之史学不同于钱锺书之文学,其学术入口和落脚处皆不相类,安可粗暴比较?如果硬要说陈氏《论东晋王导之劝业》一文之历史洞见,钱氏无法企及,那么钱锺书《论通感》和《诗可以怨》诸文中呈现出的文学感受力,陈氏又如何望之?此类不伦比较,多半出自文人,借推崇自己不通之学问,以满足同行相轻之私欲。
至于哈罗德·布鲁姆,其犹太先知般的宣谕批评风格与钱锺书大相径庭,放在一起厚此薄彼,也堪笑场。如果硬要找寻对应人物,钱锺书与布鲁姆的死敌特里·伊格尔顿倒有相似之处。伊格尔顿《文学阅读指南》一书,针对布鲁姆而发,嬉笑怒骂,旁征博引,其文风和博学,与钱锺书庶几近之,“如果人对作品的语言没有一定的敏感度,那么他既提不出政治问题,也提不出理论问题”,对伊格尔顿此言,钱锺书定会欣然许之。另一位可与钱氏相比较的当代西方文学批评大家,是今日中国文学读者也颇为熟悉的詹姆斯·伍德。他赞赏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等文论之精微,又进而惋惜,觉其毕竟是“小说家、散文家,非奋战第一线的批评家,有时我们希望他的手指能再多染些文本的油墨”,遂在其《小说机杼》一书中,以札记形式,状若信手实则精心援引大量小说文本材料,条分缕析,剖判比较,读完后我们未必能获得某种对小说艺术的肯定性观点,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若干言之凿凿的小说标准和美学结论也许可以因此获得松动瓦解,这种釜底抽薪之力,很难让人不联想到钱锺书。《文学阅读指南》和《小说机杼》限于篇幅,或可视作两部小型《谈艺录》,而钱锺书《谈艺录》、《管锥编》,征引古今中外典籍近万种,涉及诗歌、散文、小说、戏剧诸领域的微细文心与复杂修辞,其“沾染文本油墨”可谓甚巨,不妨视作一部大型《文学机杼》或《文学阅读指南》。
今日治当代文学者,多视《管锥编》、《谈艺录》为畏途,却以福柯、阿甘本、詹姆逊等西方理论家为捷径,依我之浅见,多半因为后者难读易解而前者易读难解之故。时人皆欲以己昏昏使人昭昭,何尝乐意以人昭昭见己昏昏?
钱锺书并非不通理论,而是通多种理论,因此他明白,“至少在文学里,新理论新作品的产生,不意味着旧理论旧作品的死亡和抛弃,有了杜甫,并不意味着屈原的过时……法国的新批评派并不能淘汰美国的新批评派,有了什克诺夫斯基,并不意味着亚里士多德的消灭……”和他相比,我们很多文学理论家倒像是暴发户和山大王。在钱锺书这里,文学批评领域并无所谓原创性的、革故鼎新般的发明,只有在掌握大量材料基础上慢慢生成的、对习焉不察之物的“相识”如何转变成体贴入微的“相知”。
钱锺书《管锥编》之外,有直接用西文写作的《管锥编》外编《感觉·观念·思想》,评论但丁、蒙田、莎士比亚等十位西方作家与作品,虽未刊行,但其书名甚为显豁,可以用来映照钱锺书对于文学的认识,即文学既是一种超越时间的、同时性的感官存在,又是一切复杂幽微观念和思想交汇变迁的历时性场域,文学一如人身,其感觉、观念和思想浑然一体,并通过杰出的修辞来表达。是钱锺书这类不隔且知止的文学从业者,才终于令文学批评不再沦为创作的附庸,和学问的阑尾,而真正成之为一项激动人心的志业,即从此时此地出发,去理解曾经有过的人类情感与创造。
编辑/吴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