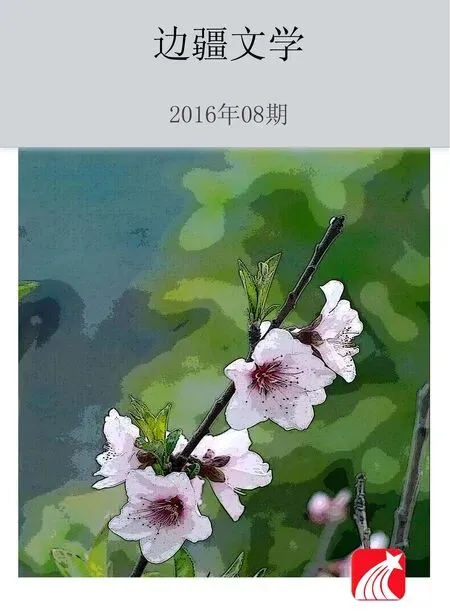漫谈童年记忆与儿童散文写作
◎吴 然
漫谈童年记忆与儿童散文写作
◎吴 然
在这里见到一些老朋友,认识许多新朋友,非常高兴。
我主要写点散文,现在也写得很少了。听力和记忆力都在下降,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的写作,但是这也不应成为自己变懒了的借口。我也很想清晰地听到朋友们的声音,记住朋友们的容貌。祈愿这次到杭州,能使自己的听力记忆力有所改善,能够再写点儿童散文。杭州是有灵隐寺的,很灵的啊!
我们这次会议的主题是“打磨精品创作研讨会”,我本来想挑几篇自己比较满意,后来选入教科书的作品,看看原稿是怎么涂涂改改,甚至推翻重来的,和大家交流,可能有些意思。后来觉得有江边卖水自称“精品”之嫌,实在不合适。而且怎么展示原稿呢?我也弄不来,就算了。下面,我还是漫谈式的讲讲“童年记忆与儿童散文写作”,要是离开了题目,也请大家原谅。
我总觉得记忆是很奇妙的。时间流逝了,像水一样的流逝,“逝者如斯夫”,你根本抓不住。但是奇妙的记忆,把已经消失掉的东西保存下来了。记忆之门一旦打开,许多记忆中的东西,小时候的,遥远的,痛苦的,快乐的,就都会杂杂乱乱地涌了进来,和你相会,和你打招呼。记忆成了一种相会的形式,一种缘分。
我和浙江儿童文学界就很有缘分。
33年前的1983年8月,我应邀参加浙江作协在新安江白沙林场招待所举办的儿童文学作品加工会。在会上,我认识了倪树根、李建树、严雪华、郑钦南、徐迅、冰波、谢华、张婴音等新老作家。特别荣幸的是我被安排和蒋风先生同住一室,得以朝夕相处,向他请教。去年是蒋先生90大寿,我在光明日报写了篇《记第一次见到蒋风先生》的文章,向他致敬,为他贺寿。我听建江说,蒋老师高寿,行动不便,不能来参加这次会议,在此遥祝蒋老师健康长寿!白沙林场会议后,我回到昆明时,好友建江已经登上赴浙少报到的的火车了。
我第二次参加浙江的儿童文学活动是2005年8月。会后正好遇上麦莎台风来了。我呢要去上海看望一些朋友。王宜清送我去火车站,人很多,又热。宜清忙来忙去地安排我候车休息,又买了冰水和茶点。我在心里一直都很感谢她细心周到地关照我。
在许多儿童文学活动中,我也常常碰到浙江的朋友们。和冰波、王一梅等还跑过一趟香格里拉。2010年在南京参加第八届儿文奖活动和儿童文学会议,汤汤的发言让我记忆深刻。她有一句话说:她是一个幸运地遇上了童话的人。她说她得奖后,她的先生抱着她“像抱着一个奇迹”。汤汤的确是浙江儿童文学的一个奇迹。
我猜想,汤汤除了她的天分,她的阅读和爱好,以及她生活在孩子们中间,她的童话或许也留下了她童年记忆的痕迹。因此我想说,童年记忆是所有作家的财富。小说家把童年记忆写成精彩的故事,童话作家把童年记忆写成神奇的童话。诗人在诗篇中歌唱童年,散文家在散文中抒写童年的梦想。
我也一直认为,写作主要靠记忆。当你坐下来写作的时候,向你涌来的是你的记忆。这些记忆包括镌刻在心灵上的印痕,以及曾经使心灵颤动的种种感受。就我自己来说,这样的写作在早期的写作中比较多一些。比如《妈妈教我一个字》有这么一段:
你喜欢打扮我,妈妈。你说我是你的心肝、你的花朵。你给我绣了多么好看的“兜肚”,你用碎布拼接了多么好看的“百宝衣”“百宝裤”。还记得吧,妈妈,有一次绣花针戳伤了你的手指,我看见了红红的血珠珠。我抱过你的手轻轻地吹,吹。我说,吹吹就不疼了。妈妈,你笑了,把我亲了又亲。你真的不疼了吗?妈妈。
有一段时间,我们家生活很苦。爸爸不在家,他帮人家做事去了。你带着我,妈妈,过着很艰难的日子。我们吃了很多野菜汤。我的那碗,总是放了盐的。妈妈,你那碗没有放盐,你为什么会说比我的还香?我没有鞋子穿,赤着脚去放牛,脚上戳了刺。妈妈,你给我挑刺的时候,手为什么颤抖?你说你看不见刺,一点也看不见。妈妈,那是泪水模糊了你的眼睛。我知道,妈妈,你是流着眼泪给我挑刺。
这段话被建江引入他的著作《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文学导论》,作为关于“母爱原则”的一个例文。文中“母爱”的点点滴滴,都深深地嵌在我的童年记忆中,现在读来,母亲的样子还在我的眼前。
我们知道不同的童年,包括生活环境、教育、家庭和人生境遇、都给童年记忆打上自己的烙印,从而形成自己个体的不同于别人的童年记忆。正因为童年记忆的不同,我们才看到从冰心、丰子恺、郭风、任大霖、台湾的林良等前辈大家,以及徐鲁、张洁、金曾豪、林彦、孙卫卫、周静、毛芦芦、孙雪晴、韩开春、台湾的桂文亚、谢武彰、冯辉岳、林芳萍等散文好手们丰富多彩、千姿百态的儿童散文。没有记忆就没有写作。失去记忆,对一个作家来说就是写作的终结。所以,曹文轩说,记忆比想象重要。
但是,任何一个儿童文学作家,包括儿童散文作家,都不可能或者说完全靠纯悴的记忆来写作。我们知道,记忆有如旧照片,时间久了是会发黄脱色的。许多记忆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成了远去的背影,会变得模糊,也会被淡忘。因此,这就需要儿童散文作家把这些记忆重新找回来细细端详,重新回味,重新发现,重新想象。记忆在这里被重新激活了。在这些环节中,“想象”尤为重要。作为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艺术创造,“想象”丰富了丰满了也艺术了记忆。如果说一切艺术都是想象的创造,散文也一样。不同的想象就有不同的散文。而给孩子们写散文,尤其需要张开想象的翅膀而飞翔。这种想象,有时候就直接由作家自己的童年记忆而引发。
冰心老人在给我的一封信上说,“给儿童写散文不容易,要有童心。”我们这些成年人,并非生活在童心世界。生活中不如意事多了,很难再有一颗纯真的童心。儿童文学作家要想办法找回自自己的童心。我的办法是,当我执笔之顷,我干脆回到童年去,在回想童年中唤起自己的童心。虽说我的童年并不快乐,不过也有许多美好与温柔让我久久回味,因此诗人徐鲁说我一直在“寻找回到童年的路”。我觉得,“寻找回到童年的路”这也是每一位儿童文学作家必修的功课,我们正是在回望童年,唤起自己的“童心”,并在童心跃动中完成一篇儿童散文的写作。
难以忘怀的是,童年时代的一切,是那么深那么可以捉摸地留在我的记忆中,以至于烙印在我的肌肤里和气质上,浸润着我的散文写作。每当我铺开稿纸凝神结想,或者因了一支歌一首诗一幅画一件什么事的触发,眼前就会出现故乡的山,故乡的水,故乡的小树林,出现童年时代的小伙件。尽管我知道,故乡那条童年的小河已经干涸,村后的那片树林已经消失,我还是情倾笔端,写出了《一碗水》《走月亮》《学校旁边一条河》等等篇章。童年的影子伴随着我,怀念的欢乐中有无言的忧伤。但是我的这些散文,已经不是童年记忆的复制,因为添加了“想象”而“艺术化”了。既遥远又现实,时间概念完全模糊了。我散文中的童年,仅仅是我“童年的影子”了。
在这方面,建江较早地注意到了。他在1990年写的《吴然的文体意识》的长文中从“叙述视角”“叙述时间”,以及我多用第一人称写作等方面,作了理论的分析,给了我许多启发。我觉得这是一篇学术性极高的文论。不是因为他写的是我的散文评论,而是他提出并论述了儿童散文的文体意识的问题。
说到儿童散文的文体意识,儿童散文前辈们是极为注重的。相对其他散文来说,他们开创了儿童散文这一文体。冰心老人的《寄小读者》无疑是书信体儿童散文的瑰宝。今年是《寄小读者》最后一篇《通讯二十九》发表90周年。冰心在1980年6月写的《自传》中说,“一九二六年后,北新书局出版了诗集《春水》和散文集《寄小读者》”。到1927年3 月,《寄小读者》已经印了4 版,她特意写了篇《寄小读者四版自序》。这些作品的影响是永远的。冰心之后的郭风前辈,对儿童散文的文体作了许多独创性的开拓。比如他把散文和童话结合,创造了“童话散文”,又和散文诗相渗透,示范性的写了许多带有散文诗节奏的儿童散文。他还写了许多日记体儿童散文。各位前辈都很注意儿童散文的“叙述身份”,如冰心所说,“不能小孩子尽说大人话”。说到这里,我想起钱淑英博士在《〈小霞客西南游〉阅读印象》一文中,指出我在“叙述身份”上有时会“不经意间显露自己的(成人)身份,有时在思想和语言的表述上出现错位,使角色定位产生模糊性。”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而中肯的提醒,使我在后来的儿童散文写作中,在添加某种“想象”的时候,对自己的叙述身份保持了警惕,把持住自己是作为或者是“幻化”为某个孩子,这个孩子也许是牙牙学语的幼童,也许是跑跳吵闹的小学生,或者是花季少男少女,作者作为某类孩子的行为代言人,势必要与“这个”孩子的身份相符合。借此机会,向钱淑英博士表示诚挚的感谢!
由此我想到我们的儿童散文,需要加强理论研究和批评指引。在现代散文中,儿童散文是一种新的文体,一种新的独立存在。前辈们写了许多儿童散文,但是专门研究儿童散文的理论还是相对缺失。
我不知道“儿童散文”这一概念最早是那位作家或理论评论家提出来的。1989年,海燕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中国儿童文学艺术丛书”,由浦漫汀教授编选的《散文十家》,选了冰心、郭风等10位作家的儿童散文。每位作家都有一篇关于散文的短文。任大霖先生在文中说,“1962年底,我曾就儿童散文的创作问题写信向冰心同志请教。我提出,儿童散文的特点不是在于‘情节性’,即需要一点儿抒情的、淡雅的情节。冰心同志复信说:儿童散文确实可以有一点情节,这样更适合儿童的口味;但好的儿童散文必定是有浓厚清新的儿童生活气息的,而且语言上必定是真挚而且优美的,为儿童所能够欣赏并乐于接受的,而不是‘大人说小人话’或‘小孩儿说大人活’的干巴巴、粗拉拉的东西。”这段话非常重要,对儿童散文作了清晰的阐述。只是我在《冰心书信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10月北京第1版),以及在《冰心全集》(卓如编,海峡文艺出版社2012年5月第3版),均未查到冰心回复任大霖的信,也没有能够看到任大霖给冰心的信。但是我确信其有,只是还未发掘到吧。在未见到这两位前辈关于“儿童散文”的通信之前,我觉得,最早定义儿童散文的,可能是台湾的林良先生。他的《浅语的艺术》,初版是1976年,其中专门有谈儿童散文的一章,“儿童散文”四个字,也许最先出现在这本具有教科书意义的著作中。而我读到这本书的时候,已经是1994年4月桂文亚寄赠的了。
由于针对儿童散文理论研究方面的缺失,我在练习儿童散文写作时,一方面是尽可能的阅读前辈们的作品,同时只好用成人文学方面的散文理论来套儿童散文,如从散文的真实性出发,我就曾经说过散文和小说的不同,其中一点就是,小说讲的是“故事”,散文写的是“事情”。“故事”是想象,“事情”更多的是“事实”。在散文中编故事,就破坏了散文的“纯粹”。后来我觉得,这些看法虽然有点道理,但是给儿童写散文,也不完全是那么回事。我从童年记忆中发掘写作资源,但我又同时也不完全靠童年记忆写作。我写了一些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儿童生活的散文,这里面有我自己童年记忆的参照,更多的则是在了解了少数民族儿童的心理特征,以及不同的民风民俗以后加以“想象”,借用小说的手法,而成了另一类带有故事性的儿童散文。这里既要注意自己的角色传化,转化成文中的那个少数民族儿童。同时在叙述描写上,又要注意保持散文本身的意蕴,最终还是散文。也就是说,即便是在散文中“添加故事”,我也尽可能的不铺陈情节而多注意细节的饱满。
总之,我认为,儿童散文不能拘泥于某种形式,它应该是多样的,多姿多彩的,正如树木在不同的季节总是用不同的色彩打扮自己,但它还是树木。
本文为作者在“打磨精品创作培训研讨会暨2016年浙江儿童文学年会”上的发言。
(作者系著名儿童文学作家)
责任编辑:杨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