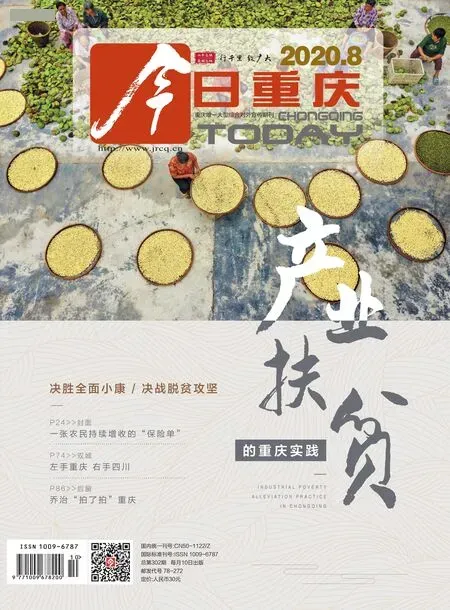那位瞿塘峡口的人,老了
◇ 文|本刊记者 李仕羽 图| 受访者提供
那位瞿塘峡口的人,老了
The Man at the Entrance of Qutang Gorge Is Aging
◇ 文|本刊记者 李仕羽 图| 受访者提供

赵贵林
重庆奉节人。奉节县诗城博物馆馆长、重庆市三国文化研究会秘书长、重庆市作家、戏剧家、摄影家协会会员。创办《夔门报》《白帝城》报刊和诗城博物馆,有《天坑地缝》《诗城奉节》《大足石刻》《三峡竹枝词》《乱世英雄》等著述出版。
汽车驶过奉节新县城,在“夔门”下道,进入宝塔坪不到10公里,便可以看到著名的诗城古迹——依斗门。
十多年前搬迁至此,如今的依斗门外依然有码头,但县城的人早已不需要从这里进出。斑驳的墙砖垒起高高的两层门洞,空对着平静的长江以及那座著名的白帝城。
拾阶而上,穿过门洞,对面就是此行的目的地——诗城博物馆。
赵贵林,那位曾经用双脚丈量遍瞿塘峡口古城的老人正挥动双手示意。
“大东门,我来搬”
“大东门”是老奉节人都熟知的一个地名。
始建于清末民初、位于奉节老城大东门街的大东门民居,是三峡重庆地区最重要的古建筑群之一。那里充斥着精美雕花的窗户、刻满岁月皱纹的门板、简练优美的建筑线条,更是一本记载古夔州繁荣商贸、居民市井生活的鲜活史书。
赵贵林的故事便从这里开始。
因为三峡工程,大东门古建筑群被奉节县政府列为整体搬迁对象。但是,由于需要搬迁的项目非常多,相应的经费就显得紧张,大东门古建筑群整体搬迁项目预算被砍掉,只能采取资料保存方式留存。
这就意味着,古夔州府的繁华商业过往,后来的人们只能在文字与图片中寻找。
那时,赵贵林刚刚从旅游局党组书记的位置退下来。但是,在很多人眼里安逸的退休生活还未开始,他便坐不住了。
“我来搬。”至于资金从哪来,搬到哪里去,搬来干什么,赵贵林没想,只是固执地想把大东门民居保存下来。
面对20多米长的老街,咬咬牙,赵贵林拿出了半辈子所有积蓄10多万元,说服做生意的妹妹资助他20万元,加上国家三建委以文物整体搬迁的科研课题经费赞助他20万元,然后又东拼西凑借来20余万元,就这样,“大东门民居搬迁项目”蹒跚起步。
2002年1月20日上午10时,同其他奉节人一样,赵贵林站在高处目睹了“三峡第一爆”。随10栋高楼轰然倒下,奉节老县城开启沉入江底的模式。当拥有千年历史的老城以飞快的速度向人们告别,赵贵林心中突然有些明白了:或许我要保存的,不仅仅是大东门民居。
在58岁那年,赵贵林开始了一生中最后的奔波——他要用博物馆的形式将奉节的根留存下来。
老城里有个“破烂王”
“做标记的文物都搬过来了吗?”2003年8月,奉节县宝塔坪一处坡地旁,骄阳下的赵贵林额头汗珠密布,他正指挥一帮工人搬运杂物。
在他身后,博物馆已初具雏形。
一年来,当人们陆续搬离故土,赵贵林却在老城租了一间暂未拆除的居民楼住下,一头扎进搬迁工地。
每敲开一户移民的家门,赵贵林的开场白一如既往:“你认为贵重的,你自己收藏,你认为自己无法收藏、没有价值或者不必要收藏的,我帮你收藏,我们共同来保存诗城的文化和历史。”
就这样,刘家老宅的板壁、房屋内壁、各种老家具、日用品等全进了他的竹篾筐;在李诗龙家,他寻出一架上世纪30年代的纺车和那个年月的一张地契。地契上说,房屋是我姐姐的,姐姐死后,房产归侄儿,但我的生老病死侄儿要负责到底。赵贵林如获至宝,如癫似狂。
从中学生的课堂笔记本,到成人的结婚证,从汉代的鬼脸瓦当,到清代的铜制消防车,还有庙前的老树根,无人问津的旧书报、明信片,甚至整间木结构民居,都被赵贵林小心翼翼地收藏到还未竣工的博物馆里。
不大不小的奉节县城里,赵贵林成了远近闻名的“破烂王”。
“大家都说老赵发了财。”但只有赵贵林自己清楚,“破烂儿”越来越多,家里的生活也越来越拮据。他掏出的每一分钱都在精打细算,就连理发都要跑到数里外的工地理发店,“只要两块钱,城头五六块。”
2004年3月17日,博物馆终于建好了,赵贵林却瘦了10多斤。
他给博物馆取了一个诗意的名字,诗城博物馆。
纵将万管玲珑笔,难写瞿塘两岸山。“不是诗人来到奉节要写诗,是不得不写,到了奉节还写不来诗,那就称不上诗人了。”赵贵林笑着说。
古城在水底,诗城在这里
虽然“相貌”不扬,条件普通,但在许多观者眼中,诗城博物馆却堪称“世界级”。

上图:诗城博物馆建馆工地

下图:诗城博物馆展览大楼
15个展厅,面积近3000平方米,从上古的青铜器到大汉的陶俑,从盛唐的砖瓦到宋朝的瓷器,从明清的家具到近代的书画,无一不在向人们述说三峡悠久灿烂的历史文明。
这里有“巫山人”的发现者、古人类研究所黄万波教授提供的奉节古人类和古动物化石;有当年科克伦、阿迪力相互较量走过的三峡夔门钢丝;有守护甘夫人墓的千年黄连树根以及英法探险者勘测奉节天坑地缝的所有资料。
透过赵贵林的“宝贝”,我们依稀可以看见,一支古老的鱼复巴人在瞿塘峡边生息繁衍,逐渐发展成一个渺渺百万人口的大县;一个边城小邑的版图不断拓张,直至繁华风流的夔州路;城市的四次迁徙并没有妨碍帝王将相在这里上演叱咤风云的历史大剧,无数史诗记录了这方土地流光溢彩的往昔。
如今,搬到新城的奉节人,很乐意坐上20多公里的公交车,来博物馆“怀旧”,摸摸曾经睡过的木床,拍拍曾经用过的泡菜坛子。
二楼展厅,老城的旧窗棂组成了一面墙。
赵贵林在上面挂了一些钟表。这些钟表的时间,全都停留在10点52分。2002年11月4日10点52分,那是奉节老城“最后一爆”的时间。
许多奉节人关于老城的记忆,也定格在这一瞬。
人们在这儿停留,搜寻着脑海中关于老城过往的点滴,然后,有人会微笑着泪流满面,有人会低头不语,还有人会忽然跑到展馆中老城的沙盘模型前,寻找自己住过的地方。
“在这儿,我找到了过去几十年的记忆。”这是赵贵林听到的最多的话。
让乡愁有一个归宿
老赵今年72岁了。
凭一己之力收藏一座城的历史,对于这位年逾古稀的老人,是义无反顾的执着,更是肩头沉甸甸的压力。

良好的社会效益,鼓舞赵贵林一步步走到今天,但与社会效益形成巨大反差的经济效益却有些苦涩。
2005年,赵贵林开始尝试收门票:15元/人。“每月门票收入只有2000元左右。”这与维持博物馆运转的费用比起来,简直是杯水车薪。面对每年数万的亏损,如今,赵贵林已裁掉了大部分员工,只留一个厨师。整个博物馆就靠他和老伴经营。平常日子,一人接待游客,一人充当讲解员。
十多年来,有人觊觎博物馆的“财富”,但不管多么困难,赵贵林从来都没想过打藏品的主意。
有人提出门票涨价,赵贵林认为博物馆具有公益性质,也不同意。
更有朋友劝他把博物馆关了,把门面租出去,安心养老,而且博物馆地处旅游码头,商业价值高,只要一转手就可换来巨额财富。赵贵林急了:“我要立个遗嘱,子孙后代可以作为博物馆的工作人员领取薪水,但谁也别想改变博物馆的性质。”
在赵贵林心中,他始终是文化人,而不是商人。
惟一可以为之呼吁的,便是当地旅游业能够带更多游客到博物馆感受、传递三峡历史文化;文化部门可以更加重视远在区县的民营博物馆,不要让根断在三峡文明的源头。
荆棘满地,坎坷无数。
但赵贵林依然觉得,这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更是他一辈子的追求,“不然若干年后,十几万老奉节人该到哪里去寄放乡愁?无数外乡人又靠什么了解诗城?”
他已经做好了打算,等经济稍微好转,便以博物馆为基地,约上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创建“夔州文化研究中心”,专门研究、传播三峡历史文化;多增加几个展厅,更多、更全面地把奉节的全貌反映出来,展示三峡文化的博大精深。
“烟尘中蹒跚于老街深巷,拾砖捡瓦,铢积寸累,茹苦含辛,三载方成,展沧桑老城之风情,扬千古三峡之文化。”迈出诗城博物馆,进门左墙上的话,仿佛更加醒目。
馆外,江风夹杂着雨点渐大,不断冲刷着屹立千年的依斗门,有些落寞,有些惆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