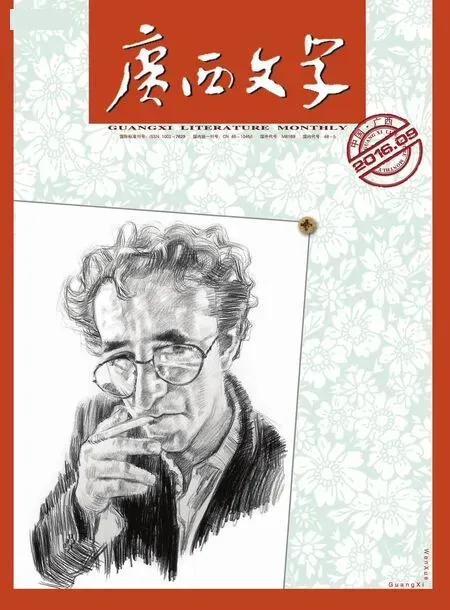天 井
短篇小说·左雯姬/著
我叹口气,也就在这天井里,才能让自己稍加放松点儿。我仰望着被三十多层的楼群围合的四方天,今天刮风,天蓝云低,就像在青藏高原。虽然天有意放低姿态,却还是被这高楼大厦强撑起来。天井里无风,只有怪异的呜呜声,还有小小的水系和绿植点缀,弄得颇有情调。
有人叫了我的名字,并说,嗨,你可溜得真快呀,又在这儿。
我胆小,惊吓得捂住胸口,慌忙回头,也不忘松弛面部,笑盈盈地。我眼前走来的这位四十不惑的男人,可谓意气风发,气宇轩昂。他刚才还和总裁在一起,跟我们这些部门负责人确定年度预算的事。往年我们都是跟总裁一对一地谈,一个一个地过。这回总裁身边就多了这么个碍眼的家伙,邓凯洋。总裁都不怎么说话,在一旁的邓凯洋倒是老说,同意这个,不同意那个。我申报了一批信息中心机房必须要更换的老旧设备,而且,我们准备今天就把这些设备下线了。邓凯洋连看都不看就说,你们是职能部门,不增收还不在节支上下功夫?设备还能不能用?能用就接着再用一段时间嘛!
他没有商量的余地,他从不跟我商量。我,硬吞下这口气,只好来这儿吐一吐!才吐多会儿呀,他就阴魂不散,还要人活不?
邓凯洋不以为意,只说,我跟你说过的,得赶紧整理公司客户关系坐标图了,还得拿出相应的解决方案。邓凯洋递给我一张名片,继续说,她是我们客服的老人了,找时间你们交流一下。
邓凯洋走后,我就觉得天井索然无味了。在我们公司楼群北面还有很多造型奇特不成方圆的天井,称之为走廊天井,处在不同的楼层间。我想,以后有时间应该去那里才好,因为待在那些天井里,可是不容易被找到的吧。
我跟邓凯洋介绍的那位客服人员约好,下午四点半在我的办公室见面。这段时间一般日常工作都已结束。原计划是,轻松聊会儿,我就能按时下班了。可我见她第一眼时,就预感到,接下来的谈话不会平淡,也不会是预想的短暂。
她,身着老式套装,没有任何脂粉,人长得,要不客气地讲,是有点丑的。不过,她气度不凡,直觉——怪怪的。我的直觉,向来灵得很。尽管我是个五大三粗的男人,但心细如发,观察细微倒是我的强项。在说不清道不明的气场里,我们的谈话迅速“变异”,原本简单的公务,在她几度明显的导向下,急转到了复杂的邓凯洋身上。
她竟然直接问我,你觉得老邓(邓凯洋)这人怎么样?我被问得心惊肉跳,而眼前这个女人,倒是挺泰然的。
以我的经验——唉,悲催的人生,步步都是被逼出来的。而跟我同年不同命的邓凯洋,则截然相反。他总是先发制人,霸气十足,对公司的大事小情,总爱插手——老有他。这话,我不便跟这个女人讲。她,之前我们可从未见过面。她一直在我们客户的中高层游走,帮公司跟那些客户的大人物牵线搭桥,一般情况她不来公司。她一向归邓凯洋管,现在可能有些变化,我也不便多问。我跟她是两条线,我管公司内部运营,原本不归邓凯洋管,直到去年年底,邓凯洋提任常务副总裁(被看作总裁接班人),我这才不幸落入他的“铁爪”。我没在邓凯洋手下之前,就已经被他毫不客气地呼来唤去了。介于他的淫威,我只得屁颠屁颠地为他效力,在所不辞。
我不清楚她跟外界是如何打交道的,但她毕竟是公司的一名普通员工,问我这个常行走在“上书房”的公司中层元老对“上书房”的高层领导的看法,这有点……她也三十好几了,不该是个菜鸟,能问如此冒昧的问题,我想她背后必定大有文章。我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反复思量,才说,老邓这人吧,挺有主见,意志力也比较强硬。
虽然话里有话,倒也不会让对方觉得,我是在随便敷衍和糊弄她。她就开始进一步,更加直白地问,老邓最近身边又有女人啦?我淡淡一笑,掩饰着内心的诧异。她是地道的北京人,北京妞儿的大胆我见识过,但这么直接的,也还头回见。
我无意间已被她的话“绑架”,顺着说,嗯,最近是有个女朋友。她说,还是同事吧!我笑笑,点点头。邓凯洋爱吃窝边草这副德性,只要跟他关系稍近的同事都清楚。我这人也有个毛病,不露点儿消息灵通人士的能耐就全身奇痒难当,于是我又添了一句,嗯,又吹了,倒是和平分手的。
你对老邓这方面怎么看?她步步为营,简直是有预谋的啊!我心里不断打鼓,聊到这地步,我竟有些不愿舍弃。我叹口气,说,老邓嘛,我不是说,也老大不小了,找个差不多的得了,别老折腾。不过老邓吧,我跟他聊过,他是不愿意被婚姻束缚的。唉,也是啊,都独身逍遥了半辈子。
我一边说,一边暗中观察这个女人。这个不好看的女人,此刻竟显露出某些风韵。如此风韵,难道是因一股醋意调动?由爱意煽起?
邓凯洋是钻石王老五,这个我也没法儿否认。他年薪过百万,还顶着上市公司副总裁和名牌大学博士的帽子到处招摇。他身边从不缺女人,对女人却是向来挑剔。别看邓凯洋其貌不扬,可我所知道的,他谈过的那有一排球队的女友,全是我们公司的靓妹。她们不是海归,就是白富美。人长得漂亮那是必须的,“附加值”也一个不能少——气质、学历、能耐、品性,甚至脾气,她们似乎都不差钱。眼前这位……或许只是单相思吧!老邓也有个毛病,他喜欢被人崇拜,无论男女,一旦让他感受到这点,他会把这人留在身边,重用他(她)。所谓重用,自然是少不了好处的。老邓对他的亲信向来大方,反正又不是花他的钱。我是从未被列入邓凯洋亲信行列的,这点,唯有我和他心知肚明。我想,这个女人是不是也有她自己的小心思呢?
她接着问,你了解老邓的过去吗?你跟他到底有多熟?
我想,在公司里,或许我是最了解邓凯洋的。不光因为我们同事多年,我和他几乎是前后脚进的公司;更在于,他处处压迫我,让我强烈地感受到他的存在。他是技术出身,学历背景比我好,于是平步青云,混得与我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今年即将任期结束的总裁,对我算是不错,但他对邓凯洋更是一贯的铁,那种亲密与信赖我是没法儿比的。总裁力推他做接班人,这个不用我多说,大家都能看出来,一目了然。而他呢,可谓势态逼人啊,似乎势在必得。所有高管人员,都已经默许了这个不可言,也似乎不必言的势头。唯有咱们的老板,董事长的态度,还有些莫测,不甚明朗。直到今天的早例会,老板终于拉着他坐在了自己身边,这被大家看作是具有“历史意义的瞬间”。我,观察极细的人,自然是把老板的每个细节都看透了,也揣摩透了。老板向他看了几眼,说了几句话,说话的表情是平和中带了几分喜又参了几分忧,皱没皱眉,与平时的皱眉有没有不同,又有几分程度的不同。他当时是什么时候眨了眼,眨眼频率又如何,我眼明且全烙在了心上。我的推论是……不,我的推论还重要吗?重要的是明天就出结论了。明天就是总裁办公会,老板将在高层会议上先发布最终的、板上钉钉的——结论:下一任总裁——邓……
好吧,我稳稳神,揩揩汗,好在我先下手,见到形势苗头,就作为“亲密”下属,屁颠屁颠地给他出谋划策了。当时谁都看得出来,老板还在犹豫,如何打动老板的心呢?!支招哇,说到老板心坎儿里去的话……我是要促进他成功的,可我暗下的心思却是胆怯的。我害怕他成功。一旦他登上总裁的位子,我可就更没什么好日子过了。公司政治路线就是这样,非亲即仇,他是一日没把我当亲信,便终生不会拿我当亲信的。而中庸这条路是找不着门儿的。我早晚是个死,死的过程越漫长,我翻身的机会就越渺茫……我,坐以待毙?!
在外人眼里,我跟邓凯洋的关系还蛮铁的。这就是一场绝对的误会。我最大的能耐,恐怕就是我总能做到周全,不断地委曲求全,造势——表面一团和气,甚至可以跟“敌人”交心。邓凯洋对我的政策始终如一:多干活,少奖励,苛责到底,暗地压制,明面儿见风使舵,有落井下石的大好机会,绝不放过。他能对我用上如此高妙的策略,全在于“权衡”。我在公司也是有不少大领导和实权派护佑的,这才换来了与邓凯洋表面上的和平共处。
我俩“假作真时真亦假”,有时也入了戏。但我是装糊涂,他也许不是真犯糊涂,但跟我确实说了不少实话。他的心思我明白透了,他太想当总裁,捞取好处和权力永远没个够。我成全他,帮他想辙可不止一两回。他在我面前露出的马脚,就越来越多。但是,他或许才是真正把形势看透的人。他是无比强大的狮子、老虎,而我就是颗肉团儿,怎么扑腾,也改变不了给人下嘴饱腹的本质。这个本质会在我扑腾得越欢的时候越奏效。我不糊涂,对他少有微词,偶尔胆肥点儿,又深信那人不会传话,即便传了也无大碍,那我才会好歹让自己透口气。
在这个女人面前,我只能编排些常规话儿说说。她连连摇头,说,不是工作上的事情,是他的生活,邓凯洋曾经的生活。
生活?曾经?来公司前我不知道,但他进公司后得的每一笔好处,我可门儿清。在偌大而昂贵的京城,他已经有好几处大宅子了。那些大宅院他都不去住,“偏安于”西三环内的一套不足六十平方米的小居所。就他那样儿,都想象得出那居住的环境,比狗窝还要脏乱差。不过,近年来的房价抽风似的涨啊,每晚睡着觉都能感觉那日进斗金的快意吧。无论他睡在什么上头,就算是睡在了狗屎上头他都会乐醒的。他的生活简单,一个单身汉,无非是工作,找女人,谈恋爱。他最爱深更半夜给我等属下发信息,好证明他是个多么一心为工作的人;他一门心思惦念着,如何把各种繁多复杂费力不讨好的任务发派给我们;他时刻警醒着,以便随时把我们从昏沉中提拎起来,训斥一顿,畅快淋漓。
以前,他家里——很困难。她的声音轻盈柔美,真是个很好的诉说者,像施了魔法,能让你安静地听下去。她说,他从小在单亲家庭长大,母亲对他不好,只有哥哥对他最好了。可是,哥哥早逝。他一直认为,是妈妈把哥哥逼着去跳江的。他妈妈极端强势,哥哥选择什么专业什么大学,跟妈妈发生了强烈冲突,就……爸爸起初是跟妈妈离婚了,离婚不到一年,也自杀了。据说,是妈妈威逼的。邓凯洋一上大学就跟妈妈断绝了关系,一直是自己赚学费和生活费……
噢,是嘛。我感叹了一声,思绪便像触电般乱跳起来。我的着眼点在于,邓凯洋怎么能跟她说这些?她到底是邓凯洋的什么人?她在邓凯洋面前扮演的到底是什么角色?她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
她又补充说,邓凯洋认为,亲人即最大的敌人,亲人即地狱。最能伤害自己的就是亲人。所以,他不想再有亲人了……
噢……我不觉倒吸口凉气。我对此没话说。然而,我的脑海里闪现出上次去邓凯洋办公室的情景。在他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一盒叶酸。男人也吃叶酸?他既然不避讳,我便直接问,想要孩子了?他回答也干脆,是。我说,恭喜啊,什么时候发请柬?他问,什么请柬?我笑了,说,你都准备要孩子了,还不结婚?他满不在乎地说,谁说不结婚就不能要孩子了?他那语气真不像是开玩笑的。
我有意将某种预感忽略,好像在逃避。而她显然要将那面“旗帜”直插目的地,无论绕开了多少回,恍惚间,我还是走进了一个叫作“芝麻开门”的黄金通道。
她终于如是问道,杨总,您是不是知道我跟老邓的关系?我不得不怔怔地瞅着她。我心里很清楚我不知道她跟老邓还有什么别的关系。不可能啊?邓怎么可能看上她?可她既然这么问了,那就一定是有关系喽,而且关系还不浅呢。她的眼底流露出一种失落。她还未开口,我就以一种自救的本能,脱口而出,你跟老邓有过?她果然被我这句话点亮了兴奋之光,眼底的笑意洇开到了整个脸颊,显得很有光泽。我这才更明确地说,你曾经也是老邓的女朋友啊?!
我依然非常小心,她这时就更加落落大方地说,我们岂止是曾经!她像有千言万语,瞬间堵在了嘴边。这难道不是邓凯洋的一次“阴沟里翻船”?我的心肝儿直颤,偷笑得不行。她又说,我们……曾经就像夫妻……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他唯一隐秘的女友……现在可不同了,他连一个电话都不愿接我的。
我感觉她的确是个憋屈坏了的女人,急需向人倾诉。我是个老好人,总愿意成全别人。大家都下班了,我邀请她吃顿便饭。她当然很乐意,说,要去就去远一点的,香山脚下有家徽菜馆,就去那儿吧!
那餐馆在古树环抱间独处一隅,徽派建筑典雅幽静,是个四合院,天井是被四边古朴的屋檐合围着的,天空里飘着些淡灰色,似乎有意要跟这土灰色的屋檐接近。她很熟悉这,直接把我带进一间包间,并说,这是我跟老邓曾经常来的地方,这包间,也是十年没怎么改变。我环视包间里的雕梁画栋,一派古香古色江南风韵的家具,低调的奢华,叫人心瞬间沉淀。
她不看菜单,直接点了几样菜,并跟我说,就咱俩人儿,几样特色小菜就够了。我差点又要无聊地问,这几样也是老邓常点爱吃的吗?
她的动作跟她的快人快语一样,迅速而敏捷。她的手机已递到我眼跟前儿,说,看看我儿子。我在手机屏上看到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彻底惊呆了。
“岂止曾经”在我的脑海里,像红色警报一样拉响。那孩子活脱脱就是婴儿版的邓凯洋。我不禁惊呼,天哪!她明知故问,你看他像谁?
我说,他是老邓的……她垂下眼帘,一手托着一边脑袋,说,老邓不承认,除非做什么亲子鉴定。我是绝不会做的,我和儿子并不需要他,儿子已经长到三岁半了,他有爸爸。
可你的儿子这么像老邓,以后怎么可能骗过你现在的老公?
你有没有听说过呀,小孩刚出生时,也许是上苍的故意安排,会特别像爸爸,好让爸爸不要抵赖,要承担父亲的责任。可是孩子长大了,会有变化,也许变得一点儿也不再像爸爸了呢。
那你老公……你是知道你已经有了,才和你现在的老公匆忙结婚的?都这样了,你为什么不和老邓结婚?
老邓不可能和我结婚的。我老公嘛,是个半拉老头子,从来没有过孩子,得了这么个宝贝,开心极了。他从没怀疑过,这孩子不是他的。他那么爱……我们生活得很好。就这样,这样很好!
我感到一阵眩晕,眼前这个貌似平凡的女人,该有怎样“波澜壮阔”的一生啊!
老邓到底有什么魅力,值得你做出那么大的牺牲?我不禁为她鸣不平。她只是笑笑,半天才说,在我看来,老邓是个心思缜密、有王者风范的男人。他是很自我,可有时候,他倒是挺令人怜爱的。
我没听错吧!典型一个薄情寡义的男人,自私自利唯我独尊的男人,还能让女人“怜香惜玉”?我不得不对这个北京女人的“二”,重新慎重地审视一番了。
我可以离开他,她说,我老公早就想把我调到别的大公司去了,他觉得我在这里太辛苦,我原本可以得到更好的待遇,更轻松愉快的工作环境……但是……我并不是放不下跟老邓的感情。只是,他一直单着,再跟我断了联系,他将来老了、病了,可怎么办啊?谁来管他?
他由谁来管关你屁事?爱谁谁。我内心愤愤不平,脸上却只能显示出一团柔和的理解万岁。
她说,我想回公司,想离老邓近点儿。你看,我有没有调回公司本部的可能?调到你那,怎么样?我可以帮你干很多活。
噢,我沉思片刻,说,我那不是问题,你也应该清楚,关键还得老邓点头……
我们一时沉默。我在想如何能把我解脱出来了,又不至于伤害到她。于是,我琢磨着说,老邓这个人吧,有时是挺倔的……
哼,那不过是表面。他为人其实挺犹豫的,并没有主见,时刻都是在变的。
我愣住了,女人说话声儿不大,语气随意,我却像是被一个炸雷惊着了。她看我不信,进一步说,他都是在看,所谓见机行事,他要看到的是势态……势态明了,他才会决策,你说这样的人怎么可能称得上有主见?
过往许许多多事,风驰电掣般呼啸而来,似乎一下子都变成了这个女人所言的最好佐证。
我的电话不择时机地响了,吴胖子打来的。
吴胖子是公司的人力资源总监,跟我关系不错。他在电话里,毫不客气地低吼,喂,贵人多忘事了吧!竞聘稿子呢?其实各级干部的升迁名单,早就定了。但,形式即内容:所谓的竞聘人在台上演讲,一群评委在台下提问打分,场面必须生动热闹,就像升天的通道,必须走,否则之前的修行全废。
吴胖子说,就等你一人了啊,你真要我今晚回不了家嘛!
吴胖子看我不说话,就语重心长地说,你的决心能有多大?能扛得过老板?吴胖子停顿良久,好像非得叫我品出他的一语双关来不可。
我现在的确有私心,想跟从前的一个老领导出去创业。我在公司是做到头了。老领导还跟我说,我要走了而你最终不走,那你就是孙子。我说,一言为定。可我心想,我当孙子还少嘛,不差这一回。
我的确是想离开公司了,最好就让老板忽略掉我。怎么着,我还能在这节骨眼上升职?还想着能借此“平步青云”?算了吧,让“小生”默默地、轻松地离开公司吧。不承想啊,被老板盯住不放了,非要提我做副总裁。升官都为发财,可副总裁跟副总裁有天壤之别,比如我这副总裁就绝对远远赶不上邓凯洋这个副总裁。我当副总裁只会增加更多的责任而不是利益。
我的话不带拐弯儿地说,不是,我不能胜任这岗位啊!吴胖子冷哼哼的笑声,别提有多瘆人了,话都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你敢公然对抗老板?老板说你行你就行。
我无奈地说,我现在身体不好,家里操心事儿太多,不可能保证百分之百地精力投入呀……吴胖子又笑起来,话说得更狠了,就这理由能上得了台面儿?老板不把你整死才怪呢。噢不,死对于你来说都是一种美好的解脱。好啦,一小时后给我交稿啊!
挂了电话,我才发现,她不在包间了。我透过包间的窗户看到她正在天井里,坐在一把小木椅上,低头看手机。天色黯淡,就像一条灰色雅致的披肩披在她的肩头,显得高贵而孤寂。当我走到天井时,华灯初上,天井里的灯显得有些苍白。她提醒我,饭吃完了吗?
我笑笑说,吃完了吃完了,我哪比得上老邓啊,就知道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她扑哧一笑,不以为然地说,他那只是装装样子罢了。我不置可否,摆弄着手机。她以为我还是不信,就强调说,他可不止一次亲口跟我说过,他只用了三分之一都不到的精力放在工作上,所谓工作也无非是处理各种人际关系。他最擅长拉关系,关系网。其实,他大部分精力都放在——女人身上。说完,她轻笑了几声。
我抬眼瞅了瞅天井的上空,没有星星,也还没有黑透,灯是蒙蒙亮的,像起了雾,一层一层地叠加、渲染。我这才恍然,早就没风了啊!是雾霾?从上空往下倾泻。江南建筑仿佛处于大漠黄沙中,这样的景象多少感觉别扭。我把手机放进了裤兜里,问她,老邓为什么是个没主见的人?做事犹豫?在我们看来,他多雷厉风行啊!女人说,那都是表面文章啊,我跟他亲密那么多年,我还不了解他?他说话语气短,给人感觉斩钉截铁,其实他心虚得很。我们做任何项目,都是我们做前期调研、后期验证,研发部执行,责任都压在下边。当然他也知道自己是责任人,逃不掉的,他也会先想好退路,先保全自己。所以他做事从不创新,按别人的成功路线走,就这样也不一定成吧,他就会想尽办法找理由把责任推给别人。他说过,工作在工作之外,决策在决策之外……关键是要找到权衡的支点,钳制他人的软肋。唉,工作如此,感情也这样。你看看,他有哪一样儿是真正成功的!
我说,在邓凯洋面前,我看我们是不是需要重新定义下成功的意义?我和那个女人相视而笑。
最后我还有一点不明白。这个女人看透了邓凯洋,也声明自己对邓已毫无感情。她明明在情感上、思想上都远离了邓,可为什么她在行动上还分明在亲近邓呢?她不是还想回公司本部嘛,还像个亲人一样在考虑邓的养老问题吗?她还想看到邓,跟邓保持长久联系嘛……但我没有把这个问题说出口。
回到公司,已经晚上八点半了,该死的堵车。吴胖子在等我。
吴胖子半掩着人力资源办公室的门,低声细语地跟我谈心。老杨,我的云鹏大哥,你真要走哇?你走不了啊,老板不肯放的。我哀叹着摇摇头。
吴胖子会意了,继续说,你知道老板为什么要提拔你吗?
这点慧根我还是有的,我说,咱们是上市公司,每届就有一次高管人员的变动,副总裁人员要调整了,需要“新鲜血液”,老板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呗。
吴胖子点点头,眯笑着说,是啊,今年高管层,包括董事会,要走好几个人呢。唉,老板是不喜欢那帮人的!你放眼全公司看看,老板的人还有几个?在公司里还有多少分量?这家上市公司,真的已不再是老板的了。老板不甘心啊!公司里所有实权派,都在跟老板唱反调,以总裁为首的那拨人马都是些什么角色?个个如狼似虎,聪明绝顶。聪明都用在了钩心斗角上,跟老板耍心眼儿上。“老板派”是被公司全体员工孤立和重点防范的对象。我知道你的难处,你怕被老板拉拢,亲近老板一人,就将失去所有人。这回你还是老板“钦点”的。
我说,是啊,我真的会“死”,搞不好会“死无葬身之地”。吴胖子又笑了。我想,唉,哪个会真正为你设身处地着想哟?我说,老板也是不满意老邓的吧!
唉,吴胖子叹口气,说,不满意大发了,可现在这形势……所以你走不了哇!
我说,我今天见了一个女人。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掏出了手机,打开了一段录音……
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坐在苍白的灯下,看着空荡荡的办公室,内心总有些无法安放。我终于把演讲稿写完,发给吴胖子。我又去了他的办公室,人力资源部的门已经关了,门缝里也没有透出光来。吴胖子回家了?我正疑惑,听到门内压低的说话声,还有吴胖子那特有的、冷哼哼的笑声。我的直觉让我紧张起来,顿时脸发烫。
我是个一捶就扁、一砸就烂,但无论成何面目,依旧能“活”着的老江湖,在这一刻,我好像气力全散了,散到了九霄云外。可是瞬间我又聚集了力量,仿佛复活一般,比过去更有力量了。我下到大楼首层,走到了那个四方的天井里。地灯迷离,流水声沁入夜色,回荡在这合围的小天地里。
我感到有些困倦,还得开至少一个小时的车才到家呢,想想,伸了伸懒腰。信息中心的经理打来电话,他在电话里急促地说,杨总,机房着火了。我的困倦立马儿惊吓得退避三舍。是,是哪儿着火了?我问。哎,就是咱们准备今天下线的老旧设备呀!他回答。
我忙不迭地跑到楼群北面的机房,目光在层层叠叠、形态崎岖的天井走廊里跌跌撞撞。最后,稳住神,目光才锁定在那层楼, 机房的大门正冒着火光,浓烟滚滚。
释放的全是毒气,而我们需要冲进去抢救资料、设备……
我忽然看到,三十多层的楼顶上,有人影晃动。据我的观察、推断,那应该就是邓凯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