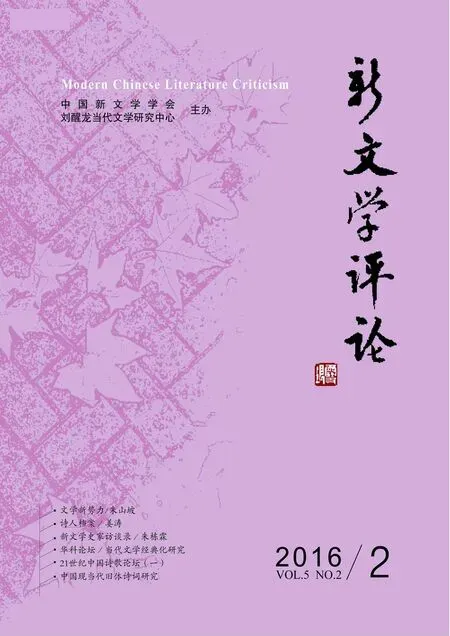“王二”:蛮荒年代的精神幽灵
◆ 张棋焱
“王二”:蛮荒年代的精神幽灵
◆ 张棋焱
“王二”的身份辨识与身份游离
“王二”是王小波小说中连贯出现的人物,他的经典形象几乎都打上了“文革”时代的烙印。《黄金时代》的创作背景是70年代中期,文本中记载“王二”时年21岁,因此王二大约生于50年代;在《红拂夜奔》和《革命时期的爱情》中,“王二”与王小波一样,都是1952年生于北京;《似水流年》中的“王二”出生在1950年……王二的出生年代、背景、瘦高的身形,甚至曾经在美国客居、欧洲旅行的经历都与王小波有着相似之处。 《黄金时代》中的王二“面色焦黄,嘴唇干裂,上面沾了碎纸和烟丝,头发乱如败棕,身穿一件破军衣,上面好多破洞都是橡胶粘上的,跷着二郎腿;坐在木板床上,完全是一副流氓相”①;《革命时期的爱情》中的王二“才过二十岁,就长了连鬓胡子,脸上爬满了皱纹,但一根横的也没有,全是竖着的,自然卷的头发,面色黝黑,脸上疙疙瘩瘩。脸相极凶,想笑都笑不出,还有两片擀了毡的黑眉毛”②;《我的阴阳两界》中的王二,“长了一嘴络腮胡子,活像一个老土匪,而且满嘴都是操你妈”③。王二虽为知识分子,但素来不拘小节,不爱打扮,穿着邋遢、相貌不堪;王二虽为下乡知青,但不甘遵循知青时代的话语语境和生存规则,以相貌和心灵上的“痞子”形象、智慧和有趣的方式来对抗时代的荒诞规则。王小波笔下的知识分子,与传统“士”阶层人物形象格格不入,完全颠覆了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王小波对知识分子外在形象的塑造,折射出了他笔下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
对个体的尊重、对自由的渴望,对权力、公共意志的抗拒,是王二坚守的品质。“王二”用常识解构社会既定生存规则,用黑色幽默般的生存智慧拆解权力和欲望的生存理念,是极权社会下知识分子生存困境的写照,也是先进知识分子在“文革”时期的反抗缩影。王小波通过“王二”的现代性人格特征的书写表达了其对自由知识分子身份的认定标准和期望。也可以说,游离在小说文本中的“王二”形象,几乎是王小波本人思想的倒影。
用常识解构反常识的生存规则
在“文革”时代,人人浮夸,思想的禁锢、人性的扭曲,民众在封闭时代里的狂欢,致使人在社会中只能按照社会规则、权力话语而行。但王小波认为:除了自由主义立场,知识分子没有其他立场可取。他认为,平庸的角色、不断地为社会变换扮演角色,持续压制着人的发展。王小波在致李银河的书信中写道:“把人都榨干了,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尽义务,我们自己的价值标准也是被规定了的。”他笔下的王二始终保留着不羁的精神思想,诉说着挑逗的时代话语,饱含着对自由理性的追求;王二对自己所处时代制定的荒诞规则不以为然,质疑规则、质疑权力,不能不被划为“另类”。
王二个性孤傲,不屑于那一套反常识的社会人情规则,导致人际关系的处理比较艰难。《黄金时代》中,他和陈清扬“伟大友谊”的缘起,是两个因素促成,一是“农忙时队长不叫我犁田,而是叫我去插秧,这样我的腰就不能经常直立。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的腰上有旧伤……”④,按常识判断,王二不适合插秧,人人知道;可惜他并未因此巴结讨好队长,认为队长应该会按常理来安排,定不会勉强有腰伤的人插秧。正是因为王二严重忽视了权力的重要性,导致被队长安排专干插秧的活儿,最后腰伤复发。二是王二“队医务室那一把针头镀层剥落,而且都有倒钩,经常把我腰上的肉钩下来”⑤,队里的医务室把人的生命当作儿戏,护士不经严格培训便上岗,针头不经检测便使用,导致病情在治疗中愈发严重;王二认为陈清扬“对针头和勾针大概还能分清”,去找陈清扬打针而相识。《三十而立》中的校长,解释王二不能出国的理由:“大家说,放你这样的人出去,给学校丢人。同志们对你有偏见……”⑥按常识来判断,一个人是否应该出国学习,是按照学术科研的成果以及是否必要来安排,但校长列举出的王二不适合出国的理由,竟是外在形象不好,出国会给伟大祖国丢脸,滑稽之至,令人发笑;《似水流年》中的王二认为“我向来不怕得罪朋友,因为既是朋友,就不怕得罪,不能得罪的就不是朋友”⑦。这也是交朋友的常识,如果友情只是用来相互吹捧、吃喝玩乐,那就有悖“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交友法则,但王二因不怕得罪人,而失去了许多所谓朋友。然而,王二所遇到的常识问题,并非个体性问题,而是时代虚伪的生存规则所造成的普遍问题,王二所做的事情和持有的逻辑,看起来似乎“很傻很天真”,但实质上是用常识来反抗了反常识的生存规则,这是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对社会的尊重和对人的尊重。
《革命时代的爱情》中少年王二冷眼旁观当时的炼钢热潮,并且思考高炉温度与炼钢纯度之间的关系,后来还请教过冶金学教授,一个有常识的人不会相信炼钢是用家用铁锅可以炼出来的,也不会相信一亩地可产万斤粮食的浮夸;王二通过对荒诞“炼钢”事件的思考,达到了思想上的挣脱,没有被时代话语所洗脑、禁锢。《黄金时代》中的王二响应号召,去云南的偏远地区当知青锻炼自己,但却没有专心革命,而是对“性”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这看起来是不务正业,实则符合常识和常理。一个正在读书的青年,突然不读书学习了,而是下乡种地,精神生活的空虚必然带来身体的空虚,对性的渴望自然也在情理之中,并非是什么破坏革命的违法犯罪。王二作为年轻人,直面身体上的需求,同时用对“性”的大胆实践来反抗权力。在王二对生存规则的反抗中,常常用身体进行对抗,王二的“性”像是一面悬在空中的鲜艳旗帜,在高空蔑视“文革”的社会规则和主流文化,向他们招手,向他们挑战。王小波说:“只有在非性化的时代,性才会成为生活主题,正如只有在饥饿年代,吃才会成为生活主题。”王小波通过性的问题进行了 “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反思”。王二正是要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向人们展现生活的常识、生存的规则,控诉摧毁人性的时代,体现出对个体的尊重,保存人的尊严。
王二除了行为上的反常识,在思想逻辑上也是反常识的。王二的思维与当时的大多数人背道而驰,大多数人用时代盛行的荒诞、反常识的生存逻辑来对生活中的任何事件予以“审判”,把人的尊严、人的权利当作玩具和游戏来践踏和摆布。然而,大多数人所遵循的所谓规则和逻辑甚至不符合常识和人情,让人啼笑皆非。如《黄金时代》第一章这样写道:
我是这样想的:假如我想证明她不是破鞋,就能证明她不是破鞋,那事情未免太容易了。实际上我什么都不能证明,除了那些不需证明的东西。春天里,队长说我打瞎了他家母狗的左眼,使它老是偏过头来看人,好像在跳芭蕾舞。从此他总给我小鞋穿。我想证明我自己的清白无辜,只有以下三个途径:
1. 队长家不存在一只母狗;
2. 该母狗天生没有左眼;
3. 我是无手之人,不能持枪射击。
结果是三条一条也不成立。队长家确有一棕色母狗,该母狗的左眼确是后天打瞎的,而我不但能持枪射击,而且枪法极精。在此之前不久,我还借了罗小四的气枪,用一碗绿豆做子弹,在空粮库里打下了二斤耗子。当然,这队里枪法好的人还有不少,其中包括罗小四。气枪就是他的,而且他打瞎队长的母狗时,我就在一边看着。但是我不能揭发别人,罗小四和我也不错。何况队长要是能惹得起罗小四,也不会认准是我。所以我保持沉默。沉默就是默认。⑧
又如,要证明陈清扬和王二的无辜:
我说,要证明我们无辜,只有证明以下两点:
1. 陈清扬是处女;
2. 我是天阉之人,没有性交能力。
这两点都难以证明。所以我们不能证明自己无辜。我倒倾向于证明自己不无辜。⑨
这是因为“大家都认为结了婚的女人不偷汉,就该面色黝黑,乳房下垂”⑩,陈清扬在这样的生存语境下,却要拼命证明自己不是破鞋,证明大家认为的所谓“常识”是错误的。如果一个人已被社会既定为一种“破鞋形象”,而这个人又千方百计想证明自己不是破鞋,实际上说明她已在内心认可了“破鞋可耻”这样的一种公共道德观,急于逃脱这个道德枷锁。如此一来,这个人就已经被这样一种道德观绑架了,开始了自证清白之路,而“清白”与否的标准界定,却是人们心中的反常识的判断,是一个无法证伪的问题。而王二却用自己对陈清扬破鞋形象的“认定”来对抗当时不符合常识的生存规则。
陈清扬竭力让王二证明她不是破鞋,王二却说“但是我偏说,陈清扬就是破鞋,而且这一点毋庸置疑”。这段话的逻辑看似有些无厘头,但实际上很有意思,有这么两层意蕴:第一层,王二所处的年代,人云亦云成风,个体丧失独立思考的意识。所以,跟随大众的偏向,对个体而言才是最为保险和安全的办法。对王二而言,即使在逻辑上无法证明陈清扬是破鞋,但事实上她是破鞋已经成为现实的口伐,是大众所指的“破鞋”。逻辑让位于现实,这就是特殊历史时期荒诞的生存规则。王二在起初只能非逻辑地跟随现实行走在荒诞生存规则的沼泽中。第二层,更为隐性的伏笔是,他计划用自己和陈清扬的媾和实现陈清扬是破鞋的事实,从而让陈清扬是破鞋在逻辑上获得完满。“王二”让荒诞在逻辑上获得合法性,从而解构了“革命年代”的生存规则。

用理性追寻生存智慧


王二的文化品格和理性的思索,恰恰表现出了对于人类存在的真正关注,表达了对于建构人类普遍价值和共同命运的关怀。王二只是历史潮流中一个普通的人,一个小人物,他处在那个虚空的年代,不去走溜须拍马、入党提干这样的道路,而是用生存的智慧告诉普通人,人应该如何理性、自由、真实地活着。这是千千万万的普通人难以做到的,正因为这一点,王二精神上的自由和理性才能获得文化与价值上的认可和期许。
王二作为历史大变革潮流下的知识分子,坚守了知识分子的理性思维,对理性的探寻经历了重重波折和困难。王二对理性的追寻有真实的一面,也有“智慧的虚伪”的一面。王二被“出斗争差”和花样百出的“批斗”折磨,王二在写交代材料时,事事都如实交代,包括和陈清扬敦“伟大友谊”的细节,弄得看材料的人尴尬不已又沉迷其中。后来,王二开始用自己的智慧保护自我、尊重自我,比如王二在人保组写交代材料时,没有交代偷越国境的事,因为他认为“没有必要说的话就不说”。后来,他带人保组的人去他和陈清扬住的地方实地勘察,王二指认场地,人保组无论如何不相信,后来王二就不带他们去看了,因为“没必要做的事就别做”。这是王二在苦难和愚弄中得出的生存智慧,也是王二对生存事实的一种尊重方式,对人的尊严的一种理性保护。《三十而立》中的王二,为了出国而奋力科研,结果出国的名额落空,自己被调包顶替,又被谣言弄得心神不宁,觉得生活很无趣,但是他却用自己独有的阿Q式的“乐观主义”生活,时时安慰自己。支撑着他而行的,正是理性的生存思维和对人性的洞悉。王二的理性建立在对社会规则的明晰之上,建立在他的生存智慧之上,王二明白多说无益多做无益,唯一的方法是用自己的生存智慧来理性地生活,保留“文革”时期作为人的尊严和底线。
钱理群曾在演讲中说,“本来在整个社会激进时,知识分子应该保守一点;当整个社会保守时,应该激进一点,这是知识分子和一般人区别所在。可中国的知识分子恰恰相反”。中国知识分子在政治的绝对控制和权力的重压下,往往不敢言,不能言,王二却通过真实的语言、异于常人的逻辑,甚至是“想入非非”的思维,来追寻失去的理性世界。王二在整个激进却无激情的时代,深切感受到“无智”民众被权力操控的悲哀,而王二在整个时代的“无智”中注入了“明白的理性”和“深沉的勇气”。
对生存趣味的挑战

《我的阴阳两界》中,小孙想要治好王二的阳痿,将来还会写一部纪实医学报告或者心理学、社会学方面的研究报告,要干好这件事,和王二结婚是必然的,否则就会受到社会的指责。考虑到这个伟大的计划,为了确保它的万无一失,还得演出恋爱的戏码,让世人信服。这样荒诞的“为科学而献身”的行为,究其原因:非婚同居治疗阳痿,是要受到社会舆论谴责的。乍一看,结婚治病似乎是一种荒诞的、不可理喻的做法,但实质上他们用这样荒诞有趣的行为来对抗社会中既有的信条,用黑色幽默来对抗荒诞,挑战公共信条,反抗权力。
被王小波称为“我的宠儿”的作品《黄金时代》中说道:“在我的小说里……真正的主题,还是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反思。”在文本中,王二常常在那个“革命时期”反思自己,反思权力,反思“革命”,反思生存状态。王二的生活也是有趣的,王二的生存空间主要在两个层面上:一是外在自然环境,即王二下乡插队所生活的“农田”、出逃的“后山”、“荒地”、“森林”、“玉米地”等,王二作为知识青年,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中生存,在田地上劳作,显然不能使自己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反而在荒谬的污蔑中,正常生活受到无端干扰,只得出逃到后山、荒地等清静之地寻求安宁,用“出逃”的方式来坚守自我。王二受了伤,不住医院,却突发奇想去了后山,过着一种恬淡的田园生活,好不逍遥自在,面对这样无趣无智的时代,他选择了自己创造生活的趣味,而非顺从于当时民众思想被控制的狂欢中。二是王二生存的人文现实环境,那是一个“批斗”横行、常常“交代”、相互倾轧的“无智”时代,这个现实的生存环境对于王二来讲,有着太大的残缺,王二为了坚守自由的精神,只能选择退却,用自己的生存方式寻找理性的自由和乐趣。
《黄金时代》中王二被打受伤之后,独自进山,罗小四带人去医院找王二,没找到,询问队长,队长却说“谁是王二?从来没听说过。罗小四说前几天你还开会斗争过他,尖嘴婆打了他一板凳,差点把他打死”。谁知道这样提醒之后,队长就更想不起来王二是谁了。于是,王二便说:“大家都说存在的东西一定不存在,这是因为眼前的一切都是骗局。”王二认为,“对于我自己来说,存在不存在没有很大关系”。公共性存在和个体性存在的关系,更多的是指,个体在一种社会公共关系中得到承认,比如在生产大队里大家是否认为有王二这个人存在的问题,在当时民众的认知中,王二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不被承认的小人物,而他也甘愿如此被不公共关系所认知,所以他觉得在这种公共关系中存在不存在无所谓。实际上,在那个时代,公共关系是不认可任何个体的。但是作为个体,他如何获得自身的存在认知呢?那就是从肉体性上,从他和陈清扬的性中获得肉体的认知,这是他能够确认个体存在的唯一方式,用肉体反抗宏大,用肉体证明存在。性是一种很个体性的行为,而且是不可取代的个体性活动。就像他人可以取代某个个体成为公共关系里的某种角色,比如队长、军代表等等,这种角色性的存在是可以被取代的,但是性是他人无法取代的。
性作为人类的自然需求,本来是没有颜色的,甚至应该是美好的。但是,从西方宗教的角度来看,禁欲、对性的压抑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特征;从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来看,性绝不是一个可以公开谈及的话题。王二们在小说中多是身强体壮的年轻人,性是他们的天性和自然需求,王小波的性描写是干净的,王二对待性的态度是坦然的、自然的、健康的。王二的颠覆性对抗则是用荒诞行为本身来对抗荒诞,展现其对生命欢乐的极力渲染与刻意张扬。正如《黄金时代》中的陈清扬,人们可以肆意谈论她的“破鞋”身份,但却不能公开谈论有关性的行为。性,成了王二的反抗方式之一,他用性来表达对社会权力和荒谬规则的对抗,是一种对非性时代的最具力量和颠覆性的反抗方式。《革命时期的爱情》中,王小波在序言中写道:“这是一本关于性爱的书。性爱受到了自身力量的推动,但自发地做一件事在有的时候是不许可的,这就使事情变得非常地复杂。”文本中,王二和老婆在英格兰,在一片森林里“享受一个带有雾气,青草气息和寂静无声的性”。性本是一种自发的行为,是个体之间的私密之事,但这样一个应当充分自由和自主的事情,在当时却变得狭隘和辖制,“革命时期对性欲的影响,就像肝炎对食欲的影响一样大”。王二用自由的性来反抗当时的“革命时期”,反抗压抑人性的时代。

王二形象的功能

王二作为时代里的小人物,他的形象超越了精英受难史带给我们的震撼和意义。王二是“知青”,是学校里的普通教师,是豆腐厂的小工人,是工读学校的校长;王二从来不是干部,不是手握话语权和行政权力的精英团体。但是,王二这样的小人物成为受难的主体,它的意义在于让王二形象承载更多的历史语境和历史功能。大众所熟知的精英受难事件,只是历史时期中的粒粒尘埃,王二作为小人物,用自己幽默的方式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受到缓慢的、侵入骨髓的倾轧和屠戮,这是更应被记住的受难细节。
王二形象的美学意义
王小波在《似水流年》中说:“在我看来,人生最大的悲哀,在于受愚弄。”而王小波笔下的王二却总是处在“看”与“被看”、“愚弄”与“被愚弄”的循环之中。正因如此,王二的形象显得颓废而又激进,痞子而又正经,富于诗意而又粗鄙不堪,在幽默的诗意中完成对生存世界的独特审美。
王二的人生如戏一般上演,一直在“看”与“被看”、“愚弄”与“被愚弄”中循环往复。《黄金时代》中,王二的人生是一场表演,和陈清扬一起“出斗争差”,“看”台下的观众,“看”其他一起被批斗的“演员”,仿佛自己置身事外,作为“人”在看一场滑稽的表演;而当自己和陈清扬上台,又变成了“被看”的演员,久而久之,已然对批斗会麻木了,陈清扬甚至做好一切准备,等待上台“被看”。斗争过后,王二和陈清扬回到住处,为了证明自己不是批斗的机器,而是有血有肉的活人,便开始用性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反抗权力的荒诞,拾回自己的尊严。这还不算完。王二和陈清扬经常被反反复复的审查弄得疲惫不堪,审查中,让他们写交代材料,他们积极愉快地汇报了搞破鞋的过程,也指认了发生“破鞋”罪行的场所,却不被领导和民众相信;审查过后的再次审查,又是问同样的问题,说同样的话,他们反反复复被权力所“愚弄”。然而,他们始终原原本本交代做爱的经过,弄得看材料的领导十分欣赏、躁动不已,他们用自己的真实“愚弄”了权力。最后,“被愚弄”的王二反而用自己的真实“愚弄”了掌握话语权的领导。

王二是个幽默的人,这种幽默不在于语言的滑稽,而在于王二敢于自嘲的性格。自嘲是一种自我矮化,王二的自嘲或许更像网络语言上“自黑”一词的含义。敢于自嘲,敢于自我污名化,为的是嘲弄外部世界,通过自嘲的行为揭示生存世界的荒诞和日常生活的真相。英国戏剧评论家马丁·艾思林在《荒诞派戏剧》一书中,指出了荒诞派戏剧的美学特征,其中一个重要的方式是:用轻松的喜剧形式表达严肃的悲剧主题。王二的自嘲、反抗更像是一出荒诞派戏剧的现实体验。《我的阴阳两界》中,王二被年轻的孙姑娘幸运选中,要为他治疗阳痿,后来阳痿还真被这种奇特的方式给治好了,王二又回归了正常的生活,上楼开会,被选拔为骨干,被单位公派出国……如果只是写到这儿,那王二的生活还是极其肤浅的生活,王小波的小说也是极其肤浅的小说。王二用黑色幽默所反抗的荒诞,它真正的意义在于揭示出:回归正常生活的王二,却像被套上了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就是自由的枷锁。卢梭曾说过:“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样荒诞、幽默、滑稽的故事有了这样一个严肃的悲剧性意味,这是王二的幽默意义。
结语

注释:
①王小波:《黄金时代》,《王小波全集》,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4页。
②王小波:《黄金时代》,《王小波全集》,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78页。
③王小波:《黄金时代》,《王小波全集》,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328页。
④王小波:《黄金时代》,《王小波全集》,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
⑤王小波:《黄金时代》,《王小波全集》,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
⑥王小波:《三十而立》,《王小波全集》,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56页。
⑦王小波:《似水流年》,《王小波全集》,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06页。
⑧王小波:《黄金时代》,《王小波全集》,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5页。
⑨王小波:《黄金时代》,《王小波全集》,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5页。











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