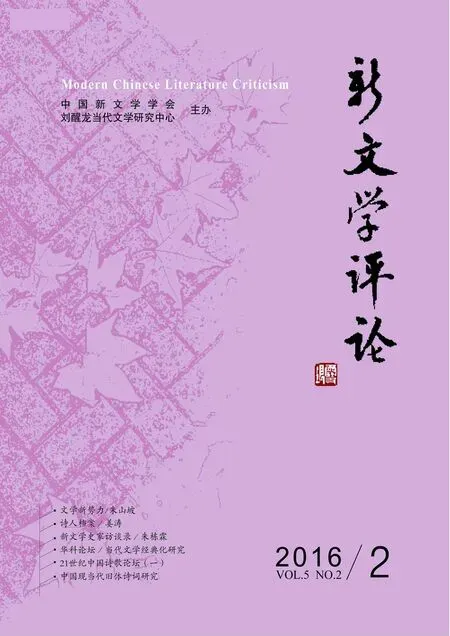“70后”的精神转型
———以朱山坡小说为例
◆ 唐诗人
“70后”的精神转型
———以朱山坡小说为例
◆ 唐诗人
一、“70后”的例外
对于“70后”作家作品的特征问题,很多论者指出它们普遍失去了历史的厚度,没有“50后”、“60后”作家作品的那种沉重感,难以在纯文学领域获得足够的正面评价。而相比于“80后”、“90后”,他们的作品又缺乏适应市场、适合大众阅读口感的语言和思想性质,因此难以在这个商品经济时代占据多少市场份额。持这类判断的评论者很多,比如洪治纲认为:“从代际群体的共性特征上看,他们既不像‘50后’、‘60后’作家那样专注于叩问沉重而深邃的历史,热衷于追踪幽远而繁复的人性,也不像‘80后’作家那样紧密拥抱文化消费市场,热心于各种商业化的文学写作,而是更多地膺服于创作主体的自我感受与艺术知觉,不刻意追求作品内部的意义建构,也不崇尚纵横捭阖式的宏大叙事,只是对各种边缘性的平凡生活保持着异常敏捷的艺术感知力。”②这种观点几乎成了人们对“70后”文学的基础共识,认为“70后”作家的思想更多的是向内挖掘,在自我性、主体性问题上下功夫,故事也更侧重于日常生活,很少向历史的纵深度扩展、向广阔的空间延伸。这种情况,在普遍有着史诗情怀和广阔视野嗜好的论者们看来,是有待提升和不够理想的。
仔细思考,这种认识或许与上世纪90年代末最早冒声的“70后”女作家作品特征相关。当时,棉棉和卫慧的作品大受“青睐”,引起很多争议之声。她们书写自我、描写欲望的率性风格,一度成为时代的弄潮儿。棉棉和卫慧那种飘满欲望的作品,无法在纯文学内部听到太多赞赏的声音,但却给人造成了一种印象,即“70后”女作家对欲望问题情有独钟。“欲望”确实是“70后”作家作品的关键词,物质欲、性情欲在“70后”作家的作品中遍地开花。比如后来的盛可以、魏微、周洁茹、金仁顺、冯唐等。当然,他们的作品呈现的欲望与棉棉、卫慧等人的有着完全不同的风景。盛可以的作品书写欲望,但更是用欲望来袭击欲望,抵达了先锋之域;魏微等人的作品,在书写欲望的时候,呈现了更多的困惑和反思,是一种更传统的叙述风格。冯唐的作品用一种“流氓”加“才子”式般的口吻把欲望之花开得迷乱、芜杂,有一种文学异类的气质。欲望之外,更多的“70后”作家关注的是日常生活中的诗意和痛苦,比如徐则臣、戴来等人的作品,徐则臣大多数中短篇都是以呈现日常生活中的问题而来,有着清晰的智气;戴来的作品充满内心话语,用日常的话题书写了人内心世界的广阔。不管是欲望还是日常生活,这种写作更侧重于以书写世俗生活来呈现一种深刻的存在之思,以欲望问题来探究主体性问题、灵魂价值问题。应该说,这些文学创作观念并没有问题。这呈现了它们独特的写作取向,但也因为这种取向,导致小说空间视野的不够宽阔、历史向度的不够深厚,限制了其影响力。
或许,这种写作取向更适合于中短篇小说。“70后”作家们擅长于截取生活片段,成就一种精悍的叙事,来发现生活的秘密,甚至冲击人性灵魂,体现作家的不俗思想洞见。这是“70后”作家们的长处。但于当前,热衷厚重的语境下,若这一代作家没能超越中短篇所塑造的日常生活见解,无法用长篇来书写一种完整的命运感,叙述一片宽阔的地理空间,呈现一幅厚重的历史画卷,用密实的生活细节和沉重的历史图景来触及一些深沉的灵魂之思。那么“70后”的命运很可能将继续尬尴。
可喜的是,近年来,我们看到了“70后”作家翅翼已近于壮实,他们或者把长篇写得充满历史的厚重感,或者有宽阔的地理视域,这些拓展让他们的小说生发了丰厚的生命经验,也使得“70后”作家所探讨的灵魂问题变得更为博大。比如《朱雀》,葛亮把这种苦难的家族史与苦难的南京城市史结合在一起,学习王安忆把历史放在“物”上的怀旧式叙事方式,同时也呈现一些民间话语,把这些凝聚在“朱雀”这一“文物”上,通过它勾连起了一座城市的苦难史,连带一个家族的生命历程。徐则臣最近的《耶路撒冷》,不但在空间上链接了故乡与生活之地北京,展现了非常宽阔的地理视域,而且在历史深度上有所挖掘,借助人物家族的命运,道出了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史,有着厚实的人物情感表达和沉重的家国命运书写。还有田耳的《夏天糖》《天体悬浮》,虽然没有挖掘历史,但他有意地要勾连乡村和城市,用侦探式的通俗故事实践了纯文学写作,融合了现实主义的小说叙事和现代主义式的精神品质,从一个别样的角度丰富了“70后”作家作品的精神气魄。
用厚度和深度来丰富“70后”文学视野和精神品质的作家还有很多,王十月的《米岛》、《收脚印的人》,乔叶的《认罪书》,这些都从各自的角度扩展了“70后”文学视野,也壮大了“70后”文学势力。此外,我们还必须特别地注意到广西作家朱山坡,他一直在寻找自己的例外性特征,以拓展“70后”风格来实现自我定位。他曾说:“……我一直有与当下的热门写作保持距离的自觉,不是我离群索居、故作高深,而是躲开,因为我写不过他们。其实每个作家都有开疆拓土的野心。我也有我自己的判断和追求,也许我要往这方向努力,无论是过去的作品,还是今后的写作,我都要努力写出属于自己的东西,形成自己的风格。在当代中国作家中,真正能形成自己风格的并不多,这并不说明他们不努力,而是不容易。”③这种追求的成功最直接地呈现在其最新的长篇《懦夫传》里。朱山坡用一种异样的风格充实了“70后”文学内质。《懦夫传》是一部有历史厚度,也有地域宽度,还有着鲜明先锋精神的长篇之作。《懦夫传》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它的出现让朱山坡抵达了文学之梦的新高峰,更在于因为它的独特性为广受质疑的“70后”文学添上了另一朵例外之花。如果说大多数“70后”作家作品依然存在着局限于日常、受制于欲望的小打小闹,那么《懦夫传》也如《耶路撒冷》、《夏天糖》、《收脚印的人》等“70后”作家的长篇新著一般,呈现了一种生命厚度,但又有着区别于它们的例外性特征,实现了一种从密室转向旷野、由内在性开拓出宽广空间的题材和精神转型。
二、由密室走向旷野
谢有顺曾有文章指出当代小说要实现一种从密室向旷野的精神转型:“当代小说要发展,我以为要着力解决一下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通过恢复一种感受力,接通一个更广大的物质视野;二是如何从一己之私里走出来,面对一个更宽阔的灵魂视野。”④就我的理解,这种转型既指精神上的放宽视域,走向博大精深,也指题材、故事上的解放,实现一种日常的、主体的向宽阔的、超越自我局限的写作。这种转型,对于“70后”作家来说,尤为迫切。
朱山坡早年写诗,他的诗有着清晰的地域色彩,乡土气息浓郁,有着对重大问题的关切,但总体而言,呈现的情感依然固执于自我感受。后来转向小说创作,一开始的一些短篇,比如他的第一篇小说《大宋的风花雪月》,哀婉动人的爱情故事,虽打着历史的旗号,其气魄却还是局限在情感世界。即使是最为人所欣赏的《陪夜的女人》、《天堂散》、《鸟失踪》等,更多的也是经验记忆,或者是一种想象,并没有超拔出日常生活。就如《陪夜的女人》,朱山坡曾谈论过这个故事的原型,即是他瘫痪了的祖父,在临死前一段时间总是在呼喊着亲人的名字⑤。《天堂散》的故事也只是一家人的情感伦理,写父亲的奇妙故事。《鸟失踪》也是书写父亲对鸟的爱,最后和鸟一起消失。这些故事基本属于点滴记忆的思想性想象延伸,显示了作者不浅的虚构能力和思想见地,但视域依然不够宽阔,能承载的思想含量也有限。
经过如上的化简.我们已经知道了一般的仿射坐标系下两个外积的坐标表达式.这个表达式中的每一项都是与e1,e2,e3这组基向量的选取相关的,但是最后我们算出来的结果却是与基向量的选取无关的量,体现了解析几何中的一个重要的本质问题:坐标只是一个强而有力的工具,我们更关心的是那些不依赖于坐标的选取而变化的量.
诚然,书写日常经验,并不直接等同于能量有限。《陪夜的女人》对临终老人的关怀,把一种临死的人心状况呈现,予人特别的感受。这个小说写出一个淳朴妇女的高贵品格。“陪夜”的职业可能并不存在,但塑造这样一个妇女,无疑是要为乡村世界继续守护一种沈从文笔下湘西式的风俗。在《躺在表妹身边的男人》里,表妹的伤,身边男人的死,都是底层社会的伤痛,悬念式的故事把底层社会中那些令人悲慨又带着温暖的东西传达得很细致。写底层的《灵魂课》、《最细微的声音是呼救》,是对城市高楼大厦淹没灵魂的现实进行文明批判。其他,《单筒望远镜》、《捕鳝记》、《爸爸,我们去哪里》、《骑手的最后一战》、《山东马》、《少年黑帮》等,有着特定历史时期的印记,用特殊的故事背景来抒写底层世界的苦难与荒诞。更如《回头客》,调用了历史背景,却把故事的核心放在村人与“乞丐”的交往中,书写时代灾难中人性的变化过程。这里不简单控诉历史,只是用它来衬托一种丰厚深幽的世俗人心。小说很短,缺乏细节,但可以绽放强大的光芒,它像个缩写的长篇,有很丰厚的想象空间。
可以感知到,朱山坡的中短篇小说,背景在什么时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有着清晰的现实指向。这“现实感”,或者是个人记忆之疼,或者是社会现实之病,“现实”的重量在小说中尤其突出。这是一种把“问题”置于小说中,有现实感、土地情怀、历史承担的写作观念。朱山坡曾经表示:“我的创作灵感来源于现实,但小说更多的是虚构。现实是窄小的、局限的、坚硬的,但虚构是无限的、浩瀚的和细软的,小说必须是从现实出发但最终回到虚构本身。”⑥他也在小说集的后记里明确说:“对小说而言,想象力和虚构能力比生活经验更重要。”⑦这种创作观并没有问题,但如果小说中的现实程度过于柔弱,虚构过于强盛,小说的思想性会压倒故事性,容易走向概念式写作。如《天堂散》、《鸟失踪》两篇,能够感受到一种浓郁的思想倾泻而来,故事戏剧性不强,但对老人的关怀感特别浓郁。如此,小说就显得单向度化,张力不够。
相比于朱山坡认为的小说写作想象力和虚构能力比生活经验更为重要一说,我更认同这样的看法:小说的虚构和想象必须有一种独特、细致的经验和记忆作为根基。正如普鲁斯特不断地回到某些记忆的原点,让想象去丰富记忆,让记忆变得饱满一样,也如略萨的小说中有着厚实的历史和生活经验,通过这些点滴记忆,再发挥想象,把干巴巴的记忆,叙述得感官饱满。厚重的小说必须要呈现广大的物质视野,就像《红楼梦》有着许多呈现日常琐碎事情的闲笔,《城市与狗》中有着大量看似无关紧要的杂碎内容一样,饱满的物质基础暗示的是作家丰富的素材准备和经验积累。当然,这里所谓的经验并非去经历一种和故事近似的生活,而是各种感受的经验积累,在运用于故事建构时,都自然而然地呈现出来。我还记得略萨在《城市与狗》中,阿尔托控告美洲豹谋杀,上校跟他谈完话、教训完他之后,阿尔托离开上校的办公室,他不坐电梯,而是顺着楼梯往下走,略萨这里这样写:“像整个这座建筑物那样,每层台阶都像镜子一样地光亮。”这笔看似简单,其实要有着细致的生活经验。失落的时候、被骂之后离开一座大楼,我们往往会选择走楼梯,而且是低着头,眼睛看着阶梯,对眼皮底下的东西有着特别的感触。略萨后来说这部小说有着儿时的经验,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感受式的东西是无法记忆的,这种记述只能是来自其他阶段的类似感受。平时、日常的感受都可以是小说的经验来源,虚构和想象也是因为有着这些记忆和切身感受的铺垫,而变得更为细密,更具真实感。
对小说真实感的要求,只能针对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需要精致,太多闲笔和杂碎内容容易分散小说的力度。朱山坡的两部长篇《我的精神,病了》和《懦夫传》,从标题中,我们能够感觉到一种先锋气息,思想浓郁,这是朱山坡小说一贯的特质。思想是展现一个作家最为核心、最为耀眼的层面。李敬泽先生曾说:“文学的创作需要一种思想背景,一个作家需要为自己建立广阔的对话场域,文学要把自己放回到一个时代的思想前沿上去。作家终究要和具体的活生生的心灵对话,但是如果他不是同时和这个时代最前沿的头脑对话的话,他可能根本不知与面前这一个的对话如何开始和如何进行。”⑧从这个角度来看,朱山坡的小说占尽了思想的优势。《我的精神,病了》,朱山坡的思考对象是城市文明对人性、灵魂的束缚。小说寓言性很强,用一种“精神病”的视角去观看城市自身的“精神病”。这是个乡村文明与城市文明碰撞出来的故事,用精神病者去认识,不仅仅是批评城市,也有着对乡村陈旧观念的反思。在《懦夫传》里,通过讲述一个懦弱者的生命轨迹,为懦弱者的性格树立起顽强的价值。小说有着余华《活着》的影子,但思想针对性完全不同。《活着》是悲悯大历史中的小人物,而《懦夫传》,是用历史来成就懦夫的坚韧,也用懦夫来讽刺历史的可悲。甚至,朱山坡似乎是在用长篇故事来阐释《活着》中的福贵何以能够一直活着!
从中短篇相对狭小的空间和浓郁的记忆感受,到长篇小说通往城市地理和历史时代,这能够见出一个作家的自我超越。《我的精神,病了》,空间瞬间放大,文本书写广州城,有着清晰的地理视野,这是作家视野扩展的直接体现。而在《懦夫传》里,除开有着宽阔的地理因素之外,更为清晰的是历史视野。懦夫马旦的性格,因为特殊历史的衬托才变得丰富。作者用懦夫形象来接触、观看历史,又是一个崭新的视角。由这两部长篇的题材特征来看,我们就已经感觉到朱山坡那从密室通往旷野的志趣和雄心。而且,这两部长篇通往旷野的方式,与以往现实主义风格的小说又很不同,它们都是由人的内在性延伸拓展而来,历史、地理等因素,是围绕某种精神特征和人物性格而去,而非传统的宏大叙事,在现代式的锐气上,补上了厚实的“物质基础”。《我的精神,病了》、《懦夫传》,既显示了朱山坡对自我风格的坚守,也表露出他超越自我的心力,逐渐延伸出宽广情怀和超拔野心。
三、用生命厚度挖掘灵魂深度
虽说长篇小说可以更清晰地实现由密室转向旷野,但并不意味着篇幅的长短即可成功实现一种真正的精神转型。继续检视朱山坡的转型,他的长篇叙述,以鲜明的思想作为标志的写作,有没有引发其他问题?
《我的精神,病了》中,叙述者是个精神病人,或者说被视作为精神病的“我”,这种叙事方法继承了现代小说喜欢以愚者、病者为叙述者的惯例。这第一人称,有一种误导作用,精神病人作为叙述者,那是不太可能的。这种叙述视角,先天地让读者赋予“我”同情感,会相信“我”所做的申辩,即“我”并非精神病人,而是被荒谬的城市文明逼迫为、强制为精神病患者的。搁置这种叙述视角问题,那么整部小说即是用“精神病人”的视角去观看城市文明。在“我”看来,城市才是真正的病者。“我”来自米庄,从乡村进入城市,规则在变,“我”用乡村伦理去碰撞城市规则,注定了一碰再碰、屡碰屡败,最后被送进精神病院。小说中,“我”与王手足的关系非常诡异。王手足打了我一巴掌,于是开始变得晕乎乎的,此后,“我”总是和王手足扯上关系。这一对底层人物,相互“厮杀”,也相依为命,最后王手足也成了乞丐、呆子,作者还让他们的手在垃圾桶里相碰。总体而言,这一小说是很有可读性的,事件堆叠而来,情节曲折变化,让人读了感慨万千。朱山坡曾说:“我认为,作家的最高思想境界是‘悲悯’,小说的最高境界是‘孤独’,表现手法的最高境界是‘荒诞’。”⑨这虽然是一种普遍性的、带着形而上色彩的观念,但《我的精神,病了》却用了具体的东西来呈现这些层面的特征。它对底层劳动者的悲悯,“我”是其中之一,王手足、凤凰、侯小耳、马茜等等,都是底层社会的辛劳者,结局都很悲惨;而“孤独”,对于“我”而言,被人看做精神病,后来回到家也无人认出来,母亲一口认定却也无能为力,“母亲”和“我”都是孤独者。其实,这里面每一个人最终都以孤独收场。“荒诞”方面,这是朱山坡小说最为清晰的叙事特征。“我”所遭遇的一切都是荒诞的,在“我”眼里的一切也都无法理解,荒诞、怪异把故事变得极具可读性,也让人物性格保持了一种恒性。
对于《懦夫传》,朱山坡曾经直言自己要为中国文学史树立一个经典的懦夫形象。我想,如果余华《活着》中的“福贵”能够成为经典,再继续百多年能够被人知晓,那么朱山坡笔下米庄的“马旦”,也应该借着福贵的影子,成为经典的人物形象。福贵不是马旦那样的懦夫,只是一个败家子,后来也只是逆来顺受、老实巴交的中国传统农民形象。余华塑造这一形象所用的篇幅不长,用历史点缀了个人的生命史,这里荒诞的是历史,而非人物性格,余华要从人物的悲剧命运中发现历史的残酷和现实苦难的深重,从大历史中拯救一种小人物的灵魂。《懦夫传》里,马旦的形象是以性格荒谬为特征的,历史成为烘托、成就马旦人物性格的情节要素,围绕马旦的一切都可以是真实的、正常的,只有马旦的懦夫性格被极端化、戏剧化。如果仅由此点判断,这确实更像是一个“漫长的短篇”。可贵的是,朱山坡希望树立的懦夫形象,确实弥补了文学史上的这一“性格缺憾”。而且,这一“补懦夫之缺”文本并不孱弱,而是有了饱满的内质。比如作品中的历史和战争,虽为侧影,但也勾勒得妥当恰切。把马旦这一懦夫虚构、嵌入历史的缝隙里,虽粗略,但已经有了广阔的视野。触及现代史上的军阀混战,是一种通往宽广世界和深厚历史的最清晰元素。此外,朱山坡对物质的关注,也有了更具生命力的表现。比如米庄的米,它就成功塑造了康姝形象,她对米的感情,呈现了饥饿感把人逼向荒诞的特殊境遇之实,又写出了米本身的现实和历史意义。

《懦夫传》的可贵之处,并不局限于书写出了懦夫的可怜与可憎,而是书写了懦夫性格在很多事情上非常值得敬佩。我们会跟着作者的叙述,一会儿为马旦父子懦弱无能感到可悲可气,一会儿又可以对马旦的懦弱性格倍加欣赏。这种阅读感受的变化,其实就意味着朱山坡小说观念的成熟,它不是简单地批判,但也不可能单向度地欣赏。虽然要讲述一个懦夫的典型性格,他也时刻把懦夫、懦弱等近似含义的字眼放在小说中,但这并不使得懦夫性格就是单一的含义。很多时候,朱山坡也表达了“懦夫”不等于软弱、更不是恶劣的形象特征。比如马旦一心为妻子赚取米饭,为了填饱康姝的肚子,他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可以舍弃,这是一种最伟大的责任感。在这样的观照下,与其说朱山坡要书写一种性格,不如说他是呈现了一个完整的人。一个完整的人,那肯定有优异之处,也会有悲哀所在。同样,性格也是如此,并没有哪种性格就完全等同于一种性质,懦弱与悲哀、可怜并不相等,勇敢和可贵、可敬也不天然相通。朱山坡这种写作,抵达了其所认为的作家之最高思想境界,即悲悯——在懦夫性格中看到了何为卑弱、何为伟大,在残酷的历史里见证了何为真正的软弱与勇敢!
由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出结论。朱山坡近年的小说,自觉地逃离了多数“70后”作家沉溺多时的写作状态,从一个侧面透露这“70后”作家的精神转型。对于朱山坡,这种逃离除开依靠自身成长经验的特殊性,更依靠他对文学的独到理解。他的中短篇故事有着清晰的乡土、底层、苦难、记忆、历史等元素,这与城市出身的多数作家完全不同。他的很多作品,虽视域不宽,但可以不拘泥于个人、不参附于欲望,而是有着深广的关怀社会意识和沉重的灵魂凝视追求。而其长篇小说,也尽可能地拓展故事的空间和时间,努力去书写城市与乡村世界的广阔性,去呈现历史与个人命运的隆重感。这一切,让注重内在性的“70后”写作,开始彰显宽大的辐射力,逐渐通往更为宽广的物质世界,透视出他们正在雕刻一些更完整、更博大的生命体和灵魂世界。
注释:
①陈思和:《低谷的一代——关于“70后”作家的断想》,《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6期,第122页。
②洪治纲:《重构日常生活的诗学空间——代际视野中的“70后”作家论》,何锐主编:《把脉70后》,江苏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
③郑小驴、朱山坡:《我追求什么样的小说》,《文学界·专辑版》2011年5月,第56页。
④谢有顺:《从密室到旷野——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转型》,海峡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151页。
⑤朱山坡《〈陪夜的女人〉创作谈》,《广西文学》2010年第2期,第94~95页。
⑥郑小驴、朱山坡:《我追求什么样的小说》,《文学界·专辑版》2011年5月,第55页。
⑦朱山坡:《灵魂课·后记》,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291页。
⑧李敬泽:《思想性断想》,见李敬泽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4002d30100g97s.html。
⑨郑小驴、朱山坡:《我追求什么样的小说》,《文学界·专辑版》2011年5月,第56页。
⑩心懿、朱山坡:《经典是一种理想——朱山坡访谈》,见朱山坡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32afe30102vn2l.html。

中山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