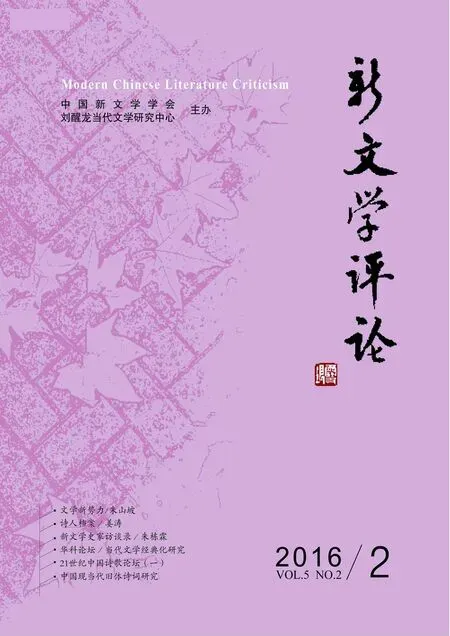圈套·虚幻·隐蔽·多声
———论朱山坡小说的叙事修辞
◆ 陈 莉
圈套·虚幻·隐蔽·多声
———论朱山坡小说的叙事修辞
◆ 陈 莉
朱山坡从2005年以黑马的身份闯进文坛至今,已经渐为广大读者所熟悉,2010年他以《陪夜的女人》获得首届郁达夫文学奖短篇小说提名奖之后,在全国文坛中便占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2015年金秋时节,朱山坡作为“广西后三剑客”的成员在北京的研讨会上为众多评论家所认可。朱山坡是个勤奋的作家,有着强烈的创作自觉意识,在形成自己创作风格的道路上执着前行,他说:“阅读、思考、观察、争论、情怀,与虚无的抗争,对世俗的质疑,精神病一样对存在的东西进行永无休止的探究和追问,在这过程中,作家像蚂蚁储备过冬的食物一样积攒自己的力量。我不害怕自己从少年变成了中年,又从中年步入老年,而是害怕我无法积攒足够多的力气去完成下一篇小说。”①尤其是经过这几年的积攒,朱山坡的创作成绩斐然,他写作上的丰收并不仅仅止于数量上的增加,更重要的是他在这些年的不断探索中,努力超越自己,在文坛上发出了自己日趋成熟、日渐独特的声音。
每一个作家穷其一生进行创作,都希望有朝一日能形成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风格就如同DNA,专属于某个个体生命,是作家对人生的感悟,也是作家生命的独特表达。朱山坡在一次题为“我追求什么样的小说”访谈中曾谈到他的《陪夜的女人》:“我很喜欢这种从容、淡雅、不动声色的叙述,宽阔而深厚的内涵,独特而诗意环境,尤其是诡异、惊险和回味深长的结尾。……我把小说的环境移到了富有江南水乡意味的凤庄,安排了一条神秘的船和一个来历不明的女人,时空交错,真假难辨,事关生与死、命运与爱情、坦荡与恐惧、亲情与救赎,混沌,暧昧,模糊,似是而非,很难三言两语把它说清楚。虽然它远非完美,但体现了我对小说的另一种追求。”②从这段话中不难看出,朱山坡对小说文体的审美追求旨在营造小说的叙事氛围:神秘,模糊,真假难辨,似是而非……综观朱山坡的小说文本,这样的叙事修辞效果在其作品中一再显现出来,造成一种斑驳隽永的韵味,让读者意犹未尽,回味无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看你怎么讲出来,这种讲述的方式就是作家的叙事修辞。
在朱山坡小说中最常见的四种叙事修辞手法分别是设置圈套、制造虚幻、隐而不谈和多重声音。作者在讲述故事的时候有时是设置叙事圈套,有意造成读者的误读,结局却出人意料。或者是通过制造幻觉,精神迷离,造成一种时空交错,亦真亦幻,诡异神秘的效果。抑或是作者干脆选择将情节线索直接掩蔽,隐而不谈,留下一个谜团,直至结局都没有揭开谜底,留给读者无限的想象空间。多重声音指的是言说的困境,作者让故事由不同的人物去叙述,他们讲述的事件内容既有重叠又有分歧,真相依然似是而非,悬而未决,没有定论,直至小说结尾作者也没有给出答案,令读者依然无法抵达真相的彼岸……这四种修辞手法与作者选择的叙述者有很大的关系。当作者确定创作一部小说时,他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选择一个恰当的叙述者来讲述故事。传统小说通常会选择一个全知视角,即全知全能的叙述者去讲述发生的故事,结局往往也是封闭的,读者在故事的结尾知道了事实的全部真相,作者会对人物的结局进行交代,事情最后的解决等等,总之谜底得以揭开,真相大白……朱山坡在小说中虽然也选择了第一人称“我”作为叙述者,但是作品中的“我”的视角常常是有限的,“我”做为作品中的人物,既无法亲历故事主人公的境遇和内心感受,又不能解释所见,只能将所见呈现在读者面前,由读者自己去解读。
圈套
作为有特定视角和目的的叙述主体,他不仅仅报道故事世界,也反射出他如何观察故事世界,同时他的观察又影响了读者的观察。设置圈套是指作者让叙述人讲述自己的经历和境遇,作者不动声色,一直小心翼翼地掩藏真相。《躺着表妹身边的男人》里运用的就是设置叙述圈套③的修辞手法,作者选择了第一人称“我”作为叙述者,“我”作为表哥讲述着表妹的全部经历,“我”的视角很灵活,时而有限制,时而无限制,无限制表现在“我”对表妹的一切是全知的,有限制则表现在对表妹以外的人和事则是无知的。因为“我”在讲述表妹的经历时而采用内聚焦方式,有时又转向外聚焦,叙述者并不知道除了表妹以外的事情。在整个故事中只有作者本人才是全知全能的,他有意设置了这样的叙述圈套:我显然不是跟着表妹亲历她的所见所感,因为在文中“我”的出场是当班车到达株洲站时,表妹下车时我才出现接表妹。但在讲述表妹经历的全部过程中“我”却如影子一般跟随表妹,讲述她在长途班车上经历的一切,甚至可以聚焦于表妹的内心世界:“他躺着里面靠近窗口的座位上,被子已经盖住了他的半边脸。他的脸斜对着窗口,背对着表妹。表妹觉得他臃肿的身躯稍稍越过了中间线,侵占了她的领地,而且他有可能得寸进尺甚至在离株洲还很远的路上将她重重地压在身下蹂躏她。这个推测使她警惕起来……”第一、第二句话显然是外聚焦,是表妹看到的情景,而第三句的“觉得”已经属于内聚焦,呈现了表妹的内心想法,对过界的男人可能做出的非分行为都进行了推测,此时的表哥已经暂时充当了“上帝”的角色,告诉了读者此时表妹的所思所想,“我”的叙述让我们了解表妹身边发生的事情和表妹的内心反应。在这里“我”的视角等同于故事中表妹的视角,读者享受着这个叙述者提供的所有信息,直至表妹醒悟过来:这个躺在她身边的男人原来是一具尸体!这种惊骇不仅来自表妹,同时来自读者,结局如此惊心动魄!
同样的圈套还在《小五的车站》中再次设置,十四岁的小五独自一人第一次乘火车从株洲去遥远的玉林给外婆过生日,故事是以小五的第一人称“我”来讲述此次旅行,母亲反复叮嘱“我”:火车上只有乘务员的话才可以信任,她(他)会提前告诉你哪个站快到了,你要准备下车了。“我”之所以相信了坐在“我”对面的年轻女人的话,前提是“我”对她的好感,也因为列车上的广播声音含糊不清,加上方言口音太重,根本听不清楚乘务员到底说什么。而女人因为不想搭理不怀好意的男乘客的搭讪而对之撒谎说自己是到玉林下车,她的话既搪塞了男乘客也让小五信以为真:“女人将在玉林下车。我也是。我只要跟在她的屁股后面就成了。因此,我不再需要伸长耳朵猜测乘务员的广播或伸头捕捉火车站的站牌,心一下子轻松起来。”这里展现的“我”是作为一个孩子的视角对事件的态度和看法,包括“我”对年轻女人的信任、对占了我位置的“一直打着呼噜的看上去穷凶极恶的男人”的厌恶,还有对后来上车的“比那头死猪还要粗俗”、“满嘴烟味,一身肉气,脸上还堆着下流的笑意”的彪形男人的憎恶。通过一个十四岁孩子那双对世事尚未充分理解的眼睛,他将自己所作所为所思所感不修饰地描述出来,这种讲述是主观性的,而作者未加干预,一任小五的讲述引导着读者,结果,读者和小五一样错过了玉林站。
高明的作者设置的叙述圈套往往选择了这样一个有限视角的叙述者,因为限制的视角使得他所见之处必有盲点存在,作者总是不声不响地放置好他的圈套,精心包裹起真相,既不显山更不露水,让读者跟着叙述者进入作者早已布置好的圈套中去,让读者跟着叙述者一起上当受骗。
虚幻
制造虚幻是朱山坡小说叙事修辞的第二种方法,让故事中的人物产生幻觉导致叙事如同梦魇一般,故事情节虚幻离奇,事实真相支离破碎,叙述者自己无法解释,作者也没有把真相提供给读者。这种修辞方法营造的是小说氛围的诡异和神秘。如《捕鳝记》里“我”跟父亲在深夜到河里捕鳝,父亲在前面,我举着火把跟在后面,开始父子间还有你问我答的对话维系着,我后来再没有听到父亲的声音了,父亲彻底消失在黑暗里,恐惧、寒冷和饥饿导致我产生了幻觉,见到了死去的母亲,最后我躺在母亲身边,母亲把我轻轻地搂得更紧了……现实和幻境、真实和虚幻交织在一起,我已经完全迷失在一片虚无中。
《送我去樟树镇》中的“我”接到母亲来电:“儿子,你爸还剩下最后一口气,就想看你最后一眼。”于是我挂了母亲电话后开车回老家,作品讲述了“我”在一个“暴雨如注,狂风大作,天地间漆黑一团”的夜晚在高速路上的离奇遭遇。“我”在高速路上靠边停车撒尿之后“无意中看到前方的路旁靠防护栏处站着一个人”!闪电中我看清了“一个女人瑟缩地站立在雨中,穿黑色裙子,白色衬衫,没有雨具,雨水直接打在她身上,长发遮挡了她半边脸。我被吓得惊叫起来。脑子里首先想到了鬼”。这里写了“我”当时的惊恐:我浑身冒着冷汗,双手和腿都禁不住颤抖……“女人直了直腰,理了理头发。她的嘴唇发黑,苍白的脸上竟挂着诡异的微笑,好像对我不屑一顾,又好像对我早已经了如指掌,在此等候多时”。这个如鬼魅一般的女人要求“我”送她去樟树镇,作者把“我”与女子的相处写得惊心动魄、毛骨悚然,那女子除了重复说“送我去樟树镇”和“后面的人追杀我”!还说了一句“本来我已经死了,可是现在又活了过来”,更让“我”胆战心惊,感到寒气逼人,读者也因此汗毛直竖。后来女子莫名其妙地消失以及我在服务区遇见的中年男人肯定无疑地宣称:“世界上根本就没有樟树镇!”更加剧了作品的诡异气氛,而“我”回到家后,“哥哥提醒我,父亲在一年前就去世了。……母亲是老糊涂了……我也彻底糊涂了”。作者通过离奇的情节、鬼魂似的女子,糊涂的母亲和糊涂的“我”来制造虚幻,使得情节扑朔迷离,构筑了小说的奇幻空间,营造了神秘诡异的故事气氛。
作者在《灵魂课》里塑造了一个“脑子吓坏”的老妇人形象,采用的叙事修辞手法也是制造虚幻。“我”是灵魂客栈的骨灰盒保管员,有一天接待了一位老妇人,她来寻找儿子阙小安的骨灰盒,执意要把儿子的灵魂带回家。“我”还陪同老人去阙小安生前寄钱给老人留下的地址:民主路时代大厦三号工棚。老人告诉“我”,阙小安跟堂兄弟来到城里当建筑工人却从脚手架上摔下来摔死了。“我”根据地址后面记的电话号码找来了阙小安的堂兄弟,让“我”意想不到的事情是,来人就是阙小安本人!“我惊愕不已,脑子一下子乱了。”原来,摔死的是阙小安的堂兄弟,阙小安并没有死。但是阙小安堂兄弟的死讯吓坏了阙小安的母亲,老人家因此产生了幻觉,认为阙小安已经死了。作品中老妇人的言行举动和她对灵魂存在的执念令人印象深刻,老人第二次出现在灵魂客栈是在半年后,她手里捧着一只骨灰盒,“老人用颤抖的手,艰难地将盒子举放到九号位,然后一丝不苟地将它摆正,直到认为稳妥了才松手。‘谁的?’我的心一沉。‘阙小安。’老人的脸上已经没有了悲伤,或者说她被皱纹和污垢覆盖的脸已经无法展示她应有的表情,‘摔死了,粉身碎骨,魂飞魄散……他不愿意回家,死活要留在城里。就让他留在城里吧,反正他的灵魂我也带不回去’”。鉴于之前老人说过阙小安摔死实际又没有死的事实,“我”的反应是“我将信将疑。从老人的神态和表情我完全看不出真伪”。“我”作为叙述者第一次听到老妇人讲述儿子阙小安摔死的事情时信以为真,结果并非如此。当“我”再一次听到老妇人说阙小安摔死的事情时还是无从判断,无法辨明真伪,在这里作者通过一个被惊吓后“脑子已坏”的老妇人来制造虚幻,混淆视听,真真假假,真假难辨。到底阙小安死了没死,“我”不知道,读者也不知道。
隐蔽
隐而不谈是朱山坡小说中一个重要叙事技巧,如果说设置圈套是作者利用叙述者有限视角的盲点,让叙述者在讲述开始时并不知情地进行叙述,但到了故事最后作者还是会将谜底揭开,让读者与叙述者同时获得事实真相的话,那么隐而不谈则是作者有意将真相隐蔽,自始至终就没有打算告诉叙述者和读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作者有意让疑团悬而未决,直至最后还是没有结果,读者掩卷之余依然会对故事里的某些疑点念念不忘,究竟发生了什么?读者依然惦记着故事里的某个人物的下落,想知道他(她)的最终去向,他(她)究竟去了哪里?还会不会回来诸如此类的问题……但是作者就是选择有意隐瞒事实真相,拒不交代。
《一个冒雪锯木的早晨》里那个陌生男人戴着爸爸的帽子出现,声称是来替爸爸办事,“陌生男人说,你爸爸在监狱里吃不饱饭,每天饿得睡不着觉,让我给他捎带一些吃的东西”。面对这个一再索要粮食的陌生男人,兄妹三人表现出的态度是不一致的,在这里作者显然充分考虑到了他们三个孩子因为年龄和经历的不同在处理事情时候判断力的差异,哥哥略显成熟,在整个过程中始终保持着怀疑态度,甚至采取了迂回的策略,回应陌生男人:“我妈妈不在,事情由不得我们做主。”“我”则稚嫩一些,相信了陌生男人是爸爸叫来的,“我”更关心的是“我爸爸在监狱里好吗”?而妹妹最幼稚,对陌生男人深信不疑,把家里所有的玉米棒都端到了陌生男人的面前,“‘好了,你一定要将它送给我爸爸。’妹妹郑重其事地嘱托陌生男人”。最后,男人拎着玉米棒走了。“他的脚印很小,像狼走过的痕迹。”这句话是从“我”的视角进行描述的,将男人比作了狼,细细品读,让读者似乎隐约感觉到了那么一丝不安和不可名状的其他东西。一直到作品的结局,这个陌生男人究竟是谁?是不是真的如他自我宣称的那样是爸爸叫他来家里拿吃的?这些疑点一直萦绕在读者的脑海中挥之不去,而作者不打算给出答案,反而再一次推出新的秘密:“此时从屋子里传来妹妹一声撕心裂肺的惊叫。哥哥连滚带爬,风一样扑过去。被他卷起来的雪,在我眼前溃散开来。”作品以这样的场面作为结局再次设置了新的疑点:屋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妹妹为何撕心裂肺地惊叫?失去了全部粮食的兄妹三人最终的命运究竟如何?这一系列的疑团也随着结局的到来而弥漫开来……
朱山坡的《信徒》在开篇迅速地吸引住了读者的眼球,他设置了这样一个场景:“夜里十二点,按照平时的习惯,我早已经睡着了。但昨晚是个例外。昨天我有了一堆钱——甭管从哪里来的,多得让妻子睡不着觉,她兴奋得一直在数。”之后,妻子一遍又一遍地数那一堆钞票,数到了第十三遍还是无法知道钱的准确数额,“她发狂了,较真了,来劲了,无论如何也要得出一个准确的数字,中途我曾三次提出做爱,都被断然拒绝……”在我打算睡觉,妻子依然乐此不疲地数钱的时候,家里突然响起了急促的不容拒绝的敲门声。“我本能地弹跳起来,心里咔噔一声,手忍不住颤抖。妻子惊慌失措地跑出来示意我不要开门,还让我去厨房取菜刀,我去了厨房一趟回来,她已经把刚刚整理得整整齐齐的钞票胡乱塞进一个行李包,在屋子里到处转了几圈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秘藏的地方。”面对敲门声,夫妻俩惊恐慌乱的表现更激起了读者对那一大笔钱的来路的好奇心,妻子既担心是警察找上门来,也怀疑招来了劫匪,面对妻子的担忧和疑问,我也不知道究竟是警察还是劫匪,但是我已经做好了准备:“菜刀已经放在饭桌底下,随手可取。”看来情势危急,“敲门声越来越急促,要是再不开门,会破门而入了。我只好去开门。妻子咬咬牙将装钱的行李包扔到了阳台的杂物堆,跟那些旧报纸、废弃的塑料袋混在一起。然后跑进书房,抚慰可能被惊吓到的女儿。看上去,妻子沉着机智”。
作者花费了一番心思去营造小说开头的紧张气氛,充分调动起了读者的阅读兴趣:那一大笔钱是怎么来的?半夜急促的敲门声更加深了读者的好奇心和疑虑:钱的来路和去处是什么?但是作者接下来给出的情节跟这笔钱再也没有任何交集直至到小说结局都没有再直接提到这笔钱(关于这笔钱在后来的叙述过程中隐晦地提到两次:妻子“猛然想起了什么,站起来,径直往阳台走去,踢了踢什么东西”,“我瞅了一眼饭桌底下的菜刀”),这个疑团就一直保留到读者读完整部小说也没有得到解开……半夜造访的不速之客是“我”的同事,也是妻子的大学同学兼前男友郭敬业,接下来的篇幅主要集中在讲述郭敬业的故事——尤其是郭敬业糟糕的夫妻关系上。谈话中我无意发现郭敬业的裤脚上有血迹。“淡淡的,星散的,像一朵朵没有枝蔓的桃花在黑暗中慢慢地舒展开来。”面对“我”的疑惑,郭敬业的回应是:“‘我太爱她了,你不明白。’郭敬业一再解释说。他又重复了一遍绳索绞紧脖子的动作。……‘刚才我把她做了。’郭敬业斩钉截铁地说。……郭敬业直了直身子重复了一遍:‘刚才我把她做了。’……郭敬业激愤地说:‘她外头有人了……’”一直到小说的结局,那笔钱的来路都没有交代,又加上郭敬业裤脚上的血迹和郭敬业妻子的生死都让读者疑点重重。小说的最后结局是:“我去打开房门,让郭敬业离开。时候确实已经不早了。郭敬业迟疑了一会,双手一甩,昂然抬脚离去。门外月色撩人,夜空如深渊。”作者显然压根就不打算告诉读者真相是什么,任由疑团不断地扩散,弥漫,如深渊一般的夜空,不可捉摸。
《等待一个将死的人》的开头和《信徒》的开头有异曲同工之妙,作者开篇便营造了一个紧张得令人喘息不过来的气氛:“春天刚过,突然来了一场洪水,把米河上的石拱桥冲垮了,还来不及修复,便传来阙越要回来的消息,村子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了。”接下来作者将全村人的各种表现以及阙越的过往一一展现,阙越对妻子淑媛的冷淡和谩骂,还有作品中屡次提到的湖北女人以及最后把淑媛母子接走的陌生男人究竟是谁?“我”哥哥在阙越回来前到镇上给妈妈买药,回来时因为搭桥的人不让他通过,“哥哥说,我去寻找第二座桥!……他一副毅然决然死不回头的样子,沿着河岸一直往南面走去……哥哥很快淹没在狗尾巴草丛里”。哥哥何去何从?爸爸也曾经外出去找过哥哥,但是回来后的爸爸“描述了南行看到的形形色色光怪陆离的奇闻怪事,唯独没有提到哥哥”。哥哥就这么消失在叙述人的讲述中,对于作品中的所有疑问,作者并没有给出任何的答案。
同样的情况还表现在《爸爸,我们去哪里》中的爸爸在对待那个瘸腿女人的态度也是令人费解的,一会儿跟儿子诋毁那个女人不知廉耻是母狗:“你妈妈跟她不一样,你妈妈从不在别的男人面前喂奶——只有母狗才让自己的乳房露出来让所有的人看!”在看临刑前的犯人吃东西的时候父亲又尽一切努力帮助这个女人,甚至在作品的最后父亲又带着“我”去寻找这个女人,“我”无法理解父亲的做法:“‘我们和她素不相识,为什么要找她啊?’我对父亲的不可理喻第一次流露出不满。”而父亲给出的答案却是:“‘她是你妈妈!’父亲不耐烦地吼叫着说。”对于父亲前后行为和语言的自相矛盾,“我”作为观察者不可能以理性的是非标准来衡量、判断。“我”对自己所遭遇到的外部世界的复杂面貌充满了迷茫不解,这显然是作品采取的儿童视角决定的,关键是作者也没有告诉我们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作者有意隐蔽了事实的真相,疑团再一次弥漫开来,一如小说的结局“沉重的江面开始缓缓下沉,越来越低……奔腾而至的夜色很快便要把我和父亲一并淹没,谁也将看不到我们,我和父亲也将看不到对方。”
多声
多声是指作者在构建自己的叙事话语时,让多个叙述者讲述同一个事件,每一个叙述者都从自我意识出发去描述客观世界,这样便形成了叙事的多重声音。每一个叙述者关注的问题不尽相同,他们的讲述有交叉的地方,有些却大相径庭,形成了“多声”的叙事模式。这样的叙事修辞效果打破了小说结局的封闭性结构,让意义因此变得不确定,文本的内在张力得以形成,小说呈现为一种开放式的叙事结构。
这种“多声”的叙事模式在《跟范宏大告别》有所体现:垂死老人阙天津在临终前念念不忘的是一个叫范宏大的人,他执意要在死前找到范宏大跟他告别。这桩夙愿未了老人死不瞑目,于是老人的四个儿子用担架抬着老人去寻找范宏大。范宏大到底在哪里呢?他过得怎么样?不同的叙述主体对范宏大住养老院的经过讲述都各有侧重:阙天津老人认为范宏大“到县城跟他的表侄,表侄却把他送到了养老院,跟一帮素不相识的老家伙在一起,岂不等于坐牢”?而儿子们都知道范宏大“他的远房表侄在县城开了一间收购废旧物资的店铺,正需要他的帮忙。他虽然年纪大了,但力气也还有,甚至还能干重活,诸如搬运旧货物、看守店铺。……四五年前的一个夜里,范宏大起来轰赶小偷,却一脚踩进废旧堆,被一根钢筋刺穿了右小腿,筋骨断了一截,瘸了,干不了重活,他的表侄把他送到了养老院。养老院好呀,吃住不愁,用不着干活,连洗澡拉屎也有姑娘服侍,省得久病床前无孝子,在家被子女讨厌。米庄的老人们对范宏大羡慕不已,唯独阙天津老人不以为然,哪里是享福?养老院是供人待着等死的地方”。两代人对养老院的看法呈现出不同的价值观念。
阙天津的儿子们抬着担架走了两天的山路把他带到县城后,他们找到了养老院,但是养老院的守门老头却说:“范宏大?不就是那个又聋又哑的老瘸子吗?三年前就离开这里了。……他交不起费用,帮他交费用的表侄,失火烧光了废旧站,破产了,养老院跟旅馆一样,交不起钱就得退房……范宏大都退了三年了,他走的时候写了一张字给我,说自己快要死了,得回乡下跟亲人告别,人活一世,走前总得跟谁说一声。”阙天津一行人找不到范宏大很失望,守门老头追出来说:“两年前,他在东门菜市北门口看见过范宏大,吃别人的剩饭剩菜,好像还做起了乞丐……”在东门菜市,“老大看见了一个人,一个老头,半躺在栏杆缺口的内侧,穿着破烂的黄色雨衣,但狭小的雨衣并不足以保护他的全身,或者是他故意露出了他光秃秃的右腿。这条褐色的腿最醒目的不是涂抹了一层红药水的膝盖骨伤的黑洞——一个令人恶心和震撼的黑洞,仔细看也许还能看到里面的骨头,而是写在小腿正面上的两个大大的蓝字:骨癌”。当阙天津老人认出这是“范宏大”的时候,旁边又有人提醒他们:“你们不要相信这个老瘸子,他在这里乞讨三年了,哪有骨癌能挨三年的?我从来不可怜骗子。……他原来待在养老院的,菜市场的人都认得他,都没有人给他钱了,也不换个地方试试。”当阙天津要去扶起“范宏大”的时候,“范宏大”突然甩掉老人的手,猛站起来,挣扎着往菜市场跑。阙天津命令大儿子快去拉“范宏大”要把他带回米庄去!“然而让老人吃惊和失望的是,那老头突然回头嚷嚷地蹦了一句:他妈的什么米庄?五毛钱竟把老子的美梦吵醒了!”在作品里对范宏大状况的讲述有多重声音,这种众声喧哗的叙事模式让寻找范宏大的目的彻底破灭。
同样的“多重声音”叙事模式还出现在《最细微的声音是呼救》。作品讲述了派出所实习民警小宋接到一个老太太的报案:仙鹤居民小区有人呼救。报案人说“虽然不知道声音从哪里传来,但确实听到了低沉的、哀求般的呼救声,尽管声音低微,若隐若现,如海面上溺水者的惊叫,但还是像闪电一样穿透了她们的耳膜,让她们既心惊胆战又焦虑不安”。小宋前往小区进行调查,根据报案人的线索敲开了小区七幢四楼402号单元的门,据说,呼救声是从这套房传出来的。但是房子的主人矢口否认说:“不是……肯定是你们听错了。”随着小宋又在上一户人家的指点下继续走访、调查、询问,不管问到的是哪家,大家都承认听到了呼救声,但是都否认了呼救声是从自己家里发出的,都认为是别人家发出来的呼救声,调查最后毫无结果。直至查到了顶楼的小水塔,小宋仔细端详了一番小水塔,似乎发现了秘密似的:“呼救声是小水塔发出来的!”面对保安的质疑,“小宋不容置疑地说,就是小水塔发出的呼救声!”之前每一层楼的住户对呼救声的种种判断都不可靠,因为作为有特定视角和目的的叙述主体,他们各执一词,他们不可能带领读者抵达事实的真相,而文中的叙述者之一小宋以民警的身份试图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至此,看似关于呼救声的秘密终于被揭开了,人们终于找到了根源。但是作者并没有给予任何一个叙述者以最终的权威,作品结尾处再次对这个做出权威论断的叙述者小宋进行否定,解构了他的叙事权威性:“小宋离开仙鹤小区的路上,耳朵嗡嗡地一路响着,开始以为是什么噪音,可仔细一听,却是低沉而急促的呼救声。这声音不知道是从哪里传来的,好像从遥远的地方,又好像就在身边;听不清楚是谁发出这声音,好像是正在捡破烂的小老头,又像是行色匆匆的陌生人……反正是有人呼救。”
这种“多声”的叙事模式让形形色色的叙述者自由地展现自己的观点,任何一个独立的叙述者都无法成功地讲述所谓的真相,任何尝试归纳和判断真相的企图和努力都将以失败告终,“多声”叙事模式就是要告诉读者:在叙述中,根本就不存在焦点和权威,个体不具有追寻真相的可能性,谁也无法讲述世界的真相,我们要探究的真相或许就隐藏在这些声音之中,也许,这些包罗万象,众声喧哗的声音本身就是世界的真相。
小说就是要讲故事,“许多人怀着读到一个完整的——一个拥有清晰的结构和‘信息’的故事的愿望来阅读小说”。读者阅读小说通常希望获得一个满意的结局,在文本的最后所有的疑团终于解开,秘密将得到揭示,真相大白于天下。朱山坡设置叙事圈套的这种叙事修辞手法更符合传统小说的审美要求,更能满足读者的阅读期待。而制造虚幻,隐而不谈、多重声音则更接近后现代小说的旨趣,即放弃对故事意义的清晰解释,倾向目的追求的不确定性,更能增强作品的内在张力,凸显文学的审美价值,进而引发读者关注其裂缝、空白所在并深思其产生的原因,从而揭示出这种矛盾之下的深层意义,有利于我们对作品思想内涵的把握。
朱山坡的小说充满了无限的想象力,作者的虚构能力令人折服。笔者粗略归纳的这四种叙事的修辞手法并不能涵盖他全部的小说创作技巧,而且他在任何一部小说中也并不仅仅用某一种或两种修辞手法,有时候在一部作品中多种修辞手法综合运用。朱山坡的才华不仅仅表现在他的想象力方面,还有他的语言表现力,他的语言精准洗练,文采斐然,常常冷语惊人,或云卷云舒,或泥沙俱下。朱山坡擅长以新颖独特、形象生动的语言展开精彩的写作,体现了他驾驭语言的不凡能力。阅读他的作品总有与众不同的感受,他可以一次次挑起读者的阅读兴趣,让人意想不到,或者意犹未尽,或者给予暗示却又逐一破灭读者的阅读期待,这都归功于他高超的叙事技巧,期待朱山坡给读者带来更多的惊喜。
注释:
①朱山坡:《灵魂课·后记》,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4年版,第292页。
②郑小驴、朱山坡:《我追求什么样的小说》,《文学界》2011年第5期。
③李遇春:《底层叙述的圈套——评朱山坡的〈躺在表妹身边的男人〉》,《文学教育》2008年第5期。
④安德鲁·本尼特、尼古拉·罗伊尔著,汪正龙、李永新译:《关键词: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版,第234页。
广西艺术学院设计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