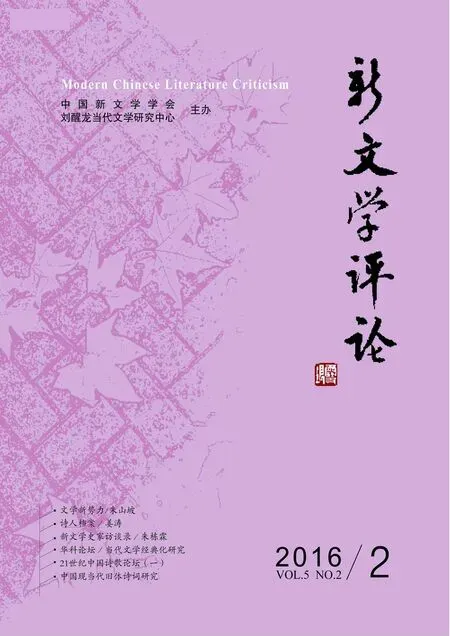“再给它们两天南方的气候”
◆ 姜 涛
“再给它们两天南方的气候”
◆ 姜 涛
十多年来,“70后诗歌”的提法,作为泛滥全社会的“代际”话语之次级衍生品,不断出现在相关的诗歌批评和编纂中。诗人胡子(续冬)早就预言,在当代文学主板市场极不规范的情况下,作为概念股的“70后诗歌”,即便沸沸扬扬上市,最终也会因“不合格包装引发的大量投诉和文本业绩的匮乏”而沦为一支垃圾股。我实在是同意这种说法,加上自己也曾忝列某个序列之中,更是相信某种集体同一性的虚妄。然而,十年后再看,当时的想法可能有点傲慢、也太轻佻了,在并不高明的营销策略之外,这支“概念股”还是包含了基本的现实性。这种现实性,不是由好事者四处张贴的美学标签来说明,更不是由“新陈代谢”的历史豪情来保证,而是因为30年来当代中国的剧烈变动,的确给出了时间的节奏,先后给出了几代人的界限。当年曾在文学史想象中剃着进取发型的青葱少年,至今部分已年届不惑,作为落寞大叔,或许更能感到这种节奏的强劲、专横。
这一次,感谢《诗建设》同仁耐心编出的“70后”专辑,让我有机会相对完整地阅读同代人的作品,包括熟悉的与不熟悉的、认可的乃至不大认可的。走马观花的感觉是,当代诗蓬乱芜杂的图像,似乎已被修剪成一畦畦整饬地块,大部分的诗可以满足美学与伦理多方面的要求,也几乎没有技术上、情感上彻底失败的东西。即便忠实于相对类型化的主题,由于并不夸饰到喜剧的程度,也会显出一份自如与精准。对于一本诗选而言,能取得这样的效果,其实相当不易:
这就像园艺,为了精致
或者枝干更加挺拔,你必须修剪
它们的枝蔓。
——江离《南歌子》
借用上面的诗句,编辑也像一种“园艺”。从文学形象学的角度看,出于工作的耐心和趣味的认真,或许可以说,《诗建设》的朋友们成功地编辑出了一种风格,一种“70后”的风格。它与诗歌理念、方式的统一无关,而是显现为总体写作质量的稳定(入选诗人似乎构成了当代诗的中坚),显现为一种相对浑厚的语言姿态(即便有所激进也不过分乖张),也显现为某种被分享的情感类型(不少作品浸透了温润的抒情伦理)。即使出于“编辑”,这种代际的风格还是大致可以信赖。
在当代诗30多年野蛮的成长史上,不只一次赶上社会政治与世道人心的大变动,诗歌与诗人也曾有过十分醒目的时代形象。那些风格强悍的前辈们,成长于运动与斗争的火热年代,往往能在特殊的转折时刻,强有力地提出新的美学,提出自己的方法论和世界观,他们的写作与表述,也往往有了“克里斯马”的非凡气象。针对沉闷的生活教条、语言教条,一些逆向提出的方案,无论多么粗糙、简单,无论有多少夸饰和浪费,却也总能歪打正着,洋溢了价值创造的率真热情,也在更大的视野里,扩张过语言和伦理的边际。延续非凡的惯性,连创业之后的贪腐、享乐中,这代人也不乏自我戏剧化的英雄气概。
相对而言,“70后”出生时,大规模的群体性运动已经过去,“文革”后期的中国其实不怎么折腾,家庭的规模也开始收缩,兄弟姐妹开始稀少以至于变得珍贵。乡村的情况我不了解,至少在城市中,双职工家庭模式带来一种普遍的成长经验,不管顽劣与否,这代人与自己独处的时间毕竟多了些,剩余的精力没有更多牵扯到成人世界的热闹中去消耗,只能转向日常性的学习、幻想、暴力和欲望。这方面,或者还缺乏社会学研究的支持,但70年代人是在一个相对平稳、孤独的环境中成长的,这带来部分人性格的早熟,身上各种各样的好坏毛病,不像前辈们那样有机会大大发扬。
二十世纪,父亲
已是长方的机器,
母亲是折叠入墙的
床,是塞不进抽屉的
日内瓦湖,花园的尺寸
已是屋顶的家务,山与云
是齿轮与皮带,转动的灿烂
是砂石磨废又一条小径的火星。
——韩博《勒·柯布西耶双亲住宅》
韩博的写作,体现了这代人心智早熟的一个极致,虽然已身为人夫人父,冷峻的洞察中还是包含了少年人的厌倦,又没心思去刻意挥霍,回头在与世界的不甚关联中,打磨一个微观而灿烂的人生系统。在句子和意象的自由传动中,不出意外显出一副好眼光、好性格。
但早熟,并不一定就是优势,却如同代批评家所称那样,导致各方面“尴尬”的处境。等到这代人结束漫长的少年时代,在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外出求学或自由飘荡,各种轰轰烈烈的造山运动接近了尾声,那些能够强劲扭转感受力的正反力量也基本耗尽,整个社会处在快速致富与快速自学之中,年轻人的野心更多表现在怎样去游戏规则,而不是首先考虑去推翻规则。社会迁徙、分层带来的重重震荡,当然也在神经纤维上密集传送,但社会主义时代的熹微记忆或小镇情怀,也会在内心形成牵绊,不肯发自肺腑地为时代乱象欢呼,认真地对待变化中的一切。结果是,无论进城鬼混、还是下乡探访,某种感伤、讥诮的小知识分子心绪,似乎还颇为流行,浮光掠影地造成某一类叙事抒情的套路。诸多“尴尬”合到了一处,无论经商、进机关、还是混迹媒体或学院,这代人中的佼佼者,即便占尽先机,但大多还是低调致富、低调上进,网络上尚缺乏他们可歌可泣的功德和丑闻。表现在写作中,“70后”的诗歌技艺普遍合格甚至优秀,结合特定的风土与心性,发展出各自的斑斓色彩,但总体上说,这些风格似乎不再具有“非凡”的气质。
对“非凡”的渴望,曾激发过上两代诗人开疆扩土的语言激情,普遍压抑也曾赋予激情以强劲的形式。前辈诗人可能的问题,是被既往“非凡”的时刻所凝固,对自身成就熟稔到不想有所突进。对于后来者而言,“遗憾”不在于错过了造山运动的机遇,而是他们开始写作的时候,当代诗若干浅近的主张已开始固化、常态化。个人的风格似乎可以从习得、磨炼中产生,而不再是自我挣扎、冲突的产物,也并非必然伴随观念上的否定与辩难。只要依了心性选取一种,安心或纵情地发展就是。大概十五六年前,曾与周边友人提出一种“偏移”的诗学,即:不再幻想另起炉灶,在承认当下写作格局的前提下,试图在一种修正关系中找到自己的可能。现在看来,这个看似世故、保守的立场,不是缺乏抱负的表现,而是基于对当时诗歌风尚的一种信任。这样说难免唐突了他人,因为此后不久,也眼见同代中不断竖起反叛、激越的旗帜,但彼此心知肚明,反叛的只是诗坛的秩序,而不真的具有价值原创的野心。挪用诗人孟浪的名句——“连朝霞都是陈腐的”,年轻人好勇斗狠,还是落在巴掌大的格套中。这也解释了新世纪以来诸多耐人寻味的变化,我们不断目击了“崇低”与“崇高”、纵欲代言与良知代言之间的悄然转换。
因为早熟,因为在价值前提上并不好斗,因为能够在社会上较早地容身立命,我们不断目击这一代中的作者,不需要为了入场而炮制抢眼姿态,反而能在相对独立、纵深的地带展开诗的“建设”,能在并不十分开阔的范围内,尽量扩张、拉伸语言的肌腱。那些肆无忌惮的想象力、自我凌虐的想象力,因为有了生活的阅历,似乎也不会脱缰于平凡实感之外,能如蝌蚪般自由甩动,带着蝌蚪般沉重的头颅和娇小下身:
像讣告上的黑字,人在天下。
你们不
停地扭动。像白纸上的蝌蚪。
——魔头贝贝《履霜经》
刚才说了,这本专辑中的作者,可算当代诗写作的中坚,相信不少人能持续写出令人信赖的、可读的作品。这一点毋庸多言,但从某种内在限制的角度,倒可以再拉杂写上几句。
坦率地说,写诗这个行当,目前表面热闹(你看大江南北,各类诗刊绿肥红瘦,让人眼花缭乱),实际不尴不尬,可能早早透支了曾有的历史红利。整个社会处在前途未卜的状态,诗人的写作也缺乏清新的导航系统,大家忙于应酬、研讨、集体出版,一切欣欣向荣的背后,或许是精神上普遍的松懈感。“70后”的作者们,对于写诗的行当敬重有加、勤勉有加,但一不小心也会构成“不紧张”的中坚,体现当代诗整体的水准,也体现了其内在的界限。这几年,有个不大稳妥的想法,常和几个朋友交换,这里不妨再重申一下,简单说:当代诗的前景,不一定在常态风格的深化、制度化,而在能否恢复某种现实针对性和价值紧张感。改变的前提是,诗人应考虑挣脱愤青、花花公子、神秘通灵者一类单调形象,主动培育某种成熟的、开阔的、具有关联感的人格。20年前,有感于时代、心境和文学趣味的变化,曾有人提出“中年写作”的方案。回头看,提出者当时不过三十左右的小伙儿,因为历史经验过快被压缩,所以年纪轻轻就有了对晚期风格的期待。“70后”一代心智早熟,但也可能因早熟而耽搁继续成熟,许多秋风迟暮之作还藏了少年情怀,就是一个明证。想到这里,有时恨不得遵从大师教诲:“再给它们两天南方的气候/迫使它们成熟”(里尔克《秋日》)。
当然,成熟的表现不一而足,至少应包含以下几个方面:不再以小知识分子进城或返乡的感伤姿态,来看待周遭世界的变化,这种视角除了自怨自艾,不能再说明什么;也不再扭捏于看似高深实则表浅的人文情怀,这种人文情怀即使有了各类文化经典的包装,也会因不断自我回收而显得沉闷;同样,各类撒娇卖乖、装神弄鬼的技巧,将来也不会有太大的出息。成熟的心智会带来语言和感受的层次感和针对性,也会唤醒语言创造的崭新欲望。考虑到当代诗在整体上还可能发育未完,对于高低错落的各代诗人而言,就没有了先来后到、扶老携幼的分别,这是一条共同的起跑线。对于包括自己在内的一代人,虽然从未抱有特别热烈的期待,但至少在这条起跑线上,有关写作前景的想象,还有可能被再三地鼓起。
北京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