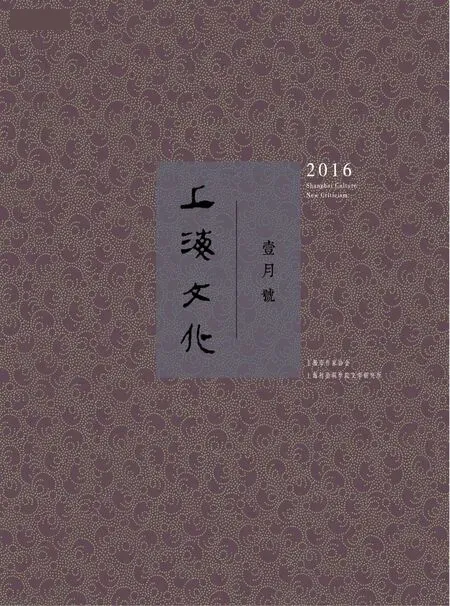伍尔夫的黑暗:拥抱那不可言说1○
丽贝卡·索尔尼特(Rebecca Solnit)米 语 译
伍尔夫的黑暗:拥抱那不可言说1○
丽贝卡·索尔尼特(Rebecca Solnit)米语译
1
○丽贝卡·索尔尼特(Rebecca Solnit,生于1961年6月24日),美国当代作家,现居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目前已出版十七本著作,涉及艺术、政治、环境、公共空间等不同主题,其中包括广受欢迎的《迷失的野外指南》(A Field Guide to Getting Lost)、《浪游之歌:走路的历史》(Wanderlust:A History of Walking)、《遥远的近旁》(The Faraway Nearby)等;同时她也为《哈泼斯杂志》与《纽约客》等撰稿。
索尔尼特曾多次获奖,包括两次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奖(NEA),古根海姆奖(Guggenheim Fellowship),兰南文学奖(Lannan Literary Fellowship),《连线》杂志激赏奖(Wired Rave Award)等,并在2010年被“Utne Reader”选为“25位改变你生活的创见者”之一;而她的《遥远的近旁》(The Faraway Nearby)一书则在2013年被提名为美国国家图书奖(National Book Award),并候选美国国家书评奖(National Book Critics Circle Award),同年亦被《纽约时报》评为2013年100本最值得关注的书籍之一。
本文选自《纽约客》(2014年4月24日刊),原文地址:http://www.newyorker.com/online/blogs/books/2014/04/virginia-woolf-darkness-embracing-the-inexplicable.html.
“未来是黑暗的,我认为这就是它最好的归宿。”伍尔夫在她1915年1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当时她差不多三十三岁,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演变成一场空前规模的灾难性大屠杀,且将持续数年。比利时已经沦陷,欧洲大陆处于战争状态,许多欧洲国家正在侵略世界其他地方,巴拿马运河刚刚开通,美国经济陷入窘境,两万九千人在意大利的一场地震中丧生,齐柏林飞艇正准备袭击大雅茅斯(Great Yarmouth,英国东海岸城市),空袭平民的时代即将开始,而德国在数星期后的西部前线首次使用了毒气。然而,伍尔夫所写也许是关于她自己的未来,而非世界。
这就是作家和探索者的职责,他们要去看见更多,他们要轻身进入先验的世界,他们要睁眼进入黑暗
五个多月前,她因发疯或抑郁企图自杀,因而仍被照料看护。事实上到那时,她发疯的日子与战争的日子相近,但伍尔夫痊愈了,战争的失控却又持续了血腥的四年。未来是黑暗的,我认为这就是它最好的归宿。这是一句非凡的宣言,主张无需通过错误的预言,或冷酷的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叙述之投射,将未知改变成已知。这是在颂扬黑暗,即便在自己的主张中也愿意保留不确定性——正如“我认为”所指明的。
大部分人都害怕黑暗。正如许多大人所担心的,表面上对孩子而言,黑暗是一种未知、不可见、隐晦。然而在一个难以确定区别和定义的夜晚,爱会发生、事物会融合、变化、使人着迷、被唤起、被充盈、被占有、被释放、被更新。
当我开始写此文的时候,我曾拿起一本劳伦斯·冈萨雷斯(Laurence Gonzalez)写的关于野外生存的书,看到这样一句令人信服的话:“计划,是一种关于未来的记忆,它被用在现实身上检视它是否合适。”他的观点是当两者难以互相弥合,我们通常会坚持计划,忽视现实给我们的警告,于是就陷入麻烦。我们害怕未知的黑暗,在那里凡事总隐约模糊,于是我们通常会选择另一种黑暗,是闭上双眼,是将它遗忘。冈萨雷斯继续写道,“研究人员指出,人们通常会用任何信息作为对于他们精神模型的肯定。如果乐观主义代表我们相信我们所见的世界就是其本身,那么我们天生就是乐观主义者。这样在计划的影响下,我们很容易就会看见我们想看见的”。这就是作家和探索者的职责,他们要去看见更多,他们要轻身进入先验的世界,他们要睁眼进入黑暗。
不是所有人都希冀这样做或者希冀成功。我们这个时代,非虚构类作品正在越来越接近于虚构作品,但是这并不代表对于虚构作品这一类别的肯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因为有太多的作家他们无法接受过去是如何变为黑暗的,正如未来一样。我们所知甚少,要真实地去写作你自己,或者你的母亲,或者一个人的回忆录,或者一个事件,一次危机,另一种文化,需要你反复不断地去接触那许多黑暗的碎片,那些历史的晚上,还有那些未知的地狱。它们告诉我们世上有知识的界限,世上有必要的神秘,这所有的起点是一种观念,即我们只知道有些人在缺少确切信息时候的想法和感受。
许多时候,即便有些事物在我们面前出现,我们还是不知道它们,更不用说是某些消失在过往时代的人,其表象和映射远不同于我们时代。填补空白这种行为替代了一种真理,即我们有时错误地认为我们知道,但事实上我们不完全知道。当我们错误地认为我们知道时,其实我们知道的远不如我们认识到我们不知道时所知道的。有时候我认为这些权威性知识的假象其实代表语言的失败:鲁莽断言的预言相比于微妙的含混的臆断的语言更加简单,而不是那么费力的。伍尔夫在后一类语言上无可比拟。
连她的名字(Woolf)都甚而带有一丝野性的意味。在法语里幽暗被称为“entre le chien et le loup”,在狗与狼之间的时间,弗吉尼亚·斯蒂芬(Virginia Stehpen)在她的时代嫁了一个美国犹太人之后,主动选择了走向野性,为了想要踏出一点她自己的阶级和时代。“尽管也有许多人叫Woolf,但我的姓却像Vigil(译注:维吉尔,古罗马诗人)一样在所有对于漫游,迷失,丢失身份,不确定,未知的使用中引导我。”我用她的这句关于黑暗的话作为一句警句,推动我在2004年写完了《黑暗中的希望》(Hope in the Dark)这本关于政治的书,我那时希望这本书能够用以抵消在布什政府入侵伊拉克之后所造成的绝望感。
两次冬日散步
对于我来说,希望的基础仅仅就是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并且不可能或者无法想象的总是很快消失,而且关于世界的非官方历史显示有奉献精神的个人和大众的运动能够并且已经塑造了历史,尽管我们无法预计如何,何时以及需要多久才能取得胜利。
冈萨雷斯反复提到绝望是一种确定性的形式,即未来非常接近或者差于现状。绝望是一种对未来充满信心的记忆。乐观主义同样也对未来会发生什么充满信心。这两者都不鼓励行动。希望可以是一种知识,即我们没有这样的记忆,并且现实与我们的计划不相符合;希望就像是一种创造力,可以来自于一种浪漫主义诗人济慈称作的消极感受力。
1817年一个仲冬的夜晚,也就是伍尔夫在日记里记下黑暗前的一个世纪,诗人济慈在散步回家时与一些朋友交谈,他在后来一封非常著名的书信中这样描写这次散步:“有许多事情非常符合我的想法,我突然意识到,什么才是塑造一个有成就之人的品质,特别是在文学的领域……我是指一种消极的感受力,那意味着一个人必须要有在不确定性,神秘,怀疑中生存的能力,而同时不会暴躁地试图去寻求事实和理性。
我是指一种消极的感受力,那意味着一个人必须要有在不确定性,神秘,怀疑中生存的能力,而同时不会暴躁地试图去寻求事实和理性
通过散步,交谈以及将很多事物融进他的思想,济慈展示了散步是如何带来想象力的漫游,和一种关于创造本身的理解,散步这种行为将内省转化为一种室外的活动。伍尔夫在她的回忆录《一段过去的素描》(A Sketch of the Past)中写道:“有一天我沿着塔维斯托克广场(Tavistock Square)散步,我突然毫无意识地飞快地走起来,就好像我在写《到灯塔去》时有时会飞快地写作一样。一件事情突然变成另外一件事情。从吹管中吐出泡泡的样子会给我一种独特的感觉,就好像是想法和场景飞快地从我的思想中出现,于是当我散步时音节便不自觉地从我的嘴唇中吐出。是什么吹出了气泡?为什么是在那个时候?我不知道。”
在我看来伍尔夫的某些天才之处在于摒弃了认知,也就是消极感受力。我曾经听说过一个夏威夷的植物学家,他在寻找新物种上的诀窍就是在野外迷走,去超越他的所知及其所知的方法,让经验超越他的知识,并在现实和计划中选择前者。伍尔夫不仅是在实践这种思想和身体的无目的漫游,更是在赞颂它。在她写于1930年的一篇伟大散文《令人向往的街头:一场伦敦探险》(Street Haunting:A London Adventure)中,尽管也有许多她早期散文中惯见的轻快笔调,但已经描写了一场深入黑暗的旅程。
仅仅需要杜撰一个在伦敦冬日夜晚出门买铅笔的借口,就可以开始一场探索黑暗、漫游、发明、销毁身份的历险。对身体来说这是一种寻常的活动,但对于精神来说这是一次宏大的探险。她还写道:“傍晚的时光同样给我们另外一种东西,即黑暗与路灯消除了我们身上的责任感,我们不再是往常的自己,当我们在傍晚四到六点钟走出家门的时候,我们褪下了所有我们的朋友借以认识我们的特征,然后加入了一支庞大的无名漫游者共和国军队,他们的社会在我们经历了各自独处的时光之后显得令人愉悦。”在这里她所形容的是一种不会强加身份的社会形态,它反而解放了身份,这是一个由陌生者、街头的共和国、匿名和自由的经验所组成的社会,这是一个大城市所创造的社会。
内省总是被描绘成是一种室内的孤独的事,就像一个在她房间里的僧侣,一个在她书桌前的作家。但是伍尔夫并不同意,在谈到家时她写道,“在那里我们坐在所有那些强化关于我们自身经验的物件当中”。她这样形容这些物件,然后接着说道:“但是当我们关上门,所有那些便消失了。所有我们灵魂排泄到屋子里的东西组成了一个壳状的事物,藉此与他人区分开来,在这一刻全都破碎,被遗留下的全部褶皱和粗糙中有一颗关于认知力的珍珠,那是一颗巨大的眼睛。冬天的夜晚是多么的美丽!”
屋子的躯壳是某种监狱,也是某种保护,还是一种关于亲近性和延续性的集中,它们只要踏出室外便消失。行走在街头可以是一种进入社会的形式,当我们在一起行走时,这甚至有可能是一种政治行动,就好像是在起义、示威或者革命中,但它同样也可以是一种带来冥想、主观和想象的方式,这是一种双重奏,一方是外在世界的刺激和打搅,另一方是来自内在世界的影响、欲望和恐惧。有时,思考是一种室外的活动,一种身体的活动。
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向前推进想象力的总是一些细小的干扰,而不是不受打扰的集中精力。思考的工作方式没有明确的方向,通过迂回的路径漫步抵达目的地而不是直接到达。在《令人向往的街头》一文中,想象力的旅程可以是纯娱乐性的,但是这样的漫步却使伍尔夫能够构思出《到灯塔去》的形式,这就是促进了她坐在写字桌前难以做到的创造性工作。创造性工作总是依赖无法预计的方法,要求你离开房间去漫游,并且回避计划与系统。你无法把它们拆解成可复制的公式。
公共空间,城市空间,在其他时候服务于公民,即需要互相保持联系的社会成员,但那些空间在这里却是让个体身份的界限和联系消失的空间。伍尔夫赞颂的迷失,不是指迷路而是指开放地接受未知,这样可以让物理的空间提供精神的空间。她在这里所写的是白日梦,或也许是夜晚之梦,这可以让你想象自己是另一个人,身处另一个地方。
在《令人向往的街头》中,她探索身份本身:
创造性工作总是依赖无法预计的方法,要求你离开房间去漫游,并且回避计划与系统
是不是真正的自我,既不是这样也不是那样,既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而是某种变化万象,随意游走的事物?是不是只有当我们让愿望不受限制,不受干扰地发挥,这样我们才是我们自己呢?外界的情况要求统一,考虑到方便性,一个人同时又必须是一个整体。能够在夜晚打开家门的好公民应该是一个银行家,高尔夫球手,丈夫,父亲,而不应该是一个身处沙漠的游牧者,一个仰望星空的神秘主义者,一个在旧金山贫民窟里的浪子,一个领导革命的士兵,一个在怀疑和孤独中嚎叫的弃儿。
但是他却与此无关,伍尔夫说道,影响他是谁的约束与她的约束是不同的。
不确定的原则
伍尔夫所呼唤的比诗人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的诗句“我包含许多”更加内省,比诗人阿蒂尔·兰波(Arthur Rimbaud)的诗句“我是他者”更加透明。她呼唤一种不会强加统一身份作为限制或甚压制的环境。人们常可注意到,她总在她的小说中为她的主人公这样做,有时在她的散文中她同样也会如此展现,借由调查性和批判性的声音,在她对于多样性、不可还原性、神秘性的坚持中,去赞颂、讨论、要求这样的呼唤,如果神秘性是指事物能够不断发展、超越、无法被限制、包含更多的能力。
伍尔夫的散文通常既是这种不受限制意识和不确定性的原则的宣言,同时又是展现或调查。它们同时也是反批判的模式,因为我们通常认为批判的目的是将事物确定下来。我曾经是个艺术批评家,我经常开玩笑说美术馆喜爱艺术家就像标本师喜爱鹿一样,在那样一种过程中,许多在这个我们称之为艺术世界的小空间中工作的人,常常渴望将艺术家们的开放的、含混的和开创性的作品用确定性固化和表达出来。
一种类似的对于艺术作品中的不确定性和艺术家意图中的含混性的征服,同样也存在于文学批评和学术领域,他们渴望在不确定性中归纳出确定性,在未知中找到已知,将划过天际的翱翔变成一份盘中的烧烤,去分类、去装载。无法被分类的就无法被察觉到。
这是一种想要发展艺术作品的反批评主义,通过互相联系、开启含义、引入可能性。一份伟大的批评作品能够解放一件艺术品,使它能够被全面地看到,保持活力,能够出现在无尽的讨论中,不断地激发想象力。这不是要反对阐释,而是反对限制,反对扼杀精神,这样的批评本身就是伟大的艺术。
这种批评不是要将批评者与文本对立起来,不是要试图建立权威。相反它是要与作品和想法共同游走,令它绽放,让其他人加入过去曾被看作是无法穿透的讨论,去绘出难以被察觉的关系,去打开可能被紧缩的门。这是一种尊重艺术神秘本质的批评,这是它本身的美、欢愉,而这两者同时又是不可还原和主观的。
一份伟大的批评作品能够解放一件艺术品,使它能够被全面的看到,保持活力,能够出现在无尽的讨论中,不断地激发想象力
解放
伍尔夫解放了文本想象力、虚构人物,然后也为我们呼唤那种自由,尤其是女性。这就是伍尔夫对于我所展现出来的所有特质的核心,它总是在歌颂一个非官方、非体制、非理性的解放,而且这也是超越熟知的、安全的、关于世界已知性的精神。它对于女性解放的要求,并不仅仅在于去让女性从事男人所做的事(现在女性也可以从事),更在于一种漫游的全面自由,包括地理上的和想象力上的。
她意识到这要求许多不同形式的自由与权力——她在《一间自己的屋子》(A Room of One’s Own)中就这样认识到了,但是人们通常只记得那篇文章中对于房间和收入的争论。这篇文章中同样也要求高等教育和一个全新的世界,伍尔夫在文中通过一则关于朱迪斯·莎士比亚(Judith Shakespeare)的美妙而悲惨的故事展示了这样的要求,这个人是莎士比亚命运多舛的妹妹:“她没有受到任何职业上的训练。她能够自己去小酒馆享用晚餐或者在午夜的街头游荡吗?”在小酒馆的晚餐、午夜的街头、城市的自由都是自由的关键元素,这不是要确定一种身份而是要放弃它。也许她的小说《奥兰多》(Orlando)中的主人公,就蕴含了她这种对于在意识、浪漫、身份和地域间游荡的绝对的自由的想法,那个主人公活了好几个世纪,在不同的性别间转换。
关于自由的问题在她的谈话“女人的职业”中以另外一种方式被呈现出来,她愉悦而又残忍地形容在屋子里杀死天使的行为,也就是一个只满足他人的需要和期望而非自己所需的理想女人。
我过去二十年创作的任务是试图寻找一种语言去形容微妙的、无法言说的、令人喜悦的以及一种难以归类的、来自事物核心的意义
“我尽我的全力杀了她。如果我要上法庭的话,我的理由是自卫……在屋子里杀死一个天使是一个女性作家的部分工作。天使死了;那还剩下什么?你可以说剩下的是一件简单而常见的物体——一个年轻女人和她的墨水瓶在她的卧室里。换句话说,这个年轻女人已经排除了她身上的虚假,现在她只是她自己。哈,但“她自己”又是什么?我是说什么是女人?我向你保证我不知道。我也不相信你知道。”
现在你已经注意到伍尔夫经常说“我不知道”。
“在屋子里杀死那个天使”,她继续说道,“我以为我已经解决了。她死了。但就在那一刻,作为一个人讲述我自己真实的经验,我认为我还未解决这个问题。我也质疑其他女人解决了这个问题。她面前的障碍依旧十分强大,但是它们却很难去定义”。这就是伍尔夫关于谦和的不服从的最佳诠释,而她所说她的真相是现实的说法在她说出之前根本是无法想象的。相对于乔伊斯的作品,具体化在她的作品中展现得更加高雅,但是尽管她也去观察如何得到权力,但是看起来在她的散文《关于生病》(On Being Ill)中体现出了非常明显的伍尔夫特征。她发现即使是最无力的病人也获得了某种解放,可以观察到健康的人看不到的事物,才能够用新鲜的视角去阅读文字,以及去改变。我所知道的所有伍尔夫的作品与O-vidian(译注:奥维德,古罗马诗人)式的变形等同,即要追求的自由是一种继续发展、探索、漫游、超越的自由。她是一个逃遁的艺术家。
伍尔夫在号召某些社会变革时是一个革命者(当然她身上也有她那个阶级、地方和时代的缺陷和盲角,有些她能够超越,但并非全部。在我们身上同样也有盲角,我们的后代可能会也可能不会谴责我们)。但是她理想中的解放是内在的,情感的,智力的。
我过去二十年创作的任务是试图寻找一种语言去形容微妙的、无法言说的、令人喜悦的以及一种难以归类的、来自事物核心的意义。我的朋友切普·瓦德(Chip Ward)所谓“数量化的统治”,能够被计算的总是要优先于不能够的:个人的收益相对于公共的利益;速度与效率相对于享受与质量;实用的相对于神秘和意义,而后者对于我们的生存、对于超越我们的生存、对于能够使我们的文明有价值继续存在下去的超越我们存在的有目的和价值的生活有更大的用处。
数量化的统治代表着更加复杂、微妙和流动的语言和辩论的某种失败,同时也是那些塑造想法、做出决定以理解和评估这些不确定事物的人的失败。想要评估一样无法被命名或者被形容的事物是困难的,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所以命名或形容是在反针对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现状的反抗中必要的一部分。地球最终的毁灭有部分原因是想象力的失败,或者是不知如何记录重要事物的会计系统对于想象力的侵蚀。对于这种破坏的反抗是一种想象力的反抗,它钟情于微妙的事物、金钱买不来和企业无法控制的快乐、自己作为意义的生产者而不是消费者、缓慢的、游荡的、离题的、探索的、神秘的、不确定的。
我想要借由伍尔夫的一段话作为结束,这是我的画家朋友梅·斯蒂文斯(May Stevens)写在他的一幅画上后赠予我的,而我在我的《迷失的野外指导》(A Field Guide to Getting Lost)这本书中引用了这段话。在梅(May)的画中,伍尔夫的这一长段话被撰写得如流水一般,它变成了一种将我们冲走又浮起的基本力量。在《到灯塔去》中,伍尔夫写道:
现在她不需要顾忌其他任何人。她可以做她自己,与自己独处。这就是最近她常常感到需要的——去思考;当然,甚至是不思考。去沉默;去独处。一切外扩的、闪耀的、有声的存在和行为,全都消失了。人在一种庄严感中缩回自我,一个楔形的隐秘的内核,是别人所看不见的。尽管她仍笔直而坐,做着编织,但她正是这样感受到了自我;而这个摆脱了一切身外附属之物的自我可以自由地去作最奇特的冒险。当生活有片刻的下沉,体验的领域就会显得无边无垠……那之下全是黑暗,它在扩张,深不可测;但时不时地我们会浮上表面,那就是你们看见我们的地方。对她而言她的地平线看起来没有边际。
伍尔夫给予我们的无限,无可捕捉,但必须拥抱,它如水一般流动,如欲望一样无尽,是一枚可以让我们迷失的指南针。
编辑/黄德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