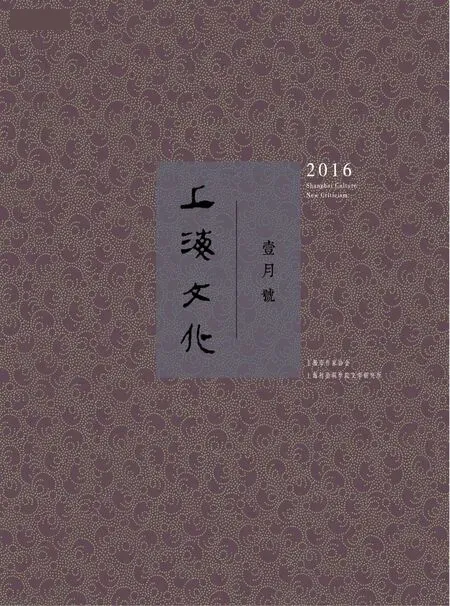薄弱的幻觉城市文学观察笔记之一
项静
薄弱的幻觉城市文学观察笔记之一
项静
生活的戏剧化是不健康的,张爱玲说生长在都市文化中的人,总是先看见海的图画,再看见海;先读到爱情小说,后知道爱。这是文学加之于城市生活的表现,但城市与文学的互为因果的关系中始终是双重运动,城市生活加之于文学跟文学加之于城市生活一样绵长。文学既是历史和生活的符号,也是历史和生活的反抗。
作家们往往都在城市与文学的双重运动中左右摇摆,仿佛一直有一个接近不了本质在诱惑,无法呈现出一种想象中的“真正”的城市生活。还有一种有关城市的讨论令人厌倦,乡村与城市作为两种生活方式,一旦与文学连接在一起,所碰撞出来的不是两种生活方式的娴熟地呈现和记录,而是文学的“经世治国”和混杂了各种附带品的论说体系,比如对于家国时代的承担和表现,还有城乡矛盾冲突、地域文化消长所带来的势能高低,写作品味以及文学评价体制内的高下。作家描写城市不像描写乡村那样自然娴熟,农村的生活因为依附于土地而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而城市往往是跟交通运输,人来人往,交易买卖甚至是陌生人群联系在一起的,生活的不安定性是它的一个重要特点(这并不是否认城市本地居民生活的安定性,是就城市这个空间而言)。所以有关城市的描写和叙事,对土生土长的城市居民来说,也会不自觉地出现类似于外来者的视角,就像《红楼梦》里的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时刻,忍不住一事一物地去打量观察。这种时刻仿佛是一种无意识的恐惧,也可能是一种得先机者的炫耀和夸饰,当后面的意识失去存在必要性后,单纯地描写和对城市外部的描写可能苟延成一种惯例。
还有一种情况属于拥有“江声浩荡,自屋后上升”的恢宏气象的时代,时代的气息催生了大于现实的多余情感,于是它们转移到城市或者乡村的外景上,碰撞与眩晕指向远处的幽灵。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子夜》开端,吴老太爷由于土匪作乱,红军燎原,被儿子吴荪甫接到上海。小说详细地描写了1930年5月上海的一夜,一个震撼的场景,也是作家俯视之下的现代上海,从苏州河的浊水,两岸的浮得高高的各色船只,到黄浦江的夕潮,外滩公园里的音乐,被暮霭薄雾笼罩的外白渡桥,爆发出碧绿火花的电车线。然后叙述者从桥上向东望,看到浦东的洋栈像巨大的怪兽,蹲在暝色中,闪着千百只小眼睛似的灯火。向西看到洋房顶上异常庞大的霓虹电管广告,射出火一样的赤光和青燐似的绿焰:Light,Heat,Power!这种描述城市的方式曾经对有关城市的写作打上深刻的烙印,全能视角高调地开启一个世界,城市中的每一个事物都不仅仅是它们本身,而是跟一个遥远的真理或解释遥相呼应,灯光和河水在这个遥控者的呼唤下,变得强光在身,物我交融。与《子夜》这个高昂的开头相对应和让人释然的是,茅盾社会学背景的写作方式,他是在对1930年代的城市乡村有一套政治经济学的观察之后,而写作的一本回答问题的小说。城市是一个巨大的道具,也是一个跟作家的理解和认识相匹配的舞台,城市本身是什么反而是无关紧要的。
在一个相对平静和庸常的时段,高蹈的气韵必然回到市井人声,回到普通个人的存在,以及城市寻常的面目
一、密林中:质实与忧思
在一个相对平静和庸常的时段,高蹈的气韵必然回到市井人声,回到普通个人的存在,以及城市寻常的面目。城市从一个庞然大物,逐渐形销骨立,对于常住居民来说,它比吃穿用行更遥远,像太阳一样不会成为思考对象,尤其对愿意思考者来说,心灵的不安宁更重要。周嘉宁的《密林中》是一部书写城市文艺青年的小说,可以看作一部文艺青年的小历史,也是一个群体灵魂的描摹,可能因为这是一篇直指内心的小说,那些覆盖在小说人物身上的外在身份和生活环境,譬如庞大的上海,在灵魂的密林中不见片瓦。而在新世纪十几年的回忆中,作用于一个写作者的内心的东西,也都极度凝练收缩,对于一个以文学为日常生活,孤立、敏感、任性、又羞怯又勇敢的文艺青年来说,太容易被辨识的文化符号、太过于虚假的意象、太承蒙关照的爱都是不消领受的。那些在咖啡馆里漂浮不定的文艺的生活方式,可能是这部小说里最具有城市感的东西了,城市为这样的生活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性:群体性地关注写作,聚会见面,互相衡量,彼此争吵和较量,寻找那种未被程式化无法命名更接近心灵的东西,同时又在寻找和失望中消耗着年轻的生命,而最终是不断地自我反思和厌弃,“美术馆,展览,电影院,地下电影,读书会,乐队,这些东西全部都令阳阳感觉厌倦,过去她所执迷的,现在都想抛弃。那些假模假式的玩意儿”。
《密林中》最可贵的可能就是这种对虚假和非切身之感的不断舍弃,在时间和个人的成长中,曾经的热情也会变成陈旧和虚假的形式,这个群体同样走在一个腐化的路上,他们始终找不到属于自己的生活和表达方式,比如著名作家山丘,“与大部分中年男作家不同,他从西方文学和城市精神中汲取营养,对小镇,乡村或者底层毫无兴趣。他听莱昂纳德·科恩的歌,读米沃什的诗。这些不都和阳阳一样吗”。他们的问题在于已经成为了另外的人,却沿用原来的调子,“他的一部分已经成了自己讨厌的人,却还在浑然不觉”。
文艺青年们暂居在城市生活中一个十分微弱的部位,比如刚开张就知道随时都会关闭的咖啡馆,一群在语言中寻找自己道路的青年人,他们一直在观察同类和自我观看,好像已经没有时间打开窗户观看街道上的陌生人群,观看男男女女的扰攘,小说中的人们对空间和人群,没有愿意抛洒的爱和物我之间的感情。即使有,也没有人与物直接的对接,是通过文学,“我哭是因为我爱这条让我离开亨利的街道,有一天或许也会因为它让我再回到亨利的身边”。或者是通过艺术,比如摄影师大澍,他的摄影对象是什么,小说中没有明确的交代(大概是为了祛除关于上海形象的惯性思维),只有对他风格的交代,“大澍像是一个突然的闯入者,他不使用变焦镜头,长焦镜头,这使得他从来不躲避,不管拍摄的是风景,楼房,静物还是人,他都采取正面强攻的姿态,迎上去。因此他常常不得不近距离地面对陌生人的惊恐甚至愤怒”。他的照片“粗暴,任性,生机勃勃,同时又癖性十足”。他们索爱于语言、影像,而不是任何外在于这些的东西,虽然最终的目的地依然是质实的生活。
城市比故事和人物都重要,它独立成行,拥有自我意志
周嘉宁写了一段文艺青年逝去的时光,并且在小说中完成终结,敏感的心灵和寻找的焦虑给人一种枯瘦和寒怆感,让人禁不住怀念另一个时代的荣光,那个时代,人们把居住之地看得重要而有意义,王安忆曾在一次访谈中说:在《长恨歌》里面,“我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但事实上这个女人只不过是城市的代言人,我要写的其实是一个城市的故事”。城市比故事和人物都重要,它独立成行,拥有自我意志。《长恨歌》开头是这样写的:“这种弄堂的房屋看上去是鳞次栉比,挤挤挨挨,灯光是如豆的一点一点,虽然微弱,却是稠密,一锅粥似的。它们还像是大河一般有着无数的支流,又像是大树一样,枝枝杈杈数也数不清。它们阡陌纵横,是一张大网。它们表面上是袒露的,实际上却神秘莫测,有着曲折的内心。那全都是用手掬水,掬一捧漏一半地掬满一池,燕子衔泥衔一口掉半口地筑起一巢的,没有半点偷懒和取巧。上海的弄堂真是见不得的情景,它那背阴处的绿苔,其实全是伤口上结的疤一类的,是靠时间抚平的痛处。”城市同人进行类比,弄堂的形状、性情和居住在里面的人们之间没有区别,这种手法非常独特,属于一个有热情和倾诉欲望的年代,以语言的共通性特点为基础,对人和物之间的联系的感知,城市被同时展示为一种社会现实和一种人文景观,在其中被戏剧化展示出来的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情感结构,作家对这个城市的爱和理解在她叙述语言里完全可以体会得到。
《密林中》里面的爱情故事都是简洁明了的,不枝不蔓,跟外在不断膨胀扩张、复杂幽深的城市生活形成一个对照,这的确是另一个时代的声息,而且不足以证明前一个时代的“虚假”,前一个时代是确凿存在,也是今天的忧思所面对的对象。它只能用来质证今天依然虚张声势的宏大叙事,同时也在证明一条向内走,只见局部,不见整体诚挚的写作在今天的城市是可能的。也许是唯一亲切的方式。
写作者对城市有许多隐秘的期望,城市是反抗的介质,是记忆的留痕,是众多“过去”的遗址,还是人群聚居处和危险之地,是孤独、黑暗、深渊的另一个称谓
二、个人史:路障和清理
写作者对城市有许多隐秘的期望,城市是反抗的介质,是记忆的留痕,是众多“过去”的遗址,还是人群聚居处和危险之地,是孤独、黑暗、深渊的另一个称谓等等。正是侈望的各种情感,引导了对城市的全景观看方式,展示的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让写作中的城市生活在日常生活之外,附加了许多价值。比如邱华栋1990年代的北京,那些无法略过的城市地标描写,好像无法停下的欲望的战车,韩东、朱文们给出的几个无聊的身姿,氤氲着一股消极对抗的气息,卫慧廉价的名牌清单,肆意扫荡着上一代人的游魂。城市文学的概念也是在1990年代被反复提出的,一开始是作为乡土文学的对立面被提出来的,当小说以粗糙的物质“清单”和各种真假欲望来列举城市之时,尽管知道这是过于浅表的一面,但也不得不承认,这也是城市重要的一面,城市的物质性和现实性,一方面与熟悉的乡村“自然”拉开距离,也在消解文学与时代、思想、社会发展轻易缔结的亲密关系。这种看似反叛的方式其实并不新潮,但肯定是比较容易驻留的方式,它可以轻易绕过那些细密论述和追根究底的方式,在获得空间的同时,也必然会造就拙劣的后继者。
张怡微对上海这个城市拥有的爱是天然而特别的,《你所不知道的夜晚》、《旧时迷宫》里那种新村生活,是政治和历史的产物,也曾经塑造了一种阶层文化。在高度城市化的过程中,田林,小闸镇这样的地方,以及它们所承载的生活记忆无可挽回地要走到消逝的路上去。因为正在消失,聚焦的目光中,就有了全景的意义,有了对于整个历史进程的关照。《你所不知道的夜晚》开头的大量篇幅用来介绍新村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就有一种解释和珍爱的味道,“第一,它地理位置的特别;第二,它的配套设施很完善,教育、医疗机构都有,它甚至还有一个火葬场,不用跨区一个人的生老病死都能完成,它是向内的。但是呢,田林有个蒲汇塘,咸丰年间就有,还有一条铁路,一直到1997年才拆掉的徐家汇火车站。一个封闭环境内,挤着那么多一生一世,但其实门口就有两个通向遥远的通道”。这是一个具有自我完满性的生活方式,是粗犷的胃口巨大的城市文学之下的一个小小群落,徘徊的目光所造就的说明阐释,一是打捞和珍重的需要,另一个则是承担了反拨的意味,这个城市的生活在通行的理解之外有另外一面。《细民盛宴》是张怡微继《你所不知道的夜晚》之后的一部长篇小说,依然是上海生活,不同之处在于,除了上海人情世故的部分,几乎没有关于上海历史沿革的只言片语,虽然这个人群中的一部分几乎就是从《你所不知道的夜晚》中的搬迁过来的,经历着同样的风雨。
小说以父亲预约的家族饭局开端,以自己给父亲做饭结尾,从父亲喧闹的大家庭生活一次次回到“我”,我是他们的观察者,而非同路人,无法分享那个群体的情感和秘密、尴尬,却又难解难分,依然要被叫去告别,聚会吃饭,体会血脉之撕扯。“我”在家庭的缝隙中走出来,按照生活赐予的给养自己去建筑一个世界,却又连连失败。细民的盛宴其实也就是细民们内心的摆设,父母离异,家族嫌隙中的爱与恨,最后引出了一段抒情,好像是对自己通篇侧身旁观和自怜的一点反省,“我想我一定还错过了许多事,因为我的私心与偏执。然而除了父母,我又有什么可想。错过了就是错过了,遗憾也不在乎多一件还是少一件。许多珍贵的记忆留在心中,像土壤潮湿,依然在奋力滋生着新的生命气息。没有什么不能忘记”。这一段看起来语无伦次的内心戏,有对父母生活史的收束,有个人记忆的遗憾,有生存的意志,又有更新的愿望。总之,在个人的基点上,像雨后的蘑菇一样滋生出文理细密的伞盖,层层叠叠,身形肥硕,又远到达不了树的高度,也不再是从外面建筑房屋一般瓷实、倾力大于倾心。《你所不知道的夜晚》、《旧事迷宫》是非常自然的具有传承性质的作品,经常讨论的城市话题都在其中可以找到回应,《细民盛宴》离开的较远一些,除了带有标志性的世俗人情,除了在城市的几个落脚地,好像跟“上海”这座城市关系也不大。因为是回到一个具体普通家族的生活,又没有那种可以勾勒出几十年历史变迁的野心,所遇者无非生计之艰和生老病死的大关,不适合放大展示和有意识观看,就像一条只能一人侧身的巷子,只能低头走路。
经过当代文学几十年的发展,城市在写作中形成了许多固定印象,也制造了一堆堆的路障和绊脚石,好像已经到了开始一块一块搬掉的时刻。《密林中》和《细民盛宴》都是躲闪城市文学既有路障的作品。被展示的城市,总是抛给身份不明者们的,到底是本地人怀旧的需要,还是远方的人们猎奇和朝圣的需要,或者是作家写给自己的记忆整理和理念整合。作家在社会的发展中,已经感受不到个人与城市的共振,或者失去说话对象。对象模糊的时候,在文学中如何呈现城市?城市是个人生活,社会记忆,家居伦理;城市又是矛盾,危险,是资本、政治运作之下的结果。好像除了真诚的“个人”这条小路,已经没有中间道路,中间道路很容易走成不伦不类的样子,而社会学的方式不是说失去了可信度,最重要的是它考验着一个作家的思想能力和对时代的把控能力,还有不断更新的形式能力。关于城市的道德修辞,与黑暗深渊、欲望一样,都越来越不可靠,“没有共同的人世生活,因为只有当多数人找到通往属于每个人自己现实的道路,才会出现共同的人世生活”①。城市里的小众人群,有政治背景的群落(工人新村、工厂)最主要的诉求是讲述自己的个人史,在个人抵抗流行的集体叙事后,或者仅仅是自我整理后。城市对于写作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或者它是否已经无关紧要,这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事情不会到此为止。
《密林中》和《细民盛宴》都是躲闪城市文学既有路障的作品
三、外来者:魅影和梦魔
城市成为一个问题,外来叙述者功不可没,甚至可以说更重要,他们是观摩式写作的始作俑者。差异、震惊和征服曾经是这个群体的第一眼和叙事动力。城市对于外来者,不再具有那种独一无二的属性,1980、1990年代描写进城的小说中经常出现的强烈反差感,也开始稀薄淡化,缘由刺激而生出的奋斗豪情和征服的期望也弱化了,开始强化的是各种形式的挫败感,语焉不详的落寞。李敬泽在评论甫跃辉的小说集《动物园》时候写过一句话,“这本集子基本上是以上海为背景,虽然常常语焉不详,但我们确知,这是一座大城,这不是故乡,在这里,人是没有故乡的,没有过去,也就很少有回忆。他的小说和他的人物似乎一开始就被紧闭在这个地方,这个庞大都市、这个此时此刻,没有远方——空间和时间之远,有的仅仅是某种来路不明模糊不清的气息”。
进城带来的落寞和挣扎,在近三十年的文学作品中几乎是常识
甫跃辉的《巨象》、《晚宴》、《动物园》等,城市本身是遁形的,几乎不再以直面的方式出现在小说中。《巨象》里主人公李生挥之不去的噩梦,转而成为一种心理阴影或者梦魇,“巨象”的碾压其实就是城市的形象。《动物园》里有一个场景:顾零洲看到大象的那一瞬间,居然泪水一再涌满眼眶,“他莫名地觉得,它们不再是庄严和温柔的,它们赭红色的庞大身躯里,似乎隐藏着同样庞大的痛苦”。《饲鼠》写了一个青年与老鼠的同居生活,别人遛狗他遛老鼠。最后他把老鼠放到对面楼上。老鼠缩在笼子里一动不动,抖了抖笼子,老鼠看看他,仍不往外走。他索性放下笼子让他自便。他走到楼梯口,回头看,那只老鼠仍蹲在铁笼子里,不知何去何从。这两个场景写尽了都市外来者的寂寞与空虚,只有在面对动物的时候,他们才释放了自己的真感情,仿佛看到了自己。《动物园》看起来是一对青年男女的日常消磨,其实是一个被动漂泊的青年在惶惶不安的都市中的寂寞感,这种寂寞和绝望不是由某个特定的不幸造成的,甚至并没有具体地失去什么,想得到什么,虽然有很多理想,但在表述中又迅速规约化,模糊不清:前途,房子,爱情等等,一切都是不具体的,难以出口成形的。顾零洲深感生活陷入了一团迷雾中,他既想看清去路,也在竭力回想来路。高考、工作、恋爱都有一种误打误撞的感觉,他总是惶惶不可终日,担忧自己无法适应工作和生活,时间一天天催逼着他去面对。回望近三十年的生命,顾零洲惊讶地发现,自己几乎没什么梦想可言,即使跟女友之间没有任何可以交流的话题,也没想过要离开她。她大学毕业后离开这座城市,他没和她一起离开,因为他实在没有勇气去面对一个全新的城市。
进城带来的落寞和挣扎,在近三十年的文学作品中几乎是常识。描写1975年到1985年北方乡村生活变迁的《平凡的世界》,路遥的写作时间是1982年到1988年。这样一部以写乡村生活而闻名的小说,其实是以叙述者温情细致地扫描县城的街头开始的:“在这样雨雪交加的日子里,如果没有什么紧要事,人们宁愿一整天足不出户。因此,县城的大街小巷倒也比平时少了许多嘈杂。街巷背阴的地方。冬天残留的积雪和冰溜子正在雨点的敲击下蚀化,石板街上到处都漫流着肮脏的污水。风依然是寒冷的。空荡荡的街道上,有时会偶尔走过来一个乡下人,破毡帽护着脑门,胳膊上挽一筐子土豆或萝卜,有气无力地呼唤着买主。唉,城市在这样的日子里完全丧失了生气,变得没有一点可爱之处了。”叙述者显然对这样的县城是不满意的,它是缺乏生气和可爱之所在,于是镜头转到了县城中学喧闹的放学场景,那些活跃、进取、青春躁动的少年都是县城最好的注脚。除此之外,乡村少年孙少平只要学校没什么事,就一个人出去在城里的各种地方转,他用全部的身心感受和抚摸这个梦想之地:大街小巷,城里城外,角角落落他都去过。由于人生地不熟,他也不感到身穿破衣服在公众场所中的寒酸,自由自在地在这个城市的四面八方逛荡,他在这其间获得了无数新奇的印象,甚至觉得弥漫在城市上空的炭烟味闻起来都是别具一格的。在路遥的另一部影响较大的作品《人生》中,被清退出教师队伍的高加林做了农民,再次来到县城,县城也是以全貌的形式出现在他的视野之内,一片平房和楼房交织的建筑物,高低错落,从半山坡一直延伸到河岸上,“亲爱的县城还像往日一样,灰蓬蓬地显出了它那诱人的魅力。他没有走过更大的城市,县城在他的眼里就是大城市,就是别一番天地。他对这里的一切都是熟悉的,亲切的;从初中到高中,他都是在这里度过。他对自己和社会的深入认识,对未来生活的无数梦想,都是在这里开始的。学校、街道、电影院、商店、浴池、体育场……生活是多么的丰富多彩!”
在这种用脚步测量和检验过的城市的每一个地方,都带着审美的色彩,这也是城市在较早进入文学视野之时的暧昧微妙时刻,环境本身包含着对环境的阐释。尽管高加林失败后回归了传统的乡村道德,是“卖了良心才回来”,但城市是丰富多彩的,是值得被细致描绘和感受的,城市指向“未来”的不具体,包含着热情、活力、伤害和各种可能性。今天许多青年作家笔下的城市已经失去了这样的张力,城市是薄弱的幻觉,它单向度地决定自己的生活和世界。
普鲁斯特在批评圣伯夫时说,对智力的评价与日俱减,而与日俱明的是,作家只有超越智力方能重新抓住我们印象中的某种东西,就是触及他自身的某些东西,也就说触及艺术唯一的素材。而智力以过去的名义向我们反馈的东西,已不是那个东西本身。有关城市的写作也是如此,城市在青年写作者的笔下,荡开了远在天际的样子,避开了以往文学写作设置的路障和绊脚石——那些看起来生硬的外部描写和地区实例,出现在小说中的是一个人生活中不断遭遇的困境难题,是世俗人间的爱和疏离,是魅影和梦魇,忧伤而失望地划定了一个个真实的界限,让人没有办法怀疑它的诚挚与可靠。表面是明显的个体化现实,但超越于此,又常常隐藏着共同的命运和情况。被空置化的“城市”,在釜底抽薪之时,是不是顺便也被抽离了作品气象上升和生活扎实的可能?绝不是作者在寻找他的世界,“当作者通过作品揭示一个世界时,这就是世界在自我揭示”2○。世界走向哪里,怎么走,作家们怎么写,怎么感受,互相感应着,彼此寻觅,触及艺术的唯一素材才会现身,它藏匿在客体中,是等待被个人生命不断唤醒和重新创造出来的声色和记忆。
在这种用脚步测量和检验过的城市的每一个地方,都带着审美的色彩,这也是城市在较早进入文学视野之时的暧昧微妙时刻
❶【德】奥尔巴赫:《摹仿论》,[译]吴麟绶、周新建、高艳婷,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P457。
❷转引自,赵园:《北京:城与人》,米盖尔·杜夫海纳:《美学和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P29。
编辑/吴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