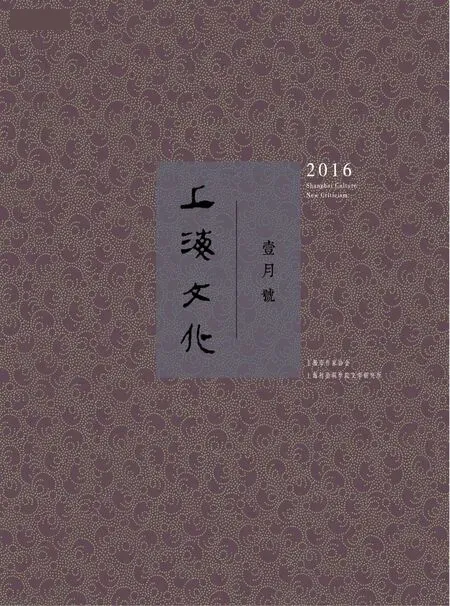上海地理注疏(一)
沈仲旻
上海地理注疏(一)
沈仲旻
一次回访
多伦美术馆
那年在郊区旅馆的地下室餐厅吃早饭时,我读完了一部小说的最后几页。它是一本深灰色封面、镶着半公分黄色装饰边的口袋书。小说的尾声波澜不惊,没有连贯的对话,画面也毫无焦点,一切都乘着一股平淡无奇的自然力流向大街,男主人公的自画像被难以辨认地凝固在由公交车站和旋转栏栅门围起的嘈杂街景之中。我推开餐厅的门,铰链在身后发出了嘎吱声响,我以一步两级台阶的速度从旋转楼梯走上一楼。前台上方挂着三面指向不同时区的挂钟,自动落地玻璃大门好像坏了,一直处在试图不断关合的敞开状态,我向外走下三级台阶,街道上的阳光令我一阵晕眩。这片淹没在白光中的陌生街景,让我想起了上海市中心的一个地方,虽然两者的布局和形状并无任何相似之处。那条马路位于老虹口心脏,它穿过一片住宅和市政工地,两头都顶住了四川北路绵长的腰间,与之形成了蜿蜒紧缩的环状丁字路口。
那一次,图森猝不及防地站在离我只有十几公分的地方,我第一个走进电梯,图森是第二个,L是第三个。L跟我跟得并不紧,他跨步的节奏展现出一种熟悉的悠然与傲慢。一阵不停的机械行走,让我彻底忘了十分钟前争吵的原因。另外两个陌生人最后走了进来,矮个儿的男人脸上有一块白癜风,他负责按了关门的按钮。电梯内,五个人站得像一排风尘仆仆的鞋刷,各自面朝着略微不同的方向。我们都将去往四楼,都会坐进由右边这个小说家主持的演讲厅。图森靠在电梯最右侧,紧贴着电梯的金属墙壁。这个有着球型下巴的小说家,也许是从那个名叫科西嘉的岛屿始发的,经历了夜不能寐的长途奔波,从划过极地边缘的干燥飞机客舱,到换上了洁白布座套的大众牌出租车,途经申字型高架的不同闸道,最后踏进一家走廊里铺着酱红色格纹地毯的星级宾馆,在两个一高一矮的美术馆接待人员的陪同下,去对面的汤团店吃了一碗难以下咽的本土料理,此时此刻,他的外套和皮肤上应该夹带了十几种刺鼻的混合气味,哪怕是为了掩盖疲惫前夜而喷洒的古龙水也会因为空间的快速辗转而发生轻微的变质,更可能明显的是,他几分钟前在路口抽过的香烟粉尘会伸出触手,负责黏合这些渐渐消散的气味分子,就像一个个沾着焦油的微型红毛丹在他的轮廓线上整齐地自旋着排开——可是,这台电梯里除了通风管道中送出的塑料味人造风之外,什么也闻不到。
他的肩膀朝一边倾斜,单肩背着一个黑色书包,看了眼电梯的计数器。红色的数字从1至2开始缓慢地递增。L将双手插进了牛仔裤口袋,我低着头,看不到他的脸。电梯门缝的接合处透出黑暗和光亮的过度交替,看起来像是一种人工设计的灯光效果。光线变换了两次后,我又瞥了一眼图森,我发现此刻他也正在迅速扫视我和L,接着又立马将视线低转回了红色计数器——这期间还伴随着嘴角的一记上扬的抽动。那是什么?一种类似于微笑的表情?
多伦美术馆的电梯虽然狭小,但似乎折叠着长度足以绕着大楼好几圈的透明褶皱,我想起《神秘博士》(Doctor Who)电视剧里反复出现的那句台词:“bigger on the inside”(里面比外面大)。那些密集的褶皱相互盘旋伸展,穿插进我们五个人的身体,我们却对此毫无知觉。但如果仔细回想,也许有人会察觉到,在这个电梯内,没有谁能长时间直视着别人,我们的视线只是相互翻过透明的褶皱山,进行着路径的交叉,即便相遇,也是在一种尴尬的短暂中进行有限的停留,而除此之外的所有时间里,我们只能莫名奇妙、全神贯注地被这个立方体内由银色四壁围构成的虚无山体所吸引。
电梯最后的一声“叮”化为了一个被过久注视的字符漫射而成的陌生拖影,在这悄无声息的十几秒钟内,只有万有引力在假装呜呜作响。
新旺茶餐厅
让-菲利普·图森(Jean-Philippe Toussaint),比利时法语小说家,午夜出版社的单色描绘者,用阿兰-罗伯·格里耶的话说,他是“叙事体的抽象画艺术”的创造者;他也被看成是新小说的代表人物,但用图森自己的话说,又变成了什么“新新小说”。据其小说集《迟疑、电视机、自画像》[La Réticence,La Télévision,Autoportrait(à l'étranger)]的中文版编后记中提到,图森的口头禅可能是“peut-être”(也许)。
我读的他的第一本小说是《先生》(Monsieur),最后一本是在今年黄梅天的某个雨夜以体育节目中高速摄影机的帧数读完的仅几页纸的《齐达内的忧郁》(La Mélancolie de Zidane)。第一次在多伦美术馆见到图森时是2006 年6月,《齐达内的忧郁》是他于一个月后发表的一篇报刊短文,内容当然是有关足球史上那个最奇异的瞬间的——“他没有办法了,也没有力量、能量和意志,去完成最后的辉煌一击,最后一个纯粹的形式——漂亮的头球,在几秒钟以前被布冯扑出了,这终于使他看到了自己不可救药的无能为力。现在,形式在对抗他——这对一个艺术家来说是不可接受的,我们知道艺术和忧郁的内在联系。无法留下一个进球,他将留下精神。”
自从那次电梯相遇后,他的作品很少再被媒体提起,后来再一次见到图森,是在多年之后女青年大厦的一个放映活动上。当时他带来了一部根据其新作(《逃跑》)拍成的短片,故事发生在中国。短片乏善可陈,但我却总是记得小说封面上由图森自己拍摄的那张黑白照片,它反而更像一部早已秘密完成的电影:一辆行驶的助动车上骑着三个紧紧靠着的人,他们正背对镜头飞驰而去,夜色晦暗难辨,只有他们的轮廓被偶然经过的车灯所定格。
放映活动结束后已是晚上十点多,他们问我知道现在哪里还可以吃宵夜,“这个点……好像只有去新旺了”。
在新旺的时候,我们正好面对面坐着,几个由崭新白色人造大理石桌拼成的长桌,刺破了茶餐厅无数个整齐的小矩阵。餐厅明亮宽敞,摩登的暖色节能灯使得米灰色的密胺餐具呈现出一种类似于肌肤的柔亮调子。
活动的组织者、出版人、评论家、翻译、杂志编辑、报刊记者在食物中开始变得亲切而善谈。一个冰火菠萝油下肚后,我忽然感到一阵来自胃部强烈的不适,我放下筷子,将干净的方形纸巾一叠二压在盘子底下,捡起已经落在地上很久、被自己无知无觉踩在脚下的黑色外套。告别时,图森和我唯一的对话被茶餐厅的喧闹所淹没,这一次,他抽动嘴角并上扬的动作拉得更长了,现在,那看起来简直就是一种常见的微笑了。但这一次——我确信,这并非是一个微笑。这是一段录像的回放,磁带信号的划痕在重播的过程中显露在画面里,它们是握手、语言和器皿敲击所发出的若隐若现的干扰。
路
我跟了这辆破水果车一个短短的街区,从陕西南路华光性保健用品商店门口,一直到襄阳北路的光头面馆老板的哈雷车前,然后,我决定恢复正常的速度,从它的右侧超了过去。
巨鹿路
今天上午,我骑在一辆拉着几箱水蜜桃的电动黄鱼车后面。我保持前脚掌低速运行,尽量靠近黄鱼车的尾部,直到自行车链条的声音可以轻松碾进电动马达的自言自语中,好像两者是一个由达芬奇亲手制造的像模像样的联动机械装置。
这是丰饶之神极度有限的公然展开自己私密部位的时刻:潮湿的空气和微风,将水蜜桃的浓密香味送向鼻腔,但这条香道非常狭窄,狭窄到差不多和我的自行车手把的宽度一样,所以我要既谨慎又放松地,将我/自行车与水蜜桃的香味隧道进行精准的暗中交合。整个过程既如一场欢愉的小型运动会,又像一次肃穆的伽马刀手术。
我跟了这辆破水果车一个短短的街区,从陕西南路华光性保健用品商店门口,一直到襄阳北路的光头面馆老板的哈雷车前,然后,我决定恢复正常的速度,从它的右侧超了过去。
常熟路
礼拜二中午走在常熟路上的时候,天是灰蒙蒙的。“天边亮,要落雨了。”
延庆路不到一点的地方有一个公交车站,人流在这里汇集出两股黑色的洪流,在这其中,还有搁浅的自行车夹在其中左右倾斜。
挤过这个丁字路口后,人群散去了许多,行人们纷纷消逝在7号线地铁入口,马路一下子变得宽敞起来,这段新修的路在夏天变得非常难走,林荫道从这里开始断开,一直要走到宝庆路才能重新得到树荫的遮蔽。在接近五原路口时,一个老妇人出现在灰白色的大道中。她拖着一种奇怪的碎步,每步迈开的距离极小,换步的频率却很高,两只脚几乎不离开地面。一双沾着污迹的黑色粗中跟皮鞋在混凝土地砖上发出嚓嚓嚓的声响。黑色乔其纱裙下的双腿像两根发育不良的铁棍山药,僵直的双臂笔直地下垂着,并没有随着身体前进形成自然的弯曲摆动,驼起的背部让整个身体的重量都压到了前倾的脖子上。她提着一个皮质已经斑驳掉落的咖色编制手提袋,因为里面装了太多东西,所以拉链只拉上了一半,从包的开口处露出一些彩色的塑料袋。灰白色的半卷中发稀疏地耷拉在肩膀上,显得有些邋遢。她的左眼似乎是得了严重的白内障。当右眼目朝着路的正前方远远眺望时,那只被与其发色相仿的灰白色浑浊膜衣攀附的左眼,正死死地斜视着我。虽然我知道她并没有在看我,但我还是匆忙地移开了视线,加快速度往前方的林荫道十字路口走去,再也没回头。
小木桥路
那一年冬天,我在中山医院底楼的留院观察病房里遇见过一个老头,他睡在我父亲隔壁床的隔壁,因为并不知道他的真名,所以我只能称他为“小木桥路老克勒”。由于某种绝症的折磨,“小木桥路老克勒”已经无法开口说话,或者说无法用常人可以听清的语言说话,但是他一旁五十来岁的女儿却听得很明白,由她做翻译,我们才能和他做有限的交流。她说:“……哦,他说你们别看他现在没用了,以前小木桥路的邻居都叫他老克勒……年纪轻的时候人样子很好的,块头很大的,胖墩墩的……哦,他还说,小木桥路是最好的地方,他从来没搬过家,搬家这种事情最没意思了……”我们笑笑,他的脸一动也不动。我的一只手开始在包里掏掏摸摸,找到一支黑色水笔,但包里没有任何本子或纸张,唯一能使用的是一张已经被我捏在手里很久的脏兮兮的餐巾纸,我将它撸平垫在皮包上,由于生怕被周围的人发现,我默不作声地迅速勾了几笔老克勒的面容,就将纸巾对折塞进了包里。再坐了一会儿看时间差不多了,我就上楼去血透室接我父亲了。
两天后,我提着一袋橘子去留观病房,发现老克勒的床上睡着另外一个人。几个月后,餐巾纸也丢失了。
汽车们围绕着它缓缓转圈,花园里的石凳湿漉漉的,等待着第一个坐下的老人。风不大的时候,植物轻微地朝着不同方向颤动
流动坐标测绘
4.长乐路三角花园
它并不是完全规则的三角形,只是由几条小马路交汇切割出的陆地,如同一颗边缘有些融化的桉叶糖,它的上街沿以一种不高不低的坡度延向马路。汽车们围绕着它缓缓转圈,花园里的石凳湿漉漉的,等待着第一个坐下的老人。风不大的时候,植物轻微地朝着不同方向颤动。我走在马路对面从它北面经过,预备到路口左转去富民路,与我反向的汽车们围绕着三角花园缓缓转圈,好像一群清晨启程却还没睡醒的角马。
3.富民路小酒馆
黄昏的时候,富民路名叫“小酒馆”的小酒馆门口坐着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她抽出一支箭牌香烟在桌子上敲了几下,以确保烟丝压紧,双眼一直望着马路对面的伍缘超市,注视着那些手里提着彩色塑料袋、从粉皮一样的塑料挂帘里进进出出的老人们。香烟在嘴里含了有一会儿,她摸起一旁的红色打火机。打火机就是一次性的塑料打火机,但是上面的彩色商标已经被撕去,露出了通体的红色。窜起的火苗将顶端已经被敲空的烟纸迅速点空,女人猛地一吸,脸颊上露出了两道阴影。
她有个特别的表情。也许是下意识地,鼻翼和嘴部总是微小地抽动,眉头时不时地会皱两下。她并没有注意到我,她的视线从超市大门移到了行道树干枯的枝条上,顺着树枝杂乱无序的路径,她的眼珠会一次次和黑漆漆的悬铃木球型果子重合。她用大拇指抵住烟屁股,弹了两下烟灰,视线却还在树枝之间穿行。大部分烟灰越过玻璃烟灰缸的边缘,散落到栗壳色的桌面上。
她从皮夹克口袋里拿出手机,一个来电,她没有接,直接又将手机塞回了口袋,接着抽了一口烟,换了胳膊的姿势,侧身转向了我。我下意识将视线转向了她身后的行人。她又换了一个姿势,右腿搁在左腿上面,右脚面又绕到左腿肚后面紧贴着。她举起夹着烟的手到嘴边,动作戛然止住,好像想到了什么。她将烟按灭,从口袋里抽出一张二十元纸币一叠二压在杯底,迅速收起东西起身离开。穿过马路的同时,她重新从口袋里掏出手机,好像拨了什么号码,短促的碎步躲避着车流。
电话似乎没有接通。
现在她站到了街对面的伍缘超市门前,望着这边的小酒馆,然后将手机放回口袋,我试图捕捉她的目光,但她的脸几次淹没在闪烁而过的红色汽车尾灯中。一个几分钟前走入便利店的老妇人从里面走出来,低着头,捏着一把彩色塑料袋,从她身后走过。塑料袋擦到了她的胳膊。
就在这短短几秒钟内,天色迅速暗下,她又掏出一支烟塞进嘴里,利索地点燃,最后朝我这边看了一眼,转身朝着北面的高架路口走去。
服务生过来收走了钱和杯子。我将位子换到了她刚才坐的地方,抬头看去,悬铃木已经和天空混为了同一种颜色。
2.静安寺
我曾经在南京西路华山路口的轮锁大厦里上过一年多的班,同事们时常议论这幢浦西第一高楼的外墙设计和斜对面那座寺庙的风水关系。轮锁大厦的外立面的确没有一处锐角的构造,尤其是对着静安寺的那个转角处被薄薄削出一条绸带般优雅的钝面,在大厦门前立有一把十几米高的刀状景观雕塑,宽厚的刀背对着寺庙,刀刃对着大厦,雕塑的底座埋在一汪浅浅的方形池水里。轮锁大厦和老海军服饰、久光百货以一个柔润的直角三角形将静安寺的金刚宝座塔稳固地夹托在十字路口。步行走过这个街区,大约只需要三到五分钟,也有人在里面兜兜转转几小时走不出来。夜晚的静安寺,行道树上长着密密麻麻的紫色灯泡,像一排排荧光战车将天空围剿起来,只露出一个个泥浆般的窟窿。喷水池前高高矗立的绿化雕塑笼罩在一层粉色的底光之中,一对身体由植物构成的情侣相互拥抱着,一个呼啦圈状的金属环倾斜着穿过他们的腹腔与背脊。它们身上的植物在六月的季节里疯狂生长,好像正努力形成一个全新的雕塑。一旁的下沉式广场是静安寺周边唯一下陷的地势,它的台阶层层叠叠伸向看不见的“涌泉”深处,而那口占据着轰隆隆的地铁入口的涌泉井,传说曾经昼夜沸腾,琦琦曾考据过它的另一别名,因为其深可通海,所以也称“海眼”。在干涸的海眼圆心四周,是一圈过时的小商店禁闭着大门,无人的庭廊里还躺着上世纪理发店音乐的回声,在没有市集和节庆活动的日子里,整个下沉式广场只是一个重力的凹槽,一块静安公园与南京西路之间的废墟。而就在几十米外的芮欧广场,则出现了一面崭新的、闪烁着幽幽光晕的LED幕墙,驱车经过的人们都从后座伸出脑袋,像金鱼一样仰望着这片通电的银河星光。而那些更明亮的、倒吊着玻璃钢模特的银白色橱窗、变幻着惰性色彩的霓虹灯管,则在四周刀锋般与昆虫模样的摩天大楼的反射下,以光速插入观光者的视网膜。观光者们忘了看时间,他们来回从橱窗的右边进入,从左边出来,又转进了右边,循环往复,商店定时喷洒的香氛经由观光者经过留下的气旋,形成了一个粘稠的环带。站在路边等待空车的黄袍僧侣、在花坛里吃盒饭的乞丐、在马路中央跳着慢速回旋舞的肥胖交警、拎着纸袋折线穿过马路的观光客、脸上洋溢着手机屏幕彩光的下班族、夜公园长凳上捏着利乐包装豆奶打着瞌睡的老人……站在这样一个自行构建的迷宫里回看静安寺,金顶变得不同寻常,它看起来不再是一个金箔与柚木构成的藏宝盒,而是一座搭载着千万手机调频的信号发射塔,向四方辐射出音符含糊的咒语,它进入那些正搜寻着无线网络的人的指甲盖里、进入报刊亭招贴栏的名人肖像里、进入唱着《欢乐颂》的冰淇淋车的奶油螺旋喷头里……这个路口好像正举行着一场今敏(Satoshi Kon)动画片《红辣椒》(Paprika)的露天放映:行人的梦在这里开始迅速渗透、相互连接,他们不得不加入迎面而来的花车游行,无数个奇装异服、五光十色的敌人将陪伴自己去往最后一夜的狂欢——或者说——这一切也完全被泽拉兹尼(Roger Zelazny)的《光明王》(Lord of Light)所预言:“战争打响那天,破晓的天空宛若处女大腿上的咬痕般呈现出一片粉红。”
在没有市集和节庆活动的日子里,整个下沉式广场只是一个重力的凹槽,一块静安公园与南京西路之间的废墟
1.江宁路桥
江宁路如今是丑陋的,但我还是要去走它。我走在它身上,就好像用一条腿在另一条腿上行走,每一步都知道踩在哪儿,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感觉。但我想,那还算不算是走路呢?国棉六厂在上个世纪发生过多次火灾,我每次都闻讯赶来,站在纱厂医院门口的瞭望点,嘴里含好桉叶糖,聚精会神地注视着熊熊升天的黑烟,幻想着自己正在里面做着死前挣扎,挣扎到一半忽然醒来,发觉不过是因为盖太多被子而导致的一场热梦。19路电车在转弯的时候一根鞭子掉了下来,售票员从被挡住的墙角出现时,懒洋洋地抬着头,脖子上的零钱布包左右摇晃,她以米开朗基罗的姿势伸手去拉那根凭空坠落的天际线。没有火灾时,我就从19路车站那里走去路的尽头,路名结束的地方会出现一座桥,一些人站在桥上看着苏州河里的塑料袋和破球鞋飘来飘去,我则思考着假如将身后上海造币厂里所有的钱币都扔进河里,河能不能被填满。后来我才知道,填满这条河的是一个名叫世纪之门与另一个名叫中远两湾城的楼盘的倒影,不过我奶奶说世纪之门在很多年前已经在河面上同样的位置出现过,只不过它是云朵的颜色、云朵的形状,它的出现是“派好的”。她描绘世纪之门的神情,总是让我想到她遇见玉佛寺上空显灵的观世音菩萨时快速翕动的嘴唇,或是发现蟒蛇在老宅现身的那次,她一声不吭地朝着蜡烛香掉眼泪,眼泪一滴一滴像蚕豆那么大,掉在地上的印子三天都没有消失。
很多人都在江宁路桥上看到过耸人听闻的景象。只有真正的河水在脚下流过时,从未有人见过。
0
踏浪者看浪,描述总是不确定的。每一次都在修正。错误本身形成了完美的波浪曲线。
-1.岛
落日时分,礁石另一侧的海平面上泛着耀眼的金色光芒。
在来到这片海滨之前,我被一种毛虫飞蛾叮咬,它们还在我的左手臂上产下了卵,这些前所未见的虫子是L带来的。他睡在我旁边,似乎愿意和我冰释前嫌,但是我得了这样的病,必须进行隔离。独自到了海滨后,我找了一个老中医,连续服用了三天蛞蝓汤,已经痊愈了。我的房子向着海岸,但是需要绕过几栋小楼和一个海滨体育场才能走到海滩上,体育场里每周举行一次赛狗、一次回旋舞表演、一次足球比赛、一次田径运动会、一次吃龙虾片大赛、一次天文爱好者集会以及一次睡觉比赛,睡觉比赛每个礼拜天傍晚举行。礼拜天傍晚,我绕过体育场,来到海滩边,铺了一条干爽的紫色毛巾毯在沙滩上,活络着双腿准备下水。琦琦对我说:“太阳要落山了,水已经很冷了,你还是要下去吗?”我目测从礁石背后游到了金色海面上的距离。
“我下去的,来得及的。”
大约是早上八点一刻,开进瑞金一路地铁站工地的土方车歇斯底里地滚动着轮盘。我爬起来关窗时看到弄堂里的青桐长出了几片新的叶子。我忽然意识到,去年在海浪巨大的斯里兰卡东岸游历之前,那个岛屿其实并没有在地图上出现过,它是在刚才的那次睡眠中凭空诞生的,一切在极端的瞬间完成了所有的进化,这瞬间之短,以至于蒙过了所有的地理学家和考古学家。但它的确是新的,泪滴形的身体还是湿漉漉的,带着一身臭纸浆味的羊水。
考古学地图
上博雕塑厅
一个男孩走到雕像前,要求父亲给他照张相。他的头只到这尊愤怒相的天王的膝盖。男孩的相貌独特,若不仔细分辨,也像是个英气的女孩。他的额头与眉骨很高,眼眸大而亮,长睫毛反射着来自展厅上空的灯光,泛出一种明亮的金褐色,看起来不太像纯正的汉人血统。从父亲的背面与其擦身而过,父亲的背形成了一片迅速隆起的黑色山丘,他举起相机,遮住了那张阴影背后的脸。视线越过父亲的肩膀落在男孩那张被展厅射灯打亮的脸上。男孩也瞥到了我,露出了一个没有门牙的笑容,以及忽然的,他好像想起什么似的,回头认真望了一眼雕像的脸,转过身时,他做了一个跟天王像一模一样的表情:眉头紧锁、杏眼圆睁、双唇用力地抿紧,嘴角如铁锚般一样坚决地坠下。“咔嚓”。男孩随即又恢复了微笑,朝他的父亲腼腆地扑过去,就像一只归巢的灰雀。
斗兽场
静安公园门口的两个咖啡馆前有一片广场空地,空地的中央矗立着一头犀牛青铜雕塑。去年初秋,我在公园门口溜达,见到一对母女正走向这头犀牛。母亲边走边熟练地从手腕上挂着的黄色塑料袋里拿出了一个石榴,将它高高举向空中,接着两步后,朝着犀牛鼻头上的尖角用力往下一砸。女孩紧跟上去,向母亲伸出手,几瓣红宝石落在了她手里。
远征饭店
K那天说要借一本书给我,我们约在了愚园路的一个新疆餐厅吃晚饭。
我们坐在靠窗的位置,外面下着非常密的小雨,隔着玻璃很难看清雨到底有没有停,或是不是还下着。我们来得太早了,餐厅里只有稀稀拉拉的两三个客人,餐厅只开放了一个区域。深处台阶卡座上方的水晶吊灯关着,含铅玻璃碎片和廉价铜色金属一丝不动地悬在暗处。它靠近我们的一侧能略微反射到一些暖色的灯光,而另一侧则吸收着傍晚五点二十八分来自街道的蓝黑色。
有那么一刻,水晶吊灯那原本一动不动的透明锥形体忽然微微抖动了一下,并从其内部颤射出一丝幽幽的白光。这光亮在一颗钉子落地发出声响的时间里迅速出现又消失。水晶吊灯随即又回到了原来的样子。
我们点了羊肉串和抓饭。一声不吭、狼吞虎咽地吃饱后,K把那本薄到只有几页纸的书递给我。叫结账的时候我多打包了一块馕。
一块从米黄向浅棕色过渡的热乎乎的馕,随着几个零钱铜板被送上来。
绣着墨绿植物花纹的酱红色桌布、白色的书封、灰色的硬币、银盘里正凝结的橙色羊油,在馕的周围依次排开。
馕表面的深褐色烤痕一圈一圈地向外散开,断断续续地隐没在与之同形的渐变边界上,“像一种古老的文字”。我将它小心翼翼地装进了一只透明塑料袋里,又将塑料袋系在包带上,打了两个结实的活结。
走在回家路上的时候,我一直忍不住低头去看那只在腰间晃荡的馕,看它在空中撞击我身体的样子。虽然我打着伞,但还是生怕它被淋湿。“毕竟是一种古老的文字。”
馕表面的深褐色烤痕一圈一圈地向外散开,断断续续地隐没在与之同形的渐变边界上,“像一种古老的文字”
编辑/张定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