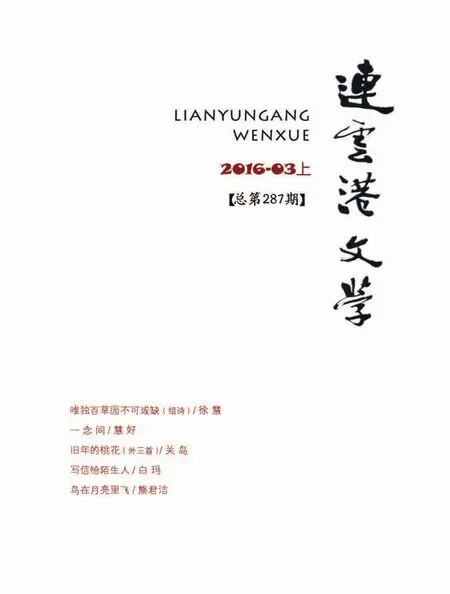故事,或者聒噪
冯磊/山东
故事,或者聒噪
冯磊/山东
1
一九七O年代末期,村里组织村民去修整荆河的河道。
那是一个周日,我跟着当民办教师的父亲去了工地。记忆里工地上竖着红旗,到处都是干活的民工。大家把河道里淤积的沙子铲出来,用胶轮排子车拉到河滩上去。
那时刚上小学。大人干活,我坐在沙堆上看。沙子里到处都是青色的砖头瓦砾。那些只有半个拇指大、甚至更小一些的青砖的琐屑,早已被河水冲刷打磨得圆润、光滑,不再有一丝棱角。相对于正在忙碌的民工,它们要年长很多。——多年以后,当我的眼角泛起水一样的涟漪,我才发现时光不仅是一把杀猪刀,它不仅会在最美女人的脸上留下深深的刻痕,也会把一些原本面目峥嵘的东西消灭得干干净净。
比如那些年代久远的青砖和石块。
河滩上有一种质地坚硬、带着黑色斑点的石块,我曾把它们带回家去,在夜晚、在自家楝子树下进行对击,竟然碰撞出了耀眼的火花,鼻子里闻到一股火星火燎的味道。我曾一度猜想,在久远的年代,生活在附近的先民就是这样取火的:那时候人烟稀少,他们在树林子里打来猎物,用石块那锋利的刃将肉一块块割开;然后有人拿来两块石头,彼此对撞击打,终于引燃干草,并进而美餐一顿。
我还捡到过一些硬币。在河滩上,我碰到的硬币有两种:一种是铜板,上面有“湖北军政府”或者“广东军政府”的字样;另一种则是伪满洲国的钱币。与民国的铜圆不一样,溥仪政权铸造的钱币正面是双龙戏珠,背面书有“大满洲国”几个字。
人生而短暂,满打满算不过几十年。在和平的岁月里也就罢了,毕竟生命处于常态。如果不幸遭遇战火和动乱,则会瞬间制造出千百万个故事和千百万种命运。——这样想着,就产生了类似毕加索名作《格尔尼卡》中的幻觉。
和人一样,那些钱币也有自己的故事。它们本来是一块金属,被人投入到熔炉里去,再后来它们以货币的形式出现。当集市上的商贩从别人手里拿到了一个硬币,他说:“看,这是一枚暂新的银毫子!”他乐得合不拢嘴,一边走一边感叹自己的好运气。
这枚硬币被放入一个小布兜里珍藏起来。有一天,商人的儿子偷走了它,顺手买了一串糖葫芦。回家以后,他的屁股上留下了通红的掌印,那是对一个孩子不诚实和贪嘴的惩罚。
这枚硬币继续在无数人的手里辗转。终于,它落到了一个士兵的手里。那时候,它仍然闪着亮光。士兵把它放在一个硬皮夹子里,带着它从东北平原来到了华北平原。再后来,他被击毙于河道里,那枚硬币则从口袋里滑落到水里,至此需要经历四十多年的时光才得以重见天日。
我的故事并非完全出于臆断。一九九零年代初期,年近九十岁的老祖母曾经告诉我,一九四O年代,曾有大批的军人在此渡河。因为战事紧张而河水湍急,他们中的一些人从农民家里抢来黄泥缸,坐到里面试图漂浮而过渡河。其中,很多人被对岸的军队开枪打死。还有一部分,则因为泥缸被子弹击碎而落入河里淹死。
“那是些年轻人,年龄都不大。”祖母说。
2
关于这条河流,我的同学黄安讲了很多故事。他个子矮小,脸上有几颗雀斑,一双老鼠眼滴溜溜乱转。他的脸色苍白,像很多用功的少年一样,脸上总带着几分吃不饱的颜色。他来自于一个叫做大巩庄的村子,那村子就在河流的边上。
黄安曾告诉我,他们村里有人在掘土的时候挖出过锈迹斑斑的金属盒子。盒子被打开以后,里面有锃亮的天平、卡尺一类的东西。“特别像咱们物理老师手里的游标卡尺”,他说。
我一直不相信黄安的话。要知道,小尹老师手里的游标卡尺是极其精确的度量工具。不仅我们第一次见,我们的父辈乃至祖父辈,从来都无缘见过这种精密仪器。数百年来,鲁南地区极为封闭,本地人素以以中正、简朴为家训,尤以刻板而出名。我无法想象,两千多年前的人们是如何使用这些工具的。我一度怀疑黄同学的诚实。
二OO六年,我见到了扬州市博物馆收藏的青铜卡尺,卡尺的造型与当年物理老师展示的工具几乎一模一样。我的大脑突然间一片空白,像被电击了一样说不出话来。
黄安还告诉我,他们村里有个传说。一个大雨磅礴的暗夜,滕国的公主乘船出门,远远地看到了一对红灯笼。年少无知的女孩子对着灯笼射了一箭,没想到那竟是蛟龙的一双眼睛。因为大水肆虐,蛟龙奉命用自己的身躯为村民阻挡洪水,不想却遭此厄运。剧痛之下,它猛地一甩尾巴,瞬间消失在河道里。黄同学说,自此以后,大巩庄村民盖房子用沙都要到滕城村去买,大巩庄村后河道里的黄沙都被蛟龙用尾巴拨到滕城村去了。
3
滕城村就是滕国的故址。于我而言,关于这村子的记忆,则源于每年的庙会。
“三月三,蚂蚁上灶山”。每年三月,荠菜都要开花。此时,它的菜梗都中空了,已经不能食用。在故乡,每年三月初三那天早上,村民们吃过用荠菜煮熟了的鸡蛋,就三三两两地赶大集(庙会)去了。
大集的中心在滕城庙。这里曾经香火鼎盛,但却是个极为破败的地方。我曾跟着祖父去赶庙会,在集市上第一次吃到了五分钱一团的棉花糖,第一次见到了本地民间的玩具“王八打鼓”,第一次心惊肉跳地看大一点的孩子吹脆玻璃做成的“琉璃嘣嘣”。
我也曾跟着大人攀上古庙的高台,在高台上四处游走(那庙的墙有一丈多高,有一段是用被打烂了的泥塑垛成的)。时至今日,我仍记得高台的东半部分有三间厢房。那是上下两层的建筑,中间用厚厚的松木隔开。那木板既是二层楼的地板,也是一层楼的顶棚。彼时,厢房的木板已被人掀去大半,站在门外可以看到脚下的空房间,就像是一张恐怖的大口,令人望而止步。
我却从此对那古庙充满了好奇,总觉得那是一个充满了传说与神秘色彩的地方。
读初中以后,我曾多次到古庙去看废墟。在古庙高台的北侧,我们见到了无数的瓦砾和青砖。黄安说,那瓦砾是一九六O或七O年代被人掀翻的古庙的屋顶。至于里面被人毁掉的泥塑,至少应是明代的遗物。古庙地下有条神秘通道,据说一头通往庄里村的点将台,一头通往峄山。庙里的也曾有过和尚,老和尚死去多年,每年清明都有人前来给他上坟。
4
这古庙就是周代滕小国国都的中心。站在河流的边上,遥望古庙高台,时常会油然而生一种仰望的感觉:那曾是一座繁华的城市,有君主,有将帅,有士兵,有歌妓,有乞丐,有牛马,有田野,有粮仓……热闹非凡。时隔两千多年,古城的轮廓仍在。那城的外围墙上栽满了槐树。至于那树,传说是民国时的人栽种的。每年五月,槐花的芬芳在附近每个村落飘散,我们因此年年享用前人栽树的余荫。
现在想想,那些古树都是见过世面的老者。它们遇到过战火,见识过人间的悲欢冷暖,认识每一个在地里劳作的农民。在它们的面前,所有的一切都是年轻的,所有的痴妄都是可笑的。它们安静地站在那里,只是伫立着看,看多了,河道里的风和水也就有了味道。
每一年的春天,日头开始散发出香气,它唤醒大地,催生果实,是真正慈爱的长者。黄安告诉我,这古庙的后面和东北,曾经有两座封土堆,不知道是谁的坟墓。黄安又说,古庙地下的秘道通往庄里村的点将台,那其实是两千年多前滕国贵族的墓地。
一九八零年代,本地兴起了盗掘之风。一些人挖掘出青铜器销往外地,然后销往海外。为此,本地开始对盗墓者进行严厉的打击。
一九九八年,我在图书馆借到一本名为《商周断代史》的著作。那本书里有数十张图片,都是些上古的玉器。其中的一些精品来自于鲁南地区,现在收藏在芝加哥或纽约的私人博物馆。
一块古玉,就像是一块上古时期人类的眼睑。
5
少年时代,我曾多次造访那古庙和高台。夕阳西下的时候,和伙伴们坐在古城外围的寨墙上,看天上那些带钩的云,看斑鸠飞过村庄,听“咣咣朵夫”(杜鹃鸟)那亮丽的嗓音在芒种时分响彻每一寸田野。那时候,直觉自己是这块土地上的一份子。
中年之后,我曾一再地问自己:为什么关心那高台,又为什么屡屡到那地方去?
默想许久,我终于明白:相对于完整的现实,斑驳陆离的废墟更有魅力;相对于触手可及的物质生活,精神的叠加与断层更令人迷醉。
一九八O年代后期,有日本学者前来古庙考察。再后来,他们投资对古庙进行改建,同时收集了部分碑刻并对其进行集中保护,一时传为美谈。
在新落成的东跨院,我见到过一块苏东坡的诗碑,感觉异常亲切。也见到了一块宋太祖颁布的《戒石令》,上面有黄庭坚的楷书:“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那书法气韵亨通,令人耳清目爽。
站在高台上放眼望去,只见故城东南一带早已颓屺。千百年来,不知道是哪一朝哪一代,滔滔洪水冲垮了高台的一角,将“蕃阳八景”之一的“文公台夕照”给冲没了。在这里,老邻居孟轲教授曾坐着纹饰的车子前来讲课,并顺手拎走过几升小米……因此,《孟子》里也多了一行文字:“孟子之滕,馆于上宫”。
6
无数个夏夜,扯了席子睡在大门口,听蛐蛐儿没完没了地演奏。在梦里,我曾经多次见到那座高台,那两棵据说有一千多年高龄的家槐树至今仍然屹立不倒。
在梦里,我对自己说,那在路上走的都留下了足迹,那在水里生的都有自己的记忆。生命是多么奇妙的事情!大自然孕育万物,给了人类以悲悯和廉耻之心,也给了万物以阳光和雨露。在这块土地上,每一块瓦片都让我感到神秘,每一朵梧桐花瓣的味道都沁人心脾。
我当然知道,这土地和别人的故乡没有什么区别,所有人的故乡都会长出传说与欢乐的谷穗。但是,在我的内心深处,唯有这块土地最难忘怀。关于这块土地的种种,在我的心里始终纠缠不清。那记忆就像一根神秘的脐带,扯一扯就能引发千言万语。
这个晚上,我再次读到了莱蒙托夫的那段话,他说:“一个人心灵的历史,哪怕是最渺小的人物的心灵的历史,也要比整个民族的历史有趣和有益。尤其是,当它以毫无哗众取宠之心写来的时候”。
读到这里,我有种卸下包袱的感觉,并因此长长地舒了口气。
(责任编辑赵士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