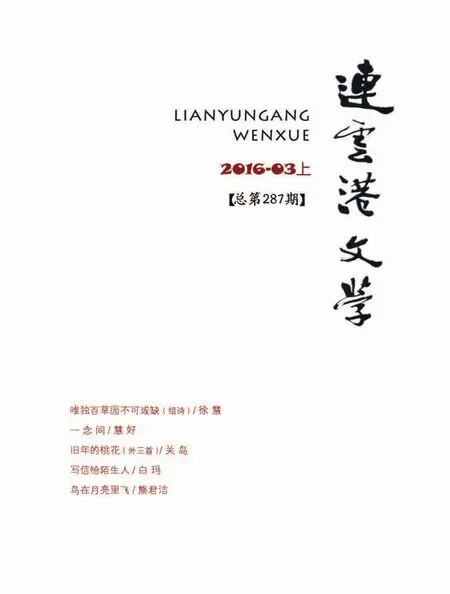老姑娘
田凤梅/江苏
老姑娘
田凤梅/江苏
一
如今农村到处盖起了小别墅,有些村子开始翻建起了商品楼,俨然农村走向了城市。哪里还能看到三十年代“建筑”的影子,然而幸福村外就有一处别样的风景,别样的建筑。它是荒野的奇迹——那间百亩农田边鹤立鸡群的破旧的矮矮的茅草房。远远看去好像谁家在农田边堆了个大草垛,茅屋顶的茅草风一吹就会四处飘散。茅草不知换了多少回,眼下,又已经薄薄的,但仍然还很结实的覆盖着。四周用土坯垒砌的土墙,土墙的外围已经长满了青苔,一些不知名的小花,小草将茅草屋修饰出另一副自然画面。这间茅草屋在这片荒野里坚强的守护着它的主人,一个白发苍苍的八十几岁的老太太,村里的小孩子都叫她老姑姑,大人们都叫她老姑娘。
原来这个地方也不全部是农田,和茅草房并排还住着七,八户人家。后来因为村里人口增多,要扩展田地,村干部就让大家搬到村子里去了。一来,可以增加农田的面积以增加粮食的产量,二来,村里人多了也热闹,乡亲们也可以互相照顾,大家都觉得村长说得很对,乐呵呵地搬家让村民们来拆房子,高高兴兴地在村里盖了新房子住下。唯独老姑娘死死守着这间茅草房,不让拆,不管谁来劝都不行。最后村里想到了她远在远方某个城市唯一的亲人——远房表侄,希望表侄能将老姑娘劝说了搬离这个地方。
表侄抽空回到幸福村,带了一堆礼品给这位十年没见的表姑,老姑娘看到表侄的一瞬间仿佛什么事情都看透了。
“你回来干什么?你怎么舍得回来了?”老姑娘瞪着眼睛看着表侄子。
“姑姑,您还是将这茅草屋拆了和我去上海吧,您一个人在乡下爸妈也都不放心您,再说在这空野之中住着,到了晚上真的挺让人害怕,所以他们让我来接您!”表侄子边说着边往老姑娘身边靠近。
“带我去上海?那时候我娘生病时,请求你爹娘把她带到上海去治病。你知道吗?你爹娘是怎么说的,说什么已经病成这样了再治就是往水里扔钱。没必要这么浪费了。我就奇怪了,他们都没回来看一眼我娘,怎么就知道她病成什么样子了?分明就是舍不得花钱,要不然我娘也不会……”老姑娘说着用衣袖拭了拭眼角。
“姑姑,这么多年我爸妈也很内疚,一直没脸回来看您。这不,他们想起您了,非要我回来看看您,还一再叮嘱要我带您一起和我回去呢。”表侄子一脸的歉意。
“当初,还不是这里的房子,这里的土地,这里的人,把你爹养大的?你爹小的时候,你爷爷奶奶在外面做生意,将你爹扔给了我们家。然后你爹就成天粘着我,让我喂他吃饭,晚上还得陪他睡觉,他睡觉的时候总喜欢拽着我的衣服不放。我稍微动一下他就醒了,为了让睡个安稳觉,我就一直侧着身子睡,不敢动,害怕把他动醒了。再冷的天也是一个姿势,我的半只胳膊一直露在被子外头,时间长了我的肩膀到了夏天就开始钻心的疼。我一把屎一把尿地照顾他,我也只是比他大了十岁,我也还是个孩子呢,有一次他生病了我就整夜整夜地守着他,他不肯喝药,我就陪着他,我喝一口,他才肯喝一口,最后他的病好了,我却累倒了,他总以为自己是有钱人家的孩子,总是在外面欺负别人家的孩子,不是抓破了人家孩子的脸就是撕烂人家的衣服,我爹娘给他做了多少善后,赔了多少铜钱啊。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是我爹娘的儿子……小兔崽子,我知道这次你是听了村里人的话,被他们喊回来要拆我这宝贝房子的吧?你给我滚。这片土地对你没有感情对你爹可是有恩啦!你和你爹娘,你爷爷奶奶一样的没有人性吗?”老姑娘挥起手中的“龙头”拐杖朝表侄打去。
表侄被老姑娘这么一嚷嚷,吓得抱着头求饶“姑姑,这么多年我一直没时间回来看您,真的很想您,我真的是回来看您的。以前爸妈是对不起老太太,我也常常听爸妈说他们愧对了幸福村的堂嫂,非常后悔。老太太去世后决定给您在村里盖间瓦房,您就是不要,您看您现在这样子,您这是何苦呀……”还没等他的话音落下,老姑娘的拐杖已经落到了他的头上。
“滚,滚,想拆我这命根子,除非我死了,我们老陵家的地方就这么容易让了,这房子我得守着,老陵家也就剩这么点地方了……”老姑娘气得猫着腰直喘气,还不时跺着她的三寸金莲。
“好,姑姑,我走,这些补品您就收下吧。”表侄将礼品往地上一放逃也似的跑了。
“回来看我?回来看我是假,要是真想我了怎么十年多没个消息?这个时候回来看我?”老姑娘边说着边用拐杖敲着表侄带回来的大大小小的礼品盒。
后来表侄来看过几次老姑娘,但没再提让她拆房子的事,她看到了老姑姑的倔劲,也明白了老姑姑对祖屋的一片深情,在村里住了几天,就走了。
二
这个茅草房是老姑娘的曾祖父留下来的。老姑娘的爷爷是地主,大大小小的土坯房,砖房五十余间,耕牛十几头,大船四、五艘,良田几百亩,上上下下家丁二十多个,陵家的财富,别说是在幸福村,即使在方圆八十里内,也算得上数一数二了。后来土地改革,地主阶级自然成了批斗的对象,老姑娘的爷爷被拉去批斗,整天被捆绑在电线杆上不给吃喝,头上戴上用纸(一般用白纸)糊的长锥形帽子(俗称:椒帽)让受压迫的人民群众在大会上陈述他的“累累罪行”,说到动情处往往会受到群众的爆打和侮辱!再坚强的人都受不了这样的折磨,何况老姑娘爷爷身体弱年纪又大,老人家终于倒下了。随后老姑娘的爹自然接替了老姑娘爷爷的“被批斗”工作,但是她爹爹是公子出生,一介文弱书生,大风都可以吹跑的身子骨,哪里经得起这么些大风大浪的冲击。没过多久也追随爷爷离开了这个世界。
转眼间,他们从富裕十足,家丁兴旺的大宅院子,变得破落不堪,一夜间从天堂跌进了地狱。老姑娘家的田地房子全部被没收走了,只留下两间茅草房。因为经受不住长年累月风雨的摧残,一间已经渐渐倒塌,老姑娘和她的母亲相依为命,唯一的亲人就是父亲的堂弟的堂弟——老姑娘的远房堂叔。在她们家落难时带着妻儿,离开了幸福村定居在了远方的城市。
老姑娘的母亲原来是一个贫下中农的女儿,忠厚老实。无论大家怎样对她冷嘲热讽,给她白眼,甚至有捣蛋的孩子用小石头打她,母亲都只是默默地低着头忍受着。她常常告诉老姑娘:“孩子,这是咱们的命,以前你爷爷他们那一辈子作的孽,我们给他们还吧。”
为了和老姑娘继续生活下去,母亲在乡亲们的吐沫星子里忍气吞声着,有时候还会连连道歉:“对不起,对不起。”
时间长了以后,大伙见她们母女俩品行很好,挺规矩的一对母女,没有地主人家霸道和嚣张的影子。看着也挺可怜,慢慢也就接纳了她们。还让老姑娘的母亲加入了集体地养猪劳动,可以挣得工分。这样老姑娘和母亲在幸福村艰难地生活了下来,五十岁那年母亲也因病离开了她。从此三十多岁的老姑娘就这么一个人守着那间茅草房。曾身为小姐的她既不会种地更不会干农活,好在她干得一手绣花的活。远近村民谁家办喜事了,都得请她去给新娘子做绣花鞋,在被子,枕头上绣上个龙凤图,喜娃娃。说来也真神了,老姑娘绣的龙凤似要盘旋而飞,绣只兔子仿佛要吃草,绣个娃娃简直就想伸手抱一抱。老姑娘也总是尽心尽力地为大家绣着花,她也只有在绣花中才能找到她的快乐。
三
张二狗的弟弟原本是年底才结婚,哪知道张二狗的爹爹在刚过年就突然患上了破伤风,不治身亡。按照农村的习俗,家里有人去世的当年不可以办喜事,必须等到三年后才行,张二狗的弟弟急坏了,好不容易找到的媳妇,三年后还会是自己的吗?
“结婚,可以边办丧事边办喜事,农村这就叫冲喜。”张二狗的母亲最后决定着。
“可是谁帮咱们绣鸳鸯?听说老姑娘被十里村的张三魁请走了,一时半会回不来呀。”张二狗告诉母亲。
十里村离幸福村有二十多里路,一个大男人去个一趟还得大半天,何况小脚的老姑娘,她来回就得两天两夜,眼下火烧眉头。
“托人给老姑娘带个话,不管如何都请她帮了这个忙,尽快地赶回来。”张二狗的母亲还是决定试试看。
正在十里村的老姑娘,晚上接到张二狗家捎来的信,瞧着手里还有一堆没有完成的绣品,她皱紧了眉。
“怎么办呢?连夜赶吧,前不久刚害过红眼病的眼睛还有点疼;不赶吧,对不起村里的乡亲们。赶,赶紧绣好了,回去吧。”老姑娘觉得自己村里乡亲的事就是她老姑娘家的事,这样想着不禁手加快了许多。
夜半三更,人们都已经进入了梦乡,夜很静,静得连张三魁家吵得最凶的大黄狗都睡着了。只剩屋角草堆里“唧唧”为她唱歌的小虫陪伴着她。
“冷哦。”老姑娘拉了拉那件单薄的衣衫,继续着。她很想休息一下,但是一想到张二狗家的事,她的手好像更加快了起来。
“不能停下来。”她告诉自己,她一定要在张二狗爹爹出殡前赶回去。
瞌睡虫找到老姑娘,“哎呀,痛。”她惊叫着,绣花针再一次刺到了她已经受伤的手指,鲜血直流。不知道这个手指已经被刺破了多少次了,她用嘴唇吮吸了一下。顺便耸了耸酸痛得麻木的肩,揉了揉微微发疼的眼睛,只停留了片刻。终于在天亮之前赶完了张三魁家的绣品,谢绝了张三魁家的早饭。张三魁也是个心善之人,不但多给了老姑娘几个铜板,还硬揣了几个馒头给她,老姑娘告别了张三魁便一刻不歇地往幸福村赶。
两天两夜的路呀,赶到幸福村的时候,老姑娘已经三宿没合眼了,半路上她撞在了田埂边的大堤上。半天才爬了起来,最后她索性从路边的槐树上折了根粗树枝当拐杖,坚持着一拐一拐地走回幸福村。
“喝口水,吃点点心吧,老姑姑。”张二狗看到风尘仆仆赶到他家的老姑娘便急忙迎了上去。
“不用,正事要紧,耽搁不得,快将绣品拿来。”老姑娘吩咐张二狗。她已经疲惫不堪,不愿意多说一句话,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不能耽搁了孩子的婚事。”
“老姑娘,你不要着急,来得及的,你先休息一下吧,瞧你眼睛红得能吃人了呢。”张二狗母亲瞧着满脸倦容的老姑娘心疼极了。
“没事。”老姑娘接过张二狗母亲递来的绣品,开始跳动着绣花针。
张二狗的弟弟终于迎来了顶着老姑娘绣起来的金黄色龙凤盖头的新媳妇。
然而,老姑娘却病倒了,病倒在她茅草屋里那张“吱吱呀呀”唱着歌的小竹床上。那也是茅草房里唯一的可以看得上眼的“家具”,老姑娘一病就是半个月。大伙忙着地里的庄稼,忘了健健康康的老姑娘也会累得病倒了,而且还是一病不起。病倒的日子里,老姑娘每天坚持着为自己煮好一锅粥,将就着吃一天。或许是老天保佑着老姑娘,抑或是老姑娘年轻身子骨强硬,半个月过去老姑娘的病自然地康复了。
大伙很喜欢心地醇厚、没有脾气的老姑娘。在大伙的心里她就是绣神。很多大娘小媳妇一有空闲就喜欢跟着她学绣花,她也总是很耐心地不厌其烦地教着大家,日复一日的绣花,她的手指上结成了厚厚的老茧,她时不时地坐在太阳底下,抚摸着手指上的老茧感叹着:“老咯。”
四
日月如梭,光阴似箭,老姑娘已经五十多岁了。她的眼睛开始不好使了,穿个针都得好几回,有时候干脆都穿不上。总得请别人帮忙,并且穿针的时候手总是抖个不停,做事情没了原来的利索劲。她已经不是那个“绣神”了,找她的人也就渐渐地淡了。后来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漂亮的嫁妆,被子、枕套都已经早早地被机器绣上了各种精致的图案。那些手工绣品也不被年轻的后生们看好了,老姑娘的手艺渐渐地被人们遗忘了,自然老姑娘也就失业了。
失业后的老姑娘闲时,白天就在村子里东家西家的串门。到了中饭时候帮着老人们烧烧锅,刷刷碗,捡捡菜。只要她干得动的活她都帮着干,农忙的时候大家都去田里干活了,她便在村里东头走到西头的“巡逻”。好在她的腿脚还很利索,脚虽小但是不觉得累,整天总是乐呵呵的。也别说,大家好像也习惯了老姑娘在村里“巡逻”,如果哪天在村里没看到老姑娘的影子,大伙心里就好像丢了一样宝贝,在地里干着活也总是不踏实。如果谁家里实在忙得没人照顾小孩子,只要被老姑娘知道了,准会主动找上门帮人家照看孩子。乡亲们都会留下老姑娘请她吃一顿饭,条件稍微好点的还会给她几个铜钱或者旧的衣服。
那是个收稻子的季节,天气晴朗,风轻日朗。大伙吃完午饭都匆匆地赶到地里收割去了。“这么好的天气赶紧把庄稼收回来,这个时候的稻子,不能淋雨的。”大伙都这么想着,村子里就看不到一个青壮男女,很多人家都是大门紧闭着。少数的家里留有老人看着孩子,老姑娘和往常一样在村子里转悠着。
村东边的老赵头一个人在家看着两个孙子和一个孙女,大孙子六岁,小孙子刚会走路,孙女三岁。吃完午饭没事情做人自然就会犯困,老赵头靠在门框上看着孙子,孙女们在自己家门前玩耍,开始还偶尔的喊几声“喃喃,叮叮,宝娃,不要到前面的河边玩哦。”
“恩,好的。”大孙子宝娃总是很乖巧地回答着。
“秋困如山倒”,看着看着,老赵头的眼皮就抬不起来了。“没事,他们玩得挺高兴不会乱跑的,我就眯一小会。”老赵头实在是困啊,不到一袋烟的功夫就鼾声如雷。
“哥哥,我的手脏了。”喃喃突然不小心摔了一跤,手正好按在了刚才和了水的泥巴小人上。
“走,我们去小河边洗洗吧。叮叮你站在这里别动。”宝娃对着叮叮说的同时,回头看了看正在与周公相会着的老赵头,然后悄悄地带着喃喃往小河边溜去。
“咦,这里有小鱼,真好玩。”喃喃惊奇得像发现新大陆。
“怎样?我捞一个给你。”作为哥哥的宝娃,想在妹妹面前显示一下哥哥的伟大。
两个孩子完全忘了回去,也忘了还有个更小的弟弟。等了很久没看到哥哥姐姐回来的叮叮,终于忍不住好奇,朝着宝娃他们的方向走去。
“扑通。”一声过后,紧接着“哇”的声音还没让他们回过神就消失了。
两个小小的孩子被吓蒙了。不知道哭,也不知道喊,只是傻傻地站着,他们身后的水里只看到弟弟的手在挥舞着。
“扑通”又是一声。老姑娘村东村西的来回已经转了两遍,准备第三遍转过了,到王老太太那里休息一下。刚才王老太太好像找她有事要帮忙。过了老赵头家两步,老姑娘停住了脚步:“刚才还看到老赵头家的三个孙子,这会转回来的时候三个孩子就不见了。地上的泥娃娃还没干,老赵头睡得不省人事似的,不会……”老姑娘心里嘀咕着,没来得及喊醒老赵头,转身往河边跑去。
水只淹没到老姑娘的胸口,但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在水里行走还是很困难。何况还得拼了命地往前走,河底的软淤泥稍不注意,脚下一滑,很可能摔在水里,爬不起来。
“叮叮,叮叮,孩子呀……”老姑娘奋力地在水中划行。
“近了,近了。”老姑娘抹了把汗水安慰着自己。
“孩子呢?孩子呢?”
在老姑娘在抹汗的当口,叮叮落在水面的小手终于沉入了水里。老姑娘拼了最后的力气划到了叮叮的位置。
“叮叮,孩子。”老姑娘一把从水底抓住刚沉下去的小叮叮。
此时老赵头已经被大孙子宝娃从梦里喊了回来,站在河边的他双腿直哆嗦,颤颤巍巍地哭着问:“老,老,老姑娘,孩子,孩子,孩子没事吧?”
“快,快送医院。”老姑娘抱着叮叮已经累得说不出话。
后来,幸好孩子救得及时,才保住了性命。老赵头悔恨地打了自己几个耳光。他为了感谢老姑娘,将秋收后的粮食分了一半给老姑娘。老姑娘笑笑:“老赵头,你拿回去吧,我一个人吃不了多少,你们家六七口人呢,再说孩子们还在长身体,以后你千万要小心看着孩子,他们是我们的命根啊!”老姑娘说什么也没收老赵头送来的粮食。老姑娘腿抽筋的毛病也是那时候落下的。那天救了叮叮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半夜被腿疼醒了,坐在床上揉了一整夜。以后只要下雨前她的腿就会准时地折磨着她,坐立难安。
五
老姑娘的脚很小。村子的小孩子最喜欢围着老姑娘看她的脚了,那个年代的女子,脚必须用长布条紧紧缠住,使脚畸形变小,以为很美观。在缠足时代,大多数妇女大约从四、五岁起便开始裹脚,一直到成年之后,骨骼定型,方能将布带解开;也有终身缠裹,直到老死之日。老姑娘的脚真的很小,小至三寸,也就差不多五六岁孩子的脚一样,而且还有点弓弯,村子里的孩子们没事就喜欢围着她,有时候还会叫她“小脚姑姑”。总是喜欢缠着她,让她把鞋脱了给他们看她的脚,还有调皮的孩子把自己的脚伸过去和她比。每每这个时候,老姑娘就笑眯眯地拍下小调皮的头说:“别看我的脚小,走路可快了,而且还给家里省了很多很多买布做鞋的钱哦。”看着她弓弯的脚,有好奇的孩子会问:“老姑姑,您疼吗?”
“刚开始很疼,疼也得忍着,不过忍着忍着就不疼了。”老姑娘说着就像现宝一样,乐颠颠地往地上一坐,捧起她那金莲笑。在她憨憨的笑容里,在那饱经风霜的脸上仿佛还能看到她年轻的模样,其实她年轻时候真的是个美女。因为家庭是地主成分,所以没有谁家敢上门提亲,有一个和她同年龄的小伙子,当年随着父亲在老姑娘家做过短工,那时候小伙子就偷偷喜欢上了十来岁的老姑娘,因为家庭的悬殊,小伙子只能远远地看着老姑娘。关注着她的一笑一颦。后来,老姑娘家被反了,小伙子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和父母商量着要去老姑娘家提亲,被父母一口否决。
“如果你要去娶老姑娘,你就不是我们的儿子,我们不能和有地主成分的女人沾上边,懂吗?”小伙子最终还是屈服在了父母地劝说威胁之下。后来村里村外的一直没人愿意和地主的后代结亲了。
岁月就这么无情地让一个美丽漂亮的女子,孤单地过了一辈子,人们也忘了她的姓氏,她的名字,渐渐地开始了她的老姑娘之称。起初她还会争辩一下“不可以叫我老姑娘的,我的名字叫“陵梅花”,可是人们还是记不住她的名字只记住了“老姑娘”。时间久了,老姑娘也没了争辩的力气,只要大家这么叫着她就笑笑答应着,老姑娘已经八十耄耋。背已经驼得直不起来。
“奇怪了,怎么好像很长一段时间,没看到老姑娘到村子里串门了?”
“不会是出什么事情了吧?”
“会不会她来了我们没注意?”
“要不生病了?”
“我们什么时候去看看她吧?一个人住在田那边也挺可怜。”人们在忙完了田里的活儿后,三五个坐下来闲谈了。
“她家我还从来没去过呢,上次她干嘛这么拼了命的不让拆那茅草房呀?”王家婶子说道。
“是呀,村里给她盖新房她都不要,就是不让拆,这老太太是不是老年痴呆了啊?”张家媳妇也发言了。
“不知道,这里面肯定有原因。等哪天我奶奶从我大姑姑家回来我问问她,她肯定知道点什么故事。”孙家丫头插了一句。
“是啊,也只有村里的老人们知道了呢。可是年纪大的老人不是被子女接到城里住,就是生病在医院,要不就干脆去了西天。”王家婶子感叹了起来。
“她一个人住在那里真不容易,夏天蚊子多得一抓一把,上次听谁说老姑娘家里爬了一条很大的红蛇。”老赵头的儿子也发言了。
“其实,老姑娘这个人真的挺和善,上次我们家黑妞在村口玩,被刘二家的大黄狗咬了一口,后来孩子哭着回来,我们一看是被狗咬的,问她也不知道是谁家的狗咬她了,这时候老姑娘把老刘家儿子带来了,硬是要他带我们家妞去打预防针。”曹妇女主任拍着大腿说。
“不如我们现在就去她家看看吧,我回去把我家今天中午烧的红烧肉,带点去给她吃。”曹主任接着说。
“等会儿,我也回去一下,上次给奶奶买的衣服小了,正好可以给老姑娘穿了。”孙家丫头也站了起来。
“恩,我记得昨天孩子他爸还买了牛奶呢,也给老姑娘带点去。”
“……”大家纷纷站起来准备回家。
“十分钟后在这里集合。”曹主任说着头也不回地走了。
不到十分钟的功夫,大伙提着,拿着吃的,穿的,拎着喝的一起向老姑娘家走去。村子的尽头,过了一座小桥,再走五里路才能到老姑娘的家。茅草房没有门,只有用一小块一小块木板订成的大木板站着。高个子进家门必须猫着腰。否则一定会碰到头,四周是用土坯堆成的墙,靠在门边的一张小木椅上放着不知道谁家给的三个苹果。一个矮土灶上有两个小瓷饭碗,碗上的花纹图案很是精致漂亮,“好美的碗。”孙家丫头好像发现了新大陆。靠里面的一张单人床上躺着一个人,屋子里没有灯,光线很暗,基本上看不清屋里的东西。因为离电线杆很远,没有办法接电线。又因为她离乡亲们比较远,老姑娘不提装电线的事,大伙也就想不起来给她装电灯了。白天人们都会看到她在村里串门,天一黑她就回家睡觉。黑乎乎的屋子里根本没办法做事情,有时候都是摸着上床,乡亲们只要看到她串门到谁家了都会留她吃个饭。或者送她一些吃的、用的东西,老姑娘便会在心里牢牢记住。下次家里没人带小孩,不用叫她就会准时出现在家门口。或者她会在大家农忙的时候,帮忙捡掉在田里的稻子,麦子。总之,她不会白吃了大伙的饭,白拿了大伙的东西。
“老姑娘,老姑娘……”张家媳轻声唤道。
“老姑娘,老姑娘……”大伙纷纷叫喊着往里走。
“吱吱”竹床摇晃的声音“哪一个呀?”老姑娘有气无力地问道。
“老姑娘你怎么了?你没事吧?”曹妇女主任关切地问。
“没事……就是有点发烧了……人老了,病就来了,不中用了。”老姑娘真的很虚弱,就连说了一句话都不停地在喘。
“好烫!”张家媳妇惊呼。
“快,快,带老姑娘去医院。”
“我不去,我没事,你们都很忙不用管我,很快我就会好的。”老姑娘拒绝着,不肯起床。
“抬。”曹妇女主任一声令下。抬老姑娘腿的,抬老姑娘胳膊的,纷纷动了起来。在送老姑娘去医院的路上大伙沉默了,谁都没有吱声。医生诊断老姑娘的肺出了问题,而且是晚期了。大伙呆住了,她们怎么也不能相信,那么善良的老人怎么就得了这种病了。“医生,你们就救救她吧。我们给你们跪下了,求求你们了。”曹妇女主任哭着求医生。
大伙见曹妇女主任跪在那里,也都跪在了医生面前。医生扶起大伙摇摇头:“对不起大家了,你们还是带着老人回去好好照顾她,让她在剩下不多的日子里过得开心点吧。”医生拒绝了大伙的请求,让大伙带着老姑娘回村子,他们没有回天之力。
“医生,她老人家还能活多久?”老赵头的儿子问。
“照顾得好,可以活个三个月,照顾不好的话也就一个月吧。”
大家无精打采地抬着老姑娘往回走。
“我都说了没事,我会好的,不用来医院,你们非要抬我来医院,你们看看,累着你们了吧?”老姑娘似乎在埋怨着大家。
“老姑娘……”孙家丫头哇的一声哭了,大伙也在偷偷抽泣。
“傻丫头,哭什么呀,你看我现在不是好好的。没事,退了烧我就好了,可以去村里串门了。你们要给我吃的,不许嫌弃我哦。”老姑娘给孙家丫头擦眼泪。
“恩,我不哭,今天我还给你带了一件衣服了,等一下回去你要穿。明天我让妈妈给你炖鸡汤喝,不许像以前一样,好吃的你都不吃。”孙丫头点了点头止住了哭。
“你们都是怎么了啊?张家媳妇我最喜欢听你唱歌了,来段小曲吧。大家都忙着收庄稼,我都好久没听你唱了。”老姑娘拍了拍张家媳妇的手。
“老姑娘,我,我……”张家媳妇实在唱不出口。
“张家媳妇,你就满足了老姑娘的心愿吧。今天不唱,或许你就真的没机会唱给她听了。“孙家丫头悄悄在张家媳妇耳边嘀咕。
“奶奶您听我说,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虽说是,虽说是亲眷又不相认,可他比亲眷还要亲。爹爹和奶奶齐声唤亲人,这里的奥妙我也能猜出几分。他们和爹爹都一样,都有一颗红亮的心……”张家媳妇唱起了老姑娘最爱听的,也喜欢唱的《红灯记》选段。一段小曲唱完,接近幸福村了。
“其实我早就知道我的病了,这也是我很长时候没去村里的原因。大伙事情都很多,我不想把我的病样子给大伙看到,让大伙为我担心。当初我娘最后就是我这病样子,也是这么悄悄地走了。”老姑娘拉着王家婶子、张家媳妇的手喃喃自语。
“你们不要难过,我一个孤老婆子能这样让村里人挂念,我也很自足了。我家里还有一些古董,你们把它们送到市里博物馆吧。我想着应该有点价值,那些都是我曾祖父留下来的。”老姑娘说到这里时情绪有些激动,抓着曹妇女主任的手微微动了一下,眼里丝丝泪光中带着笑。或许是因为她觉得她的存在没有给社会添乱,也将这些古董还给了国家。她也是为她的爷爷辈做了点好事吧!
“你们肯定认为我是个固执的老婆子吧?其实那间屋子是我们老陵家留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财产。是养活了我们老陵家几代人的地方呀。我走后,过了三七,你们就把那间破旧的茅草房拆了吧。”老姑娘终于说出了大伙一直很想知道,她为什么拼命守护着茅草屋的秘密。最后一句话竟然说得是那么地果断,但是她的手却轻轻地颤抖起来。大伙知道老姑娘的心里还是舍不得她的那间茅草屋。那是她们老陵家的根啊!
大伙互相分工,张家大婶照顾几天,孙家丫头照顾几天的,轮流照顾着老姑娘。每天都有着一拨一拨的人去看望老姑娘,老姑娘的精神感觉也是一天比一天好了。三个月后,老姑娘竟然奇迹般地好了起来。不但可以到村里窜门,而且还能张家媳妇一起唱段小曲了。比医生预料的三个月还多了一个月。根本看不出得了癌症。
“我出五十。”张二狗的弟弟张三弟首先叫了起来。
“我三十。”
“我家上次盖房子多了好多砖头,哪天找几个人去搬来吧?”
“对,我家也有多余的砖头。”
大伙高兴地聚一起商量着,准备凑钱给老姑娘在茅草屋旁边给她盖座瓦房了。拉上电,接上水,以后轮流照顾她,给她送吃的……给她一个快乐的晚年,计划总是美好的。时间总是走了不能回头的。在那个万家团聚的中秋夜,老姑娘带着微笑告别了幸福村的人们。走向了父母的怀抱,结束了她八十八岁的孤单之旅。
老人说,那段大伙都以为老姑娘的病好了的日子,其实是一种回光返照。快要死的人,即使病得再严重,哪怕不能吃饭,在最后快要离开人世的时候总是能吃,能喝,俨然就是一个没有病的人。只有他们自己知道那是离活着的日子不多了。
“是啊,那段日子老姑娘总是笑呵呵的,特别爱到村子里找大伙唱小曲。有时候晚上还能听到她唱歌的声音呢。”不知谁突然像听到了老姑娘正在给大伙唱那段她喜爱的《红灯记》。
“那段时间应该是她在幸福村过的这一辈子最开心的时光吧。”大伙都觉得。
“老姑姑,您怎么就这么走了啊!我还没来得及给您买吃的,买新衣服穿了啊!”当年被老姑娘拼了命地从河里拉上来的,老赵头的小孙子叮叮,已经长成了壮小伙。在城里读书,他一直记着他的命是老姑娘给的。老姑娘就是他的亲奶奶。每次放假从城里回来,他都将自己的生活费省下来,给老姑娘买一些镇上没有见过的东西。吃的,穿的。他知道老姑娘为了救他腿患上了关节炎,总是从城里带回来各种各样的药和药膏。
“老姑姑,我还准备等大伙给您盖好了新房。给您买张新床,给您把您家里的桌椅全换了,您怎么就……要不是您那么辛苦的给我绣喜房,我哪能抱得今天的美娇娘……”张二狗的弟弟张三弟不断抽噎起来。全村的男女老少全都低着头哽咽着,他们将老姑娘的茅草屋围得结结实实,整整一天一夜不肯散去。
“大家不能总是这样呀,也得早点让老姑娘入土为安吧。她如果知道大家这样肯定很不开心的,我和大家一样,真的很舍不得老姑娘就这么离开了我们。但是,人死不能复生呀!”最后老村长发话了。
大家终于收拾好了情绪,将准备给她盖房子的钱拿了出来,给她办了一场隆重的葬礼。在她最后的天堂之路没有让她孤单地走。按照村里的习俗,有子女的老人去世后,她的骨灰都是有子女捧着送完最后一程的,因为她是无子女的老人,所以她的骨灰是用椅子,由村里年长者抬着安葬的。她的墓地就是她拼命护着的那个茅草屋。只不过后来大伙在那个茅草屋的外面建了一道围墙,在院墙上刻上了“陵梅花之墓”。村里人还会经常去看她,给她带花,会唱小曲的大姑娘小媳妇,都不忘了唱上一段给老姑娘听。从此不再让她孤单了。大伙春耕秋收时,更是离不开老姑娘。在她身边嬉戏,说笑,告诉她今年的收成是多么的好。谁家又娶了新媳妇,又添丁了……总之村里发生的事情大伙都会说给她听,仿佛她还活在大伙身边。一直让全村人遗憾觉得最对不起老姑娘的事情,就是大伙在她没有生病的时候忽略了她地存在。没有好好照顾她,生病了再去照顾她已为时太晚。那时候大伙都只是在忙着自己的事情,从来没想过村里这个孤单着的老人。大家都说:“在幸福村上空那颗最明亮的星星,就是老姑娘的眼睛,总是在天气晴朗的夜空对着大伙笑。”
老姑娘静静地走完了她的一生,她苦了一辈子,孤单了一辈子,无奈地挣扎着生活了一辈子。没有亲人却是亲人无数,孤单地活着,死了却带了无数颗思念她的心。祝愿老姑娘在天堂的路上不再孤单。
(责任编辑卜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