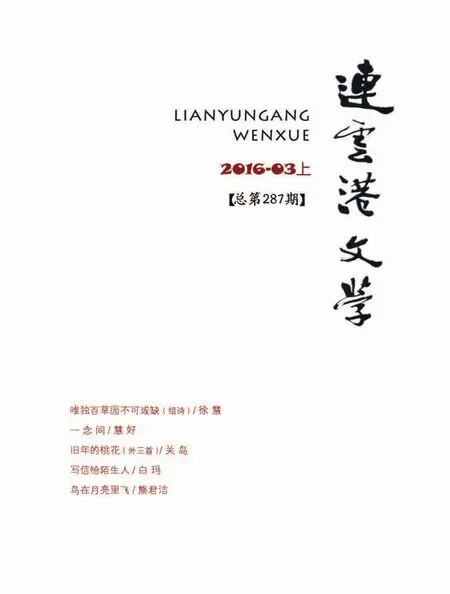在鸿雁飞过的地方
周骏/江苏
在鸿雁飞过的地方
周骏/江苏
天空很蓝,像被水洗过一样。我从车窗向外望去,遥远天空的白云,在湛蓝的天幕上无拘无束的移动,一会儿是驼峰的样子,一会儿是马儿奔腾的形状,变幻无穷,偶尔有几只灰色的鸿雁,掠过天际,往南方的天空飞去,还有一只落单的孤雁,也许受了伤,落在后面……霎时,有一种悲凉的心绪,滞留在我的心头。
罗总,我的一个远房表舅,叼着香烟,双手紧握方向盘,让越野吉普车在环山公路上尽量走得稳当一些,我问表舅,还有多长时间到嘉峪关。他说快了,顶多还有一支烟的功夫。我有些莫名其妙地亢奋起来,因为从今天起,我将面对的是陌生的人群和陌生的环境。也许,表舅猜着了我的心思,说别瞎想了,到了老响这个工地,你只要吃得了苦,吃得了亏,就能混得下去。再说,也就是借个地儿歇歇脚嘛。说话间,到了丁口镇,车子拐了几个弯,到了目的地,是老响承建的镇办公大楼工地。
正是中午,明晃晃的太阳把整个工地照得通透。老响看见了我们的车,连忙奔了过来,见到表舅又是握手,又是递烟,似乎见到了亲爹一般。表舅却沉着脸,说我侄子就交给你了,好好待他。老响眯缝起细眼,上下打量起我说,哎呀,罗总,你看你侄子白面书生,细皮嫩肉的,到我这儿受得起这份苦?表舅说他有这个思想准备,是来挣钱的,挣钱就得吃苦,天经地义!表舅瞄了我一眼,我明白他的意思,赶紧从车子后面取下了铺盖行李。
我注意到,有表舅在,老响自始至终腆着一张笑脸。那带着肉麻的恭维让我反胃,但,表舅走开了,老响对着我的脸却冷冷的,板着脸问我干过什么。我答我干过保险,送过快递,在北京城里还站过柜台。老响的脸更冷了:在我这儿,你这些活计,没哪样派得上用场!我听罗总说,你是锦州人,我听说锦州那儿有这么一句话,瞎猫常常抓个死老鼠,你就在我这儿逮逮死老鼠吧,技术活轮不上你,就做做小工,水泥拌黄沙,石灰拌酱纸,每天60块工钱,小子,想干不?我一秒的犹豫都没有,立刻答应了下来。
晌午开饭,五十多位工友围拢在一起,有的站着,有的蹲着,有的坐在水泥梁架上。饭是高粱掺米饭,菜是白菜煮粉丝,还有一大锅海带汤。煮饭的女人,工友们都叫她巧珍嫂,给她打下手的叫素琴,稍微年轻一些。巧珍嫂给我打菜时,看了我几眼。我憋不住了,也抬起眼皮打量她。我看到一张红扑扑的脸,一张女人味十足的脸。没有涂眼影,没有修睫毛,没有施粉,也没有擦唇膏,但那天生红艳艳的嘴唇,一开一合间,那中年女人的俏丽和诱惑无处不在。此时我听到了自己内心深处怦然心动的声音。就在我心猿意马时,她的问话传进了我的耳膜:是新来的吧?瞧你像个文化人,咋来这受这份罪?她把“罪”字咬的特别重,生怕我听不见似的。我选择了沉默。她又说晌午将就点,晚饭有红烧肉,管够。说着,她扭动着丰满又好看的腰身离开了。她一走开,素琴凑了过来,问我贵姓,问我何地人氏,问我为啥来这儿打工,问了一大堆。我一一作答。临了,素琴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说邹老弟在这儿好好待着吧,别人不打紧,那个老响,还有巧珍你可得提防着点。我向素琴投去探询的目光,她却一蹦一跳走开了。
做小工,确实没啥技术含量。凌师傅干这活好几年了,把水泥拌黄沙的比例告诉我后,我就照葫芦画瓢干了起来。到了收工的时候,就有些腰酸背疼了。凌师傅对我说,时间久了自然会习惯的,晚上开饭,果然是红烧肉,外加炒茄子。巧珍嫂掌着一把铜勺给大伙儿打肉,几乎每个人的碗里都有六七块红烧肉。轮到我时,巧珍嫂一勺下去,准备搁到我碗里了。老响走了过来,黑沉着脸把铜勺挡了回去,说做小工的三块肉够了。巧珍嫂说凭啥只给三块肉呀。老响不答话,从她手里抢过铜勺,把铜勺里的红烧肉翻进钢盆里,又抖抖索索弄了三块肥肉往我碗里一砸,吃吧,小子,别心大了。这时候,我心里的委屈冒了出来,虽有委屈但我忍住了想哭的念头,但我没有想到的是,巧珍嫂却圆睁双目,那双眼似乎要喷出火来一样的——从老响手上抢过铜勺,一勺下去又捞起好几块红烧肉搁进我的碗里。老响骂起了娘,咋的,不把老子放进眼里!巧珍嫂也不相让,说不带这么欺侮人的,我的一份给小邹吃,你总没屁放了吧。老响恼了,怎么的,你看上这小白脸了,你还要脸不?巧珍嫂答我看上他也不天打,美女爱俊男,佳人爱才子,有错么,没错!见没有落场水,老响只得走开了。
而我肚子里的委屈,却悄悄化成泪水,从眼眶里流了出来。我相信,巧珍嫂还有周围的工友,一定看到了我晶莹的泪光。
这晚,我彻夜难眠。
翌日清晨,还没有到七点,我起了床,走出工棚,往前走了一百多米,一条清澈的小河挡住了我的去路。我索性在荒草遍地的河畔坐了下来。眼下正是初冬时节,河畔的杨树经不住寒风的拂动,片片枯叶飘落下来,有的落到我的头顶,我不经意地用手拂去,用双眼凝望遥远的天空。天空很蓝,像被这清澈的小河洗过一样。有几只鸿雁从我的头顶飞过,我心底的忧伤又悄悄升到心头,情不自禁低声唱起了《鸿雁》:鸿雁,天空上,对对排成行。江水长,秋草黄,草原上琴声忧伤。鸿雁,向南方,飞过芦苇荡,天苍茫,雁何往,心中是北方家乡。
唱了一遍不过瘾,我又唱了第二遍,直到我身后响起脚步声,我才刹住了车。是巧珍嫂拎着一木桶的衣服来河边洗衣服了。她在河畔一块青石上,一边用棒槌打衣服,一边侧过俊俏的脸蛋对我说,小邹你唱的真好听,你肯定去过草原,不然你唱不出那个味道。小邹,你再唱一遍让嫂子听听,行不?我念着她的好,便又唱了一遍。唱完了,她低声叹了口气,说草原真好,我却回不去了。从这句话中,我隐隐觉得这首歌可能触到了潜藏在她内心里的伤痛。我没追问,她却三言两语说起她的身世,她是内蒙古人,中年丧夫,也没落下一儿半女,一夜之间生活无着,跟着表姐来京讨生活,后来认识了老响,就跟着建筑队“南征北战”。看到她洗好了自己的衣服,又从木桶里捞起几件男人的衣裤,那件深灰色夹克上装,我一望就明白是老响昨天穿的。由此,我心里多多少少揣测到她和老响之间,恐怕有那么一层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还没有容我往深处想,她又问起我的状况。我告诉她由于性格的缘由,我总是和老板处不来,最近就是送错了两份快递,被老板吼了几声,便炒了老板的“鱿鱼”。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只能到这儿做小工了。她叹了几口气,说委屈你了。她还问我成家了没,我说没有,我还央她帮我介绍介绍。她说外面的姑娘我都失去了联系,建筑队吧倒有两个,素琴是个离过婚的女人,年龄倒和你相配,另外一个就是卫生护理员桂艳,人样子一般,心气可高着呐,一般的小伙子不入她的法眼。我默默听完,知道在这儿找女朋友没戏了。
巧珍嫂还问起我的初恋,这触动了我的隐痛。好不容易痊愈的伤口,我不想再去揭开。没有提,只是问她,巧珍嫂,你有没有看过《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这部电影。她眼眶内的眼珠子转动了老半天,才说我没有看过,真的没看过。我笑了一笑(是我到了丁口镇后第一次笑),说那也无所谓,这部电影不过是说,许多男人追一个特别可爱的女人,结果只有一个男人追到了,而这个幸福的男人绝对不是我,就这么简单,巧珍嫂你懂了吗。巧珍嫂朗声笑了起来,那笑声真好听,好像阳光把一粒粒闪光的珍珠落到了河床里。
我想,她应该懂了。
……
上午我拌泥沙时,不小心碰到了铅桶上沿的铁铅丝。我右手的食指冒起了血泡,正想找一块旧布包扎伤口,被洗菜回来的素琴看到了。她说,这铁铅丝已经锈了,不消毒的话要破伤风的,那就小事变大事了。说着,她把菜篮子搁在地上,一手拉着我直奔护理室。进去后,只见叫桂艳的卫生护理员,正斜靠在木椅上,两个耳朵插着耳机,悠悠闲闲听随身听播放的歌曲呐。这素琴是个爽快人,上前就拔去桂艳的耳机,说你就听听听,听死你罢,快,给伤员干活。桂艳脸上涌起恼意,很不情愿地站起来对我说,你这个新来的,怎么这么不小心,一来工地就惹事。我无可奈何苦笑一下,算是对她的回答。素琴说别磨叽了,你快动手啊,桂艳动起了手,挤血、擦伤、上药、扎纱布,倒也麻利。看着她做完这一切,我向她报以感激的一笑,也对素琴报以一笑,算做感谢吧。
素琴转身走出了屋。我正欲转身,却见老响走了进来。他是来讨安眠药的,看到我右手食指上的纱布,他皱起了眉头,说今天又少了一个干活的,桂艳说他最少要休息三天。老响说,行啊,小子,你还是回北京休息吧,我这儿不养闲人。我说,老板,我闲着也是闲着,我能干活。老响端详我半天才说,这还像个人样。见老响的背影渐渐远去,桂艳用力向地上唾了一口,狠狠地说,比资本家还资本家。
我嘴上不说,心想:这话说到点子上了。
由于表舅关照过,老响专门腾出一间工棚让我住宿。因为我晚上要看书,还有写作的习惯,1990年代末期,我已经很少写小说了,转而写些触景生情的散文。我的双肩包里除了世界名著,就是一些国内著名的散文月刊(经常刊发我的散文)。白天手指虽然受了伤,我还是忍住伤痛赶写一篇构思已久的文章。大概夜里九点左右,门被轻轻敲响,我起身开门,见是巧珍嫂到了,忙迎进来。坐下后。她说,你受了伤,我来看看你,还疼不?我说,好些了,让你担心了,谢啦。说着说着,她把目光移向桌上的稿纸,拿过去看,轻声念起了标题彼岸的月亮花。一会儿,这篇两千字的散文她就看完了。她低着头沉思了一会,才说昨天一见面我就看出你是文化人,没想到你还是散文作家。我自个儿没啥文化,但我喜欢文化人,我那死鬼没权没钱,可他是一个中学的老师,我才嫁给了他。说话间,她的眼圈发了红,还有点点的泪光,在她眼里闪烁,我一时怔在那儿,不知道应该怎样劝慰她。
好长一段时间的沉默,彼此几乎听得见对方的心跳。
还是她打破了僵局,她说,现在还不算太晚,我们到镇上散步吧。我欣然从命,走出建筑工地,我俩到了镇上,大多数的商铺关了门,只有镇上的一家公园还闪着点点灯光。夜色静谧之中,我俩走进了公园,走得累了乏了就在公园深处靠一颗老槐树下歇息。一会儿,我俩抬头看看月亮;一会儿我俩仰首数起星星;一会儿我们又唠嗑起来,渐渐地说了一些掏心窝子的话……渐渐地,心与心的距离拉近了,身体与身体的距离也拉近了。忽然,她叫我转过身去,待我站定,她忽然用双臂从背后环抱住我,霎时我感受到一个女人浓重的柔情包围了我,我同时嗅到了顺风而来的女人的甜美的体香。我不敢有所动作,像一个木偶听她摆布。忽然她又扳转我的身体,紧紧地将我拥抱,在她饱满柔软的乳房触到我之后,她把嘴凑到我的嘴唇,与我深深相吻。
我俩就这样相拥相吻。尽管她是我的巧珍嫂,我还是被她吸住了。
尽管我心中滋生了一点点罪恶感,但我抗拒不了这样的诱惑。
理智,让我与她仅此而已。
夜深了。回到建筑工地,远远地见到一明一灭的烟头。走进一看,是老响站在寒风中等人。他劈头问她:你们去哪儿了?
在融融的月色中,我依稀看到巧珍嫂镇定而坦然的面容。她对着老响投去轻蔑的一瞥,然后才说我和小邹到镇上溜达溜达。怎么啦,碍到你啦。
老响怔了一怔,才说,你有种,你再钻进我的被窝,我打断你的双腿。
巧珍嫂从容不迫:当初,是你没心没肺,把我拉进你的被窝,你说,跟了你让我一辈子幸福。可直到今天,我也不是一个幸福的女人,你骂过我,打过我,你给过我幸福吗?我跟你说,我不是一个任人摆布的女人,假若这个世界还有真爱,我会去寻找的。
老响愣住了,瞥了半天也没有吐出一个字来。
这一晚,我又是彻夜难以入眠。
在我干了两个月之后,我大哥给我来了一封加急电报,称父亲病危让我尽快返回锦州。我向老响请了一个星期的假,急急赶回了家乡。回锦州的当天,父亲与我见了一面,便撒手归西。办完了丧事,我几乎是心灰意冷。回到了丁口镇,我只知道闷头干活,和谁都不说话。老响只是拍拍我的肩膀,说了句人死不能复生,别太难过了。凌师傅特意带我到镇上一家小酒馆,给我解愁解闷。素琴偷偷地塞给我三个熟鸡蛋,还对我说,路长着呢,好好保重身体。桂艳贴着心把随身听让我听,我谢绝了她的好意。巧珍嫂看我整天以泪洗面,劝了我好几次,并对我说,做儿女的终会有一天失去父母这两颗参天大树。一旦失去父母,我们就要有勇气面对人生及今后的风霜。我没想到,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女人能够说出这样有哲理的话,真不简单。我向她投去赞许的目光,她却怯怯地说我是从书上看来的,这不是我的话。我问是哪本书。她答我在京城打工那会买过周国平的一本散文集,这些话是周国平说的。我于是释然了。
就在我渐渐平复的日子里,一件必然会发生的事情在我的生活里发生了。
老响去京城采购原材料了。他走的当晚,我靠在床上看书,大约三个小时之后,我看了一下手表,时针已指向晚间11时,那熟悉的敲门声又悄然响起。我按捺住心中的欣喜,赶紧下地开门。门开了,巧珍嫂穿着一件从来没有见她穿过的紧身红棉袄,胸前的双乳高高耸起,就这样向我骄傲展示着双乳的曲线。我赶紧关了门,把她——我已经爱上的女人,比我大十岁的女人,紧紧地拥在怀里。在这样的时刻,说任何一句话,哪怕说一个字也是多余的。我俩先是接吻,然后脱了衣服,钻进温暖的被窝相互摸着彼此的身体。激情在我的体内燃烧,也在她的体内燃烧……爱像一把火,点燃了我们的心灵,也同时点燃了我们的身体。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我俩却不感到有一丝疲惫。
……稍稍平静之后,她问我:你会娶我吗?
我连着说了三遍:我娶你。我娶你。我娶你。
然后,我又说:巧珍,你是我在这个世上遇到的最好的女人。
然后,她贴着我的耳根说:我把BP机号码留给你,不管你身处何方,你都能找到我。
半年之后,我离开了丁口镇,去了广州打工挣钱。但,我和她音讯不断。
次年三月,我到北京郊外另一处工地找到了巧珍,当天我俩登上了长城,眼下正是万物苏醒的春季,成群的鸿雁从南方飞了回来。
天空很蓝,像被江水洗过一样。她又让我唱《鸿雁》。不过,我这一次只唱了下半段:鸿雁,北归还。带上我的思念。歌声远,琴声颤,草原上春意暖……听着,听着,她的泪流了下来,我的热泪也夺眶而出。
站在长城上,我从心里对她喊了出来:我爱你!巧珍!
(责任编辑解永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