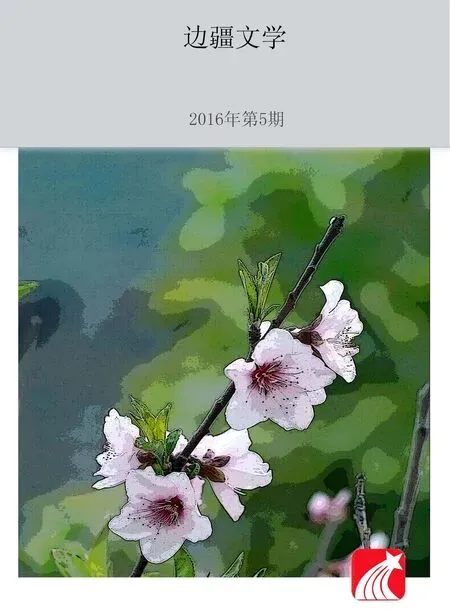民族、命运以及女性
——和晓梅文学作品研讨会
◎宋家宏等
民族、命运以及女性
——和晓梅文学作品研讨会
◎宋家宏等
主持人语:和晓梅是云南近年来创作丰厚的一位小说家,很有特色,评论对她的关注不够。“云大评刊”论坛组织了一期讨论,年轻的批评写作者们对她的小说直言不讳地说出了他们的看法,这对推动读者了解和晓梅的创作,是有意义的。本期“新锐批评”转发了“云大评刊”的讨论,并配以几篇短论,相对深入地解读了和晓梅的小说。稍有不足的是对和晓梅的长篇小说涉及不够,然而,那是和晓梅很重要的作品。由此,也可以看出,在今天,要读者认真地读一部长篇小说有多难!作家写长篇小说实在是一件需要谨慎对待的事。(宋家宏)
主持人:宋家宏(云南大学教授、云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讨论者:云南高校教师及研究生十余人
记录整理:唐诗奇
时 间:2016年6月13日
地 点:云南大学文津楼云南文学研究所216室
主持人宋家宏:各位朋友,大家好!“云大评刊”本期(第三十一期)讨论的是云南作家和晓梅的小说。她是云南作家中这几年来小说创作成就很突出的一位,而且她的创作在不长的时间里发生了很明显的变化,这一点大家读她的作品会有感受,我这里不多说了。她居住在丽江,离中心城市有点距离,但她的小说与同类型的作家很不相同,我也不想多做评述,还是请各位自己判断。这一期我们准备更多地采用空中连线的方式进行,整理的时候仍然保持“云大评刊”的一贯风格。请传稿来的各位同仁仍以片断的方式进行。同时,完整的附稿也是非常需要的。
一、印象:和晓梅作品的总体观感
主持人宋家宏:是不是先说说大家对和晓梅小说的总体感受?
陈方(云大2013级研究生):和晓梅作为一名纳西族女作家,其创作的立足点无疑多来自于民族和女性,民族和家族是其写作的重点,以独特民族的视角对女性命运和生命的表达。但和晓梅的眼光并没有局限于少数民族题材,她的思考也上升到了对命运和生命过程的关照。
郭鹏群(昆明学院副教授):和晓梅的小说有一种神奇的魅力,可以抵达人的心灵深处。……她的小说,是以现代人的眼光,审视古老的纳西族文化,并在对人性的挖掘中直击人生的无力感。
唐诗奇(云大2016级研究生):从开始猎奇式的窥探,到沉醉在这个浪漫的美梦中,再到忽然从梦中惊醒,透出生命的苍凉。和晓梅拥有这样的能力,让人一步步沦陷在喃喃的纳西古语之中。
徐睿(山西太原学院教师):就阅读感受而言,和晓梅的小说无疑是非常好看的。这种“好看”体现在由措辞精美、叙事完整和引人入胜的情节所构成的可读性,体现在她用斑斓的色彩词汇为读者绘制的文字画卷呈现出的视觉美,也体现在她通过对多种意象的灵活运用、叙事视角的娴熟转换和贯穿作品始终的巫性灵气所展现出的艺术性……
轶名:在读和晓梅的小说时,我竟会眩晕,就像是跌落到另一个时空的感觉。和晓梅小说有意拉开与现实的距离,传奇色彩较浓,纳西文化增添了作品的神秘色彩,放蛊、殉情、念咒、祭祀等这些远离现代文明的文化符号,增添了作品的传奇性与神秘性,但和晓梅无意以猎奇的心态去描绘和展现,让她动容的是这些仪式的背后的心,她所关注的是隐藏在仪式背后的人物命运。
孔莲莲(文学博士、曲靖师院教师):和晓梅的作品以她漫衍而直感的语言,神秘主义的文化呈现,以及对女性命运的特殊热情,再次让我读到了“巫”的气息。确实,以上特征深受 “文坛三巫”(林白,陈染,海男)的女性主义作家的影响。但是,除了以上的特征之外,作为一位纳西族的后裔,她以血浓于水的深情表达着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和种族的依恋、崇拜、审视和批判。
张旭(2015级研究生):她的文字背后蛰伏着她的生命意识,这种生命意识是她作为一个纳西族对自己文化历史的一种自觉地反思,这种生命意识包含了她对本民族女性的理解和同情,她借此作为出发点,建立自己写作的王国。
朱彩梅(现代文学博士、云南师大教师):其作品致力于当地少数民族题材的书写,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浓郁的民族风情。在写作中,她有意识地去尝试、探索民族性与现代性、本土性与世界性的融合,但目前,汉语表达的艰难和超越自我局限审视民族文化的困难,如两块巨石,双双横亘在她写作的道路上。
陈林(苏州大学文学博士):从爱神康美久蜜金到英雄连长,再到当下的“成功人士”,和晓梅的小说超越性别、民族、地域,她的创作把独特的个人经验融合到历史意识中,写出了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人的生存境况与文化心理的变化。只有把她的小说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晓梅把握世界、书写世界的独特方式,才能看到她为我们勾画出的不同文化形态下鲜活的心灵的历史,这些真实的心灵世界构成了历史真实不可或缺的侧影。正是从这个角度,我认为和晓梅是一位颇有抱负的写作者。
二、女性视角下的生命观照
主持人宋家宏:和晓梅是一位女作家,我们讨论一位女作家时往往会从她的性别意识入手 ,这其实并不公平,但女作家的性别意识又是与生俱来的,它不自觉地呈现在作品中,读者很容易就看到了这种女性意识,和晓梅的作品是不是这样的?
徐睿(山西太原学院教师):纵观和晓梅的作品,我们不难从中读出其对女性命运和精神世界的持续关注。身为女性的和晓梅基于自身性别体验的女性言说,细腻的情感表达和纳西族人、东巴后人、知识分子等的多重身份,均使她的作品增添了更具感染力和说服力的别样魅力。她既是民族历史的传承者又是亲历者,既是作品中受难的女性本身又能站在知识分子的高度冷静思索女性的过去与未来、存在和价值。
陈思颖(云大2014级研究生):和晓梅在多篇小说中展现了对女性的关注,尤其是纳西族女性的书写展示了作为一个女性作家所具有的敏锐和细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作者和晓梅就是一个女性主义的话语者,她只是运用独特的女性生命体验诗意的表现纳西族美丽女性的苦难、爱恨以及美好的人性。
陈琴(云大2014级研究生):在她的笔下,纳西女性特别的美妙常常让人过目难忘,与美相呼应的是纳西女人感情的纯真高洁,她们为了爱情常常是义无反顾,无视世俗的任何障碍,可以抛弃财产、名誉、甚至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和晓梅在一个个委婉动人的故事里,有着人们期盼而现实生活中难以寻觅的肝胆热血侠骨柔肠,女性的肉体与心灵之美被推到了极致。
唐诗奇(云大2016级研究生):正如陈琴所说的,这样的母题抛开纳西族“玉龙第三国”的美丽传说,很容易找到相类似的故事。不同的是,和晓梅对女性的关注不仅仅限于对爱情和自由的追求,更在于对自我命运的把握和反思。同时,和晓梅尖锐地指出女性在情感上的弊病和悲哀,过于盲目的爱情让她们陷入了极端的痛苦之中,一定程度上注定了她们的悲剧命运。
刘敏(云大2015级研究生):“大部分女人,不过是活在一张自结的网中,活得平淡,寂寞而痛苦。”这也许是大多数纳西女人的命运写照。……然而和晓梅并没有把女性的悲剧一味偏执的归结到男性,而是引导我们走向了对民族文化的反思,对生命存在价值的追问。
徐睿(太原学院教师):在和晓梅所构建的女性世界里,很少出现充满阳刚之气、果敢决绝的男子汉形象,就连外貌都大多是矮小、苍白、孱弱的。男女之间的情感关系主要表现为女性的牺牲和男性的索取与不作为,从而使得牺牲和付出,成为和晓梅笔下女人可怜、可惜、可叹的爱情模样。……与传统爱情故事中,落难的女性总是由生活经验丰富、有勇有谋的男性拯救不同,和晓梅笔下男性形象的弱化和男权神话的消解注定女性从困境的解脱主要依靠以下两种方式来实现,即:女性群体的互助和女性的自我救赎。
轶名:是的,与鲜活的女性形象相比较,她对男性形象的塑造则太漫不经心了,甚至有些敷衍了事,类型化、模式化,基本处于失言、甚至失真状态。《女人是“蜜”》是一曲关于女性命运的哀婉之歌,对女性,作者倾注了一腔热血,对男性,则横眉冷对,但过度的将两性关系对立起来,是否会导致女性情感的虚空感?无所依托的虚空。
徐睿(太原学院教师):源于有意识地想要在男权文化的天空下做一个翻转的想法,使得她作品中这种显而易见的女性写作和女性关照,不光是一种“我、我的身体、我的自我”式本能表达,更是一种想要以一个“民族代言人”的角色,为她们发声言说的自觉性女性写作。
三、纳西文化的代言人,抑或反思者?
主持人宋家宏:和晓梅还是一个纳西族作家,云南有的少数民族作家有的在刻意强调,有的又在有意识地回避自己的民族身份,这有很复杂的原因,和晓梅与他们不同,她不回避,但也不刻意地强调。说和晓梅是一位纳西族女作家,不仅仅是说明她的身份,其实更重要的是她的作品里有很明显的民族意识,大家在读她的作品时应该明显地感觉到这一点。
张旭(云大2015级研究生):作为纳西族的作家,和晓梅的小说里无法忽略的是纳西东巴文化的影子。作家的民族意识,对于纳西文化的自觉认同,通过地域、语言、民族文化、风俗习惯作为媒介完成。……和晓梅对于自己本民族的文化一方面是赞赏,以至于在小说中反复的描绘纳西族的风俗文化,语言习惯;另一方面,这些文化认同心理背后又隐含着作家对本民族价值以及出路的思考。
朱彩梅(现代文学博士、云南师范大学教师):
其民族思维、信仰,在小说中常化为“我说是这样就是这样”的一锤定音、不容质疑的肯定语调,很像《圣经》的“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如对殉情者的描写,与彝族《阿诗玛》、白族《蝴蝶泉的传说》、傣族《召树屯》及汉文化中流传的《梁祝》相比,其殉情主题作品淡化了绝望、哀伤、凄美的意味,在《情人跳》中,她的叙述语调坚定不移,很好地传达出相爱而不能自由结合的纳西族恋人对待殉情那种近乎宗教信仰般的虔诚、执着,在他们的意识深处,殉情是超越生命、到达另一片天地延续幸福生活的美好寄托与理想。此种作家思维、信仰与作品语调、内容的呼应、和谐,颇为珍贵。
陈思颖(云大2014级研究生):她善于挖掘本民族生活题材的特点,将地方色彩和浓郁的民族特色串联成神奇的传奇故事。没有将写作的目的指向对旧时的封建落后、迷信思想的谴责,而是将自己独有的民族文化注满新鲜血液让人们重新感受纳西族文化的生命气息。和晓梅所写的纳西族文化除了增加小说的传奇色彩之外,更重要的是对蒙昧与文明共存的纳西文化的审视。
马丹(昭通学院教师):作为一个有着女性意识和民族意识的作家,和晓梅擅长以民族的视角思考女性的命运,她的叙述安静、绵密、低沉,写尽了女性一生命运的沉沉浮浮。和晓梅有意无意的和现实世界保持着疏离感,她所注意的是那个已在尘埃中逝去的世界,她领着读者掀起过往的一角,像个好奇的孩子,打量着已被尘封的过去,以独特的叙述方式拂去历史的尘埃,复活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重述那些过往生命中的故事。
陈林(苏州大学文学博士):“玉龙第三国”所代表的超历史范畴暗示了存在不可改变的事物,它与我们的有限性和脆弱性达成象征性的妥协。尽管“情死”文化包含着反抗现存秩序的因素,但更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退缩,它回避、消解了社会危机。
陈琴(云大2014级研究生):对情死的态度值得斟酌。情死并不是因为对生命态度的随意性,而是对一种极端文化的反抗。但在文中,情死成了纳西族的一种传统、一种习俗、一种规矩,凡是不能在一起的就得死,这种带有虚幻性、自欺性、附带盲目的奴性的行为,是必须指出来的。
王瑞(云大2014级研究生):几乎每一位民族作家都会婉曲地表达对民族传统、文化记忆在现代文明发展浪潮中流散与消失的忧虑与警惕。阿来、霍达、晓雪等作家们都在作品中流露出主流文化冲击下本土文化边缘化的危机感。和晓梅也不例外,对文化全面商业化的疑虑与忧思、对跨国文化产业对本土现实包装及生产的反感、对全球化所带来的巨大的失落与错置的创伤体验等诸多情绪的认知与记录,使和晓梅的作品逐渐显现出了一种挽歌情调。全球化的时代,人们无可避免地面临着“史实性的消退,以及我们以某种积极的方式来体验历史的可能性的消退”。和晓梅以她优美婉曲的文字试图还原逐渐消逝的记忆,在不断城市化、全球化的社会和文化空间中寻找文化之根。
马丹(昭通学院教师):目前,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关注,有重文化性轻文学性的倾向,从民族文化的角度切入较多,主要阐释作品所呈现的文化特质,这本是无可厚非的,文化的独特性是少数民族文学的亮点,但文化与文学的转变机制是非常复杂的,过于强调文化性,少数民族文学将沦为文化研究的注脚,而对表现手法,叙事方法等文学手法加以关注,能瞥到文化对文学的渗透不是流于表面的磅礴大雨,而是润物细雨,看似无影,却无处不在。
郭鹏群(昆明学院副教授):建议作者多阅读少数民族历史,特别是土司制度、汉族统治、国共政治、民族关系等,尽快的扩大自己的民族视野与社会容量。
四、对具体作品的讨论
主持人宋家宏:我们还是从具体作品的分析评价,她的哪篇作品给你印象最深?也可以说说那篇作品的问题所在。
陈林(苏州大学文学博士):和晓梅二十出头发表处女作《深深古井巷》颇为令人惊讶,这让人联想到现当代文学史上那些才华横溢的年青作家。《深深古井巷》是和晓梅最出色的作品之一,这部小说在她的整个创作中占据比较重要的地位,它已触及和晓梅小说艺术的“内核”及诸多相关问题,之后的作品多为它的延伸和扩展。从现当代文学史的角度看,这部小说可置于张爱玲的《金锁记》、陆文夫的《小巷深处》、苏童的《妻妾成群》等作品系列中加以考察。放到这些名篇佳作之中,《深深古井巷》依然有它的夺目之处。
孔莲莲(文学博士、曲靖师院教师):说到这个作品,让我想起了曹禺的具有强烈的现代启蒙精神话剧《雷雨》:一个雷雨一样性格的女人以及由此产生的封建家庭悲剧。和晓梅的这个作品则是通过一个汉族女人阴鸷的性格完成对纳西家族传统文化的破坏。小说每个场景的设置都比较精心细腻,随着叙述节奏徐徐展开,作者把我们带到独特的纳西族家族文化中来,这里有专制的家长制,也有粗暴蛮横的男权文化,还有着微妙纠结的民族矛盾。叙述者经常跳出故事的叙述,以一种身处世外的理性眼光,既写出了对本民族的爱和同情,也写出了对本民族的批判和沉痛。
王瑞(云大2014级研究生):小说《有牌出错》是和晓梅作品中我最喜欢的一部,作品中塑造的女主人公“我的奶奶”也是我最喜爱的人物。“奶奶”聪明过人、有着飒爽英姿,讲江湖义气的男子风范,她的一生可谓传奇,与《红高粱》里“我奶奶”似有几分相似。她所追求的并非只是自由自主的爱情,她真正在意的是要拥有能够自我掌控的人生,一如她始终能够掌控的赌局。在这篇小说里和晓梅回答了女性的生命价值——自主、自由。
孔莲莲(文学博士、曲靖师院教师):《蛊》这个作品在我看来,是最有想象力和异域风情的小说。刚一开始读,以为是武侠小说,读到最后,发现竟然是一个情感小说。作者比较聪明的将纳西族人的历史、神灵以及女人的“情死”等民族风情带入故事。南方的古丝绸之路,丽江古城,马帮;两位外形、性格和功夫了得,却不堪情蛊的大侠;一个体弱貌美,情泪点点,对爱情至死不渝的纳西族姑娘:以上地域、时代和人物的设置,即使没有多少思想性,也足以吸引读者的眼球。
轶名:我倒觉得《蛊》过度的求奇求异了,以武侠的形式来讲述这个故事实在不是一个明智之举,过于奇异的故事反而会伤害到作品的内质,读者会更关注表层的故事形式,难以沉静下来体察人物的内心。
陈方(云大2013级研究生):《未完成的成丁礼》也非常有意思。作者通过将泽措与威廉这一个人不同时间的不同身份并置在一起,将繁华的北京和质朴的泸沽湖畔并置,将现代性与民族性并置,产生出巨大的差别,都市的争名逐利和古老朴实家族的爱的滋养,以表明泽措成长的代价。成长不仅仅只有温情,还有撕裂。而缓解疼痛的方式,则是遗忘。
陈林(苏州大学文学博士):革命的枪声在《连长的耳朵》里响起。连长不得不饮下自己枪管里的最后一颗子弹,即便如此,他也摆脱不了遭受怀疑、难证清白的困境。最大的荒谬莫过于,连长不仅丧失了听力,还丧失了与战争相关的某些重要记忆。没有记忆意味着时间性的消失。历史的真相无人知晓,战后的世界竟是一片意义荒芜的不毛之地。连长变成“完全没有身份的人”,除了战争遗留下的疼痛,没有什么能够证明他的存在。这让人想到余华《一九八六年》里不断割裂自己身体的历史教师。
马丹(昭通学院教师):在技巧的使用方面,和晓梅已经很熟稔,但就意义的深度开掘,她还有一段路要走。《宾玛拉焚烧的心》是她对自己创作的一次突破,叙事的手法与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十分相似,将两部小说进行比照,便可发现和晓梅在文化内涵的深度思考和呈现方面的欠缺。
郭鹏群(昆明学院副教授):她的长篇小说《宾玛拉焚烧的心》,已经显示了较为深厚的艺术功底,颇有前途。但社会容量不够,思想厚度不足,与《尘埃落定》等相比差距较大,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朱彩梅(现代文学博士、云南师范大学教师):我认为《宾玛拉焚烧的心》有故事,有传奇,而缺乏形象生动的人物,缺乏直面存在的追问。她浅表化的叙事展现了各民族的习俗、仪式,但描写偏向于外部生存环境,没有向内挖掘,很少深入到人与人之间的道德伦理冲突,未能触及此时此地、此情此景中人物内心深处的挣扎和精神疑难,是浮光掠影式的。……宾玛拉家族、威廉都是作者生命的表达形式,但是,比之沈从文、张承志、阿来创作少数民族文学的深入、深刻,和晓梅小说缺乏深厚的历史感,缺乏雄阔的生命气象,缺乏从某个高度去发现、挖掘自己民族传统中内在因素的意识、视野和思想能力。
赵靖宏(德宏师专教师):相比于诸如《宾玛拉焚烧的心》这类小说,《青昌街纪事》显然看不到“纳西”的影子,没有民族元素,更像是在探讨人的成长和爱的关系,探索人存在的意义。
陈林(苏州大学文学博士):小说《青昌街纪事》没有给出明确的故事时间,历史叙事比较隐晦、暧昧,不过从细节中依然可以判断,小说以一条街道里的纷繁乱象,管窥的是“文革”至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历史。在文学的历史叙述中,这段时间一直是叙事的重要内容之一,“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知青文学”、“改革文学”的叙述焦点均在于此。放到这样的文学史系列中,这部小说显然有些另类。那些暗无天日的杀戮背后的意识形态色彩被淡化了,暴力仿佛只是一代又一代昌青街青年的力比多宣泄,小说仅仅在某些细节处提示我们与当时的红卫兵武斗和“革命”联系起来。我们知道,那些无休止的令人发指的杀戮实际上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年青人的内在冲动而忽略了悲剧的社会性。它与墙上频繁更换的标语密切相关。这些标语改变着人们的命运,人物的活动也因此是历史化的。从“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到“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分子”的标语替换,提示了中国历史从革命向后革命时代转移。昌青街的青年在社会转型中走出他们的故乡,和晓梅的小说也穿越历史回到当下,然而,我们对历史的反思远未完成,诸多问题依旧悬而未决。
孔莲莲(文学博士、曲靖师院教师):这个作品(《青昌街纪事》)带着少有的理性批判精神,只是,她对昌青街的故事更多的是一种“现象”的描述,而缺少更深层的根源追索。
五、得与失:谈谈和晓梅的艺术创作
主持人宋家宏:大家多从思想意识这方面说了和晓梅的小说,能不能更多地从艺术这个角度说一说呢?包括她的小说艺术上的不足。
陈思颖(云大2014级研究生):和晓梅的小说注重叙事技巧的运用,作者擅长在小说中进行多条线索,多故事的穿插,不断打断读者的阅读,最后出其不意地将多个故事统一归为一条线索,形成一个完整的故事。这种叙事扩张了小说的空间,使小说跨越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框架束缚。
马丹(昭通学院教师):和晓梅还偏爱用第一人称“我”叙事,但“我”一般不参与故事的发展,主要是一个讲述和审视的角度,在“我”的心理时间中展开叙事。……以心理时间叙事一方面可以打破物理时间对叙事的限制,另一方面主观化的叙事能更精准的传达人物的心绪和感情,与传统的叙事相比较,心理时间叙事不再专注于事件发生的过程,而着意人物的感受与思绪,叙事呈现出片段化特征。
孔莲莲(文学博士、曲靖师院教师):和晓梅的小说讲述故事的节奏控制很好,她对故事场景的设置也很有想象力和画面感,细节的处理很见功力。同时,她的很多小说的叙述常常带着“间离”效应,叙述者常常跳出故事本身,对故事进行评价和预设,显示出知识分子写作者的共性。这也使得她带着纳西迷离气质的叙述里多了些现代气息和理性精神,从而较好的平衡了民族性与现代性,神秘迷离与“去魅”写实的关系。
轶名:独特的叙事成就了和晓梅,但也限制了她的视野,过分倚重叙事技巧,从某种程度上说,也会导致其对作品主题深度开掘的忽视。
王瑞(云大2014级研究生):故事的类型化、气氛的阴郁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作品的张力,不够收放自如。在对民族、地域的塑造上少了几分历史感和厚重感,过多的集中在表现个体上,少了整个群体的整合力。但是,这是一个有才情、有责任的作家,她试图用文字还原逐渐消逝的文化记忆,指出时代的症候,敢为失语的文化呐喊,可以说,和晓梅是有力量的!
蔡漾帆(云大2015级研究生):我发现和晓梅的小说喜欢采用冷色调。这种冷色调描写,代表女性的阴性的冷静、内敛,但是和晓梅笔下的女性在这种阴冷的沉默中爆发出生命之光,如同黑暗中沉静的湖面突然冲出一个火热的太阳。而且,和晓梅作品中时常出现神秘的动物意象,如猫和蛇,都带有极其浓郁的神秘色彩,黑暗且忧郁。和晓梅选择这类动物,表现出女人的神秘、忧郁、孤独,让人有一种心灵无处安放的感觉。
陈林(苏州大学文学博士):说到猫这类的动物意象,我补充一点。在《深深古井巷》中,李儿翠和她的猫既合二为一,又一分为二,既是诱惑之源,又是引起恐慌与悲剧的病灶。如果说李儿翠是本能欲望的化身,那么那只不知年龄、超越时间、带着鬼气的成精之猫则是一种超我力量的象征。纳西族三兄弟都受到李儿翠的诱惑,但那只猫无时无刻不在某个角落以鬼魅的超越之眼注视他们,以示警告、威胁,前者召唤着欲望,后者则竖起了警戒牌。小说的深层结构是一个俄狄浦斯式的弑父娶母的悲剧,它超出个体、民族而具有更为普遍的文化心理内涵。
马丹(昭通学院教师):和晓梅还是一位“造境”高手,她不吝笔墨对环境进行细描,不是为了细致客观的展现环境,而是为故事造设空间,空间在她的作品中充满了隐喻意味,是叙事的基调和氛围。
朱彩梅(现代文学博士、云南师范大学教师):
和晓梅的作品,尤以《宾玛拉焚烧的心》为代表,在表达上普遍存在用语刻板、对话生硬的问题。作者想渲染故事之神奇,刺激读者的猎奇心,但不免空洞、乏力,有些甚至显得故弄玄虚。从节奏与谋篇看,为串入故事或讲一些新奇事件而硬设一些人,硬造一些事,很多穿插与前后文并无内在关联,有重复堆砌、画蛇添足之嫌。而且全篇几乎都是概述性描写,看上去像是另一部鸿篇巨著的梗概纲要。整体而言,作品语言字句上处处抹不去作者的主观痕迹,文字背后却无精神支柱,缺乏一种来自作者心性自然流淌的气韵、神采。
陈琴(云大2014级研究生):个人觉得她的语言的应用太过个人化,虽然有助于对鲜明的个人风格的建立,但换句话说,作家所拥有的使用语言的能力并不能只有一种。小说最重要的是语言,语言多样化会极大丰富一个作家的作品,用太过个人化的语言反而会使这个人的作品成为类型化,只用一种语言来写作品很可能会导致最后写作的失败。
朱彩梅(现代文学博士、云南师范大学教师):总体而言,和晓梅独特的民族身份、生活环境、生命体验,是一座别人求之不得的写作资源宝库,但其现在作品多是民族学、人类学的价值意义甚于文学。好在她的写作是在路上的,如果能不断提升表达、叙事的能力,敢于直面存在的真相,获得超越民族、反观自身的普世视角和思想力量,把荒诞、奇异的境遇中人物灵魂深处的隐秘描述出来,把民族生活中那种原始趣味、野性力量营造为气息、氛围传达出来,她的作品将获得真正震撼人心的力量。这是可以期待的!
主持人宋家宏:通过这期云大评刊的讨论,大家对和晓梅的小说创作有了一个较为深入的了解,各位的评价并不一致,而且也都畅所欲言,这是好事,有不同意见,有争议,才会推进理解,也才会对作家以后的创作产生一点启示。和晓梅的创作之路还很漫长,她也是一位可以听取不同看法的作家。
谢谢!
责任编辑:程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