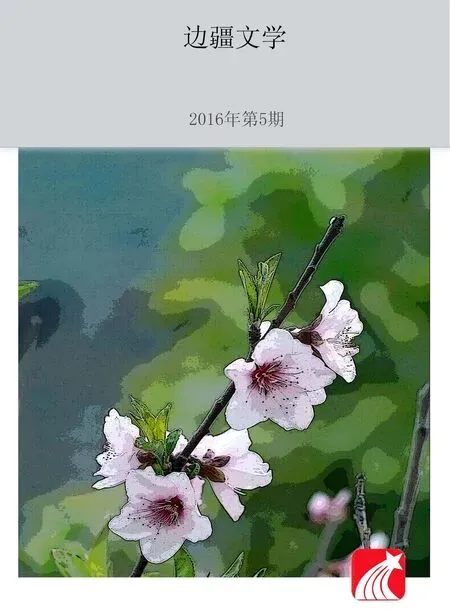“全集”的泛滥与贬值
◎黄桂元
“全集”的泛滥与贬值
◎黄桂元
出版一部个人“全集”意味着什么?无论此人是否健在,都是一件不得了而不是无所谓的事情。它象征一种授勋仪式——对“大师”量级的辉煌成就的认可和历史评价,无异于在大众的心中矗立起一座偶像的文化丰碑,它带给人们的应该是一种近乎朝圣般的高山仰止。透过煌煌“全集”,读者看到的是一个隆起的文化、智慧与精神的海拔高度。“全集”剔除了一般文集的筛选和拔萃,要求尽可能全面地展示作者最客观、最真实的文字内容,包括未刊稿、私人书信、日记、便笺,看上去宽松得没了界限,其实不然,包罗万象的另一面便是巨细无遗,便是纤毫毕现,它使得扬长避短和去芜存菁失去了可能性,即使最轻程度的文过饰非和“为尊者讳”,都会践踏“全集”的定义。总之,此绝非等闲之事。
很显然,不是随便哪一位学者作家的文字全貌都具有珍藏价值,都值得“曝光”和展示,都无愧于“显微”。从这个意义上说,“全集”的质地应该是纯净的,品性应该是透明的。它抵制虚伪拒绝炒作,也容不得浅薄、乏味和平庸。它理应得到人们跨时空的仰慕和珍爱。而我所看到的事实,是许多已经面世的“全集”处境尴尬,颜面难堪,无人喝彩,命运很不美妙,更别提得到书界的尊重。这里,无辜的作者和读者不应承担什么责任。它们如同一个个违章建筑,虽搭出了像模像样的框架,却地基松软材质低劣,工程的质量便可想而知了。
记得1998年,曾有南北两家刊物联袂推出了一个“寻找大师”的理论栏目,参与者众多却一无所获,那情形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也像一场煞有介事的捕风捉影,寻找的结果,当代中国的文学地理并没有诞生哥伦布和他的新发现。我理解选题策划者的美好动因和激情创意,却和许多关注者一样不得不正视了这样一个无奈的事实,当代中国文坛看上去各领风骚群雄逐鹿,若寻找起真正的所谓“大师”来,又何其艰难。其实,当人们把目光转而投向近现代文学史,就会发现那种“寻找”的难度仍然存在。想象大师如繁星满天,对于东西方的任何时代和国家都只是一种寓言,何况我们这样一个环境、土壤、气候都不利于大师成长的百年中国。一些聪明的出版人却不这么认为,他们面带无所谓的微笑,以批量生产和销售的姿态,很轻松地就把一套套名家“全集”供上书界的庙宇,同时也很轻易地用这种方式稀释了名家们原有的含金量,使人们不能不质疑这些出版人的诚意所在。
我的质疑缘于一次逛图书大厦的经历。那是个深秋的中午,幽幽日光透过落地玻璃窗洒进来,笼罩着几个位置显赫的专柜,我不经意地发现,那光影斑驳中竟满满当当排放着各种个人全集,鲁郭茅巴老曹就不用说了,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严复、胡适、周作人、傅斯年、李叔同、郁达夫、沈从文、刘文典、刘师培、赵元任、张爱玲、叶圣陶、郑振铎、徐志摩、钱钟书、朱自清、闻一多、梁漱溟、吴梅、萧红、冰心、丰子恺、俞平伯、张恨水、路翎,史学家钱穆、顾颉刚、陈寅恪、陈垣、范文澜、吕思勉,哲学家熊十力、牟宗三、冯友兰、金岳霖、美学家朱光潜、宗白华、语言学家王力等等,自然也是谁都不能少,他们的全集已经问世,而《萧军全集》、《艾芜全集》、《汤用彤全集》、《顾随全集》、《萧公权全集》、《丁玲全集》、《俞平伯全集》、《田汉全集》、《吴世昌全集》、《竺可桢全集》、《费孝通全集》、《何其芳全集》、《季羡林全集》、《启功全集》、《柏杨全集》、《艾青全集》、《郭小川全集》、《闻捷全集》、《陈香梅全集》,又一宏大阵势前来助兴,少则数卷多则数十卷,令我大开眼界。一位朋友听了我的唏嘘,说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我可以再加上《冯至全集》、《姜亮夫全集》、《贾祖璋全集》、《孙犁全集》、《汪曾祺全集》、《王小波全集》、《路遥全集》,大家已经见惯不怪了,你又何必认真?看来我的确是少见多怪。一天,我读到了某报,第五版以整版篇幅向读者“公示”了用来接受社会监督的“第六届国家图书奖初评入选书目”,里面依次出现了《臧克家全集》、《吴梅全集》、《傅雷全集》、《梁思成全集》,继《钱钟书全集》之后,《杨绛全集》也将面世。一阵光景,我接连遭遇了各种“全集”的一通轰炸,头晕脑胀,很难一笑置之了:从什么时候起,我国文化界已经是大师云集“全集”林立,竟如同变戏法一般?为何那些出了“全集”的作家学者,在我心目中的位置反而降低了?这种无人喝彩的廉价“繁荣”原因何在?
上述各位,皆为各自领域的翘楚,是不是所有的文字纸屑都有流传和珍藏的价值,却未必然。比如,臧克家老人能为读者记住的作品只有《老马》和《有的人》等几首诗,更多的诗文属于思想和艺术都平平一类,更别提书信日记,如此良莠杂糅很容易弄巧成拙,既有损老诗人的原有名声,也是对读者的蔑视。傅雷先生作品有限,译作却声名远播,如果把巴尔扎克的那些巨著拿来充数,则难免牵强。我曾在书店看到过《傅雷文集》,包括文学卷、艺术卷和书信卷,虽非著作等身,却很有含金量,还算是实事求是。如今臧克家和傅雷的“全集”不仅出版了,而且还堂而皇之入围了某年的国家级图书奖的初评,我想不清楚这里遵循的是一种什么“游戏规则”。丁玲女士的《沙菲女士日记》在当时尚有些影响,《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却因太多图解政治的痕迹而被时代淘汰,其它作品则少有问津,这位生前主张“一本书”主义的女作家,身后却出版了远谈不上珍贵文学遗产的所有文字,也是一件趣事。诗人闻捷恐怕生前做梦也不会想到,30年后会有自己的“全集”问世,这种事怎么解释都无法令人信服。闻捷作品的审美效应早已过时,篇幅冗长而诗意寡淡,鲜见令人震颤的艺术创造和思想深度,稍具水准的读者自有判断。还有其中的一些学者、作家,其学问有高下,成就有大小,说到出全集,也都有一定水分。最有意思的是,尚健在的美籍华人陈香梅女士也被隆重推出了“全集”,陈女性在22岁时因其年龄悬殊的跨国婚姻而一举成名,进入中年,寡居的陈女士开始独步美国政坛而成为风云人物,同时经商理财,还风尘仆仆地在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之间搞穿梭外交,也常常“客串”作家且有著述数十种,水准最多属于文学“票友”之类。作为卓有政绩的社会活动家的陈香梅,我可以诚惶诚恐,但作为才情一般的女作家的陈香梅,我实在不敢恭维。
如果大家不嫌添乱,上述先生女士够资格出“全集”,那么我可以不无保守地列举一长串都曾响当当的名字,来一番锦上添花,否则,我认为就是有欠公正和公平。他们是诗人戴望舒、李金发、殷夫、胡也频、蒋光慈、李广田、穆旦、田间、穆木天、卞之琳、浦风、袁水拍、徐迟、辛笛、杜运燮、曾卓、郑敏、贺敬之、李季、昌耀、牛汉、阮章竞、李瑛、北岛、舒婷、顾城、海子、于坚(事实上新时期诗坛一批年轻诗人的成就、造诣和影响已经超越了一些前辈),小说家、散文家、剧作家、学者王统照、张天翼、沙汀、夏衍、李健吾、洪深、庐隐、端木蕻良、许地山、吴组湘、姚雪银、骆宾基、废名、赵树理、欧阳山、柳青、杜鹏程、张中行、余光中、王鼎钧、白先勇、余光中、王蒙、顾准、陈忠实、刘小枫、史铁生、莫言、贾平凹、韩少功、余华、苏童、格非、王朔等等,似乎就没有理由不给他(她)们出“全集”(没准已经有人正忙着张罗了,也未可知)。只是如此一来,放眼世界再没有比中国文化界更热闹更喧嚣更光怪陆离的了,注水的“全集”便如同儿戏,所谓的“国际笑话”也真闹到了世界舞台。
陈平原曾在《中华读书报》上很认真地开列了一个包括从晚清到五四一代的著名学者在内的大名单,认为应该给他们出“全集”,论述这些珍贵的名字所创造的学术价值是我力不胜任的,陈先生是研究近现代文史的实力派专家,所言自然颇具权威性。陈先生说“出全集,并非对所有的文人学者都有利,如果本身并不怎么完美,出了全集,其光辉形象反而可能大受损伤”,事实上,这种危险对名单中的任何一位都存在,只是程度不同。并不是每个在生前享有盛誉的作家学者,都具备“大家”的禀赋、气象和出全集的条件,也并不是大师的数量现代要远远大于当代,死人要远远多于活人。其实我最想强调的是,二十世纪百年中国文学的总体成就,远没有陈先生估计的那么乐观,并无多少本钱向世界供奉如此之众的“大师”和“全集”,硬要供奉,结局或束之高阁,或只能杀价以求。
退一步说,即使有谁打算为什么人出“全集”,也需要一种严格的“资质”认证,以防泛滥成灾滥竽充数,硬是各行其是也没人拦着,更不用担心会触犯法律,只是这种做法太不负责任了,既害作者又坑读者。如果放在世界文化坐标中考察,就更不难发现其中的荒唐和可笑。其中,一些“全集”出版或计划出版的原因复杂微妙,有的是受制于乡谊乡情,带有地方保护主义的色彩(比如山东之于臧克家,云南之于姜亮夫,湖南之于傅斯年、安徽之于朱光潜),有的相互攀比,有的则可能取决于财力的支持或文化与出版官员的偏爱等诸多因素。也有例外,河北出版界这些年一直身体力行,相继推出了丁玲、陈香梅、何其芳(以上为河北人民出版社)、田汉(花山文艺出版社)李大钊、吴梅、顾随、吴世昌(以上为河北教育出版社)的全部文字,有备而来一意孤行,几乎成了各类“全集”的生产基地,此举可谓某种深思熟虑过的战略举措,却似乎不具市场和功利意图,不免令人匪夷所思。只是如此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很不利于创作环境的清洁、学术秩序的改善和文化遗产的整理,容易产生一种阅读误导,败坏文化消费者的胃口,使人们对那些“全集”熟视无睹麻木不仁,未必符合作者的意愿。
还是拜托罢,大家很恐惧看到有中国地方特色的那类大师和“全集”。无论如何,大师应该获得精英文化、文化史和几代读者的多重认可,要在几代学者、作家中鹤立鸡群才不会枉担虚名,他们并不是完美无缺,毫无局限,但这不妨碍他们是一个划时代并能够影响以后时代的文化巨人,他们具备了超凡脱俗的心灵质量和人格魅力,同时拥有足够丰厚的精神遗产、足够分量的文化建树和足够辉煌的艺术杰作。对这样的大师,读者需要也愿意了解一切,包括作品之外更多的个人生活细节、思想微痕和心理涟漪,历史也不会任其自生自灭,如果以一种最好的纪念和继承方式表达人们对大师的敬仰,莫过于出版他的“全集”,这也是对大师的一种盖棺论定。当我们面对这样的“全集”,会联想到峰峦、森林、大海和天空,而不是闪电、雷鸣、昙花、飞瀑。后者更多的是属于天才和名家,更适合出文集或选集,而出全集者则非大师才能享此待遇。全集和文集、选集之间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数量关系,而是有本质的区别。用袁枚在《随园诗话》的说法,“诗有大家,有名家。大家不嫌庞杂,名家必选字斟句。”在文化艺术领域,大师和天才、名家之间的区别有时候并不清晰,甚至见仁见智,但多数文化人绝不糊涂,心里还是有杆秤的。
大师不是一顶纸糊的桂冠,经不起岁月的风吹雨打,也不是一颗媒体廉价炒作出来的明星,很容易随时尚潮流的起伏而生而灭。大师意味着博大精深,海纳百川,气象万千,承前启后,并不靠局部的光芒和短暂的声响吸引人们的关注。像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陀思妥也夫斯基、雨果、罗素、毕加索、泰戈尔和博尔赫斯等,谁能指出具体哪一部作品是他们的代表作?他们的思想和艺术能够跨越国别和年代而浑然一体,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而走向永恒,因此,大师不仅需要巨大的才能,还要具备不懈的劳作和承受大起大落的坚强神经。
天才也是不多见的。天才多指那些偏执、怪异之才,他们不是靠“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加一分灵感”,也不靠“取百家之长”,用勋伯格的话,“天才只向自己学习,有才干者则主要向别人学习”,比如莫扎特、肖邦、梵高、马勒、尼采、维特根斯坦、荷尔德林、卡夫卡、李煜和徐志摩等,他们的创造常常表现出了尖锐的原发性和鲜明的独创性,一般人很难模仿和重复。天才的才情缺乏节制和收控,很容易在极短的创作燃烧中化为灰烬,往往难以达到大师那种高度、深度、广度所必需的精力、体力、从容、坚韧、平衡力、吞吐量和寿命。
而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名家了。这不需要饶舌,每个年代每个地区都有可能出现各自的名家。名家的才华有时候看上去也能直逼大师,由于各种原因也可以声名显赫令人赞叹不已,但他们很难企及大师的高度、成就和境界,时过境迁,多成为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文化“鸡肋”。据说巴金就对自己的文学成就评价不高,甚至称自己不是“文学家”,我想大概不都是出于谦逊之辞。
依我看,天才和名家们大多身怀绝技,笔墨风格各有特色,精选出能无愧于作者水准的文集就可以了。在一个明明是大师稀有的时代,出版人不必“皇帝不急太监急”,草草推出各类低质量倒胃口的“全集”,给人的感觉很像是在人为地造“神”,结果“神”一多就不值钱了,把好事情往砸里办。出版人不是魔术师,谁也不可能通过“全集”就能摇身而变为大师,这种闹剧似的做法很不明智,也是对历史和读者的欺弄。当务之急是让诸“神”归位,回到凡尘,我想,大家的心情都会好受一些。
(作者系著名评论家,茅奖评委)
新锐批评
责任编辑:杨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