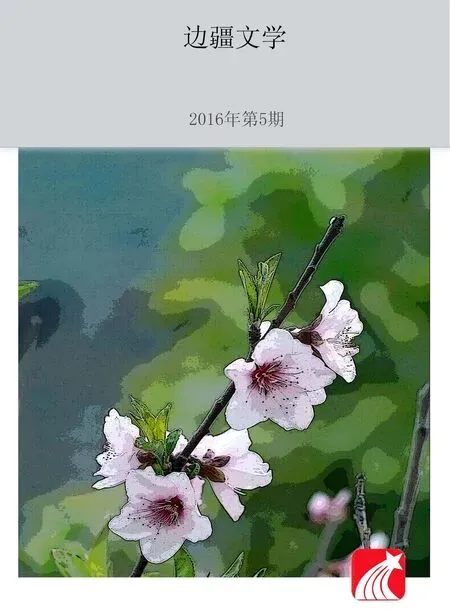和晓梅中短篇小说整体观
◎陈 林
和晓梅中短篇小说整体观
◎陈林
如何理解和晓梅的小说?有太多熟悉的理论资源可供选择、调用,可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切近。
和晓梅的女性身份、作品中得到充分表现的女性形象系列、以及文本的女性意识、女性视角等,都提示我们可从性别的角度走进她的作品。我们熟稔的女性主义批评为这种解读提供了相应的话语资源。作为纳西族的一员,和晓梅的写作关注民族题材,得益于民族文化、民间文学的滋养、哺育。她小说中那些纳西族奇异的家族故事、民风民俗、神话传说,则会让读者从民族意识、地域文化或者文学人类学等角度切入。较之于中原地带,和晓梅生于斯长于斯的丽江地处边缘;较之于汉民族的主流文化,纳西族文化是边缘,她对本民族文化的特殊感受和体认,实际上暗含着与作为他者的主流文化的参考比照,这自然为后殖民理论提供了阐释空间。和晓梅多处写到纳西族不同阶层之间的情感纠葛、矛盾冲突,因此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理论也成为阐释文本的武器。她小说中那些充满原欲冲动的人物形象,那些社会——文化环境中的病态人格,则让人想到弗洛伊德等人的精神分析学说和早期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从代际来看,和晓梅属于“70后”作家,尽管对“70后”这一命名的质疑和不满之声不绝于耳,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一代作家与“50后”、“60后”已有很大不同。代际视野同样不失为理解和晓梅的一种方式。套用某种理论“强制阐释”文本的做法无疑是削足适履、缘木求鱼,而不囿于一家之言,以各家理论作为关照文本的视野和对话空间,并将和晓梅的小说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考察,则有助于我们对其人其作的有效理解。
一
和晓梅二十出头发表处女作《深深古井巷》颇为令人惊讶,这让人联想到现当代文学史上那些才华横溢的年青作家。《深深古井巷》是和晓梅最出色的作品之一,这部小说在她的整个创作中占据比较重要的地位,它已触及和晓梅小说艺术的“内核”及诸多相关问题,之后的作品多为它的延伸和扩展。从现当代文学史的角度看,这部小说可置于张爱玲的《金锁记》、陆文夫的《小巷深处》、苏童的《妻妾成群》等作品系列中加以考察。放到这些名篇佳作之中,《深深古井巷》依然有它的夺目之处。
小说讲述了一个纳西族家族的悲剧故事。主人公“二伯妈”李儿翠是个悲剧人物,她甚至从来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由做娼妓的母亲一手带大并因“太贪钱又爱慕虚荣”把她嫁到异族他方,之后遭受丈夫的冷落、家暴、施虐,最终伴随一声枪响,她双目失明、胎死腹中、情人分离。“深深古井巷”不只是物理空间,也是纳西族人的生存空间和文化空间,它包含纳西族的“哭嫁”、“情死”、“东巴驱鬼”等文化密码,李儿翠的悲剧命运在此特定的空间中展开。不过,这部小说蕴含着超越性别与民族的深刻内涵。李儿翠和她的猫既合二为一,又一分为二,既是诱惑之源,又是引起恐慌与悲剧的病灶。如果说李儿翠是本能欲望的化身,那么那只不知年龄、超越时间、带着鬼气的成精之猫则是一种超我力量的象征。纳西族三兄弟都受到李儿翠的诱惑,但那只猫无时无刻不在某个角落以鬼魅的超越之眼注视他们,以示警告、威胁,前者召唤着欲望,后者则竖起了警戒牌。
三兄弟的不同选择代表了处理本我与超我关系的三种可能。“父亲”先是患了疯癫症,对猫极端恐惧,听见猫叫声竟会“脸色煞白,全身抽搐,几乎晕死过去”,几年后几乎痊愈,诸事顺遂。这是对超我力量的臣服、顺从,“父亲”的欲望没有得到表达,他因乱伦焦虑而陷入疯癫。对“二伯父”而言,超我之猫锁死了他的性欲插销,但并没有阻断他的攻击性内驱力,而是转化为这种力量。这表现为他的弑猫、家暴和施虐行为。弑猫可以理解为弑父的隐喻(“二伯父”年青时十分叛逆,即便被“爷爷”暴打也绝不交出抢来的铜钹),弑猫不成,继而把愤怒与恐惧发泄到李儿翠身上,变成一个施虐狂。“三伯父”是最彻底的反叛者和破坏者,“二伯父”即他的超我压抑性力量,杀死他意味着弑父行为的完成,而这是“父亲”想做而不敢做的事情,所以事发当晚“父亲”“睡得安稳浓沉”、“快乐极了”,他的焦虑和恐慌随之减弱。小说的深层结构是一个俄狄浦斯式的弑父娶母的悲剧,它超出个体、民族而具有更为普遍的文化心理内涵。
如果“三伯父”选择带着李儿翠奔赴“玉龙第三国”“情死”,即可演绎出类似《女人是“蜜”》、《情人跳》里的故事,不过“玉龙第三国”的神话在“读过书识汉字”的他那里已经破灭,或者说在现代性的冲击下已被“祛魅”。《女人是“蜜”》、《情人跳》两部小说的重点放在现代性“祛魅”前纳西族的“情死”文化上。这种文化许诺一个无比美好的乌托邦世界,那里住着统治“玉龙第三国”的爱神康美久蜜金,爱情受到现实阻碍的男女双方可通过“情死”的方式进入“玉龙第三国”。“情死”是种悲剧文化,在通往爱神的途中必先跨过死神的门槛。死亡因此被赋予了神圣的光环,具有献祭意味。在《女人是“蜜”》中,阿菊旦是康美久蜜金的肉身化显现,她以无私的爱挽救了布朗等人,自己却成为爱情祭坛上的祭品。《情人跳》里的木、吉在完成最后的仪式后,毅然赶赴情死地。这实际上是一个“爱与死”的主题,和晓梅的另一部小说《蛊》借用武侠小说的形式表达了同样的主题。
阿菊旦、木、吉都是无辜的替罪羊,他们并没有犯罪却承担了集体的罪责。替罪羊是整个社会集体暴力与仇恨的体现,小说中表现为香格里因收留布朗等洋人而被外族洗劫一空,木、吉遭遇众人围堵乃至死于枪下。在伊格尔顿看来,古代的替罪羊正是现代革命主题的预兆。激进的革命家必然是“情死”悲剧的坚决反抗者。“玉龙第三国”所代表的超历史范畴暗示了存在不可改变的事物,它与我们的有限性和脆弱性达成象征性的妥协。尽管“情死”文化包含着反抗现存秩序的因素,但更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退缩,它回避、消解了社会危机。在我们熟悉的现代启蒙叙事或者革命叙事中,此类传统文化会被草率地当作纯粹的虚假意识而被摒弃,它被视为扼杀自由的真凶和统治阶层的阴谋。试想,倘若鲁诺家的短工最终没有听从“玉龙第三国”的召唤,而是抢过火枪杀死拓,并联合起他的无产阶级兄弟——《水之城》里沉溺于鸦片不可自拔的长工恒之、《有牌出错》里的酒鬼“爷爷”,把枪口对准鲁诺老爷及其代表的阶级,那么一场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革命就此拉开序幕,革命的火药将无情地摧毁“玉龙第三国”的乌托邦世界,历史由此换上新装。
二
革命的枪声在《连长的耳朵》里响起。战争是残酷的,鲜活的生命瞬间灰飞烟灭,毫无任何道理可言,人的恶魔性因素被释放,仇恨、杀戮难以止息;战争也是荒谬的,现代武器作为人类文明的产物反过来对准人自身,成为人类的掘墓者。连长不得不饮下自己枪管里的最后一颗子弹,即便如此,他也摆脱不了遭受怀疑、难证清白的困境。最大的荒谬莫过于,连长不仅丧失了听力,还丧失了与战争相关的某些重要记忆。没有记忆意味着时间性的消失。历史的真相无人知晓,战后的世界竟是一片意义荒芜的不毛之地。连长变成“完全没有身份的人”,除了战争遗留下的疼痛,没有什么能够证明他的存在。这让人想到余华《一九八六年》里不断割裂自己身体的历史教师。
对于“70”后的和晓梅一代来说,历史记忆中的公共性不复存在,经验的碎片化、叙事美学的琐碎化成为一种普遍倾向。仅从《连长的耳朵》这一标题即可看出端倪。耳朵是身体的边缘,身体是战争的边缘,在主流的经典革命历史叙事中,身体叙事是被压制的对象,和晓梅所做的恰恰是把肉身化、边缘化的小叙事从战争的宏大叙事中解放出来。这篇小说的历史背景模糊难辨,我们很难从中找到任何关于战争的正义性、合法性的言说,敌对双方都没有清晰的历史轮廓。和晓梅拾捡起历史边角处往往被忽略的细枝末节,水煮或红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会撒上点人性、人情、人道主义的调料。这味调料来之不易,它曾给人带来厄难。对1980年代的写作者来说,能以人性的温暖抚慰历史的创伤是一种解放和进步;碎片化更像是一种叙事策略,以此完成的是它的反抗使命,历史记忆的公共性作为写作的潜文本并未缺席。和晓梅及更年轻的一代则可能是,他们已经没有了这种公共性,在人性化的历史碎片背后,仅是一片虚无。
《昌青街记事》写的是发生在一条沉寂、凋敝、破败的街道里的故事,那里有一群无所事事、游手好闲,只知道打架斗殴、调戏女人的年青“小流氓”。这篇小说没有给出明确的故事时间,历史叙事比较隐晦、暧昧,不过从细节中依然可以判断,小说以一条街道里的纷繁乱象,管窥的是“文革”至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历史。在文学的历史叙述中,这段时间一直是叙事的重要内容之一,“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知青文学”、“改革文学”的叙述焦点均在于此。放到这样的文学史系列中,这部小说显然有些另类。那些暗无天日的杀戮背后的意识形态色彩被淡化了,暴力仿佛只是一代又一代昌青街青年的力比多宣泄,小说仅仅在某些细节处提示我们与当时的红卫兵武斗和“革命”联系起来。我们知道,那些无休止的令人发指的杀戮实际上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年青人的内在冲动而忽略了悲剧的社会性。它与墙上频繁更换的标语密切相关。这些标语改变着人们的命运,人物的活动也因此是历史化的。从“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到“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分子”的标语替换,提示了中国历史从革命向后革命时代转移。昌青街的青年在社会转型中走出他们的故乡,和晓梅的小说也穿越历史回到当下,然而,我们对历史的反思远未完成,诸多问题依旧悬而未决。
三
《我和我的病人》是一部直面当下的作品,它试图写出我们时代的精神症候和社会病理学。小敏的病不是个体的心理、生理造成的,而是当今社会文化的副产品,因此具有普遍性。心理医生“我”和病人小敏其实都是病人。人都病了,举目所见几乎无一例外。我们时代的这种病可以叫做抑郁症、焦虑症或者神经症。按照卡伦·霍尼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一书中的说法,这种病症与现代文化的关系约略可做如下表述:因为现代文化在经济上是建立在个体竞争的原则上,这一情境的心理后果乃是人与人之间潜在敌意的增强,敌对性紧张导致不断产生恐惧,在现代意识形态的压力下,摇摇欲坠的自尊心建立在竞争取胜的基础上,所有这些因素共同在心理上导致了个体的孤独感,作为补偿性需要的爱遂受到过高的评价和强调,乃至成为一种幻觉。所有现代人都置身于神经症形成和发展的文化语境中,所不同的仅仅是这些文化因素产生后果的严重程度不同而已。
中国当下的文化状况可能比霍尼所说的还要复杂。从这部小说谈起,病人小敏和他的丈夫代表着1990年代粉墨登场的“新富人”阶层,这一阶层在文化上被阐释为“成功人士”,成为大众仿效的对象,他们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社会结构的巨大转变。然而在“成功人士”的光环下,他们无法摆脱“异化”、“物化”的陷阱。这些消费主义时代的弄潮儿早就住进富丽堂皇的高楼大厦,然而他们的灵魂却飘荡在户外淋雨。他们原以为手中掌握的资本足以自证,结果却发现挥金如土正是以丧失自我为代价。他们生活在意义的真空中,因为时间被如此廉价地出卖给空间。他们将自己移栽到城市,甚至连根须上的泥土也要抖落干净,就像小说中的矿老板要彻底涤清身上的乡土气息,尽可能把自己包装成现代都市的假面人。
问题的复杂性还不止于此。矿老板的公司被查证为非法企业意味着“新富人”阶层的合法性成为问题。这提示了该阶层得以产生的历史环境以及它的历史生成过程总是被刻意抹去的个中缘由。小敏的丈夫是一家声名显赫的房地产公司的老板,如果把他手中鳞次栉比的高楼还原到土地,那么我们要追问的是,国有资源转化为个人资本的真实的历史过程究竟如何?“我”与小敏之间如此巨大的贫富差距与此过程有着怎样的关系?我想,仅以“文革”时期的“革命英雄”作为反例来为1990年代崛起的“新富人”阶层辩护恐怕难以令人信服。
如何实现从“英雄”形象到“成功人士”形象的转换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今天我们已经看不到英雄,因为理想主义已被污名化,英雄甚至成为一个让人蒙羞的称谓。堂吉诃德不再被视为英雄,而是疯子或者妄人。小说中的钢琴老师或许是唯一有英雄主义倾向的形象,然而,他对旷世之作的追求反复遭到揶揄、嘲讽。当然他并不是英雄,这不单指他最终回归到世俗生活的浪潮中,更重要的是他对堕胎一事的看法表明支配他的思想和行为的恰恰是集体意志,换言之,他不能对时下的种种谬见置若罔闻,不能克服诸多虚假期待的蛊惑,按卡尔·亚斯贝斯《时代的精神状况》一书的观点,他所缺的正是当下可能有的真正的英雄主义所需具备的品质。
四
从爱神康美久蜜金到英雄连长,再到当下的“成功人士”,和晓梅的小说超越性别、民族、地域,她的创作把独特的个人经验融合到历史意识中,写出了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人的生存境况与文化心理的变化。只有把她的小说作为一个整体来看,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晓梅把握世界、书写世界的独特方式,才能看到她为我们勾画出的不同文化形态下鲜活的心灵的历史,这些真实的心灵世界构成了历史真实不可或缺的侧影。正是从这个角度,我认为和晓梅是一位颇有抱负的写作者。
和晓梅对传统、对历史的叙述当然是基于对当下的理解,反过来,对传统和历史的认知结构影响了对当下的理解,这是一个解释学循环。借用福柯的名言,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年代,重要的是讲述话语的年代。《我和我的病人》出示了和晓梅“讲述话语的年代”,这个年代的现实、文化语境决定了她如何看待自身的传统和历史。个性解放、人的觉醒是“五四”留下的精神遗产,1980年代的人性、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接手了这一遗产,和晓梅的小说世界有人性、人道主义的视角,因此她对“玉龙第三国”的乌托邦世界有所反思;对战争中的受害者投以人道主义的关怀。此外,生活在一个后革命时代,1990年代思想文化界对百年激进主义的反思、“告别革命”文化潮的兴起,使和晓梅对革命历史的书写具有明显的新历史主义倾向。再者,对本民族文化的切身体验以及对世俗化浪潮冲击下人类精神状况的忧思,使得和晓梅笔下的传统与现代不再被置于愚昧与文明的二元结构中加以理解。她的小说呈现出不同的社会秩序、文化形态与人的存在方式和精神状态之间的内在关联,其中既包括她对历史与当下的反思,同时又不乏理解和同情。
当然,对和晓梅这一代来说,“大写的人”早已死亡,他们实难创造出任何正面有力的人物形象,因此所有的批判都显得疲软无力。和晓梅小说给人印象深刻的恰恰是一些病人形象,不同之处似乎仅在于,他们所患的是桃花病、疯癫症还是抑郁症。这些晒在历史围栏上的病态形象反映了和晓梅悲观主义的认识论图式,她小说艺术的美学风格在此认识论基础上形成。小敏和“我”最终看似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不再像病人。克尔凯郭尔曾把绝望视为一种“致死的疾病”,我的困惑是:绝望而不死,难道只能犬儒主义地活着?
(作者系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
责任编辑:杨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