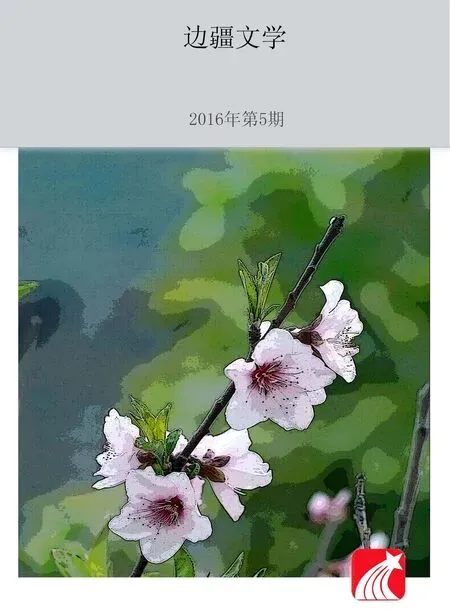提升语言表达 深化民族书写
——和晓梅作品简评
◎朱彩梅
提升语言表达深化民族书写
——和晓梅作品简评
◎朱彩梅
丽江纳西族女作家和晓梅是云南70后代表性小说家,其作品致力于当地少数民族题材的书写,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浓郁的民族风情。在写作中,她有意识地去尝试、探索民族性与现代性、本土性与世界性的融合,但目前,汉语表达的艰难和超越自我局限审视民族文化的困难,如两块巨石,双双横亘在她写作的道路上。
对民族传奇的书写
和晓梅对民族题材的钟爱,源于其独特的民族身份和成长环境,她熟悉当地纳西族、摩梭族、傈僳族、彝族、普米族、独龙族、拉祜族等各民族的乡土风物、人文景况、宗教习俗,作品常给人带来陌生、新鲜的见闻与感受。这集中体现于长篇小说《宾玛拉焚烧的心》,在这部作品中,读者能见识到诸多奇风异俗:落风村的木楞房、花楼、傈僳村寨、火塘神、生死屋;赤脚格木人乌卡,深信自己是熊的后代,夜晚习惯在树藤吊床上睡觉;宾玛拉墨和乌卡用眼睛看到的第一样事物为刚出生的孩子命名,叫做“胎盘”;彝族人在手臂上整整齐齐纹上漂亮的梅花印;乌卡带“我”去他的家乡,一路上奇事不断,经历了吃爬沙、过溜索、被断头蝇咬伤、过吊桥,遇见来自干热河谷地带的商人,他们患有严重的龟裂症,看到文着面的独龙族人用清水吸引蚂蟥;到了乌卡故乡所在的热带雨林,更是眼前一亮,格木人盛行大环垂耳,女人们喜欢用拍屁股的方式传达祝福,人们靠占卜来决定女人生产的地点,每年老翁里带领族人用外族男人的首级祭祀……
和晓梅倾注笔墨于这些原始、自在的事物,人物也多至情至性,忠于内心信仰,这或许源于作者纳西族祖辈对神的信仰和当地源远流长的祭司文化。她还没有受到太多现代化、全球化进程中科技至上、物质至上风气的影响,作品展现的是一个“人——神——物”同名共体的奇妙世界:莎莎里姐妹俩一胖一瘦,对比鲜明,随年月变化,体型竟发生对称性的递增递减,让人惊讶!宾玛拉墨小时候被亲昵玩耍的小黑熊“噜噜”咬断一根手指,后来她与熊的后代乌卡生活在一起,两人不声不响展开了捕熊、救熊的暗战与较量,直到一只大熊叼走儿子“胎盘”,乌卡切断其前掌为止,以熊之前掌抵消人之手指这种思维,及二人虽为“夫妻”亦不能消弭不同民族之间的意识阻碍,令人唏嘘。“我”离开乌卡,回到落风村,带回一只名叫乌卡的狗陪伴左右,狗与人同名,似乎就能替代那个人。宾玛拉家族会占卦,能与神对话,预知未来,宾玛拉金沉迷于石板镶嵌术,想寻找粉红色的石头,以制造光线回到过去的某个时刻,在大多现代人看来,这是解释不清的迷信活动,或是江湖传说中的算命、通灵术。“我”成为总管夫人的仆役后,整日炼制珍珠丸,每天打扫一间空闲的牛圈,在食槽里添上草料,牛圈里曾经喂养的那头黑牛早被贼偷走,黑牛与四个盗牛贼之死及“我”背上那把一离身就发出嗡鸣的牛筋弩弓之间有着怎样神秘的关联?宾玛拉墨与外祖母、宾玛拉金等人,在熊熊烈火焚烧中,她们仿佛互相融合,彼此的生命不断延续、循环、轮回。
作者通过主人公富于传奇色彩的一生,把对各族群生命力、生活状态的理解表达出来,其笔下世界的原始、野蛮、魔幻、荒诞,与拉美作家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有几分相似。小说糅合现实与虚构,融入神话故事、民间传说、祭司文化、宗教仪式等神秘因素,来讲述宾玛拉家族的故事。
她还有不少作品也都致力于民族题材的挖掘,在2011年接受中国作家网访问时,她以“我们因责任而坚守”为主旨谈到:“丽江共有16个世居少数民族,我们关注这些特殊群体中人的生存状态,关注他们的命运,体察他们的情感与觉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尽量让自己的眼光和思路都适应当前的社会,能引起现代社会读者的阅读兴趣。对于我们而言,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既要试图让文化的精髓在文字中彰显,并努力让它们成为全人类都能够共享的资源,又不能让它们偏离现代社会,陷入到无人问津的孤芳自赏中。”这是和晓梅的心声,对她来说,关注民族题材是一种自觉的民族文化意识在写作中的延伸。
而她,也确实具有天然的资源优势。其民族思维、信仰,在小说中常化为“我说是这样就是这样”的一锤定音、不容质疑的肯定语调,很像《圣经》的“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如对殉情者的描写,与彝族《阿诗玛》、白族《蝴蝶泉的传说》、傣族《召树屯》及汉文化中流传的《梁祝》相比,其殉情主题作品淡化了绝望、哀伤、凄美的意味,在《情人跳》中,她的叙述语调坚定不移,很好地传达出相爱而不能自由结合的纳西族恋人对待殉情那种近乎宗教信仰般的虔诚、执着,在他们的意识深处,殉情是超越生命、到达另一片天地延续幸福生活的美好寄托与理想。此种作家思维、信仰与作品语调、内容的呼应、和谐,颇为珍贵。
汉语表达之艰难
少数民族作家对民族题材的书写,是一种以文字保存族群、再现故乡世界的尝试与努力。这种意识与诉求可以是写作的出发点,但写作最终抵达何处,则另当别论。从文学的层面来说,“写什么”和“怎么写”是个人的选择和自由,“写得怎样”却自有其恒定的标准。
笔者觉得,好的艺术作品是创造一个场,这个场具有它独特的气息、氛围和震撼人心的力量,阅读时,读者不知不觉被浸润其中,如亲身经历。场的创造与作者的个性气质、思想能力、见识眼界息息相关,在作品中则表现为对语言、节奏、构架、形象塑造等的把握。
先从语言表达方面来说,可能是我一向偏爱像丰子恺、沈从文、汪曾祺、孙犁等作家“饥来吃饭倦来眠,眼前景致口头语”那样自然、朴素的作品,在读和晓梅小说的时候,首先留下的一个鲜明印象就是:她虽然没有受到太多消费社会叙事风尚的不良影响,但有些表达诗化不当,过于刻意、矫饰,部分人物对话不仅太书面化,而且所有人说话的语气,几乎都像是一个人,显得僵硬、刻板,让人觉得梗、涩。如《宾玛拉焚烧的心》中的一些片段:
她们轮流亲吻我的额头,说了许多鼓舞人心的祝福,然后把我独自留在夕阳中,翻过一道漫长的山梁,回各自的家去了。
“说了许多鼓舞人心的祝福”,这样的表达更像是某些政府官员视察贫困地区老百姓时的报道惯用语。在此,既非借用,亦非反讽,难免生硬。作者不小心陷入政治术语、行话的滑道,若不警惕,写作会带上新闻宣传的味道。
当烤牛肉的香味在山谷里四处飘荡的时候,他们警惕地守护着自己的战利品,不准我靠前,包括那个受伤的人,都拿充血的眼睛瞪着我。“你没有出力,所以不可以和我们一起分享。”
“嗨,你到哪里去了,我正漫山遍野地找你,脚都快走断了。”他兴高采烈地跟我打招呼,然后夸张地瘸着腿走向我,脸上带着讨好的笑容。
细细思量,盗牛贼会使用“分享”这样的语词?此情此景中,“他”会说出“我正漫山遍野地找你”这样的话?一个词,一句话,意思大体一样,表达方式却可以千差万别。表达的风格及自然、贴切与否,是辨别作品文类及品相高下的依据。文学表达所求的精准、微妙,容不得一丝一毫牵强、将就。
再如《未完成的成丁礼》中的片段:“我可以把花拆了,如果是花的原因的话。”母亲再次做了妥协,也许是因为她随时都有可能爆炸开的身体使她在大儿子面前感到有点羞愧,她的语气有讨好的成分。在现实生活中,母亲这样说会更自然:“你不喜欢花,那我把它拆了。”
从上述引文可以直观感受到,和晓梅的作品,尤以《宾玛拉焚烧的心》为代表,在表达上普遍存在用语刻板、对话生硬的问题。作者想渲染故事之神奇,刺激读者的猎奇心,但不免空洞、乏力,有些甚至显得故弄玄虚。从节奏与谋篇看,为串入故事或讲一些新奇事件而硬设一些人,硬造一些事,很多穿插与前后文并无内在关联,有重复堆砌、画蛇添足之嫌。而且全篇几乎都是概述性描写,看上去像是另一部鸿篇巨著的梗概纲要。整体而言,作品语言字句上处处抹不去作者的主观痕迹,文字背后却无精神支柱,缺乏一种来自作者心性自然流淌的气韵、神采。纳西民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字,也许汉语是作者后天习得,并非出生地母语。用汉语写作,会不会影响到她表达的自然、流畅、妥帖?这是一个不可忽略的问题。
对于少数民族用汉语写作之痛苦与艰难,是多年深受英语考试折磨的国人都应该有所体会的。但对一名作家来说,语言就如战士的兵器、医生的手术刀、裁缝的针线,过不了这一关,写作终将走不远。
小说创作的根本要义
关于人类各民族的历史,德国哲学家赫尔德的观点比较中肯:历史中有两个基本因素,一是外部自然力量所构成的人类生存环境,二是内部的力量即人类精神或民族的精神特性,而后者更为根本。推及写作,作家就更应着力展现一个民族的精神特性。因此,塑造人物形象,挖掘人性奥秘,直面人类精神难题,是小说创作的根本要义。没有这些根基,小说就容易沦为故事,甚至是流水账。
遗憾的是,《宾玛拉焚烧的心》有故事,有传奇,而缺乏形象生动的人物,缺乏直面存在的追问。她浅表化的叙事展现了各民族的习俗、仪式,但描写偏向于外部生存环境,没有向内挖掘,很少深入到人与人之间的道德伦理冲突,未能触及此时此地、此情此景中人物内心深处的挣扎和精神疑难,是浮光掠影式的。通篇读来,只觉群像混杂,如皮影戏一闪而过,似影像般飘乎不定,几乎没有一个立体丰满的人物,且很多人物像是被作者隔空牵线、随意控制的木偶,没有属于自己的语言、表情、动作、思想、神态和悲欢喜怒,更遑论独立生命与独特个性。
此外,不同民族文化的融合与对抗,在现代化进程中无处不在。在多民族文化的碰撞、交融中,与族群分离的撕裂感,与民族文化断裂的疼痛感,时时折磨着个体的身体、心灵。和晓梅的另一篇小说《未完成的成丁礼》中,“威廉”就承受着这样的苦难:“威廉,人们喊着这个来源蹊跷的名字时不同程度地感受到一种深长的意味,来自异域,来自不可知的遥远,来自人的最初记忆,它们蛰伏不醒,仿佛活在漫长的冬天。……和他的母亲一样,威廉学会了忘记。地铁呼啸而过,威廉面向窗户的脸也转瞬即逝。他的手仿佛触到了无处不在的细小沙尘,但他面无表情,心若止水。”作为一名纳西族作家,和晓梅对自身存在、自己民族境遇的敏感、关怀是超乎常人的,如何在写作中呈现当下处境?又如何超脱自身的民族局限,在人的意义上探索存在的真相?
像卡夫卡、马尔克斯等作家,他们把人置于非人的境遇中来写,反而能够把人内心中的隐秘事物逼现出来。和晓梅恰恰忽视了这一点,她的作品没有心灵揭秘、命运呈现,也未能创造出让人亲历其中的场域。宾玛拉家族、威廉都是作者生命的表达形式,但是,比之沈从文、张承志、阿来创作少数民族文学的深入、深刻,和晓梅小说缺乏深厚的历史感,缺乏雄阔的生命气象,缺乏从某个高度去发现、挖掘自己民族传统中内在因素的意识、视野和思想能力。
对于自小受汉文化熏陶长大的我们,与少数民族作家的情感、思维、意识多少有一些隔膜。也许正是因为隔膜,笔者不能切身理解其作品内蕴,感受其写作的艰难,读后才会有上述粗浅断语。但这也引出两个同时并存、值得思考的问题,从评论者的角度看,面对少数民族作家作品,是选择沉默,还是尝试摒弃成见,打破思维模式,与作家作品实现较深层次的对话、交流?从作家的角度说,如何超越玄炫的猎奇色彩,处理具有资源优势的故事、题材,如何挖掘文学更深邃的内部空间,呈现更为丰富、动人的艺术世界,使作品真正向读者敞开?
记得当代学者陈思和教授曾呼吁,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解读,应该由本民族的作家和学者来完成。的确,这是比较理想的创作批评状态。若由具有本民族传统、对本族文化怀有热烈深沉感情的评论家来解读,或许能将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民族性格、深层意蕴阐释得更到位。本民族批评家易于“入乎其内”,若亦能“出乎其外”,对作家作品得失成败的判断就更准确了。
(作者系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文学博士)
责任编辑:杨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