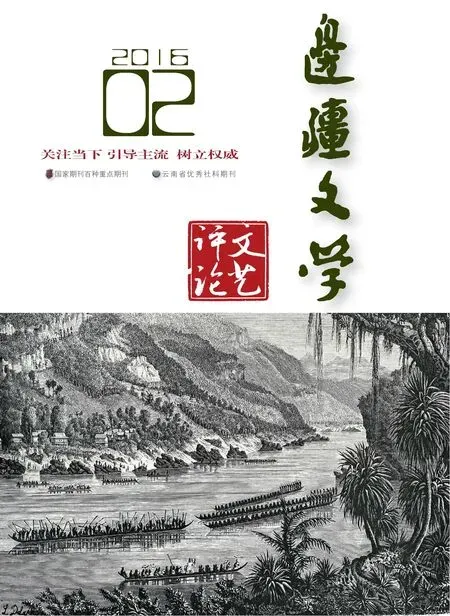独特地域下的女性书写
——以汪曾祺《大淖记事》为例
◎杨 雨
独特地域下的女性书写
——以汪曾祺《大淖记事》为例
◎杨 雨
汪曾祺先生创作的《大淖记事》,给我们展现了一幅充满田园牧歌式的生活画面,给当时的文坛带来了不小的震动。在作品中,作者以一群生活在大淖东头的女性为表现对象,用充满诗意的语言表现了她们对生活的乐观心态。小说中所表现的人物是一群有血有肉的,敢爱敢恨的普通劳动人民,作品写出了她们的勤劳和勇敢,同时,对她们在生活中所谓“有伤风化”的行为也进行了肯定性的描述。经历了“文化大革命”洗礼之后,作家们都不同程度地对“文革”期间的错误进行了反思,“文革”期间文学中失掉的人性,成为这一时期的重点表现对象。《大淖记事》是汪曾祺先生为我们展现的一幅充满生活情调的民间画卷,而作品背后所蕴含的深层意蕴,无疑是《大淖记事》最有魅力的书写。
一、女性书写界定
女性书写作为伴随着女性主义崛起后的一种书写方式,它本身是对女性本体存在的确认,同时也是对以男性主导下形成的话语权的挑战。在以男性为主宰的社会中,男性通过各种途径获得各种生存的话语权,使男性社会活动中形成的价值判断成为左右社会的价值判断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对女性具有压迫性的“父权制”。“父权制”确保男人对女人实行统治的各种制度及相应的价值观念,父权制是普遍的、无所不在的,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中,并非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妇女的解放并不是国家在法律上承认妇女的权利后就能实现,也不是消灭了资本主义制度就自然完成,而是要在一切领域、一切社会体制中改变男女之间的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1]“父权制”使男性在社会及家庭中占有绝对优势,男性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制定出一系列能够体现自己意志的,能够使所进行的活动顺利完成的规则。这些规则,对于男性来说,可以以性别优势,顺理成章地成为规则的制定者和裁判者。而作为弱势群体的女性,只能作为男性社会下的附属品,既没有参与男性活动的权利,也没有切实可行的维护自身合法权利的途径。
由此可见,男性主宰下的社会对女性带来的压迫是无所不在的,为此,女性的反抗在男性建构的话语体系下显得富有挑战。女性文化运动的方向,不是要向男性看齐,而是要认清自身的女性品质——被男性文化压制、排斥了的“女人性”。[2]西美尔认为,女性“更倾向于献身日常要求,更关注纯粹个人的生活”。[3]这样的书写模式在林白、陈染等作家的作品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女性书写更关注女性的主体性建构,用自身的体验和感知创造一种有别于男性眼中的女性形象。
同样,男性作家笔下也表现出类似的女性书写,就汪曾祺先生的《大淖记事》来说,他对女性的书写没有女性作家那样的激进和具有批判性,他将女性置身于作家创造的美的世界中,通过女性形象的生动塑造来表现出男性作家笔下女性的生活状态。自古以来,生活于以男性为主导力量的社会中,女性都在以自身的生存状态表现出对男权社会的反抗,只是在中国独特的文化背景下,这样的反抗是不自觉的。汪曾祺将《大淖记事》的背景设置在一个远离喧嚣的乡村世界,目的是通过乡村世界的宁静和淳朴,将人生存的原本状态还原出来。通过一个远离社会主流的生存环境,使女性对欲望的追求合理化,其人性美的创作倾向得到彰显。作家将一系列女性的生存状态置于一个没有道德礼教束缚的世外桃源中,透过女性的“男人化”书写,张扬了女性的主体性,使男性的主体地位被架空。
二、女性书写的独特性体现
(一)女性书写中的男性缺场和女性独特性的表现
在《大淖记事》的女性书写中,男性的存在是被刻意消解了的,被置于一种可有可无的状态。正如文章所言:
“这里的姑娘媳妇也都能挑。她们挑得不比男人少,走得不比男人慢。挑鲜货是她们的专业。大概觉得这种水淋淋的东西对女人更相宜,男人们是不屑于去挑的。”这样的描述,无疑是把女性“男人化”,通过女性“男人化”的书写方式,把男性在社会中的支配地位架空,以达到解构男权社会的目的。又如:“她们像男人一样的挣钱,走相、坐相也像男人。走起路来一阵风,坐下来两条腿叉的很开。……打起号子来也是‘好大娘个歪歪子咧!’——‘歪歪子咧……’”。
在以男性为主导力量的社会中,女性的主体性总是被忽略,不被社会予以重视,而男性的主体性却与社会生活融为一体,制约和影响着社会中的所有活动及其形成的后果。《大淖记事》对女性的“男人化”书写,打破了男性在社会活动中的主体地位,架空男性主导权的同时,使女性的强势面得到体现。当然,汪曾祺也注意到了女性所具有的独特性:“这些‘女将’都生得颀长俊俏,浓黑的头发上涂了很多梳头油,梳得油光水滑(照当地说法是:苍蝇站上去都会闪了腿)。脑后的发髻都极大。发髻的大红头绳的发根长到二寸,老远就看到通红的一截。她们的发髻的一侧总要插一点什么东西。”女性所具有的“女性美”在作品中也得到了足够的重视。小说通过作品中的男性缺场和女性具有的独特美的书写,颠覆了以男性主宰社会的传统观念,消解男性主体地位的同时,使女性的主体性得到彰显。
(二)对“卖弄风情”的独特叙述
独特的地域和乡土风情,使女性具有了彰显女性本色的舞台,通过对女性形象的细致且传神的刻画,使女性美在作品中得到表现。尤其是巧云形象的塑造,成为表现女性美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作品以充满乡野气息的大淖,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作为女性本该有的生活状态:“这里人家的婚嫁极少明媒正娶,花轿吹鼓手是挣不着他们的钱的。媳妇,多是自己跑来的;姑娘,一般是自己找人。她们在男女关系上是比较随便的。姑娘在家生私生子;一个媳妇,在丈夫之外,再‘靠’一个,不是稀奇事。这里的女人和男人好,还是恼,只有一个标准:情愿。有的姑娘、媳妇相与了一个男人,自然也跟他要钱买花戴,但是有的不但不要他们的钱,反而把钱给他花,叫做‘倒贴’”。作者以男权社会下形成的言说方式。表现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该有的与传统女性不一样的生存状态:她们像男人一样会爆粗口,享受着劳动带给她们的快乐,无拘无束,毫无顾忌,把“小家碧玉,大家闺秀”的古训亵渎得一文不值。除此之外,她们在男女关系的自由,也使传统的婚嫁习俗彻底无用:媳妇不用媒人说媒,自己便会跑了来,可以在家生私生子,即便结了婚,在外头还可以靠一个男人,管他们要钱花,或干脆给他们钱花。诸如此类的叙述,作者从男性的视角出发,将本该属于女性的权利交还给女性。一改往昔女性处于被压迫、被附庸的局面,使女性从传统的贞洁观念中解脱出来,对自己的身体享有支配权,即以情愿的方式选择伴侣。私生子、出轨等被看作是女性身上最肮脏、最邪恶的代名词,使诸多女性成为贞洁观念的殉道者,按男性社会赋予她们的“贞洁”苦苦度日,而男性则可以为所欲为。汪曾祺通过女性生存状态,将女性在男权社会下享有的权利获得了实现。甚至作者自己以叙述者的口气说:“因此,街里的人说这里‘风气不好’。到底是哪里的风气更好一些呢?难说。”
作品成功塑造了巧云这一女性形象。在她身上,我们看到了作为一个女性本该具有的“女性之美”,这也使得她成为众多男子追求的对象,作品中的巧云,已然实现了女性在男女关系上由被动转为主动的颠覆。巧云与十一子的爱情承续了“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古训。不同的是,作品中的巧云对自己身体的认知已摆脱了传统观念的束缚,成为了一个具有女性意识的新女性:内心深爱着自己的恋人,却能把自己的身体交给别的男人,这本身就是对女性“贞洁观念”的挑战。在特定地域下形成的女性意识,是一种男性视角下的女性书写方式,而作为巧云来说,通过支配自己的身体,达到自己对欲望的渴求。
女性通过打扮自己,让自己从外表看起来美丽动人;通过肢体语言和妩媚动作的展现,让女性在近似游戏的状态中使男性沉浸在对异性的渴望当中。“一个东西之所以对我们来说充满魅力,令我们渴望,经常是因为它要求我们付出一定代价,因为赢得这个东西不是不言而喻的,而是需要付出牺牲和辛劳才能成就的事情。这种心理转变的可能性导致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发展成了卖弄风情的形式。”[4]的确,女性越是徘徊于由肯定与拒绝形成的中间状态中,越发使男性对女性具有好感,越能在两性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女性通过移开注意力,从事其他活动,使关注者(男性)感觉到她的美无处不在,以至于让追求者甘心徘徊于其左右,或甘心为其承受一切。
(三)男性社会下性别的相对与绝对
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两类男性:一类是以代表了正义和道德的锡匠群体,他们秉持着男性社会的道德准则,以“仁义”作为做人行事的准则。另一类是一群住在炼阳观里的水上保安队员,他们虽担负着保卫大淖水上安全的责任,却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作者之所以要安排这两类截然相反的男性形象,一方面是在书写男权社会下男性的生存状态,强调对正常秩序的遵守和对责任意识的担当。另一方面,也在强调作为一个普通人所该有的生存状态。以老锡匠为代表的锡匠群在小说始末都在坚守着人所该具有的道德准则。但另一类男性代表刘号长之流,他们虽然在人欲上体现出不懈的追求和敢于实现的勇气,可是,男权社会下形成的痞子习气,使他们在犯了大错后选择了逃避,暴露男性社会下男人的虚伪和懦弱。小说中,笔者看到的男性是一个逐渐被弱化的男性,虽然责任意识的强调在作品中有所体现,但这种意识是被弱化的,在其背后隐喻着作者对女性意识的彰显。
女性形象,不论是作为特殊环境下的女性团体,还是作为以巧云为代表的具有女性意识的新女性,她们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中,彰显出作为一个女性本该有的“女人性”。她们享受着性别带给她们的优越感,能够按自己的意愿去做自己想做之事。但是,我们还必须考虑到作者设计十一子和刘号长冲突的深层内涵:巧云内心深爱着十一子,作为报答,只想把自己的身子交给十一子。可是,巧云的身子却偏偏给了一个带有痞子气的男人,巧云表示接受的同时,这种身体上的交易维持了一段时间。当然,巧云并非毫无顾忌,由于对十一子的爱恋,使她产生了深深的愧疚之心。最终导致了十一子与刘号长的直接冲突。
女性的人性美,主要通过其身上具有的“女人性”体现出来,而且,在社会生活中,女性对女性的认知不会因为何种原因而遭到质疑。但是在男性社会中,女性是被制造出来的。因此,社会价值判断倾向于男性一方就变得不那么难以理解。笔者认为,汪曾祺笔下的女性书写是以男性的眼光来审视男性社会中女性的生存状态,无论是对于独特背景下的女性群体的书写,还是作为独特个体的女性书写都是如此。巧云和十一子的结合本是顺理成章的事,但虽然心灵的相通,也没能实现巧云的心愿(将自己的身子交给十一子)。女性意识使巧云有权利支配自己的身体,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但是,传统观念始终在巧云的内心回荡,使她在与刘号长的私会中对十一子心怀愧疚。当十一子与巧云的事被刘号长得知后,十一子对巧云发自内心的爱却成为了男女关系上的受害者。由此可见,在肯定女性勇于追求自由,敢于挑战男性权威的过程中,作家还是持男性立场,肯定男性社会中女性应有的生存状态。
综上所述,《大淖记事》的女性书写,始终以男性视角下的女性生存为关照对象,肯定女性在男权社会中该具有的女性生存权利。通过作品中男性形象和女性形象的对比,意在对男性社会中的男性生存状态的贬抑,以此达到张扬女性主体性的目的。当然,作家在对女性书写时加入了主流价值判断的因素,使笔下的女性去掉了女性书写中本该具有的激进和挑战性,而变得温婉和富有人文关怀,这也是汪曾祺笔下女性书写的独特之处。
三、结论
众所周知,作家的创作和时代背景有着深刻的联系,也就是说,文本的产生与社会是分不开的,它间接地反映了时代思潮和社会走向。“文革”十年的冲击,将人本该具有的自由抹杀殆尽,当人们沉浸在对“文革”进行反思时,汪曾祺却为我们创造了一个远离喧嚣的乡村世界,并且表现了一群不受传统道德束缚,自己对自己具有绝对掌控权的女性形象,这除了响应当时提倡“人性复归”的呼声,还体现了作者对现实生活的逃离。“大淖”是一个没有被道德文化熏染过的乡村世界,在某些布道者眼中,这种生存状态是一种有伤风化的,不道德的,因为作品中的“大淖”女人所具有的种种“不良风气”。但是,作家的创作目的并不在于对这一种风气的展览式的赏玩,而是要通过这些充满野性的女性表现一种与传统观念迥异的生存状态。即没有礼教的束缚和三纲五常的硬性规定,没有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婚嫁习俗的制约。她们可以仅凭自己的意愿享受女性所该有的快乐和自由,而不用去顾及旁人的看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种倾向可视为80年代“尚古主义”思潮的思想渊源之一,这一思潮“反对现代文明对人性的压抑和束缚,转而崇尚古代社会以及现代社会中相对落后地区的生活状态和民风民俗,赞赏那种状态中人们无法无纪、无拘无束、为所欲为的生活方式,尤其是两性关系上的自由放纵,以为这才是没有受到现代文明污染的人性的本真”。[5]
汪曾祺以男性的视角对男权社会下女性生存状态的书写,摒弃了以往男性作家眼中表现女性的传统套路,用温婉、平和的方式书写女性在男权社会下的生存。这种独特的书写方式显然是对长期积淀下来的男性对女性书写方式的反叛,这种反叛还可以在汪曾祺此前所创作的作品中得到印证。作家将另类女性作为书写对象,放弃当时大部分作家所坚守的创作理念,这种创作姿态是作家对主流创作意识反叛,在创作上摆脱的公式化倾向。从隐性层面看,《大淖记事》是作家对主流意识介入文学创作的一次实践,为当时的读者打开了一个全新的文学世界。
对于当下流行的下半身写作、身体写作等以女性视角来对女性本体的书写,以女性本身具有的独特性将女性的生存状态赤裸裸地呈现给世人,通过对女性本体的认知达到对男权社会的解构,这从女性解放的层面来说具有进步意义。对女性意识的张扬和对“女人性”的认知,使女性书写成为一道独特的文学风景线。但是,文学创作一旦与社会环境脱离,势必使文学叙述走向琐碎化、媚俗化。作家作为社会中的人,应该对社会的观察采取理性的方式,若文本脱离了社会,作家也会陷入到无话可说的地步。
《大淖记事》的女性书写方式,可以对当下盛行的女性主义写作起到一定的引领作用,用理性的眼光看待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生存状态,不但可以使女性本身的“女人性”得到更好的体现,也可以使女性书写更具审美深度。
【注释】
[1]诸慧《挑战男权传统:来自女性主义者的声音》,复旦政治学评论·2005年第00期,第225页。
[2]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4月第1版,第10页。
[3]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4月第1版,第10页。
[4]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4月第1版,第158页。
[5]王澄霞《〈大淖纪事〉人性解放主题的当代反思》,中国现代文学丛刊·2012年第五期,第208页。
(作者系云南民族大学2015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研究生)
责任编辑:程 健
——细读《孔雀东南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