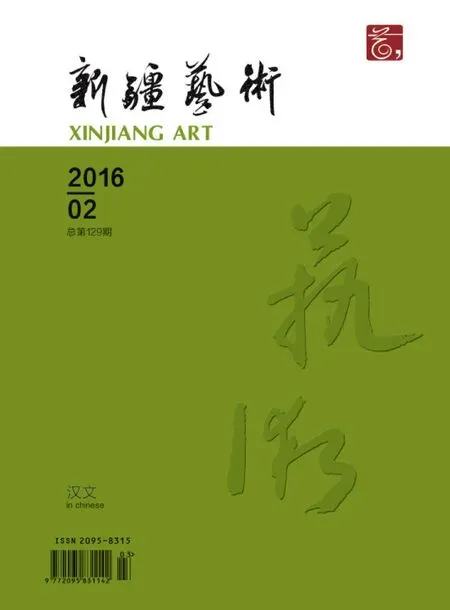文学理论的视觉文化转向
□赵勇

文学博士赵勇先生
“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①这是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在1978年做出的判断。30多年之后,我们这里也应验了他的这一判断。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已大踏步地走进一个视觉文化时代:几乎所有的文化产品都围绕着视像化展开,视觉美学、眼球经济业已成为文化生产的内在逻辑。而在此过程中,文学的生产与消费也成为视觉文化的一部分。既如此,这个视觉文化究竟是什么文化?视觉文化与文学的关系几何?文学生产在视觉文化时代已然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文学理论该如何应对这种变化,又该如何做出调整?所有这些问题正是需要我们加以面对的。
一、视觉文化是什么文化
虽然关于视觉文化的论说已有许多,但为了更好地分析视觉文化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对视觉文化做出相关的梳理与界定依然是必要的。
从一般的意义上看,视觉文化对应于印刷文化,是当代文化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之后所形成的文化形式。在哲学界和美学界,与视觉文化来临相关的另一表述是“图像转向”(pictorial turn),以此对应于当年的“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②而结合西方学者关于视觉文化问题的相关思考,视觉文化又可在如下层面上加以确认。
首先,视觉文化是一种后现代文化。米尔佐夫(Nicholas Mirzoeff)认为:“印刷文化当然不会消亡,但是对于视觉及其效果的迷恋(它已成为现代主义的标记)却孕生了一种后现代文化,越是视觉性的文化就越是后现代的。”又说:“后现代主义标志着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视觉图像以及那些并不必然具有视觉性的事物的视觉化在戏剧性地加速发展,以致图像的全球流通已经达到了其自身的极致,通过互联网在高速运转。”③无独有偶,艾尔雅维茨(Aleš Erjavec)在论述视觉文化时也指出了它与后现代主义的关联:“后现代主义最突出的特点是从视觉出发。它是一种图像和图画不仅相互纠缠、而且可以互换的视觉文化。”“在后现代主义中,文学迅速游移至后台,而中心舞台则被视觉文化的靓丽辉光所普照。”④
如果从文学的角度出发,以上两位论者的思考似可延伸出如下理解。在视觉文化时代,文学从总体上看已经处于一个边缘的位置,这不仅是因为文学的可视性差或者简直就不存在什么可视性(所谓的“文学形象”其实不过是我们借助于自己以往的视觉经验并通过想象在头脑中形成的一种幻象,所以才有“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之说),而且也因为视觉文化的传播载体(如电影、电视和互联网等)要比印刷媒介更直观、迅捷、方便,从而形成了一种媒体霸权,并对印刷媒介构成了一种压制和排挤。在这个意义上,视觉文化的后现代性其实意味着文学的没落,它逼出了文学的前现代性或古典性。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曾经扮演过第一小提琴手的作家与文学在视觉文化时代已经易位。
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在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格局中思考文学所发生的种种变化。一般而言,模糊人物性格,淡化故事情节,注重描摹人物的精神世界,努力挖掘人物的潜意识心理等等,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对此,法国新小说作家兼理论家萨洛特(Nathalie Sarraute)甚至指出:“现在看来,重要的不是继续不断地增加文学作品的典型人物,而是表现矛盾的感情的同时存在,并且尽可能刻划出心理活动的丰富性和复杂性。”⑤如果转换到视觉文化的语境中来加以思考,我们可以说现代主义的文学策略努力淡化的是小说的可视性,增强的则是小说的可思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文学策略是与视觉文化背道而驰的,而因此写就的小说也给视觉文本的转换带来了极大的难度。例证之一是,从《永别了,武器》到《老人与海》,海明威的全部小说几乎都改编成了电影,但据茂莱(Edward Murray)分析,这些改编基本上都是失败之作。⑥而在我看来,失败的原因之一便在于海明威小说的可视性差而可思性强。
但是,后现代主义的文本策略除了大量使用戏仿、反讽、拼贴、征引等多种技巧外,还在某种程度上接通了传统小说的写法,把故事性强,情节紧张有趣等等放在文学写作的重要位置,从而让小说具有了更多的可视性而非可思性。这种小说的后现代性或许可被看作是对视觉文化的一种有意无意的迎合。当我们说后现代主义小说变得更“好看”或“可读性”强时,这自然是对现代主义的反动,因为它降低了理解的难度,去除了某种深度模式,进而完成了从“思”到“视”的转移。
其次,视觉文化也是一种消费文化。可以从多个角度进入到有关消费文化的理解之中,若从视觉文化的角度考虑,视觉文化与消费文化的连接点有二:其一是视觉形象,其二是视觉消费。
为了让所有的一切具有可消费性,消费社会采取的基本手段是让其产品统统经历了一个物化、商品化、形象化的过程。在这里,商品物化仅仅使其产品具有了消费的可能,而要刺激人的购买欲与占有欲,则必须让其产品形象化。这样,制造视觉形象便成为消费文化生产的内在逻辑。杰姆逊(Fredric Jameson)曾经论述到语言文字在广告产品中的Logo化倾向,⑦这既是对文字的物化处理,也是把字词转化成一种视觉形象的过程。唯其如此,才会出现弗洛姆(Erich Fromm)所说描绘的那种情景:“一瓶可乐在手,我们喝的是漂亮的少男少女在广告上畅饮的那幅景象,我们喝的是瓶上那条‘令你精神百倍’的标语。”⑧在这里,商品的视觉形象虽然造成了能指与所指的彻底断裂,但这也恰恰是消费文化生产的秘密。
如果说视觉形象涉及到的是生产环节,视觉消费则直接与消费者有关。韦里斯(Susan Willis)指出:“在发达的消费社会中,消费行为并不需要涉及到经济上的交换。我们是用自己的眼睛来消费,每当我们推着购物小车在超市过道里上上下下时,或每当我们看电视,或驾车开过广告林立的高速公路时,就是在接触商品了。”⑨这里把视觉消费界定为仅动用眼睛而不动用钱袋的消费行为,固然也可算作一种重要的消费文化现象。但在我看来,视觉消费的真正要义在于它不过是生产-消费活动中的一个中间环节,其最终目的还是要把那种通过眼睛的象征性消费转化为一种通过行动的实体性消费。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的短篇小说《马科瓦尔多逛超级市场》就很能说明这一问题。受广告视觉形象的召唤,马科瓦尔多一家人进入了超市,而他们目迷五色的过程便可看作视觉消费的过程。但他们终于没能止于视觉消费,而是把货架上的许多商品装满了自己的手推车,从而把过眼瘾的视觉消费转化成了实实在在的购买行动。只是当他们意识到自己囊中羞涩无钱购物时,他们才从那种迷醉状态中惊醒,然后选择了仓皇出逃。⑩这篇小说可以看成视觉消费转化为实际消费的经典案例,其中隐含的视觉消费的逻辑走向不能不让人深长思之。

第三,视觉文化还是一种大众文化。根据笔者的梳理,在西方世界,大众文化经历了从近代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到现代大众文化(mass culture)的演变过程。⑪这里我想进一步强调的是,在通俗文化时代,由于媒介载体主要是印刷媒介,所以通俗文化虽然已经出现了洛文塔尔(Leo Löwenthal)所描绘的情景——犯罪、暴力与感伤成为结构小说情节的重要元素,作家甚至“像好莱坞影片中所表现的那样”,“纤毫毕现地细致描绘攻击、暴力、恐怖的场景”,⑫但与现代大众文化相比,通俗文化毕竟还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而近代通俗文化之所以能演变成现代大众文化,除了其他原因之外,电子媒介的介入以及对相关产品的再生产与再加工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波兹曼(Neil Postman)之所以会把美国19世纪以前的年代称为“阐释年代”,而把后来的年代称为“娱乐业时代”,关键在于“从17世纪到19世纪末,印刷品几乎是人们生活中唯一的消遣。那时没有电影可看,没有广播可听,没有图片可参观,也没有唱片可放。那时更没有电视。公众事务是通过印刷品来组织和表达的,并且这种形式日益成为所有话语的模式、象征和衡量标准”。⑬转换到传播媒介的层面思考这一问题,“阐释年代”向“娱乐业时代”的转变其实就是印刷媒介霸权向电子媒介霸权的转变。而在此转变中,娱乐成了电子媒介产品的重要内容。
供人娱乐也正是现代大众文化的主要特征。而电子媒介与娱乐内容的结合,则是让大众文化充分视像化了。换句话说,在今天,越来越多的大众文化内容恰恰是通过视觉文化的形式体现出来的。而视觉文化对大众文化的包装与制作除了让大众文化变得更加“好看”之外,还降低了进入大众文化的门槛,也进一步让大众文化变成了一种轻浅之物。在印刷文化时代,一个人即使要去接触赵树理的通俗小说,他也必须具备起码的识文断字的能力。但在视觉文化时代,诉诸于视听感官的大众文化却已不需要阅读训练的武装。波兹曼说:“看电视不仅不需要任何技能,而且也不开发任何技能。”⑭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指出:“一个人没有必要在看‘复杂节目’前,一定要先看‘简单的’节目。一位只看了几个月电视的成年人与看了几年电视的成年人对电视的理解可能相差无几。”⑮他们说的便是这个道理。
另一方面,大众文化本来就不是厚重之作,而经过视觉文化的生产之后则又变得更加轻浅单薄了。事实上,无论是精英文化还是大众文化,它们一旦被视像化,都必然会经历一个从深刻到肤浅、从复杂到简单的叙事转换。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电影不是让人思索的,它是让人看的”;⑯“电视之所以是电视,最关键的一点是要能看,这就是为什么它的名字叫‘电视’的原因所在。人们看的以及想要看的是有动感的画面——成千上万的图片,稍纵即逝然而斑斓夺目。正是电视本身的这种性质决定了它必须舍弃思想,来迎合人们对视觉快感的需求,来适应娱乐业的发展。”⑰例证之一是《百家讲坛》的节目虽然在一段时间内做得非常成功,但几乎所有的主讲人都遵循着“把传统文化通俗化、历史人物故事化、故事情节传奇化”的叙述套路,而最终所形成的结果也无非是“把深刻的思想肤浅化,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⑱出现这种局面,显然与迎合视觉文化的生产特点有关。

以上,笔者分别从后现代文化、消费文化、大众文化的层面分别释放了视觉文化的内涵。那么,做出如此分析又有什么意义呢?大体而言,我想由此说明如下问题。第一,视觉文化并非仅仅就是与视觉相关的文化,在其背后还隐藏着许多常常被人忽略的意识形态内容。所以,视觉文化表面上是眼睛美学,实际上是生产方式的革命;表面上是生产方式的革命,实际上又是生产者与消费者价值观的潜移默化。第二,由于后现代文化、消费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基本对应项分别是现代主义文化、审美文化和精英文化,那么视觉文化的来临一方面意味着现代主义文化、审美文化和精英文化的衰落,另一方面也意味着这些文化要想继续生存,不得不或者借助于视觉文化为其张目,或者寄生于视觉文化为其整容。文化生产因此呈现出更加迷乱的格局。第三,视觉文化最重要的对应项是印刷文化,而文学恰恰是印刷文化的产物。当视觉文化来势汹汹甚嚣尘上时,文学也不可能不受到冲击与影响。那么,在视觉文化时代,文学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二、视觉文化时代的文学生产
视觉文化时代的文学生产涉及到的问题很多,本文显然无法充分展开。这里我只是想择其要者,分析视觉文化怎样影响到了文学的内部构成。而由于在视觉文化的内容中,电影电视与文学的关系最为密切,所以下文中我也将着重思考影视对文学的影响。
电影的发明时间是1895年。在电影未出现之前,文学的生产相对比较单纯。那时候,作家虽然会与书商、出版商交往,却不可能与电影导演往来。文学生产不存在影视改编的问题,也不存在受电影语言、电影叙事和电影技巧的影响问题。然而,自从有了电影之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在《电影化的想象——作家和电影》一书中,茂莱通过大量的事实举证与理论分析,指出了20世纪重要的戏剧作家、小说家与电影交往的情况。而这种交往又可分成两个方面:其一是电影对文学作品的改编,其二是电影对作家写作的影响。对于前者,茂莱的分析令人绝望:那些大作家的作品改编成电影之后几无成功之作;对于后者,他则借宝琳·凯尔之口指出了如下事实:“从乔伊斯开始,几乎所有的作家都受过电影的影响。”⑲
中国当代作家与影视的大面积交往是从1990年代开始的,而这个年代也恰恰是视觉文化在中国开始走向兴旺发达的年代。在这种交往中,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二者合作的基础。众所周知,1980年代中后期,一方面是第五代导演集体出击的时候,另一方面也是先锋作家横空出世的时候。而在80年代的文化氛围中,第五代导演的作品与先锋作家的小说在精神气质、叙事模式等方面显然存在着一种同构关系。于是,当导演找到作家时,气味相投或惺惺相惜便成为其合作基础。那一时期张艺谋与作家的交往就可以说明这一问题。
据莫言讲,《红高粱家族》之所以能吸引张艺谋,并非里面的故事很精彩,而是“小说中所表现的张扬个性,思想解放的思想,要轰轰烈烈、要顶天立地地活着的精神打动了他”。而莫言之所以会把《红高梁》交给张艺谋拍,“是考虑到小说里面的高粱地要有非常棒的画面,只有非常棒的摄影师才能表现出来。因为在建构小说之初,最令我激动不安的就是《红高粱》里面的画面,在我脑海里不断展现着一望无际的高粱地。如果电影不能展现出来,我觉得不成功。我看好张艺谋”。⑳刘恒能够与张艺谋合作并成为《菊豆》(1990,改编自他自己的中篇小说《伏羲伏羲》)、《秋菊打官司》(1992,改编自陈源斌的小说《万家诉讼》)的编剧,是因为张艺谋“很有艺术才华,是‘第五代’导演里的佼佼者”,他觉得他遇到了一个好导演。㉑陈源斌的《万家诉讼》面世后,有三家电影制片厂都看中了这篇小说,想改编成电影。但“陈源斌认定只有张艺谋才能理解自己的这部小说,不是张艺谋当导演,他宁可不接受”。㉒而余华则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为什么“张艺谋是中国最好的导演”,因为“他给钱特别痛快”。——当年《妻妾成群》被改编成《大红灯笼高高挂》,因张艺谋给了苏童4000元的授权费,苏童“笑得嘴都是歪的”。而1993年张艺谋找余华改编《活着》时,给出的授权费是2.5万元,后来还主动加到了5万元。㉓
现在看来,八、九十年代之交的一些作家确实是乐于与张艺谋合作的,而乐于合作的动因除了张艺谋出手大方外,更主要是因为作家对张艺谋有一种信任感。而这一时期,张艺谋本人借80年代文化热潮之余威,一方面扮演着文化英雄的角色,另一方面也努力把他执导的电影打造成了一种精英文化(艺术片)。这一时期的作家本来就有着某种精英文化的诉求,他们也就更希望其作品借助于精英化的形式进一步传播。于是在与导演的合作中,他们不仅不会有掉价之感,反而会觉得那是自己的一种机遇和荣耀。
或许正是基于这一背景,才在1993年发生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文化事件:张艺谋同时约请苏童、北村、格非、赵玫、须兰、钮海燕等作家撰写《武则天》的小说,以为他筹划开拍的电影《武则天》做改编底本。而六位作家也欣然领命,在一年左右的时间内纷纷完成了导演布置的写作任务。虽然张艺谋的拍摄动机非常隐秘——想让他的心上人巩俐当一次女皇,㉔六作家的写作因此也就多了一层反讽意味,但是今天再来面对这一事件,我们或许已可以拋开这些八卦因素,而把它看成一个作家与影视关系的转折点,其值得深思者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伴随着市场大潮的冲击,中国当代文化从1992年也开始了它的转型。伴随着这种转型,作家、导演的角色扮演与生产方式也开始发生变化。如果说在此之前,作家还不同程度地扮演着“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角色,那么从此之后,王朔所谓的作家就是“码字的”之观念开始深入人心。作家从80年代的文化精英变成了一个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谓的文学“生产者”。与此同时,电影导演也脱下了文化英雄的战袍,开始充当昆德拉(Milan Kundera)所谓的“意象设计师”。于是,六作家与张艺谋的合作便不再可能是精英文化之间的对接,而应该看作大众消费文化之间的联手。文学写作则不再遵循其自主的艺术原则,而是开始追随他律的商业原则。六作家走向张艺谋的商业“召唤”中,实际上可看作当代文学市场化的一个重要信号。
第二,对于其他作家来说,六作家(当然也需要加上莫言、刘恒、余华、陈源斌等作家)与张艺谋的合作应该是一次重要的示范。它意味着一个作家若想迅速地声名远播,为导演写作并让其作品影视化,可能是一条终南捷径。与此同时,它也给后来者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作家与导演合作没必要半推半就,犹抱琵琶,而应该光明正大,明码叫价。梁晓声说,中国的前几代作家对“触电”的态度是既怕又想,“但是‘晚生代’们并不这么做作和暧昧。他们对‘触电’都怀有史无前例的高涨热忱。有时作品被高价买了版权还不算,还一定要亲笔改编为影视。所谓‘肥水莫流外人田’。他们都尽量脚踩两只船,生动地活跃于小说与影视之间。这使他们名利两方面获得快捷,并且受益匪浅”。㉕验之于不绝如缕的相关报道,梁晓声显然所言不虚。兹举一例,点到为止。2003年,《人民日报》曾有广西作家集体“触电”的报道,说的是广西作家与电影界亲密接触,频频“触电”成功,堪称“名利双收”。其中又数李冯的《英雄》、东西的《天上的恋人》、凡一平的《寻枪》和《理发师》、胡红一的《真情三人行》最具代表性。㉖而他们恰恰也全部是“晚生代”作家。作家“触电”如火如荼愈演愈烈,以致成了中国作协“七届九次”会议(2010年3月29-4月4日)的热点话题。㉗
第三,更值得注意的是如此合作给小说本身带来的影响。早在六作家与张艺谋合作之初,王彬彬就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为了能被张艺谋的法眼青睐,便须按张艺谋的趣味来写作,便须使作品尽可能地合张艺谋的口味。”由此而形成了文学写作的“张艺谋模式”,即“强烈的故事性情节性”,而故事情节“通常又具有强烈的暴力、性爱、色情色彩”。除此之外,由于巩俐在张艺谋电影中的重要性,所以“按照‘张艺谋模式’写小说,一个女性人物,而且是并非可有可无的女性人物,便是一项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对按这模式写作的人的一项起码的要求。至于在张艺谋约请下写作,小说往往便是主要写某个适合于巩俐扮演的女性了”。㉘今天再来重温这番思考,我们可以说当年的王彬彬已凭借其敏感意识到了作家与影视交往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为导演或影视写作,导演意图与影视逻辑也就必然会进入到小说的结构之中,进而影响或改变小说的内部构成。实际上,后来者与影视交往的情况也不断验证了这一判断。而六作家与张艺谋的合作不过是得风气之先,他们开启了一个小说写作影像化的时代。
那么,在小说的影像化时代,小说本身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概而言之,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思考。
(一)写作逆向化。在作家没有与导演和影视交往之前,小说写作无所谓正向逆向之分,但交往的结果却因此出现了小说写作的逆向化问题。所谓逆向化,即作家先是写出了电影剧本,然后才在电影剧本的基础上改写成小说。当今一些作家的“影视小说”(尤其是所谓的“影视同期书”)往往都是这种逆向写作的产物。比如,刘震云的小说《手机》与《我叫刘跃进》就是先有剧本,后有小说。但是对于这种做法,刘震云却为自己做了如下辩护:“现在有一个理论,先有电影剧本再有小说的话,小说会成为电影剧本的附庸,这证明以前这些作家对这件事情做得不是特好。”㉙“在剧本原创阶段,冯小刚的一些点子开阔了我的思路。在我写小说的时候,吸收了剧本阶段冯小刚的智慧,从这个角度说,我占了冯老师的便宜。小说虽然由剧本改编而成,但并不是剧本的简单扩充,也决不是电影的附庸。如果把电影当作素材,把剧本当作一次实验,小说就会在一个更高的台阶上。”㉚
不能说这种辩护没有道理,因为即便是“影视同期书”,由于作家写作水平、用心程度等等方面的不同,也存在着高下之分。比如,同样是先剧本后小说,刘震云的《手机》就比冯小刚的“首部长篇”(腰封广告语)《非诚勿扰》(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技高一筹。因为后者与电影几无区别,前者则在电影的基础上增加了第一章《吕桂花——另一个人说》和第三章《严朱氏》,这让小说稍稍有了一些纵深感。但即便如此,《手机》也存在着诸多缺陷,而无法成为一部优秀的小说。比如,小说第一章的文字占24个页码,第三章占33个页码,而第二章则占全书的194个页码(此处统计采用的是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的版本)。如果有人要为这种结构上的严重不对称进行辩护,或许可称之为“独具匠心”?而事实上,也确实有评论家把这种奇怪的安排称作是让人惊叹的“山形结构”。㉛但这种结构说白了其实很简单。因为第二章是电影着力表现的部分,所以在剧本写作阶段讨论得就充分,展开得也从容。第一、三章是为了写小说而加上去的内容,而又要赶在电影放映时同步推出,所以便写得匆忙,加得草率,甚至出现了一些低级错误(如第二章中严守一的奶奶是“小脚老太太”,第三章却变成了“大脚女人”,并因此围绕“大脚”设计出了一些细节㉜)。所以,这里表面上是一个结构问题,实际上却是电影化思维或视觉思维给小说带来的一个后遗症。

这就不得不涉及文学艺术创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不同的文学艺术形式是否需要与之成龙配套的艺术思维方式?按照传统的文艺创作观,回答应该是肯定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说过:“艺术自有其奥秘,其叙事的形式完全不同于戏剧的形式,我甚至相信,对艺术的各种形式来说,存在着与之相适应的种种艺术思维,因此,一种思维决不可能在另一种与它不相适应的形式中得到体现。”㉝这也就是说,种种艺术门类如文学、绘画、音乐、电影等等均有其属于自己的思维方式。而具体到文学,作家甚至需要有更为精细的小说思维,戏剧思维,散文思维和诗歌思维。因此,当写作逆向化之后,就不单单是一个剧本改写成小说的技术问题,而是意味着影视剧的剧本思维(视觉思维)进入到了小说的内部构成之中,进而改写或破坏了小说思维,小说也因此失去了小说的魅力,变得淡乎寡味。大概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布鲁斯东(George Bluestone)才说:“人们还没有充分地认识到,小说的最终产品和电影的最终产品代表着两种不同的美学种类,就像芭蕾舞不能和建筑艺术相同一样。”㉞茂莱也指出:“一个小说家为使他的作品在技巧上手法多样化而借助于电影化方法是一回事,如果他把小说电影搅混到如此程度,以致名为写小说而实际成品是电影剧本,那就是另一回事了。”㉟这里我把茂莱的说法调整为“名为写电影剧本而实际成品是小说”,同样也是成立的。实际上,在写作逆向化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的便是把小说与影视剧搅成一锅粥的情景,作家不再按照艺术思维规律办事,也对小说文体失去了起码的尊重。
(二)技法剧本化。作为一门叙事艺术和语言艺术,小说发展至今已形成了丰富的技法。戴维·洛奇(David Lodge)在《小说的艺术》一书归结出50种之多,便可见出小说技法的盛况。而种种所谓的“小说修辞学”,“小说叙事学”,其实又是对小说技法的理论提升和深度归纳。由于小说叙事运用了多种技法,我们甚至可以说当今的小说写作是一种富于难度的叙事艺术。相比之下,剧本写作则相对简单一些,这是因为复杂的叙事电影或电视剧既无法胜任,也容易吓跑观众。而对于许多剧本来说,除了必要的场景提示,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写好人物对话。有着丰富影视剧本写作经验的沃尔特(Richard Walter)说过:“正如我们强调的那样,影视剧本主要是由对白组成的。”“既然影视作家与对白关系密切,琢磨和运用语言的妙计和圈套就成了自然、正当的事情。”㊱既然剧本主要是写对话,那么小说技法的剧本化即意味着小说叙事的简化。

小说技法剧本化,其始作俑者或许可以追溯到王朔那里。当王朔的小说人物全部滔滔不绝仿佛得了“话痨”时,这固然可以理解为北京人的“贫”,或者理解为王朔拥有了一种口语化写作的快感之后语言释放的汪洋恣肆,但也必须指出,由于王朔的一些小说其实来自于相关剧本的改写,他又做过“国内最抢手的影视编剧”,㊲这样,剧本化的写作技巧,影视化思维也就不可避免地进入到了他的小说之中。如果说王朔还属于歪打正着,并非有意为之,那么随着作家与影视的亲密接触,如今已有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如此制作小说,小说也呈现出越来越浓的剧本化特征。有学者曾对刘震云的非剧本化小说《一腔废话》和剧本化小说《手机》做过如下统计分析:《手机》实际字数117302字,加引号的人物对话1458句,平均每80字中包含一句人物对话,其人物对话率是《一腔废话》的2.08倍。这一统计结果表明:“在影视剧制作的影响下,作为以‘陈述’为主的小说其艺术手段正在向‘展示’倾斜,而‘展示’正是影视戏剧的基本手段。”㊳而人物对话的增多也延续在刘震云的《我叫刘跃进》中。
从叙述学的层面考虑,小说去掉了描写的枝枝哑哑,主要以人物对话展开情节,或许有助于叙述的简洁。但问题是,当小说的环境描写、心理描写、肖像描写等等都被拿掉之后,小说的叙事也就变得扁平化了。而且如此操作,还会带来小说整体语言的退化。正是因为这一原因,刘恒才有了如此思考:“如果长期从事电影剧本的写作,也就等于长期处于忽略语言的那么一种状态,长此下去,作者的语言运用的能力便会衰退。等你返回身去再写小说的时候,有可能语言这个肌肉已处于萎缩状态,功力不足了。所以有很多人写电影剧本时常常是点到为止,把对话给它撩上,谁谁怎么说就完了,大不了再给人物带上点表情,别的任何描述性的东西都不要,我反对这样做。”㊴他之所以把剧本写成“文学剧本”而不是“电影剧本”,便是出于对语言退化的恐惧。但对于更多的作家来说,他们或许已把语言退化的结果体现在了小说的写作中。刘恒的这番说法其实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小说剧本化之后会给小说带来怎样的伤害。
(三)故事通俗化。为了谈清楚这一问题,有必要从赵树理的小说创作说起。为了达到“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的写作效果,赵树理在内容上增强了小说的故事性,因为“农民喜欢看有故事、有情节、有人物的作品”。㊵《婚》能够出版,不仅得益于彭德怀的推荐性题词:“像这种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而且还特意在封面上标注了“通俗故事”的字样。㊶“通俗故事”在当时已是赵树理小说的一个基本定位。另一方面,赵树理又在小说形式上把“可写性文本”变成了“可说性文本”,即他把作者/叙述者当成一个说书人,把他写成的小说当成一个可供说书人说唱的底本,从而把阅读置于一个“你说我听”的规定情境之中。㊷经过了这种从内容到形式的全方位改造,赵树理的小说才走向了通俗化之途。
我这里之所以重提赵树理,是因为影视化影响下的小说写作与当年赵树理的写作追求异曲同工。当赵树理把故事通俗化时,他面对的是“前现代”的听觉文化氛围,而他的写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听觉思维”驱遣的结果。当今天的小说家置身于“后现代”的视觉文化语境中时,他们动用了“视觉思维”,而最终所形成的小说叙事也依然是故事化、悬念化、通俗化和大众化。这种殊途同归一方面表明,赵树理式的“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很可能已置换成了今天的“老百姓喜欢看,商业上起作用”,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无论是听觉思维还是视觉思维,很可能都不是真正的小说思维。而前两种思维进入到小说的内部结构中之后,又会给小说带来某种损伤,并把小说置于一个尴尬的境地。
这里我们可以以莫言的《白棉花》为例略做说明。刊发于1991年的中篇小说《白棉花》原来并不在莫言的写作计划之中,只是因为张艺谋找上门来想拍一部大场面的电影,才有了这篇小说。作为一篇为导演而作的小说,莫言写作时的视觉思维是非常明显的,由此也带来故事通俗化,情节影像化等诸多问题。莫言后来在多处地方提到过这部小说所存在的问题,其中又尤以以下说法语重心长:
命题作文很难写,我也写过,但事实证明很难成功,而且永远也不会满意。《白棉花》是一个半命题作文,当时我和张艺谋一块讨论,他希望写农村大场面那样的故事。我说你在纱厂干过,我在棉花加工厂干过,在我们农村,和平年代里的大场面就是修水利,开山挖河,但这样的大场面在电影里很难实现,你现在没法组织几万人去挖一条大河;另外一个农村的大场面就是收购棉花,当时我们老家一个县就一个棉花加工厂,到了棉花收购的旺季,成千上万的棉农赶着车挑着担子,无数的棉花集中到一个地方,而且那个地方不像现在的仓库房子,是露天的,棉花堆得像山一样高,这个场面特别壮观。那时候张艺谋刚开始拍了《红高粱》,那个电影一出来,反响非常好。我对他说,你刚拍完《红高粱》,再拍一个白棉花,首先视觉上就有很强烈的反差。因为有事先商定的东西,写的时候就不知不觉地向故事性、影视性、画面跑,结果出来的小说不伦不类,剧本的要求也不够。㊸
莫言的这次经历让他有了如下反思:“写小说的人如果千方百计地想去迎合电视剧或者电影导演的趣味的话,未必能吸引观众的目光,而恰好会与小说的原则相悖。”“我认为写小说就要坚持原则,决不向电影和电视剧靠拢……越是迎合电影、电视写的小说,越不会是好的小说,也未必能迎来导演的目光。”“我的态度是,绝不向电影、电视靠拢,写小说不特意追求通俗性、故事性。”㊹可以把这种思考看作是一个误入迷途者的痛定思痛,也可以看作是一个成熟作家的理性选择。但问题是,当下的许多作家并不像莫言这样清醒,而是像美国的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那样,当他们认真关注着、深度介入着电影电视剧时,他们的“文学作品开始质量大降”,但他们不但浑然不觉,反而会像托马斯·沃尔夫那样饱含着如下期待:“如果好莱坞要买我的书拍电影,以此来奸淫我,我就不仅心甘情愿,而且热切希望诱奸者快快提出他们那头一个怯生生的要求。实际上,我在这件事上的态度颇像比利时的处女在德国人攻下城池的当晚的心情:‘何时开始施暴?’”㊺是视觉文化时代的文学现状。
(四)思想肤浅化。小说需要思想,思想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小说的境界,这其实已是常识。昆德拉的小说之所以思想深刻,就是因为他响应着“思想的召唤”。而这种召唤“不是为了把小说改造成哲学,而是为了在叙事的基础上动用所有理性的非理性的,叙述的和沉思的,可以揭示人的存在的手段,使小说成为精神的最高综合”。但昆德拉也同时意识到,小说在今天已日益落入传播媒介之手,它既简化了小说的思想,也简化了小说的精神(复杂性)。㊻
实际上,电影电视便是简化小说思想和精神的一种大众媒介,原因无他,关键在于其媒介特性。布鲁斯东指出:“由于电影只能以空间安排为工作对象,所以无法表现思想;因为思想一有了外形,就不再是思想了。电影可以安排外部符号让我们来看,或者让我们听到对话,以引导我们去领会思想。但是电影不能直接把思想显示给我们。它可以显示角色在思想,在感觉,在说话,却不能让我们看到他们的思想和感情。电影不是让人思索的,它是让人看的。”㊼这种媒介特性延伸到所谓的“影视小说”之中,也必然会让小说变得画面感增强,思想性减弱,从而远离小说的精神。茂莱认为“电影小说”这个文学新品种具有如下特点:“肤浅的性格刻划,截头去尾的场面结构,跳切式的场面变换,旨在补充银幕画面的对白,无需花上千百字便能在一个画面里阐明其主题。”㊽我们今天的“影视小说”无疑也走进了茂莱的描述之中。
让我们依然以《手机》为例略加分析。小说《手机》面世不久,李建军曾有过如下感受和分析:“‘没有收获’也是我读完《手机》以后的感受。这部小说是一个被同名电影挤压得扭曲变形的文本。它虽然具有小说的形式,但是本质上依然是烙有‘冯氏’徽章的电影剧本。它不仅缺乏小说的文学品质,而且还缺少一个深刻的主题。如果我们一定要给这部缺乏深度的小说概括出一个可能的主题的话,那么,这个主题似乎可能是:手机给人们提供了交流和沟通的方便,但也因其便于随时询唤,严重地挤压了私人空间,从而导致人们以伪陈述(即说谎)来逃避突如其来的询唤,并最终造成被询唤者的情感紧张和道德扭曲。如果这个主题能得到有力量的表达,那么,这部小说将有助于人们反思一种高度现代化通讯工具的弊端。然而,刘震云对这个主题不感兴趣。他的眼光很快就滑向另外的地方。他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了男女之间那点小事情上去了。他把自己的趣味、想象力和兴奋点,统一、化约到了冯小刚的道德视境和价值水准上。”㊾
李建军勉为其难地概括出来的这个主题显然是《手机》所无法胜任的,因为作家那种可能的命意与导演的意图相互纠缠,从而导致了两种立意的潜在冲突和小说主题的暧昧不明。按照电影逻辑,作品所要呈现的是“手机变手雷”的故事,这既是商业卖点,也是电影所能直白表达出来的一个主题。而按照作者意图,刘震云的兴奋点依然是“说话”,这其实是《一腔废话》之主题的延续。然而,当他换一种角度来面对这一问题时,一方面他还没想清楚,另一方面电视逻辑与视觉思维也不允许他想清楚。直到六年之后他不再与冯小刚合作,独立写出《一句顶一万句》,“说话”的问题才得到了较为妥善的解决。因此,我们可以说正是“电影小说”打乱了《手机》的思维方向,模糊了它的主题呈现,也限制了它的思想开掘。
在“影视小说”的思想呈现上,连刘震云这种据说非常优秀的作家尚且如此,其他作家就更是可想而知了。
以上我分别从四个方面概括分析了小说影像化之后所发生的变化,这虽然不是小说变化的全部,却也足以让我们看到作家的写作观念、小说的美学精神在视觉文化时代已经位移,视觉思维与影视逻辑也已经进驻小说,改变着小说的生产方式、叙事方式和语言表达方式。而小说内部构成的变化也必然会延伸到其外部交往中,从而带来接受方式,消费模式等方面的一系列变化。因此,这种变化不仅仅是一种美学现象,而更应该把它看作一种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现象。既如此,文学理论该如何应对这种变化,又该如何做出相应的调整呢?
三、视觉文化时代文学理论何为
从最本来的意义上考虑,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理论都是对当时文学实践活动的概括和总结。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之所以是诗话词话,是因为诗词歌赋是文学的主要形式。后来兴起了小说评点理论,又是因为叙事文学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进而逐渐兴旺发达。20世纪后半段,文学理论先后受政治观念(1950-70年代)和审美观念(1980年代)影响,也可看作文学理论与当时文学现实的一种互动与交往。那么,文学理论发展到今天,它又如何与文学交往,如何回应了现实问题呢?
答案很可能比较悲观。在我们的文学研究中,许多学者使用的依然是“纯文学”的理论评判尺度,而并没有意识到今天的文学已变得严重“不纯”。在我们的文学理论教科书中,“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核心命题依然盛行,而实际的情况很可能是文学已无美可审。在这里,我丝毫没有责怪“纯文学”评判尺度和“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核心命题的意思,而只是想指出如下事实:当我们的文学现状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时,我们的文学理论却反应迟钝,没有做出应有的及时回应,理论因此显得滞后,变成了一种“不及物”的理论。如此一来,理论也就失去了阐释文学现实的能力。
这时候,重温拉尔夫·科恩(Ralph Cohen)在《文学理论的未来》(1989)序言中的如下文字便显得非常重要:“人们正处于文学理论实践的急剧变化的过程中,人们需要了解为什么形式主义、文学史、文学语言、读者、作者以及文学标准公认的观点开始受到了质疑、得到了修正或被取而代之。因为,人们需要检验理论写作为什么得到修正以及如何在经历着修正。因为,人们要认识到原有理论中哪些部分仍在持续、哪些业已废弃,就需要检验文学转变的过程本身。”㊿实际上,我们现在首先需要检点的也正是今天的文学已发展到何种地步,文学已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并且还将发生怎样的变化,然后才能对文学理论本身做出清理——清理哪些文学观念已经落伍,哪些思维方式已经陈旧,哪些批评方法已经滞后,哪些理论话语已经错位。只有做出这种清理并调整其应对策略之后,文学理论才可能被重新激活,进而焕发出某种生机和活力。
那么,如何才能激活文学理论呢?鉴于前文所列举的已经发生变化的文学事实,我在这里谨慎地提出一种应对方案:文学理论的视觉文化转向。而由于视觉文化其实就是后现代文化、消费文化与大众文化,所以文学理论的视觉文化转向实际上也是文学理论的后现代文化转向、消费文化转向和大众文化转向。
这里需要略做解释。自从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r)发表了《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的文章之后,“文学终结论”便成为国内文学理论界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米勒认为,文学的消亡起因于印刷时代正在走向终结。印刷文学曾经对民族国家公民的理想、意识形态、行为方式、判断方式进行过塑造,但如今文学的这些功能却由新媒体取而代之。于是,“技术变革以及随之而来的新媒体的发展,正使现代意义上的文学逐渐死亡。我们都知道这些新媒体是什么:广播、电影、电视、录像以及互联网,很快还要有普遍的无线录像。”他甚至举证说:“如今最受尊敬、最有影响的中国作家,显然是其小说或故事被改编成各种电视剧的作家。”“人们看书是因为他们先看了电视改编”。[51]与此同时,享有“先锋文学之父”称号的马原也宣布“小说已进入了漫长的死亡期”,[52]因为小说家在今天这个时代只有三条路可走,第一条是走向影视。第二条是走向媚俗,写畅销书。第三条路是走进博物馆。[53]
无论是米勒还是马原,他们都认为文学或小说将是终结之物,而既然文学终结新媒体活跃,文学理论的视觉文化转向莫非是转向电影电视等等新媒体那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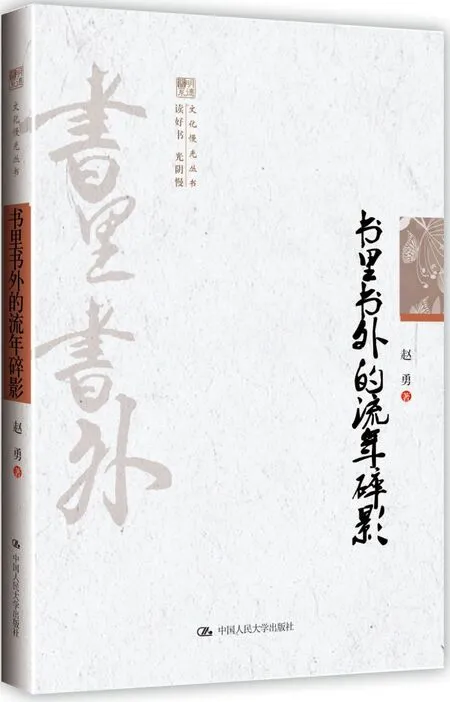
其实这并非我要表达的意思。关于“视觉文化转向”(或曰“文化转向”与“图像转向”),国内早有学者提及并做过相关思考,但是他们的思路似乎主要是去关注那些承载视觉文化的媒介形式和媒介内容。在这个意义上,研究视觉文化其实就是做“文化研究”,而与文学理论几无关系。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才导致了“文学理论边界问题”的相关讨论。我所谓的文学理论的视觉文化转向与上述思路并不相同。其基本意思可以表述为:文学理论更应该去关注文学与新媒体之间的中间地带,这个地带或许可以称之为文学与新媒体的“结合部”。而之所以如此考虑,又是基于如下理由。如果我们承认“文学终结论”有一些道理,那么这种“终结”并非“猝死”,而是会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谁也无法预测这个过程会延续多长时间)。在这个将死不死、似死非死或者死而不僵、回光返照的过程中,文学将会寄身于种种新媒体,从而与新媒体形成诸多复杂暧昧的关系,由此也会催生出许多文学的新品种。我在前面主要提及的是“电影小说”或“影视小说”,但除此之外还有所谓的电视散文,摄影文学,网络文学,手机短信文学等等。与传统文学相比,这些文学新品种或许只能称之为“亚文学”,其文学性和审美价值自然乏善可陈,但正如“城乡结合部”的混乱、无序、驳杂、丰富会蕴藏着许多值得书写的故事一样(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便是对“城乡结合部”的聚焦),文学与新媒体的结合部也蕴含着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文学理论聚焦于这一场域,或许也可以像路遥那样大有作为。
既然如此,文学理论就必须做出调整。而在文学理论的视觉文化转向中,笔者以为文学理论的研究视角可进一步调整到印刷文化与视觉文化之间,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学之间,美学分析与意识形态批判之间。
(一)在印刷文化与视觉文化之间。如今常常被人忽略的一个问题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其实是印刷文化的产物,而由此形成的文学研究也大都依托于印刷文化语境。即便像“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之类的命题,也是“前印刷文化”语境中的思考之物。它能够解释古典文学中的诗歌意象,却无法解释当今视觉文化时代的文学现象。
视觉文化时代,文学的存在方式一方面依然是印刷媒介,但另一方面,电子媒介与数字媒介也成为文学的寄身之所。媒介的载体发生了变化,文学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文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分析框架、理论资源等等也必须随之改变。比如,在比较纯粹的印刷文化时代,文学往往会以严肃的面孔出现(严肃文学的说法或许由来于此),深度模式还是文学追求的目标。但是在视觉文化时代,是否“好看”并吸引眼球却成了文学的致胜法宝。网络文学往往以戏仿、戏说、反讽、搞笑等等作为其修辞策略,想要达到的就是“好看”的效果。这其实是新媒介带来的一种视觉思维。而这种思维也早已波及到作家的写作观念与文学期刊的办刊理念那里,让他(它)们做出了迅速的调整。例如,1999年,刘震云曾经说过:“至于那种强调‘故事性’的看法更是十分落后。如果要读故事的话,看看电视、电影足够了。现代传媒的发达对文学来说是一件好事,它使文学变得更为纯粹。那种讲故事的东西只是白天喧闹的交往,而文学则更应成为夜晚在心灵深处与好朋友的交流。”说这番话时,刘震云是在为他的《故乡面和花朵》辩护。因为此小说可读性差,记者在阅读时甚至一度打起了瞌睡。[54]但是几年之后当刘震云推出《手机》《我叫刘跃进》《一句顶一万句》时,他已在追求小说的“好看”,而故事性、可读性、无巧不成书也成为这几部小说的共同特点。又如,《北京文学》在1998年推出了“好看小说”的概念并设计相关栏目。2003年,《北京文学》又创办选刊版《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其办刊宗旨则是“好看、权威、典藏”,“好看”被放到了首要位置。[55]既然无论是网络文学还是传统文学,“好看”甚至已内化为某种艺术法则,文学理论便需要面对这个问题。
而类似这样的问题还有许多。像图文关系问题,语词钝化问题,由于轻巧而导致的文学失重问题,由于集体生产而形成的孤独的个人写作不复存在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仅仅借助于印刷文化背景下的文学理论并不能获得有效的解决,而动用视觉文化的研究视角、理论与方法或许才能看到问题的真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学理论才需要在印刷文化与视觉文化的交汇处用力使劲。
(二)在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学之间。也可以把这种研究视角表述为在高雅文学与通俗文化之间,在审美文化与消费文化之间,在先锋与媚俗之间等等。之所以要做出这种调整,是因为以往的文学理论大都是在精英文学、先锋文学、雅文学、美文学、纯文学基础之上的概括和总结。这种文学理论关注的是作品的思想价值与艺术价值,分析的是文本的叙事模式、修辞方式和语言特色。鲁迅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56]托尔斯泰说:“真正的艺术不需要装饰,好比一位被丈夫钟爱的妻子不需要打扮一样。伪造的艺术好比是一个妓女,她必须经常浓妆艳抹。”[57]
昆德拉说:“小说的精神是复杂性。”[58]汪曾祺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59]阿多诺(Theodor W.Adorno)说:“艺术只有具备抵抗社会的力量时才会得以生存。除非艺术将自己物化,它才会变成一种商品。”[60]韦勒克(René Wellek)说:文学的有用性体现在文学作品可以给人带来一种“高级的快感”,“可以把那种给人快感的严肃性称为审美严肃性”。[61]
这些论说虽角度不同,侧重点不一,但因此形成的文学理论其实都是对精英文学或高雅文学的要求、认识、阐释与呵护。
然而,在视觉文化时代,精英与大众、高雅与通俗、审美与消费、先锋与媚俗之间的分野已基本抹平,由此带来的是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学的混沌不分。于是,文学当然还可以是灯火,但更可能是引导国民娱乐精神的灯火;文学当然也可以不需要装饰,但这样做的后果很可能是无疾而终;文学已与社会握手言和,但它们却也生存得如鱼得水,因为它们已然物化而变成了商品;文学还在给人提供快感,但这种快感已远离审美,而是变成了一种“养眼”式的消费快感。与此同时,小说已在追求简单,它把“写语言”简化成了“写对话”。面对这样一种文学,我们不得不借助通俗文学、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的理论面对之,分析之。如果动用的还是精英文学基础上生长出来的文学理论,很可能会形成某种错位。
兹举一例,略做分析。余华的《兄弟》面世后,有评论家便指出其成功的秘诀在于“好看”。邵燕君认为,“好看”的原因“不仅在于《兄弟》写了很多性,很多暴力,写得很煽情很刺激,而更在于《兄弟》扣准了大众心中隐藏的密码,顺应了大众内心的情感趋向和阅读习惯”。而由于《兄弟》的语言基本上是“段子”式的,如此处理,这部作品就变得好读不累。[62]
梁鸿也指出:“阅读《兄弟》是轻松的。伴随着情节的发展,你的精神会越来越放松,越来越没有担待,到最后,你完全松懈而且畅快了,因为余华与你灵魂的世俗要求完全吻合,与这个时代的大众文化内核完全一致,换言之,时代大众精神在余华这里没有遭遇到丝毫抵抗,反而被赋予逻辑严密的合情性与合理性。”[63]而在我看来,《兄弟》的“好看”不仅意味着余华已参透了视觉文化时代的高级机密(《兄弟》一开篇的写法,正是视觉思维的产物:作者通过逼真的场景展示,制造出一种视觉奇观,而最终则把丰富的文学叙事变成了一种平面的欲望化叙事),而且意味着曾经先锋的余华与转向媚俗的余华之间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利害冲突,而更应该是一种流畅的换位与熟练的对接。因为卡林内斯库(Matei Calinescu)早已说过,先锋派(Avant-Garde)与媚俗艺术(Kitsch)并非彼此对立,水火不容,而是眉来眼去,秋波频送。[64]而这样一来,《兄弟》也就打通了精英文学与大众文化的疆界。
但是,对于这样一部充满着视觉文化时代诸多文学症候的作品,一些学者却用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做出了非常隆重的解读,并认为这是一部有望进入学院,进入文学史的好作品。[65]在我看来,这种分析使用的便是精英文学理论的阐释框架,而并没有意识到《兄弟》已是审美文化与消费文化的杂交之物。于是,这种文学理论的阐释力度越大,其错位的幅度也就会变得越大,从而引起价值评判的混乱。
(三)在美学分析与意识形态批判之间。既然以往的文学理论建立在对精英文学研究的基础之上,那么面对文学作品,文学理论和批评所做的主要工作就是美学分析:依据自己阅读鉴赏过程中获得的审美经验,再依据相关的文学理论知识和文学批评标准,然后对作品进行解读、阐释、分析、评判,进而做出审美价值的定位和审美意义的确认。尤斯(G.E.Yoos)指出:“文艺批评、合理的艺术判断产生于对一特定的艺术品的欣赏之后。批评所评价的是对欣赏的经验的回忆。”[66]汤普金斯(Jane P.Tompkins)在梳理了多种文学批评流派后认为:“批评家的任务首先是阐释,然后才是评判。”“当代批评家面对文本的姿态就是注释家的姿态,正如柏拉图假设的那样,文本不再是可以立即澄清自己的意图,因此,批评家的任务多少就总是与阐释联系在一起。这种对文本的姿态为一切当代文艺批评流派所共有。”[67]以上两种说法的关键词一是欣赏,二是阐释,它们确实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以往文学理论与批评的通常做法。
但这种做法首先来自于如下假定:许多文学作品像托尔斯泰的《复活》或曹雪芹的《红楼梦》一样,其生成非外力所为,而是作者生命体验的结果;作品面世后又在较长的时间段里得到了读者的认可与批评家的检阅,它们的思想品位与艺术价值已达到了相当的水准。于是面对这样的作品,后来者除了欣赏便只剩下阐释的工作了。但问题是,当下的许多作家既不是托尔斯泰也不是曹雪芹,他们受“意象形态”召唤,被视觉文化引领,他们的作品也就有了太多的非文学因素和非审美因素,他们已失去了写出《复活》与《红楼梦》的现实土壤。当越来越多的文学作品渗透着视觉文化逻辑,散发着商业文化气息时,对它们进行美学分析将显得奢侈或多余。这时候,批评家唯一可以做的工作很可能就是意识形态批判。甚至我们可以借用马克思的经典说法做出如下表达:这种文学“虽然低于历史水平,低于任何批判,但依然是批判的对象。”[68]
追溯一下,意识形态批判其实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传统之一。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当中的许多人都把这种批判理论与方法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运用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如阿多诺与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对大众文化的解读与批判,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对“症候阅读法”的发明与使用等等。而根据杰姆逊的解释,意识形态批判之所以大有可为,正是在于现象与本质之间存在着距离,而造成这种距离的正好是意识形态本身。[69]
由此来思考中国的当下文学,我们便会发现文学除了依然承受着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还接受着商业意识形态、消费意识形态乃至视觉意识形态、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等等的支配。文学本来是审美意识形态的产物,但由于今天的文学已被其他越来越多的意识形态进驻着、占领着、相互纠缠着、进退失据着,审美意识形态也就被裹胁、被绑架乃至被出走或被自杀,而几无藏身之处或活动空间。如此一来,文学的价值观、文学作品的呈现方式、文学生产的流程、文学的消费方式等等也就比以往更显得迷乱和诡异,由此造成了现象与本质之间更远的距离。在这种情况下,文学正需要我们加大意识形态批判的力度。
如果说美学分析是对文学的阐释,意识形态批判就是对文学的揭示;如果说美学分析是对文学的附魅(enchantment),意识形态批判就是对文学的祛魅(disenchantment)。从阐释到揭示,从附魅到祛魅,既可看作文学理论面对当下的文学研究姿态调整,也可看作文学理论的批评范式转换。而只有做出如此调整和转换,我们的文学理论或许才能有所作为。
注释:
① [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56页。
②参见[美]W.J.T.米歇尔:《图像理论》,陈永国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
③ [美]尼古拉斯·米尔佐夫:《视觉文化导论》,倪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9页。
④ [斯]阿莱斯·艾尔雅维茨:《图像时代》,胡菊兰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5,34页。
⑤ [法]纳塔丽·萨洛特:《怀疑的时代》,林青译,见《法国作家论文学》,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89页。
⑥参见[美]爱德华·茂莱:《电影化的想象——作家与电影》第16章,邵牧君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89年版。
⑦参见[美]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224页。
⑧陈学明等编:《痛苦中的安乐——马尔库塞、弗洛姆论消费主义》,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8页。
⑨Jonathan E.Schroeder,Visual Consumpiton,London:routledge,2002.转引自周宪:《视觉文化的转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8页。
⑩参见[意]卡尔维诺:《马科瓦尔多逛超级市场》,刘儒庭译,见《卡尔维诺文集》,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247-252页。
⑪ 参见赵勇:《透视大众文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2-7页。
⑫ Leo Lowenthal,Literature,Popular Culture,and Society,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1961,pp.55,81.
⑬[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4页。
⑭[美]尼尔·波兹曼:《童年的消逝》,吴燕莛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3-114页。
⑮[美]约书亚·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肖志军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⑯[美]乔治·布鲁斯东:《从小说到电影》,高骏千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82年版,第51页。
⑰[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0页。
⑱参见赵勇:《大众媒介与文化变迁——中国当代媒介文化的散点透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44,50页。
⑲[美]爱德华·茂莱:《电影化的想象——作家与电影》,邵牧君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89年版,第129页。
⑳ 莫言:《小说创作与影视表现》,《文史哲》2004年第2期。
㉑ 刘恒、王斌:《对话:电影、文学及其它》,《电影艺术》1993年第1期。
㉒ 黄晓阳:《中国印象:张艺谋传》,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113页。
㉓参见《张艺谋是中国最好的导演,给钱痛快还主动加价》。
㉔参见黄晓阳:《中国印象:张艺谋传》,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157-161页。
㉕梁晓声:《中国当代作家的经济状况》,《中华读书报》1998年3月25日。
㉖ 赵娟:《广西作家“触电”名利双收》,《人民日报》2003年2月14日。
㉗《作家“触电”现象成作协七届九次会议热点话题》
㉘王彬彬:《一份备忘录——为未来的文学史家而作》,《文艺争鸣》1994年第2期
㉙《冯小刚刘震云新浪访谈》,http://ent.sina.com.cn/m/c/2003-12-09/1338249389.html。
㉚ 张英:《刘震云:“废话”说完,“手机”响起》,《南方周末》2004年2月5日。
㉛ 参见《刘震云新作〈手机〉研讨会实录》,http://book.sina.com.cn/longbook/1074066519_shouji/1.shtml。
㉜ 参见赵勇:《从小说到电影:〈手机〉的硬伤与软肋》,《理论与创作》,2006年第1期。
㉝《陀思妥耶夫斯基论艺术》,冯增义、徐振亚译,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第343页。
㉞[美]乔治·布鲁斯东:《从小说到电影》,高骏千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82年版,第6页。
㉟[美]爱德华·茂莱:《电影化的想象——作家与电影》,邵牧君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89年版,第283页。
㊱[美]理查德·沃尔特:《电影电视写作——艺术、技巧和商业》,汤恒译,河海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80页。
㊲王朔等:《我是王朔》,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65页。
㊳黄忠顺:《近年影视剧对文学创作影响调查》,见王先霈主编:《新世纪以来文学创作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
㊴ 刘恒、王斌:《对话:电影、文学及其它》,《电影艺术》1993年第1期。
㊵ 赵树理:《谈〈花好月圆〉》,见《赵树理文集》第4卷,北岳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345页。
㊶ 见戴光中:《赵树理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166页。
㊷参见赵勇:《可说性本文的成败得失——对赵树理小说叙事模式、传播方式和接受图式的再思考》,《通俗文学评论》1996年第4期。
㊸ 莫言:《我是被饿怕了的人》,http://www.gmmy.cn/html/moyanfangtan/2007/1214/184.html。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此文有两个版本,正式版(8000多字)发表于《南方周末》2006年4月20日,另一版本(20000余字)曾在山东高密的一家网站发表,如今该网页已被删除。笔者当时下载了网站发表的版本,才得以见到莫言的这个说法(正式版中未收入)。
㊹ 莫言:《小说创作与影视表现》,《文史哲》2004年第2期。
㊺[美]爱德华·茂莱:《电影化的想象——作家与电影》,邵牧君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89年版,第278,226页。
㊻[捷]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孟湄译,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5,17页。
㊼[美]乔治·布鲁斯东:《从小说到电影》,高骏千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82年版,第51页。
㊽[美]爱德华·茂莱:《电影化的想象——作家与电影》,邵牧君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89年版,第306页。
㊾李建军:《尴尬的跟班与小说的末路——刘震云及其〈手机〉批判》,《小说评论》2004年第2期。
㊿[美]拉尔夫·科恩主编:《文学理论的未来·序言》,程锡麟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51][美]希利斯·米勒:《文学死了吗》,秦立彦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17页。
[52]参见陈熙涵关于“读图时代的文学出路”研讨会的报道:《今天我们还读小说吗?》,《文汇报》2006年6月28日。
[53] 参见马原:《小说和我们的时代》,《长城》2002年第4期。
[54] 沈浩波:《刘震云访谈》,《东方艺术》1999年第2期。
[55]参见《畅销未必好看小说出版警惕泡沫化》,http://book.sina.com.cn/c/2004-11-03/3/124180.shtml。
[56] 鲁迅:《论睁了眼看》,见《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40页。
[57]《列夫·托尔斯泰文集》第14卷,陈燊、丰陈宝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06页。
[58][捷]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24页。
[59] 汪曾祺:《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见《汪曾祺文集》第4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7页。
[60]Theodor W.Adorno,Aesthetic Theory,trans.,Robert Hullot-Kentor,London:The Athlone Press,1997,p.226.
[61][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1页。
[62]邵燕君:《“先锋余华”的顺势之作——由〈兄弟〉反思“纯文学”的“先天不足”》,《当代文坛》2007年第1期。
[63]梁鸿:《恢复对“中国”的爱——论当代文学的批判主义历史观》,《当代文坛》2007年第6期。
[64] 参见[美]马泰·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斌、李瑞华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74。
[65] 参见陈思和:《我对〈兄弟〉的解读》,《文艺争鸣》2007年第2期。
[66][美]G.E.尤斯:《自立标准的艺术品》,见[美]M.李普曼编:《当代美学》,邓鹏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
[67][美]简·汤普金斯:《读者在历史上:文学反应的演变》,刘峰译,见《读者反应批评》,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版,第261页。
[68][德]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页。
[69]参见程巍:《中产阶级的孩子们:60年代与文化领导权》,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44页。
(本文图片由赵勇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