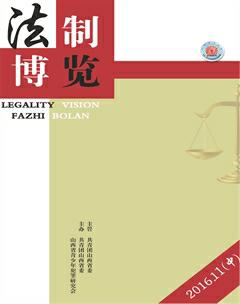浅论聚众斗殴罪之“聚众”的构成形式
摘要:聚众斗殴罪是司法实践中常见的犯罪之一,其来源系分离于1979年刑法的流氓罪,虽属多发犯罪,但客观方面的表现、入罪标准却一直因其现实状态相对复杂而存有争议。其中的“聚众”+“斗殴”之“聚众”是否为绝对必要条件,更是需要据实予以评析的关键问题。
关键词:聚众;斗殴;聚众斗殴罪;客观表现
中图分类号:D924.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379-(2016)32-0153-02
作者简介:马超(1985-),男,天津市宝坻区人民检察院,助理检察员。
一、“聚众”在现实中的表现及争议
介绍一个实际案例。犯罪嫌疑人黄某超与被害人田某曾共同经营一演艺团,后二人意见不合分道扬镳,各自经营演出,并因争抢生意、互挖演员素有积怨。2016年3月的一天,黄某超与田某经营的演艺团同时被邀请至某户农家演出。表演结束后,双方人员发生口角,黄某超一方人员郭某新声称要打电话让老板过来,并让田某一方人员在原地等候。田某一方人员明知黄某超等人到达现场要发生斗殴,依然不听旁人劝阻,为逞强争胜而在现场等候斗殴。后黄某超纠集温某等二十余人到达现场与田某、韩某、黎某元等五人在村口相互殴打,期间温某持铁板致田某、韩某轻微伤,韩某持刀将温某手臂划伤,田某持械欲殴打他人,被周围群众拦下。
本案中黄某超一方人员构成聚众斗殴罪无疑;田某、韩某等五人于案发前曾共谋斗殴,具有了犯罪故意,但在案发当场,却没有聚集的行为表现,只是共同在现场等待斗殴,后续实行斗殴,其行为是否涉嫌聚众斗殴罪则存有极大分歧。
争论的核心是对“聚众斗殴罪”的理解,即此罪构成要求的犯罪行为,是复合行为还是单一行为,换言之,成立聚众斗殴罪犯罪构成要求的行为是“聚众+斗殴”,还是“以聚众形式发生的斗殴”。
观点之一认为“聚众”+“斗殴”为必要条件,即田某等五人虽事先有斗殴的意思联络,但在斗殴的当场没有明显的聚集行为(聚众),仅有斗殴的行为,因此不构成聚众斗殴罪;另一种观点认为应考量以聚众形式发生的斗殴,即田某等五人事前有斗殴犯罪的意思联络,且犯罪共同故意的形成与斗殴的发生在时间因素上衔接的相当紧密,斗殴当场虽无明显聚集的行为,但田某等五人明知嫌疑人黄某超等人到来后要发生斗殴,其五人仍为逞强争胜而等候在斗殴现场,最终在客观上以聚众的形式同对方发生了斗殴,该五人的行为亦涉嫌聚众斗殴罪。
二、“聚众+斗殴”的入罪必要条件之考量
刑法第292条对聚众斗殴基本犯罪构成采取了简单罪状描述:聚众斗殴的,对首要分子和其他积极参加的处以刑罚处罚。此外还有加重情节的规定:聚众斗殴人数多、规模大,社会影响恶劣的;在公共场所或者交通要道聚众斗殴,造成社会秩序严重混乱的;持械聚众斗殴的。另外还规定了转化情形: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的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从文意解释的角度可以明确两点:一是刑法对聚众斗殴犯罪构成核心行为,未明确规定成“聚众+斗殴”的模式,二是伤害结果不是构成聚众斗殴犯罪的客观必备要素。
(一)主观目的之考察
聚众斗殴罪的成立首先要求参与斗殴的一方或者双方具有“逞强争霸的煞气”,斗殴的起因或是出于争抢地盘、或是出于哥们义气,总之是包含有一定的流氓意思,而不是单纯因为日常的民事纠纷而引发[1]。本案中,嫌疑人黄某超与田某因为争抢生意、演出人员而素有积怨,嫌疑人黄某超因己方团员与对方发生争执,纠集人员与对方斗殴是“为了给团员出气”,田某一方人员留在现场等待斗殴是因为“我们要是走了,以后在这行我们就没法混了”,说明双方人员不是单纯为了解决民事纠纷,而均是怀有“逞强争霸的煞气”,进而发生斗殴,双方都具备了构成聚众斗殴罪的前提条件。
(二)侵害的法益
聚众斗殴行为侵害的是社会公共秩序,实行行为应是“斗殴”,只是由于该实行行为以“聚众”的形式发生时,才具有了侵害社会公共秩序的犯罪属性[2]。单纯的“聚众”行为难以认定具有该罪的法益侵害性,即使是为斗殴而“聚众”,在到达现场而未发生斗殴的情形下,也易认定为犯罪预备。如果按照“聚众+斗殴”是本罪实行行为的观点,则本案中嫌疑人黄某超的行为将面临两种截然相反的矛盾评价:一是黄某超虽为斗殴而纠集人员到达现场,但其后来并无斗殴行为,不符合“聚众+斗殴”的实行行为模式,所以黄某超不构成犯罪,该思路与解释田某等人不构成犯罪的思路相同;二是黄某超为斗殴而纠集人员到达现场,已经形成了共同犯意,依照共同犯罪理论,后其表演团成员实施了构成犯罪要求的全部实行行为,黄某超虽未亲自完全实施实行行为,但其亦构成聚众斗殴罪,且是犯罪既遂。至此可以看出,在“聚众+斗殴”的犯罪构成模式下,如对黄某超按犯罪处理,而田某不按犯罪处理,明显适用法律标准不一致,并且在“聚众+斗殴”的模式下,聚众斗殴罪完全排除了共同犯罪理论的适用空间,完全排除了犯罪预备成立的可能,这在客观上给放纵犯罪留有空间。
(三)“以聚众形式发生的斗殴”之解析
将“聚众斗殴”解释为“以聚众形式发生的斗殴”并从共同犯罪的角度,将能够合理的解释黄某超的行为。聚众斗殴的本质是必要共同犯罪,嫌疑人黄某超为斗殴而纠集他人,其一方人员主观上已形成了犯罪的意思联络,完成了“聚”的主观要求,黄某超一方二十余人在现场聚合,具备了“众”的客观要件,但此时仅为犯罪的预备形态,当黄某超一方人员开始对田某一方人员进行殴打之时,犯罪才发展为既遂。在必要共同犯罪中,一人实行即既遂,则共犯全体既遂,对于嫌疑人黄某超来说,其行为当然构成聚众斗殴罪的既遂,且在犯罪中属首要分子,此种解释,合理避免了第一种解释所产生的矛盾结果,同时将聚众斗殴犯罪按照法益侵害的现实危险性程度的不同,区分出不同层次,为准确打击犯罪限定了范围。由此,将聚众斗殴犯罪的实行行为锁定为“斗殴”,认定犯罪的客观必要条件是以“众”的形式实施,且众人在斗殴之前或者当场已形成主观的犯意联络,即“聚”的主观要求,同时要求斗殴的一方或双方具有逞强争霸、显示煞气的主观前提,满足以上条件,即充足了聚众斗殴罪要求的基本犯罪构成。此种解释对认定嫌疑人构成聚众斗殴罪是合理的。
(四)期待可能性角度之评价
田某等五人的先后行为,没有阻却聚众斗殴罪的成立。田某与黄某超两方人员素有矛盾,斗殴当日双方人员也发生了口角摩擦,用张某微的话讲:“这场仗早晚都要打。”当黄某超一方人员郭某新让田某等人留在原地等候黄某超到来时,田某等五人及其他在场团员均明知之后必然发生斗殴,当时田某一方团员中也有人劝其五人离开的情节,但田某明确表示:“离开了栽面,以后没法再这个地方混”,执意留在现场等候与黄某超一方人员斗殴,其五人为逞强争胜而至正常社会公共秩序于不顾,在可以采取报警或者及早离开现场等方式避免聚众斗殴发生的条件下,依然藐视法律权威,由此,五人具有明确的“因逞强争霸而斗殴”故意。
对于文中所举例的案件,在评价田某五人的行为时,应遵循以下逻辑思路:田某等五人因与黄某超一方人员素有积怨,案发前即完成了“斗殴”的主观意思联络,已完成了“聚”的主观要求;在与共同犯意形成时间因素上紧密联系的第二天下午,田某等五人明确意识到黄某超一方人员到达现场会发生斗殴,但为逞强争霸,显示一方煞气,在他人劝说离开且有离开或报警条件的情况下,田某五人依旧为斗殴而留在现场,具备了“众”的客观条件,案发当场,田某等五人与黄某超等人在村口公路处相互“斗殴”,且在斗殴过程中,张某微持刀划伤温某,田某两次持械欲殴打黄某超一方人员但被在场群众拦下。田某等五人的行为已涉嫌聚众斗殴罪。
[参考文献]
[1]郑翼.聚众斗殴罪若干适用问题探讨[J].法制与经济(下旬),2012(05).
[2]何柏松,范雪旺.聚众斗殴罪疑难问题探析[J].人民检察,200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