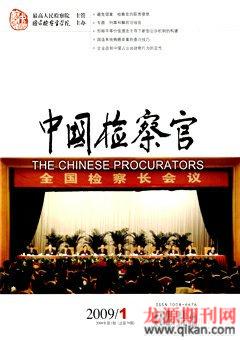关于聚众犯罪客观行为的司法认定
刘德法 孔德琴
众犯罪是我国刑法中独有的概念,它是指刑法分则明文规定的,在首要分子的作用下以聚众的行为方式实施的一种犯罪类型。我国《刑法》第97条在界定“首要分子”时,规定了“聚众犯罪”的概念,并且在刑法分则中规定了19种具体聚众犯罪的罪名。根据聚众犯罪的概念和刑法分则的相关规定,聚众犯罪具有法定性、“聚众”性和“首要分子”必备性等三个不可缺少的法律特征,这些也是聚众犯罪区别于其他犯罪的鉴别性标志。
聚众犯罪在客观行为模式上,表现为由“聚众行为”与“直接危害行为”两个行为组成。其中的“聚众”行为是由“首要分子”实施的,是之后实施聚众犯罪直接危害行为的前提。直接的危害行为是首要分子组织、策划、指挥的行为结果。对于犯罪的结果而言,聚众行为与直接危害行为具有因果性的统一关系。
一、关于“聚众”行为的界定
笔者认为,所谓聚众就是首要分子组织、策划、指挥或者纠集、纠合不特定的众人同时同地参加刑法规定的某种具体危害行为。对我国刑法规定的“聚众”的涵义,学界有不同的理解:一种观点认为所谓聚众,是指聚集多人,多人应为3人以上,而且不应包括纠集者在内。聚众的众人或多人中既有犯罪分子即首要分子或其他积极参加者,也有其他不属于犯罪分子的参加者。[1]也有观点认为,聚众是指犯罪分子为满足其某种无理要求,纠集、煽动、诱骗3人以上(包括犯罪分子本人在内)参与扰乱社会秩序的犯罪活动。[2]还有观点认为聚众犯罪的众,泛指3个以上的参加者,并非仅指3个以上的犯罪人员。[3]另有观点认为,所谓聚众是指聚众纠集多人实施的犯罪行为,一般应当是纠集3人以上。纠集3人以上是指包括聚首和积极参加者3人以上。1人或2人闹事引得众人围观起哄的,不构成本罪。[4]
我国刑法学者几乎无一例外地把聚众犯罪中的“众”理解为3人以上,至于3人以上是否包括3人,则有不同的见解。我国现行刑法对“众”究竟为多少人也没明确规定,在相关司法解释中,常把多人解释为3人以上(包括3人)。如,“两高”《关于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答》第9条规定:《决定》和本《解答》中的“多人”、“多次”的“多”,是指“三”以上的数(含本数);“两高”《关于办理赌博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聚众赌博”第一项规定:组织3人以上赌博——把“众”认定为3人以上(含3人)。但作为例外,“两高”《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5条规定:邪教组织被取缔后,仍然聚众滋事、公开进行邪教活动,或者聚众冲击国家机关、新闻机构等单位,人数达到20人以上的——该解释把“众”认定为20人以上。我国刑法重视“聚众”的量化标准,具有可操作性,但没有考虑到聚众行为造成社会危害性的实际可能性。
我国台湾地区的刑法学者林山田先生认为:“至于集合多少人才算为聚众之问题,则须从个案加以判断,其决定之关键点乃在于聚众之人数是否足以妨害公务之执行。如执行职务之公务员只有一人,而行为人只聚集三人,当然足以该当聚众,但如执行公务之公务员有数百人之众,而行为人只聚集三人,则非聚众。”[5]这些理论观点是从危害行为的“违法性”判断“聚众”行为性质的,即使纠集的人数在形式上具備了构成条件的“符合性”,由于其在实质上可能不足以侵害特定的法益,也不当然地构成聚众犯罪。
关于聚众的“众”是否包括纠集者本人。有观点认为,纠集者本人应包括在聚众的“众”之内。首先,纠集者纠集众人之后,纠集者本人也成为了众人之一,只不过是较为特殊的众人之一;其次,纠集者一般不仅实施了纠集众人的行为,而且往往也是直接危害行为的实施者,也就是说,纠集者集“聚众”行为与实施具体犯罪行为于一身,纠集者直接实施犯罪行为实际上是利用了聚集的众人的人多势众;再次,把纠集者排除在众人之外,就要求聚众犯罪至少由四人以上才能构成,不符合我国通说众人为3人以上的概念;最后,聚众犯罪的人共同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这种聚众性恰是其社会危害性的表现之一,应包含参与犯罪的所有人员。[6]但笔者认为,根据汉语的文词构成原理,聚众中的“众”是“聚”的宾语,而纠集者是“聚众”的主语,聚众是指为首的人聚集其他的众人,不应包括为首者本人,否则就要犯逻辑循环的错误。至于说要求聚众犯罪至少要四人以上才可构成,对此并不产生影响。实际上,我国刑法上“众”的涵义应超越三人,包括首要分子在内的聚众犯罪人至少是四人,否则难以体现该类罪的特点,难以体现“众”在该罪的意义,体现不出该类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也与司法实践不相吻合(司法实践中认定的“众”一般要超出三人以上)。我国《唐律.名例》规定:“称众者,三人以上”。被聚之“众”应不少于三人,当首要分子也参与具体犯罪行为的实行过程时,聚众犯罪的人数应在四人(包括四人)以上。但如果聚集起来的众人均是首要分子,即共同故意聚集起来或共同预谋聚集起来,共同从事扰乱社会秩序的犯罪行为,则纠集者本人可包含在“众”内,但是他是属于他人聚集的“众”,而不是本人聚集之“众”。
二、聚众犯罪的直接危害行为
聚众犯罪在客观上,除了由首要分子实施的“聚众”行为外,刑法均在“聚众”行为之后明文规定了相应的直接危害行为。如:持械劫狱、冲击、斗殴、扰乱、哄抢、淫乱、阻碍解救、赌博、哄闹、闹事等。具体分析这些具体行为,有以下一些共性特征:
(一)分则条文的法定性
哪些行为应属于聚众犯罪的直接危害行为,我国刑法分则采取了明示的方式予以规定,其构造模式为“聚众”+“直接危害行为”。其中的“直接危害行为”则紧接“聚众”之后,形成双动词词组;并且,直接危害行为的概念是明确的,刑法限定了它的范围。尽管有些法律用语在含义上不甚具体,如,“闹事”、“哄闹”、“扰乱”等,但可以看出其是群体性行为,而非自然人的个体举动。前提行为的“聚众”性限定了聚众犯罪具体行为的群体性,如,《刑法》第242条第一款也规定了“阻碍解救”被收买的妇女、儿童的行为,因其前面没有“聚众”的限定,它只能认定为《刑法》第277条的妨害公务罪;只有聚众实施这种行为时,才能构成第242条第二款的聚众阻碍解救被收买的妇女、儿童罪。
(二)行为主体的特定性
从《刑法》关于聚众犯罪的规定来看,尽管首要分子有时也参与实施直接的具体行为,但“聚众”行为只能由首要分子实施。在构成共同犯罪的聚众犯罪中,刑法一般把直接危害行为的实施主体规定为:积极参加者,其他参加者,多次参加者。其中的积极参加者,是指除首要分子以外的在聚众犯罪中起重要作用的犯罪人,其在主观上对聚众犯罪意愿强烈、积极响应、主动参加;客观上行为积极,作用突出,危害较大,是直接危害行为的主要实行者。如,在聚众哄抢罪中哄抢财物数额最大的参与者,在聚众斗殴罪中打击力度强、下手最狠的参与人等即为积极参加者。其他参加者,是指在聚众犯罪中起次要或辅助作用,一般只是参与实施了聚众犯罪中较轻的危害行为,有时只是在犯罪中为积极参加者提供运输工具、购买作案器械、参与助威、壮大声势,其行为不是引起危害结果发生的主要原因。《刑法》第301条规定的聚众淫乱罪,本来只处罚实施聚众的首要分子,对被聚集参加淫乱的人一般不以犯罪论,但是,如果参与淫乱的人属于被聚集参与淫乱的“多次参加者”,则也要追究其刑事责任。笔者认为,多次参加者应指在主观上积极主动,客观上参与作案次数不少于3次的行为人。对于偶尔一次参加、被裹挟参加的或者在犯罪过程中作用很小的参加者,一般不以犯罪论。我国刑法对聚众犯罪主体的规定,显然是根据犯罪后的情况进行判断和归责的,它也说明聚众犯罪人在聚合程度上是无组织的,表现为结构上的松散性。这种犯罪中的首要分子虽然是确定的,但被聚集的参与者之间欠缺紧密地联系性,没有聚合体的稳定性,大多是首要分子临时聚集的一群乌合之众,参与人员的规模随着审时度势的心理判断而不断进行增减,案发的导火索性质、共同情绪人的关注程度、犯罪现场的气氛、场面的环境及参与人的成分等因素,都会在聚众犯罪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三)行为方式的公然性
我国刑法规定的犯罪,绝大多数是以秘密、隐蔽的方式实施的,聚众犯罪大多是以公开对抗的方式进行的,甚至是在公共场所、光天化日下明目张胆、有恃无恐,其对社会公众的公共安全心理、社会道德、公共秩序具有较大的破坏性。公然性是指“事实上众人所共见共闻之情形,或众人得共见共闻之情形”。聚众犯罪公然性的表现,就是这种犯罪能够被公众所感知和体会,有较大的社会传染性,对其控制不当,极有可能在较大范围内蔓延扩张,甚至形成突发性、大规模的群体事件,导致社会的骚乱或动荡。聚众犯罪的直接危害行为一般发生在车站、码头、民用机场、商场、学校、影院、公权力机关、集会、农村集市等公共场所,它能够被不特定的公众所共见共闻。发生在赌场、特定淫乱密室、监狱内的聚众犯罪,虽然其人员规模不大,公开性不明显,但由于是在聚众情况下发生的,也仍然能使除首要分子以外的其他多人所共见共闻,很容易形成心理感染、群体仿效,公然聚众藐视社会公德,破坏正常的社会管理秩序。
三、聚众犯罪的因果关系及责任承担
对于聚众犯罪而言,造成该罪危害结果的原因条件包括:“聚众”行为和直接危害行为,二者往往存在前后相继的关系,但都共同促成犯罪结果的发生。
在单独犯罪的聚众犯罪中,只处罚首要分子一个人,他既是聚众者,也可能同时是直接危害行为的实行者。这里的因果关系表现为单一性,即只考察首要分子的行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联系,由其对聚众犯罪的全部结果负责。如,对于《刑法》第289条规定的聚众“毁坏或者抢走公私财物的”行为,可能是由其他参与人实施的,由于这种行为源于“聚众”行为,是聚众行为的结果,聚众行为与最终的危害结果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因果关系。即使首要分子没有实际实施“毁坏或者抢走公私财物的”行为,刑法规定也要对其依照抢劫罪定罪处罚。
在共同犯罪的聚众犯罪中,同时处罚聚众的首要分子和其他积极参加者。这时的聚众犯罪在因果关系上表现为多因一果的联系,首要分子的聚众行为和其他参与者的直接危害行为,都是聚众犯罪的实行行为,对结果的影响具有同等的价值,但是,在判断二者对结果发生的作用时,则应注意其有量的差异,行为人所承担的刑事责任在程度上是有区别的。我国刑法一般把首要分子的聚众行为作为最重要的原因条件,规定首要分子对聚众犯罪的全部损害承担刑事责任,因此,在构成共同犯罪的聚众犯罪中,首要分子是当然的责任主体,且刑法为其规定了重于其他参与者的法定刑。对于积极参与者的行为,如果其原因力与首要分子大致相同,则要与首要分子负同等的刑事责任。在刑法规定的一些聚众犯罪中,往往对积极参加者适用与首要分子相同的法定刑;对于作用轻于积极参加者
的其他参加者,刑法规定了较轻的刑罚。
注释:
[1]赵秉志、刘志伟:《论扰乱公共秩序罪的基本问题》,载《政法论坛》1999年第2期。
[2]陈兴良、曲新久、顾永中:《案例刑法教程》(下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92页。
[3]张正新、金泽刚:《论我国刑法中的聚众犯罪》,载《法商研究》1997年第5期。
[4]赵秉志主编:《扰乱公共秩序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4—255页。
[5]林山田:《刑法特论》(下),(台)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929页。
[6]王作富主编:《刑法分则实务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7年版,第1252页。